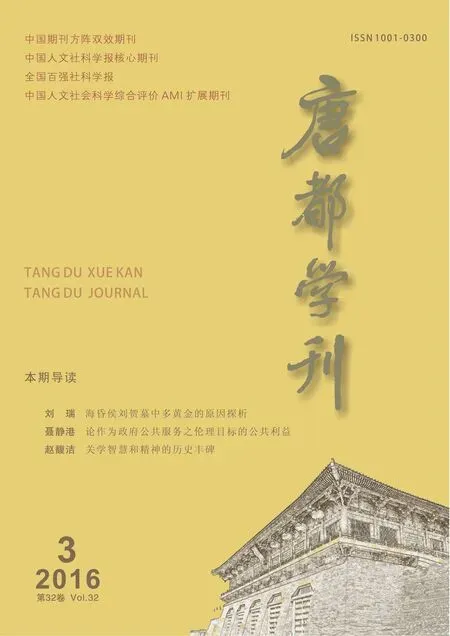“异数”《多湾》
刘 琼
(《人民日报》 文艺部,北京 100733)
【西部文学研究】
“异数”《多湾》
刘 琼
(《人民日报》 文艺部,北京 100733)
长篇小说《多湾》是一部具有“异数”气质的作品,它重新继续了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宏大的历史线索伴随着一份日常而持久的生活。历史中的日常也是历史,日常中的历史也是日常。小说不再对“政治”和“革命”本身兴致勃勃,而注重考察在“政治”和“革命”中的人。它写人的持续性和日常性,人是主题,重大事件是生活客观进程的背景,这是对重大叙事的一种颠覆。《多湾》写家族史,并不设定家族文化的整体性,而是观察现实变迁中的生命个体的文化演变,用这些个体集合成整体,这也是对前辈作家写家族文化善于预设概念的一种打破。
《多湾》;“异数”现实主义传统;日常性;家族史;中庸文化;古典化写作
关于周瑄璞的长篇小说《多湾》,有许多议论,有说它是“女版《白鹿原》”,有说它表达“欲望与情感”,等等。好作品一定具有多义项阐释维度,因为它的丰富性。无论是对于女性作家写作,还是对于70后创作,《多湾》应该都是一部具有“异数”气质的作品,它完全超过了预期。因此,如果我们足够谨慎的话,就不会轻率地把一些标签贴在这部作品的身上,更不会轻易地放过它。
一、重新接续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现实主义创作是“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大户,它以介入和记录历史现场著称。关于现实主义创作,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和议论,对客观现实和历史的关照是基本共识。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节点,现实主义创作明显遭遇寒流。首先,整个创作生态变化,80后、90后陆续进入文坛并在市场和资本的诱导下,现实生活和历史经验不足的年轻一代以书写主体内部世界为旗号迅速掀起文学创作“向内转”潮流。其次,在诸多创作方法中,现实主义创作易学难工,一些仍在现实主义创作大旗下的作家比如50后,大多功成名就,距离生活现场越来越远,他们这个时段的作品往往观念在先,文学焦点不够具体,现场不够鲜活,呈现“伪现实”或“心理现实主义”趋势。现实主义创作缺席,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对于现实的干预性减弱。文学创作提倡多样化,不能唯一招鲜,不能唯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创作严重缺席或不力,显然不是文学的繁荣。激荡复杂的社会现实,渴求文学或作家的笔墨关怀。在这种背景下,以直击现实和主观干预现实为特征的非虚构写作勃兴,成为近些年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小说创作领域,2015年比较典型,一批从先锋派起家的60后以及受其影响的70后成为中坚力量,开始面向现实写作,《装台》和《篡改的命》这两部60后作品引起关注,现实主义写作的魅力和知识分子的情怀一览无遗,在这两位男性作家作品的边上,就是这部70后女性作家的《多湾》——《多湾》的出版提振了70后写作的士气。
《多湾》写70年的中国社会,一小部分是周瑄璞熟悉的生活,一大部分是周瑄璞不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生活要靠想象和虚构,作家想象和虚构的依据是间接经验。对于间接经验,比如《多湾》里写到的土改等历史事件,基本常识容易获取,之前的一些文学作品如《白鹿原》《圣天门口》等对此已有精彩书写。在已知的常识面前,特别是经典名作在前,怎么写出个性化经验或新鲜经验?怎么构筑文学形象?怎么对历史和重大事件进行独特表达?《多湾》怎么能区别于《白鹿原》和《圣天门口》?
或许真是年龄的缘故,陈忠实和刘醒龙这两位40后、50后作家的笔墨重点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至“文革”这一长段历史时期,当然,这是一个跌宕传奇的历史时段,中国人的人性、命运在此间有精彩细致的展现。陈忠实和刘醒龙是主体意识强、世界观稳定的作家,因此在这两位小说大家宏阔有致的文字里,对于国家、民族、人群和个体命运的思考非常自觉,也通过文字和形象表达了个体的判断。《多湾》应该是借鉴了这两部经典作品的编年史和家族史写法,也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家族的历史变迁写历史风云和人物命运。《多湾》里前后70年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历史剧变期:政权形式巨变、社会制度巨变、文化形态巨变。每一种巨变都充满了事件和现象,比如国共关系、土改、文革、高考等等。回想一下,20世纪初以来,能够并乐意正面书写宏大历史的女性大概除了萧红、丁玲外,余者少见,这与女性思维细致片面的惯性有关。像封面一样,《多湾》色彩明艳,色调稳定,像唐三彩,历史在日常里绽放。周瑄璞温婉秀气的外表下一定隐藏着理智坚定的性格,否则在历史叙述中很难从容裕如。
这个从容裕如,一是表现为历史和现实线索的主次、详略的平衡感,这是格局的处理,没有这个大局,长篇小说写着写着就成了汤汤水水一锅粥,拎不出干货,许多作家都在这个方面翻船,比如苏童,那么优秀的一位作家,中篇几乎篇篇好,但长篇的确出色的不多,这就与苏童的性格气质有关,像苏童这样的“中篇王”也不一定非要写什么长篇——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多湾》里的“政治”大事件的数量其实远远超过了《白鹿原》和《圣天门口》,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涉及城乡社会,涉及改革开放,涉及当下生活。写“重大”而不觉其“沉重”,作家举重若轻。说到这里,宕开一笔。这与70后作家的成长轨迹有关。70后的基本轨迹是由文学期刊养成,从中短篇起步,最后进攻长篇。这种稳步成长的轨迹,在写作上也派生出共性,即对于叙事技巧和结构谋篇的锤炼讲究,这一特点,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自觉地用中篇或短篇的节奏和密度进行长篇叙事,比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就被誉为是一部用力如中篇的长篇。与同代人相比,周瑄璞在长篇上更加用力,包括《多湾》在内已经出版了5部成型的长篇。大家头疼的长篇的结构问题,对她应该不是问题。
从容裕如的另一表现是价值表达的日常性和淡定感。《多湾》对于70年历史经验的叙述的独特性在于,对于任何一个重大时期的叙述,其破题之处不是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而是日常生活、日常事件和日常人物,在“日常性”的映衬下,写历史的变迁。日常中的变化是具体的,也是典型的、有血肉的。因此,《多湾》写出了每个历史时段的质感和特殊性。比如,罗掌柜的两个儿子参加共产党后一死一生,写出了大的历史关头个体命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写出了命运感。这两个人物都不是书写重点,都只是线索和背景,重点是写罗掌柜这个乡村世界的有点势力的人物。这个复杂的人物,与小说中的大青衣季瓷同时出场、同时在局,牵出了章家的许多来龙去脉。像罗掌柜这样,《多湾》里每个人物基本上都有头有尾,这些人物在历史性的典型事件中都有扎实的活动,比如办户口、大学分配、转编制、买房。写这些事件,目的还是为了写人,写人的局限性、特殊性和恒定性,而个体的完整形成了整体的丰富。
所以,《多湾》其实是一部“郄父”之作。
第一,它与50后作品对于“政治”和“革命”本身的兴致勃勃不同,它的兴趣显然是“政治”和“革命”中的人。小说从一个类似于白嘉轩的老太太季瓷第二次出嫁开笔,到季瓷的孙女儿章西芳收笔,宏大的历史线索伴随着一份日常而持久的生活。这才是周瑄璞的写作重点:历史中的日常也是历史,日常中的历史也是日常。它关注人的持续性和日常性,人是主题,重大事件是生活客观进程的背景,这应该是对重大历史叙事的一种颠覆。
第二,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书写一个章姓人家的历史变迁,以章家和章家的婆姨季瓷、章家的女儿章西芳为基本视角,面对70年纵深历史和近百个人物,作家显示出很强的平衡和掌控能力。但是,《多湾》写家族史,并不设定家族文化的整体性,而是观察现实变迁中的生命个体的文化演变,用这些个体集合成整体,这也是对前辈作家写家族文化善于预设概念的一种打破。
第三,也是最明显的变化,是至少用一半的笔墨写“文革”以后的社会生活,包括当下的诸多呈现,显现对当下发言的能力,这是现实主义创作可贵的品质。
二、文化出身和笃定的文化倾向
《多湾》具有笃定的文化倾向。说到倾向,往往有主观色彩。文学写作不必回避这种主观倾向。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都是主观活动,所以才会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文学写作的魅力恰恰也在于这个“主观”——它产生创造性,产生神秘性,也才有“文如其人”。文化倾向与文化基因有关,即便作者刻意掩饰,沉淀其中的文化基因还是无法逃避检测。这不是坏事。它表明了有果必有因,溯果可以求因。具体到周瑄璞这部40万字的《多湾》,文化的果在哪里?文化的因是什么?
对于一个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认真阅读其作品。对于《多湾》,认真阅读后会发现它的叙事笔致曲曲弯弯——如其书名,就会知道它既不是《白鹿原》的关中高腔,也不是《情感与理智》的世俗智慧。这种独特的笔法和表达源自何处?源自作家自身的文化出身。先说小说中的章家。这个章姓人家,虽然它的后代因为各种原因移民西安、北京……但它的根在多湾。“颍河水从少室山走出,来到大平原上,没有了山谷的冲击力,漫漫漶漶犹豫着不知往哪里走,就在平原上曲曲弯弯地流着,像一首悠长回环的歌谣……在南北长几十里的地界就拐了一百多个弯,于是这里从西汉末年设县时就叫颍多湾县。……在颍河的一个又一个湾处,撒落着一姓又一姓的村庄。”[1]对于颍多湾县这样具象的写法,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周瑄璞的出身。作家出生在河南临颍县,临颍位于河南中部,处中原腹地,儒释道三教文化都在这里扎根传播。为人物安放这样一个生存环境,凝结着作家自己的经验。
写身边以及熟悉的人和事,是作家写作的一个特点,但不是都能写出“文化”,这不仅需要作家有典型的文化出身和文化结构,还要有写作的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具体的概念官司不去扯。文化有大小内涵之别,大到国家制度,小到族群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可以是“文化”。在无所不包的文化中,文化的异质性、特殊性在哪里?
《多湾》作为一部家族史,更多的是写河南颍多湾县乡村学堂季先生的女儿季瓷这位活了81岁的女人的一生,因此,在这部兼及农村和城市两种生活场域的小说里,季瓷是名副其实的大青衣。从季瓷21岁开始写,写到季瓷81岁去世后的十多年,生生死死,都以“中土”文化为底色。河南是典型的“中”土、中原、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起源早,人类生存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儒释道三教影响很早,它的特点是重学重文。这个重学,凝结着人物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动力,比如季瓷这个大青衣,她的两次出嫁为什么那么顺利?她遇到苦难为什么获得帮助?因为她是受人尊重的季先生的二闺女。好吧,她为什么受到尊重?因为她知书达理,勤勉节俭。对乡贤文化的敬仰是儒家传统,乡贤的一个共性是“正能量”。虽然贫穷不等于粗鲁,不等于罪恶和下流,但小说重点是奋斗上进、造福他人的乡贤文化。核心叙写的章(河西章)家,季瓷也好,章楝也好,章西芳也好,章津平也好,章柿的妻子胡爱花也好,章楝的妻子罗北京也好,都是“正面人物”,他们性格中的共性是勤勉上进。与他们相比,章家的大伯和三叔是败家子,章西滢好吃懒做,章西平随遇而安,是作家价值判断中隐在的“负面人物”。此外,还有历史传统中的乡贤阶层,比如新中国成立前的常掌柜、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罗掌柜、在山东当县太爷的大舅、有钱的老爷章四海,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个有具体身份的人,写他们在文化主导下的一些行为,有没有批判?有,但不是政治批判,而是人性的批判。
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周瑄璞笔下的文化表现为一种分寸。这个分寸是诱人的。有相处的分寸,也有做事的分寸。比如相处的分寸,40万字的小说,开篇写到罗掌柜对季瓷的觊觎、意淫甚至言语撩拨,但没有挟强势和武力而进的举止,遭到拒绝后,罗掌柜虽然恼怒,他的言谈举止也还是委婉有节制。这是礼教的约束,人性跟兽性搏斗后保留了人的分寸,没有形成断裂,这种分寸为日后他们再次相见甚至结为亲家预设了可能——故事也才能继续讲下去。比如章四海与桃花的关系,可能会让我们想到《白鹿原》里的鹿子霖与田小娥,但还是不一样。章四海与桃花由同情到欲望到相濡以沫,其间挨批斗后章四海一度因为不能再接济桃花打算终止往来而桃花不同意,写出了人性中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比如常掌柜在章家欠债后接受了季瓷的求情,“缓期执行”,并在特别困难时期给章家送了一点粮食,等等。包括写到当下,写到男女关系时,也写到“交易”和怜悯的分寸。
这个分寸也是我们说的中庸文化。写苦难,但不是为了写苦难而写苦难,而是写苦难中的懂得和成长,更多的是写做人的快乐。写人性,不是极恶和至恶,而是写人性善恶的层次和转化,甚至连恶也被宽容和谅解。比如,在季瓷的葬礼上,同族的章节高讹钱、偷东西,季瓷的儿子章柿最终选择容忍,这是孔孟中庸思想的一种变体。这种文化,显然有别于睚眦必报和黑白分明,让我想起蒋勋谈红楼人物时说,“我们性格里都有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永远都会在两种性格之间矛盾。林黛玉带着不妥协的坚持死去,薛宝钗因懂得圆融,跟现世妥协而活下来。我们在内有自我的坚持,在外又能与人随和相处,能在这两者间平衡,真是大智慧”[2]。这种文化倾向已经沉淀在作家的血液里,并在写作中经由人物的命运进行文学地呈现出来。我还相信,作家也并不是想要说服或教导他人,她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种取向。
笃定的文化气质,使《多湾》与众不同。
三、作为女性作家的古典化写作
我们通常认为,由于生理特点,女性更适合干精细活。就写作来说,女性是不是更适合写看上去很精细的中短篇以及散文诗歌?显然不是这样,萧红的《生死场》有“越轨的笔致”,并“力透纸背”[3],要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文本上更具有文学性。可见,虽然长篇写作需要体力,但是男性或女性,不能必然决定写作的体量和风格。特别典型的案例是,当代有建树的诗人中,男性的比例远远超过女性,这是为什么?诗歌不是精巧的细活吗?再看看当代的王安忆、方方、迟子建、严歌苓,她们都是写长篇的好手。假使一定要去判断,一个人的阅历、感受力、判断力和表达力的综合素质,才决定了他或她更适合选择哪一种写作类型,当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兴趣和志向。
无论出行的花车多么诡异,人类写作的宗旨终究是朴素的。写作无非是对人的情感奥妙的探索,是对这个世界变化动机的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样的社会环境里,长篇小说因其相对庞大的体量,可以盛放丰富细致的社会人生,常常被当作历史和现实观察的一个横切面,也由此被视为文学创作重镇。在这个重镇里,女性作家毫不示弱,她们中的杰出者既有逝去的身影,也有正在奋力的50后,生理年龄正当盛年的7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已经表现出实力。周瑄璞已经完成的5部长篇各有好处,但显然,《多湾》是持续加速后的冲刺。《多湾》清楚地昭示了她的文化优势。
性别没有高低等差,但写作中一定会留下性别的痕迹。爱情是全部,这是女性的政治,也是女性写作的玄机。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获诺奖作品《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的封面上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4]即便是书写核辐射这样极端恐怖的意外事件,作家依然把爱情与生存并列。曹雪芹笔下的古典社会里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纵然才高八斗,也是百般纠葛于婚姻和爱情。无论章四海和桃花,还是章西芳和转朱阁,女人通过驾驭男人而驾驭世界,这种欧洲16世纪骑士文化以来的一种古典式生存形态,在《多湾》里,浓墨重彩地出演了。我还想说,这一点,作家本人或许并没有“自觉”。这本书写出了一种客观的深刻性。这个客观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投射:从20世纪初提出妇女解放以来,对于男女平等,我们的基本认识还停留在同工同酬层面。真正的问题是,直到今天,女性个体的独立性自觉以及女性价值评价体系的独立性并没有真正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些因为依附性和性别特色而有的社会现象。更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人向这种依附性投降。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一些观念还停留在古典式阶段,还不具有真正的现代性。
《多湾》写出了什么?写出了“食色性也”,写出了一种承认和悲观。爱情或者是婚姻,“这便是爱情:大概是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这是关于男女之情的一段精彩的比喻。蝴蝶固然美丽,但难求难得,是虚妄的想象,日常化的形态还是蛾、蟑螂、蚊、苍蝇、金龟子。因此,《多湾》里的爱情大多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物质的身体,物质的地位权利,物质的食物,物质的环境,等等。这说明作家对当下生活体察深刻,但她这样写,依然令人绝望。这大概也是作家不曾预料的吧。而且,坦白地说,我不喜欢小说里个别地方对于性的直白描写。文学写作中,不是直白就更加真实。《多湾》中这种直白的描写,对整部小说的古典文质其实是有伤害的。《红楼梦》写贾宝玉和花袭人、贾珍和秦可卿的“苟且”,虽不及《金瓶梅》直白,但《红楼梦》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叙事技巧余味长。
写到这里,突然意识到,现实主义关照也好,文化倾向也好,古典化写作也好,都是文学写作的既有元素。那为什么还叫“异数”?可能因为这种“既有元素”如今已不常见。
[1] 周瑄璞.多湾[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12.
[2] 蒋勋.蒋勋细说《红楼梦》[N].新华日报,2015-07-28.
[3] 高艳丽.经验与话语的冲突与逃逸——解析萧红《生死场》中“越轨的笔致”[J].文艺争鸣,2013(6):98-100.
[4]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M].方祖芳,郭成业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6.
[责任编辑 张 敏]
“Uncommonness” Book Review on Gone with the River
LIU Qiong
(ArtsDepartment,People’sDaily,Beijing100733,China)
The novel, entitledGonewiththeRiver,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novels in that it keeps the realistic writing tradition with an ordinary and permanent life, accompanied by a grand historical line. Everyday life in the past became history, history in everyday life became a daily routine. Instead of focusing 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this novel focuses on the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the continuous and daily life, people are the theme, the major event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objective life process, which is a great subversion on narration. This novel is a record of a family history, yet not with a fixed integrity of family culture, also an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s’ cultural changes in real life, with these individuals combined together into an entirety, which is also thought to be a breakup of the fact that the previous writers would like to write about the family culture with the preconceived notions.
GonewiththeRiver; uncommonness realist tradition; daily routine; family history;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ulture; classical writing
I206.7
A
1001-0300(2016)03-0066-05
2016-03-05
刘琼,女,安徽芜湖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编,高级编辑,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艺术及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