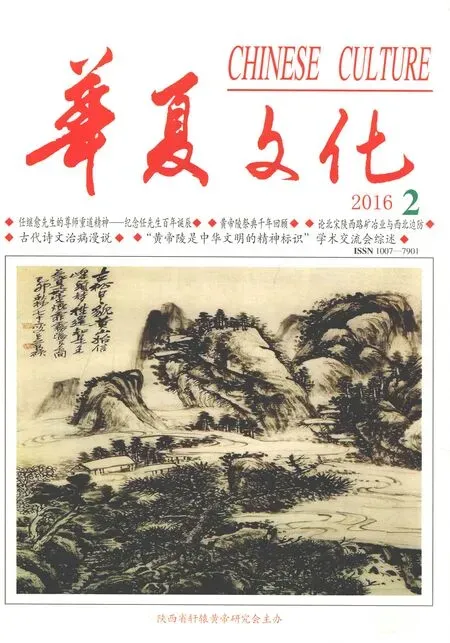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经学百年研究回顾
□ 郭海涛
魏晋南北朝经学百年研究回顾
□ 郭海涛
众所周知,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学术主流。从秦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里,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代表型态,后世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遗憾的是,处于两汉向隋唐以迄宋明理学变化过渡阶段的魏晋南北朝经学却一直受关注较少,研究不多。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社会动荡和政权分裂致使文献大量散佚,南北的地域差异也深刻影响了学术发展,这些都加大了后来研究工作的难度。但无论如何,承前启后的魏晋南北朝经学都不能为儒学研究者所忽视。本文就尝试将百年以来魏晋南北朝经学的研究成果作一回顾。
一、从经学到玄学时代的学术转变及认识问题
纵观儒学发展历程,经学从发轫至今已有数千年时间,但以经学为对象的经学史研究却晚得多。自从清末《经学历史》开风气之先,经学史研究逐渐成为儒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对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转变时期的经学探讨,研究者首要面对就是经学为何被玄学取代,二者之间又是什么样关系的问题?
皮锡瑞主张现实政治发生变化是学术更替的最大原因。他认为,东汉末以来的政治衰败致使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经学一并衰落。特别是党锢之祸和政权频繁更迭令学风萎靡、士人凋零,重视师承和积累的经学因此难以立足。虽然皮先生提到“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的经学内在弊端,但他依旧力主外在因素主导说。缺憾的是,书中没有对经学向玄学转变及二者间的关系作相关论述。(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后来,马宗霍论述魏晋玄学与经学问题时认为:在王弼、何休影响下,经学的治学方式从训诂转向义理;杜预和范宁的春秋研究在学风上变汉代经学的专门为广博。马书以代表性学者为经学转变的核心因素,但单举个人影响来说明时代学术的转变还显得立论单薄,且也没有说明玄学和经学的更替原因。(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从玄学开创者何晏、王弼入手,对比汉人经学的烦琐弊病,指出玄学是变革经学旧病而出新的结果。书中视何、王为相对于两汉旧经师的新经师,认为他们解经“不过是复古的途径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96页)。侯书是本时期经学研究中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变化的原因,虽然书中对这种内在的思想变化没有更细致说明,但将玄学视为经学并且探究内在新思想发生、发展的理路启迪了后来的研究。学者余敦康便主张时代危机只是经学衰落和玄学兴起的直接原因。他认为,以经学为代表的旧伦理纲常和天人之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要求,而此时会通经学和诸子学说的玄学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更高、更系统的理论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玄学思潮怎样代替了经学思潮》,《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余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学术思潮的变化,认为经学思潮不等于经学,但对经学自身固有的弊端有所忽视。稍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在郑、王经学的对比中认为,以郑学为代表的汉经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王学也“没有提出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崭新哲学体系……这就是王学最终不能战胜郑学并且不能为经学开辟新时期的主要缘由”(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8,第621页)。将以何、王为代表的义理之学看作是义理经学,而义理经学又是玄学的一部分。在编者看来,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有着内在哲学层面的要求,经学与玄学两种学术类型之间存在着玄学与经学的交集。虽然编者讨论了学术变革过程中思想需求的变化,但需求的具体内容还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后来,王克奇《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专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政治统一局面的破坏只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实际是玄学的宇宙本体论、人格哲学取代了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宇宙哲学,而这种更替背后的思想变化规律才是变革的主要原因。作者着重分析了经学与玄学间内在的不同,这是对前人研究未尽地方的补充。(王克奇《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严耀中从南朝四门学设立的前后过程和学人传、治学术的复杂性两个方面说明玄学对经学的影响。作者认为玄学使经学在学科设置和治经对象上出现交叉、多元,讲谈成为经学传、学的主要方式,简约和变通成为此时经学的新特征。(严耀中《试说玄学对南朝经学之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第1期)
对经学与玄学二者关系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玄学思潮是儒学内部分化后的一部分与道家思想合流的结果,而致力于经学内部改造的另一派则融合今古文发展为“郑学”(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还有学者认为“魏晋玄学就是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思潮”,这和部分学者主张玄学思潮不等于玄学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魏晋玄学是对汉代经学的烦琐形式的否定”。还有学者主张玄学是由经学反动发展而来,二者间有承续关系。
(张岂之主编,刘学智编《中国思想学说史》魏晋南北朝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从上述研究结论看,对经学被玄学取代的原因,学者们主要是在政治、社会因素和经学自身弊端与时代思潮变化因素等内、外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但内在理路的探索相对较少。在经、玄关系问题上,研究成果中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论断,甚至存在观点分歧。
此外,学者的研究不只从上述两个问题展开,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侧重、立场上不尽相同,所以探究的重点、结论有同有异,在著作成果里就表现为撰著形式、研究方向的多样性。如刘师培著《经学教科书》就侧重于十三部经典传学过程的梳理,虽然文义清晰、简明,但并未揭示这一时期经学研究的深度内容(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长沙:岳麓书社,2003)。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对魏晋南北朝经学只是略有提及,并且依旧是列述南北传学脉络,细节分析不多(李源澄《经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另外《中国经学思想史》的作者总结、概括魏晋经学的特色为博采群言和综合兼治两个方面。《南北朝经学史》是近来对这一时期经学研究的全面总结,对于本时段内经学的发展轨迹、传承脉络、经师著作、经学与其他学术关系作了详细述论,特别是在人物研究上,几乎囊括了目前所能钩辑出资料来说明的全部代表性经师,并且对他们的学术旨趣、治学风格、贡献影响都有说明。(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牟钟鉴《南北朝经学述评》 运用整体综合的视角考察南北经学,他主张南北除各传魏晋、汉末传统外,在宗经、学风上也有相互渗透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南北学术不断交流互动,以熊安生为代表的经师及著作已经表现出综合南北的倾向。(牟钟鉴《南北朝经学述评》,《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上述研究和成果大体沿经学与玄学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一般都比较宏观,单独的经学研究不多。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问题中的细节考察逐渐增加。
二、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发展认识问题
侧重时代政治原因,今文学家立场的皮锡瑞就对魏晋南北朝经学评价不高。在他划分的经学十个发展阶段里,此时期的经学是衰微和分立时代。他认为两汉经学在魏晋时期的衰落正是由于郑、王败坏家法而来,特别是王肃传注造经更是蠹害经学。但本田成之却首重郑、王学术争端,认为郑玄和王肃的经学之争不仅不是“恶结果”,反而“给予(经学)一转机,使回复其生命的。”([日]本田成之著,孙俍工译《中国经学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本田从时代发展需要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王学对郑学展开反动的积极意义,并且侧重它的“绍述”作用。田汉云撇开玄、经分开研究的方式,从宏观整体上探讨二者的有机关联,对伪古文经典和王肃造经问题持不同于传统的批评意见,他从儒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王肃对经学的积极贡献。(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牟世金在《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中认为,虽然《魏略》、《晋书》、《南史》等史籍中有不少儒学颓废、人才匮乏情况的记载,但这种“衰微”是相对于统治术性质的“儒术”而言,他认为魏晋时期衰微的不是经学,经学著作数量的众多和不再单一化的经风便是证明。(牟世金《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吴雁南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将魏晋及其后经学的发展概括为多元倾向。书中以当政者对经术的重视和经学传注作品的涌现说明此时期经学的发展并不是停滞、倒退状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李金河《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通过对王弼、韩康伯、范宁、雷次宗等经师的考察,他认为魏晋经学派别杂多、训诂义理互见,虽未形成经学一统局面,但已对前代有所发展和创新。(李金河《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与李文观点相似,庄庭兰《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一文以史料中政权对儒学特别是教育重视的诏令繁多为经学恢复发展的标志。(庄庭兰《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张祥浩在《汉书》与汉末文赋中发现,士人对政治的失望引发了儒学信仰危机。他认为信仰危机、佛道盛行、太学的衰废和儒家大学者的缺乏都是儒学衰落的具体表现。(张祥浩《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在儒学衰落原因上,他提出的中央政权衰落、儒学虚伪化和理论匮乏都是突破传统单一政治因素的新见解。在《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中,田汉云主张魏晋南北朝经学处于一个由复苏到发展的过程;魏、蜀、吴三方经学比较,曹魏因对经古文学的继承而优于孙吴,孙吴又略强于蜀汉;经学到东晋是在低水平上对前期的发展。(田汉云《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程平等通过史料整理发现,西晋一代经学著作有七十多种,风格上今古文合治,中原、东吴、蜀三个地域经学共同构成了西晋经学的源头,经师世家大族身份的影响和经、玄、佛以及今古文的融合共同促使经学居于西晋学术主流的地位。(程平、刘运好《西晋经学考论》,《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汤其领主张此时期经学非但未衰竭反而经历过郑学小一统时代,后来经学玄化和春秋学兴起就是经学取得的表现。(汤其领《魏晋经学探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张承宗考察魏晋经学发展的内在脉络,主张西晋石经的刊刻是为王学兴盛的顶峰,但是随着政治依托的消失,王学也迅速为玄学所取代,不过儒学在此过程中一直持续发展。(张承宗《魏晋经学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从研究结果来看,学者们对此时期经学是否存在发展的看法是较一致的。他们不赞同皮锡瑞主张的“中衰”说,反而认为此时受到时势、玄学、佛教的影响,经学更深度地融合经今古文学,打破了汉代经学繁琐和迷信的局限。笔者以为:一方面,皮氏因今文经学家立场的局限导致学术观点发生偏颇;另一方面,从经学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治经方式上义疏体的运用和风格上义理的重视都是经学取得发展的表征。但是,以上学者在儒学和经学关系上并未作出严格的区分,因此对待经学的发展状态问题常因儒学与经学的代称混用而产生矛盾见解。
三、魏晋南北朝经学差异表现及其原因
《隋书·儒林传序》中论南北朝学术风格差异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皮锡瑞首先就不赞同这种含有褒贬色彩的评判,他认为书序的论断只是唐人自身学术趣味上重南轻北的结果。然而,后世学者却常以《序》论作为评说南北朝经学的最佳论断。不过书序的仅仅十几字还不能完全揭示经学风尚差异的具体原因,差异原因的深入考察也成为魏晋南北朝经学研究的重点。
刘师培认为北方重实际和南方尚浮夸的社会风气致使学术风格产生差异,不过刘氏对六朝南北学特质的概括没有超过唐人论断。有学者在研究南北经学差异产生原因时已注意到其中的玄学因素,譬如有学者主张“南学与北学的重要区别,是基本上没有受到玄学的影响,而较多地保持着汉代经说的传统”。除了玄学因素外,还有学者从社会等其他方面进行了探索。
吴先宁《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根据南北经学宗主郑玄、王肃差异,分析认为南北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促使了差异的产生,而北方帝王政治和南方门第政治的不同是众多原因中的核心。(吴先宁《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4期)
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异同论》在地缘政治因素外,着重分析不同的南北自然环境对经学的影响。文中主张,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产生了安稳、浪漫环境,这使得学风较为自由;北方礼乐教化深重并且地力匮乏,反映到经学上便是学风笃实厚重。(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异同论》,《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孔氏还有《北朝的经学与儒者》一文,认为经学内在的融摄性使它能适应任何政治环境,而北魏以来统治者对儒学重视的措施更促使了经学的复兴。虽然北朝经学因追求实效使得经风朴素甚至保守,但在学以致用上,以熊安生为代表的北方经学家比南方更积极主动。(孔毅《北朝的经学与儒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此外,汪奎《永嘉南渡后南北经学的差异》一文也是从南北地理环境和玄学风气两方面分析了南北朝在崇经类目、承袭经统以及学术风格上的差异,基本观点与前人类似。(汪奎《永嘉南渡后南北经学的差异》,《华夏文化》2007年第3期)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南北经学受不同社会风气影响是经学发生差异的主要原因。这里可突出强调的是,佛教对经学的影响使得经学发生了不同于汉代经学和北朝经学的变化。只是目前学者对这种影响的深浅、具体表现还存在不同意见。
章权才以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虽然在南朝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经师重佛同时也弘儒,因此佛教对于经学的影响并非巨大。(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论略》,《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的作者孔毅提出经学在发生玄化的同时也发生着“佛化”,证据便是以梁武帝为代表的南朝经师已经不是纯正的儒生。不过孔文只注意到经师在信仰或起居上受佛教影响,还不能有效地说明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孔毅《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熊承涤在《南北朝学校教材的特点》中从教学、治经方式的角度说明佛教对经学的影响。他认为佛教聚徒登坛的讲经方式被经师学用,流行于南北朝的义疏治经体例也是源于六朝佛典注疏,因此经学受佛教影响明显。(熊承涤《南北朝学校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87年第11期)牟钟鉴、田汉云都赞同盛行于梁代的经学义疏体例是仿效佛典注疏而来,并且这种治经方式对唐以下解经影响深远。不过,两汉经学本身就有繁琐的特征,注疏也是经学常用例法,简单从义疏体的运用上判断佛教对经学的影响还难有说服力。申屠炉明《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就对义疏的产生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虽然南朝经师不可避免地受玄风、佛学影响,但是他赞同陈澧对义疏渊源于汉代的论断。他通过对《论语义疏》研究认为,义疏不能仅仅作为佛教影响的产物而忽视了它内在的汉代经学元素。(申屠炉明《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关于《论语义疏》上所体现出来的佛学影响,张文修《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分析书中注释时所采用的佛教词汇,揭示了佛学对于经师注经的影响不仅是在经学的释字解义上,甚至深入到了思想领域。(张文修《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此后,柏宇航的《论佛教对皇侃〈论语义疏〉的影响》全面细致地梳理了皇氏此书所受佛教影响的事实,侧重皇疏中所用“方便”等大量佛教词汇、“义疏”体例来源问题、以佛教义理解经说明皇氏著作受佛学影响的明显性。(柏宇航《论佛教对皇侃〈论语义疏〉的影响》,《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四、专经研究与其他
以上所述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研究中较为宏观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以单经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也有很多。譬如闫春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便重点梳理整个两汉“论语学”的注经特色,进而对比魏晋时期玄风兴起下的论语学发展,南北朝时期儒玄释三家合融时期论语学的特点。通过汉代经学、魏晋儒学、魏晋玄学、东晋南朝经学四个方面考察整个汉唐之间“论语学”的发展状况。(闫春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孙敏的《六朝诗经学研究》则截取六朝为时限,通过上溯秦汉“诗经学”的发轫到魏晋时期经学衰落、佛道兴起的背景,进而以《诗经》研究者为线索,以时间先后的顺序逐次分析“诗经学”研究的状况和社会影响。(孙敏《六朝诗经学研究》,扬州: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户瑞奇《魏晋诗经学研究》总结毛诗主导地位和义理化倾向的特点,从诗学的角度分析郑、王的学术争论(户瑞奇《魏晋诗经学研究》,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刘新忠《南北朝诗经学研究》除了就《诗经》研究在南北朝不同的流传脉络进行梳理和总结外,还从众多文论家的角度展现经师之外的《诗经》研究。(刘新忠《南北朝诗经学研究》,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吕华亮《略论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新趋向的开创》则是打破原来学界侧重此时期对秦汉“诗经学”继承性的研究。他认为义疏、名物、音类等新研究方向是对原来伦理解诗方式的一种转变和创新。(吕华亮《略论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新趋向的开创》,《兰州学刊》2014年第6期)
礼学方面以张帅《南北朝三礼学研究》最为全面,述论了整个时代“礼学”的发展状况,认为礼学在南北朝的兴盛背后都有着突出的政治因素。(张帅《南北朝三礼学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刘增光以刘炫《孝经述议》为切入点,认为魏晋南北朝“孝经学”的特色便是在忠孝观上孝重于忠,即对家庭的重视高于政治;律法思想和“孝经学”的融合,这是现实政治趋向统一在学术上的反映。(刘增光《刘炫〈孝经述议〉与魏晋南北朝〈孝经〉学——兼论〈古文孝经孔传〉的成书时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在《尚书》学研究上,程兴丽《魏晋南北朝〈尚书〉学研究》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充分运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发现《尚书》学此时期呈现出删繁就简、义疏治经和注音学独立发展三大特点。个案研究上,通过马、郑、王、敦煌卷本、《尚书释文》的对比发现了系列新见。(程兴丽《魏晋南北朝〈尚书〉学研究》,扬州: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春秋》学方面,李飞从《春秋》学传播脉络、经师及著作存亡现状、基本内容和后世流传状况等几个方面梳理了整个时期的研究情形,文后附录的《春秋》著作分类表与著作辑佚对《春秋》学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李飞《魏晋〈春秋〉学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张鹤泉《论北朝〈春秋〉学的传授》分析北魏与东、西魏时期三个阶段《春秋》学的变化与特征,发现《传》的传授在地域上不平衡的特点。(张鹤泉《论北朝〈春秋〉学的传授》,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易学》方面,张苧对比秦汉象数解易的风气,以魏晋时期王弼、姚信、蜀才、王肃、干宝等易学家所治易注分析魏晋《易》学的义理风尚与特色,对于《周易》在当时的问学、占卜等应用状况及对文学的影响也有涉及。(张苧《魏晋易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张勇《南北朝〈易〉学研究》着重突出易学在分裂时期所形成的地域色彩和门阀贵族特征,认为《易》学虽存在南王北郑的宗奉差异,但象数学的占验派已然式微,只部分思想留存于中下层,南北《易》学虽继承前代,但在筮法、名称意义等细节上依旧有所创新,特别是《易》学与《礼》学的互动促进了现实政治的变化和礼学理论的发展。(张勇《南北朝〈易〉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以上是对此时期专经研究的介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此相关的研究。早先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辑佚史料,对汉魏时期时期经学博士的门类设置、兴废沿革、地位作用都作了简要说明。宋晔《两晋南北朝经学博士考论》不仅上溯秦汉博士起源问题,并且对魏晋南北朝的博士制度、博士名录及博士与世家大族关系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此时期经学博士在官学教育中成效不高,但仍旧具有保存和推动经学发展的作用。
(宋晔《魏晋南北朝博士考论》,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李珊从经学教育的角度出发,梳理汉末三国经学在官学、私学中的发展状况,透过经学教育的变化展现经学出现的玄学化趋势,并着重分析这种趋势和今古文经学变化的原因,强调私学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李珊《汉末三国的经学教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五、总结与思考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学术积累。玄学与经学的时代学术转变问题受关注较多,学者一般认为两种学术型态存在着前后影响和继承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经学对两汉经学部分继承的基础上,在治经方式、注经语言、思想旨趣方面有所变化和突破,特别是义疏解经体例的出现与盛行,不仅体现此时期文化开放、多元及融合的局面,同时也为隋唐及以后的治经方式定下基调。此外,义理解经和圆通释滞思想的追求进一步瓦解了繁琐、谶纬、迷信对经学的干扰,使得经学回归人文理性,为宋明理学的出现作了思想铺垫。
就魏晋经学的玄化和南北朝经学的差异问题来看,魏晋经学虽然变化前代经风,但依旧不离汉代经学基础;南北朝经学虽有差异,但两地经学一直处于交流和互相影响的状态。现实政治、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共同影响了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此同时,文化传播、经师流动、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促使南北朝经学走向融合,这是隋唐经学统一的内在原因。
然而,通观目前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为历史文献严重散佚等原因,学者的经学研究往往缺乏详实有力的资料说明。譬如南北经学差异,虽然有史书的零星论断,但没有具体的文献对比,结论只能流于泛泛。再如儒、释关系和影响问题,虽可见佛教对经学的影响,但仅仅通过皇侃的单本著作研究很难说明整个时代的风貌。另外,从研究深度上来看,学者多是通过史料中的经师生平、论著等介绍性文字,以排列的方式陈说史实,这样的学术研究易停在表面而缺乏深见。因此,对此一时期经学的研究,除了期待新文献资料出现和使用新材料外,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必须突破现有模式,强调问题指引和综合考察,否则就只能沿袭旧说,缺乏创新和洞见。最后,学术研究需要学人共同努力,对港、澳、台与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关注和借鉴也有必要,而这也是目前魏晋南北朝经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方面。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