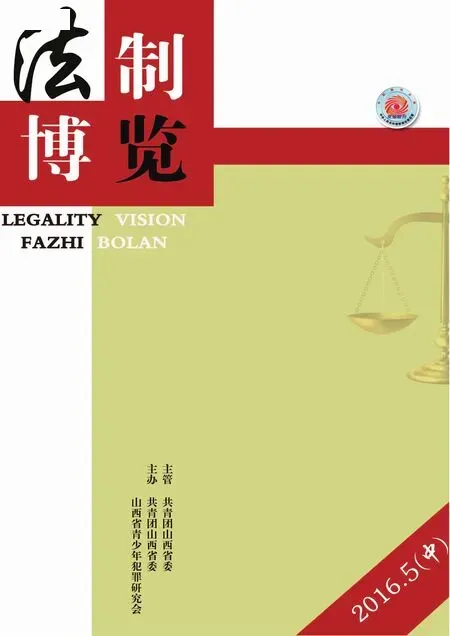职场性骚扰法律规制的困境与思考
周倩颖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职场性骚扰法律规制的困境与思考
周倩颖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要:职场性骚扰问题日渐严重,而我国对这一问题的法律规制却十分有限,本文通过分析职场性骚扰概念本身及侵权责任的法律要素,总结其法律规制的困境,并从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现法律制度的相关问题,同时,引荐美国相关法律制度。完善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对受害者以及潜在受害群体的最大保护。
关键词:职场性骚扰;法律规制;困境
职场性骚扰这个长久以来隐藏在光鲜亮丽的制服背后的问题,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大众媒体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在我们面前。媒体报道虽然是零散的,但足以让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妇女观察”项目曾经在2011年进行过一次关于职场性骚扰的调查,根据数据显示,19.8%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1]但是当前我国对于职场性骚扰的法律保护却十分有限,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对受害者以及潜在受害群体的最大保护。
一、职场性骚扰法律要素
(一)职场性骚扰概念的法律要素
“性骚扰”一词,来源于美国女权主义者Catharine A.Mackinnon,在她的定义中已经将这个词限定在了存在不平等关系的雇主与雇工之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她在自己的书《工作女性的性骚扰:一个性歧视的案例》[2]中进一步将性骚扰进行了分类,分别为“交换型”性骚扰和“工作环境”性骚扰,这样的分类也在1980年被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所采纳,成为对职场性骚扰行为进行追诉的法理基础。
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的概念和界定,但欧盟、台湾等地[3]均就这一概念在法律中进行过解释,虽然由于各国的国情和法律文化的差异,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总结,从这些定义中提取出职场性骚扰的三大法律要素:
第一、骚扰行为违背当事人意愿。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是受害人所排斥的,不受欢迎的,这里并没有要求受害人有明确拒绝的言辞或行为,而是更多的从主观态度上来阐述,有厌恶等类似的态度。
第二、骚扰行为表现为与“性”有着直接关联的行为。此处的直接相关行为应当包括刑法之中规定的“猥亵”“强奸”的行为,同时它也包含程度更轻微的一些柔性、隐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通常没有遭受到身体上的暴力伤害。
第三、骚扰行为在工作场所,或者在职务履行期间发生。主要表现在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应当存在雇佣关系,行为人能够利用两者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站在主导地位,实施骚扰行为,并使被行为人迫于这种关系而忍受这样的行为。
(二)职场性骚扰侵权责任的法律要素
我们通常将职场性骚扰看作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通说认为,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包含四个条件,即存在侵权行为,有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证明职场性骚扰行为人责任的过程,也就是证明侵权责任的过程。这里主要对职场性骚扰的损害结果和主观过错加以讨论。
损害结果。就侵权行为来说,损害结果通常意味着权利人的既有权利受到了他人的侵犯或损害,并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有学者认为职场性骚扰侵害了他人的人身自由[4],它给他人的精神施加了痛苦,属于人身自由之中的精神自由。Edmund Wall也曾经在他的书中提到性骚扰侵害了他人的私生活[5],这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因此他认为性骚扰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另外,作为劳动者,被行为人还具有劳动权[6],职场性骚扰使得劳动者无法平等就业,或无法平等的获取晋升、培训等职业机会。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行为均可以达到法律追诉的效果,只有对工作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才可能被追诉,如Harris v.Forklift Systems,Inc.案中,法庭就着重对骚扰行为是否造成了工作环境的敌意性进行分析。
主观过错。侵权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故意或者过失行使行为的过错,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在明知或者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侵害的基础上实施骚扰的行为,如果由于本国文化的原因,而使某些正常的社交行为在其他国家受到误解,而在了解到此种误解后,行为人及时停止了这类行为,那么并不能认为是具有主观过错。
(三)从职场性骚扰的法律要素看法律规制的困境
职场性骚扰的法律规制是具有很大难度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职场性骚扰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构建法律体系的时候,就不得不制定大量的规则使其规范化。
第一,行为界定困难。职场性骚扰源于道德概念,仍具有道德性质。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非暴力性的行为,这类行为界限模糊,形式多样,要界定什么样的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是十分困难的。在美国,“普通女性标准”经常被法院采用,这一标准是指,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时,就看一个普通的女性在同样的情况下是否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性骚扰行为。这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性骚扰行为界定的困难。
第二,行为存在隐蔽性。性骚扰的行为本身就多是隐性的,不易被发现的,加之发生在工作、雇佣关系之中,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可能由于工作机会、工资待遇、前途发展等原因而选择隐忍不发、默默忍受,也会因为害怕自己的私生活遭到非议而不愿公开自己的遭遇。
第三,主观态度起到重要作用。不论是与当事人的意愿相悖的要求,还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要求,都与当事人的主观态度相关。证明主观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这在刑法理论中的到印证。如何证明嫌疑人具有故意、过失或直接占有的目的等主观状态,学界争论了很多年,有观点称:“在查明故意、特定意图和动机等心理要素时会遇到很多重大困难,只有从外部事实及心理学上的法则进行多少是必要的反推,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7]
二、我国职场性骚扰法律实践
(一)“殷某诉刘某名誉权纠纷案”背景及争议焦点
被告刘某是某公司的员工,2012年她向公司投诉自己的上级,原告殷某,对其进行性骚扰,公司终止了与殷某的劳动合同,殷某于是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请求,仲裁庭经过审理之后裁定某公司与殷某终止劳动关系是违法的。在此之后,某公司向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合法。法院经过调查审理,支持了仲裁庭的意见,认为殷某的行为并不构成性骚扰,因此公司无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基于此判决,殷某再次提起诉讼称自己名誉权受损,要求刘某在报刊上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8]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公司单方面与殷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被告刘某向公司投诉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第二个问题与本文主题无关)。在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证明殷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因为公司与殷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其“存在性骚扰和辱骂员工的行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职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如果殷某存在此类行为,那么公司的行为就有法可依,反之,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为了解决性骚扰行为的认定问题,法院分析了主要证据——谈话录音,该证据由被告刘某提交,用以证明殷某存在性骚扰行为。录音中,殷某与刘某有一段对话,对话内容涉及“潜规则”一词,对于这个词的含义双方各执一词,殷某认为这仅仅是指公司的一项制度,而刘某却认为这是一种性暗示。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从谈话录音的内容上下文分析,从社会大众的理解角度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下面对这两种方法进行具体论述。
首先,从录音的上下文分析。这一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证据所包含的内容本身加以理解,从而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它与其中的系统解释相类似,系统解释指在解释法律条文时,要联系这一条文所在的法律、法律部门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从整体上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9]但是,法院并没有就其具体如何理解录音内容进行阐述,我们也只能从判决中看出法官笼统的态度。
其次,从社会大众的理解角度分析。这一方法又与英美法系中“理性人”标准不谋而合。在侵权领域,要判断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及他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要以社区中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理性认识来判断,此即“理性人”标准。我国法官的“社会大众的理解角度”虽然与“理性人”标准相似,却略显单薄,我们无法理解“社会大众”怎么界定,也无法知道法官如何具体运用这种方法。
(二)我国性骚扰立法状况
我国当前的性骚扰立法状况十分堪忧,几乎是空白的状态,对性骚扰的行为、行为人的责任、证据规则等问题均没有加以规定。与职场性骚扰相关的法律如下:《宪法》第38条,2005年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第58条,2012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1条、第12条,《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劳动法》第3条、第12条、第13条,2001年《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44条。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将“性骚扰”写入法律,“性骚扰”一词在中国也成为一个法律概念,但这一次的修订只是抽象而笼统的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而解决办法也是不痛不痒的有权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投诉。相比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原则性规定,民法对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尊严的规定更具有现实意义。《民法通则》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的方式侵犯公民名誉权,还规定了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也是司法实践中追究性骚扰行为人责任的主要依据。最高法院在2001年出台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职场性骚扰侵犯人格权的赔偿提供了支持,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严重伤害,受害人可以据该解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性骚扰行为情节较为严重,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可以被处以罚款和居留。此外,职场性骚扰往往会损害他人的劳动权,导致不公正的职场待遇,《劳动法》对此作出了规定。
在2012年,国务院通过《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其中第十一条、第十二条首次明确提出了用人单位在职场性骚扰中的义务和责任,表现为“预防和制止”,同时,进一步规定了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的四个组织和团体。
三、我国性骚扰法律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借鉴
我国性骚扰的立法、司法存在很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仍然处在从“无法”到“有法”的过程中,而性骚扰规制走在最前端的美国,已经在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实践中逐步完善其各项法律制度,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一)行为判断标准模糊
对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判断是一件棘手的事,通常只有显而易见的性骚扰行为才被认定为性骚扰,并没有表现出法律对于群体利益的保护倾向。在广州首例职场性骚扰胜诉案[10]中,原告提交了其同事拍摄的照片作为证据,照片明显显示出被告对原告的越界行为,法院才以此认定被告的性骚扰行为。
在美国,职场性骚扰案件主要以行为是否受欢迎来判断是否构成性骚扰。在MERITOR SAVINGS BANK v.VINSON[11]中,法官阐述了性骚扰的行为应当是不受欢迎的(unwelcome),而不是以是否自愿(voluntary)来判断的。由于在工作环境中,职工有可能因为工资、晋升等原因接受性骚扰的行为,所以法官认为以自愿与否来判定并不适当,不受欢迎才应当作为判别标准。
美国法院还常采用“理性女性”[12]标准,1991年Ellison v.Brady 案中采取了此标准来判断职场性骚扰。这一标准是由英美法系侵权责任中的“理性人”标准发展而来的,由于在职场性骚扰案件中,受害人多为女性,而且在性骚扰行为认定的态度上,女性的观点与男性的观点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理性女性”标准的出现较合理的解决了这一矛盾。
(二)责任制度缺失
在我国对行为人的责任并没有特殊的规定,我们仍然依据民法中的侵权责任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法使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
美国的雇主责任再一次在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的发展中率先走出了一步。2013年VANCE v.BALL STATE UNIVERSITY ET AL.[13]一案中对雇主责任进行了解释,职场性骚扰的雇主责任会由于性骚扰人的不同地位和状态有所不同。如果行为人只是共同工作者,那他只需要对控制工作条件的过失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是管理人,而骚扰行为以一个有形的职业行为(比如一次重要的职位变动)为结束,那么他就要承担严格责任。但是如果不存在这种变动,行为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免责:第一是雇主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来防止和改正性骚扰行为,第二是原告不合理地没有从这种预防和纠正中获取利益。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于中国妇女研究网[EB/OL].http://www.wsic.ac.cn/,2014-11-6.
[2]Catharine A.Mackinnon.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M].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3]1991年欧盟<反性骚扰议案施行法>;德国<德国工作场所性骚扰受雇人保护法>;台湾<两性工作平等法>均对职场性骚扰做出了定义性质的规定.
[4]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4.
[5]Edmund Wall.The Defini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Confrontation and Decisions:Sexual Harassment[M].Prometheus Books,2000:345.
[6]李廷彬.论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劳动法规制[D].辽宁大学,2013.5.
[7][德]冈特.斯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M].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8.
[8]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黄浦民一(民)初字第583号.
[9]周农,张彩凤.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8:192.
[10]邓新建.广州首例原告胜诉性骚扰案背后的较量[EB/OL].法制网www.legaldaily.com.cn,2014-11-11.
[11]U.S.Supreme Court,MERITOR SAVINGS BANK v.VINSON,477 U.S.57(1986).
[12]徐爱国.侵权法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J].学习与探索,2012(3).
[13]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VANCE v.BALL STATE UNIVERSITY ET AL.No.11-556.Argued November 26,2012—Decided June 24,2013.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4-0012-02
作者简介:周倩颖(1991-),女,江苏南京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