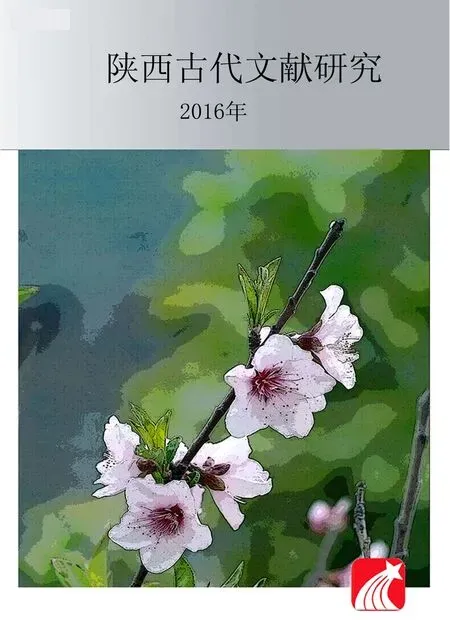从《思庵野录》看渭南薛敬之的读书观
朱成华
从《思庵野录》看渭南薛敬之的读书观
朱成华
薛敬之(1435—1508),字显思,号思庵,渭南人,明代中期陕西著名的理学家,其在关中学者的学术往来交流基础上,结合关中风土人情及时代风气,将关中理学思想推向新的阶段。
薛敬之在年幼的时候就很聪慧,五岁时就酷爱读书,十一岁时能作文赋诗。其作秀才时,居止端严,不同于流俗,但在科场方面却很不利,屡试不中。成化二年(1466)时,薛敬之以积廪充贡入太学,当时江门心学的开创人陈献章也在太学,二人并称,名闻于京师。成化二十二年(1486),其出任山西应州知州。在任期间,体恤民情,尤其重视百姓生计,经常到田野中巡察,劝导百姓努力耕稼纺绩。在播种期间,向贫困户提供耕牛和种子,并且“买牲畜数十,给之茕民,令孳息为养”①冯从吾:《关学编》卷3。。对于那些无力交纳地租的贫困农民以及无力婚娶、丧葬的,都给予一些资助。在平常年份,他注意积蓄粮食和干菜等,以至于在三四年间,就积累了粮食四万余石,干菜几万斤。后来遇到灾荒,就用平常年月积累的粮食干菜救济灾民,帮助他们度过荒年。有本已经逃荒在外的三百余家,听到这个消息,全都回归家园,薛敬之给予他们衣食,还帮助他们修葺住房,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免死于饥馑。薛敬之在担任知州期间,很重视学校教育,多次到州学学舍巡视,宣讲孔孟之道,传播理学思想,“由是应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学”②同上。。后以“奏课第一”,于弘治九年(1496)升任浙江金华府同知,在任两年后辞官。
就其学派而言,薛敬之师从甘肃兰州周蕙,颇受其师艰苦力学的影响。薛敬之平生好为人讲说道学,又好静坐思索,酷爱读圣贤之书,读书若有所得,必记之于笔记,并阐发自己心得,形成著述。一生著述颇多,盖有《思庵野录》、《心说》、《性说》、《定心》、《定性》、《道学基统》、《洙泗言学录》、《尔雅便音》、《田畴集》、《百咏集》、《归来稿》、《礼记通考》、《易箦》、《金华乡贤祠志》等,但因历经多次地震,其著述大都佚失,现仅存的有《思庵野录》三卷及几首诗文。
从存稿《思庵野录》可大致考察薛敬之理学思想的主旨,从而揭示自河东薛瑄之学至薛敬之这一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凸显薛敬之在明代关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而从《思庵野录》亦可管窥理学家薛敬之的读书观,这主要是因为《思庵野录》本身就是薛敬之阅读前人圣贤之论著有所得而形成的读书笔记。
一、为治贵读书
薛敬之本人自幼爱读书,能文善诗,称古则贤,《思庵野录》云:“五岁爱读书,十一岁解属文赋诗,稍长言动必称古道则先贤。”又,“景泰七年,为渭南学生。自为学生,居止端严,不同乎流俗,乡闾惊骇,或且以为迂怪。善为文章,说理而华”。可见薛敬之因读书而才华出众,惊骇乡里,且擅长作文。
在薛敬之看来,读书意义重大。一个人不读书,就无见识,更不能成就大事,正所谓“器识不远”,则“不能成大事”。一个人若想要治理好政务,那更需要认真读书,即其所言“为治贵读书”,若不读书就无法明理,即文中所云“不读书无以明理”。其以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为例,云“周濂溪决南康事,日如流,非读书明理不能也”。
二、读圣贤言语
关于读书的选择,薛敬之认为,不能随便乱读,应读圣贤书,即该“读圣贤言语”,而“圣贤分明别是一段问学”。并且读圣贤言语之后,才能“见圣贤底分量”。比如,薛敬之赞同读儒家经典《论语》,他说“读《乡党》一遍”,则能“重见圣人一番”。并且要常读《论语》,“学者不可一日不读《论语》”,一旦读了《论语》,其结果就如其所云“一读之便消融多少渣滓”。而“读《孟子》之书”,“自觉底胸次与天地一般气象”,因为他认为“孟子是胸次大底人”,而对于孟子本人来说,“其发言自不觉其廓大”,读者只有亲自读了《孟子》,才能感觉其胸襟宽广。一人想要成为圣人,成为贤人,那就要读书,可以读《礼记》中的《大学》,这正如其言“学之成圣成贤,只好一部《大学》便了”。
薛敬之还鼓励读朱子之书,“不读《朱子全集》,无以知此老在当时为道扶持之艰难”。而“不读《朱子四书》,又无以知此老为天下立教见道之精粹”。读后,其大赞朱子“真孔孟后一大成之儒”。他还认为,“为学而不本诸尧、舜、周、孔,则非究心本领之学矣”。并且告诫读者“学者须知所学为何事”,这样“然后知所向慕”,结果“则其趋自不差谬”。否则的话,正如其言,“不然,学其学而非圣贤之学,不过成一鹘突人耳”。而且要注意,“凡读圣贤书,不可以俗心窥伺圣人大度”。
三、学应本诸道
作为理学家,薛敬之认为读书还应学道,才能提升个人水平,才能学有所获,若“学不本诸道”,“则所就终无过人之事”。并且,“言学不志于道”,则“不知所学者何事”。
至于学道,还得有所选择,要避俗就雅,学习圣人之道。薛敬之认为:“学者之造道,须掘得源头活水,然后流脉无穷,否则终为俗学而陷于汉唐陋习,其与圣贤立言教人何如哉?”并且认为:“有宋以来,学者入道,莫勇于吴草庐。朱子之后,一人而己。”
读书学道不在追求物质上的吃穿和美貌打扮,而在追求儒家之道,即薛敬之所云,“嗜学者,自不知隆外貌。苟言貌一饰,则放僻邪侈,无所不至,何足言学仲尼谓‘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
四、读书贵在自得
薛敬之认为,对于读书务求必得,否则不如不读书,难以知书中之境界。《思庵野录》云:“读书而不自得,终为皮肤之学,是犹及宫墙而不入,未知百官宗庙之富且美也。”而对书中之道,不读书自然无法了解,而读书不得其中之义,终究索然无味,即其所言“凡义理不自得,虽读书终无味,眼虽见口虽言,终为外物”。
因当时有学者觉得读书无味,自然无法有所得,更无法得圣人思想。正所谓“如今学者读书咀嚼无味,只是不曾有自得”。
读书不自得,只是当作说话而已,最终是一无所获。有的学者对于“得力处凡于圣贤所言或是非处”,“亦不曾见得善恶或利害处也”,更“不曾见得死活”,大概“泛泛只做场话说,终不亲切”。做学者应“须把圣贤言语在一边,声乐在一边,于其中见得个轻重,方为亲切有味,心自不能不然”。若“仰面顾鸟,回头应人”,虽“名曰读书”,最终“不知充腹者几希”。
五、读书贵在知要力行
《思庵野录》云:“读书不在多,贵在知要。”又曰:“知要不在言,要在力行。”由此可知,薛敬之认为读书并不在于读很多书,但一定要知道书之要害及道之关键,而且这些读来的道之要旨不在于嘴上宣传,要身体力行。正所谓“学不难,力行惟难”!反之,若“行之不力”,“则学亦不坚”。
为了能读书自得及知要力行,还得进行自身质量的修养,也就是对阅读素质的培养,才能在读书过程中“知要”,正如薛敬之所云,“学者读书知得涵养工夫,方见得学力有进处”。
六、读书须节气
在薛敬之看来,读书要培养气质之一便是要“节气”,正如其所云“学者切须要节气”,若“气但不节”,“则近名外慕之心生”,最终导致“流荡忘返,无所存主”,那么“其何以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而欲有以达古人之地哉”。
只要“学者到心洪大处,即是气质变”,这样之后,“气质变方可言学”。
因以为“志动气,气动志”,从学者读书实际看来,“而今人读书数日,为事所扰,便有数日收拾不上来,亦是动之也”。故而学者要“节气”。因此,薛敬之劝告“学者切患气易盈”,因为“志易满也”,也要防止“气易盈”,因为会导致“慕外之心重”,而“志易满”,则会“为己之心轻”。解决办法也是有的,薛敬之认为,“人之气量根于性,唯问学然后可充之”,而“人之骄吝乃气浮使然,知道者自无此状”。
七、读书可疗疾
由于学者读圣贤之书,能知其要旨而有所得,同时锻炼了读书涵养功夫,培养了“节气”能力,故这样的读书对人体本身也有益处,甚至能够治病。这正如《思庵野录》云:“读书亦可疗疾。”又云读书能“平其心,易其气”,自然就“无邪僻之干”。因此,薛敬之认为,为了要把书读好,用心是必要的,这对身体有好处,对所学道也是必须的,故曰,“学者第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与道畔”。又说,“为人之学放心也,为己之学存心也,心存则不知外之显晦,心放则不知内之轻重”。
在关学的发展历程中,薛敬之是个承上启下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与时代精神相一致,融汇理学各派思想,为关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思庵野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宇宙论、本体论,还是道德修养论,薛敬之都是在先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融汇自己的心得而生发独到之处。书中也涉及薛敬之的读书理念,如为治贵读书、读圣贤言语、读书贵在自得、读书可疗疾等,在当今应试教育、功利教育大行其道,学风浮躁的背景下,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