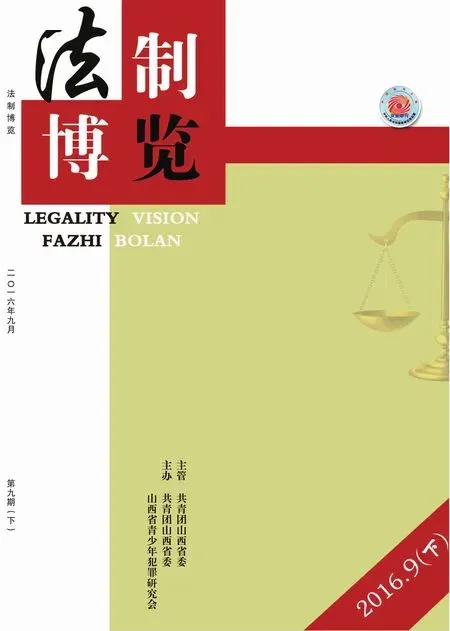法理学视角下我国公民迁徙权的形成与发展
杨 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70
法理学视角下我国公民迁徙权的形成与发展
杨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
我国没有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迁徙权,但由于迁徙权以公民在一地的选举、受教育、医疗等权利的实现表现出来,因此迁徙权的提出在现代法治社会已不可回避。本文将探寻我国公民迁徙权的由来与现状,从法理学视角解释公民迁徙权在限制与保护中的博弈、发展。
迁徙权;性质;限制与保护
特大城市居住证和积分制落户缓解歧视待遇带来的社会不公,城乡一体化建设去除城镇化过程中的身份差异,社会保障异地认证转移便利就业人口常态流动,都是在去除迁徙的阻碍。公民必须享有迁徙的权利,是研究劳动就业和城市化问题得出的必然的逻辑结论。[1]更进一步讲,在当前发展环境下,公民迁徙权利的保护应该落实到关乎公民未来生存发展和国家繁荣稳定的战略层面。
一、迁徙权的内涵与性质界定
迁徙权是指现代社会公民所具有法定的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定居、就业、生活的权利。从主流的学术研究来看,迁徙权的性质被界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但迁徙权已经延展到一些法律尚未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逐渐予以保障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权利,比如出于偏好的选择,故迁徙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
二、我国迁徙权的历史渊源
封建社会,礼的概念在社会群体中根深蒂固,人民长期束缚于宗族约束之下。[2]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是不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与联合,以及统治时期的贸易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这种迁徙并非人民的自生自发使然,而是受制于国家的对外战略。礼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迁徙的发生,甚至至今仍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因此,封建时期迁徙的权利化并没有形成。建国初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出台了一系列户籍管理的规定,新中国开始建立起自上而下、严格区分市民身份的户籍制度。农民有了土地,也受土地的束缚不轻易离乡,市民安于现有的温饱和受教育待遇。这种户籍管理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朴实本分品质,帮助新中国度过了困难时期。改革开放后这种束缚才逐渐松绑,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离乡打拼。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能意识,人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成为大多数人迁徙的动因,我国终于出现了迁徙权利化的概念。
三、限制与保护的并存与博弈
建国初至70年代,迁徙权以限制为主。改革开放后,随着资源在全国的自由流动,迁徙现象变得普遍,保护公民迁徙权就成为必要。限制与保护博弈并存的局面为我国各项民生事业的改革既提供了契机,也带来了挑战。首先,农民与市民身份导致的差别待遇违背了现代法治社会的法理基础。长期牺牲农业发展来支持工业发展使农民难以享受城市的发展成果。身份是特权社会的显著特征,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取代以身份为基础的契约,进而摆脱人治实行法治。[3]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基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就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发展权。为了消除城乡社会的身份差异,我国逐渐重视农村人口的人权事业,推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个体越来越自主独立,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分离,迁徙成为可能但现实困难重重。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中,人口不需要流动,家族这一社群基于血缘关系固定于地缘之上。[4]然而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促使人开始离开原有的社群和居所,插入到另一个社群和地域,血缘和地缘形成分离。但迁徙的人是以插入的形式进入到新社群,与新社群成员的语言、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等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成为产生矛盾的源泉。再次,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既促使迁徙的发生,又限制着人们的迁徙。人们抱着趋利避害的想法迁徙到新的地域,新的地域就必须接纳迁入者的一切生活生产需求。而新的地域容量有限,大量的涌入会导致人们享受公共服务的质量普遍降低、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以及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为避免这种无序,新地域的可容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政府通常就会采取控制手段规范稀缺资源的获得,防止本辖区内出现失范现象。
根据梅因的“法律应变机制”理论,迁徙权的限制或保障本身就是社会渐变和突变的产物,也必须适应社会的渐变突变。迁徙权的提出,形象地表明了现代法治的权利本位思想,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愈加自由自主,迁徙权甚至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基础性权利。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和人民认知和理性的日益提升,公民迁徙权作为关系公民生存与发展的综合性基本人权,在不久的将来在法律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1]冯兰瑞.论公民迁徙自由和宪政建设[N].中国经济时报,2003-4-7.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邱本,董进宇,郑成良.从身份到契约——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J].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1999.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6-94.
D921
A
2095-4379-(2016)27-0219-01
杨婷(1990-),女,汉族,山西吕梁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