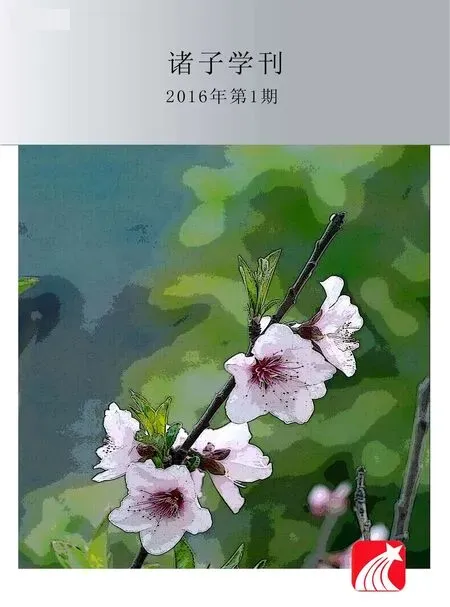儒家式與道家式:“新子學”政治自由論的兩種構建路向
——以康有為、嚴復為中心*
莊 沙
儒家式與道家式:“新子學”政治自由論的兩種構建路向
——以康有為、嚴復為中心*
莊 沙
中國現代思想史可謂又一“軸心時代”的開啓,康有為、嚴復無疑屬於現代具有開闢意義的“新子”,他們對古典諸子思想中的政治自由思想的詮釋構成了“新子學”的獨特内容。康有為主要從儒家的角度詮釋政治權利的古典根源,揭示了自主之權和先秦思想之間的内在聯繫,將權利理解為名分,又將之誤解為利益,大加撻伐。嚴復明確地從道家那裏發展現代政治自由思想,他將楊朱和莊周等同起來,為政治自由的展開奠定了個人主義的邏輯基礎,並將“在宥”解讀為自由,將老子詮釋為民主之道,成為道家自由主義的濫觴。康嚴兩位的詮釋顯示了“新子學”構建政治自由論的儒家式和道家式兩種路向。
關鍵詞 新子學 政治自由 權利 康有為 嚴復
中圖分類號 B2
“新子學”是方勇先生獨創的一個概念,引起了學界廣泛的反響*參葉蓓卿編《“新子學”論集》,學苑出版社2014年版。。筆者無意於對此概念作出全面的界定,而是想指出,本文所謂的“新子學”,一方面是對中國現代具有創造性思想家的肯定,認為他們也是新的“軸心時代”的重要人物,是可以稱為現代諸子的,或者説“新子”。顯然,在中國現代思想開啓的早期,康有為和嚴復是兩大代表人物;另一方面,本文也不是全面地討論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觀點。這種討論很有必要,但不是本文短短的篇幅所能够承擔。因此即便是為了寫作的方便,本文所説的“新子學”還有第二層含義,這就是“新子”對於先秦諸子思想的解讀,在本文語境中,顯然是對先秦諸子的政治自由思想的解讀。
如果説康有為更多地從儒家角度詮釋政治自由,那麽,嚴復主要從道家角度展開論述,可謂道家自由主義的濫觴。他們分别顯示了“新子學”構建現代政治自由的兩種典型路向: 儒家式和道家式。
一、 康有為: 儒家與現代政治權利論
在現代思想史語境中,政治自由往往首先表現為權利,政治自由甚至就是政治自由權的簡稱。
在康有為政治思想中,處於基礎地位的,首先是某種抽象的自主之權。他系統地揭示了自主之權和儒家思想之間的内在聯繫,表明一切古已有之;他還從儒家的角度將權利理解為名分,又將之誤解為利益;他還對各種具體的權利和儒家思想之間的關係作出了刻畫。
康有為指出人人有自主之權是現代文明的標誌:“夫人人有自主之權一語,今日歐美諸國,無論其為政治家,其為哲學家,議會之所議,報章之所載,未有不重乎是者。”“總之,人人有自主之權,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極點,無可訾議者也。”自主之含義即為自由、平等:“自主云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代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復湖廣總督張之洞書》,《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329、331頁。“人人有天授之體,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權。”*《大同書》,《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58頁。
康有為認為,先秦思想中已經具有豐富的主張自主之權的觀點。他説:“若夫人人有自主之權,此又孔、孟之義也。《論語》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言己有主權,又不侵人之主權也。孔子曰: 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有立達之權,又使人人有之也。孟子曰: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人直接於天而有主權,又開人人自主之權也。其他天爵自尊,藐視大人,出處語默,進退屈伸,皆人自主之。《易》曰: 確乎不拔,《禮》曰: 强立不反,貴自主也。”*《駁張之洞勸戒文》,《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337頁。其中溝通現代和傳統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同樣明顯的是,在此康有為對自主之權的理解是廣義的,其中也包含了“志”等實際上屬於道德哲學領域的内容。這從一個角度表明,康有為並未明確意識到權利本質上屬於政治哲學的範疇,不能和道德哲學相混淆。而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理解問題,無疑又從一個角度凸顯了康有為受到的傳統的影響。
同時,康有為也試圖重新解釋《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語,從中解讀出自主、平等的思想。他説:“中心出之之謂忠,如心行之之謂恕。違,去也。道者,人所共行也。必與人同之而後可。物類雖多,而相對待者,不外人己,同為人類,不相遠也。人莫不愛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張子所謂: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孔子告子貢以一言行終身者‘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與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故子思特揭之。”*《中庸注》,《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374頁。
康有為還指出,孔子的“群龍無首”表達的就是自由平等的觀點。“《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以元統天,則萬物資始,品物流行;以元德為政,則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所謂乾元用九,見群龍無首,而天下治。行太平大同之政,人人在宥,萬物熙熙,自立自由,各自正其性命。”*《論語注》,《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387頁。從歷史上看,後來熊十力也以“群龍無首”來表達其政治自由觀,無疑顯示了他和康有為思想之間邏輯上的聯繫。
康有為不僅在儒家的經典文本中解讀出了自主自由權,而且,他也從儒家有争議的文本中詮釋出了相關觀點。這主要體現在他對莊子的解讀中*一般總將莊子劃入道家,但在康有為那裏,莊子屬於孔子再傳弟子,故為地地道道的儒家。。康有為認為,莊子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其師為子贛之徒田子方。他説:“子贛不欲人之加諸我,自立自由也;無加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子贛蓋聞孔子天道之傳,又深得仁恕之旨,自顔子而外,聞一知二,蓋傳孔子大同之道者也。傳之田子方,再傳為莊周,言‘在宥天下’,大發自由之旨。蓋孔子極深之學説也。但以未至其時,故多微言不發,至莊周乃盡發之。”*《論語注》,《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411頁。
然而,與對儒家的高度讚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康有為認為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及法家的殘暴思想卻嚴重損害了自由。他説:“老子之學,分為二派: 清虚一派,楊朱之徒也,弊猶淺;刻薄一派,申、韓之徒也,其與儒教異處,在仁與暴,私與公。儒教最仁,老教最暴。故儒教專言德,老教專言力。儒教最公,老教最私。儒教專言民,老教專言國。言力言國,故重刑法,而戰國之禍烈矣。清虚一派,盛行於晉,流於六朝,清談黄老,高説元妙。刻薄一派,即刑也,流毒至今日,重君權、薄民命,以法繩人,故泰西言中國最殘暴。”*《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康有為全集》第二集,第108頁。顯然,中國要建設現代政治自由,必須批判老子的殘暴思想,繼承儒家思想。
不過,康有為指出,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卻是適合於大同世界的。换而言之,無為而治可以賦予民衆政治自由。“夫一統之世。不憂虞外患,不與人競争,但統大綱。以清静治之,一切聽民之自由而無擾之,雖不期冶而期於不亂,此中國秦漢二千年來之政術也。其政術如此。自蕭何立法,曹參隨之。曹參者,奉老子學者也,老子之治術,曰為者敗之,曰以無事治天下。故曰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在宥之説,在一切聽民之自由而勿干涉之。此在地球一統之時,民智大開,民德大化,則誠可矣。”*《官制議》,《康有為全集》第七集,第231頁。
當然,康有為同時指出,老子無為而治思想中所包含的愚民主張需要摒棄,不適合競争之世。他説:“其術又曰為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民安其居、樂其業、美其服,老死不相往來,如放鵝鴨於大澤中,聽其知鳥飲啄而已。若施於諸國並立之時,窮精角力,各視其團體之凝散與提絜之寬嚴以為强弱之對取,如以一統之漫無提絜、團體散涣而與諸國之團體結凝、提絜精嚴比較,猶驅市人烏合之衆而當百煉節制之師也,鮮不敗矣。”*同上。
然則何謂權利?以上論述也從某些側面揭示了康有為心目中的權利的内涵,不過,還比不上他從名分的角度來理解權利來的直接。
康有為從名分的角度來理解權利:“所謂憲法權利,即《春秋》所謂名分也,蓋治也,而幾於道矣。”*《日本書目志》,《康有為全集》第三集,第357頁。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他在戊戌變法時期為了引進現代權利觀念而做的解釋。這個觀念持續到後期。他指出:“中國政教之原,皆出孔子之經義,孔子作《春秋》以定名分,君不曰全權,而民不為無權,但稱其名而限其分,人人皆以名分所應得者而行之保之;君不奪民分,民不失身家之分,則自上而下,身安而國家治矣。憲法之義,即《春秋》名分之義也。中國數千年之能長治久安,實賴奉行經義,早有憲法之存。”*《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康有為全集》第八集,第411頁。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在遊歷了西方各國,見識權利觀念在現實社會中所引起的後果,尤其是經歷了辛亥革命,權利觀念已經成為中國人的某種基本的意識甚至是陳詞濫調之後,康有為一方面繼續着權利名分觀,另一方面,卻又將權利和廣義的利益等同起來。
此時的康有為對權利觀念深惡痛絶:“總之權利二字一涉,即争盜並出,或陰或陽,其來無方,入其中者,必狡險辣毒與之相敵,然後可。”*《與梁啓超書》,《康有為全集》第九集,第128頁。之所以如此,和他將權利理解為利益密切相關。他説:“歐美之新説東來,後生販售,不善擇别,誤購權利之説挾以俱來。大浸稽天,無不破壞,而險詖悍鷙之姿,遂悍然争利,而一無所顧矣。……嗚呼!今而後知孟子口不言利之慮患深長也,今而後知孔子憂不講學之救世深切也。”*《祭梁伯鳴文》,《康有為全集》第九集,第142頁。康有為將對權利思想的批判和孔孟對利的警惕聯繫在一起。不過,很顯然,“權利”和“功利”(即便是廣義的、作為某種效果的功利)是不同的,康有為有所混淆。
這種混同便導致康有為從利益的角度所展開的對權利思想的批評中包含着某種緊張。衆所周知,儒家也並非不講利,而是主張公利。因此,當康有為一般性地反對利益,從而試圖批評權利思想時,他一定程度上也將公利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問題在於,事實上康有為害怕權利觀念會導致對國家公利的損害。他説:“今舉國滔滔,皆争權利之夫,以此而能為國也,未之聞也。《孟子》開宗,《大學》末章,皆以利為大戒。使孔子、孟子而愚人也則可,使孔子、孟子而稍有知也,則是豈可不深長思也。鄙人至愚,亦知宫室飲食、衣服起居、親戚宴遊,無不待於財利焉,豈有異哉,但晝夜溺心,唯知利之是慕,則市怨寡恥,其反則悖人悖出為禍矣。……今吾國人唯權利之是慕,各競其私,各恤其家,而不知國;國既亡,身將為奴,而權利何有乎?”*《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説》,《康有為全集》第十集,第138頁。
這段話給我們一個啓發: 如果我們將權利理解為利益,康有為贊同的是國家層面上的權利,即國家公利。换而言之,由於權利本質上是政治自由權的簡稱,所以康有為更多的是在主張國家的自由。這又是和他一貫的救亡主張相一致的。當然,這並不妨礙康有為對具體的個人權利做出某種論述。只是説,和個人權利相比較而言,他更加傾向於國家權利。
那麽,從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康有為的認識又如何?他的解答也主要是儒家式的。
康有為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就認識到了自由權利包含的豐富内容:“法之革命也,天賦人權之説,載於憲法。美之獨立也,權利自由之書,布之列邦。其他各國所有者,曰人民言論思想之自由權,曰出版之自由權,曰從教之自由權,曰立會之自由權,曰居住移轉之自由權,曰身體之自由權,曰住所之自由權,曰信書秘密之自由權,曰産業之自由權。載之憲法,布之通國,人人實享其利益。”*《代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復湖廣總督張之洞書》,《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329頁。
以下對這些自由權利進行簡要討論。
每一位学生因其生长环境和所处的教育氛围不同所以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性格特点和行为习惯,每一位学生都有其长处和短板,想要达到最优质的小组合作学习效果就要把不同性格的学生安排在一个学习小组中。但是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我国推行时间较短,所以老师对这种模式还不是非常熟悉,在小组成员安排方面还做不到非常合理,经常会有小组成员之间性格相近,互相之间得不到补充提升的情况,小组成员安排不合理也是导致英语小组合作学习效果不理想的问题之一。
康有為清楚認識到言論自由權是現代基本自由權之一:“言論自由一義,為文明之國所最重。”*《劉、張二督致英沙侯電駁詞》,《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268頁。而且,他也指出言論自由的一大表現就是輿論對於政府的批評,其間也包含着社會進步的契機:“而政府當權之人,既擔荷一國之責任,則一國人皆得監察而督責之。故報紙之攻擊政府、攻擊官吏,乃報紙應行之義務、應執之權利,非政府官吏所得而禁也。而國家之所以日進文明者,亦恒由是。苟欲禁之,是為侵犯自由權利。為報館者,例得抗拒之。若上能禁,而下不能抗拒,則其國政紊亂,國勢之杌陧,不問可知矣。”*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從兩個方面指出現代言論自由和先秦思想之間的聯繫。其一,他指出現代的言論自由是對古代鉗制言論做法的反駁:“中國古來無報館也,而暴君污吏有偶語棄市之刑。近年以來,官吏之仇報館甚矣,屢次禁印行、禁售賣、禁閲讀、捕主筆、捕館東,數見不一見。究之報館何嘗能禁絶?公論何嘗能泯没?毋亦枉作小人已乎?”*同上。其二,康有為指出,先秦思想中其實也有强調言論自由的重要性的觀念:“古語曰: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同上。同時康有為認為避免自由言論之鋒芒所及,關鍵在於自身的道德修養。他認為,古語所説“止謗莫如自修”就是這個意思*《劉、張二督致英沙侯電駁詞》,《康有為全集》第五集,第268頁。。
不過,康有為也看到了言論自由權可能包含的消極成分,其所依據的是《書》中的觀點。他説:“臣有為謹案: 《書》稱無稽之言勿聽。泰西俗例,不得造無據之言,妄相是非,其罪極重。以謡言無據,最易惑人聽聞、顛倒是非、變亂黑白也。既惑聽聞,則能亂政,於用人行政關係極大,故尤惡之。”*《日本變政考》,《康有為全集》第四集,第116頁。雖然康有為説這段話的背景是在鼓勵光緒皇帝以雷霆手腕一心一意變法,但其中包含的對於言論自由的觀念似乎也有某種一般性。
由上可知,康有為一方面意識到了言論自由作為現代政治自由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看到言論自由不能成為誹謗的口實,而且兩方面都能在先秦思想之中找到相應的根據。那麽,言論自由的限度何在?這個問題似乎尚未得到康有為深入思考。某種意義上,康有為更多的是借助先秦的相關言論來表達具體的立場和觀點,而對於其中所包含的一般性的問題則似乎缺少反思。
除了言論自由權之外,信教自由無疑是現代政治自由的一項重要内容。康有為認為孔子有信教自由的觀點:“蓋孔子之道,敷教在寬,故能相容他教而無礙,不似他教必定一尊,不能不黨同伐異。故以他教為國教,勢不能不嚴定信教自由之法。若中國以儒為國教,二千年矣,聽佛、道、回並行其中,實行信教自由久矣。”*《中華救國論》,《康有為全集》第九集,第327頁。
二、 嚴復: 道家自由主義的濫觴
如果説康有為主要是從儒家的角度詮釋現代政治自由,那麽,嚴復的特點尤在於從道家的角度構建現代政治自由,反而對儒家的重要觀念比如仁政有所批評。
話題要從現代政治自由的個人主義基礎説起。
從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來看,個人主義是其理論基礎。這點《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英] 阿巴拉斯特著、曹海軍譯《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篇之“自由個人主義的基礎”。的作者説得非常清楚。自由主義首先設定了原子式的個人,在原初狀態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天賦的權利,為了生存和發展,人與人之間勢必發生鬥争。長期的鬥争所導致的結果是每一個人不僅自身的發展不可能進行,而且,自身的生命也處於岌岌可危之中。為此,人與人之間訂立了契約,組建了社會、政府、國家。也就是説,社會、政府、國家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利而存在的,它們不得侵犯個人的自由權。這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路。顯然,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中,政治自由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
嚴復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在《民約平議》中,嚴復近乎開天闢地地介紹了《社會契約論》的大意。。事實上他對原初狀態有自己的描繪:“自繇者凡所欲為,理無不可,此如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繇界域,豈有限制?為善為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群而後,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强權世界,而相衝突。”*嚴復《〈群己權界論〉譯凡例》,《嚴復集》(1),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32頁。“如有人獨居世外”這顯然是中國特有的説法,其實對應的就是西方的原初狀態。雖然嚴復在此説道“為善為惡”的問題,表明這段話還具有除了政治自由之外的其他含義,然而,毋庸置疑,個人主義在政治自由中的前提性地位得到了確認。另外,嚴復翻譯的密爾的《論自由》其基本思路就是從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角度高揚個人主義。雖然現有的研究表明,嚴復在翻譯的過程中其實和翻譯《天演論》一樣,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譯,但是,嚴復還是深知個人自由的道理的,他並未完全以國家的自由壓倒、替代個人自由*參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主義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其實,無論嚴復的真實意圖是高揚個人自由,將之置於國家自由之前,還是因為當時中國特殊的生存境遇,而將國家自由的重要性置於個人自由之前,這樣的争論終究顯示了一點: 嚴復認識到了個人自由的重要性。事實上,他比自由主義還要更加激進: 個人自由不僅僅是組建社會、國家的邏輯前提,而且,也是國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當然,這麽措辭很容易又引起嚴復研究中的另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嚴復究竟是把個人自由當做價值本身,還是當做實現國家富强的手段,僅具有工具價值?然而,這種問法本身恐怕也是需要反思的。個人自由和國家富强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兩者本質上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個人自由是國家富强的原因和動力;另一方面,富强的國家又擔保了個人自由更好地得以實踐。不錯,從其原始教義上看,自由主義也始終提防國家權力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侵犯,可是,在更大的範圍内,自由主義還是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的區域。因此,富强的國家對於個人自由而言,雖然也可能是一個危險,但由於這種富和强無疑也具有對外的向度,從而保衛了内部個人的自由不受外族、外國的侵犯,所以,它對個人自由的保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參崔宜明《個人自由與國家富强》,《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1年第3期。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了民族國家如何保障個人自由的機制,此即民主機構。英國當代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揭示出民主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内在聯繫: Although not all nationalists have been democrats, there is an implici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deas: Nations are the units within which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hould operate, and since each member of the nation has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to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mocracy becomes the natural vehicle for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David Miller: Nationalis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Edited by John S. Dryzek, Bonnie Honig & Anne Philli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32.)這些都為個人自由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積極關係提供了論證。。
我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來討論嚴復的個人主義的。衆所周知,嚴復喜讀《莊子》。晚年嚴復做了一個大膽的揣測,他從音韻學的角度論證先秦時代主張極端個人主義的楊朱其實就是莊周。他説:“頗疑莊與楊為疊韻,周與朱為雙聲,莊周即孟子七篇之楊朱。”*嚴復《〈莊子〉評語》,《嚴復集》(4),第1125頁。他明確説道:“莊周吾意即孟子所謂楊朱,其論道終極,皆為我而任物,此在今世政治哲學,謂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同上文,第1126頁。照我們看來,嚴復將莊周詮釋成楊朱,其根本意圖不在於考證莊子和楊朱的關係問題,而是試圖在中國先秦思想中發現個人主義的思想,從而為其政治自由觀的建構提供邏輯基礎。
這種思路顯然是受到了密爾很大的影響。個人主義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個人和個人之間的界限之所在是後起的問題。首先必須確定個人的本體論地位。回首中國古代,雖然儒家也講“為己之學”,將自我(己)放到了崇高的地位;然而,深受傳統浸染的嚴復知道還有一個人物對個人的看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楊朱。楊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這句話可以作多重的解釋,既可以理解為對群體的漠視乃至否定,也可以理解為對個體自身的高度重視,甚至以一種極而言之的方式表達出這個觀點: 哪怕是身上的一個毫毛,也不是可以隨便與人的,何況作為自身自由權利的各種規定?顯然,嚴復採取的是後面一種解釋路徑。
這裏需要再三强調的是,個人主義的楊朱,或者説莊周,不是道德上自私自利的楊朱或者莊周。因為嚴復這裏的個人主義不是倫理學意義上的,而是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它指向的是對個人種種自由權利的肯定。從倫理學的角度看,嚴復從來對群體予以高度的重視。他所推崇的忠孝節義等傳統道德顯然包含了對群體的關懷*嚴復《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嚴復集》(2),第343~344頁。。這個證據從另一個角度否定了這樣一種猜測: 嚴復稱讚楊朱或莊周的個人主義,看重他的為我主義,俗稱自私自利。
嚴復終於從莊周那裏發現了現代自由主義的邏輯基礎: 個人主義。這個發現得益於其創造性的改編: 楊朱居然就是莊周。我們也能體會嚴復的苦衷,這種近乎移花接木式的做法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如果缺乏莊周飄逸的思想作為深厚的後盾,楊朱僅僅是一個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的吝嗇鬼而已,不僅在道德上飽受譏評,而且,這種個人主義難以引發其他的邏輯後果。畢竟,楊朱的文本資料太少,而政治自由不是只有個人主義一層單調的含義。它的内涵十分豐富。而這正是嚴復接下來要闡釋的内容。
1. 自由就是在宥。
從消極的層面講,自由就是以他人的自由為界。但這並不意味着自由只是退守。事實上,嚴復所理解的自由之基本含義是個體主體性的發揮。值得考量的是,晚年的嚴復試圖在《莊子》文本中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對個體主體性的肯定。在詮釋《莊子·應帝王》時,嚴復説:“自夫物競之烈,各求自存以厚生。以鳥鼠之微,尚知高飛深穴,以避矰弋熏鑿之患。人類之智,過鳥鼠也遠矣!豈可束縛馳驟於經式儀度之中,令其不得自由、自化?”*嚴復《〈莊子〉評語》,《嚴復集》(4),第1118頁。當然,嚴復此處所詮解的個體主體性顯然主要是一種生物本能,接受了進化論的嚴復進而將作為本能的主體性上升到了政治主體性的高度。
還是在《應帝王》的詮釋中,嚴復認為真正的帝王是主張“在宥”,聽民自治的。他説:“郭注云,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此解與挽近歐西言治者所主張合。凡國無論其為君主,為民主,其主治行政者,即帝王也。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聽民自為自由者,應一切聽其自為自由,而後國民得各盡其天職,各自奮於義務,而民生始有進化之可期。”*同上。
在較早時候討論政黨的一篇論文中,嚴復指出主張個人主義的政黨的思想内容是“一切聽民自謀,不必政府干涉而已”*嚴復《説黨》,《嚴復集》(2),第240頁。。值得注意的是,嚴復在此還運用了一個顯然來自《莊子》文本中的概念:“在宥。”他説:“再進亦不過操在宥勿治之學理,謂一切聽民自謀,不必政府干涉而已。”*同上。也就是説,嚴復將自由主義的學理理解成了“在宥”。
結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嚴復認為,政治自由的内涵之一即“在宥”。“在宥”也即使得民衆自己發揮政治主體性。嚴復同時認為,能够這麽做的帝王才是真正的帝王;或者説,真正的帝王是應該這麽對待民衆的。
2. 嚴批儒家的“仁政”思想。
如果我們從更廣的範圍内看,就會發現嚴復對民衆的政治主體性的肯定已經超越了帝王的苑囿。即,實際上他已經得出了否定帝王乃至否定仁政的結論*當然,嚴復的思想是複雜而矛盾的。有時他又肯定了帝王存在的必要性,有的學者比如蕭功秦甚至認為嚴復是一個新權威主義者。這點下文會分析。。這個結論也是推崇民衆的政治主體性必然的結果。嚴復説:“自由云者,不過云由我作主,為所欲為云爾。其字,與受管為反對,不與受虐為反對。虐政自有惡果,然但云破壞自由,實與美、法仁政無稍區别。虐政、仁政皆政也。吾既受政矣,則吾不得自由甚明,故自由與受管為反對。受管者,受政府之管也,故自由與政府為反對。”*嚴復《政治講義》,《嚴復集》(5),第1287頁。無疑,當嚴復説“自由與受管為反對”時,他對自由的詮釋有點極端化,因為在以他人之自由為界的自由中,法律為自由做出了規定和劃界,但法律在廣義上也是一種管制。但讓我們暫時撇開這些問題。嚴復在此透露的一個意思值得高度重視: 仁政之下個體很可能没有自由。
嚴復以百年前的南美洲為例來説明這點。他説:“至政府號慈仁,而國民則不自由之證,請舉百年前之南美洲。當時西班牙新通其地未久,殖民之國,為耶穌會天主教士所管轄,此在孟德斯鳩《法意》嘗論及之。其地名巴拉奎,其政府為政,無一不本於慈祥惠愛,真所謂民之父母矣。然其於民也,作君作師,取其身心而並束之,云為動作,無所往而許自由,即至日用常行,皆為立至纖至悉之法度。吾聞其國,雖男女飲食之事,他國所必任其民自主者,而教會政府,既自任以先覺先知之責,唯恐其民不慎容止,而陷於邪,乃為悉立章程,而有摇鈴撞鐘之號令,瑣細幽隱,一切整齊。夫政府之於民也,如保赤子如此,此以中國法家之言律之,可謂不溺天職者矣。顧使今有行其法於英、法、德、奥間者,其必為民之所深惡痛絶無疑也。且就令其政為民所容納,將其效果,徒使人民不得自奮天能,終為弱國。總之,若謂自由之義,乃與暴虐不仁反對,則巴拉奎政府,宜稱自由。脱其不然,則與前俄之蒙兀政府二者合而證之,知民之自由與否,與政府之仁暴,乃絶然兩事者矣。”*嚴復《政治講義》,《嚴復集》(5),第1283頁。
這段的意藴十分豐富。這裏嚴復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民之自由與否,與政府之仁暴,乃絶然兩事者矣”,然而,我們顯然也能看出仁政之下民衆的政治主體性受到戕害這一事實。同時,雖然南美洲的遭遇緣於其宗教的背景,似乎和中國傳統社會中宗教甚弱没有多大關聯;然而,嚴復已經認識到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相似的因素,“如保赤子”的字眼便是來源於傳統;更加明確的是,嚴復指出,從中國法家的角度看,政府實行仁政的做法“可謂不溺天職者矣”。也就是説,嚴復在這段話中至少隱含了這樣一層意思: 把民衆當孩童一樣管理的做法,即便是出於善意,也是一種對政治主體性的傷害。這個見識實在是深刻。
對於仁政可能包含的弊病,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思想家薩托利也有所認識。仁政的特色在於一方面剥奪民衆的政治權利,另一方面,對民衆的民生高度重視,並由此獲得政治合法性。薩托利指出,僅僅依靠民享(民生)並不能證明一個政府是民主政府。他説: 在林肯關於民主的三個因素中,“只有第三個因素‘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民享)是不含糊的,‘民享’明確地是指為了他們的好處、他們的利益、他們的福祉。但過去有許多政權從不自稱民主制度,卻宣佈自己是‘民享’的政府。”*[美] 薩托利著、馮克利譯《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但是,薩托利隨後説:“今天,共産黨的專政制度自稱民主,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顯然是錯誤的,懷有極大的偏見。
内在地看,嚴復對仁政的批評與他道家自由主義的立場相關。其實當嚴復指出自由與否和仁政惡政無關時,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在為惡政辯護,因為其言外之意可以是惡政之下也有自由。但此處就其對仁政的批評而言,矛頭最終所向往往涉及帝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嚴復對民衆政治主體性的强調包含了否定帝王的傾向。但同時要指出的是,這種傾向又被嚴復自己扼殺了。
3. 嚴復認為老子主張民主之道。至少具有兩個層次:
層次一: 嚴復認為老子雌弱的哲學為民主提供了本體論的論證。《老子》説:“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嚴復的詮釋是:“以賤為本,以下為基,亦民主之説。”*嚴復《〈老子〉評語》,《嚴復集》(4),第1092頁。無疑,這是肯定了民衆在政治活動中的基礎地位。
層次二: 嚴復認為老子的無為論展示了民主的真實内涵。衆所周知,老子主張無為,但所謂的無為不是毫無作為,而是指君王充分尊重民衆的主體性,不任意發號命令,這樣就能獲得巨大成就。此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子》三十七章)。這種觀點,頗類於自由主義盡量縮減政府權力,而讓公民自身發揮自由權利。顯然,這又是和他對仁政説戕害民衆政治主體性的主張相一致的。
餘 論
總體來看,嚴復在詮釋政治自由的時候當然也離不開對儒家思想的觀照和反思,但其根本特點則在於從道家出發為政治自由作出前提性論證,並一定程度上展開其某些内涵。正是這點,使他與康有為有所不同。上文已述,康有為雖然也没有忽略莊子,並且也認為莊子主張“在宥”,但他實際上視莊子為儒家。康、嚴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先秦儒道二家與現代政治自由之間的内在關係,展現了“新子學”詮釋政治自由的兩種典型路向: 儒家式和道家式。前者主要為現代新儒家繼承,後者為胡適、殷海光、陳鼓應以及當下若干中國自由主義者所發展*參拙作《論“道家自由主義”三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2期。。他們在雙重意義上豐富了“新子學”的内涵: 一方面他們本身構成了“新子”;另一方面,他們的思想的闡發是以與古典諸子的對話為表現形式的。
[作者簡介]莊沙(1978— ),本名蔡志棟,上海人。中國哲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傳統思想研究所暨哲學學院副教授。目前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哲學史,已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①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先秦諸子與中國現代自由研究"( 批准號: 10CZX029) 、上海哲社一般課 題“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跟蹤研究"( 批准號: 2015BZX003) 、國家社科重點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的傳統文化根基研究"( 批准號: 14AZ005) 、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馮契哲學文獻整理和思想研究"( 批准 號: 15ZDB012) 以及上海市高峰高原計劃資助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