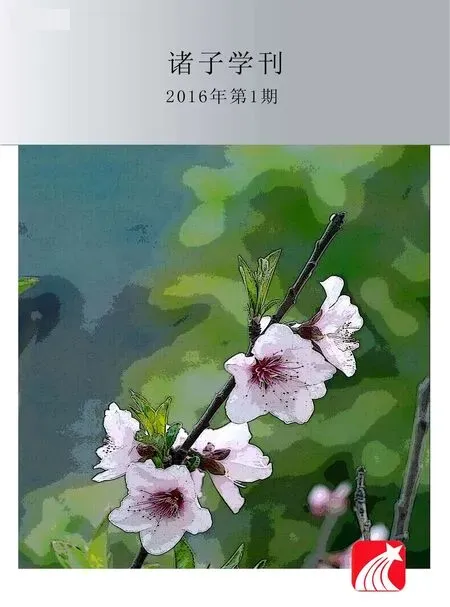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新子學”與雜家
張雙棣
“新子學”與雜家
張雙棣
“新子學”即當今形勢下的諸子學,或者説即諸子學在新形勢下的發展。我們現在討論“新子學”,應該充分借鑒雜家吸納百家的做法,本着積極的、公開的、寬容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學説,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舍之。
關鍵詞 新子學 諸子學 雜家
中圖分類號 B2
昨天看了林其錟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的最後呼吁大家,在繼承優良傳統,發掘中國文化資源,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構建中華現代文化體系中,應該重視和發掘過去長期不被重視的雜家文化思想資源。對於他的這種看法,於我心有戚戚焉。去年會上,我談到先秦諸子與雜家的問題,所以想就這個問題再説幾句。
我們研究諸子學,大多比較關注儒、墨、道、法等,對於雜家,大家關注得比較少。我覺得,雜家在諸子各家中,更具有開放性和多元性以及服務於現實的特點,它批判性地兼採各家之長,兼收並蓄,融會貫通,形成相似於各家又有别於各家的獨特的思想體系。
春秋戰國時期,各家思想相互交鋒,相互辯難,形成百家争鳴的局面。在交鋒與辯難的過程中,各家自有分化,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各家之間又互有滲透。吸收他家以為己有,早見端倪,以後逐漸成為一種趨勢。雜家的形成,就是這種趨勢的必然結果。當然,也是社會變革的一種需要。
《漢書·藝文志》是這樣描述雜家的:“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雜家的特點是,兼顧儒墨,融合名法,知道國家政體、王者政治必須將各家融會貫通。班固對雜家的論述是全面恰當的,絲毫没有貶損之意。治理國家,不能專守一家之説,而必須取各家之長,融會貫通,才能稱得起是王者之治。雜家政治家,正是符合這一標準的。
有人没有理解班固對雜家的説明,對雜家産生錯誤的理解,以為“雜”是雜湊的意思,以為雜家是雜湊各家思想拼合而成,没有自己獨立的體系。這種看法在學術界和思想界長期占據着主導地位,從而使雜家研究長期處於不被重視的境地。只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雜家研究才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出現了一些研究專著,但是與其他各家的研究比較起來,仍然顯得薄弱。
我們以雜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為例,看看雜家的特點和雜家研究的意義。
在《吕氏春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體系是非常系統的,甚至是其他諸子著作所不能比擬的。漢代高誘極其推崇這部著作,曾為它作過注解。在《吕氏春秋序》中,他説此書“大出諸子之右”。這部書的思想雖大都取自各家,但不是簡單的抄取,而是有所取舍,並將所取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有機地構築成自己的思想大廈。《吕氏春秋·用衆》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正好説明雜家的由來和體制。
《吕氏春秋》是吸收各家思想之後所形成的自己的完整的思想體系。它吸收了老子、莊子的道家思想,也吸收了儒家子思、孟子、荀子的思想,還有墨子、孫子、韓非子、管子的思想。我在《吕氏春秋譯注》的前言中曾經説過,《吕氏春秋》是以道家思想為基礎、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並融合各家之長的一部自成體系的著作,是一套有綱領、有規劃、可實施的治國方略。
《吕氏春秋》吸收或融合各家思想是自覺的、公開的、批判性的、有所揚棄的,是緊密結合當時政治、軍事鬥争現實的。
《吕氏春秋》吸納道家的思想,並作為它的哲學基礎。漢代高誘《吕氏春秋序》説:“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吕氏春秋》吸納了道家的“道”,不過他認為道不是虚無,而是“一”,即“太一”,或即“精氣”,這種精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基本物質。《吕氏春秋》也吸納了老子的“無為”思想,並限定在君道方面,他提出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主張。君道無為是前提,只有君道無為,才能做到臣道有為。對於老子的某些思想,吕氏認為與時代發展相左的,則棄而不采。比如老子提倡小國寡民,這與當時秦帝國統一天下而形成的大帝國,完全不相適應。吕不韋是要為統一的大帝國製定治國方略,如何能够採用小國寡民的思想?所以他必然將其舍棄。吕不韋作為統一大帝國的宰相,大帝國的管理者,他的態度是積極的,向前看的,因此對於道家的某些帶有消極色彩的東西,他也只能棄而不取。
《吕氏春秋》大量吸納了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吕氏春秋》也講到仁,《愛類》説:“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儒家把孝弟看作仁德根本,有子説:“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吕氏春秋》也很重視孝道,《孝行》説:“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吕氏春秋》受孟子民本思想的影響很深,它强調民衆是國家安危存亡的根本和關鍵。它説:“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又説:“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同時,《吕氏春秋》還吸納了儒家關於教育、音樂教化等思想,在《三夏紀》中突出闡述了教育和音樂對治國的重要作用。
《吕氏春秋》也很重視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在秦國一直處於獨尊的地位,吕不韋的門客中就有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但吕不韋對於法家思想多有改造或批判。法家强調法的重要,强調耕戰的意義,把它作為治國的根本,同時强調法、術、勢綜合運用。法家不重視德化,不重視賢人。《吕氏春秋》則强調德治為本,賞罰只是輔助手段,同時特别强調用賢,認為求賢用賢是實現君道無為的重要條件。《吕氏春秋》也吸納了法家法後王的思想,主張與時俱進,隨時變法。
《吕氏春秋》吸收了墨家的節葬思想,主張薄葬,但否定了他的非攻思想,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義兵説。這是根據當時秦國政治、軍事鬥争需要而採取的做法。主張節葬是為國家積累財富;反對偃兵,是因為秦國正在以軍事手段推進統一六國的鬥争。吕不韋認為,秦國統一六國的戰争是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是義兵,是不能停止的。
《吕氏春秋》廣泛吸納各家有用的東西,即使是方技類的内容,也兼而採之。比如它有專講農業耕作種植技術的篇章。
《吕氏春秋》以後的雜家著作,都遵循包容、兼收並蓄、服務於現實的傳統。我們甚至看到,儒家獨尊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也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這種雜家風格。
“新子學”,即當今形勢下的諸子學,或者説即諸子學在新形勢下的發展。我們現在討論“新子學”,應該充分借鑒雜家吸納百家的做法,本着積極的、公開的、寬容的態度,對待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學説,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舍之。
一、 建立“新子學”,首先要徹底瞭解傳統子學的内涵與真諦,釐清每一子産生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從而為“新子學”的建立奠定基礎。正如吕不韋召集天下各國智略之士,其中自然包括各個學派的人士,以是集思廣益,作為完成《吕氏春秋》的第一步。
二、 建立“新子學”,要積極地研究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不管是西學還是東學,不能有畏縮感、自卑感,也不能有傲慢和輕視的態度,我們要建設的是强國思想文化的基礎建築,應該有這種不卑不亢的自信。正如吕不韋要規劃秦統一大帝國的治國方略,正是本着這種精神,去吸納各國各家的思想,去採擷各家成熟的成果,而為己所用。
三、 建立“新子學”,要將傳統與現代、外域與本土有機地融合,傳統要為現代服務,外域要為本土服務,也就是説,要從傳統與外域的思想文化中吸取營養和智慧,為當今社會的政治文化注入活力。正如吕不韋從前代和當代、從秦國和六國的思想文化中汲取可用的成分那樣。
四、 建立“新子學”,要特别着眼於創新,不能墨守成規。時代是發展的,社會是進步的,我們的思想文化建設不能只停留在一個層面上,必須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創新,是思想文化建設的生命,也是學術進步的生命。《吕氏春秋》政治思想體系的建立,就是吕不韋創新思想的産物。
我們説“新子學”的建立要借鑒雜家的做法,並不是因襲雜家。首先,還是諸子多元的、獨立的發展,在諸子獨立的發展過程中,借鑒雜家的寬容的、兼收並蓄的做法。諸子多元的發展應該是“新子學”首要工作。在諸子多元發展的基礎上,會産生統合的需求,這時會産生新的雜家。
[作者簡介]張雙棣(1944— ),男,北京人。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淮南子校釋》《淮南子用韻考》《吕氏春秋辭彙研究》《吕氏春秋譯注》(合著)《吕氏春秋詞典》(合著)《王力古漢語字典》(參著)《古代漢語字典》(主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