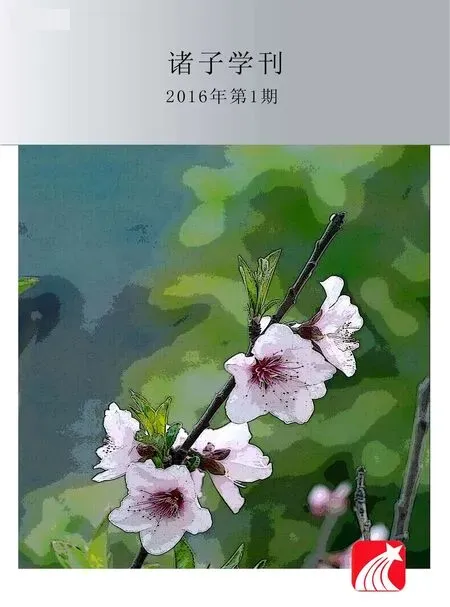現代學術視野下“新子學”的困境與出路*
何浙丹
現代學術視野下“新子學”的困境與出路*
何浙丹
“新子學”作為一個新興的概念,目前正處於困境與出路並存的狀態。從現有的情況來看,它應當明確自身的基本内涵與構成,進一步開拓研究方法論層面的創新,並及時調整部分理念以便更好地應對當前時代的諸多社會課題。
關鍵詞 新子學 傳統文化 現代學術 學術轉型 方法創新
中圖分類號 B2
“新子學”是近年來傳統學術界提出的一項新話題。在其概念産生之初,諸多現代文化研究者曾給予較多關注,並表示出對其銜接古今、打通中西的期待。但不久之後,來自相關領域的聲音稍有沉寂。這種先熱後冷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相關概念存在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其自身發展慣性中帶來的深層次學理問題。
應該説,作為一個新興的概念,“新子學”目前正處於困境與出路並存的狀態。如果從現代學術的基本要求看,它可以進一步明確自身的内涵與構成,同時提升自身學術理念與方法論的創新,並及時調整部分理念以更好地應對當前的諸多社會課題。它在現階段所呈現出來的一些特點,雖然可能使其在此後的發展中陷入一定的困境,但同時也是其發展的契機,可以創生出新的生長點與可能性。
一、 對自身認知的曖昧
總體上,“新子學”强調其自身是在繼承傳統子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但關鍵是目前對傳統子學的内涵界定尚未取得共識。
方勇先生在《“新子學”構想》中强調:“所謂子學之‘子’並非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而應是思想史‘諸子百家’之‘子’。”*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14版。思想史上的“諸子百家”範疇一般與馮友蘭提出的“子學時代”相對應,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將中國思想史分為“子學時代”、“經學時代”等,前者從孔子至淮南子,後者自董仲舒到康有為。方先生對該觀點是加以繼承的,《“新子學”構想》便稱引其“在中國哲學史各時期中,哲學家派别之衆,其所討論問題之多,範圍之廣,及其研究興趣之濃厚,氣象之蓬勃,皆以子學時代為第一”的觀點。此後《再論“新子學”》又再次提及馮友蘭“子學時代”概念,指晚清為“經學時代之結束”,强調“經學時代重回到了子學時代”*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15版。。應該説,方先生對子學範疇的界定是在繼承馮友蘭觀點的基礎上又加以拓展,將兩漢時期的思想家都囊括在内。但對於兩漢之後的哲人是否為“諸子”則不置可否。比如《“新子學”構想》中只是提到説:“魏晉以後,在詮釋、發揮和吸收經學文本與子學文本並自我解構的基礎上,……諸子學不斷汲取外來學説,又陸續産生了以何晏、王弼、周敦頤、二程、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人學説為代表的諸代子學(或凖子學)著作。”這裏模糊地使用了“凖子學”這個説法,但至於哪些屬於“凖子學”著作,以及它和子學之間的區别和界限是什麽,均未明確。即使到《再論“新子學”》中,也只是表示:“‘子學精神’即是大變革大轉型時代所孕育的精神,晚周三百年的思想冒險,充分展示了它典重與恣肆並舉的多面性。……‘新子學’就是要繼承這一傳統,發揚多元並立的‘子學精神’,以面對時代的諸多課題。”相關論述也依然强調“晚周三百年”,涉及魏晉及之後學術時,依然不置可否。對子學範疇界定的曖昧,牽涉到“新子學”之“子”的不明確。
當然,“新子學”作為一個公共的學術課題,它也同時向所有學術研究者開放。因此,其他學者對其内涵的解構與建構,均是其内在的構成部分,本文也一併予以考察。
歐明俊先生在討論相關問題時曾對“子學”給出較為直接的鑒定。他認為:“凡著書立説自成一家之言者,除經學外,統稱子書,研究子書的學問稱為‘子學’或‘諸子百家之學’或‘諸子之學’或‘諸子學’。”*歐明俊《“新子學”界説之我見》,《諸子學刊》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16頁。在此基礎之上又對子學作出廣義與狹義的區分。自廣義説,其稱引章太炎《諸子學略説》“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為主”的看法,指兩漢以後思想家著作以及研究諸子著作者皆可歸入子學;自狹義而言,則稱引梁啓超“漢以後無子書”的觀點,指先秦諸子百家學術。但對“新子學”之“子”到底是採用廣義還是狹義之説,也未給出明確看法。不過,從《“新子學”界説之我見》一文的基本思路來看,歐先生也是倡導以所謂中華固有學術為前提,魏晉以後中國佛學、近代結合西方思想的中國新學術是不包含在他所討論的範疇中的。
相比較而言,玄華對“子學”觀念的界定更具有顛覆性*玄華《“新子學”: 子學思維覺醒下的新哲學與系統性學術文化工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81~94頁。。他首先是繼承了李學勤先生等對馮友蘭“子學時代”、“經學時代”先後次序的質疑,强調“經學”先於“子學”,並認為“經學”起源甚早,而“子學”是對它的否定與消解,且兩漢到晚清是兩者相争的時代,最後“子學”不斷發展,“經學”日益消散;其次在内容構成上,他認為“子學”自身具有開放性,先秦諸子、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及其相關流派等皆是其組成部分。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魏晉以後的中國佛學、晚清民國的中國“西學”(或稱“新説”),乃至“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思想及相關流派等,皆是“子學”在各自時期將中國傳統學術與西學相結合發展出的新内容,均是“子學”的構成部分。
如果説玄華的看法打破了學界對“經”、“子”的常規認知,那麽高華平先生的“子”論則更為天馬行空。他認為“子學”就是獨立平等的思想創作研究之學:“當下我們‘新子學’的‘子’,固然是以往中國思想史上的‘為學’諸子,但更應該指當代具有獨立人格精神的知識分子。這裏强調的不是學科分類意義上的一種界定,即不管是從事文科、理科或自然科學的學者,都應該是‘新子學’之一‘子’。……在當代從事諸子學研究者固然是‘新子學’之一‘子’,……從事政治、經濟、法律、文學、歷史、文化,乃至於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倫理等屬於自然科學或部分屬於自然科學的學者,只要他們的研究與思想史有關,就也應該是‘新子學’中之一‘子’,而且他們很可能是為數衆多和更為重要的‘諸子’。”*高華平《“新子學”之我見》,《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第54~58頁。
在高先生看來,“新子學”的“子”為獨立平等的思想者個體,他們所從事的能充分體現作者獨立平等的學術就是“新子學”。以此出發,它的内容不僅包含了傳統“子學”,也包含了對“西學”的消化。高先生所謂“西學”,包含東漢傳入的佛教、近代以及當下也在不斷傳入的西方學術。在此,“新子學”與它們的關係是:“我們構建的‘新子學’不應該成為與‘西學’相對應的關係,更不是相對立的關係。在某個‘新諸子’之一‘子’的學術思想中,‘西學’可以與他堅守的‘中學’觀點相對應甚至相對立;但在作為整體的‘新子學’中,‘西學’應該已經融匯於其中,並已成為它的一部分或它的血肉。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子學’之‘新’,就在於它乃是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學術。”*同上。即“新子學”是當下“新諸子”消融傳統學術乃至西學的一種會通。
由上可知,在“子學”的構成問題上,以方勇為代表的,是將“子學”視作中華固有文化的産物,它有着産生與完成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下限是先秦或兩漢;而歐明俊的廣義“子學”論,則將時間下限延伸至晚清;玄華則認為“子學”不存在一個所謂完成的時代,因為它本身從來就是一個未完成品;高華平則將“子學”理解為獨立平等的思想創造與研究。以此為基礎,對“新子學”基本構成的認知便各不相同。
總體而言,“新子學”之“新”本就内在地包含了重新定位“子學”這一本質訴求,“新”不在於一味地割裂過去繼而推出一個全新的事物,也不是僅僅將歷史滯留於過去而不再走入當下,而是帶着歷史的生命感融入當下,繼續存在。因而“新子學”並非僅僅立足於當下之學術,它同樣是帶着歷史的生命感走入當下,是歷史與當下互為一體之學問。以此來重新審視“新子學”的基本構成,就不至於使得傳統學術的發展進入歷史斷裂的困境。在此,“新子學”自身的構成需要考慮更加多維的關係,在古今、中西的相遇中獲得新的學術視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性”的延伸是其自身發展的深層次需要。當然,這種延展也不應該是無底線的擴容,以致取消了自身的邊界。
二、 在徘徊中的方法論創新
方勇先生認為“子學”研究,乃至整個中國傳統學術研究都存在一個盲目崇拜西學並以之為金科玉律的大背景。無論是近代以來受西方“賽先生”的影響而倡導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還是受西學人文精神刺激而由“考據”走向“義理”,中國傳統學術已經脱離它固有的格局,而照搬西方的學術理念,結果是逐漸喪失自身的理論自覺,淪為西學的“附庸”。“新子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端,自覺認識到中國學術的特殊性,因而“從客觀歷史出發,在辯證之下對其進行繼承發展,以促進其更好地完成現代化轉型,實現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新進化”(《“新子學”構想》),即在强調扎根於中國文化土壤的同時又不排斥西學的影響,實現兩者的辯證,以促成其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轉型。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層面,《“新子學”構想》認為:“我們結合歷史經驗與當下新理念,加强諸子學資料的收集整理,將散落在序跋、目録、筆記、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資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時,深入開展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對原有諸子校勘、注釋、輯佚、輯評等的進一步梳理;最終,則以這些豐富的歷史材料為基礎,綴合成完整的諸子學演進鏈條,清理出清晰的諸子學發展脈絡。”同時,“站在‘新子學’的立場上來看,迷失在西學叢林裏難以自拔的自由主義既不可取,一味沉溺於‘以中國解釋中國’的保守思維同樣不足為訓。……唯有擺脱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固定思維模式,才更為接近文化多元發展的立場。……中國學術既不必屈從於西學,亦不必視之為洪水猛獸,而應根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豐厚沃土,坦然面對西學的紛繁景象。子學研究尤其需要本着這一精神,在深入開掘自身内涵的過程中,不忘取西學之所長,補自身之不足,將西學作為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石。”
此後的《“新子學”申論》在涉及相關問題時,又繼承馮友蘭“照着講”與“接着講”的説法,“所謂照着講就是要真實的領會古人,探其精神,理清其脈絡,而不是隨意講解,任意切割。對於現代學術的研究成果積極借鑒,也要客觀分析,認真吸取。所謂接着講就是保持學術的時代性品質,認真觀察社會,思考未來,把學術研究真正問題化,着重討論根基性的問題,把中國古人的真實洞見引申出來”*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第73~77頁。。且在涉及對西學的態度時,認為“‘新子學’的研究者不拒絶西學,如果把其他的學問比作眼鏡,我們也嘗試戴戴不同的眼鏡。但是‘新子學’不是提倡所謂中西融合的隨意性的研究,‘新子學’希望以家族相似的原則處理傳統學術與其他學術體系的關係。所謂家族相似,就是在中國複合多元的學術中找到與其近似的資源,嘗試引入其視角,從而開闊自身的理解”*同上。。
可見,方勇先生所提的“新子學”方法論,主要繼承傳統“子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對子學資料進行收集、整理,然後加以校注、研究,最後闡發諸子精義,梳理出子學發展脈絡。其基本理念大致停留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傳統觀念上。
王鍾陵先生則在主張敬畏經典,尊重原意的前提下,對馮友蘭的“照着講”、“接着講”有所修正。他强調:“不是‘接着講’,而是‘對着講’。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應該是在全球化中發揮自己的優長。那種僅僅接着在漫長的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傳統話語所説的話,很可能産生繼續為舊事物、舊現象服務的效果;並且,傳統文化也必須在與西方話語的對話中,在解決現實困境的作用中,來鑒别其價值。因此,我們需要‘對着説’,針對西方的話題,對照中西兩種話語,在對話中求深入、求新意。”*王鍾陵《建立中國學術的核心價值》,見《“新子學”筆談》,《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11月2日12版。至於如何在“子學”研究實現“對着講”,從而講出新意,王先生認為需要建立一種新的詮釋學:“當代人研究子學,研究傳統學術,可以借鑒新理論方法,如用西方的闡釋學來重新解釋諸子思想,用傳播學來研究子學的傳播,用接受學來研究其接受,還可以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努力理論方法上的‘新’。”*同上。
此外,劉韶軍先生也認為“新子學”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在忠實於‘舊子學’留存文本的基礎上對其中的豐富内容做出科學的闡釋”,同時稱引了美籍華人學者傅偉勳的“創造的詮釋學”方法,指“新子學”闡釋也應有五層次,即“實謂層次”、“意謂層次”、“藴謂層次”、“當謂層次”、“必謂層次”*劉韶軍《論“新子學”的内涵、理念與構架》,《江淮論壇》2014年第1期,第59~64頁。。賴賢宗先生也對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詮釋五層次加以論述,並對相近的勞思光“基源問題研究法”加以詳論,認為這些詮釋學方法已在中國學術中被廣泛運用,“新子學”也應將其作為自身的基本方法之一*賴賢宗《“新子學”的方法論之反思——基源問題研究法與創造的詮釋學的知識建構過程》,《諸子學刊》第九輯,第95~112頁。。
除此之外,玄華則認為“新子學”研究方法上所要採用的最直接的方式是文本研究與生産(《“新子學”: 子學思維覺醒下的新哲學與系統性學術文化工程》)。他認為文本的生産與研究才是“子學”最基本的發展方式。比如“子學”的誕生就源於對“經學”文本的解構和自身“子學”文本的生産。唐宋以後以“古文運動”為標誌所形成的“文體革命”,近代以“白話文運動”為標誌所形成的文本“語言變革”,均是從文本變革的體裁與語言維度,進一步促進“子學”文本的改造與生産,從而直接促成近代“子學”轉型的發生。當下研究者若自覺意識到這個層面,就可以借助新環境,再次實現“子學”文本的全面解放,實現“新子學”大發展。
從總體上看,“新子學”目前所提倡的方法論,如被大多“新子學”論者視為基本方法的文獻整理、考據、訓詁、辭章、義理等皆是傳統“子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學術固有的基本方法。“詮釋學”雖一直是“新子學”倡導者們最為熱衷的研究方法,但其基本理念仍大致停留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傳統觀念上,而實際上西學作為中國學術共生的參照系,若僅僅將其作為一種工具,以之去理解中國傳統學術,就只能是變相地遺忘或縮減它。因為傳統的學術不是我們以對象化的思維方式就能帶出它的全部。當下的我們,並非是要傲慢地以自身為中心對歷史傳統進行重寫,而是要重新去發現它,那就不能削足適履以之為對象,而只能將它完整地、客觀地從歷史帷幕後帶出。
三、 面對時代課題的異聲
方勇先生《“新子學”構想》强調“新子學”所處的當下是一個多元並存的時代。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已經不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時代。此後《“新子學”申論》又强調“當今世界已經不再是古典中國的‘天下’”,而“新子學”命題的提出則是順應時代多元性的産物。
玄華在强調時代多元格局的基礎上,認為當下中國社會正處於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相雜合交錯的階段:“當我們學術界在面對傳統文化與當下文化的鴻溝而思維尚停留在現代性階段,意圖用經學的形而上思維與體系一統天下時,社會早已將我們抛在身後,大踏步地走入了後現代階段。也就是説,我們當下所面對的社會是,學術文化還停留在前現代階段、正努力着進入現代性階段,但最底層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構成已身在後現代世界中。”*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江淮論壇》2013年第5期,第104~109頁。
那麽“新子學”面對如此紛繁複雜的當下社會現實,又是如何應對的?方勇先生明確指出,“新子學”主張以返歸自身的方式來處理多元世界中不同學術與文化之間的張力,“面對現代學術中世界性與中國性的衝突,‘新子學’的主要構想是以返歸自身為方向,借助釐清古代資源,追尋古人智慧,化解學術研究中的内在衝突。所謂返歸自身,就是要平心静氣面對古人,回到古代複合多元的語境中,把眼光收回到對原始典籍的精深研究上,追尋中國學術的基本特質”,與此同時,也認識到“今日我們已經完全置身於複雜多元的廣闊世界中,勢必要去理解與我們完全不同的異己者”(《再論“新子學”》)。這一求同存異的思維模式是中國傳統固有的觀念,本質上是從“己”出發,以己之同情去理解異己者,最終求同存異。這也為目前大多數“新子學”倡導者所接受。
對此,玄華則認為傳統的“求諸己”、“反歸自身”等方法無法實現真正的和諧共存。他説:“從表面上看,以自我反思為基本方法的倫理觀似乎足以為法,實則不然。其實質是一種潛藏的自我中心主義,……這種我與他人地位的内在不對等必然導致倫理上的帝國主義,最後淪落為他人即地獄的境地。……在他者被排斥在外之下所進行的追求完滿純粹的自我反思,必然是無根之水、無本之木,同時也是永遠飄浮在空中、無落足點的虚幻之羽。”(《“新子學”: 子學思維覺醒下的新哲學與系統性學術文化工程》)在此基礎上,他强調在“我”與“他者”之間,以“他者”為前提,才能真正確立“我”的存在。此後又將相關理念進一步發展為“自我否定”論:“對於每個個體而言,不存在脱離社會而純粹孤立的本質,是在面對他者中獲得自己的確立。同時,也以此進行着自我否定式的發展。它永遠在多元而豐富多彩的世界中,在永不停息的自我否定式發展中。”(《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
從上可知,“新子學”在面對當下多元時代的諸多課題時,内部理念存在着一定的衝突。相比較而言,目前主流看法主張反歸自身,然後去理解異己者。但實際上,這種理念的有效性依然值得商榷。在玄華的論述中,它甚至作為“經學思維”的一種表象而被加以批判。同時“新子學”主張自身的基本内核是思想性學術,對於思想系統建構與研究之外的文化學術,則皆排斥其外。這種帶着“純粹主義”的思維,也與傳統諸子學的博雜相違背。若再以此純粹且近乎單薄的“己身”為中心與起點,再以相“近似”之法去尋求和理解當下如此多元複雜的文化學術和社會現實,難免顯得無力與被動。
更為重要的是,“新子學”作為歷史與當下互為一體之學術,立足於當下的現代性社會中,更需警惕對現代性邊界的重視。現代性又在何種意義上成就了“新子學”?作為生長在當下時代之中的“新子學”要審視它,首先必須獲得對現代性的溢出能力,因為“子學”的發展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簡單的鏡像與對應關係,而是相互的改變。由此“新子學”作為一項時代工程,才能更有效地應對當下的諸多課題。
小 結
“新子學”作為一項時代課題,它是在當下特定的歷史語境中生成的,故其並非依賴某種傳統的或者西方的理念所能簡單處理。它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已變得更加多維,不再是簡單的傳統的延伸,或者是西學的折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攝取影響和改變。或許當務之急不是如何去應對這些問題,而是看清問題到底在哪裏。正如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曾説過: 矛盾始終存在着,反思的目的不是消除矛盾,而是使之存在。那麽就“新子學”而言,以上的種種困境與尷尬是它自身生成過程中的裂隙,也是它自身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學理問題。而我們的質疑與困惑並非否定它的存在,也並非能有效解決它的種種問題,而是使之更清晰地呈現出它内部的縫隙與矛盾,從而真正實現它的價值。
[作者簡介]何浙丹(1985— ),女,浙江紹興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領域為身體美學,已發表學術論文數篇。
①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先秦老學研究》( 15YJCZH008)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 年課題《先秦老學研究》( 2015EWY001) 、上海財經大學校立社科項目《先秦老學研究》( 2014110882) 、上 海財經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之青年教師預研究項目《諸子學現代轉型研究》( 2015110125) 的階段性 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