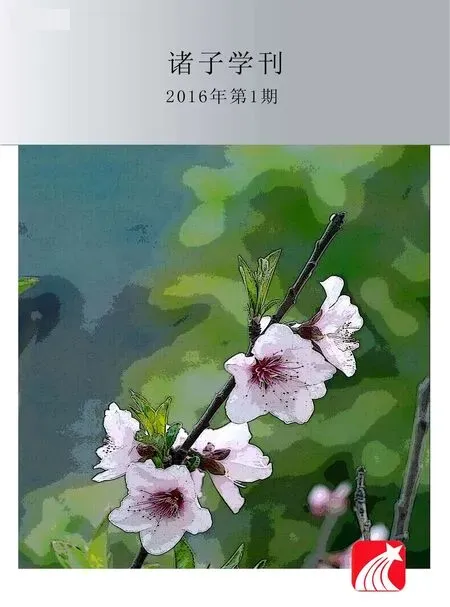後現代語境中的知識建構
——試論“新子學”的境遇與未來
三 莫
後現代語境中的知識建構
——試論“新子學”的境遇與未來
三 莫
“新子學”是針對知識守舊派主導的學術傳統與各種“新”學思潮並起的當代知識界提出的全新命題。它强調當代知識者的主體性,倡導建構一個産生於後現代語境的全新知識共同體。而未來的“新子學”將延續知識傳統的内在理路,在傳統學術的進路中,力圖將架空的學術回歸到倫常日用中來,將碎片化的專題性研究統合到時代問題的界域中來,將學術研究與當代生活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新子學”將以系統知識的有效梳理和學術成果的全面傳播為宗旨,促使當代學術的後現代轉化。
關鍵詞 新子學 後現代語境 知識建構
中圖分類號 B2
引 言
自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學’構想”已近三年,在各種質疑與觀望的態度中,“新子學”已從最初的“構想”逐漸成長為一種具備全新理論内質的學術思想。“新子學”就是要“把握現代學術的自覺意識,以開放的心靈面對傳統,以沉潛的姿態面對現實,以複合多元的研究,尋找通貫古今的中國智慧”,在一個複合多元的時代構建複合多元的學術,“不争宗,不争派,以求返歸(學術)自身”*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第7期,第77頁。。本文試圖圍繞後現代語境中的知識建構這一核心命題,全面分析“新子學”的境遇及未來。
一、 當代知識界與“新子學”
世事人文,遭時代變,故一代有一代之問題,亦一代有一代之學術。自清末迄於今日,學術凡三變,一為以西學改造中學的維新致用之學(鴉片戰争至新中國成立),一為以馬、列、毛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之學(改革開放前的新中國),一為理論界全面西化的人文主義之學(20世紀八九十年代迄今)。所謂人文主義之學,是指20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界普遍盛行的一股西方人文主義精神。它迫切要求重新確立知識者的角色,建構知識者的精神家園,並在現實世界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而與此同時,西方後現代虚無主義思潮不斷向學界滲透,促使正在尋求獨立、重返中心的中國知識界不得不轉向中國文化傳統尋求擺脱精神危機的能源。緣此種種,倡導國學的聲音甚囂塵上。一時間,上至大學教授、國家政要,下及販夫芻蕘、憤青“細民”,莫不交口品議“國學”。於是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講《論語》,王立群讀《史記》,各類“大師”也登上各種“大講壇”和“文化娱樂”節目,得到媒體和大衆的熱捧。然而這一現象並非偶然,正如枯竭的心靈急切渴望慰藉的湯藥,焦慮的時代同樣渴求知識的靈魂。它既是衆聲喧嘩的時代之音,也是知識者感應時代之變,尋求知識建構,實現知識價值的直接表達,是知識領域的分野、社會意識的多元與尚未成熟的知識訴求共同構成的特殊文化心理。在這一文化心理的作用下,知識界明顯呈現出兩種態勢,要麽堅守傳統,要麽鋭意標新。前者我們可稱之為知識“守舊”派,而後者則姑且名之為知識“標新”派。
(一) 知識“守舊”派主導下的學術傳統
知識“守舊”派的學術特徵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以經典文本作為知識材料,追求知識材料的“原始”性;二是注重對知識材料的進一步整理和完善,有意識地排斥宏觀、化約的理論建構,以“知識貴族”的高傲姿態睥睨通俗的知識普及與傳播。這種保守態度由來已久,而以現代史料派為主流的古典學界尤其如此。傅斯年曾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要》(1928年)一文中明確提出“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直到1943年,仍堅稱要“純就史料以探史實”,“史料有之,則可因勾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要》,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335頁。。當時的傅斯年顯然受到方興未艾的歐美“新史學”思想的影響,而其主要目的是要用史料學的方法來統合“新史學”,並借機批判以章炳麟為首的“國故”派權威對待新材料的冷漠、“守舊”態度。但“史料派”後學只知墨守祖師爺的成規,大多没能繼承傅斯年先生科學史觀及方法論思想的精髓,最終只知道尋找材料,不懂得讀書思考,果真成了材料的“奴僕”,因此也没能逃脱遭遇當代國内“新史學”派批評的命運*桑兵對傅斯年學派有過較為深入的研究,也有公允的認識:“人們似乎也傾向於將理論與事實分離甚至對立,覺得事實不如雄辯有力,總希望用雄辯壓倒事實。而‘史學只是史料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所謂‘理論’,所以同樣遭遇總有部分道理: 其至徒子徒孫之手,便有了印版而已的尷尬。不過流弊畢竟不同于本意,批評前人,同時也是對自己見識功力的檢驗。”《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41頁。。從求實的層面看,重視材料固然是學術應該葆有的精神,但是從知識的創生看,這種單純注重外緣材料的積累,而忽視時代精神和主體價值介入的學術範式,勢必令學者迷失知識建構的根本目的——構建真理價值的世界和情感想象的世界,最終變革當下的世界、指導未來的世界。知識本身便具有理性的激情和豐富的想象空間,故不能就事論事地屈服於知識的材料。即便是史學也不純粹是事實的收集,或在歷史現象中尋找規律。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的德國著名史學家兰克也不得不承認,歷史的動力乃是“理念”(Ideas)或“精神實質”(spiritual substances),而在“理念”和“精神實質”之上還有“上帝”。每個時代的重要制度和偉大人物都應表現那個時代的“理念”和“精神”,並使之客觀化為“積極的價值”(positive values)。正所謂“每一個時代都直接與上帝覿面”,而“上帝”是不可能直接呈現於知識材料之中的,它依賴於理性、情感、觀念、體制等多元知識的複合共生。即便是知識本身也絶非單一的事象,而是藴含着豐富的價值、意義和精神觀念形式。因此知識的世界便是觀念的世界,只要是觀念的世界,就必須遵從“理念”與“精神”的原則,而這一原則只有通過對“全部人生的透視”才能實現*轉引自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自序》,《卮言自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頁。。這正是司馬遷為何允許《史記》撰寫存在想象、夸張甚至虚構事實的根源所在。因為情感的真實與事件的真實並不違背,而是共同抵達真理的世界,那便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所成的“一家之言”(司馬遷語)。這是知識者通過對天道、義理的傳承性闡釋逐漸建立起來,或是直接從人性中抽離出來的對道義的執著,是文化基因或某種集體無意識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知識傳統。它依賴於知識材料的積累,同時又必須超脱知識材料本身。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知識體系的封閉性和知識接受的局限性造就了知識材料的權威性,從而使知識的傳播帶上了某種神聖屬性,遂令知識者成為某種知識材料的“附庸”,從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整個學術傳統的封閉與自守,極大地損害了學術自我發展的可能性。
(二) 知識標“新”派粉墨登場的當代學界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進入所謂“後新時期”,整個知識領域普遍出現了知識的市場化,審美的泛俗化和文化價值的多元化三大思潮。這意味着以西方為參照體系的現代性建構的破産,也宣告了以宏大敘事為憑藉的知識者的死亡*分别見張頤武《現代性的終結: 一個無法回避的課題》,北京《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4期;陳曉明等《後現代: 文化的擴張與錯位》,《上海文學》,1994年第3期;張法等《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文藝争鳴》,1994年第2期。轉引自許紀霖《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知識標“新”派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轉點中群雄並起。
與恪守傳統的知識者截然不同,標“新”派無不以锐意求“新”為潮流,以至於各家各派皆自命為“新”。如“新經學”*當代的“新經學”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强調對經學文獻整理,對經學歷史進行研究,對舊經學觀的否定,對經學文獻價值進行辨析的一種學術思想(党躍武《新經學淺論》)。從某種程度上説,“新經學”還只是一個尚未形成概念的口號,目前也頗受詬病。、“新道(教)學”*“新道學”,既不是流派,也不是理念和概念,準確説來只能説是一種復興道教與道家文化的理想而已。可參胡孚琛《新道學文化的綜合創新之道和普世價值》。、“新墨學(家)”*1997年,學者張斌鋒、張曉芒發表《新墨學如何可能》一文,最先提出以文化“建本”和知識“創新”為核心的“新墨學”概念,倡導對傳統墨學作創造性的“新”詮釋。由於兩位學者“人微言輕”,雖得到了少數學者撰文回應,卻未有實質性的“新”成果以支撑其“新墨學”理念,故一度遭遇質疑之聲,且很快淹没在衆聲喧嘩的“新”口號裏。等。在“新”思潮的推動下,各種“新”學思想和主張皆得到不同程度的宣揚,一度出現“新國學”*王富仁《“新國學”論綱》(上):“‘新國學’不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方法論,不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指導方向,也不是一個新的學術流派和學術團體的旗幟和口號,而只是有關中國學術的觀念。它是在我們固有的‘國學’這個學術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使它適應已經變化了的中國學術現狀而對之作出的新的定義。”王富仁所提倡的“新國學”觀念,旨在梳理和思考現當代學術文化,試圖打通古今學術之分野,促成學術文化的交融和發展。的熱潮。同樣,與持續將近百年的現代“新儒學(含現代新理學、現代新心學、現代新氣學)”*20世紀20年代産生的以接續儒家“道統”為己任,力圖用儒家學説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文化現代化的一個思想流派。為區别先秦儒學、宋明儒學,史稱“新儒學”或“現代新儒學”。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張君勱、馮友蘭、賀麟、熊十力等。、“新法家(學)”*所謂的“新法學”,是自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出現的“新法家”所標舉的學術理念。其提倡重新審視先秦法家,要求以法家思想拯救中國之危局,運用當時世界的民主法制觀念重新審視法家的“法治”思想。也截然不同,當代“新”學多呈現為一種口號式的宣揚和標榜,或多或少地顯露出某種渴望主導學術文化的理想和激情。而其所宣揚的“新”理念則大多流於對某些傳統經典的比附式“翻新”和概念式演繹,因此尚未在學界泛起波瀾便已歸於寂滅了,比如頻頻遭遇質疑的“新墨學”。誠然,提出一種新的觀念或一個新的概念,甚至推動一個新的思潮都非難事,但要形成一個新的知識界域或學術流派則絶非易事。明確的知識界域、可操作的知識方法、開拓性的知識結構以及由此形成的全新價值系統才是衡量新、舊知識的内在尺度,否則所謂的“復興”與“創新”,充其量不過是對某一思想或材料的重新發現和進一步應用而已。作為當代新儒學最富影響力的學者,余英時先生曾在1990年8月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要重建現代中國的價值系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是恢復民間社會的動力,在政治力量之外有比較獨立的社會力量;第二是知識者必須改變反傳統的極端態度,並修正實證主義的觀點,否則便不可能對傳統文化價值有同情的了解*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頁。。二十多年過去了,價值系統重建的工作仍在繼續,而價值世界的分裂傾向卻日益加劇。實踐再一次告訴我們,“新”的價值系統很難依靠某種人為的“重建”得以實現,任何一家之學都不能解決多元世界所面臨的複雜問題。
(三) “新子學”的境遇
與各派“新”學截然相判的是,“新子學”竭力反對“一家獨尊”,倡導以多元對話的學術理念實現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學術範式的建構。“新子學”明確提出,以古今文化資源的全面整合和創造性詮釋為手段,以學術的“返本開新”和多元發展為基本模式,力求消除各家之學在觀念上的對立性和封閉性,促成學術的對話與互通,並以積極的姿態直面當代學術的種種問題: 比如斷裂的知識傳統將如何接續?面對知識的分野,知識者將如何自處?如何在瑣碎、虚無的後現代文化廢墟上建構精神的家園?如何在紛繁複雜的時代焦慮中建構現代中國的價值系統?通過各界學者將近三年的探索,我們認為“新子學”理論的構建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基礎。一方面,對經典文本的實證研究所取得的豐厚成果,足以為“新子學”由外緣轉向内核,由微觀轉向宏觀的理論建構奠定夯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人文學科知識在經歷了漫長的分野甚至分裂後,已各自進化出精密的學術系統,它們並非斷裂、孤立、單元的知識,而是圍繞政治—人生這一核心價值,共生於多元、延綿的現代知識結構中。因此,“新子學”足以在已有知識體系上建構起結構優化、理論多元和綜合開放的知識共同體。
二、 當代知識者與“新子學”
如果説傳統士人是諸子學的構建者和踐行者,那麽當代知識者便是“新子學”的建構主體,並且直接預示着“新子學”的未來走向。但這並不是説,有什麽樣的知識者,就會産生什麽樣的“新子學”。正如傳統子學與士人之間具有相互塑造的作用一樣,當代知識者與“新子學”同樣具有彼此對話、詮釋和塑造的主體交互空間。因此,如何理解、確定當代知識者的價值歸屬,將是“新子學”理論建構的核心所在。
(一) 當代知識者的身份歸屬與文化特征
中國當代知識者既承續着士人傳統,同時又吸收了全球化、現代化的知識内容,是全球現代化進程中逐漸形成的新型知識主體。從文化知識的角度,我們可以將其大致分為學院知識者與媒介知識者兩類。學院知識者主要是指以學術研究為職業,依附於知識體制而生存的一類技術型知識者,其身份屬性通常為專家、學者或大學教員。由於這一知識群體不僅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化修養,同時還有着强烈的普世情懷與批判精神。他們與傳統士人既存在文化上的一貫性——即對道統的承傳性,又存在着體制上的斷裂性——即對政統的疏離性,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當代知識者的主流(本文討論的知識者主要指這一群體而言)。而處於知識體系邊緣的媒介知識者則正好相反,他們未必有專深的知識素養和道德情懷,而是依托媒體獲得聲望,並以此謀求個人利益和發展的知識群體,其身份屬性主要是記者、編輯、藝人、作家以及某些活躍於媒體的草根領袖、“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在西方,媒介知識分子是一個頗受争議的群體,正如布迪厄所言:“他們要求電視為他們揚名,而在過去,只有終身的,而且往往總是默默無名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們獲得盛譽。……而這些人既無批判意識,也無專業才能和道德信念,卻愛在現時的一切問題上表態,因此幾乎總是與現存秩序合拍。”見[法] 皮埃爾·布迪厄、[美] 漢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51頁。。
但是,隨着消費文化的盛行,學院知識者與媒介知識者的邊界日趨模糊,各類學術明星、專家學者也紛紛活躍在大衆媒體之上。於是知識者所應具有的獨立性和超越性進一步瓦解,日益呈現出既清高又世俗的矛盾性,不斷向福柯所批評的“有機知識分子”轉化。比如,在尚未觸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他們通常都會表現出民粹主義的傾向,將底層民衆的道德感和正義感抽象地加以美化,但一談及具體的民衆,他們又表現出極端的鄙視和不信任,認為他們無法表達自己、代表自己,而需要自己來為民衆伸張正義,發出聲音。這一點在當代“民意代表”和草根領袖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許紀霖《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見《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頁。。
更為吊詭的是,當媒介知識者“自甘墮落”,與作為消費者的廣大民衆打成一片的同時,學院知識者卻不斷遭遇來自内心深處的困惑和虚無。廉思主編《工蜂: 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録》便以大量案例揭示了高校“青椒”們内心深處的種種矛盾與苦悶;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蔣寅《走出報銷惡夢,再談科研經費》*《文匯報》2014年12月26日。以及湯明磊博士《博士: 學術塔尖上的“懸浮族”》*http: //www.360doc.com/content/14/0116/10/175820_345651944.shtml等文章,則真切反映了身處不同階層的學院知識者心靈深處的無力與空乏。隨着有關知識者的討論在網上進一步展開,諸如“知識民工”、“知識搬運工”等流行詞彙的不斷出現,更讓自命清高的知識者陷入了自我消解的虚無境地。
總之,矛盾與虚無正在構成當代知識者重要的文化特徵。從歷史淵源看,這是自古至今知識者始終無法擺脱政治附庸命運所使然;而從現實層面看,則是知識者自我建構的主觀訴求與知識世界不斷消解的客觀現實之間的錯位所造成。換言之,這是“後學”思潮不斷消解知識權力的必然結果。
(二) “後學”思潮與知識權力的消解
筆者所謂“後學”思潮是指20世紀90年代以來深受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影響的當代學術思潮。至於“後現代主義”,則是指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於西方社會的一種新型文化理論,是晚期資本主義和媒介資本主義、後工業化資本主義和多國化資本主義的産物*參傑姆遜著、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6頁。。從某種程度上説,後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的延續和反叛,其本質特徵是從價值的建構走向價值的消解,具體表現為文化去魅、去邏各斯(理性和規則)、反中心、反本質、反一元論、反形而上學、反體制性和整體性等基本特徵*參張清華《認同或抗拒——關於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思考》,《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第138~147頁。。而後現代文化乃是文化工業生産與文化商品消費産業化的結果,並由此構成了非延續性、多元性和解構性的後現代文化語境。在後現代文化語境中,一切的闡釋都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權威性和真理性,知識表現為一種無法窮盡的意義循環。
隨着後現代思潮的不斷滲透,嚴肅的學者們深感不安,他們認為“後現代論者們正在將本已迷失方向的中國文化推上絶路。而他們要消解的,恰恰是中國根本匱乏而又迫切需要的東西”*陳曉明《後現代主義》,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這種不安的出現並不難理解,因為隨着文化資本對知識領域的進一步滲透,作為人類精神文化媒介的“知識”也逐漸淪為一種有待消費的商品。這使以“傳道、授業、解惑”自居,以立心、立命、繼絶學、開太平自命的傳統知識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失落。他們不願看到幾代學人努力建構起來的“現代性”即將淪為遊蕩於前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幽靈”。但是,後現代思潮並不會因為某些知識者的抗拒而停止,正如英國思想家鮑曼所認為的那樣,在現代社會中作為“立法者”的知識者掌握着一整套客觀、中立、有序的元話語陳述和規則,具有知識仲裁的權威性。但是隨着知識一體化的不斷解體和分化,這套整體性元話語體系也將喪失其普遍的有效性。整個社會不斷走向多元化,知識體系也日益分崩和斷裂,原本統一的知識場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彼此孤立的知識共同體,它們各自規定自己的知識範式,宣示着自己的知識傳統,彼此之間甚至是不可通約的存在*轉引自許紀霖《知識分子死亡了嗎》,見《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
因此,身處後現代知識語境中的知識者日益分化為兩大陣營: 一邊代表着傳統知識理念,他們尚未自覺到角色的變更,也無視人文社科領域的日益邊緣和没落,竭力扮演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仲裁者,不自覺地回避大衆知識傳播的現實意義。而另一陣營的知識者則欣然接受時代賦予的“新角色”,他們滿足於對已有知識的通俗化解讀和平面化傳播,對自身知識體系學理層面上的反思卻無多少興致。許多所謂“學術明星”現象都是當代知識領域值得深思的問題。對此,筆者更贊同一種公允理性的認識:“知識分子雖不可能再奢望啓蒙時代的偶像地位,但面對于丹這樣必然且已然受到大衆熱捧與追隨的現象,他們也實在無須大嚷大罵,用娱樂的武器對抗娱樂文化。保持適當的緘默與冷静的思考,盡可能地發表嚴謹的知識表述與價值判斷,或許仍是知識分子群體作為社會‘文化平衡器’的存在意義。”*楊早《評價於丹: 學術規範還是傳播法則》,《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114頁。
(三) “新子學”視閾下的知識建構
如果我們對知識者的歷史境遇稍作回顧,便會發現,當代知識者所遭遇的後現代困境並非單純的後現代文化現象,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事實。在整個中國歷史的進程中,知識者的自我消解並不少見,比如,漢代便有“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一,民國《師石山房叢書》本。的批判之聲。作為東漢知識界的“反動派”王充乃將文章之儒視為“陸沉之士”*王充《論衡·謝短》:“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學識淵博、以賦名家的揚雄也宣稱“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司馬光《法言集注·纂圖分門類題五臣注揚子法言》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晉代葛洪稱儒生是“知古不知今”、見識淺陋且不辨邪正的“守道”的“凡夫”*葛洪《抱朴子·審舉》:“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沉,以履徑者為知變。”,唐代詩人楊炯在詩中直言“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從軍行》),清黄景仁更憤言“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雜感》)。這種現象,用朱熹的話説乃是“道術分裂”的表現,實為“學者之大病”*宋朱熹《答項平父書》:“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已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謂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複合。此學者之大病也。”《朱文正公文集》卷五十四,《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常出現於歷史變革期或文化轉型期。比如宋元代變之際,便普遍出現了“儒者皆隸役”*《元史·高智耀傳》:“皇子窩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又謂:“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没為奴。”,“小夫賤隸,亦以儒者為嗤詆”*《青陽集·貢泰父文集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現象;明清之際的陸王末流和顧、李學派都把知識看做毒藥。余英時先生將這種儒學的“異端”視作極端的德性論和功利論所引起的反智識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余英時認為: 反智識主義又可分為兩個主要方面: 一是反書本知識、反理論知識,或謂其無用,或謂其造成求“道”的障礙;另一個方面則是由於輕視或敵視知識遂而反知識者……這兩個方面的反智識主義今天都以嶄新的現代面貌支配着中國的知識界。(《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事實上,當一種知識發展成熟後,便會自然而然走向其對立面,由此循環不已,曲折進化。
“新子學”遵循知識發展的客觀,否認知識之間的對立和斷裂,强調知識因為彼此的差異而實現相互的確立與共存。正如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知識者便以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從英國的約翰·密爾、格林到羅爾斯為代表的一個自由主義傳統。來實現傳統政治史學的建構;以張東蓀、張君勱為代表的知識者則多以具有古典自由主義色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主要是從休謨、亞當·斯密到麥迪森、哈耶克等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重估傳統儒家知識體系的價值;而杜威、羅素、拉斯基等西方思想家則借助中國近代知識者,實現了東西文化的深層對話,形成了延續至今的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傳統*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自序》,第13頁。。在“新子學”的視閾下,一切知識都是彼此確立而非相互消解的平等存在。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知識者對自我知識傳統消解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固有知識傳統面對新的知識參照體系而主動發生的價值重構。
總之,知識的建構必以傳統知識體系的局部解構為前提,同時還需以外來知識作為全新的對話體系,重新發現傳統知識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因此,“新子學”既不誕生於傳統的經學或子學,也不依附於任何形式的西學,它是當代知識者直面後現代困境的一次全新實踐。正如玄華所言:“我們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後現代中國’,因此繼承於傳統的‘新經學’、‘新儒學’等不足以解決中國下半身——社會現實的後現代之憂,而純粹的西方後現代理念無法回應中國上半身——學術文化的前現代之困。唯有發掘於中國固有的‘諸子學現象’、又面向世界的‘新子學’,才能整體性地予以治療。”*玄華《關於“新子學”幾個基本問題的再思考》,《江淮論壇》,2013年第5期,第109頁。
三、 “新子學”的確立與走向
(一) 傳統知識脈絡上的“新子學”
中國文化的原初思維特徵在於追求混融同一的本質性,自覺地將個體納諸天地宇宙之中,視其為整體世界的構成元素,彰顯宏觀的本原意識。《荀子》謂:“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但凡知“本”,便能找到一切問題的答案,故陸象山謂:“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一部中國學術史,可歸結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五十九《經籍考三》,民國景《十通》本。八字。而一切傳統學問無外乎兩方面的訴求: 為天理、為人事。為天理者,即闡明聖人旨意,大抵訓詁、義理之學,如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謂:“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戴震《戴東原集》卷十一,《四部叢刊》景經韻樓本。為人事者,即服務於時事民生,此人倫日用之學,所謂“道不在乎他,只在日用人倫事物之間。*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陳正仲》)天理(道)、人事看似矛盾,實則互為表裏、相輔相成,合為聖人之學,其目的乃是要解決信仰和行為上的問題。因此“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章學誠《文史通義·内篇一》,民國嘉業堂《章氏遺書》本。,換言之,天理、人事儘管有道、器之别,卻統一於人的知識生活,皆是知識者實現價值建構的必然途徑。由此觀之,經學、理學、史學皆一學,皆知識之一學,都是知識者改造世界的法術。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言:“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顧炎武提出“明道”、“救世”並用,希望通過知識者的自我改造,實現重建世界秩序的理想*《又稚圭先生畫像記王璲》:“君子之仕也,非以私市也。東坡蘇氏所謂苟可尊主庇民,則忘身為之是也。君子之有言,非以衒異也,亭林顧氏所謂以明道救世者是也。”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三十八,民國十二年(1923)刊本。。黄宗羲認為“教學者必先窮經”,“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黄梨洲先生事略》:“先生謂明人講學,襲語録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敎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為俗學。”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清同治刻本。,則是要通過對知識材料内在脈絡的梳理以確立價值世界合理性的學術理想。
在“新子學”的視閾下,文化思想史上一切返本求新、探源開流式的復古、維新之學,皆屬建構於現實世界之上,又面向知識傳統的“新”學。開唐宋兩朝文化之盛的古文運動,促成文化現代化轉型的“五四”運動以及我們的“新子學”無不如此。然而,與古文運動、“五四”運動等“新”學不同的是,“新子學”既不因循傳統的知識體系,也不亦步亦趨於西學的腳步,而是在後現代文化語境中,重新發現傳統知識與當代知識的多元性與整體性、通約性與差異性、時代性與歷史性,進而推動全部知識的後現代轉化。
(二) 現代學術進路中的“新子學”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幾乎佔據了整個知識世界,成為學者探尋一切問題的根本。而宋、明兩代儒者更將道問、德性之學做得極為細緻透闢,由“道本”所生的種種問題都得到了近乎極致的闡發。所謂“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厘之際,使無遁影。”*黄宗羲《明儒學案凡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至於清代學者只能另闢蹊徑,專事樸學*通常學界認為清代學者之所以重返訓詁、考證的老路,乃是思想上的限制,實則也是學術自身發展使然。。但儒學强調天、道的一貫性,因此在時代問題前往往顯得蒼白無力。身歷巨變的清末學者汪士鐸對此有過一番略顯尖刻的批評:
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者多宗其言仁言禮,而略其經世之説……道德之不行於三代之季,猶富强之必當行於今。故敗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輔孔子之道者,申、韓、孫、吴也。*《汪梅翁乙丙日記》卷二,文海書社影印本,第74頁。
隨着儒學的逐漸解體,一個多元、開放、延展的新的知識界域逐漸在儒學體系内孕育成形。如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所言:“雖極力推挹孔子,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創學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於諸子之列。所謂‘别黑白定一尊’之觀念全然解放,導人以比較的研究。”*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58頁。很明顯,康有為已經有意識地將孔子之學時代化、子學化。隨即,梁啓超揚其波瀾,以《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著作將中國學術引向全新的階段。隨着各界學人的紛紛加入,傳統儒學體系徹底瓦解,由此宣告了一個“新”學時代的到來。
然而,知識的衍化隨着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而不斷深化和複雜化,現代主義的“新”學不僅不能應對當代知識者所面臨的後現代困境,同時也無法擺脱以西學附會經典或以經典配擬外説的傳統“格義”之路。因此,“新子學”理念正是在這樣的學術進路中産生,其宗旨便是要構建現代主義學術與後現代主義現實之間的知識橋樑。
(三) 未來的“新子學”
“新子學”宗旨既已明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就是其現實的操作性問題。由於傳統學界通常認為學術研究與意識形態存在着根本的區别(學術研究注重個案分析,注重對具體現象的深層透視和把握;而意識形態則更多是一種化約的、整體的認知),因此,有意無意地將意識形態排斥在學術研究之外。但事實上,兩者雖有區别卻並不對立,乃是知識進路中的不同階段。當某一傳統學科的個案研究足够豐富時,其化約、整體的意識形態建構便有了現實的可操作性。换言之,學術研究和意識形態可以分别作為方法和目的,共存於知識的闡釋與傳播中。
這裏需要面對一個難題,那就是作為常識而存在的“元話語”,“只能在一個發展緩慢的(傳統)社會中發揮合法性功能……而當今世界變化之快……誰也不能擁有對常識的最終解釋權,一切只能取決於公共領域中公衆之間的理性討論……公衆的交往理性是比個人常識更可靠的東西。”*許紀霖《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見《中國知識分子十論》,第57頁。簡言之,當代社會並不缺乏知識,卻極度缺乏知識的有效傳播。人類學家Philip Bagby便指出:“今天散在無數種專門性刊物中的歷史論文,如果没有人把它們的結論綜合起來,加以融會貫通,那麽這些論文便只能是歷史研究,而不配叫做史學。”*轉引自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頁。我們可以將這一觀點推而廣之,直到整個學界。因此,未來的“新子學”將盡量避免重複繁瑣的文獻整理、細枝末節的材料完善以及毫無結果的考索訓釋,而主張系統知識的全面梳理和學術成果的廣泛傳播。作為“新子學”建構主體的當代知識者,更應自覺從傳統的知識體系中解放出來,重新確立自己的角色,讓學術研究直面廣闊的社會憂患與時代危機,以學理的方式應對普遍存在的問題,以精深的學術思考取代浮躁的宣講與空洞的説教,在提升學術品質的同時,也極力避免將學術變成嘩衆取寵的工具。
總之,未來的“新子學”應力圖將架空現實的學術回歸到倫常日用中來,將碎片化的專題性研究統合到時代問題中來,將學術研究與當代生活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只有以切實的行道之學取代虚無的書齋之學,才能讓學術恢復生機;只有用典範性的當代經典充實傳統學術,才能讓學術重塑威嚴、推陳出新;只有讓學術面對當下的真切存在,才能使學術避免僵化和空蹈的危機。
[作者簡介]三 莫(1983— ),本名曾建華,男,湖南邵陽人。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道教文獻與先秦兩漢神仙思想研究,已發表學術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