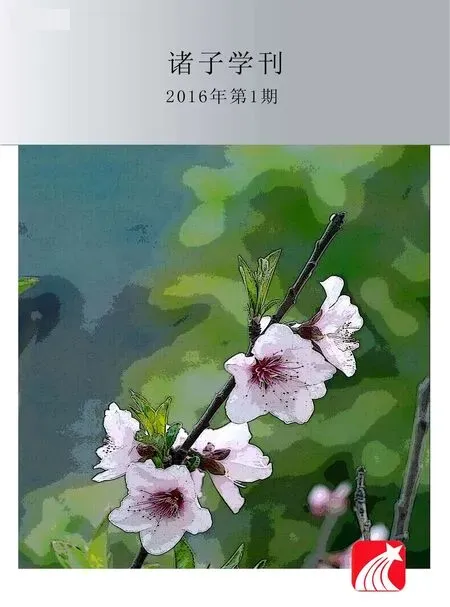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新子學”理論建構的現狀與反思
曾建華
“新子學”理論建構的現狀與反思
曾建華
“新子學”是當前學界正在建構的一種新的中國化的學術思想與方法體系。自2012年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學’構想”以來,“新子學”已經從最初的個人“構想”逐漸發展為一種廣為學界所知的學術理念,並初步形成了“新子學”的理論思想和方法體系。與此同時,由於“新子學”核心理論的缺席,這一學術遭遇了外界較多的質疑。因此,當前“新子學”理論建構的主要任務在於明確“新子學”理論的核心内容,確立“新子學”理論建構的主要目標,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實現中國學術理論的更新,重構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世界。
關鍵詞 新子學 理論建構 學術轉型
中圖分類號 B2
“新子學”是繼新儒學、新國學、新經學、新墨學、新道學等國學思潮之後的又一新學術思潮。如今,歷時半年的“新子學”已滲透到涵括文史哲等諸領域的整個學界。因此,對“新子學”當前階段的理論建構進行必要的梳理和總結,進一步探索“新子學”之發展趨勢,便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一者介紹“新子學”及其發展狀況,二者揭示“新子學”所面臨的困境並提出突圍的方法,以求抛磚引玉之功。
一、 “新子學”理念的提出及其初步建構(2012年10月—2013年4月)
2012年10月22日,方勇先生在《光明日報》國學版發表《“新子學”構想》,明確提出了“新子學”理念。方先生在文中指出,“新子學”的提出,並非一時興起,而是長久思考醖釀的結果,是對“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中“全面復興先秦諸子”這一學術訴求所作的全景式觀照,是力圖在“新子學”視域下,全面回答諸如諸子之學的復興及其在中華文化全面復興這一歷史使命中所應承擔的時代責任等問題的一次大膽“構想”。
方勇先生所謂的“新子學”,是以傳統學術資源的現代詮釋為基本方法,不斷從元典中攝取創生性、開放性、多元性和對話性的學術思想,逐步破除被封閉、專制的經學思想所主導的舊國學理念,從而為“加快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實現民族文化的新變革、新發展”,最終為中國之崛起提供思想資源的大型學術文化工程。
方勇先生的“構想”將子學從傳統的經、史、子、集的既定格局中解脱出來,更將子學研究拓展到學術史、思想史的高度,為今後的子學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而“新子學”也勢將承載“國學”之真脈,實現新時代背景下的國學復興與文化建設。然方勇先生這一宏大的“構想”始終着重於子學文獻的搜集整理,未能深入到子學發生、演化及其文化創生的本質層面,因而難以從根本的知識層面超越傳統子學,也就無法全面建構“新子學”之合法性與必然性,更無法從本質上區分新舊子學之淵藪,確定“新子學”的本體使命。從這一層面上説,方先生以“構想”命篇,並不完全出於自謙,更是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和精確的話語表達。《“新子學”構想》的真正魅力在於繼所謂新儒學、新國學、新經學等各種“新”現象之後,為中國學術再度開啓了一扇交互之門,也為學界志士仁人共同營建一個全新的學術理念找到了方向。
為促成“新子學”理論的建構,2012年10月27日,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首次主辦“‘新子學’學術研討會”。王鍾陵、徐志嘯、陳引馳、劉康德、郝雨、陳致等30多位學者參加會議並發表精彩演説。他們從不同的專業角度肯定了“新子學”的學術價值,豐富了“新子學”的理論内涵,極大地擴大了“新子學”的影響。
數日後,《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11月2日版)以“專版”刊載《“新子學”筆談》。卿希泰、譚家健、王鍾陵、鄧國光、陳引馳等學界名家圍繞“新子學”理論的具體建構及其未來發展,分别從當今時代的文化需求、“新子學”的定位與拓展、“新子學”的學術使命及其實現、“新子學”的普世價值及其學術史意義等方面聲援和發展了方勇先生的“‘新子學’構想”。
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卿希泰認為,子學誕生於時代的巨變,是時代轉型期的思想結晶,是各種社會矛盾與人生問題在意識層面的系統反映,因此各個轉型期出現的新思想都可以被納入到(新)子學的體系中來。這就從思想層面對“新子學”的外延做了一定的拓展。最後,卿先生給予“新子學”巨大的時代價值以肯定。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譚家健則給“新子學”的構建提了三點雖不十分成熟但卻極具啓發性的建議。譚先生認為,“新子學”理論建設,首先要明確研究的範圍和對象,要在嚴格區分諸子學與方技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明確“新子學”與自成體系的釋家、道家和小説家之關係;其次要處理好“新子學”與西學的關係,明確“新子學”具體的實現方式,而不僅僅是停留於“中體西用”的嫁接層面;再次,要正確界定“新子學”的國學地位,確定“新子學”是否有能力主導國學。總體上,譚先生對“新子學”的態度是既支持其發展,又堅持着一個學者對“未成熟”理論的質疑,這或許代表了當前學界許多學者對“新子學”所持有的普遍心態。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鍾陵認為,“新子學”要成其為“新”則必須建立起中國學術的核心價值。而要建立其核心價值,則必須通過四個方面的努力,其一,要對作為國學元典的先秦典籍有新的解讀方式和闡釋標準,用王先生的話説便是要“對着講”而不是“接着講”,也就是説要以中西對話的方式去解讀先秦典籍;其二,要全面革新子學研究方法,在文本原意闡釋的基礎上作出合理的自我闡發;其三,要對經典形成正確的接受心態——即要敬畏經典,不能為了某種或商業或娱樂的功利目的隨意歪曲經典;其四,要充分發揮當代大衆傳媒的積極作用,盡量避免其消極影響。
澳門大學教授、澳門中國哲學會會長鄧國光從全球文化脈絡的宏觀、發展層面闡釋了“新子學”提出的合理性與必然性。鄧先生認為: 在集部,有新文學;在經部,有新經學;在史部,有新史學。而作為中華思想文化中最具原創性與活躍性的子學自然應當應運而生,發出“新子學”的聲音。而“新子學”也當不辱使命,“過濾蕪雜的偽飾,醇化子學的本質,重建中國學術話語,激活思想,發憤人心,重振靈魂,積極解決新時代的深層次困擾,而期向未來生活世界的整體幸福”,並最終調節世界文明格局,促進人類的和諧共處。
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郝雨認為“新子學”反映了當今文化傳承的真正源頭與主體性,其構建不僅僅是古代文化研究者所需面對的課題,也是全部文化學科在全球化、新媒體時代的今天應當共同承擔的主題。因此,“作為一面新的文化旗幟,‘新子學’必將在整個文化界更大規模地激起復興民族傳統文化的時代潮流”,為整個現代文化研究者提供全新的學術基點、方向和方法。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引馳從當今多元、衝突的思想文化背景出發,肯定了“新子學”理念的合理性及其提出的時宜性。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教授吴平提出“諸子禪”的概念,將禪宗納入到“新子學”的體系中來。這不僅拓展了“新子學”的内涵,更促進了禪學思想的當代詮釋。
同年12月,郝雨、王鴻生、葛紅兵、楊劍龍、劉緒源、李有亮等現代文化學者齊聚上海大學,參與了上海大學舉辦的“現代文化學者如何認識和評價‘新子學’”的主題研討會,從現代學科的不同領域對“新子學”的文化内涵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和闡發。
此外,郝雨先生《“新子學”對現代文化的意義》、陸永品先生(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新子學”構想〉體現時代精神》、孫以昭先生(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時代召唤“新子學”》以及刁生虎先生(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新子學”研究需做到四個統一》等文陸續發表,給予“新子學”理論建構以寶貴的建議和啓示。限於篇幅,兹不一一細述。
二、 “新子學”理論的全面建構和初步形成(2013年4—7月)
2013年4月12日至14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承辦的“‘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成功召開。來自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以及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的130多位諸子學研究專家出席了會議。與會學者圍繞“新子學”及相關古代文學前沿問題,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分别對“新子學”之本質如何建構、何為“新子學”的當下使命、“新子學”如何面對“經”與“子”之關係、“新子學”能否主導國學、“新子學”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新子學”的未來圖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形成近百篇論文,促使“新子學”從“構想”(或者説“口號”)到“命題”再到“理念”的飛躍,初步實現了“新子學”理論的建構。
原中華書局總編、清華大學教授傅璇琮首先在大會中指出,“新子學”既要追本溯源、繼承傳統,全面完善子學研究體系,釐清“新子學”整體發生演化的軌迹,又要繼往開來、創新學術,在扎根民族文化的同時放眼世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雙棣認為“新子學”應在諸子學全面復興的基礎上,兼收並蓄,統合各家,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和智慧。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許抗生對方勇先生的“新子學”構想表示認同,提出“新子學”應以厚基礎、重創見、開新貌的“三步走”策略,實現多元化的理論建構。三位先生,基本代表了老一輩學者扎實、厚重的學術風格,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缺乏創設性理論思想的痼疾。
與之相對的則是一些較為激進的青年學者的觀點,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玄華的發言更將本次會議引向了高潮。他首先從整個學術史與文化史的廣闊視域揭示了“新子學”的“新”内涵和本質屬性,繼而全面指出了經學思維主導下的傳統哲學與子學思維主導下的“新子學”這兩種學術生態截然不同的宇宙觀、知識觀、學術進化方式及其最終引發的學術文化倫理與社會影響的差異。玄華博士還首次將“新子學”理論置於後現代文化視域之中進行全方位觀照,從而提出以“新子學”重新發現經學、重新發現子學、重新發現傳統學術發展的客觀面貌、重新整合當下學術資源、真正揭示學術進化的直接途徑與最新方式,最終建構一個以他者存在為根本前提的新型社會文化倫理的全新“構想”。
玄華博士的發言引發了與會專家廣泛的分歧和熱議。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韓星就從經學與子學的關係層面首先提出“商榷”。韓先生認為造成中國幾千年專制的因素中確有經學的成分,但是,經學對於中華民族精神品質的塑造之功也不容小覷。他進一步指出,我們今天的道德墮落和各種“亂象”不僅不是由於經學的影響,恰恰是經學的衰落及中心理念和思想的缺乏所致。就此層面而言,我們不但不能否定經學,反而應當重建經學的“權威”。隨之,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静也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她認為,此前的“新子學”口號多於行動,只有命題假設而没有實質性的理論内容,只有概念式的移植,缺少理念價值的建構,所以她對“新子學”的未來表示憂慮。
然而,韓國國立江陵原州大學校哲學科教授金白鉉卻對“新子學”充滿信心與熱情,他盛讚玄華博士的“‘新子學’哲學”是中國子學思想與當代後現代理論的適時融合,是反思於當代各種文化亂象後的一次系統的思想梳理,不僅能幫助我們重新探索被西方文明異化的東方,也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發現被儒教文化排斥、壓抑的“基層文化”。因此,金先生認為“新子學”將開拓“新學問的視野”,給當代中國學術發展帶來廣闊的空間和蓬勃的生機。
針對在場專家的質疑與肯定,玄華博士進一步重申了“新子學”的理論内涵,嚴格區分了作為“新哲學”出場的“新子學”與作為“學術文化工程”出場的“新子學”這兩種學術形態,重點闡釋了“新子學”消解中心、多元對話的學術思維與導向,具體闡明了“新子學”哲學介入學術文化發展的基本方式,以及在“新子學”視域下傳統經學的轉型等問題,初步實現了“新子學”理論框架的構建。
此外,本次會議還深入探討了諸如:“新子學”究竟是“新之子學”還是“新子之學”;“新子學”學科的建設與“新子學”精神的傳播;“新子學”與傳統士人精神的重建、“新子學”視域下具體文化現象的闡釋等問題。有關會議的具體情況還可參閲崔志博《“新子學”大觀——上海“‘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光明日報》,2013年5月13日第15版)以及刁生虎、王曉萌二先生專文《弘揚子學精神,復興文化傳統——“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故筆者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三、 “新子學”理論建構的困境與突圍
任何新事物的産生和成長都是需要經過衝破舊有的體制與觀念,逐步實現自我建構,從而發生積極影響的較長過程。作為學術界新事物的“新子學”要獲得自我的合法地位,就必須面對困境尋求突圍。
(一) 困 境
從當前有關“新子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其理論建構面臨着諸多困境,大致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當前學界的認知誤區
學界誤區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新”看成一種“時髦”的學術思潮,將“新子學”比附於當前所流行的新文學、新史學、新經學、新儒學、新法家(學)、新墨家(學)等時新産物,並試圖以此為參照建構“新子學”的理論體系。事實上“新子學”應是建構於諸子思想之上,並賴以融通中西學術的新哲學和新學術理念。正如華北電力大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教授王威威在《“新子學”概念系統的建構》中指出的那樣:“新子學的建構在重視子學的多元性的同時也應重視子學作為一個整體的相互融合和統一的一面。”而我們的“新子學”是超越於任何單一學科或領域的系統文化工程,是指導學術轉型,實現社會進步的全新思想。
學界另一方面的誤區是將“新子學”的“新”與傳統的“舊子學(諸子學)”相對,從而簡單地理解“新子學”即是當代的“子學”,即“新之子學”,並由此推論,“諸子”從清末就開始“新”起來了。事實上“新子學”的“新”主要體現在學術思維、學術方法以及由此建構起來的全新的思想内質。這一點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歐明俊在《“新子學”界説之我見》中已有所認識,他提出“新子學”在著作模式、著述體例上也要有新東西,要有語言上的創新;“新子學”不能只滿足於個人著述,應注重新創學派,開創學術新局面;“新子學”研究要有全球意識,追求國際大視野,大格局、大氣象、大境界。
總而言之,“新子學”不是對舊子學的單方面承繼抑或轉變,而是在舊子學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順應學術開放對話的大趨勢,充分合理地利用當今世界各個領域的知識文化成果,實現中國當代學術的整合與重建。
2. “新子學”核心理論的缺席
自方勇先生《“新子學”構想》一文刊發以來,學界對“新子學”多報以欣賞的態度,其中不乏著文回應者。“‘新子學’學術研討會”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更湧現出一系列具有啓示性的論文和學説。除傅璇琮、張雙棣等上文提及的學界前輩的重要發言以及高華平、玄華諸先生針對“新子學”理論的宏觀性論文外,尚有許多從各自研究領域出發且極具啓發性的專題性論文,比如韓星《新國學的内在結構探析——以新經學、新子學為主》、郭梨華《莊子學躍進“新子學”的變與不變》、謝清果《還原,重構與超越——“新子學”視域下的傳統文化傳播戰略思考》、張雷《新聞人要做“新子學”的推動者》以及筆者拙文《“新子學”的本質與使命——從子學與士之關係展開》等。當然還有部分學者從現實生活出發,各自提出了“新子學”的“暢想”,如湯漳平《“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李若暉《“新子學”與中華文明之未來》、楊林水《“新子學”應如何進一步走向全球》、吴勇《以諸子的精神面對現實——“新子學”的任務淺議》、鄭伯康《“子商”構想》等。
這些論文和發言無疑對“新子學”理論的建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除了玄華博士、韓星教授及金白鉉教授等少數學者外,其餘學者多未能從理論層面超出方勇先生的“構想”框架,而且直接回避了何謂“新子學”理論以及如何建構“新子學”這一核心命題,導致了“新子學”核心理論的缺席。
3. “新子學”理論價值的“新”使命仍不明確
儘管與會學者大多提及了“新子學”的當代發展問題,卻很少對“新子學”之“新”使命做出明確闡釋。誠然,“新子學”的建構需對子學的發生、發展、成熟的完整過程進行必要的梳理,但是其更要分解和重構舊子學(諸子學)、全面融入當代世界的學術體系,從而建立一個融通開放的新學術體系,促進世界學術的整體建構和發展。
(二) 突 圍
要突破“新子學”理論建構所遭遇的重重的困境,需從三方面着力。
首先必須建立中國學術的話語體系。我們應借助傳統學術資源的進一步整合充分吸收諸如天地、陰陽、道理、仁義、禮法、心性、虚静、情欲、理氣、無為、形名、名實、知行、有無、道器、體用、本末、法術、時勢等核心理念與西方哲學中的各種學術話語建構一套立足本土又融匯當代西方前沿理論的獨立學術話語體系。方勇先生在《“新子學”申論》一文中曾指出:“新子學”是理解中國傳統學術的全新視角,其探索的是一個新的學術思想圖景,是用新的視野去審視古代傳統,重新定位子學之為學術主流,是要找尋經學籠罩下被遮蔽的東西;同時用批判的視角去看待現代的學科體系,重新劃定研究對象和研究思路,要補上學科框架下被剪裁掉的東西。“新子學”還要充實國學概念,賦予其實質的内涵,以發掘中國學術曲折多元的歷史真實,推進具有中國氣派的現代學術的生長。此即“新子學”之所以為“新子學”*方勇《“新子學”申論》,《探索與争鳴》2013年7月,第74頁。。要融合西方首先要自我發現,充分去蔽。而要建構新的學術話語體系更重要的就是要吸收“異端”思想。縱觀整個中國學術史,每一類學術話語體系的新變和成熟都與新的思想文化質素的融入密切相關,比如佛學的廣泛傳播引發了魏晉南北朝學術思想的多元展開,開啓了隋唐以來以經學為主導的學術的新變,並作為“異端”成為宋明理學與心學得以開展的重要力量和構成元素。至於後來的西學東漸,則直接促成了傳統學術與現代學術的分野。因此,“新子學”理論的建構勢必在重新梳理國學典籍的基礎之上,不斷吸收外來思想,形成中西合流,直面當下之新學術。正如方勇先生所指出,“必須看到,西化是現代中國學術的命運,是不得不套上的魔咒。要進入到現代世界,就必須先要把這個魔咒捆在自己身上,直到最後解開它。所謂中國性的訴求,就是思考怎麽解開這個魔咒,也就是如何找到中國學術的問題和話語方式。”*同上,第77頁。
其次,必須真正實現學術理念的更新。方勇先生認為:“‘新子學’希望開闊視野,深入研究,開掘中國學術表象後的真實。……‘新子學’不同於過去子學的一點,在於其嚴格的學術意識,希冀在現代學術的標準下來整理學術歷史,發掘思想真意。”*同上,第75頁。方勇先生意識到現代學術的多元性、自覺性和獨立性即“新子學”所要尋求的現代“學術意識”。但是學術意識的生成有賴於學術理念的更新,因為學術理念才是學術創新的内在動力,只有實現理念的新變才能真正推動學術的發展。那麽如何才能實現當代學術理念的生成呢?無外乎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要從傳統資源中獲得創生的動力,同時又必須擺脱傳統學術思想的束縛。比如四部之學尤其是經、子之學是中國學術得以發展的源泉與動力,但是我們決不能固守這一學術傳統,而應走向哲學、詩學、美學、科學等現代學術界域,以“新子學”擺脱對傳統知識材料的依賴,整合和重構古今學術思想,引領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以獨立、開放的心態去直面不斷創生的外來知識,不斷超越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籠罩下的學術的固有局限,改變當下不合理的學術形態,最終通過學術的方式化解個體存在與技術理性之間的矛盾,創造一個以學術建構自我、刊定社會進程並影響整個世界的新時代。
再次,必須以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建構作為“新子學”理論的核心使命。
我們應通過對四部文人的個案比較和群體性分析,把握中國士人傳統宇宙觀的形成及其制約生命自由的根源,尋求中國士人精神建構、轉型與重構的歷史契機,再加以後現代哲學理論的觀照,從而既有效克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不利因素,又積極地避免後現代主義過度消解權威所帶來的精神疲敝,真正實現當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價值重構。“新子學”所提煉出的“子學精神”,是在揚棄經學一元思維和大力高揚子學多元思維的前提下,對世界和人的本質的重新理解,它是子學的真正覺醒和子學本質的全新呈現,將為未來學術文化的走向提供選項*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 年9月9日。。當代世界充斥着後現代理論所帶來的虚無主義,既有價值上的虚無所造成的痛苦,也有存在上的虚無所産生的絶望。與此同時,許多思想新鋭,敢於在思想之路上探尋的學者也都遭遇着學術上的虚無。學者的生存狀態令人堪憂,高校教育的現狀也使人憂心忡忡,博士生跳樓,教授自殺或過勞死等事件屢見報端,高校兇殺案件也時有發生,而近來的復旦投毒案更將高校教育的弊端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儘管這一切都只是特例,卻足以暴露虚無主義侵蝕下,個人價值感的喪失,責任感的弱化以及道德感的衰退所造成的種種心理失衡現象。因此“新子學”必須直面當代思想的痼疾,提供解救的良方,重塑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世界,充分確立個體生命存在的合理性。
總之,經學主導下的學術思維,遵循的是一系列雜亂無章的現象排列,從而導致中國學術整體呈現出瑣碎、無序、僵化、割裂的形態,缺乏自我創生的活力。儘管當代學界“儒學一統”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但是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卻仍然固守着一種封閉而單一的“文學性”抑或“思想性”研究,以至於將許多優秀的作品淡出於“文學”的視域。與之相對,哲學、歷史又各執一端,將中國傳統學術人為地切割成了一個看似系統實則凌亂錯糾的學術構架中。“新子學”强調“學術的還原”,提倡多元的視域和整體性的研究方法,並將學術與時代氣運、知識精神、個體價值等關聯起來,對當前先天不足,後天發育不良的困境中的中國學術無疑是一劑涵養滋潤的良藥。
縱觀數千年的中國學術史,除百家争鳴外,中國極少出現類似於西方學術的巨大思潮和運動,更缺乏系統的原創性學術成果,而“中心論”與“專制主義”為核心的經學思維下的士人傳統,則造就了一種上行下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閉合倫理模式,形成了一整套僵化保守、自私虚偽的民族人格精神,一種試圖通過自我克制而進入超越境界的道德訴求以及一門自私冷漠、忽視個體生命的處世哲學。因此,“新子學”正是要以直面問題的姿態,從複雜的學術現象研究中抽象出一套具有當代詮釋意義的理論體系,建構一個開放、延展、多元、互存的學術生態系統,實現對士人精神的重新發現,尋求以學術改變世界的全新方式。
結 語
“新子學”是當前學界正在建構的一種新的中國化的學術思想與方法體系。自2010年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學‘構想’”以來,“新子學”已經從最初的個人“構想”逐漸發展為一種廣為學界所知的學術理念,並初步形成了“新子學”的理論思想和方法體系。與此同時,由於“新子學”核心理論的缺席,這一學術遭遇了外界較多的質疑。因此,當前“新子學”理論建構的主要任務在於明確“新子學”理論的核心内容,確立“新子學”理論建構的主要目標,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實現中國學術理論的更新,重構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世界。
[作者簡介]曾建華(1983— )男,湖南邵陽人。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道教文獻與先秦兩漢神仙思想研究,已發表學術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