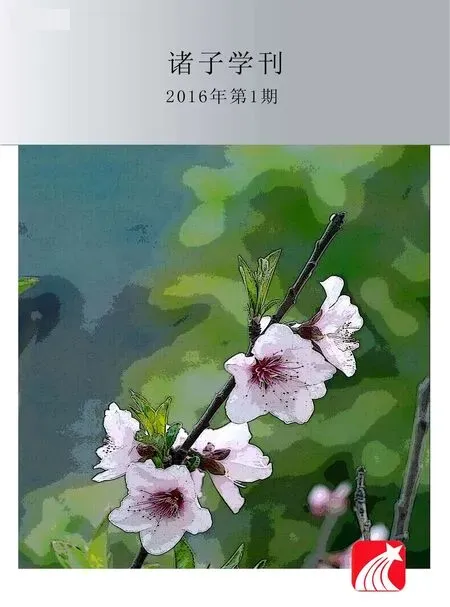構建“新子學”時代新的女性話語體系
張勇耀
構建“新子學”時代新的女性話語體系
張勇耀
傳統子學研究基本以男性話語體系為主,這導致傳統子學研究中女性話語缺失。同時,在傳統子學研究中,對先秦諸子女性觀的認識也存在頗多偏差。那麽,從當代女性的視域出發,建構女性話語體系“新子學”,這無論對子學學術層面的研究,還是對當代女性話語體系的傳播,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當代女性 女性話語體系 傳統子學 新子學
中圖分類號 B2
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學”的概念並將其進一步深化和推廣,這對於解決當代人的精神文化困境來説,是一劑良方。但我們也發現,傳統的“子學”研究中有着女性話語的天然缺失,如何構建女性話語體系“新子學”,可以説至關重要。我想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
一、 傳統“子學”研究中女性話語體系的缺失和對女性觀認識的偏差
傳統“子學”思想體系屬於男性話語體系,其“君子”話語體系就是一個明證。無論《論語》的“君子坦蕩蕩”、“君子固窮”、“君子喻於義”,還是《荀子》的“君子執之心如結”、“君子敬其在己者,不慕其在天者”,抑或《老子》的“君子有造命之學”、“君子之交淡如水”,它的話語中心都指向男性。這一方面是因為特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使女性的生活範圍更多局限於家庭和田間地頭;另一方面從堯舜禹開始,“修齊治平”的思想觀念更多是對男性提出的要求,因此男性著書立説,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思想史料。而在當代的子學研究中,處於思想體系上層建築的,依然以男性居多。男性解讀下的“子學”價值體系,對於廣大女性的接受和領悟來説,無疑存在隔膜。這就造成了兩個缺失: 一是先秦話語體系中女性話語的缺失,二是子學研究中當代女性話語的缺失。
在傳統“子學”男性話語體系視域下,常會有人得出女性在古代不受重視甚至被歧視、壓迫的結論。如《論語》中“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把女子和小人放在一起,顯示孔子對女性的不尊重甚至歧視;到《孟子》,所謂“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成為“三從四德”的理論依據,似乎毫無迴旋餘地。荀子不但説“夫婦有别”,而且提出“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荀子·解蔽》還認為:“桀蔽於妺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虚宗廟之國也。”此處所謂妺喜和妲己使夏商亡國,就是典型的紅顔禍水論。再到法家,韓非子大談“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韓非子·十過》),“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術: 一曰在同床”,“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在韓非筆下,女子實比洪水猛獸更甚,既見識短淺又工於心計,既常懷妒忌又心狠手辣,實無一處可取。
以傳統“子學”男性話語體系解釋或研究“子學”,必然會把“子學”研究引向一個比較危險的方向,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當代女性對於子學非常優秀的思想文化的價值認同,同時又會對不讀先秦諸子的普通女性産生一些不良影響,從而使先秦諸子思想的光芒無法滲透到當代女性的認知結構中去,而這對於激活、傳播先秦諸子精神的“新子學”課題的研究發展,至少是不全面的。
所以,對先秦子學中女性觀的研究亟需糾偏,要打破男性話語體系,從當代女性視域構建“新子學”女性話語體系。具體而言,一是要糾正一味聲討的態度,二是要糾正缺乏心理成熟度較高的優秀女性解讀的局面。由於性别的原因,女性天生偏於感性,偏於對現有生活方式的接受和習慣,偏於形象思維,對理性的文字有着天然的抵觸,對抽象思考有着先天的不足。
然而面對人類最初的思想文化珍寶——“子學”的發掘和研究中,如果缺失了女性的聲音以及女性話語體系,這樣的“子學”研究無疑是不全面的;在向大衆傳播的過程中,没有經過女性生命意識的内化,没有將這些人類共通的思想和情懷轉化為女性視域,没有當代女性所參與的話語構建,也依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以當代女性的視域,從女性話語體系研究解讀先秦諸子的思想要義,提煉其中的思想精華並傳播於當世與後世,這對“新子學”研究具有積極的意義和價值。
二、 “新子學”女性話語體系構建及其意義
“新子學”的内涵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發掘那些被歷代研究者忽略的子學精神和價值體系。而重新梳理和認知先秦諸子話語體系中女性話語,從而構建“新子學”女性話語體系,便是這一内涵中非常重要的一項。
我們可以回到歷史現場,對傳統“子學”女性話語體系做一個歷史分析。從歷史角度來看,“子學”女性話語體系是相對缺失的,缺失的原因在於男女學習内容和社會分工的不同。
先秦時期,雖然貴族女子和男子同樣享受教育,女子在八歲以後同樣在臨水而居的“辟雍”或“泮宫”中集體學習,但與男子所學的“六藝”不同,女子所學的大多是禮儀、桑麻等實用的生活技巧,偶有一些優秀的女子能通過家庭教育獲得一些文化知識和思想啓蒙,但總體上能够獨成體系地提出某種可以在當世和後世都産生較大影響的著述,可以説非常之難。也就是説,當時以家庭為主要活動範圍、以勞動為主要生活内容的女性,其實並没有參與到這些思想文化體系的話語構建中來,所以其中女性觀點、女性話語的缺失,就是必然的。而且,就算有過一些卓越女性,有過一些有價值的論述,在後世編訂者以一定理論框架所進行的反復遴選中,也很難得以流傳。
另一方面,那些優秀的男性思想者著書立説,其中除了作者的自我勉勵,更多是對當時先學“小學”,後學“大學”的有着“修齊治平”之志向並將成為國之棟樑的後學男性的勉勵和要求。他們所道出的大多是人類共通的哲理和情懷。
但“子學”女性話語體系則相對缺失,其實從歷史來看,先秦女性也有一定的話語體系,探賾發微,必然對“子學”話語體系産生一定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數不清的偉大女性。一條比較明確的線索是: 學宫制度加上家學,使一些卓越的貴族女子在成長過程中吸收了較多優秀思想和人格的養分,她們一旦走入社會,少年時代曾經受過的教育就會如布袋中的錐子,漸漸露出屬於她們的鋒芒。而這些女子能够顯露鋒芒的時候,常常是她們嫁為人婦,成為“夫人”的時候。由於貴族身份,她們所嫁之人也常常是與之門當户對的仕宦之子。她們的才學智慧,就常常通過相夫教子來實現。西漢劉向的《列女傳》,便是這類優秀女性的事迹彙編,所記載的優秀女性基本都出自先秦。
一位有見識的夫人,常常會成為輔佐丈夫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遇到特殊事件時更顯示出其重要作用。《左傳》莊公四年記載了一位名叫鄧曼的夫人,楚武王將伐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臨出兵感覺心慌不安,是不吉的徵兆,這仗還要不要打?夫人鄧曼歎了口氣説:“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聽了這番話,“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而帶來的結果是,隨國與楚國結盟,楚國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樣一位深明大義的夫人,在歷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頁。
到戰國後期,這類女性就更多。秦國的宣太后,齊國的君王后,趙國的趙威后,都是能够參與政治大事的優秀女性的典型。秦國的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親,昭王年幼即位,宣太后以太后之位主政。宣太后以母后之尊,犧牲色相與義渠王私通,然後設計將之殺害,一舉滅亡了秦國的西部大患義渠,使秦國可以一心東向,再無後顧之憂。趙威后是趙孝成王的母親,趙孝成王即位時尚年輕,國家大事便由母親趙威后代理。趙威后重視民生,體恤百姓,因而威信大增。《戰國策》記載: 齊王建派遣使者問候趙威后,還没有打開書信,趙威后問使者:“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有點不高興,説:“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趙威后回答説:“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這些見識,即使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有着積極的意義。讓長安君入齊為質一事,則更表現了一位深明大義的母親如何在國家大計與愛子之情之間做出選擇。齊國的君王后是齊王田建的生母,史載其非常賢德,與秦國交往謹慎,與諸侯講求誠信,因此田建繼位四十多年齊國未經受戰争。
在王室的女性如此,作為大臣的“夫人”們,又當如何?齊湣王的侍臣王孫賈在跟隨齊湣王逃亡的時候,齊湣王被淖齒騙出去殺害了。王孫賈找不到國王,回到家卻劈頭挨了母親的一頓罵:“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母親的憤怒,終於激起了侍臣王孫賈的鬥志。“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這位戰國母親,生逢亂世,她的詞典裏便有着比别的時代的母親更加豐富的辭彙——除了“愛”,還有“忠”;除了“家”,還有“國”;除了“親情”,還有“道義”;除了“温暖”,還有“責任”。再比如趙國趙奢的夫人,趙括的母親,當趙王準備派趙括接替廉頗為將指揮長平之戰時,她説:“括不可使將。”她還給趙王上了一封書,説趙括與父親心地有很大的不同,希望趙王不要派他領兵。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阻止不成,趙括的母親表現了最後的智慧。她對趙王説:“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您一定要派他領兵,如果他有不稱職的情況,我能不受株連嗎?“王許諾。”結局則被趙括的母親不幸言中了。
這些“夫人”們的智慧和見識,可以説歷經兩千年依然光彩照人。《左傳》《戰國策》雖為男性所寫,但他們在記述影響歷史的重大事件時,也並没有完全忽略和湮没女性的光輝,而是在其中表達了他們由衷的敬意。
這些優秀女性無疑增强了“子學”中的女性話語體系。誰説“君子終日乾乾”、“君子進德修業”、“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坦蕩蕩”、“君子執之心如結”、“君子敬其在己者”、“君子有造命之學”這些話語只能是對男性説的,而不包括女性?誰説孔子的修身態度、治學方法、教育思想只是對男性産生影響,而不能被女性吸收和運用?誰説老子的“上善若水”、“天長地久”反映的不是天地人生的共通哲學思考而只是對男性的啓迪?
所以,“新子學”女性話語體系構建就是要發掘和提煉傳統諸子學説中積極的女性觀並得到廣泛傳播。
從當代女性視域來説,無論先秦典籍還是傳統的“子學”中,對女性表示尊重、愛護、同情的文字非常之多。
如先秦典籍《詩經》和《周易》中就有大量這樣的文字。《詩經》對女性的歌吟非常之多,無論是“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的少女懷春,還是“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的天真可愛;無論是“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的信誓旦旦,還是“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的夫婦對話,都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生命深處的真實率性、自由美好。而其中的許多閨怨詩、棄婦詩,則表達了對於女性不幸命運的同情。許穆夫人的《載馳》,更多表達了對“大夫君子”的斥責。那首“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的《行露》,則更是保留了民間女子的尊嚴和憤怒。這就是積極的女性觀,充滿了讚美、尊重、同情。《周易》中同樣有這樣的思想體現。天地、陰陽本即是自然規律,大地“厚德載物”的母性,本身就是對女性的讚美。在“女性觀”中,它雖然强調女子矜持柔順、内斂隱忍,但仍然給予女性特有的發展空間。比如“家人”卦的“利女貞”,即倡導女性在家庭中要堅持德性,保有真正的德性。《易》還主張,特定情況尤其是不利處境下,女子要有主見,不屈於淫威。
在傳統“子學”中,諸子在當時的時代格局之下,並没有對女性提出“修齊治平”的要求;而在諸子著作中,對於女性的論述其實非常之少。無論是《論語》還是《孟子》,在當時“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的社會環境下,不大規模地提出女性應該恪守的規範和道德體系,其實已經表明了這些先進的思想家們所要探討的是治國平天下的發展大計,而非兒女情長的人生小節。許多時候,忽略反而是出於保護和尊重。更何況,先秦諸子特别是儒家對於“孝”的提倡,本身就是對做了母親的女性地位的尊重。《孟子》中,“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生命意識的覺醒和對男性世界的女性觀照。
仔細閲讀《老子》,會發現道家的一貫主張是“陰陽並重”。老子讚美“柔”,讚美“水”,並使用“牝”、“雌”、“母”等陰性辭彙來喻“道”,對女性的品格和精神抱有由衷的欣賞之情。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樣的句子,本身就包含着男女兩性的價值同等重要的意思。另外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等内容,更是歌頌了母親生而不有的博大寬容;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等句,又表達了老子對女性柔韌品格的讚賞。
因此,構建“新子學”背景下先秦諸子研究的女性話語體系,不必糾結於偶見於字句中的“女性觀”,而應積極提煉先秦思想中共通的哲學價值和人文思考。特别是當今時代的女性已非先秦兩漢的女性,更非宋元明清的女性,都有着獨立自主的思想意識和與男性同等的社會地位。應當以一種先進的歷史觀超越綁縛在女性身上的無形繩索,吸取中國最早也是最優秀的精神文化資源,在當代語境中重新構建屬於女性的話語體系,這無疑能够讓當代女性更加智慧、更加理性地參與國家社會事務、文化思想發展,從而在“新子學”的研究和大衆傳播中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 “新子學”女性話語體系傳播及對當代女性的影響
當代女性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如何?僅就生活在城市的本科學歷以上的知識女性或職場女性而言,“無知無覺”者仍是大多數。這種“無知無覺”,表現在個人生命意識的淡泊,對時間流逝的殘酷和自我價值的實現没有緊迫感。所以如何將“新子學”女性話語體系,特别是先秦諸子思想中積極的生命意識和價值觀,推廣到大衆女性當中,成為當代女性精神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説非常重要。
因為性别本身的原因,女性天生細膩、敏感,對同樣的語句可能會生發出男性想象不到的獨特理解,基於此,女性獨特的生命意識對先秦諸子思想也會有獨特體味。比如前幾年很火的于丹講述的《論語》,雖然其中的很多觀點都屬於讓專家學者不屑的“歪解”,但她所做的大衆傳播的效果卻是極其成功的。于丹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她能够以一個女性的視角,把艱澀深奥的古典智慧,通過深入淺出的話語轉换,一變而為當代語境下的當代話語。比如她説:“《論語》終極傳遞的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樸素的、温暖的生活態度。孔夫子正是以此來影響他的弟子。”“樸素”、“温暖”這樣的辭彙,就是典型的女性視角。且不談于丹解讀的學術含量,只這種女性參與解讀和傳播先秦典籍中的思想和智慧的勇氣,便是可嘉可敬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我們並不一定要急於指責于丹的專業水準過低,而是期望專業水準更高的更多“劉丹”、“王丹”出現;我們更希望出現一種女性對先秦典籍解讀的“百家争鳴”,或者女性構建當代思想體系的“百家争鳴”局面,這於社會文化的繁榮,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當然在女性解讀和傳播子學精神的過程中,女性本身所擁有的知識水準、文化視野和思想高度,也是極其重要的。歷史上就有反面的案例,有兩位優秀的女性頗讓我們感覺糾結。一是班固的女兒班昭,一是唐代的宋若華。這兩位史傳其名且有思想著述的優秀女性,前者寫了《女誡》,後者寫了《女論語》。她們無疑都是子學精神的傳承者和傳播者,而且能够在以絶大多數男性創造思想經典的時代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著述,的確非常不易,也非常令人可敬。然而從她們所著述的内容來看,她們顯然是在把先秦文化中拴在女性身上的繩索,梳理好頭緒並重重加固,力求使後世的女子都在這繩索中不越規矩。當然這也和儒家文化在當時的經學化有極大關係,並不全是她們自身的問題。《女誡》中説:“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特别是“婦德、婦言、婦功”,更為宋明之際的“貞節觀”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女論語》中的“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顯然更為具體。陳東原先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指出,班昭如此優秀,她的女兒就不會這麽優秀了,因為她的理論首先戕害的就是她自己的女兒。這也許就是後世女子再難出思想家的原因之一。
所以,當代女性解讀子學,如何從中提煉優秀的思想文化,益於當世也益於後世,既需要非常寬廣的視野,更需要非常謹慎的態度。只要有着廣博學識並有較高思想層面,且有着强大的歷史責任感的優秀女性,從當代女性視域出發,以女性話語體系參與到“子學”解讀和傳播中來,“新子學”就一定會生發出更為温暖燦爛的光輝。相信這也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作者簡介]張勇耀(1972— ),女,山西呂梁人。畢業於山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任《名作欣賞》上旬刊主編、總編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