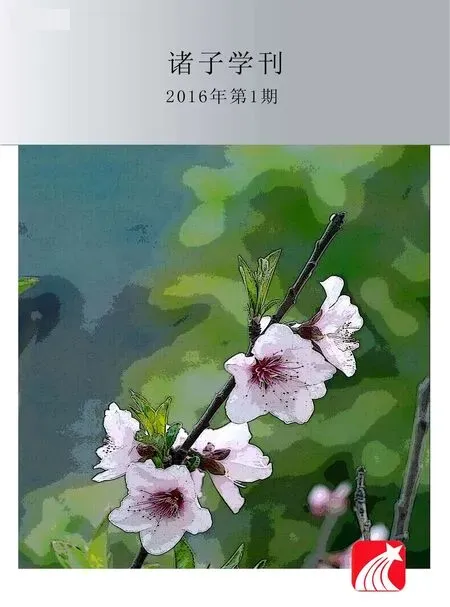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子學”之“關注現實”的思考
耿振東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子學”之“關注現實”的思考
耿振東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内容。方勇教授提出的新時期要推動“新子學”發展的學術構想無疑將為我國的文化繁榮與民族復興推波助力。本文從文化傳播普及、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對接兩個角度,對内涵豐富的“新子學”之“關注現實”的子學精神的實踐提出個人的看法。
關鍵詞 新子學 關注現實 文化普及 文化對接
中圖分類號 B2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億萬中國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也是凝聚億萬中國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動力。民族復興夢想的實現,需要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力量的提升。其中,文化的作用尤其不能忽視。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它深刻地揭示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文化建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和可能發揮的巨大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以方勇教授為領銜的旨在“為民族文化復興提供助力”(《再論“新子學”》)的“新子學”及他這幾年不辭勞苦的學術實踐,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較强的現實意義。它是倡導者内心深沉的民族關懷的體現,是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民族文化自信的表徵。
方勇教授在《光明日報》先後發表的《“新子學”構想》(2012年10月22日)、《再論“新子學”》(2013年9月9日)兩篇文章,對“新子學”的産生、“新子學”的内涵、“新子學”面對西學如何建立自己的學術體系、“新子學”是國學發展的歷史必然、“新子學”發展的時代應對策略五個方面問題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論述。他提出“新子學”是對“多元、開放、關注現實”的“子學精神”的“提煉”(《再論“新子學”》),“新子學”“是在揚棄經學一元思維和大力高揚子學多元思維的前提下,對世界和人的本質的重新理解”,“‘新子學’將承載‘國學’真脈,促進傳統思想資源的創造性轉化”(《“新子學”構想》),筆者認為,可以作為“新子學”發展的綱領性指導思想;“今後‘國學’不再是一枝獨秀的孤景,而將上演百家合鳴的交響”(《再論“新子學”》),筆者認為,它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這裏,僅就“新子學”如何“關注現實”“為民族文化復興提供助力”這個問題談幾點個人的思考。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司馬談的這句話指出了學術與現實治道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先秦諸子百家,没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粹學術研究者。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墨家“强本節用”,法家“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名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道家“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皆是緣拯救時弊有感而發,皆是積極參與謀劃國家治道之術的表現(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周遊列國宣傳“為政以德”;墨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力倡“兼愛”“非攻”;老子韜光養晦,建議“治大國若烹小鮮”;韓非甘冒“吴起支解而商君車裂”的亡身之禍,堅持“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他們“關注現實”的學術品格被之後歷代學術研究者繼承、發揚。董仲舒研究《春秋公羊傳》,從中闡發出“大一統”思想,幫助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為自西漢以來的歷代封建王朝奠定了思想統治的理論基礎。王安石研究《周禮》,從中闡發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的思想,幫助神宗進行變法革新,緩解了神宗朝政積貧積弱的緊張局面。康有為研究今古文經學,從中闡發出古文經為劉歆為王莽篡漢而偽造的新學的思想觀點,同時以“通三統”、“張三世”的今文學説為基礎,形成其變法維新的理論學説,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運動。可以説,一部子學史就是學術與現實治道互為基礎、互為動因、相互促進、相互服務的歷史。
春秋以前,學術掌握在貴族“王官”手中。無論是記史、祭祀、卜筮,製定法令、曆法,還是製禮作樂等一系列治道活動,都是由身在統治者階層、體現統治者意志的“王官”們完成的。這一系列治道活動,實際上就是當時的學術活動。春秋以降,王官失位,學術下移,王官學術一變為士學術。從表面上看,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學術,而從實質上講,王官學術與士學術並没有本質的區别。從産生淵源上看,王官學術孕育了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士學術。這正如《漢書·藝文志》所言:“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從最終的服務對象上看,無論是王官學術,還是士學術,都毫無例外地服務於現實統治。戰國時齊國稷下學宫,可以説是戰國諸子百家争鳴的縮影。郭沫若認為:“齊國在威、宣兩代,還承繼着春秋末年養士的風習,曾成為一時學者薈萃的中心,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注: 指稷下學宫)形成了一個最高峰的。”(《十批判書》)據《史記》,當時稷下學宫養士“數百千人”(《田敬仲完世家》),他們“期會於稷下”(《史記集解·田敬仲完世家》引劉向《别録》),相互切磋思想,開展辯論争鳴,其學術活動絲毫没有離開治道這個中心。關於這一點,司馬遷説得很清楚:“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自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儒家思想成為歷代封建統治的主宰思想,儒家學術成為衆多學術流派中獨領風騷的顯學。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在朝為官的上上下下各級官吏,多是深諳儒家學術的學者。由於儒家學術為中國封建社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信仰體系、價值標準,整個封建社會的各種活動便圍繞儒家立身處世的原則展開。這樣,以儒家為代表的學術思想與以專制君權為中心的封建體制開始相互支撐、相互促進。這一政治、學術合二為一的格局隨着隋唐以來開科取士,儒家經典在科舉考試中所占地位加重而越來越明顯。它所導致的結果是,精通儒學的學者多是官員,官員又大多精通儒學;學者的學術主張不離治道應用,官員的治道主張又多是對自身學術研究的實踐。
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斬斷了以儒學為業的學者的晉身之階;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子學已不再具有神聖不可動摇的地位。人們深感子學不足以救國救民,於是仰慕並學習西方的政治學説、經濟理論、軍事技術、教育體制,並開始為在中國實現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科學的社會理想而拼搏奮鬥。傳統的子學,由於失去了作為治道的用武之地,當然也就失去了昔日對其矻矻以求的多數學者的信賴與擁護。此時,很少有人再回到中國的子學中尋求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武器,即便有,也難以抵擋西方學術狂飆突進式的沖決和立竿見影的治道實效性的誘惑。從這個時候到新中國建立的三十多年裏,儘管報刊創辦、著作出版如雨後春筍,數量多得驚人,也不乏真知灼見,而且關心民瘼、關注社會發展,甚至借助子學思想為當時統治者獻計獻策的作品多如牛毛,但真正被執政者採用的東西卻很少很少。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突然的社會巨變,使現實治道主動和傳統子學分道揚鑣,傳統子學無奈地與現實治道告别。
新中國成立特别是改革開放以後,隨着中國工業化建設速度的加快和中西交流對話的不斷展開,人們愈加認識到民族文化的重大價值。“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争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固然,傳統子學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作為“帝王師”、“社稷圖”出現,但作為億萬中國人的精神之根,它卻是“中華文化最具創造力的部分,是個體智慧創造性地吸收王官之學的思想精華後,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學、美學、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技術等諸多領域多維度、多層次的深入展開。”(方勇《“新子學”構想》)它在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信方面卻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方勇教授説:“諸子學作為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主體,必然是未來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中國重新崛起成為世界中堅的有生力量之一。中國學派構建之際,‘新子學’正應運而生!”(《“新子學”構想》)他從傳統的子學現象中提煉出“多元、開放、關注現實”的“新子學”精神,並將以此“推動中華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再論“新子學”》),這種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自覺的文化擔當意識令人敬佩。那麽,“新子學”應怎樣發展才能體現其“關注現實”的精神最終“為民族文化復興提供助力”呢?在這裏,我僅就想到的兩點作以下陳述。
一、 “新子學”研究者在專業領域發展繁榮“新子學”的同時,應將“新子學”納入大衆文化普及的範圍,也就是説,他們應自覺擔負起文化普及的重任。
“新子學”研究者多是學院化的知識分子,他們在自己研究領域内創造的知識是前人無法相比的。但是,他們創造的這些知識僅僅是一種專業化的、技術化的知識,而不是一種公共性的知識。他們掌握着大量的知識資源,多數情況下是將其變成了自己私有的文化資産,而没有與大衆共享。如果“新子學”完全朝着專業化、技術化的方向發展下去,不將它“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融入大衆的知識視野,化為大衆的公共文化生活,圍繞“新子學”的一系列學術活動便不能真正體現“新子學”“關注現實”的精神宗旨,從子學中提煉出來的“關注現實”的“新子學”精神也就成為空洞的口號。
從文化學的角度講,凡是稱之為文化的東西都有一個受衆域大小的問題,越是受衆域大、越是被大衆接受掌握了的文化,就越能體現文化的普世價值,越容易發揮其教育認知功能、凝聚功能,因而也就越能够發揮文化的軟實力,從而轉化為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强動力。所以,為了順利實現“新子學”“為民族文化復興提供助力”,必須將“新子學”納入大衆公共文化普及的範圍。也就是説,“新子學”研究者在身為專業知識分子的同時,要身體力行地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大衆可以接受消化的文化形式,積極向大衆傳播。事實上,“新子學”文化普及的重任,也只能由“新子學”研究領域的專家來擔當,因為這一領域的專家占據着“新子學”方面最雄厚的文化資本,是其他專業的任何人無法相比的;他們代表着“新子學”研究領域的權威,因而也就更容易牢牢把握“新子學”傳播的話語權。
然而,一方面由於現代知識體制建構的愈趨細膩、學科之間越來越壁壘森嚴,大衆文化的公共空間日益萎縮;另一方面由於大衆公共閒暇時間的增加和大衆文化消費能力的提高,大衆文化消費的市場卻在漸次擴大。二者的矛盾運動,使社會上出現了大量以出版業、報業、休閒雜誌、影視業、演藝業、网絡為載體的文化消費産品。這樣一個文化消費急劇擴張的時代,滋生出一批借助於媒體頻頻亮相的知識分子。媒體知識分子雖然也是在傳播大衆公共文化,但他們遵循的是市場邏輯,走的是市場化道路。一旦“新子學”文化傳播路徑被媒體知識分子把持,他們很快會被大衆誤認為掌握了“新子學”精義的權威、專家,“新子學”將在“一個煽情的演員手勢、一種矯揉造作的舞臺造型、一連串博取掌聲的誇張修辭”*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頁。中扭曲、變形、異化。在商品化、市場化的動機操縱下,“新子學”極有可能會喪失“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新子學”構想》)的文化功用。
二、 “新子學”研究者要整理那些代表人類文明發展大勢的古典精義,讓現代文化建立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
經濟全球化、信息网絡化,各國政治性對話的經常開展,帶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改革開放不僅帶給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大好時機,也使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遭受外來文化的挑戰與踐踏。改革開放使中國文化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在精神層面,都亦步亦趨西方現代文化。失去了民族文化,一個國家就失去了生存的靈魂。怎樣對待這場不可避免的文化衝突,怎樣在這場中西文化的交鋒中,使中華民族對自己的文化充滿自信,這是旨在“為民族文化復興提供助力”的“新子學”必須嚴肅面對的一個問題。
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做好“新子學”與西方現代文化的對接。所謂對接,就是在子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中充分挖掘具有西方現代文化意識的思想,對其加以闡釋、傳播,引導中華文化自覺、自然地朝着現代文化的方向發展,糾正國人以為一切現代文化皆非國人自造的錯覺,力避讓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具體來説,“新子學”研究者要挖掘、闡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中體現西方現代文化傾向的科學、民主、法治、市場這些核心觀念。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乏科學的思維與科技的創新。早在兩千多年前,《周髀算經》《黄帝内經》中的數學與醫學,《墨經》中的幾何學、光學,《山海經》中的地理學,《左傳》《淮南子》中的天文曆法,就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東漢張衡創造候風地動儀,用以測定地震方位。魏晉劉徽首創割圓求周法,對圓周率進行測算。唐代僧一行運用“複矩圖”測定北極高度。宋代則有指南針、火藥的發明。明代出現了四位科學家: 李時珍、徐光啓、宋應星、徐弘祖,其著作《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天工開物》《徐霞客遊記》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在當時均領先於世界。現代的民主制度以民有、民享、民治為内容,其精義在於人民享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中國封建專制的政治架構,使民主體制没有發展起來,但“新子學”中卻不乏民本的思想。先秦時期的《管子》説:“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管子·霸言》)《孟子》説:“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孟子·梁惠王下》)《荀子》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漢代賈誼説:“夫民,萬古之本也,不可欺。”(《新書·大政上》)唐太宗説:“若百姓所不欲,必能順其情也。”(《貞觀政要·儉約》)北宋的程顥、程頤説:“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二程文集》卷五)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説:“天下為主,君為客。”(《明夷待訪録·原君》)王夫之説:“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周易外傳》卷二)這些豐富的民本思想已表現出民主的萌芽,只要適當地對它們加以引導,就能實現民本與民主的對接。中國的法治思想産生很早。兩千多年前,《管子》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理念(《管子·明法》)。戰國時期的商鞅、申不害、慎到也都强調以法治國,韓非則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並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中華民族歷史上産生了多部法典,如戰國的《法經》、漢代的《九章律》、隋代的《開皇律》、唐代的《永徽律疏》、宋代的《宋刑統》、明代的《大明律》、清代的《大清律》。雖然現代化法治體制由於受到人治思想的影響在古代没有建立起來,但傳統文化中的法治理論還是很豐富的。現代化的經濟體制是市場經濟,它主張通過自由價格機制實現對市場資源的配置。而有關市場及市場經濟的論述,在我國古代早就出現了。《管子》一書曾明確提出“市者,貨之凖也”的命題(《管子·乘馬》)。這説明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已認識到了商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並通過貨幣來表現的市場規律。明代丘浚也認為,商品的價格是在市場交换中自然形成的,“市者,商賈之事。”“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凖折取舍。”如果政府對市場强行干涉,就會阻礙經濟的正常運行,最終有弊而無利,“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大學衍義補·山澤之利上》)由此可見,古代的中國已有了市場經濟的有關論述。鑒於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現實,只要“新子學”研究者充分挖掘其中的現代觀念,並加以合理的引導,在自己文化基礎上建立一種與西方文化頡頏的現代文化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建築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現代文化有其致命的缺陷。人類對能源的無限制開採,使自然資源面臨枯竭、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導致國與國之間衝突加劇、矛盾加深,由之引起世界的動盪不安。交通、网絡的飛速發展,使世界日益變成地球村,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卻日益疏遠。對人生價值意義的衡量,一變為對金錢攫取的多少,除了金錢,在價值的天平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砝碼。面對現代文化的不足,“新子學”研究者要積極挖掘、闡釋、傳播傳統文化中可彌補現代文化缺失的思想要素,借此建立起引導現代文化健康發展的思想體系。這不僅僅是“新子學”“關注現實”的表現,更重要的,它是只有“新子學”研究者才能擔當勝任。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哪些可以彌補現代文化的缺失呢?在這裏,試舉兩個例子。比如,在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上,中國文化重視“天人合一”。《孟子》説:“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孟子·盡心上》)認為人性天賦,性、天相通。《莊子》説:“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漢代董仲舒説:“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天人合一”强調人與自然一體,强調人與自然協調。自然界可以被認識,可以被利用,但人只有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前提下才能創造自己幸福的生存空間。任何違背規律的征服自然、開採自然,只能破壞人與自然這個共同生存的空間,最終因對方的殘缺而使自身受到傷害。貴和尚中,也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早在西周時期,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國語·鄭語》)。《荀子》也説:“萬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論》)“和”,不是盲從附和,不是不分是非,而是求同存異,共生共長。“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過度,又非不及。《中庸》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如果從政治學的高度分析、傳播貴和尚中的思想,對於維護世界和平意義重大。由此可見,傳播、弘揚子學固有的文化優勢,彌補、醫治現代文化的痼疾,是“關注現實”、“為民族文化復興提供助力”的“新子學”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者簡介]耿振東(1973— ),男,山東淄博人。文學博士,現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諸子與中國思想文化研究。著作有《管子研究史》,並已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