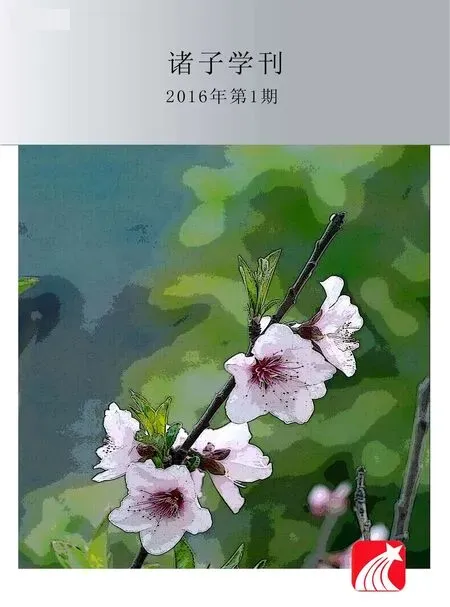再論“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
湯漳平
再論“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
湯漳平
“新子學”是當代中國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潮。我國正處於社會大轉型的時代,這樣的時代需要有科學的理論來引導和進行闡釋,“新子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種思考和回答,我寄希望於它能够在當今中華文化的重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子學”復興是時代的必然抉擇,它在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應以“新子學”推動和促進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關鍵詞 新子學 文化軟實力 中華文化重構
中圖分類號 B2
僅僅時隔兩年,海内外學者再度齊聚浦江之濱,共同探討有關“新子學”研究中的學術理論問題,反映出自“新子學”這一概念提出後,在學術界所引發的强烈反響。我以為,“新子學”不僅僅是一種口號,或是一種學術觀點,“新子學”應當是當代中國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潮。我國正處於社會大轉型的時代,這樣的時代需要有科學的理論來引導和進行闡釋,這特别需要學術理論界對相關問題、對社會現狀進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從而提出切實可行的思路來引領社會發展的進程。“新子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種思考和回答,我寄希望於它能够在當今中華文化的重構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上一届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提交了《論“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一文,側重談了經歷百年來社會大變遷之後,目前中華文化需要進行重構。而本文則希望借此機會,探討如何通過復興“新子學”,重新建構中華文化,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問題。
一、 “子學”復興是時代的必然抉擇
關於“子學”復興的重要性,在《“新子學”論集》一書中,有許多學者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林其錟先生從“子學”的原創精神、求實精神、争鳴精神、會通精神、開創精神等諸方面,提出應當承繼諸子的優良傳統來構建“新子學”學科。陳鼓應先生則在為該書所作序言中明確提出“子學興替關乎中國思想變革”,並從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發展歷程,聯繫今日兩岸的社會狀況,指出了弘揚先秦諸子百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在當今時代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義。當然,方勇先生的系列論述,更是從其内涵上深入闡述了“新子學”構想與全面復興諸子學的現實意義與歷史必然性。時代的巨變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學術理論來引領社會向正常健康的方向發展。“新子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並引起了大家共同的關注。
那麽,為什麽説“子學”復興是時代的必然選擇呢?我們有必要一起回顧一下歷史。雖然今天人們一致承認,兩千多年前的“子學”時代是中華文化史上最光輝的時期。然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子學”卻經歷了十分坎坷的發展道路。秦王朝雖然是因法家理論而興盛的,但它統一六國後卻下了一道嚴厲的“焚書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並上演了“焚書坑儒”的醜劇。漢興,黄老之學一度勃起。但至西漢中期,武帝聽從董仲舒的意見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諸子百家之學從此成為異端。即使到魏晉時期,玄學曾一度為士人所喜愛,但官方提倡的依舊是經學和儒學。其後兩千年間,歷經了衆多王朝的興替,經學、儒學一直是欽定的“官學”内容,儒家學説也由子學上升到經學的尊位。尤其是宋明理學興起至清的近千年間,歷代王朝更以經學為正道,以之作為科舉取士的依據,而以諸子學為異端,這是子學最受排斥的時期。
儒家也是先秦諸子中的一家,它對於中華文化傳承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孔孟學説中有許多民主性的精華,對於今天的中華文化重構仍有其重要價值。但因其以官學的正統自居,故自孟、荀始,儒家學者便將其餘諸子各家斥為異端邪説。《孟子·滕文公下》大罵楊、墨學派“無父無君”,《荀子·非十二子》則罵遍先秦諸子各學派,連儒學中的子思、孟軻、子張、子夏、子遊也難以倖免。在文化專制的壓力下,諸子之學由是式微,如最早的三家顯學之一的墨學,漢以後就逐漸湮滅無聞。道家一則因道教興起,將老莊作為其經典而得以保存;二則因歷代文人大多出仕為儒,歸隱則道,因此相對而言,無論在宗教還是社會生活裏,道家還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只是人們所關注的已經不是老子思想中最為重要的有關社會治理方面的内容。法家則因歷代統治者實行陽儒陰法的統治術,其香火倒也不曾中斷過。
當然,專制思想的壓制是不可能持久的。明代中後期,隨着社會經濟的空前發展,市民階層逐漸興起,社會思潮開始發生變化,“思想解放”之風漸漸萌發,那時的士人已經敢於議論朝政,表達不同意見,在學術領域中標新立異者也大有人在。李卓吾遺世獨立,以異端自居,公開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他所撰《焚書》《續焚書》,直斥封建禮教,倡導個性解放與思想自由。他的許多觀點來自對子學的傳承,如謂“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是“致一之理”(《李氏叢書·老子解下篇》)。這種倡導人類平等的思想,是對封建等級制的批判,而他的“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的説法,顯然也是源於道家學説。汪本鈳在《續藏書》序中謂:“先生一生無書不讀。”李贄著作中有《老子解》一卷、《莊子解》三卷、《墨子批選》二卷,皆為儒學之外的子書。李贄有衆多弟子,他在南京時,南都士人“靡然向之。登壇説法,傾動大江南北”;至北通州,“燕冀人士望風禮拜尤甚”(沈鐵《李卓吾傳》)。姚瓚在《近事叢殘》中也説,李贄學説深受時人擁戴,“儒釋從之者幾千萬人。其學以解脱直截為宗,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後學如狂,不但儒教潰防,即釋宗繩檢,亦多所清棄”。筆者所讀明人筆記小説,其中即多有追求個性解放,遺世獨立者在。
至晚明,士人批評時政,集會結社,東林、復社、幾社,皆為文士集會之處。他們相互間既切磋學問,又評議朝政,且與在朝的官員及市井民衆相互關聯,形成朝野互動的格局。上述種種,均顯示出社會政治局面的新變。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士人的思想觀點開始發生變化,他們對經學、理學産生懷疑,而對諸子之學發生很大興趣。尤其是在經歷了明清鼎革、國破家亡的慘劇之後,痛定思痛,得以存留下來的一批學者對傳統的學術進行反思和批判,黄宗羲作《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學術史著作,並注重研究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嚴厲批判封建時代的君權思想,成為我國最早的啓蒙思想家。顧炎武倡導經世致用,批判宋明理學和陸王心學的空疏學風,開創有清一代朴學的根基。王夫之在《周易外傳》等著作中,批判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作有《老子衍》《莊子通》《莊子解》等子學著作。他博覽群書,以為經子平等,倡導革新。而傅山則力倡諸子之學,開清代諸子學研究之先河。到清中期,學人繼清初學者之緒,樸學大興,學人以子證經,在一定程度上衝破清王朝以子學為異端的枷鎖。
晚清至民國時期,隨着西學東漸,經學難以與西方思潮相對接,於是有識之士想到了子學的傳統,開始探索以子學應對西學之路,從而有了晚清諸子學的復興。其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反孔思潮的傳播,舊有的“以經學為中心”的學術體系土崩瓦解,子學順勢而起,成為士人研究的熱點和傳播創新思想的理論依據。嚴復、胡適、章太炎等,均致力於倡導子學的復興,胡適在《中國哲學史》中就認為:“非儒學派的恢復是絶對需要的,因為在這些學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91年版。章太炎從清末始便大力倡導復興諸子學,他著有多部研究諸子的著作,並到處宣傳、演講。嚴復特别關注《老》《莊》學説,並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來比較老莊學説中所追求的自由。章太炎尤其關注荀子、老子、莊子之學,尊子而貶孔,並大倡國學,著有《國學概論》《國故論衡》等。他所著《老子評語》中,便聯繫西方的進化論,認為老莊學説與西方的達爾文、孟德斯鳩、斯賓塞相通。他認為,老子無為論具有民主的内涵,而莊子内篇的思想則包含有現代自由主義的“聽民自由”的觀念。這是章氏以西方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作的現代闡析。
由於傳統的經學獨尊觀念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强烈衝擊,幾近破滅,由此迎來了民國時期子學的復興。有人將這一時期也稱為“新子學”復興的時期,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自20世紀初起,子學已經堂而皇之地成為學者們熱心研究的對象。民國時期,經子地位平等,不分軒輊地均在學者們的關注研究之列,並由此取得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可參閲張涅《略述民國時期的新子學研究》、陳志平《諸子學的現代轉型——民國諸子學的啓示》,《新子學論集》,學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7~692、693~714頁。。民國時期的子學研究熱潮,是我國學術界對諸子學現代轉型所作的初步嘗試。
歷觀我國長達數千年的文化史,學界一致認同,先秦的子學時代和20世紀的民國時期是中華文化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時代。相對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是形成文化繁榮的客觀條件。歷史已經證明,在經學獨尊,子學遭受排擠,甚至被視為異端的時代,社會思想文化便陷於僵化乃至倒退;而在社會環境相對寬鬆,子學思潮較為活躍的時期(如春秋戰國、西漢前期、魏晉時期),文化創造力便得到弘揚與發展。即使在一些文化學術領域,情況也是如此。中唐時期,韓愈和柳宗元發起“古文運動”,雖其鋒芒指向形式主義的駢文和佛道思想的盛行,以恢復儒學道統為己任,但他們也都得益於吸取諸子學説的精華和異彩紛呈的表達手法。韓派學者就認為聖人的《六經》以及諸子百家之文,皆為“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李翱《答朱載言書》)。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提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時,列舉了伊、周、孔、孟,同時也列舉了楊、墨、老、莊等不同流派的諸子學人。至於柳宗元,其“議論證古今,出入經史百家”(韓愈《柳子厚墓誌銘》)。當然,由文體革新所引發的“古文運動”,其後也形成那一時代的一種社會思潮。
我們今日倡導“新子學”,正是從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進行思考和選擇的。毫無疑義,優秀的文化傳統應當由一代代人認真加以繼承,這也是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經常提到的“接着講”。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經談到,當今確有許多人是真心關注中華文化的命運的,提出了重構中華文化的種種思路,是一種新時期的文化自覺。但正確的道路選擇是第一位的。如有的學者提出要恢復經學和儒學,作為中華文化的核心,以為這才是弘揚傳統文化,然而歷史教訓已經表明,此路不通。把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路讓今人接着走,這種做法只能讓多數人遠離傳統文化。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子學”提出之後的兩年多來,我們的國家、社會對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已經和幾年前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作為國家層面,大力推動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與傳承。雖然在十七届六中全會的決議中已經明確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形成決議,但當時的整個社會狀況令人深感憂慮,大家更多關心的是會不會再出現意料不到的問題,對於決議能否得到實行,社會能否健康發展深感憂心。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多時間,我國的社會生活便發生了令人矚目的明顯變化: 反腐的深入開展,各種改革方案的强力推出和實施,都令人深感欣慰。也許再過幾十年,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才會更加深刻地理解十八大以來所發生和正在進行的這一場變革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和歷史作用。也只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具備了可能性。
二是目前中國確實處於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打開网絡、博客、微信,不同學派、各種思想都在激烈地交鋒,甚至一些偶發的事件也會在這些媒體上引發陣陣漣漪。這是社會的進步,因為各種聲音的發出,評判事件的是非善惡,執政當局也正可藉此瞭解民意、民情,從而為科學決策提供參考。然而我們是否可因此説,真正的百家争鳴局面已經形成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上述種種不過是潛在於民間的一些議論表達方式,類似於古代民衆聚集於“鄉校”以議國政一樣(《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它和真正的戰國時代的處士横議、百家争鳴相去甚遠。
我很贊同大家對於戰國時代出現“百家争鳴”局面所作的分析,所謂子學應當具有“鮮明的思想性,獨立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批評與争鳴以及具有深度的創造性”*張永祥《反者道之動》,《“新子學”論集》,第82頁。。大家總是説“五四”時期是繼戰國時代之後的又一次“百家争鳴”,其特點也同樣在於此。當時的各種不同學派代表人物,也是希望能够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之後,為國家“再造文明”出謀劃策。
當代中國經過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正以嶄新的面貌屹立於世界之林。然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做得好不好,直接影響到國家形象與軟實力的提升。因此,如何進一步繁榮哲學社會科學,充分調動從事文化思想領域各方面人士的積極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二、 子學復興在提升我國軟實力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强,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問題成了大家議論的焦點。
何謂國家軟實力,簡單地説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實力及其影響力。數千年來古代中國有着很强的軟實力,對内具有强烈的民族認同,它以共同的中華文化為基礎,有完整的制度文化、教育體制;對外則具有很强的影響力和輻射力,東方文化圈的形成便是以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的輻射而形成的。
然而近代以來,隨着“天朝”的衰落,西方崛起,其在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形成的制度、理念、價值觀,成為各國争相效仿的對象,而反觀我國,舊有的觀念被衝垮,新的理念未形成,經濟上又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狀況,自然形不成文化的軟實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衝破了一系列束縛社會經濟發展的條條框框,以驚人的速度崛起,這才逐漸引發世界的關注。然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文化建設方面並没有很好地跟進,出現了信仰危機、人心涣散、道德淪喪、腐敗盛行等不良的品行與惡行。它表明社會文明的控制力出現了問題,如果不重視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所取得的經濟成果也難以保持,社會也將再度遭遇困境與危機。
為什麽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在現代經濟騰飛之時,卻出現了文明的危機?這是值得世人共同關注的問題。有鑒於此,筆者這些年來一直呼吁要儘快重構中華文化,以避免出現更嚴重的危機局面。拿什麽來重構?最關鍵的要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做起,因為它是中華民族之根、之魂。過去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一次次的過激行動,已經使中華文化這棵參天大樹傷筋動骨,因此我們必須從頭做起,鞏固其根基,繁榮其枝幹,由此才能開出絢爛之花。
“新子學”構想,適時提供了重構中華文化的新思路。重構中華文化,也就是把中華文化在歷史長河中所積澱的優秀傳統加以弘揚。這其中需要鑒别和整理,何為優秀文化,何為糟粕?要經過認真梳理,將中華文化中的精華融入當代社會。
人們常驚訝於古代先賢的博大精深,他們能用最簡短、最凝煉的語言,將深刻的道理明白揭示於人。《老子》一書,不過五千言,然而書中所闡述的深刻哲理,影響了人類二千多年的文明史,對於中華民族的深層次的人格構建,更是難以用幾句話來完全概括。柳宗元《送薛存義序》,聊聊二百餘字,把官民關係講得一清二楚,可成為所有當權者的必讀教材。他指出官吏是“民之役”,即民衆的僕役,而不可以“役民”,即奴役民衆。他抨擊當時的官吏們“受其值,怠其事,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的腐敗之風。然而,現實中,“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他站在民衆的立場上指斥貪官庸吏,文章的深刻程度抵得上厚厚的一本《行政學》。而且他把“勢”這一概念提出來,指出問題的根源是“勢不同也”,即當權者掌握生殺大權而民衆居於下位,没有罷黜官員的權力,由是而引發人們的深刻思考。柳宗元所處的時代固然無法解決這個難題,而當代社會是否能建立起有效的監督與約束機制,讓權力真正被關進籠子裏呢?這至今依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一宗宗觸目驚心的貪腐大案,説明這個制度還很不健全。當然現在的反腐,是執政者的重頭戲,深得人心,但我更期待的是能否儘快地建立起讓官員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機制。一位老學者曾直言導致國民黨最終潰敗的原因,主要是官場腐敗,而現在的問題更麻煩,上行下效的腐敗之風已經漫延全社會,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如何改變全社會的腐敗之風。
我們的國家怎麽了?一面是高速增長的經濟實力,一面又是層出不窮的亂象叢生。直觀我們的教育、法律環境、制度建設、管理能力、國民心態、國民形象等,這些軟實力範疇的文化力、對外影響力、對外形象,是否與文明大國的形象相匹配?中華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以及來自文化傳統持久的一種對國民的影響力是否强大?都是我們亟待探討和解決的課題。
作為從事學術理論工作多年的老者,我的最大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國學術出現蓬勃發展的嶄新局面。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中,曾這樣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中國學術史又何嘗不是如此。從先秦時代的經子之學到漢代儒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如果没有這一代一代的學術傳承與發展創新,中華學術傳統早就不復存在了。
然而,今日之所以出現中國人的信仰危機,出現文化軟實力方面的底氣不足,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將所謂信仰神化為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文革中的“三忠於”、“四無限”是其頂點。文革結束之後,當領袖走下神壇,人們發現,信仰已經消亡。二是將信仰等同於政治信念,當一種政治理念在現實中遭遇挫折,人們便以為再無可以信仰的東西,於是信仰危機隨之産生,不知所從。社會産生無序現象,人們的行為失去約束的依據,道德底線似乎也不復存在。當今社會的種種弊端,莫不與此相關。
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不僅僅因為實力强大,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持久的文化延續,有民族文化的共同認同,也即價值觀的存在,這應當是民族信仰的最深層的内容。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本民族世代傳承的價值觀,這應當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現,例如古代的“忠、孝、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這些雖被認為是儒家所提倡的理念,然而儒家學説也是承繼着古代王道之學,長期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即使它曾經被封建統治者作了有利於其統治的解釋,但其中也有大量是涉及民衆間的人際關係的内容。過去將其完全與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聯繫在一起加以批判,其實是過激的行為,因為它集中代表的是人之所以為人需要遵守的道德準則。我們可以批評封建統治者的言行不一,可以批評封建統治者對相關内容的曲解,但不應認為這些就是封建道德,因為其中就藴含着深刻的内涵,如“恥,乃人禽之别也”。儒家的一些道德觀,至今仍在海外華人中被奉為信條。道家和墨家的理論體系中,也都有大量的人文精神、道德及倫理的闡述。中華傳統文化的許多思想理念,過去一個時期在研究中總會被貼上階級的標籤,而只要貼上“封建地主階級”的標籤,便自然對其進行嚴厲批判,於是乎作為古代思想智慧的結晶也一併被抛棄,這才是造成今日信仰空白、道德淪喪的根源。2012年十八大報告中,首次以十二個詞二十四個字來概括今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就吸取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當今世界公認的現代文明的因素,因而更能為民衆所接受。
“新子學”之所以自提倡之日起馬上受到學術界的好評與關注,正是因其根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而又坦然面向當今世界,與西方的學術思想交流與對話,這種不固守一隅的開放精神正適應了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因而可以成為今日學術界理論研究的一面旗幟,也是學術理論創新的一個典範。而在我們的學術理論報刊上,能有多少這樣有分量的文章呢?報刊不能説少,改革開放以來,期刊由文革中的20份發展到目前的上萬份了,其中社會科學類期刊以一半計算,應也有五千種,數量不可謂少,然而千刊一面的現象,讓人不能不深感遺憾。坦率地講,許多發表的文章不過是文化垃圾。為什麽會形成這種狀況,確實應當思考。難道中國人缺乏智慧了嗎?思想解放的口號喊了三十年,但在思想意識形態的研究中卻有着許多不可逾越的禁區,限制着作者和編者的創造性,形成了被稱為犬儒主義的學術風氣,寧左勿右、闡釋學依然是今日的顯學,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改變,所謂創造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話。只有當這些雜誌和報紙都成為學術理論創新管道的時候,我們才能説出現了真正的百家争鳴的局面。只有管道暢通,人人暢所欲言,民族精神、民族創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發揚。當然,這裏還有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即如何調整相關政策,使大家敢於創新,敢於發表真實的意見。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文風的問題,早在唐代,韓愈就主張文章寫作“唯陳言之務去”(《與李翊書》),我黨在延安整風時期也曾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党八股的文風,然而這些年來此風大長,甚至動輒以勢壓人,這實在是惡劣風氣。為什麽一些主管道的重要理論報刊的文章,不見學理,只有説教,越來越被人詬病。馬克思主義原是一種科學的理論,然而為什麽在一些人口中就成為教條,成為打擊别的不同見解的棍子?中央一直要求主流媒體應當貼近民生,反映民衆的心聲和訴求,唯其如此,政通人和,生動活潑的局面才會真正形成。
三、 以“新子學”推動和促進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子學時代所産生的各種學説,是我們祖先精神智慧的結晶,也是世界文化軸心時代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所作的傑出貢獻。以子學時代為起點,吸收二千多年中華文化傳統的精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構建“新子學”的學術理論體系,是一項宏偉的系統工程,如同許杭生先生所説的,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
我十分欽佩方勇先生和他的團隊所具有的勇氣和擔當。雖然在項目啓動時,我曾經有着不少顧慮和擔心。但是,經過他們幾年來的努力,我看到基礎工程的建設已經扎實地在推進,以先秦諸子為主的古代典籍整理和成果已一批批地完成並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而相關義理的闡釋也在同步地進行中。有這樣好的内外條件和基礎,加上海内外衆多學者的共同關注,我相信這項宏偉的工程將能順利完成,並為中華文化的復興提供有益的理論創新成果。
當然,如何科學、準確地對歷代的傳世作品做出評價和新的闡釋,是一項十分重要但又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例如對法家的評價問題,毫無疑義,作為先秦諸子中的一家,法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作出過重大貢獻,並産生了一批傑出的人物,但對其集大成者韓非子如何評價,我覺得要反思。我很贊同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所説,韓非是一位“極權主義者”(《韓非子的批判》),“完全是一種法西斯式的理論”(《後記》),而二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在《史記》中也用“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加以評論。我以為從對待民衆的角度而言,韓非的理論根本不把人當人,只是當成“可使由之”、與牲畜毫無二致、供任意驅使的農奴而已,一切權力都要高度集中於帝王一人身上。而對文化方面,他更是走極端,還是秦始皇文化專制政策理論的製定者。韓非的理論雖為秦國的統一立下大功,卻在兩千多年中國封建集權社會中起到十分惡劣的作用和影響。然而我所見到的國内評論者,多對其所謂歷史進步意義大談特談,而對封建集權理論和文化專制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的危害或鮮有提及,或輕描淡寫。郭沫若對韓非、秦始皇的批判,對儒家的讚揚,其後果是被“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一句詩給徹底否定。郭氏尤其在此後的批林批孔中被整得惶惶不可終日。今日的評論者至今依然沿襲過去的觀點是不應該的,我們應當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封建獨裁者的一邊。建國初,我們的文學史中對歷代文學作品的評論以“人民性”作為褒貶的標準,然而後來“人民性”、“人道主義”受到批判,而代之以階級性為標準,於是動輒對古代作家劃階級成分,亂貼標籤。直到新時期以來才重新用“人民性”作為對古代文學的評價標準。在哲學界,對傳統思想的階級屬性、歷代思想家的階級劃分也莫不如此。因此,今天我們特别要防止對所評論的人物及其作品褒貶任聲、抑揚過實的情況。這些問題我想也許是多餘的話,大家都應該是注意得到的。
三百多年前,參加抗清鬥争失敗的王夫之擔心中華傳統文脈中斷,在深山中整理古代文化經典,寫下“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對聯,表達他對這一信念的堅守不移。我們這一代學人,一定能够不負時代的厚望,在弘揚傳統文化中不斷創新,開拓出中華學術的新生面。
[作者簡介]湯漳平(1946— ),男,福建雲霄人。曾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州學刊》副主編、社長,現為閩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鄭州大學兼職教授。著作有《楚辭論析》(合著)《屈原傳》《出土文獻與〈楚辭·九歌〉》《楚辭》(译注本)等10餘部,曾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産》《中州學刊》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