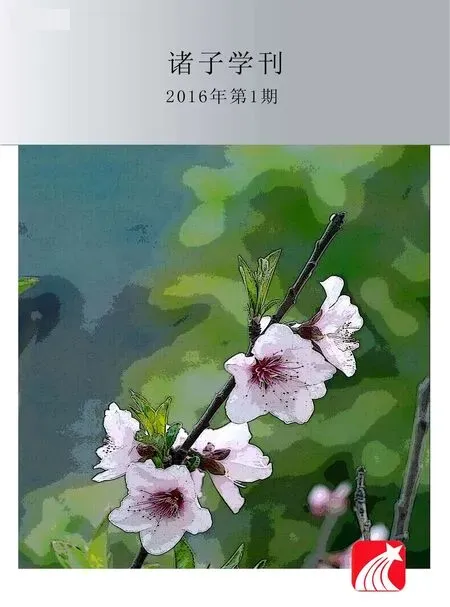諸子學的揚棄與開新
徐儒宗
諸子學的揚棄與開新
徐儒宗
本文首先對經學與子學的關係加以梳理,使之各處於適當的位置;其次主張還諸子以原貌,通過對其原典的研究,辨别其精華與糟粕而加以揚棄;然後將所得的精華進行融會貫通的綜合提升,建立起一整套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思想體系以指導實踐。這樣才能開創諸子學研究的新局面。
關鍵詞 諸子學 經學 揚棄 開新
中圖分類號 B2
一、 經學與子學的關係
以弘揚國學為宗旨而提出的“新子學”構想,自然引發了關於“國學”所包涵的範圍以及“經學”與“子學”的關係等問題的争議。對此,較為流行的傳統説法一般主張以經學為主導復興國學,但對國學應包涵的範圍則有多種不同的説法。有學者將國學等同於經學,這固然是囿於一種偏見,把國學的範圍定得過於狹窄了,因為國學除了經學之外,自然還應包括諸子百家、傳統史學和詩文等在内。
然而,目前又有一種新的説法,認為“先有儒學,後有經學,經學是儒學的核心,儒學比經學的範疇要大;儒學原在‘子學’之内,常被排在前列;‘新子學’較之傳統子學内容包孕更廣,儒學也自然屬於‘新子學’之範疇,經學也相應地位於‘新子學’之列”*見《光明日報》2013年5月13日《“新子學”大觀——上海“‘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這種觀點的論證邏輯是: 因為儒學的範疇大於經學,而子學的範疇大於儒學,“新子學”的範疇又大於傳統子學,所以,“新子學”的範疇必然更大於經學,從而得出結論:“‘經學’也相應地位於‘新子學’之列。”對於這種觀點,鄙意竊謂,除了“儒學原在‘子學’之内,常被排在前列”和“儒學也自然屬於‘新子學’之範疇”等觀點基本上可以認同而外,其餘論證實不敢苟同。
第一,究竟是否“先有儒學,後有經學”?若從“經學”之名而言,確實是後於儒學才出現,但“經學”之名後於儒學出現不等於“經”之内容後於儒學。論其先後,當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今從六經的内容看,無不在孔子創建儒學之前就已存在。以《易》而言,八卦、六十四卦及其卦辭和爻辭究竟是否分别為伏羲、文王、周公所作姑置勿論,但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則毋庸置疑;以《詩》《書》而言,是否經孔子所删姑置勿論,但都是孔子以前的作品也是古今學者之共識(古文《尚書》中有争議者除外);以《禮》《樂》而言,雖係孔門後學甚或漢儒所記,其中難免雜有後儒的思想,但基本上是記録由周公所制、由孔子所傳的内容則是可信的;以《春秋》而言,其内容是孔子所記的春秋時代之史,其觀點當然可以作為純粹的儒家思想,但至遲也是與儒學同時産生,怎麽會在儒學之後?
第二,“‘經學’也相應地位於‘新子學’之列”的觀點不能成立。因為“六經”的内容早在春秋以前就已存在,而諸子之學是在春秋戰國之交才出現的。所以,只能説子學是六經的繼承或發展,而不能説經學包括在子學之内。如果説,主張傳統經學中的《論語》《孟子》“離經還子”尚有一定道理的話,那麽主張把《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統統“離經還子”就毫無道理了。
所以,關於經與子的先後關係問題,我基本上同意方勇教授的觀點。方教授説:“商周以來的傳統知識系統,實可分為兩大部分: 一為王官之學,它是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識系統並加以創造發明的禮樂祭祀文化,經後人加工整理所形成的譜系較為完備的‘六經’系統;一為諸子之學,它是以老子、孔子等為代表的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學的思想精華,並結合新的時代因素獨立創造出來的子學系統。”*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由此可見,方教授雖然極力倡導“新子學”,但並未把經學納入子學乃至“新子學”之内。這是較為客觀的概括。
關於對經學與子學的評價,有學者認為,經學的特點是封閉、僵化、停滯而具有保守性,而子學的特點則是開放、活躍、發展而富有創造力。對於這種觀點,鄙人未敢苟同。誠然,如果以只知株守六經教條而不知變通者與諸子的開創者兩相比較,則這種評價似乎是對的;但所謂“不齊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所得結論未免有失公允。因為現在研究經學,也有“新”的趨勢,早已不是重述漢學抑或宋學的時代(當然漢學和宋學中的有益成果仍應吸取),而是把六經放到它所産生的時代背景中去研究其内容本身之價值,從中吸取精華以為今用。因此,若必欲將經學與子學進行比較,就應從六經和諸子的内容本身進行評價;判斷其創造力之大小,也應就六經與諸子的創作者進行比較,而不是以六經教條之株守者與諸子之開創者進行比較。如果將六經與諸子的内容本身之間以及兩者的創作者之間進行評價,必將得出兩者都具有巨大創造力的結論,甚至可以説,六經的創造力更為偉大。以《易》而言,伏羲始畫八卦,開創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其創造力是無與倫比的;文王、周公發展為六十四卦並作卦、爻辭以賦予各卦具體含義,孔子又把零散的卦爻義融會貫通而發展為體系嚴密的易理,無不體現其巨大的創造力;更何況,《易》之本身即以“變易”為義,而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訓,因而《易》之為“經”,不愧為最具創造力之書。以《書》而言,如果把《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分别看作記述虞、夏、商、周的治國資料,則每篇都有其創造性。《詩》為歷代詩歌詞曲之源,《樂》為藝術之源,《春秋》為史學之源,其創造性皆不言而喻。而《禮記·禮器》則有“禮,時為大”之訓,因而商代不能全盤套用夏禮,周代不能完全搬用商禮,其間的“損益”,即包含了既有繼承又有創新之意,故孔子的一句“吾從周”,即説明了所謂“守禮”,並非要求株守古代之禮,而是要求遵守當代之禮。由是觀之,在全部國學之中,六經是最具開創性的,因而也最具有開放、包容、變通、發展等特點而富有創造的活力。
因此鄙意竊謂,六經記述了遠古至三代的文化精華,為中華文化之源,因而最具開創性;諸子則自春秋末期開始,“是個體智慧創造性地吸收六經的思想精華後,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諸多領域多維度、多層次的深入展開”*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國學版。。其中孔子雖自稱“述而不作”而没有標新立異,惟將遠古至三代的大量文化資料進行整理並加以融會貫通,從而創建了體系完整的儒家學説,然而若非具有非凡的創造力,安能擔此重任?故其成就與影響較之其他另闢蹊徑的諸子更為巨大。而從事於標新立異、在六經以外另闢蹊徑,“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説以廣播於天下”的其他諸子,自然就成為六經的羽翼了。
其實,六經和諸子都是中華傳統文化取之不盡的寶庫,其間並非對立的關係,而是相濟相成的互補關係,大可不必揚此而抑彼。所以,我主張六經和諸子之間乃至子與子之間,都應將其置於平等的地位進行研究,就像人格平等那樣。然而人格平等並不等於人與人之間毫無賢愚的差距和能力、貢獻大小之差别。因為諸子之間的價值高下之差别也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學者固然可以從不同角度甚至全方位進行評價,但也難免雜有某種個人偏見。所以現在學者的當務之急,主要還應致力於從諸子這座寶庫中挖掘精華,以供現實之用。至於價值如何,有待未來實踐中去檢驗吧。
二、 諸子學的揚棄
在諸子中挹取精華,就涉及如何揚棄和取舍的問題。對此,有兩步工作是必須做的: 其一是還諸子以原貌;其二是在諸子的原典中辨别其精華與糟粕而加以揚棄。兹就二者簡述如下。
(一) 還諸子以原貌
在“還諸子以原貌”這項工作中,儒家的情況是最為複雜的,其次則是道家。以儒家而言,因為漢代以後,儒術在名義上雖受到“獨尊”,但已不是先秦時代的原儒,而是包羅了其他各家思想的大雜燴。若要從中挹取精華,首先必須把這些混入儒學中的各家思想加以辨别並遣歸其本家,把儒學還原為先秦之原儒,然後在其本身中辨清其精華和糟粕而加以揚棄,這就是當前研究儒學的學者義不容辭的任務。
今考漢代“獨尊”以後之儒學,其中混入最多者大概要數法家思想了。舉例而言,人們往往把“五倫”與“三綱”相提並論,都當作儒家思想加以論述,這實在是一種誤解。其實,五倫才是正宗的儒家思想,而三綱則源自法家思想,由漢儒吸收到儒學之内,才冒充了儒家思想。兩者思想體系不同,涇渭分明,毫無共同之處,兹試作辨析。
孔子以“仁”為宗旨考察社會倫理,區分了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類具有典型性的人際關係,謂之“五倫”。對於“夫婦”關係,孔子主張“夫婦和”(《禮記·禮運》),還提出“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易傳·序卦》),並進而提出丈夫應該尊敬妻子:“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禮記·哀公問》)孔子這種以相愛和相敬並應保持長久穩定作為夫妻關係的理論,為後世進步的婚姻觀奠定了基礎。
關於“父子”關係,具體而言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孔子把“父子”雙方相互的義務規定為“父慈而子孝”。但他又看到,在現實社會中,父母對子女一般都能盡到“慈”的責任,而子女對父母則比較難於盡到“孝”的義務。針對這種偏向,所以他平時談“孝”的言論就比較多。再則,孔子對年輕的學生設教,自然應多談孝道。
關於“兄弟”關係,乃稟同氣而生,應以互相團結友愛為原則,即所謂“兄愛,弟敬”(《左傳》隱公三年)。弟恭敬兄的道德,孔子稱之為“悌”。“孝”和“悌”都是通向“仁”的起點,所以説“孝悌為仁之本”。
關於“君臣”關係,孔子提倡“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後來孟子則强調“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並認為貴戚之卿應該“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異姓之卿則應該“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荀子亦言為臣應該“從道不從君”(《荀子·大略》)。而且,孟、荀都極力讚頌湯、武“弔民伐罪”以推翻桀、紂為正義之舉。據此,孔、孟、荀所提倡的君臣關係,乃是互相尊重的關係,也是頗含民主成分的較為開明的上下級關係,絶無後世之所謂“君令臣死,不得不死”,“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那種絶對服從的愚忠思想。而關於君民關係,孔子説:“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禮記·緇衣》)。孟子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荀子説:“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儒家進步的君民觀。
“朋友”是一種既突破了血緣關係,又不受政治所限制,而又有别於“衆人”的完全建立在道義基礎之上的人際關係,所以其間的關係是互相信任,互相學習和規勸。
由此可見,孔子給這五類典型的社會關係所規定的不同的權利和義務,都是根據其不同性質而有所區别,並從人之本性出發而深合人之正常心理的。
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為了迎合當時君主集權的專制統治日益發展,制定了一整套極端專制主義的法家統治學説。他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統統看成是互相利用的利害關係。
在君臣關係上,韓子主張“尊主卑臣”,集一切權力在君主一人之手以實現其專制統治,用權勢法術手段以馭臣。他認為君臣關係完全是“官爵”與“死力”的買賣關係。其《難一》篇云:“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禄以與臣市。”他還把人的利欲看成動物的本能。正如其《内儲説上》所謂君視臣“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這是何等露骨的獸欲論!在《主道》篇提出了“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的極端獨裁的權謀統治。這顯然是後世“天王聖明,臣罪當誅”説法之所自出。
在家庭關係中,韓子徹底否定儒家所提倡的夫婦互相敬愛和父慈子孝等道德,而看成是純粹的利害關係。其《備内》篇云:“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六反》篇云:“父母之於子也,産男則相賀,産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袵,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在韓子看來,即使是丈夫與妻妾、父母與子女之間,都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的關係。
基於以上的看法,韓子在人倫方面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這完全是從專制主義立場出發,否定儒家關於夫婦、父子、君臣等雙方之間基本對等的關係,而從理論上斷定了君、父、夫對於臣、子、妻的絶對統治權利,顯然是漢儒“三綱”説之所自出。
漢繼秦制,大儒董仲舒為了適應漢代大一統專制統治的需要而提出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口號,但是他對先秦儒學卻作了重大的改造。他吸取先秦百家中凡屬有利於專制統治的觀點使之融合於儒學之中,而對先秦儒學中原本具有的民主精神則加以淡化。在人倫方面,他直接繼承法家韓非之説而提出了“三綱”的概念。到班固《白虎通義·三綱六紀》又提出了“三綱”的具體内容:“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這就正式建立了“三綱”説。同書《五行》又説:“臣順君,子順父,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這顯然是直接從韓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脱胎而來。所以在“三綱”中,片面强調下對上的義務,上對下具有絶對權威,而無所謂責任。這樣,漢儒對原始儒家的“五倫”從理論上進行了重大的改造,把本來具有合理性的内容改造成為服務於專制統治的工具。
若將“五倫”與“三綱”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明顯區别。先秦儒家的“五倫”,是建立在仁學的人性論基礎之上的,因而每“倫”的雙方基本上是互相對應的對等關係。其中夫婦關係是互相“愛與敬”,或“夫婦有義”;父子關係是“父慈子孝”或“父子有親”;兄弟關係是“兄愛弟敬”或“兄友弟恭”;君臣關係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朋友關係為“朋友有信”。從中可以看出: 無論哪一倫,雙方都有應盡的義務,從而也相應地保證了對方所應得的權利;而且,雙方都有獨立的人格,互相尊重,毫無一方對於另一方的絶對服從之意,基本上都是合乎中道和“忠恕”之旨的對等關係,在人格上基本上是平等的。然而漢儒吸取韓非之説所提出的“三綱”,是以法家的絶對專制統治思想作為理論指導的,因而每“綱”的雙方變成為上下從屬、下對上無條件服從的關係;其中君、父、夫對於臣、子、妻完全是違背中道的極端專制主義的絶對統治關係。
而且,先秦儒家的“五倫”説,還鼓勵為子要做“争子”,為臣要做“争臣”。孔子主張“事父母幾諫”;孟子則提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甚至還可以興“弔民伐罪”之師將其推翻;荀子亦言為臣應該“從道不從君”。其中所藴含的民主精神是很明顯的。然而在“三綱”説的影響之下,就開始竭力提倡那種片面要求臣、子、妻的所謂“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愚忠、愚孝、愚節思想,誤導了整個專制時代,流毒非常深遠。由此可見,“五倫”與“三綱”有其本質的區别。
“三綱”之説,可謂是法家思想混入儒學之中影響最大的内容,故詳為辨析,以見一斑。其餘内容尚多,未暇一一論述。故學術界素有把漢代以來的儒學視為“外儒内法”之學,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漢代以後的儒學中,除了法家思想而外,還雜有其他各家的思想,諸如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陰陽家的五德終始、天人感應之説等等,不一而足。因限於篇幅,姑從略。
道家的情況之所以複雜,主要在於兩點: 其一是戰國至漢初時期的黄老之學,吸收了道、法兩家之説加以合流;其二是漢末道教出現後,在道家的清虚無為、養生貴己的宗旨下,混入了長生不老、白日飛升之類神仙方術之説。對於前者,在於將其演變的脈絡加以梳理;對於後者,其中神仙方術之説已不屬學術思想的範圍,應將其從“子學”之中剔除出去,以保持道家的原貌。
(二) 研究諸子的原典而加以揚棄
在諸子的原典中,都是精華與糟粕並存的。若要進行辨别和揚棄,無疑是一項極其複雜而繁重的工作。兹試舉《墨子》為例略作説明。
墨子創建以“利他”為宗旨的墨家學説,其積極入世的態度與欲救民於水火的懷抱,較之儒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所主張的尚賢、兼愛、非攻、節用、節葬、非命等學説以及《墨經》中所包含的邏輯思想和科學知識等,確有許多值得吸取的精華,但也雜有很多有害的糟粕。鄙意竊謂,其中危害最大者莫過於《尚同》篇中的“尚同其上”的思想。《墨子·尚同中》云:
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説而不治哉!
墨子主張,在一鄉之内要先立一個絶對正確之鄉長,而使一鄉之民皆以鄉長之是非為是非;在一國之内要先立一個絶對正確之國君,而使一國之民皆以國君之是非為是非;在全天下則應先立一個絶對正確之天子,而使天下之民皆以天子之是非為是非。這樣,天下就會没有不同的意見,思想完全歸於統一,天下也就大治了!且不説這完全是一種脱離實際的過於天真的空想,即從其思維方法而言,就犯了根本性的大錯誤。儒家正因為認識到君或天子不可能都絶對正確,故而孔、孟、荀等大儒皆主張“從道不從君”的觀點;而在方法上,又能從“異”與“同”的兩端着眼,主張用和而不同的方法來實現天下大同。而墨子妄想用一人之思想來統一天下之思想,這樣求“同”的後果,其終必將違背墨學為民立言的初衷,反而變成專為專制獨裁統治服務的理論了。
又如墨子主張兼愛,不分人我、彼此,將普天下之人等量齊觀,主張用“以兼易别”來取消社會上存在的等級差别及各種客觀矛盾。其陳義雖高,然而罔顧人情之常,實際上是一種抹煞現實階級、等級差别的幻想,所以一落入實際人群社會,就遭遇窒礙而無法推行,以致不旋踵即告衰微。再據此而檢視現代的許多思想,其理念固然高超,口號也很響亮,可是都未能衡量人情事理,因此一旦勉强付諸實行,不但無法解決現有的難題,反而將大家導入另一種困境之中。這種貌似高尚實則脱離實際的理論,尤應加以辨别才能排除其消極因素。
以上僅略舉其例而已。在諸子這座寶庫中,雖有取之不盡的精華,但其糟粕亦復不少,必須細加辨别,才能剔除其糟粕而提取其中真正的精華。
三、 諸子學的開新
對諸子進行研究而提取其精華,固然是一項重大的工程,但未足以言開新。所謂開新,還必須把從各家學説中提取出來的大量精華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綜合,從而形成一個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思想體系,用以指導實踐,這才是為研究諸子學開創新局面。這固然有賴於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但畢竟還有待於能够擔此重任的偉大思想家的大手筆來最後完成。在古代思想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經做過這項工作,兹略作回顧,可以作為從事這項工作的參考。
最早從事這項工作的,當數春秋末期的偉大思想家孔子。孔子把遠古至夏商周三代保存下來的大量文化資料進行收集研究,廣泛吸收其中積極進步的思想因素,並加以融會貫通,從中提取以人為本的“仁”(仁者人也)作為宗旨,提取大中至正的“中庸”作為方法和準則,而把“大同”作為實行大道的最高目標,從而創建一整套自成體系的儒家學説。孔子所做的綜合工作,不僅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的一次,而且也是做得最為成功的一次。他不僅創建了影響最為巨大的儒家學説,而且還開創了百家争鳴的局面,推動了各家思想的蓬勃發展,從而形成了“諸子之學”這一富有創造力的文化系統。而在他所創建的儒學本身,由於他主張以人為本的“仁”作為宗旨,使得全部儒學都體現了濃厚的民本思想。其後繼者孟子和荀子先後提出了“民貴君輕”和“立君為民”等進步思想。這種頗含民主意義的民本思想雖不同於現代的民主思想,但兩者之間並非對立的,而是同一方向上的程度之差。所以在推進現代化民主政治的進程中,起有積極進步的作用。而在當時,也樂為廣大士民所接受,故在諸子中常被排在最前列,而對後世的影響也最為巨大。
經過戰國時代二百餘年的學術争鳴,已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思想資料。隨着列國的逐漸趨向統一,按理也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來把這些豐富的思想資料加以綜合提升,以使學術思想也能趨向統一。秦國的丞相吕不韋大概有志於此,然而他畢竟只是投機大商人出身而非思想家,所以他聚集各家學派的人作為“賓客”所共同著成的《吕氏春秋》只是一部“雜家”著作。因為其著書的方法不是對各家學説在更高水平上加以綜合,而是用一種拼湊式的方法加以羅列。其《用衆》篇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由於自己並無獨立的立場和見解,企圖只靠“兼容並包”地採集衆家之説,把各家的許多觀點羅列在一起,編制一套“粹白之裘”,於是乃成為典型的“雜家”。《漢志》云:“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所謂“無所歸心”,就是没有一個自己的中心思想。所以,《吕氏春秋》並算不上一次真正的綜合。
秦國獨尊法家,及併六國後,堅持“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的文化高壓政策,而將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語”皆燒之。於是,二百餘年以來的百家争鳴之局闇然而息,亦無人敢作學術總結之事,一直到漢代董仲舒才做了這項工作。
董仲舒為了適應漢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但是他的“獨尊儒術”與秦代的“獨尊法家”不同。秦代確實是堅持“獨尊法家”而徹底燒毁了“百家語”的,而董仲舒則是從“百家語”中挹取有利於專制統治所需要的内容納入儒家學説之内。他把這些内容在儒家的名義下加以融會貫通的綜合,創建了一整套有别於先秦原儒的所謂儒家思想體系。他的這番綜合工作,從政治上説基本上是成功的,因而它能支撐了二千年之久的專制主義統治;然而從學術上説則又不無可議之處,因為他的取舍標準,並非以學術上的標準吸取百家之精華,而是以當時的政治需要為標準,吸取百家之學中有利於專制統治的思想納入儒學之内,而把儒學中原有的諸如“民貴君輕”和“大同”思想之類進步思想相對地淡化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學術思想的正常發展。
漢唐時期,儒釋道三教並存,互相争論,互有黜陟,曾一度使統治者無所適從。及至宋代,三教漸有合流之勢,統治者也有此需要,故再次出現學術思想的綜合之局已屬勢所必然。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正是做了此項工作。兩派都以儒家為主體,適當吸收釋道兩教的營養而加以融會貫通的綜合,從而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從學術上説,兩派都做得較為深入而細緻,但也未免皆有其不足之處。其一,兩派仍然出於專制統治的需要,未能完全從學術出發,將諸子中的一些進步思想加以重視和發揮;其二,兩派在理論上都有重内輕外、重心性而輕事功的傾向,因而他們所建立的思想體系難免有失全面和合理。
清代初期,滿清統治者實行閉關自守政策,與國際失去文化交流的通道,致使原本領先於世界的中華文化從此陷於停滯和落後。鴉片戰争後,西方文化乘虚而入,乃成中西文化激烈衝突之局,至民國時期達到争鳴的高峰,並漸顯交相融合之勢。按理,將各種學術思想加以總結和綜合的時機業已漸趨成熟,但因建國以後一段時期的指導思想照搬了蘇俄模式,到“文革”達到頂峰。其間除了法家思想因出於政治需要曾一度受到不適當的宣傳之外,其餘各家思想乃至西方思想都在批判之列,以致學術研究長期處於萬馬齊喑之境。
改革開放重新迎來了百家争鳴的春天,學術上的交流討論蓬勃發展,對於諸子的研究成果也已大批湧現。因此,除了繼續研究挖掘之外,把已有的精華部分進行融會貫通的綜合工作,乃是開創“諸子學”研究的新局面的應有之義。
現在的綜合工作,當然不是運用《吕氏春秋》那樣拼湊的方式,也不應像董仲舒那樣完全受當時政治所左右,也不應像宋明理學那樣偏重道德心性而諱言事功;而應效法孔子總結遠古至三代文化那樣的成功經驗,並將視野放到更為高遠而開闊的境界,對宇宙、社會、人生乃至既往、現在、未來進行全方位的通盤觀照,然後加以融會貫通,從而創建一整套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思想體系,用以指導中華民族的正常發展。
鄙意竊謂,從“諸子學”的立場看,“六經之學”好比是先天賦予的元氣,“諸子之學”則是後天培養而成的元氣,兩者共同形成人的本身所具有的元氣;而外來的各種思想,則好像是人所需要補充的營養或治病的藥物,可以根據需要加以吸收消化,但決不可取本身的元氣而代之。所以,現在創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思想體系,還應克服現代的某種“獨尊”現象。
創建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思想體系,並非意味着開創諸子學研究的新局面的終結,而是作為中華民族學術思想發展進程中的一項階段性成就,在新的征途上,用以指導中華民族的實踐和學術思想的繼續發展。
[作者簡介]徐儒宗(1946— ),男,浙江浦江人。自幼從父攻讀經子詩文,現為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著有《中庸論》《人和論》《大學中庸全注全譯》《婺學通論》《江右王學通論》《吕祖謙傳》等,整理古籍多種,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