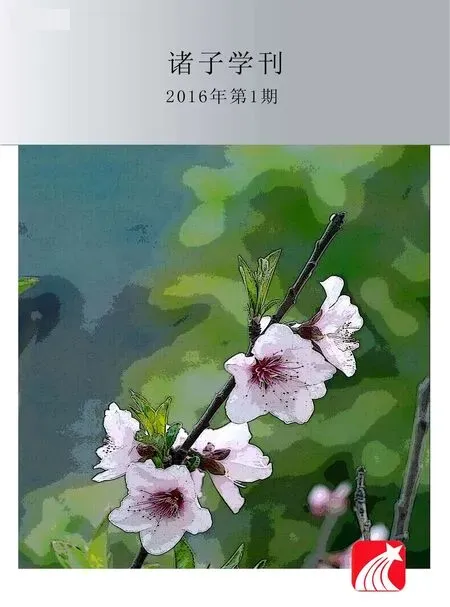對於當代“新子學”意義的思考
張 涅
對於當代“新子學”意義的思考
張 涅
“先秦子學”具有政治實踐性的品質,“子學研究”則是關於先秦諸子著作以及其社會政治思想的考釋和理論認識,兩者指向不同。所謂“新子學”,既指晚清以來對於社會政治的再思考和實踐,也包括該階段吸收了西方學術思想和方法的諸子學研究。當代“新子學”,着重指的是“新子學研究”,其賡續晚清民國時期的研究方向和範式方法,是現階段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設的必然要求。這樣的發展,自然應該重視其中的個體性、多元性、形而上性等問題。
關鍵詞 新子學 政治認識 個體意義 多元價值 形而上思維
中圖分類號 B2
近年來,在方勇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諸子研究中心的倡導下,“新子學”的研究為學界所矚目。這是賡續晚清民國子學思潮的自覺認識,是當代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設的必然要求,兼具學術和社會兩方面的意義。當然,因為問題的複雜性和深刻性,需要多方面、多層次的討論。筆者以為,認識先秦諸子思想産生和晚清民國時期子學復興的歷史原因,或有助於研究的深入,故而據此談一點思考。偏陋之處,敬請批評!
一、 “子學”源於東周時期士人的政治認識
關於“子學”有不同的界定,一般指春秋末至漢初期間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説,是士人在大一統體制建立之前對於社會政治的思考。後來有一些學人把漢以後“入道見志”(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的著作歸入“子學”,已遊離了早期“子學”政治實踐性的本旨。至於把歷代注疏批判諸子著作的成果也稱為“子學”,則是泛稱了,這個泛稱其實可用“子學研究”一詞來表達。“子學”和“子學研究”是兩個概念,“子學研究”着重於學術,而“子學”更多地具有社會實踐性的品質。所謂“新子學”,嚴格地説,是指在新的歷史階段對於社會政治的再思考和實踐。與此相應的“新子學研究”,即晚清民國以來的吸收了西方學術思想和範式方法後的諸子學研究。“子學”與“子學研究”的關係,一方面前者是核心,“子學研究”圍繞着“子學”展開;另一方面,後者也不斷地賦予前者以時代意義,使之呈現經典的價值。
這樣的認識顯然合乎歷史的客觀。今天我們細讀諸子著作,考證其生平事蹟,依然能認識到他們的社會政治實踐性的本旨,如司馬談所言:“此務為治者也。”(《論六家要指》)
例如孔子,現代學人大多强調其為思想家、教育家;或者從道德文化的層面予以評價,如牟宗三説:“孔子通體是一文化生命,滿腔是文化理想。”*牟宗三《歷史哲學》,學生書局2000年版,第89頁。但是究其一生追求,核心顯然在於政治事業。從《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可知,孔子年輕時就有明確的從政志向,中年後曾經施展了政治才能,有“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的自信。故而其弟子記道:“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論語·學而》)在當時社會,“禮”或被略棄,或流於虚文,因此孔子闡發“仁”的思想,從“禮”中凸顯出“内聖”意義。這種凸顯,在我們現在看來是思想特質所在,但在孔子本願中,主要還是為政治實踐作理論準備,提供思想基礎。一些學人認為,孔子周遊列國後專心做文獻整理的工作。從客觀的成就上講確是如此,其中當然有傳承文化的自覺意識,但是,這只是現實政治下的無奈之舉,並非意味着孔子放棄了政治活動的信念。《論語·憲問》記:“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左傳》哀公十四年也有相同的記載。當時孔子已經七十一歲了,聽到齊國的陳桓弑殺齊簡公這樣犯上作亂的事,自知不可能改變什麽,依然莊嚴上朝,請求魯哀公出兵討伐,此足以證明政治是孔子一生的信念。電影《孔子》讓銀幕上的孔子在返回魯國前説“不再過問政事”,顯然是編導的無知。
孔子志在政治,從他屢屢稱慕周公的語録中也可以清楚認識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荀子·儒效》),封土建國,制訂禮樂文化,完成宗法制度,提出“明德慎罰”與“刑兹無赦”(《尚書·唐誥》)相結合的政治思想,奠定了封建政治文化的基礎。這些繼往開來的政治成就顯然是孔子仰慕周公的原因,故而孔子説:“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歷代多認識到孔子和周公的這種本質聯繫,如《淮南子·要略》説:“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朱熹《四書集注·述而》注:“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漢唐時期“周孔”並稱,顯然也是把孔子作為政治思想家來認識。
再如《莊子》,現代學人特别重視其中的人生論意義,强調其“逍遥遊”的精神追求和“齊物論”的認識自覺。這没有錯誤,因為這樣的研究有當代意義。但是,我們只要細讀《莊子》這部著作,當不會忽略其中大量的政治論。《應帝王》篇的無治主義思想即是,“外雜篇”的諸多篇章又是對於《應帝王》無治主義思想的闡釋發展*參見拙作《〈莊子〉“外雜篇”對於〈應帝王〉篇的思想發展》,載《國學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而且,我們還應該認識到,莊子的人生論也是對於現實社會政治無奈以後的逃避,故而其在超越性的背後,有着對於儒家、法家這些有為政治的批判,滲透着生命的大悲苦。脱離了社會政治這一層面,恐難以把握莊子人生論的真諦。
再如《公孫龍子》,自從梁啓超用西方邏輯理論予以解讀,提出“名即概念”説後,學界對它的認識大多落實在邏輯學範疇内。但是,透視其背後意義,我們也能認識到,這樣“名”的表達是政治形式規範化的要求。故而顧實為張懷民《公孫龍子斠釋》所作的“序”説:“名家之於政治,其關係尤至密切重大乎,然則《公孫龍子》一書,於先秦政治思想,有重大之價值。”*張懷民《公孫龍子斠釋》,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頁。胡適也説:“古代本没有什麽‘名家’,無論那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根本方法。這種方法,便是那一家的名學。”*胡適《惠施公孫龍之哲學》,載《名學稽古》,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19頁。
其他諸子的政治意圖更不必言。諸子並非純粹學院派的,在象牙塔内,即使如稷下學宫,也“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論儒》),“咸作書刺世”(《風俗通義·窮通》)。因此可以説,社會政治的實踐性是“子學”的根本所在,其内在的理論只是有關於實踐的闡釋。後學假如局限在理論範疇内分析討論,恐怕不能獲得本質性的領會。
唐宋以來,學界以為先秦有個旨在道德修養的思孟學派,給予特别的重視。其實,這只是那個時代的解釋而已,並非子思、孟子的本旨。孟子為帝王師的精神和指示學人皆知,不必贅言;即使被學界普遍認為講修養之道的郭店竹簡《五行》,也强調“和則樂,樂則有德,有德則邦家興”,社會政治的目的顯而可見。與荀子相比,子思、孟子確實更强調心性修養的重要性,但是其言語針對的是政治人物,故而所强調的也是政治參與者的心性修養,本旨没有遊離過社會政治領域。《荀子·非十二子》斥其“略法先王而不知統”,也着重指其政治思想的錯誤。衆所周知,唐宋時期已不存在政治思想的方向性問題,當時需要考慮的是政治措施的修補、落實和在該制度下如何使個人生命具有意義的問題,因此倡導思孟學派是那個時代的需要。現時代的歷史任務和文化需要已經與宋明時代不同,我們自然不應該再像宋明理學那樣來解釋思孟學派。
顯然,“子學”的起源與東周時期劇烈變革的歷史環境有關,諸子的思想本旨指向社會政治領域,這些已經是中國思想史的常識。諸子的思想無疑已經拓展到了哲學、倫理、教育、經濟、軍事等領域,有形而上的企圖,諸子可稱為思想家、倫理學家、教育家、軍事家等,但這些都是其社會政治認識廣泛化和深入化的結果。離開這一根本點來討論“子學”問題,不免遊離了其本旨。思想史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一個新的時代需要思想資源並企圖從中獲得啓益時,必須追溯到它的源頭,如卡爾·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説所言*卡爾·雅斯貝爾斯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後,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同時出現文化突破現象:“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這個時代産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範圍的基本範疇。”(《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頁)。漢以後的思想發展都是通過對諸子思想的創造性闡述建立起來的,我們現時代也不例外。因為前一個時代的解釋是出於前一個時代的需要,而新的時代有新的需要,回到源頭上,才可能獲得真正的思想啓迪。因此,當代政治和新文化的建設不宜接着宋明理學講,而應當回到先秦諸子中去,從中去覓取思想資源。
二、 新子學的興起基於近現代政治變革的要求
在漢武帝以後,諸子的思想争鳴畫上了句號,經學走上了社會政治思想的主舞臺。這種轉變是歷史的合理選擇,因為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方針符合小農業經濟時代的需要。那個時代,家庭為社會經濟文化的基本單位,儒家的血緣親愛原則和禮樂制度最適宜家族社會的長治久安。於是,接下去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制度的落實和開展。其中當然有具體的問題需要討論和修補,但那不是屬於方向性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説,到漢武帝時,諸子思想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隨後的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則着重於解決這種社會形態下的生命意義的問題,其對於諸子思想的解讀,都是基於該時代需要的誤讀和發展,遊離了政治領域。例如關於老子,漢初一般與黄帝合稱為“黄老”。“黄老”是一種“治術”,一種政治理念。到了東漢,其開始蜕變為個人品性與人生的修養,如《後漢書·光武帝紀》:“黄老養性之福。”到魏晉以後,老子更多地與莊子合稱為“老莊”,“老莊”取代“黄老”,即衍化成了個人的性命修養之學。故而陶希聖説:“老子在西漢初期與黄帝的傳説相結為‘黄老’而為經世的思想。東漢末年以後,莊學才盛大起來,老子在此時乃莊學化而為‘老莊’,為魏晉以後士大夫間的避世思想。”*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書店1996年版,第122頁。儒家學説也是如此,從“周孔”到“孔孟”的轉折即是明證。在“周孔”中,孔子是政治思想家;而在“孔孟”中,孔子則主要以道德聖人的形象出現。
提高学习动力,激发学习兴趣,强化自控能力,抵抗手机诱惑 大学生需要清楚上大学的目的、树立学习意识,应该自我反思课堂表现,通过教师的引导,根据自身的学习动机发展水平进行人生规划、目标定位,从而激发个人对所学课程的兴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知识的学习和建构有赖于学习者积极主动地思考和参与,有赖于学习者主观思维的能动与加工。因此,学生需要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抵制手机诱惑[8]。
到明末清初,面對淪喪於文化思想比自己落後的民族的事實,士人才又開始重視政治建設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認識是: 宋明以來單純重視心性修養,忽略了政治方面的問題;正是政治的腐朽,導致了國家的淪亡。基於這樣的認識,傅山開始重視荀學,並開啓了諸子學研究的思潮*荀學被重視始於傅山。傅山著《荀子評注》與《荀子校改》,指出荀學具有刺取諸説、兼收並蓄的特點:“其精摯處即與儒遠,而近於法家,近於刑名家;非墨,而又有近於墨家者言。”“申、商、管、韓之書,細讀之,誠洗東漢、唐、宋以後之粘,一條好皂角也。”。
清中葉以後,因為西學的衝擊,諸子學更普遍受到關注,這也是出於政治變革的需要。其中荀子和墨子尤甚。這兩家在經學時代基本上被忽略,但是因為其可以提供現代政治所需要的思想元素,清末以後越來越受到重視。關於荀子,或認為其是專制主義的罪魁禍首,封建政治的崩壞與之有關;或認為其“性惡”説能開拓出現代民主政治和法制模式,中國要成為民主、法制的國家,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上較之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要堅實得多。關於墨子,一方面認為它可以接引西方的科技文明,如俞樾《墨子閒詁序》説的:“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為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另一方面,也是認為墨家的“兼愛”、“尚賢”、“非攻”、“節用”等觀點,體現着博愛、平等、民主、和平的思想,更合乎現代公民社會的需要,具有走向現代性的可能。例如梁啓超曾説:“楊學遂亡中國,今欲救之,厥惟墨學,惟無學别墨而學真墨。”*梁啓超《子墨子學説》,載《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册,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頁。20世紀末,張斌峰、張曉芒的《新墨學如何可能》還宣稱:“無論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構和科學理性精神的確立,還是從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的現實價值層上,抑或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墨學,墨家學説在建立新的全球社會時,將會比儒學和道家之學可能提供得更多。”*張斌峰、張曉芒《新墨學如何可能》,刊《哲學動態》1997年第12期。
現代以來影響甚大的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等學派,從先秦諸子中尋覓思想資源,目的也無不在於現代社會政治的轉型問題。故而賀麟説:“儒家思想的命運,是與民族的前途命運、盛衰消長同一而不可分的。”*賀麟《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載賀麟等《儒家思想新論》,正中書局1948年版,第2頁。陳啓天説:“近百年來,我國既已入新戰國時代之大變局中,將何恃以為國際競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惟有參考近代學説,酌採法家思想,以應時代之需求而已。”*陳啓天《韓非子校釋》,中華書局1940年版,“自序”第2頁。這些學派的政治思想和設計都不免有簡單化、理想化甚至迂腐的問題。例如傳統儒學的核心觀念“禮”和“仁”具有等差性的特質,難以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念,更有違現代政治的基本準則。新法家的全部設計,寄託於一個絶對遵循法律的國家領袖或領導團隊之上,要求他們都具有崇高的道德覺悟和歷史使命感,能力卓越,顯然没有普遍的可能性。但是,這些學派重視子學的志趣所在則是顯而可見的。
這裏,我們還應該注意到,近代以來的士人在重視子學研究的同時還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的實踐活動,這顯然與先秦諸子的生命形態相一致。例如新儒家人物梁漱溟,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推行鄉村建設運動,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參加組織“中國民主同盟”,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一生事業重在踐行上。即使如馬一浮這樣的純粹學者,曾謝絶北京大學的任教邀請、蔣介石的許以官職,在抗戰時也出山創辦復性書院,參與民族復興的事業。再如蔣百里,我們講現代新子學時往往只注意到其《孫子新釋》是第一部系統地運用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著述,具有現代軍事科學精神。其實,他還是現代的兵家,1937年出版的《國防論》提出全民性、持久性的抗日總戰略、總方針,與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精神相一致。他還是縱横家,1937年9月,他以蔣介石特使身份出訪意、德等國,贏得了諸多國際人士對中國抗戰的同情。這更是與先秦諸子一樣的實踐,從某種角度講,這正是“新子學”,即“新子”之“學”。
當然,現代的子學思想和新子學研究也開拓到了哲學、倫理、教育、經濟、軍事等領域;尤其新子學的研究,在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下重視形而上思想體系的建構*此類著述甚多。例如: 郎擎霄《墨子哲學》(1924),陳顧遠《孟子政治哲學》(泰東書局1924),陳顧遠《墨子政治哲學》(泰東圖書局1925),熊夢《墨子經濟思想》(志學社1925),王治心《孔子哲學》(國學社1925),欒調甫《墨辯討論》(1926),蔣維喬《墨子哲學》(1928),陳登元《荀子哲學》(商務印書館1928),蔡尚思《孔子哲學之真面目》(啓智書局1930),楊大膺《孔子哲學研究》(中華書局1931),顧實《楊朱哲學》(東方醫藥書局1931),汪震《孔子哲學》(百城書局1931),孫思昉《老子政治思想概論》(商務印書館1931),貝琪《老莊哲學研究》(1932),公羊壽《孫子兵法哲理研究》(國光印書局1933),余家菊《孔子教育學説》(中華書局1934),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山西國際學社1934),胡哲敷《老莊哲學》(中華書局1935),余家菊《荀子教育學説》(中華書局1935),黄漢《管子經濟思想》(商務印書館1936),蔣錫昌《莊子哲學》(商務印書館1937),劉子静《荀子哲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38),陳啓天《韓非及其政治學》(獨立出版社1940),陳啓天《韓非子校釋》(中華書局1940),馬璧《孔子思想的研究》(世界書局1940),洪嘉仁《韓非的政治哲學》(正中書局1941),楊寬《墨經哲學》(正中書局1942),馬雲聲《孔子和老子的政治思想》(海風出版社1946),徐賡陶《孔子的民主精神》(南賓印刷公司1947),杜任之《孔子論語新體系》(復興圖書雜誌出版社1948),趙紀彬《古代儒家哲學批判》(中華書局1948)。。張岱年曾説:“先秦時所謂‘學’,其意義可以説與希臘所謂哲學約略相當。《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其所謂學,可以説即大致相當於今日所謂哲學。先秦時講思想的書都稱為某子,漢代劉歆輯《七略》,將所有的子書歸為《諸子略》,於是後來所謂‘諸子之學’,成為與今所謂哲學意謂大致相當的名詞。”*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但是,他們對於新子學的基本點在於社會政治領域的認識也是普遍的。陳柱尊的話可謂代表:“吾以謂今日欲復興中國,莫急於復興儒家之立誠主義,道家之知足主義,法家之法治主義,墨家之節用主義。”*陳柱尊《中國復興與諸子學説》,《復興月刊》第一卷第十期(1932)。無疑,歷史轉折時期的政治轉型需要是新子學興起的根源,新子學的研究成果也主要落實在這一個領域。
三、 當代“新子學”研究的發展思考
疏理清諸子思想産生和晚清民國時期子學復興的歷史原因,就可以認識到: 當代新子學研究是晚清民國時期子學復興的接續,而核心在於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建設上;有關文化的、形而上思想體系的建構,實質上都有當代政治需要的背景。
衆所周知,現時代與産生諸子思想的春秋戰國時期有很相似的一點,即都處於舊文化規範崩壞、新文化規範尚未建立的歷史轉折期。在春秋戰國時期,戰亂不靖,禮崩樂壞,面對這樣的形勢,先秦諸子提出各自的政治方向和處世策略。而現代以來,佔據了二千多年歷史統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制度被摧毁了,傳統倫理也失去了絶對的控制力,現時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是與先秦諸子相似的歷史使命。因為新的合乎時代需要的社會政治制度建設的問題在當前依然存在,因此當代的“新子學”和“新子學研究”有着巨大的意義。
由此看,當代的“新子學”和“新子學研究”必然接踵近現代而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士人思想和子學研究成果應給予充分的重視。不但入世參政的精神應該繼承,研究的成果應該批判接受,其中的欠缺也宜有充分的認識。如此,才可能繼往開來,真正實現子學的復興,完成我們這一時代的歷史使命。
晚清民國時期子學復興的表現主要有二: 一是關注政治思想和制度文化的變革,投身於這一歷史轉折階段的社會活動;二是以科學的精神和邏輯的方法整理研究諸子典籍。前者可謂“新子學”,後者則是“新子學研究”,這些已經被學界所公認。當然,因為這一時期太短,又處於戰争的環境中,不免有諸多缺略。比如研究時斷章取義、簡單比附、割裂原有血脈等問題,已為學界所普遍認識。這裏,另外談三個比較深層次的問題。筆者以為,其是“新子學研究”中的問題,也與當代“新子學”的發展方向有關。
一是對於個體意義重視不够。强調個體意義是現代文化的基本理念。愛因斯坦曾説過:“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美] 愛因斯坦著,許良英譯《我的世界觀》,載《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4頁。哈威爾也説:“個人自由所構成的價值高於國家主權。”*[捷] 哈威爾著,張鈺譯《論國家及其未來地位》,轉引自《大學人文讀本: 人與世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頁。從人類的發展歷程看,“人”的發展有兩個關節點: 一個是群體的“人”從“天”中獨立出來,不再在“天”、“神”的管轄下,具有自存自為的意義;另一個是個體的“人”的普遍自覺,個體作為國家社會的基本單位成為常識。在中國歷史上,前者約在殷周時期,後者則在民國以後。由此可知,先秦諸子的思想必然基於群體的“人”的範式,其是“天人之分”(《荀子·天論》)後“人道”的具體展開;而民國以來的新子學研究有現時代的特定要求,宜以個體的“人”的自覺為基礎,其思想範式、思維形式當與舊子學研究有質的不同。衆所周知,民國時期是新文化得以宣傳廣大的時代,反對封建禮教,倡導個性解放,正是那個時代激動人心的口號和實踐。其中的新子學研究,自然宜以此為基本點之一。不過,從實際的情形看,其尚未有如此的普遍自覺。學界更多地重視諸子思想對於現代社會建設的作用,没有去探究其中藴含的個體性因素的現代意義。他們或者以整體統攝個體,或者以個體逃避整體,而未曾去闡述個體本位基礎上的社會意義。
毫無疑義,諸子思想的本旨指向社會整體。即使如莊子的“逍遥遊”,也並非只是自我個體的意願,而是對於一般的人的生命意義的思考和描述。但是,這不是説諸子的思想形式也是一般性的;相反,其形式往往是個别和特殊的,與内容指向構成不統一性。這種不統一性,一方面影響了思想内容的邏輯系統性,以至現代學人認為其存在概念不明確、邏輯不嚴密的問題;另一方面,其也構成了思想的張力,給予我們從形式的個别性入手闡述意義的可能性。例如關於《論語》,其語録意義的豐富性和多向性即與形式有關。《論語》的許多語録即人即事而言,屬於個體片斷經驗的記録,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的感情和思想表達往往以個體自我或個體對個體的形式出現,其原始意義只有與語録存在的具體語境和涉及的特定對象結合起來才能被客觀地認識。這種個體不是典型創造、寓言寄託的人物,而是具體實在的、經驗的,是特定時空的實踐存在。這樣的語録所包含的意義,原旨落實於特定的個體,隨後因為指向的類别化、一般化而由個别擴展至社會一般。現代以來的學界普遍重視《論語》的一般性意義構成,據此建構孔子的思想體系,這自然是極有價值的工作。但是,其形式特徵也指示我們另外的路向: 即從個體性的需要出發,認識語録的特定性意義,並加以生命實踐的體驗。後者顯然具有當代性意義,但是没有得到學界足够的重視。
二是對於多元價值缺乏普遍認同。以個體為本位,必然表現出價值的多元性,意味着多元選擇的可能性。毫無疑義,多元性也是文化現代性的基本準則。東周時期百家争鳴,對於社會政治和人生活動提出了各種認識,客觀上是一個多元選擇的時代。漢武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孔子學説提升為“經”,造成了統治階級的一統價值觀。縱然,其不乏歷史的合理性,但是在歷史的行程中導致民族思想萎縮、文化活力衰弱也是不争的事實。由此推知,“新子學”的研究應該抛棄一統的價值觀,倡導多元性。但是民國時期的新子學研究在介紹各家時能客觀列述,在價值意義的闡述時則往往繼承某一派而排斥其他各家,對於多元性缺乏足够的重視。現代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這些學派莫不如此。例如,以發揚儒學“道統”、接續宋明理學為己任的現代新儒家學派認為,只有走以“内聖外王”為本、由内聖開出新外王的道路,才可以實現中國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新墨家學派則認為,“兼愛”、“尚賢”、“非攻”、“節用”等觀點體現着平等、博愛、和平的思想,更合乎現代公民社會的需要,具有走向現代性的可能。新法家學派則以為20世紀的世界相當於“新戰國”時代,戰國時代法家的實踐卓有成效,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只要採納新法家的策略就可實現。這三種思潮各有思想角度,各有價值,但是假如以自我為唯一正確的選擇,不吸納其他各家的合理因素,顯然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有關個人的生活理念也是如此,社會不同成員有多元的選擇是自然的現象。因為無論孔子、楊朱,還是莊子的生活觀都有價值,任何適合某一個體的本性和生活形態的都是合理的。這三種觀念(也包括其他觀念),在現代社會中當可並存,但是民國時期的學人大多從社會整體的需要出發,倡導某一種觀念而不及其他。
三是對於形而上思維的考慮不周。形而上思維指的是超越現實層面的具體事物的理性認識。其以概念為基礎,通過判斷、推理等邏輯方式構成系統思想。這些基於概念的認識與現實世界有聯繫,但是已經擺脱了特殊性和偶然性。具有這樣的思維形式,無疑可以對現實層面有更客觀、全面、透徹的認識,避免那些落實於社會政治領域的形而下思維所不免有的局限性。顯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没有純粹的形而上思維。中國古代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和科學,正是這種缺乏的典型表現。現代新文化的發展,需要開拓出形而上思維;而這項工作,最有可能的是通過對諸子思想的再闡釋來完成。民國時期的新子學研究已經有這樣的認識,例如李相顯《先秦諸子哲學》説:“我作此書,完全抱客觀的態度,用邏輯及解析的方法,以研究各哲學大師底哲學理論,而敘述其哲學系統。”*李相顯《先秦諸子哲學·自序》,北平世界科學社1946年版,第1頁。後來馮友蘭也曾經説過:“把過去哲學史中的一些命題從兩方面講,分别其具體意義和抽象意義。”*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産的繼承問題》,載趙修義等編《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録與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頁。他的抽象繼承法即是形而上思維的自覺。但是,從整體上看,其尚未被充分地認識到*參見拙作《略述民國時期的新子學研究》,《諸子學刊》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如前所述,先秦諸子的思想確實基於社會政治和人生意義的認識,他們的思想價值更多地表現在現實層面。但是,在他們的背後,還是有“天”、“道”這些形而上的存在。有了“天”、“道”,現實的政治和人生活動就有了神聖性和長遠的意義,有了合理性和絶對性。故而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墨子有“天志”,孔孟把道德修養與“天”聯繫起來。郭店竹簡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可謂人倫社會與天道契合的明確表述。“天”、“道”這些形而上的存在,即是建構形而上思維體系的基礎,這方面的工作顯然還有很大的空間。
顯然,先秦諸子的思考以天才個體的形式出現,可以與現代的個體本位意識相連接。諸子的争鳴,是基於對社會政治形態和個人生命意義的不同思考,其在那個時代的並存及由此産生的思想活力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遠影響,都足以啓示現代多元觀念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先秦時代有“天”的信仰,諸子以“天”為價值的根本所在和判斷的根據所在,由此發展,也有創發形而上思維的路徑。從這一點看,個體本位意識、多元價值觀念、形上思維形式等方面的問題顯然是當代“新子學”研究可以作為的方向。當代“新子學”的發展當然與政治體制的改革相呼應;“新子學”研究的方向,則應該不排除上述的三個重點。
[作者簡介]張涅(1963— ),本名張嵎,男,浙江岱山縣人。現為浙江科技學院人文與國際教育學院中文系教授。著有《莊子解讀——流變開放的思想形式》《先秦諸子思想論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