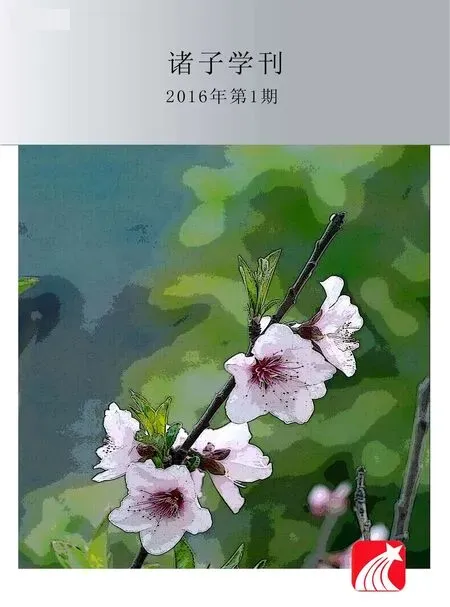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淺見
郭 丹
關於“新子學”的幾點淺見
郭 丹
文章認為,“新子學”與傳統子學在精神上應有延續性和繼承性,可以儒學為參照,“新子學”應該延續和弘揚從先秦時期肇始的子學精神。“新子之學”側重於“立説”之學;“新之子學”則包含詮釋之子學。二者都應該包含在“新子學”的範圍之内。“新子學”首先應該是内容之新。“新子學”是繼承從先秦諸子之學所延續下來的具有傳統文化意義的新學説,這是“新子學”内涵的基本定位。“新子學”要處理好雜與多的關係。還要處理好通與變的關係。“新子學”既要有繼承性,又要有開放性。
關鍵詞 新子學 精神内核 立説與詮釋 雜與多 通與變
中圖分類號 B2
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學”的概念,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在復興“國學”的熱潮中,這是一個頗具建設性的倡導,對於傳統文化的復興有重要意義。對於這一倡導,筆者以為,應有更多的學人來提出問題,補苴罅漏,集思廣益,對“新子學”的概念加以完善。有鑒於此,筆者提出幾點淺見,以供參考。
一、 “新子學”的精神内核
“新子學”,當然是相對於傳統“子學”而形成的概念。“子學”即諸子之學,其最早的含義,是指先秦諸子之學。《文心雕龍·諸子》説:“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入道見志”,不論是入哪家的“道”,抒發的是什麽“志”,諸子之學是闡發自己思想學説之學,是“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説以廣播於天下者”,是針對當時的社會進行思考而提出的治理社會、有關人性的各種主張,是堅持“立原創之見,倡導精神上的獨立與自由”。這就是諸子之學的精神内核。我們提出“新子學”的概念時,應清楚先秦諸子之學的精神内核是什麽;相對於傳統子學,“新子學”的精神内核又是什麽?如何定位“新子學”的精神特質?對先秦諸子之學的精神特質如何繼承,如何延續?這都是應該考慮到的。關於這點,是否可以拿儒家作為參照。有人反對以儒家作為參照,筆者以為恰可以作為“新子學”建設的借鑒。儒家從先秦的原儒→漢儒→程朱理學(新儒家)→現代新儒家,雖然各個不同的時代有各自的特點,但總是有一貫穿始終的儒家精神的基本内核。如宋代理學,又可稱為道學、新儒學。稱為理學,是因為兩宋諸子所創立的思想體系以“理”為宇宙最高本體,以“理”為哲學思辨的最高範疇;稱為“道學”,是因為理學諸子自認為已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統(這正是儒學歷代變化中的不變精神),並宣稱他們的學問路徑以“明道”為目標;稱為新儒學,是因為理學雖以儒家禮法、倫理思想為核心,但其張揚的孔孟傳統已在融合佛、道思想中被加以改造,具有煥然一新的面貌。20世紀20年代産生的現代新儒家,服膺宋明理學,以接續儒學“道統”為己任,面對着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試圖通過吸納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統。以儒家道統為核心,是現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核。同樣的道理,“新子學”與傳統子學在精神上應有延續性和繼承性,而不是割斷的。愚意以為,就宏觀的層面來説,統領“新子學”的精神内核,從先秦時期肇始的子學精神是“新子學”應該延續和弘揚的。就微觀的層面,或者説各個“子”學的具體内容來説,可以各有各的特色。
二、 “立説”之學與“詮釋”之學
先秦諸子學説,指的是春秋戰國百家争鳴時期諸子各家的學説。依劉勰《文心雕龍·諸子》所列,除了儒家學説之外,道家的《老》《莊》《列子》《鶡冠子》《文子》,墨家的《墨子》《隨巢子》,名家的《尹文子》,農家的《野老》,陰陽家的《騶子》,法家的《管子》《申子》《慎子》《韓非子》,縱横家的《鬼谷子》,雜家的《尸子》《尉僚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小説家的《青尸子》,都是“入道見志”之書,可歸為諸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總敘》説:“自六經以外立説者,皆子書也。”但是按照“四庫全書”中“子部”收録的範圍,確也過於寬泛。不過,立足於“立説者”,應是題中之義。宋代的程頤、程顥、朱熹等人,其為“程子”、“朱子”,是為宋代的“新子學”也。他們既符合劉勰的“或敘經典,或明政術”、“博明萬事”、“適辨一理”的“立説者”的標準,也符合《四庫提要》“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的要求。其可謂宋代子學的代表。
再者,上海世界書局編輯《諸子集成》,“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刊行旨趣》),説明已經把子學著作的注疏類文獻歸入“諸子之學”中了。就現在《子藏》第一批第二批所收著作來看,既包括先秦諸子研究之學,也包括歷代的諸子詮釋、研究著作。本來,經學研究也好,子學研究也好,歷來有訓詁和義理兩個層面,也就是説包括訓詁之學和義理之學,有的則是把訓詁和義理融合在一起。拿“莊子學”來説,《莊子》外篇和雜篇是對内篇思想的闡釋,郭象和成玄英則是對《莊子》的詮釋,一直到郭慶藩、王先謙,既包含訓詁,也包含義理,其他的莊學著作,多是如此。同樣的,朱熹的朱子學之後,也有不少對朱子學的注疏、闡釋之作。對於“新子學”,方勇先生已經注意到了“新之子學”與“新子之學”的區别。是否可以這樣來理解,“新子之學”側重於“立説”之學;“新之子學”則包含詮釋之子學(但不是全部)。以這樣的理解,愚意以為“新之子學”與“新子之學”,都是“新子學”所應包括的範圍。此外,還應注意到“立説”之諸子學與“詮釋”之諸子學的區别,二者在概念上有所不同。雖如此,“立説”之諸子學與“詮釋”之諸子學,也應該包括在“新子學”的範圍之内。
新與舊是相對的。舊即指傳統諸子學,那麽新的概念包括哪些?有論者提出所謂新思維、新方法、新觀念等等,這些當然是“新子學”之“新”的體現。但筆者以為,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内容。一個學説和概念的提出,是先有概念口號,還是先有内容,然後從内容中提煉出學説概念呢?當然應該是先有其内容,然後才能總結其精神和觀念,猶如劉勰的論“諸子”,從先秦以至兩漢,列敘諸子之産生和演變,從中總結概括出諸子之學的精神實質與特點。傳統諸子學,還不是由九流十家的諸家著述的思想内容中形成了“諸子精神”嗎?其思維方式、學術方法、時代觀念等等,都是從他們著書立説的具體内容中産生的。“新子學”的提出也要考慮這一點。“新子學”的内容是什麽?正如方勇先生所説:“‘新子學’概念的提出,根植於我們正在運作的《子藏》項目,是其轉向子學義理研究領域合乎邏輯的自然延伸。”因此,“新子學”首先應該是内容之新;精神之新是從内容之新來的。形而上的精神層面和形而下的文獻編撰層面,雖不可分割,但又有區别。所以,這就涉及,如果要編一部《“新子學”文獻》,如何編?如何收?依據《子藏》的編撰體例,“立説”之諸子學與“詮釋”之諸子學都收録,其下限到清末民國前。有論者認為諸子之學的“新”,從清末已經開始,其實如前所説,朱子也是“新子學”,並非僅從清末始。不過此説啓發一個問題,即如果以時間劃線,“新子學”的上限在哪,下限在哪?就文獻編撰來説,《“新子學”文獻》的上限在哪?下限在哪?
三、 雜與多的關係
如上所述,“新子學”可以包括“新之子學”和“新子之學”,也包括“立説”之諸子學與“詮釋”之諸子學。但在學術的界定上,“新子學”又不能太雜,不能變成國學或傳統文化的代稱,或是中國文化的代稱。誠然,把國學只理解為經學,是過於狹隘。對於國學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章太炎認為,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的總稱,它包括“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季羨林説,國學就是傳統文化,它包涵中國古代的文、史、哲以及與此相關的學科。他們雖未點明“子學”這一名稱,但所論無疑包括了子學。國學有自己的内涵,雖然它將隨着時代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子學也一樣,子學也好,“新子學”也好,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學,將應勢成為國學新主體”,這是無疑義的,但不可能是替代國學。有論者認為近代的許多學者可歸入“新諸子”,甚至孫中山也是“新諸子”,經濟之學也是“新子學”。誠如是,那麽,與孫中山同時代以及其後的諸多大家,甚至後來出現的現當代人的各種文集選集,是否也屬於“新諸子”呢?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是否都屬“新子學”呢?誠然,新的時代有新的“立説者”,也必然有新的各家之説出現。但“新子學”是繼承從先秦諸子之學所延續下來的具有傳統文化意義的新學説,這是“新子學”内涵的基本定位。對於這一點,愚意以為應該謹慎,不能讓“新子學”成為包羅萬象的雜燴。
四、 通與變的關係
“新子學”應該把握好“通”與“變”的關係。劉勰説:“變則可久,通則不乏。”“通”是指“新子學”應該繼承傳統子學的精神。“變”則指“新子學”雖然不能成為雜燴,但“新子學”應該具有開放性和創新性。這是毋庸置疑的。就“變”的方面來説,如劉勰認為,像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説苑》、王符《潛夫論》、崔實《政論》、仲長統《昌言》、杜夷《幽求》等,“或敘經典,或明證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因為從確定的標準來説,“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子”與“論”雖略有區别,但“彼皆蔓延雜説,故入諸子之流”亦為合適(《文心雕龍·諸子》)。劉勰這樣的劃分是合理的,因為漢代以後,“諸子之學”的外延已經擴大。經學以儒家經典為其核心内容,確實具有排他性。但是,經學也是開放的,鄭玄的經學吸收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内容而形成了“鄭學”。漢代經學的今古文之争曾經形同水火,主要是利禄之争、政治之争。而“鄭學”能够融合今古文經學二者,説明經學本身、經學各派在學術上具有包容性和相容性。再説五經的發展,從五經到九經到十三經,經書把子學的《論語》《孟子》也收進去。清人編“經解”“續經解”,收録了後代衆多的解經之作。應該看到,經學本身並非封閉而一成不變的。後人要“還經於子”,那是重建新體系的問題。不過,“還經於子”是否必要,還是值得考慮的。從經學的發展歷史來看,無論是紙質流傳的先秦文獻,還是出土簡帛文獻,都可以證明先秦時期《詩》《書》《禮》《樂》《易》《春秋》作為經典的觀念已經形成。後來收“子”入經,即把《論語》《孟子》歸入十三經,是漢代獨尊儒術以後的事,《論語》在東漢時被列入“七經”,《孟子》在宋代被列入“十三經”,就這兩個時期的背景來看,就知道其目的在於以孔孟思想强化儒學的道統。特别是元代延佑中恢復科舉,《論語》《孟子》被定為科舉的教科書之後,其地位遠遠超出了一般的子書。今天如果提出要“還經於子”,是希望恢復二者子書的本來面目。但無論是“收子入經”還是“還經於子”,都説明儒學本身亦非一成不變。所以,“新子學”也一樣,“博收而慎取之”,既不能太雜,又不能是封閉的,應該處理好“通”與“變”的關係。
[作者簡介]郭丹(1949— ),男,福建龍巖人。現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著作有《左傳國策研究》《先秦兩漢史傳文學史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