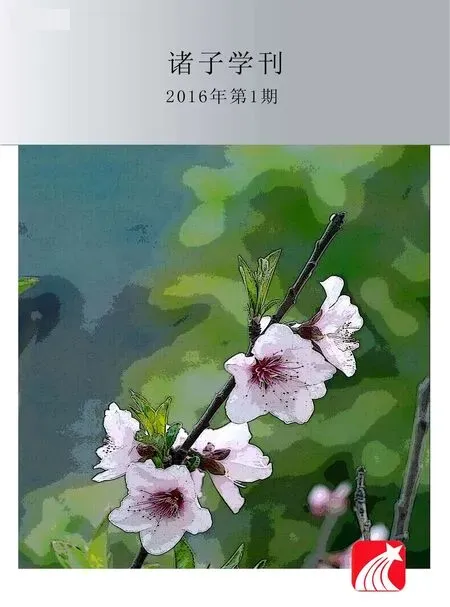論“子學思維”與“子學精神”
歐明俊
論“子學思維”與“子學精神”
歐明俊
相對於經學思維,子學思維是創新思維、理性思維、科學思維,如辯證思維、全息思維、中和思維、抽象邏輯思維、形象思維、直覺思維、相對思維、變通思維、逆向思維、否定思維等。子學精神不同於求真求實的史學精神,最重要的是理論創造,是“大丈夫”精神、執著精神、犧牲奉獻精神、尚氣節精神、仁愛精神、謙虚好學精神、科學精神、自由精神、獨創精神、争鳴精神、叛逆精神、懷疑精神、批判精神、擔當精神、會通精神、開放精神、和諧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寬容精神等。子學精神一直鮮活地存在着,“新子學”的神聖使命,就是接續子學精神的“學脈”。
關鍵詞 新子學 子學思維 子學精神 史學精神 學脈
中圖分類號 B2
方勇先生在《“新子學”構想》中呼吁重視“子學思維”研究,認為“子學根植於中國文化土壤,其學術理念、思維方式等皆與民族文化精神、語文生態密切相關”,“在思維方式上,諸子百家重智慧,講徹悟,不拘泥於具象,不執著於分析”*方勇《“新子學”構想》,《光明日報》2012年10月22日。;又於《再論“新子學”》中强調要“從經學思維和體系的禁錮中真正解脱出來,以開放的姿態傳承歷史文化,維護學術開放多元的本性,積極構建具有時代特徵、富於活力的‘新國學’”,批評以“傳統經學思維與觀念”理解“新子學”。又説:“就深層意義而言,‘新子學’是對‘子學現象’的正視,更是對‘子學精神’的提煉。學者崇尚人格獨立、精神自由,學派之間平等對話、相互争鳴。各家論説雖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現實以深究學理,不尚一統而貴多元共生,是謂‘子學精神’。”*方勇《再論“新子學”》,《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呼吁重視“子學精神”的提煉。筆者拜讀後,深受啓發,兹就這一問題略抒淺見,求教於方勇先生和學界方家。
一、 子學思維
此處所説“思維”,並不是指思維科學所研究的思維機制和實驗,而是指思維方式,即如何思考問題,是思維科學的應用問題。所謂“思維方式”,是指人們通過思維活動,為了實現特定思維目的所憑藉的途徑或方法,亦即思維過程中所運用的手段。子學思維特色明顯,大體上是學術思維,是創新思維,是理性思維、科學思維,即按一定的邏輯和道理來思考問題。
辯證思維 辯證思維强調事物的變化是量變與質變的統一,量變是質變的前提和必要準備,量變達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質變,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荀子·勸學》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方勇、李波譯注《荀子》,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頁。本文所引《荀子》原文,皆據此本。事物自身包含着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矛盾就是對立統一,矛盾雙方相互排斥、相互分離,又相互吸引、相互聯結,在一定條件下相互依存,又依一定的條件相互轉化。《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羅義俊《老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頁。本文所引《老子》原文,皆據此本。要善於從福中看到禍,從禍中看到福,看問題不能静態化、絶對化。《荀子·不苟》曰:“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心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要防止片面性。矛盾存在特殊性,矛盾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莊子·駢拇》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方勇譯注《莊子》,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35~136頁。本文所引《莊子》原文,皆據此本。事物各有自己的本性,不能以統一標準强求一律。
辯證思維是一分為二思維,堅持兩分法看問題。但是很多時候,一分為二思維容易走向極端,絶對化、簡單化、片面化,二元對立,兩極思維,極端肯定或否定,非此即彼。如孟子言性善,荀子則言性惡,《荀子·性惡》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儒家重禮治,法家重法治,水火不相容,尖鋭對立,儒家强調“隆禮”,斥法家為“無教化,去仁愛”,而法家斥儒家為“以文亂法”,為不通世務之腐儒,二者各執一端,自以為是,都是極端思維。
全息思維 所謂“全息”,指部分是整體的縮影,個體是全體的縮影。全息思維,即强調由一點見全體,通過一個表徵來看到事物的全貌。《韓非子·説林上》曰:“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高華平、王齊洲、張三夕譯注《韓非子》,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58頁。窺一斑而知全豹,從一點推出全部,舉一而反三。《淮南子·説山訓》曰:“以小見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4頁。《華嚴經》認為,一即一切,一中知一切,小世界即是大世界,知一世界即知無量無邊世界。我們見燕子歸,而知春天來了,又説牽一髮而動全身。西醫分科,頭痛医頭,腳痛医腳;而中醫僅僅通過號脈,通過一個表徵,便可知道全身疾病,即是一種全息思維。
中和思維 《論語·先進》曰:“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過猶不及”,就是恰如其分,就是《尚書》説的“允執厥中”,不偏不倚,“中庸”之道,兩極間取其中。《孔子家語》卷四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縱欲則敗。”*王國軒、王秀梅譯注《孔子家語》,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01頁。强調凡事不要過分,應把握一個“度”。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根據“意欲所向”將人類文化分為西方、中國、印度三種類型,他認為,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條路徑樣法: 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和、持中,就是“一分為三”思維,如此看問題更合理,可參看龐樸《一分為三論》。
抽象邏輯思維 抽象邏輯思維是以抽象概念為形式的思維,是思維的核心形態,主要依靠概念、判斷和推理進行邏輯思維,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和規律性聯繫的思維,是高級的思維方式。如墨家、名家,重視概念辨析,邏輯思辨。墨子善於推理,如“為善者福之,為暴者禍之”*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463頁。本文所引《墨子》原文,皆據此本。,善於歸謬法的運用,懂得矛盾律和排中律。名家惠施的“合同異”,公孫龍的“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取象類比,皆是運用抽象邏輯思維的典型。
形象思維 形象思維重感覺、知覺,是具體、可感的,人們通過形象可以抽象出事物内部的本質,可表達抽象思維的内容。《莊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中,皆多寓言故事,即是用形象思維論證問題、説明問題。《莊子·逍遥遊》描述了鯤鵬形體碩大無比,變化莫測,氣勢壯美;描述了蜩與鳩因身輕翼小、飛不高、行不遠,卻自以為得到逍遥,從而嘲笑鵬鳥的行徑;又通過朝菌、蟪蛄、冥靈、大椿等例子,用卮言得出結論: 它們都是有所待的,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至人”“神人”“聖人”才能達到無所待;又用四個寓言形象説明,使人對其結論加深理解,自然接受。莊子在“遊”中做到主觀精神與“道”的合一,進入《齊物論》所説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神與物遊,思與境諧,莊子“遊”的過程,想象與形象緊密結合,有强烈的感情活動,生動的物象,豐沛的情感,奇異的想象,不拘泥於形式,超越時空,進入自由境界。學術研究,並不排斥形象思維。
直覺思維 直覺思維就是採用非分析、非邏輯的方法,通過知覺、感悟、内省等方式思考問題。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説:“所謂直覺,就是一種理智的交融,這種交融使人們自己置身於對象之内,以便與其中獨特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符合。”*柏格森著、劉放桐譯《形而上學導言》,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4頁。《莊子》説其書中“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又説“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莊子“寓言”是借人、借物、借事所説的話,“重言”是讓人信服的耆艾之言,卮言是如酒一般的合道之言,“三言”即是直覺思維。莊子對道的體認,是憑直覺來領悟,是自主性思維,以一(道)統萬,以有顯無,以物觀物,以外托内,正反互見,模糊性,而不求精確性。莊子講徹悟,不拘泥於具象,不執著於分析,是感知,是整體觀照。
相對思維 相對思維承認並重視相對性,不絶對化。如莊子覺察到認識的相對性,指出物質的不確定性,所謂“逍遥遊”的“遊”,便是“遊心”,指遊於觀念世界,特别指不受對立範疇的邏輯限制,打破自我與非我、非我與非我、自我與自我的絶對分界,即是不是、然不然、可不可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其他還有如變通思維,根據現實的變化而採取靈活變通的方式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兵家的代表人物孫武、吴起等,其思維核心是兵無常勢,水無常態。逆向思維,如孟子提出“性善論”,荀子則提出“性惡論”。否定思維,批判思維,老子、墨子、莊子皆多否定思維,甚至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批判一切,導致歷史虚無主義和文化虚無主義。理性思維,如荀子“天人相分”的天道觀,《荀子·天論》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比較思維,求同比較或求異比較,等等。
子學思維可以經學思維為參照。經學思維,是指由儒家對“六經”和孔孟經典的傳習、注解和闡釋所彰顯或表徵的一種模式化的思維習慣或認識價值取向,持續不斷地“依經演繹”和“返本求真”。熊十力《論六經》説:“六經為中國文化與學術思想之根源,晚周諸子百家皆出於是,中國人作人與立國之特殊精神實在六經。”*熊十力《論六經·中國歷史講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頁。饒宗頤先生認為“經”講“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與自然相協調,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取得和諧的境界。經的内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四,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0頁。。經學思維,講常道,平實無奇,是穩定性思維、模式化思維。儒家嚴格規定高低貴賤社會等級行為規範,形成了固定模式。其理想狀態是: 聖王、賢臣、義士、順民。儒家的思想邏輯是: 天下都是安分之人,於是天下無紛争,無紛争則天下太平,也就達到了社會治理的極致。
經學思維大體上是守舊思維、守成思維,依傍前人,如董仲舒依傍孔子,宋明理學家依傍孔、孟。經學時代,儒家定為一尊,儒家的典籍成為“經”,為全國人的思想樹立標準,限制規範,人們的思想都只能活動於“經”的範圍之内,即使有一點新的見解,也只能用注疏的形式發表出來,習慣於依傍古人的才能思想。教條化,只以權威的思想為自己思想,故無大變化,無大進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長期處於獨尊的地位。以思想上的大一統,維護政治上的大一統,一切不符合自己思想的皆視為“異端”。如此,重在創新的“子學思維”便被窒息。經學思維不容忍不同的聲音存在,以正統思想姿態討伐“異端”並阻滯其發展和進步。經學思維是唯一思維、排他思維、專制思維,專斷、霸道,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唯一,求人與己同,排斥異己,凡是不符合我的統統都應被抛棄。學術思想,本應該是百家争鳴、百花齊放,卻變成了一花獨放、一家獨語。
經學思維是線性思維,如《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邏輯推理簡單化,實際上,事物前後環環相扣,聯繫並非那麽絶對,即便一個環節的成功並不意味下一個環節的必然成功,如果條件不許可,齊家者未必能治國,需要機會,還要看個人的能力是否真的可以治國,能齊家的人,未必就能治國,能治國的人,也未必能平天下。
經學思維是後視思維,就是一切向後看。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信而好古”,是説對於古代思想文化深信不疑,老彭是商時的賢大夫,做了許多傳述的事,“竊比於我老彭”,就是私下把自己比為老彭,以老彭為榜樣,述而不作,就是傳述而不創作,主觀上不打算自創新學。退化論,今不如古,一代不如一代。孔子曰:“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他認為所處的時代不如西周,人心不古。後視思維,消極中有積極的一面,承認自己智力和能力的局限性,重視歷史積累,尊重古人智慧,不陷入歷史虚無主義。不輕易否定古人,强調繼承歷代以來的智慧。後視思維,論證問題,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證經,可以難一切傳記。
經學思維是肯定思維,遵從,不願懷疑,不敢懷疑,無能懷疑,只説好,不説不好,肯定古代一切,對缺點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封閉,固化,缺乏活力。尊古、托古、泥古,迷信過去,不敢創新,如“疏不破注”。經學思維是絶對思維,以正統、正宗、主流自居,話語霸權,文化控制,權威主義,排斥邊緣、異端,甚至禁毁消滅。經學思維是壟斷思維、一元化思維,而子學思維是多元化思維。
子學思維與經學思維的差異只是相對而言,不是絶對的,決不能將兩者對立起來。其實,兩者有相同、相通處,如皆重視整體思維。整體思維講“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追求不同質的事物之間的聯繫、影響、滲透和整合,明顯有别於西方分析、局部、以形式邏輯見長的思維方式。《周易》重整體、系統的思維方式,對國人的整體思維方式産生深遠的影響,造就了中國人善於採用整體、全息、系統的思維方法,而不是局部、解剖、分析來考慮問題。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融合與貫通,對事物的整體把握和感悟,有可能進入事物的本源,掌握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内在聯繫。“文史哲不分家”,文學和史學、哲學相互滲透,相互關聯,它們之間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聯繫,如果將其人為地分割開來,就不可能取得正確認識。《荀子·解蔽》開宗明義地指出:“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即人之大患在囿於一己之見,而不通達於大理。他批評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而主張通識事物的“大理”,即“合二而一”的整體思維,不囿於一孔之見、一得之識。荀子主張治國安邦,要“隆禮重法”並舉,《荀子·君道》曰:“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認為禮教與法治是一個政體有效機制的兩個方面,二者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中醫就是整體思維方式最典型的代表。整體思維是全面思維,全方位思維,避免片面;是多元思維,或多維型思維,避免單一、一元;是系統思維,避免孤立。整體思維重共性、整體、宏觀,不肢解研究對象,不支離破碎,有别於西方分析思維,這是東西思維方式的最大差異。“西學東漸”,嚴格的西學學科分類,明快的邏輯和清晰的條理,研究方法趨於簡潔,便於運用,中國特色的整體研究被遺棄,甚至被當作落後的思維方式而受到批評,應破除西方學術霸權對中國學術的束縛。整體思維是“一”思維,一種從根本上把握,從大局把握,超越細枝末節的高級思維,如《老子》説:“昔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劉宗周《讀〈大學〉》曰:“夫道,一而已矣;學,亦一而已矣。”*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十五《雜著》,清道光刻本。當然,整體思維有時是模糊思維,不清楚,不够科學。
子學思維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思維,敢於創新,並善於創新,有思想,敢於並善於表達自己的思想,且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
子學思維亦有弊端,容易遊談無根,空言“義理”,一偏之見,以自逞胸臆。“新子學”思維上要創新,要時刻警惕經學思維的專制獨斷,同時也要有自我反省、反思能力,警惕新的專制思維。
二、 子學精神
學術精神是學者追求的學術之“道”,是本,它對應“術”,“術”是末。“子學精神”造就了中華民族精神文化,應注意提煉升華,承繼發展。林其錟先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一文中總結了五方面的“諸子精神”,即: 入道見志、自開户牗的原創精神;述道言治、拯世救俗的求實精神;飛辯馳術、百家飆駭的争鳴精神;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的會通精神;與時競馳、通變無方的開放精神*林其錟《略論先秦諸子傳統與“新子學”學科建設》,《諸子學刊》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1頁。。
“子學精神”可與“史學精神”比較看。史學最重要的是求真求實精神,班固《漢書·司馬遷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22頁。史學要求如實表達事實真相,真實、可靠,尊重事實,求是,求真,實録,紀實。史學求真傳統,如實揭示人類活動的基本軌跡,注重史實,不空言義理。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自序》明確指出:“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史學研究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去偽存真,尊重事實,講究實證。史學之弊,繁瑣考證,堆砌資料,疊床架屋,襲陳言,以偏概全,見小遺大。
子學精神不同於史學精神,最重要的是創新,是理論創造。
“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人格,獨立不惧。《孟子·滕文公下》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滕文公下》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説“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並説這種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大丈夫”追求高尚人格,陸象山曰:“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陸九淵《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47頁。又曰:“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 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同上書,第439頁。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曰:“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焉,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三,清康熙刻本。
執著精神 執著精神近乎一種宗教性的情感,熱愛學術,執著理想,就像熱愛生命一樣。孔子一生以追求真理為己任,説“朝聞道,夕死可也”。他生於亂世,積極入世,道不得行,累然不得志,明知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秩序很難在現實中建立,依然不屈不撓地為之奮鬥,“知其不可而為之”,意志堅決。他周遊列國,“累累如喪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講學,以禮樂文化為核心内容,推行“仁道”,正如曾子所説:“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犧牲奉獻精神 墨家以為萬民興利除害為自己使命,並為之孜孜奮鬥,遊説諸侯,謀求制止戰争,安定社會,“席不暖”“衣不黔”,“摩頂放踵”以利天下。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説:“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頁。並稱之為“中國的脊梁”。魯迅列舉的四類人中,至少有三類與墨家相符。
尚氣節精神 講求操守,保持人格尊嚴和民族尊嚴,是中華民族生存、繁衍、發展的内在生命源泉和動力。孔子提倡“殺身以成仁”,孟子主張“舍身以取義”,為了追求成仁、取義,不惜犧牲個人生命。這種精神熏陶感染了無數堅持真理,不怕犧牲的志士仁人。
仁愛精神 儒家講“仁政”,《孟子·盡心上》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要求人們從愛親人到愛百姓,然後將愛擴展至萬物。墨家講“兼愛”“非攻”“兼相愛,交相利”,視人如己,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富有同情心,悲憫情懷。
謙虚好學精神 重學習,重智慧,願意學,樂意學,善於學。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他“入太廟,每事問”,强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朱熹曰:“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静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説得去,也承載不住。”*黎靖德編、王星賢校點《朱子語類》卷八,中華書局1986年版。虚懷若谷,從善如流,博採衆家之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樂意承認别人的優點,不自滿,不自傲。謙虚不僅僅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學術精神。孔子看到知識對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論語·陽貨》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提倡勤奮、認真、嚴謹。
科學精神 墨家道、技統一,為天下興利除害。《墨經》中涉及數學、力學、光學、几何學等,又涉及邏輯學、生理學、心理學各個領域。講求實證,重事實,重歸納,《墨子·小取》“摹略萬物之然”,即反映事物本來面目,是對人類認知活動目的和宗旨的概括,實事求是。實證,即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如實認識事物本來面目,不附加以任何外來成分,不摻雜主觀、神秘或信仰因素。《墨子·非命上》中,墨子提出“立言三法”,即論證論點的三個標準:“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根據歷史事實;“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根據人民群衆的現實經驗;“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在應用中觀察符合人民利益的程度。墨子認為“察實”、“取實”重於“命名”,《墨子·非攻下》批評“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併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科學精神求真,重實驗,《孔子家語》中《困誓》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王國軒、王秀梅譯注《孔子家語》,第282頁。孔子注重親身經歷與體驗即實踐。《荀子·勸學》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儒效》曰:“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以致用,學習有不同的境界,聞、見、知層層遞進,但最高境界是“行”。嚴謹求真,朱熹强調“格物致知”,要在人世間與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窮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黎靖德編、王星賢校點《朱子語類》卷十五。反對照搬書本,主張獨立思考。
自由精神 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諸子各家各派盡量發表各自的見解,以平等資格相互辯論争鳴。不承認有所謂“一尊”,也没有“一尊”。各學派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紛紛著書立説,議論時事,闡述哲理,但是並非政治附庸,依附於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依傍,不苟且,不盲從,不迂腐,精神上獨立自由。
獨創精神 創立新義,諸子述道言治,自開户牖,不滿足,重原創性、學術個性,成一家之言。如老子貴柔,孔子貴仁,墨子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虚,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又如老子法自然,莊子法天,孟子事天,荀子參於天地。獨立思考,創造性探索。
争鳴精神 諸子百家相互辯駁,共同提高,在争鳴過程中進一步激發各家原創思維的生命力,使各種學説的獨特性得到了呈現。面對異己,確立自家學説,孟軻正是在與楊朱、墨子等人的思想交鋒過程中,才確立為子學的孟子;荀况是在與“十二子”的思想對話中才確立為子學的荀子。
叛逆精神 墨子初受孔子影響,“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逐漸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創建了與儒家相對立的墨家學派。東漢時代,儒家思想占支配地位,但與春秋、戰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説打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説,使儒學變成了“儒術”。王充《論衡》針對這種儒術和神秘主義的讖緯説進行批判,以“實”為根據,“疾虚妄”之言,《論衡·對作》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實之分”*王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頁。。《論衡》一書“詆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漢代儒家正統思想,故遭到當時以及後來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冷遇、攻擊和禁錮,將它視為“異書”。王充對正宗儒學的叛逆,是學術史上的一種寶貴精神。異端思想,解構正統、偶像和經典,以異端、另類的姿態反傳統、反正統,思想解放。
懷疑精神 不迷信權威,不迷信傳統,不迷信定論。宋代諸子“疑古”“疑經”。張載《大學·原下》曰:“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張載《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86頁。吕祖謙曰:“讀書無疑,但是不曾理會……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吕祖謙《吕東萊文集》卷二十《雜説》,《叢書集成初編》本。《朱子讀書法》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又曰:“書始漸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再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之後,疑漸讀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永瑢、紀昀等總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9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70頁。陸九淵曰:“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陸九淵《陸九淵集》,第449頁。陳獻章説:“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陳獻章《白沙子全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49頁。李贄《答僧心如》曰:“學者但恨不能疑耳,疑即無有不破者。”*李贄《焚書·續焚書》,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81頁。王夫之《詩廣傳》卷四曰:“由不疑至於疑,為學日長,由疑至於不疑,為學日固。疑者,非疑道也,疑言道者之不與道相當也。不疑者,非聞道在是而堅持之也,審之微、履之安,至於臨事而勿容再疑也。”*王夫之《詩廣傳》,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4頁。
批判精神 孟子批判“獨夫”暴君,荀子敢於非議前賢。《荀子·非十二子》不但非議墨家、道家、刑名之學,而且膽敢非議子思與孟子,斥之為“聞見雜博”“僻違無類”“幽隱無説”“閉約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他非十二子的主旨,就是因為其“學理”有不當之處,包括子思、孟子。荀子不是在故意標新立異,如《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説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就是恰當、適當,恰如其分,實事求是。批判精神是一種可貴的學術精神,没有這種精神,學術就不能發展,社會就不能進步。《非相》篇曰:“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特别强調人的吉凶禍福與相貌無關。唐甄《室語》曰:“治天下者唯君,亂天下者唯君。”“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唐甄《潛書》,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96頁。大膽批判。從某種程度上説,子學就是一種批評、批判的理論,而不是“頌贊”的理論。懷疑、批評、否定,不盲從,如果不敢懷疑,就不可能創新。
擔當精神 以天下安危為己任,就是對現實、社會、民族、國家有高度的責任感,有人間情懷,入世、濟世、救世,充滿現實關懷、當下關懷。歐陽發《先公事蹟》載,歐陽修説孔子作《春秋》,是“因亂世而立治法”*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附録卷二,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628頁。。《孟子·滕文公下》曰:“世道衰微,邪説暴行有作……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所謂“君人南面之術”,即治國之術,政治哲學。老、莊不是以德來治國,是以“道”,也就是自然而然地治國,以人的天性來治國,無為而治,“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羅義俊《老子譯注》,第133頁。,順應天道。莊子與老子一樣,主張無為治國,任其自然,認為“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同上書,第163頁。,君主要“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同上書,第125頁。。“無為”,看似消極,亦是在探尋社會矛盾的解決之道,以退為進,是在為解決社會矛盾開出一劑良方,“無為”不是“無用”。他們追求學問的目的,基本是為了應對現實社會提出的問題,為了探討家國天下的“經濟之道”。他們不做純而又純的學術,有强烈的憂患意識、責任意識、承擔意識、使命意識,關注世道治亂,以其所學影響君主,進而改造社會,是“入世之學”,是“經世致用”之學,道與術、學與術統一,不僅僅是“獨善其身”,更“兼濟天下”。這種擔當精神也是現在一些學者缺乏的,有一種觀念,只要把純而又純的學問做好了,外面的世界我是不管的,物欲横流,道德淪喪,民生疾苦,皆與我無關。佛教小乘佛是自我修煉,自我完善,大乘佛不僅拯救自己,更拯救他人,普度衆生,是一種大境界。
會通精神 《易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莊子·天下》《吕氏春秋·不二》直至《淮南子·要略》,都表達了這種追求,追求會通的多元性。《管子》内容博大精深,涵蓋了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教育、法律、倫理、軍事、自然科學等方面,書中所包含的思想流派涉及儒家、法家、道家、陰陽家、兵家、農家等。諸子百家有共用概念、範疇,“道”並不屬於道家的專利,先秦諸子對“道”的闡釋各有不同,但它作為反映事物發生和發展的依據或原則卻被共同確認,並成為學術最高範疇。“新子學”應注重宏觀研究、綜合研究、會通研究,而不能滿足於就老子論老子、就墨子論墨子。
開放精神 包容,開放,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内部各家之間,既相互争鳴又相互學習和借鑒。宋明理學吸取了佛、道兩家的某些思想和思維方式,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首要位置,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作了深入研究,構建了一整套具有嚴密思辨結構的思想體系,視野宏闊。陸象山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陸九淵《陸九淵集》,第483頁。譚嗣同《與唐紱丞書》曰:“何謂大義?明乎學術、治術之當然,合乎地球萬國之公理,可永遠行之而無弊。”“何謂公理,放之東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猶萬國公法,不知創於何人,而萬國遵而守之。”*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3~264頁。
和諧精神 老、莊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特别重視人與自己的和諧,即内在精神和諧,批評物質主義、機械文明的泛濫對人類和諧生活的破壞,是對人生終極意義的理性思考,是對幸福觀、快樂觀的理性理解。人生不能太“充實”,没有一點空白,太重功名利禄,太重物質金錢,那是人性的異化,是缺乏理性的偏激行為。
自省精神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斷反省自己,看到自己的短處,承認自己的局限,不斷調整自己、改變自己,提醒自己與時俱進。不斷吸收新知識、新思想,不拘泥舊學。
自律精神 約束自己,孔子認為“克己”是實行“忠恕之道”的先決條件,也是愛人的先決條件,要克制凡事專從自己利益出發的行為,而應該考慮别人的利益。只要嚴格遵循“禮”所規定的標準,約束自己的言行,使之一一合乎禮的規範,通過這樣,就可以達到“仁”最高的倫理道德境界。同時,孔子還把“克己”作為“復禮”的條件,《論語·顔淵》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還有如寬容精神,孔子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不專斷,不霸道。民主精神,《孟子·盡心下》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歷代以來,“子學精神”一直都鮮活地存在着,“新子學”的神聖學術使命,就是接續“子學精神”的“學脈”。“子學精神”對當下學術研究的啓示,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為了學問而學問。我們有義務和責任發揚光大“子學精神”,不斷開拓,不斷創新,不斷超越,尤其要超越自己。要做有思想的學問,有深度的學問,進入學術史的學問,傳世的學問,對當下、未來有益的學問,而不是視學術生産為一次性消費品。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當代也應該有屬於自己時代的諸子學,即“新子學”,要有大氣魄,創立學派,胸懷學術理想,追求真理。研究“子學精神”,對當下學者的人格建設,對學者學術精神的培養,對學界的學風建設,優化學術生態,皆極有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歐明俊(1962— ),男,安徽五河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古代散文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詞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理事、中國歐陽修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陸游研究會副會長等。著有《古代文體學思辨録》《詞學思辨録》《古代散文史論》《宋代文學四大家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