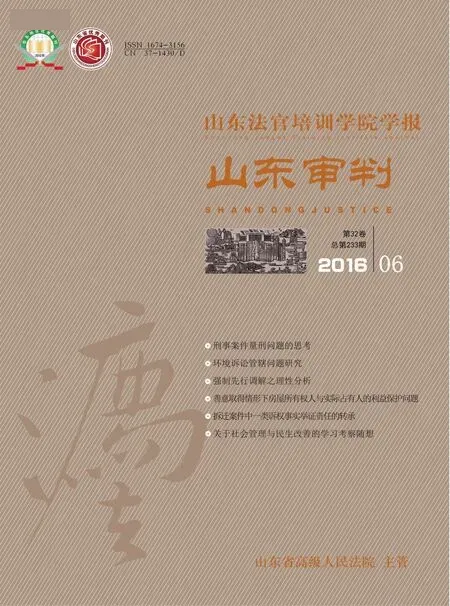拆迁案件中一类诉权事实举证责任的转承
——兼谈新《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的适用
●王鲲
拆迁案件中一类诉权事实举证责任的转承
——兼谈新《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的适用
●王鲲
证明责任乃诉讼之脊梁。①〔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举证责任的分配在任何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性都毋庸讳言。但部分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多以静态的眼光看待法律及司法解释中的举证责任规范,不能恰当地通过举证责任的合理转承确定案件事实,致使案件审理出现偏差。本文结合行政诉讼拆迁案件中一类诉权事实的证明,对其举证责任的转承进行探讨,提出:在正确理解原告对诉权事实举证责任性质的基础上,通过法官的证明评价让主观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转承,最终形成内心确信;在面对证明妨碍的特殊情形时,应当依据法律确立的证明责任规范将举证责任转承,克服案件审理中待证事实的真伪不明。
一、案例及问题的提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2010年2月12日D市人民政府下发《A决定》,将D开发区辖区内的4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列入市政府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十项民心工程。2010年12月14日D开发区管委会出台《B决定》,决定片区内住房及有关企业实施整体改造。2011年3月1日发布《拆迁公告》及《平房区、楼房区奖励政策》、《片区改造补偿安置方案》。2011年6月8日上午原告及其父亲、妻子被管委会的拆迁办工作人员分批带到拆迁指挥部,商谈安置补偿的相关事项。当天上午原告的房屋被拆除。原告程××向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判令被告将原告房屋恢复原状;赔偿经济损失每月1500元,自2011年6月8日致房屋恢复原状止。三、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办公、生活用品、工作学习资料(价值20万元)等,返还现金3万元。被告辩称,D开发区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合法有效,开发区拆迁办公室组织实施片区房屋征收程序合法有效。开发区管委会没有实施行政强拆。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1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若干解释》)第26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没有作出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决定或公告,原告所举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照片等又不能充分证实是被告实施了强制拆迁行为。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违法以及请求恢复房屋原状、赔偿经济损失、返还物品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故其请求不予支持。经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若干解释》第56条第(4)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程××的诉讼请求。
该案历经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上诉发回重审、重审再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再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当前进入申诉审查阶段。审理的曲折客观上表明了其中蕴藏法律问题的复杂。法院判决是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被告实施了行政强制行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②严格来讲,行政行为的存在与否属于程序性的诉权事实内容,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即使不符合起诉条件也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不是从实体上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因其并非本文关注重点,在此不予赘述。,因此,被诉的拆迁强制行为系被告所为这一要件举证责任的性质系属、分配及其法律后果成为本文讨论的核心焦点。
二、待证事实的类属及相应举证责任性质分析
(一)被诉的拆迁行为系被告所为,属于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诉权事实中的一项内容
所谓诉权事实,指的是能够证明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对于诉权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若干解释》第27条第(1)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证据规定》)第4条第1、3款(本文称之为诉权事实举证责任分配规范)专门作出了规定。按照上述规定,举证责任以原告承担为原则,被告承担为例外③参见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125页。。因此,尽管案例属于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但被诉的拆迁行政强制行为系被告所为这一行政行为存在与否的证实状况,仍旧是行政赔偿诉讼诉权事实部分的证明,按照上述规范分配举证责任,较按照《国家赔偿法》第1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若干解释》第27条第3项以及《证据规定》第5条(本文称之为赔偿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范)更具有规范的针对性。换言之,作为拆迁行政强制赔偿案件,即使案件整体适用赔偿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范来分配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但涉及被诉的拆迁行政强制行为系被告所为的诉权事实证明部分,应当优先适用诉权事实举证责任分配规范来进行原告、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
(二)诉权事实的举证责任,属于证明责任中的推进责任或者初步证明责任
所谓推进责任,系说服责任的对生概念,又称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并不必须证明其成立,而只须提供证据证明有成立的可能性,或者对对方的主张并不必须证明其不成立,而只须提供证据引起合理怀疑,证明其有不成立的可能性。如果对方无有力的证据予以反驳,无法合理地否定这种可能性时,则对方的主张不能成立。承担推进责任的当事人在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时,只需承担不能证明对方主张不成立的不利后果而不是败诉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大部分是推进责任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起诉是原告的权利,证明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也是原告的义务,但此种义务毕竟不同于《证据规定》第五条所规定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事实所承担的说服性义务⑤前引④。。这一点从《证据规定》第41条第1款的起草说明中可以证实:“该款规定的举证责任仅仅是原告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初步证明责任,而不是严格证明责任,审判实践中应当把握好‘初步证明责任’的度。”因此,尽管拆迁行政强制案件中原告承担证明行政行为存在的举证责任,但该诉权事实的举证责任并非严格的说服性证明责任,原告只需要举证证明被告有实施了强制行为的可能性即可,如果对方没有有力的证据予以反驳,无法合理地否定这种可能性时,不宜简单认定原告对诉权事实的举证不能。
(三)本文所述证明责任借鉴大陆法系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的分类
所谓主观证明责任,亦称提供证明责任、形式证明责任、诉讼上的证明责任或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哪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具体的要件事实举证,是指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责任,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败诉,因此它才是通常意义上的责任⑥前引①。。与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抽象而一般的实体法上的风险分配不同,举证责任是证明责任在程序法中的体现。而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中,依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举证阶段的不同以及法院对事实的评价不同,会出现一会儿是原告举证,一会儿轮到被告举证的情况,因此举证责任可以在同一个诉讼中多次被“轮换或者倒置”。显然,举证责任属于诉讼法的范畴⑦前引①。。尽管客观证明责任在证明法学中具有更重要的位置,鉴于其适用前提为争议事实的真伪不明,而我国诉讼法中普遍强调案件的审理以事实为依据,形式逻辑上两者的兼容性值得探讨;而且,我国行政实体法中并没有针对真伪不明状况设置证明责任规范,因此,本文对举证责任的探讨如果不作特别说明,主要是在主观证明责任的语境中展开。
三、举证责任分配的进路选择
(一)案例举证责任分配批判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文中案例。通过裁判文书所列各方证据可以看出,对于被告是否实施了强拆行为,原告其实已经竭尽所能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证据⑧从本文观点来看,原告所列证据从拆迁公告,被带走事实,证人证言、照片、视频,录音电话等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让法官形成房屋系被告组织拆迁这一事实的心证。。法院之所以没有支持原告的主张,如果不考虑案外干扰因素,很可能是没有将诉权事实与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将原告本应承担的推进性初步证明责任提高成了说服性责任,将《国家赔偿法》第15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所规定的举证责任视为结果意义上的客观性证明责任条款来适用,静态机械地看待法律及司法解释中的举证责任规范,认为原告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被诉行政行为系被告所为,从而作出了驳回判决。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原告在类似的拆迁行政强制案件中将很难有胜诉的可能。
(二)通过推定解决待证事实真伪不明
此类判决的存在,究其原因,是当前法律法规对此类情形下举证责任规定不够明晰确定。对于上述诉权事实的证明,有专家曾经根据分析预设的三种可能设置了解决方案:“一是原告能够证明拆除房屋时有被告工作人员在现场参与。二是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参与,亦无其他相关组织或者个人承认。三是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参与,但有其他相关组织或者个人承认。对第一种情形,应当认为可以证明被诉行为系被告所为。对第二种情形,可以推定被诉行为系被告所为。对第三种情形,不宜认为系被告所为。”⑨前引③,第126页。
应当说,以上解决方案更合乎公平正义原则。对于第一、第三种情形,尽管“原告能够证明”和“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承认”两种假定仍有判断裁量空间,毕竟条件所需的事实已经确定,在此不作讨论。对于第二种情形,也就是拆迁诉权事实真伪不明的状况,方案直接是以推定方式认定被诉拆迁行政强制行为系被告行政机关所为。对于推定,有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两种。鉴于“事实推定几乎总是改变了法律本身,这是不能容忍的。要么就是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被随意改变,要么就是证明尺度被降级。无论从方法角度还是法律角度看,这些做法都缺乏合法性”,而“毫无疑问,法律推定就是对证明责任的一种分配,亦即它属于证明责任规范。”⑩前引①。然而,法律推定系指某些法律规范中立法者以一定的事实(推定基础)直接推导出另外一个特定的法律要件(推定结果)。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无论是《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实体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没有解决方案中相关法律推定的规范。《证据规定》第69条虽是法律推定条款,但其适用条件为“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以上解决方案对此条件只字未提,难以推定就此而设。因此,实务中进行推定尚缺乏明确法律依据。
(三)通过主观证明责任的转承处理待证事实真伪不明
因此,对被告是否实施了强拆行为的证明,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缺乏客观证明责任条款,我们只能回到主观证明责任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来加以分析探讨。正如前文所述,主观证明责任随一方当事人举证程度的变化而可以数次反复,是一种动态的举证责任;同时,因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力的强弱而在当事人之间移位,是一种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互相转移的举证责任。那么在此类拆迁行政强制案件中,对被告是否实施了强拆行为的诉权事实的举证责任同样并不必然固守于原告。当原告按照证明责任的要求提供了一定证据后,法官对于事实已获得一定的事实信息,此时提供证据的责任应当转移至被告,当被告履行了反证意义上的提供证据责任,并使法官对原告的本证无法确信时,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告一方,如此反复来回,直到法官最终形成内心确信⑪参见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客观地说,通过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过程中当事人各方的积极举证,绝大多数案件事实问题能够得以解决。文中案例裁判者但凡有主观证明责任转移的意识,不机械僵化地拘泥于“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理念,在原告对相关诉权事实举证之后让被告对此提供一下反证证明,裁判结果很可能大不同。
(四)通过适用证明妨碍情形下举证结果责任的转承规则来克服待证事实真伪不明
当然,通过法官的证明评价来实现的主观证明责任的移转,并不能够使法官对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可以达到内心确信。上文案例中原告自行收集了部分证据提交法院,让法官能够推行主观证明责任的移转,拆迁中某些特殊情形下(比如无人围观的半夜强拆),因为被告的原因原告手中根本就没有留存任何证据,这些特殊状况的出现甚至根本阻却了上述举证责任移转的启动,比如证明责任理论中的证明妨碍情形。
1.证明妨碍理论的定义及性质。所谓证明妨碍,即“负证明负担的当事人的对方,如有因其有责任行为,导致原本可以为证据提出而发生提出不能情形时,将此举证不能的结果责任转由实施此有责任行为的一方,即负证明负担或举证负担的当事人的对方负担。简言之,遇有证明妨碍情形,证明负担应从原承担人转到实施妨碍举证行为的当事人承担。”⑫陈界融:《证据法:证明负担原理与法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以上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德国颇为流行,其中,证明负担转承说已经得到德国法院判例的肯定。本文籍以探讨拆迁行政强制案件中诉权事实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2.证明妨碍情形的构成。要考察当事人是否面临了证明妨碍行为,自然应当分析其是否符合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在法律上,一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分析,证明妨碍行为也不例外,也从行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两方面进行分析。证明妨碍行为的主观要件,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法律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态,由此决定行为人的行为应否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鉴于行政诉讼责任承担主体的特殊性以及国家赔偿制度较少考量行政主体的主观方面,本文重点探究证明妨碍的客观要件。
证明妨碍的客观要件,即证明妨碍行为的作为或不作为。无此作为或不作为行为,被妨碍的证据提出将成为可能,即该作为或不作为行为与该证据的提出与否,以及进而与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得不到证据证明有因果关系,而且,无论该行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所为,都不影响其证明妨碍行为的成立。一般包括以下几点:其一,须有证明妨碍行为。包括以自己的行为积极追求某一结果发生的作为,以及有制作或保管某一证据义务的一方消极地不作为致使证据不能提交的行为。其二,不负举证负担的当事人的行为,造成他方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负举证负担的当事人因对方的行为,造成自己举证行为比正常情形下没有该妨碍行为时,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不一定完成或卸除其举证负担,从而证明该有利于己的事实。其三,该证明妨碍行为与待证事实证明困难或不能证明之间具有因果关系⑬前引⑫,第206-210页。。
回到文中案例,原告自然无法留存拆迁房屋时的直接证据,被告行为已经构成了证明妨碍行为,而且此证明妨碍行为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此情形之下,基于被告实施的妨碍行为,原来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的举证负担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自然转承至被告,被告应当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实自己并未实施所诉拆迁行为,否则,即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是证明妨碍理论的客观要求。
3.证明妨碍理论的实务检讨及应用前景。一般认为,《证据规定》第69条“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的内容,系我国司法制度中对证明妨碍问题作出的具有“规范效力”的规定。应当注意,该条是以法律推定的形式对原告面临证明妨碍情形时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结果责任的证明责任规范。本文以为,以上规范内容对原告设置的条件相对苛刻,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较低。对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可以看出,平等当事人之间面临证明妨碍时只需要“有证据证明”即导致举证责任的转承,并且发生法律推定的证明责任规范的法律效果;行政诉讼中天然处于弱势,本应承担多为推进性初步证明责任的原告,在遭遇被告设置的证明妨碍时却必须“确有证据证明”,实在匪夷所思。这种立法疏漏直接导致了原告举证责任的过分加重,实务中法院极少援引上述规范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⑭截至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联合开发的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持系统——网络版涉及《证据规定》部分共收录生效裁判文书1706份,仅有一份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衡中法行终字第27号判决援引以上规范支持了原告诉请。,拆迁行政强制赔偿案件中上述规范的适用更是羚羊挂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文案例中的判决结果也是《证据规定》证明妨碍法则规定不完善的自然反应。司法实务呼唤更为公平更为严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关证据规则。
立法者及时察觉了既有证据规范中的不足:在已经公布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第38条第2款明文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该条文首先规定了原告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责任,继而表明,在出现证明妨碍的情形即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时,证明责任发生转承,由被告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只要原告能够提供其主张的受损财产存在的初步证据,被告就应当承担原告受损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反驳原告的主张,应当承担败诉责任。”⑮见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页。与现行的《证据规定》第69条相比,该条款不再强调让原告充分证明被告持有对己不利的证据,减轻了原告对于证明妨碍情形的举证责任,实质上也更为公平。此外,该条款虽看似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类案件当中,但因该法第三十八条系针对原告所负举证责任事项,而诉权类事实原本即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得以适用自是法律应有之义。参照以上条款,在类似文中拆迁行政强制案件中,要证明被诉行为系被告所为这样的诉权事实,原告只需要向法院举证说明存在证明妨碍情形,即其被带到拆迁办公室无法就房屋被拆迁再行举证的事实,举证责任就此依法转承至被告。此种情形下,被告如果不能积极举证证明自己没有组织强拆,就应当认定该诉权事实存在。
(作者单位: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校:山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