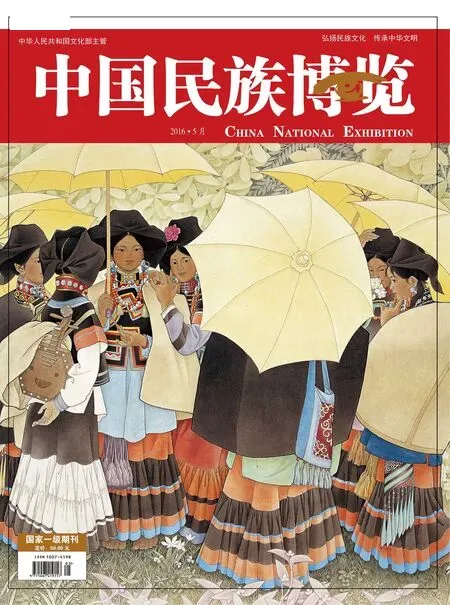一部音乐学著作
——读山口修的《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导论》有感
张珊珊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一部音乐学著作
——读山口修的《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导论》有感
张珊珊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江苏扬州225000)
【摘要】山口修先生在《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导论》一书中提出将“音乐学”代替“民族音乐学”。引起众多学者的思考与反思,同时也被认为是音乐学里面的精品佳作。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的,首先是作者将“音乐学”代替“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及定义;其次是对著作内容的理解和自身感悟的梳理;最后,是分析作者将“音乐学”代替“民族音乐学”的可能性,以及出现重视民族学而忽略音乐学的这种趋势发展。
【关键词】山口修;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定义
山口修,是大阪大学博士,1939年生,日本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他曾在夏威夷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巴拉拉·B·史密斯教授的推荐下,来到贝劳进行为期8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具山口修先生本人说:“在贝劳生活8个月的成果,决定了我作为音乐学者的人生道路。”此书成于他博士之时,是他对过去从事音乐研究的总结。这本书是山口修先生个人学术的里程碑和个人多年学术经验的总结结合,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版个人的著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界的经典之作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应用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田野采集者在数位时代中的责任:以帛琉1960年代的录音为例》。
在读过的文章及书籍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民族音乐学或者是人类学的内容,很少涉及到音乐学,单独拿出来讨论的更是少之又少。通读完全文后,内容感觉非常熟悉。因为和民族音乐学的定义、研究方法、资料搜集等都相似,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扩充了。这给读者一个新的视角和方向。对于山口修先生的这篇著作并没有太多的人去解读他,对此,相关资料在国内甚少。在这里面其实也是注重强调了作者对贝劳音乐长达八个月的田野调查,把音乐中的文化描述的淋漓尽致,可谓是一篇佳作。作者分别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去解析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山口修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整体,各民族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融合与交流,从而能够造就出一个五彩缤纷的多元化世界。山口修先生的这篇著作是按照先理论后田野的方式阐述的,这也使笔者想到自己,先有理论知识的积淀之后,再去进行反复的田野实践训练。最后,才能收获到喜悦。
一
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慢慢地被中国的音乐界所接受。正当民族音乐学迅速发展之际,山口修先生的《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以中文版的形式在中国开始发行。山口修先生在文章中最大的亮点则是:用“音乐学”取代“民族音乐学”。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对此,中国的学者、工作者们纷纷茫然。读完田耀农老师的“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兼评(日)山口修的新著《出自积淤的水中》”这篇文章了解到,对于这一名称的转变其实是对“民族音乐学”解构的一个宣言。
本篇著作主张将“音乐学”代替“民族音乐学”,在文中第四页给出了定义。这一定义原本是山口修先生1983年在日本的《音乐大事典》撰写“民族音乐学”条目时所下的定义。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又将这一定义移到了“音乐学”身上。
二
山口修先生强调从时间性上去考察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借鉴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二分法,分别以历时性与共时性为基准。所有的民族都应从修史和民族志两个方向去考察。作为文化的音乐,在音乐的研究中作者强调文化的四种属性:精神文化、身体文化、事象文化、物质文化。对于音乐学资料的收集,强调“文本”的重要性,呼吁要重视口头传承。把演奏作为一种资料,理解其中复杂的情形变化。在田野工作中,要有问题意识,注意研究者自身的身份,即主位与客位的关系转换和平衡,作者也提倡多重角度的理论思想,其中,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广为推崇。
在音乐学方法上,采用比较学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应用学的方法。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下属分支学科,民族音乐学最初是由音乐学的“比较音乐学”这一研究方法比较而成的。也就是大家所提到的民族音乐学的前身。这里的比较学方法强调要重视口头传承,而不是一味的书记性的记录。在比较学的方法中涉及到“中心和边缘”的问题,这也是平时我们在民族音乐学里经常提到的,主要是受到文化事项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关于“中心和边缘”这一话题,使更多的学者、研究者意识到,不仅要研究精英阶层的音乐,还要重视平民百姓的音乐。在这基础上还提出了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指从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寻找其比较参照物的研究方法。这也是现在很多民族音乐学家及人类学家广为提倡的,跨文化更多的是跨地域的比较,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有助于对异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透过对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变体进行比较可了解到文化变迁的过程与方式。
在历史学的方法中提到了一个“混沌性”,是时间上的除线条性和循环性以外的第三种概念。“混沌性”是包括了线条性、循环性及它们的螺旋性合成的暧昧模糊的概念。看似无序,实则有序。混合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在第二编中作者来到贝劳地区感觉到混沌的时空,该地区的人没有时间观念,只有今日和明日,加之刚到此处对该地区的陌生,在贝劳地区的所见所闻唤起了作者之前的经历,这可能就会有一种混沌之感。当了解到了今日和明日的故事和背后的意义时,作者便走出了混沌。
应用学方法:主要是将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付诸于应用领域。应用学方法一词主要来源于费勒厄的音乐体系中,将“生活中的音乐”和“音乐教育”置于重新设定的“应用音乐学”,它不同于前两种研究方法,主要是面向未来的发展。在文中还提到了德丸反对阿德勒二分法,他把音乐学分为体系、历史及行为,这里就是采用应用学的方法,应用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的是实验性的研究。应用学的方法在音乐学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归纳为三点:首先是对人的音乐性的关注,这里也囊括了布莱金的《人的音乐性》;其次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给予关注;文化接触所存在的问题。历史学方法侧重于研究过去的音乐,田野调查强调的是现在的音乐,而应用学的方法侧重的是未来的音乐。这也正好是作者在本书中的思想路线:即过去、现在和未来。
本篇著作的第二编“维系贝劳音乐的时空”中,山口修以贝劳音乐为基准,对贝劳音乐的时空观进行阐释,这里让我想到了赖斯的三维模式,即“时间、地点、隐喻”,赖斯的这一模式是在1987年提出的历史构建、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体验,这一基础上,于2003年提出的新的思考方法。可见,众多学者在这一段时间内对民族音乐学做出了很多成就,不断地涌现出很多新的思路。山口修在第四章中对大洋洲的贝劳进行了地理和历史的考察,以及在贝劳人的时间观念上作者是用了一章的篇幅去描述。从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模式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第三编中作者将视野扩展到了现代,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去探索贝劳的音乐,以及在最后一章作者抒发了对贝劳未来的展望。梅里亚姆认为,既然变化是人类经验中的永恒的因素,即使努力去推迟或阻止,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光是保存就不能成为民族音乐学唯一的目的,而应该在此同时去研究传统音乐的变化过程,研究其他因素、其他音乐对传统的影响和由此产生的效应。自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学者们开始不再局限于对传统音乐的静态研究,二是努力的去把握其动态的发展过程。这变化成为50年代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特征。这一表现在文中的第八章、第九章进行了详尽的分述。
三
作者之所以将“音乐学”取代“民族音乐学”的原因,透过田耀农的“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兼评(日)山口修的新著《出自积淤的水中》”的这篇文章,发现20世纪民族乐派的作品在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上逐渐减弱,作曲家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本身更加感兴趣,不再满足于对民族音乐学家的材料记录和描述,而是要亲耳聆听到音乐及音响材料。到20世纪后期,作曲家与民族音乐学家的距离更加拉开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到重视。可见,作曲家与民族音乐学家处于分裂状态,那么21世纪的民族音乐学家可能将更加重视民族音乐的问题。“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有可能向“民族学”靠拢,从而疏远了“音乐学”,可以看出山口修先生这一提法是对民族音乐学的重构的过程,也警醒着众多的学者以深刻的思考。
四、结语
山口修的《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这篇著作,可谓是音乐学中的精品佳作,里面涵盖的内容和知识容量非常之广。作者将“音乐学”代替“民族音乐学”这一新的视角提出后。迄今为止,这一提法并没有普遍的运用开来。虽然著作里面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缺少本体性的分析。但山口修先生对民族音乐学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的,山口修对贝劳民族志的描写为作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写作范式。山口修先生最大的贡献之处是将这些民族志材料奉献给了社会,为众多学者所分享。
参考文献:
[1]山口修著,纪太平,朱家骏译.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M].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
[2]田耀农.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兼评(日)山口修的新著《出自积淤的水中》[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及表演版),2003.
[3]山口修著,纪太平,朱家骏译.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M].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2.
[4]田耀农.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兼评(日)山口修的新著《出自积淤的水中》[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及表演版),2003.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