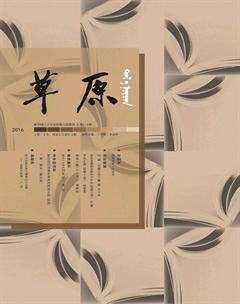峡谷,风经过的地方
宋方童
峡谷,风经过的地方
宋方童
大瓦山
英国人欧内斯特·威尔逊带着他的向导和几只猎狗出现在丛林里的时候,是1903年的7月。这个初夏,大瓦山的雾气被阳光蒸发后,形成了大片大片的露水,它们停留在肆意丛生的矮小的杜鹃灌木林上,在空寂的世界里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杜鹃林下,腐烂的银杉树干上,长满了一层层的苔藓,似乎要把整座丛林都覆盖到脚底下。威尔逊的眼睛像被雨水淋湿了一样,显得雾气蒙蒙,他极力透过被树木遮挡的阳光,打量眼前从所未见的各种颜色各种姿态的杜鹃,此刻,它们像一张张少女的脸,让丛林变得柔和有趣起来。
在地图上,大瓦山连一个像样的点或者线条也没有,平均3 236米的海拔在蓝天的遮蔽下,早已被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深深的隐藏。在1903年这个露水深重的季节,威尔逊的闯入如同丛林里飞过了一只迷途的鸟。对于丛林来说,它的出现稀疏平常,细微得犹如一粒尘埃。但对于这只鸟来说,激起的内心震撼却绝非用语言所能形容。威尔逊的职业特性使其在对成千上万种植物迷津般的追寻中,已经迅速嬗变成一名探险家。在经历了蚂蟥与各种昆虫和爬行动物的困扰之后,这名年轻的英国人看到了藏在深山腹地里的人间天堂。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探险潮流,并没有在清朝末期的封闭制度下合上大门,在死寂没落的国度里,穿梭着西方人身着奇装异服的身影。他们的相机,这个西方新兴文明产生的奇异装备,为我们封建王朝的最后背影留下了难得的回忆面容。在威尔逊的黑白影像里,大瓦山和今天呈现在彩色相机里的形态并无二致,山体的轮廓和植被的丰满,峡谷的深邃与溪流的迂回,都能在今天的大瓦山寻找到佐证的对象。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处在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恒温中,连四季都显得那么不突出,雨水成为白天和夜晚的行者,在树林中寻找自己的栖息地。与这个世界平行的,只有天空,在夜晚之后,它的明亮会重新眷顾这个被人遗忘的大地。
英国人的中国西部之行其实怀揣着另一个野心,寻找一种绝大部分分布在喜马拉雅以及我国西南部的叫绿绒蒿的植物。这种与罂粟同归于罂粟科的植物,不像其属性名字那样暗藏杀机,它外表柔弱,在高山、草甸等苦寒地带忘我地繁衍生殖。它的果实上长满了细细的茸毛,如同凤仙花。在大瓦山,威尔逊暂时忘记了那种看上去孱弱但却坚韧无比,拥有蓝、青蓝、淡黄,或者红等颜色的罂粟科植物。在瓦山的丛林世界里,杜鹃被雨水浸润后饱满的花朵深深刺激了这个年轻植物学家的眼睛,他只能透过远山的薄雾,以及层叠的冷杉林,才能参照出这并不是一个幻境。
在此后的《瓦山与瓦山的植物》里,威尔逊几乎调动了全身的文学细胞,还原大瓦山的记忆。然而,他最生动的描述还是那些朴素的文字记录,植物的分布、瓦山顶的形状、空地上生长着的秋牡丹和樱草,以及那些铺天盖地的杜鹃,远远比他夸张地形容瓦山是一座“世间最具魔力的天然公园”更为令人信服。威尔逊的收获是采集了16个杜鹃树种,以及一些稀少的植物类群。
下山的途中,探险者真正的险情才开始降临。来时的山路像一把形状怪异,棱角分明的旋梯,它们隐藏在各种植物的缝隙里,或者干脆露出灰白的骨头,到处是尖锐的锋芒。而山路之下,则是万丈深渊,被浓重的雾气所笼罩。猎狗开始发出恐怖的声音,并不停地向后躲闪。这声音让探险者感到不安,预感到一股不祥之气迎面扑来。
在狗被蒙上眼睛之后,它才和它的主人开始真正安静下来。在他们孤独渺小的身后,是巨大的群山,此刻,它异常宁静,它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肤色洁白的年轻人,会在1908年的夏天再一次对它进行了探访。
绿绒蒿的发现之地距离瓦山并不遥远,在康定的一座高山上,英国人威尔逊见到梦中的绿绒蒿,它黄色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犹如美丽的少女扬起的裙裾,简直和梦中的一样。
峭壁
在大峡谷的峭壁上,那种蓝色的成片的小花朵曾经一度让敏感的我误以为就是绿绒蒿。在我真正抵达峡谷腹心的时候,我看到了它的身体,相互缠绕,藤状的躯干击碎了我有关绿绒蒿的猜测。
在这个全部由古生代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和白云岩组成的世界里,石头既是骨骼又是身体。它仿佛被什么利器中伤过,裸露出它的全部不幸。在植被丰满的四川盆地,金口大峡谷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姿态,它衣不裹体,即使长着植物,也是那种独立的树种,它们并不完全交融在一起,形成山体的天然屏障。对于峭壁,岩石就是屏障,谁都无法剥夺它的任何权利,除了风和时间。它们几乎挡住了外面的阳光,只剩下天空,让深处其间的人感到时光的不可捉摸。
玄武岩和白云岩是时间的遗留物,和生长于遥远世界里的桫椤并不一样,它们表情凝重,让人心生畏惧。这样的面容与表情与出生有关,在人类无法想象,甚至无法通过科技还原于影像的地球裂变中,它们经历了火与燃烧。在这样的石头面前,人的心灵不堪一击,峡谷的峭壁向我们述说了一个存在的基本事实,世界的永恒只有在内心才可以假定,我们无从改变天意。
在不曾真正目睹过大峡谷之前,《中国地理杂志》所刊登的巨大篇幅的大峡谷让我联想到人类在本世纪给它加冕的“中国最美丽的十大峡谷”。这种浮于表面的美丽在插图上表现的仅仅是虚无的区别于一般的形体之美而已,在汽车带我穿越这段并不算太长的隘谷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压抑,那种在重力之下丧失了步履的轻飘。我无从理解内心的这种变化,而所能感知的便是,自然是世界与万物的母体,任何的轻蔑和藐视,将会遭致一记响亮的耳光。
大渡河在峡谷中浪急滔天,抵达这段流域是9月末的某个下午。在金口河通往乌斯河的公路上,大渡河和道路夹在峡谷中,这时候,连天空都为峡谷所主宰。河水在宽阔的河床里肆意涌动,发出这个峡谷里唯一也是最大的声音。河水也只有在这样的河床里才能拥有如洪钟般的声音,与峡谷的巨石所匹配,成为这个世界的勇者。
公路此刻成为峡谷的观景台,它消解了人类期望借助它收取门票的野心。在这条赤裸的路上,峡谷的岩石既在向人类昭示着它绝缘的一面,也暗藏着亲近的温情。
文字工作者们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叫作白熊沟的地方,却并未道出它的险境。我们在阳光中迎来的那个下午,当汽车的灰尘从道路上消失之后,白熊沟出现了。它就在公路的一边,当阳光从山的一角倾泻下来的时候,金子一样的光芒将白云岩的山体笼罩得像佛经里的极乐世界。人们忙着照相取景,那些山的形状,以及身处隘谷心中升起的巨大的欢乐,让我们忘乎所以。
一块跌落的石头溅落在附近的一个石谷里,发出叮当的一声闷响。我只能形容这个声音,在清脆中含着一股沉闷,在只剩下我们的声音里,连风经过都是无声无息的。这块跌落的石头不明方向,但是却像一把没有刀刃的利剑,穿过我们的身体时,产生了一种恐怖的疼痛。一块石头跌落后,紧接着,就是第二块,第三块,它们从我们头顶迅疾地跌落下来,在石谷里激荡起响亮的声音。其中的一块石头,从我们很多人眼前滑过,也从一名正在摄影的本地向导的脸前滑过,它的体积,有一个小南瓜大小。
我们开始逃难般的纷纷躲闪那些骤然降落的石头,此时,出口近在咫尺,却感觉远在天边。
重新回到金乌公路上。午后的阳光已经把九月的大地炙烤得滚烫,到汉源的汽车绝尘而过,把沙砾重重地打在我们每一个人脸上。威尔逊经历过的大瓦山从白熊沟翻越,亦可抵达。站在白熊沟脚底下,失望和午后的天气消磨着我的信心,越过高大矗立到天际的白熊沟山顶,我甚至听不到一点来自大瓦山清脆的鸟鸣,丛林中露水的湿润,或许正在午后渐渐蒸腾消失。
永和
时常在梦境与黑暗中穿越一座座大山,以及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洞口。在我的20岁,火车成为我走向远方的唯一交通工具。在黑暗中穿越的大山,在我返回时,终于得见真相。秋天中的茅草,飘扬在寂静的山崖上,干涸的黄土中,生长着我所喜欢的一种植物——土豆。
这样的场景在我深入峡谷腹地那个叫永和小乡村的地方得到了重现。
在中国地图上,永和镇这样的名字不断重复,多得不胜枚举,但是每一个地方,却有着绝不重复的属性和气息。一年前,我收到一斤来自永和的花椒,馈赠的主人是金口河电视台的彝族女孩邹燕。作为友谊的见证者,这包永和花椒一直保持着不灭的味道。它被盛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玻璃瓶里,一年后,当我亲手打开瓶盖时,一股扑面的呛人的味道跟我收到它时惊人一致,散发出永和大地的气息。
从远方打量,峡谷无路可走,哪怕是现代攀岩运动也会遭遇抵制。事实是,峡谷充满了人烟味,当我深入它的体内,尤其是在永和这个地方,我体会到了乡村的温暖,被秋天扬起的手掌轻轻贴了上来。在一条可通汽车的水泥路边上,我发现好几株花椒树,可能已经被采摘过,枝条上残留着不多的几株青绿色的藤椒。永和的产椒量并不喜人,每年只有500斤,这个产量体现的是其中的含金量。在茫茫的大山里,只有它们散发出不一样的味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烟火之味,带着古生代大地的远古气息。
在半山上,成昆线的铁轨在我视野里缩略变小,一列开往云南的火车呼啸而过。火车的经历,与大地息息相关,这个庞大沉重的家伙,必须将整个身体交付给大地,才能奔跑和喊叫。火车的穿越,注定了人类要为自己的远行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不只一次从对岸遥望那些远行的火车,在我童年的故乡,对岸的火车实际上是拉煤的小型煤车,除了没有顶棚,它们长长的身体和喘息的姿态和火车一样。这些黑色的家伙,穿过铅灰色天空下的大地,然后消失在半山,隐入我所不知道的山洞中。
永和镇已经开始变得更像某个城市的边缘乡村,既不显得特别繁华,但至少也不落寞。秋天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翻修新房的乡民,被农用车从山下拉上山的红砖,在道路上散落一地,粗壮的房梁,裸露着刚刚砍伐时新鲜的表皮,它们已经被支撑起来,成为永和人崭新家园的脊梁。火车到来以后,永和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它的时钟不再那么缓慢缺乏现代社会的秩序。人们从山上搬迁到山腰上,在火车通行的上方,亲身体验呼啸而过的生活。
永和镇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作为成昆线上一段浸润血迹几乎最多的地方,它成了人类祭奠那段历史的凭证。在山中一块平整的空地上,人们修建了中国铁道兵博物馆,在这个山风往来之地,博物馆的外貌更像是一墩伟岸的石头,它安详地静立在此,只有来人穿透它的内心,才会觉察到隐秘的疼痛。
在永和镇,穿梭着如我这样的旅行或者采风者。被峡谷遮挡的天空,令我们失去方向感,此时,只能凭借阳光的方向,寻找时间的指针。永和的真正道路,不是来自水泥的混合物,而是高山峭壁间,隐藏在草丛中的羊肠小道。直到今天,哪怕有火车开了进来,依然有乡民们居住于陡峭的高山上,它们犹如群山的吊脚楼,居于岩石,这种世界上极坚硬的物体上,终年享受峡谷山风的吹拂。在金口河境内,只要行走于宽阔的公路,大山就会向你呈现这样的奇迹,再险峻的岩壁上,总有人类的烟火,你以为视线难以企及的地方,就是生命的盲点。人类的可敬之处正是基于如苇草一样的生命史,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只有身处逆境,才能证实某种力量的真实存在。
即便花再大的力气,试图再现与还原历史,历史也不会撕开自己血淋淋的伤口给无关者看。所以,在永和镇的这座高山上,风光和喧哗的人类活动已经将某段历史隐去了,火车在铁轨上从这个起点到达那个终点,再由重新的起点回来,它的道路,仿佛与生俱来。而人类,这个火车与铁轨的制造者,并不仅仅满足脚下的道路。新的路径正在展开,它们与坚硬的岩石无关。
(责任编辑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