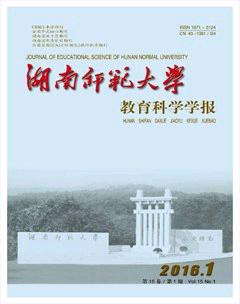人文教育的核心素养是文武双全
刘良华+冯嘉慧
人文教育是文武双全、能文能武的教育。现代教育却单向度地鼓励文明与文静,这是一种教育制度的堕落。现代教育普遍重视知识学习,现代考试制度加速了对知识学习的重视。把教育简单地等同于知识教育的危险和危机不只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分低能的人,更严重的后果是,现代教育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软弱无力的文明人或文明的“末人”(the last man)。
一、文明的进步与极限
文明当然是一种教育的重要项目,但是,如果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把文明视为教育的唯一目标,这个民族或国家迟早会受到“自然意图”的惩罚:文明的民族总是被野蛮的民族征服,而且,野蛮的民族获得统治权之后,也同样会因为贪图安逸享受而走向衰落和衰败。
如果说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压制了民众的活力,那么,此前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住中原,几乎与制度无关。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没有实行所谓的“民主政治”。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主要的原因只在于,当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接近卢梭的“自然人”。历史学家曾经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过着“自然生活” [1 ]。这种自然生活成全了他们的“高贵的野蛮人”的精神状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 [2 ]
蒙古人成吉思汗当初入主中原后,认识到舒适的生活对尚武气质是一种损害,对舒适的生活一直持警惕的态度。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他们很快就发现,舒适的生活使他们身上的“勇武”精神出现消退的征兆。皇太极制定了著名的“清语骑射”的国策:“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严禁奢侈”,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
但是,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任何人都贪恋舒适安逸。蒙古人以及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一旦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他们就再也不愿意返回风餐露宿的原始状态。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时,随即开始堕落。“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 [2 ]最终逃脱不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历史的狡黠。
二、主奴辩证法与尚武精神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为承认而斗争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黑格尔将他的承认理论称为“主奴辩证法”。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以“自我意识”为前提:承认就是一个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相遇和相争。每个人都确信自己是“自为存在”,但“它们必定要参加这一场生死的斗争”,并通过生死之争才能使一方获得另一方的“承认”(最后走向“相互承认”)。正是这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运动,推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3 ]。
最初,承认总是单向的承认。主人是对奴隶的征服,奴隶的失败成全了主人的胜利。那个能够彻底满足自己“虚荣”的人,就是那个不畏死的人。“只有通过冒生命的危险”才有可能成为主人。“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同样每一方必定致对方于死命,正因他自己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不复把对方看成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对方的本质在他看来乃是一个他物,外在于他自身,它必定要扬弃他的外在存在。对方是一个极其麻烦的、存在着的意识,他必须把他的外在存在看成纯粹的自我存在或绝对的否定。” [3 ]
可是,问题是主奴辩证法的“狡计”就在于:历史的发展将出现颠倒:主人必败,奴隶必胜 [4 ]。原因在于,主人虽然获得了对奴隶的统治,满足了被奴隶承认的虚荣并获得了不劳而获的享乐的权力。但是,主人的不劳而获的享乐也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他失去了与物的直接联系,主人与物的中间横亘着奴隶并因此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 [3 ]
主人之所以成为主人,就因为他不怕死,并因此而可以不劳动。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也因为他怕死,并因此而必须劳动。正是因为主人的无忧无虑和不劳动而使自己逐步走向堕落和衰败。相反,正是奴隶的恐惧以及他所必须承担的劳动,反过来却成全了奴隶的逐渐的强大和最后的解放。
奴隶逐渐强大的第一个原因是奴隶对死亡的恐惧、对主人的恐惧以及相关的“苦恼意识”而带来了坚实的屈辱感、焦虑感和存在感。“死的恐惧在他的经验中曾经浸透进他的内在灵魂,曾经震撼过他整个躯体,并且一切固定规章命令都使得他发抖。” [3 ]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奴隶获得了自我意识和存在感。恐惧是智慧的开始。
奴隶逐渐强大的第二个原因是奴隶的劳动带来了强健的身体和精神。主人的不劳而获虽然是一种享受,但它是消费和消耗性的,它转瞬即逝,缺乏“持久的实质的一面”。相反,奴隶的劳动使奴隶找回了他的自我意识。劳动不仅“陶冶事物”,而且给人带来独立性,“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奴隶在对主人的恐惧中丢失了自己,而通过自己的劳动“再重新发现自己”。奴隶的劳动过程,就是一个改造外物、摧毁异己者并因此而成为一个否定者的过程。“在持久的状态下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由此他自己本身便成为一个自为存在着的东西。” [3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再被看成圣经中对亚当的诅咒,而是被看做历史形成或进步的基础” [5 ]。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虽然每个人都为承认而斗争并在殊死搏斗的主奴之争中一决高下,但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暂时的,时间将取消和改变人的主奴身份 [4 ]。最初,主人自己为自己争取了主人的身份,因为主人愿意冒生命危险而坚持斗争到底,随时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奴隶怕死,自愿服从和承认主人。但是,在接下来的交往过程中,主奴关系必发生改变,因为,主人通过斗争而获得承认之后,他就闲下来,不劳而获;而奴隶在主人的命令下不得不劳动。表面看来,奴隶的劳动显示了奴隶的身份的低微。实际上,正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奴隶迟早会成为新主人。不仅因为劳动具有“培养和教育”的力量,而且因为不劳动必导致身体的衰败和精神的萎缩。endprint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已经预演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准确的说法是“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两个观念。
三、新时代的尚武精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既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 Fourier,1772—1837)、欧文(R. Owen,1771—1858)等人的启发,也来自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改造。
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借鉴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路:“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6 ]
但是,相比之下,马克思更看重黑格尔的“主奴之争”中所隐含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积极因素。正是从黑格尔的“主奴之争”中,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从欧文等人那里接受的启发是“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那么,马克思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那里接受的启发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前者把教育当做改进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手段,它把教育当做劳动者的福利(尤其是童工的福利),它关注的重点是教育;而后者却更看重劳动本身所蕴含的解放人的力量,它把劳动当做受教育者的福利,它关注的重点是劳动本身。鉴于劳动者已经失去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力,马克思主张必须采取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以便重新赢得人的劳动权力。只有赢得了自由劳动的权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自由的本质并不需要教室里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因为,自由劳动本身就是最佳的自由教育,只有自由劳动才能给人带来解放并显示人的自由本质。
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是一种无休止的战争,任何主人都不会长久。按照黑格尔的思路,主人凭借自己的奋斗(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形式的劳动)而使自己成为主人,使某些他人成为自己的奴隶。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主人表面上享受了奴隶的服务,事实上,主人反过来又会受到奴隶的控制。更严重的问题是,长期的“不劳而获”将使主人的身体和智力都渐趋衰落,而长期的劳动将使奴隶的身体和智力渐趋发达。主人表面上摆脱了繁重的劳动而获得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事实上,主人必然会走向全面衰落,因为主人不劳动。真正能够全面发展的是奴隶,因为奴隶总是让自己处于劳动状态之中(暂不讨论机器大工业的劳动是如何导致人片面发展的)。这种力量的变化迟早会导致奴隶革命的发生,迟早会导致主奴换位。
正因为如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显得至关重要,它是克服无休止的主奴之争以及劳动异化的唯一道路。也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劳动者,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赢得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成为相互承认的平等的人。否则,如果无产阶级赢得解放之后使自己成为不劳而获的人,迫使资产阶级反过来接受惩罚性劳动或成为奴隶,那么,这种暂时的胜利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主奴之争。
马克思的思路是:人将借助科学技术而彻底摆脱繁杂劳动的束缚。科学技术的最高形态是自动化机器,自动化机器将全面接管人类的劳动。如果将来有了更多的自动化的机器人,那么,人类的很多繁杂的劳动就可以由机器人来代替,那时,人类就有了新式的“亚里士多德的奴隶”。人类就可以由此而获得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精力。亚里士多德倡导“自由教育”时,他的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而他的“自由人”之所以能够拥有闲暇,那是因为古希腊社会中有大量的奴隶的帮助和支持。“自由人”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的存在,他们才有接受自由教育(或闲暇教育、博雅教育)的条件。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预演了马克思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
取消了奴隶制之后,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持条件,所有人就不得不从事繁杂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甚至不得不陷入劳动分工的困境之中而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或畸形发展。为此,马克思对“自动化机器”寄予厚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描述自动化机器的具体形态,但现代“机器人”的诞生,使马克思的及其机器自动化的想象和预言有了现实的可能。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1.
[2]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历程[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0,160.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 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24-125,126,128,130.131.
[4][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91,31.
[5][美]斯密什.阅读施特劳斯[M].高艳芳,高 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18-219.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