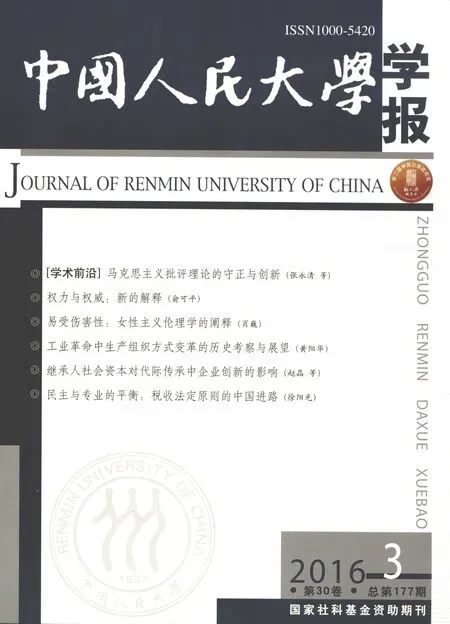城镇化的古典模式与新古典模式
吴 垠
城镇化的古典模式与新古典模式
吴 垠
城镇化发展的古典模式和新古典模式在短期内很难鉴别其各自优劣,需要从历史长程意义上加以比较分析。以宗教、安全、商业而兴起的“古典城镇模式”,虽然其生产力水平无法企及工业时代开启的“新古典城镇化模式”,但它们在历史上的发展经验需要今天的城镇加以沉淀;而“新古典城镇”的工业化内生、快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历史所赋予其任务的衰落期,其发展史、城镇病史也尤其值得当今在建中的工业城镇所警惕。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与书写中国特色的城镇史,需要我们以城镇化的古典和新古典发展模式作为镜鉴,重新定位各类中国城镇的发展轨迹。
城镇化;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关注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历史传承,“要从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看清,而需要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1](P307)。引述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以下即将展开的城镇化的模式分析作一楔子。西方国家城镇化经历了古典时代的荣光,也产生过新古典时代的机器轰鸣。城镇化从古典模式到新古典模式的转变,不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它穿过了不少“尘埃、泥泞、沼泽、丛林”。相对而言,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不只是今时今日之城镇建设规划所能概括,它本身植根于中外城镇化建设的历史传承之中。今日之城镇化建设,既不能脱离历史上一贯的、具有古典或新古典特征的城镇化模式,又必须在其之上发掘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模式和新政策。
一、古典城镇化模式的历史沿革
从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演变,“瞻前”即回顾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历史上曾经诞生过各种各样的城镇模式,有的城镇在历史长河中顺利地保存下来,其城镇文化、建筑特色、区域规划基本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巧妙结合;而有的城镇则是“昙花一现”,只在文字记录和地理位置上残存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但逝去的城镇,未必都是在发展道路或规划理念上出了问题;保留至今的传统城镇,也不见得全都是经典犹存。
对此,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起点是从固定区域的狩猎、畜牧、农业活动开始的人类活动区域,表现为简单分工条件下的初级城镇,而成熟阶段则是以商业、安全著称于世的那些古典名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把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的城镇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认为它具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函数功能,并能通过不同的城镇模式聚集或分散经济发展的各项要素,分工的精细化和生产聚集性是新古典时代城镇模式的“生产力”特征。但是,城镇化的模式,不仅仅只是经济学视角下分工、生产、要素配置等“纯经济学”话题,还包括宗教、文化、生产关系、生态系统等更深层次的城镇“境界”问题。本文所要挖掘的是历史上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其发展、凝聚、传承的城镇化思路迄今也有重要的价值。
对于古典城镇化模式的探索,乔尔·科特金在其重要著作《全球城市史》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历史名城进行分类的口径:即历史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他把这三者高度概括为神圣、安全、繁忙三个词。[2](译者序P2)按照这一划分口径,作为古典城镇化代表的那些历史名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特征呢?
(一)以宗教聚拢人气的“神圣”之域
1.宗教设施的作用
古典城镇模式的特征之一,是以精神支柱维系的,把道德操守与市民属性认同作为聚拢人气手段的传统名城。[3](译者序P2)宗教选择城镇兴起的地点往往为“神圣之地”,如历史上的巴比伦、雅典、底比斯、特诺奇蒂特兰等。但实际发挥城镇聚集功能的,却是宗教设施,如庙堂、教堂、清真寺和金字塔等,这些宗教建筑长期以来支配着古典大型城镇的景观轮廓与形象。它向人们宣示,这些城镇也是神圣之地,与直接掌握这个世界命运的神级之力相连。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名城多数选择以宗教兴城镇而不是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建设?换言之,支配早期城镇生产力的主要动力源自哪里?
蔡尔德和尼森指出,纵然是像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那样丰饶的环境,早期城镇的建造者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矿产资源短缺、建筑用料缺乏、雨量稀少,等等。[4](P4)归根结蒂,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人们不得不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对抗自然条件对城镇建设的限制,而在城镇化起步时维系这种集体行动的力量,只能是宗教信仰下的“道德与社会秩序”。最早的城、市、镇即是在宗教及宗教设施的载体之下逐渐兴起的,宗教成为这一时期城镇生产力的主要掌控者,各种城镇设施在满足生产、消费等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宗教图腾的作用,让人们对它产生敬畏。
2.宗教推动古典城镇形成规模的运行体制
(1)城镇秩序的形成有赖于宗教组织者的精心谋划。宗教祭司阶层是古典城邦时代城镇秩序的主要组织者[5](P5),其城镇建设职责和宗教秩序的安排是同时兼顾的,这就要求他们不仅是神职人员规范人们的言行,更要是合格的城镇规划者,合理安排城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布局。他们通过阐释人高于自然的神圣法则,完善礼拜体系,在复杂的大型公共活动中规范很多看似无关的人们的活动,并使宗教在城镇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扮演核心角色。[6](P5)
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7](P16)在古典城镇体制初创之时,人们汇聚于城镇,若没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及制约,在劳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环境里,城镇经济社会的运行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混乱。在这一时期,“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8](P16),并进而演化为以宗教信仰的形式来调解这种不同血族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有助于集中当时有限的生产力来建设、发展城镇。这个过程中诞生了许多在今天看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古典城镇建筑(群),其中一些经典建筑见证、贯穿了几千年的城镇发展历史。这对今天依靠各级政府和企业投资完成的城镇化建设模式有很重要的启迪意义——城镇的一些主要建筑是需要赋予其精神实质的,这样有利于形成整个社会的合力。当今中国各地的主要代表性建筑,“高、大、上”的建筑并不少见,但是真正具有中华民族或各地地域特色和精神象征的建筑,很多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修建的,有些甚至在经历过“特定年代”的破坏后,如今还要花费巨资予以保护(重修),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2)古典城镇运作体系的商业基础是从服务宗教活动起步的。古典城镇模式的发展离不开城镇商业的繁荣。但在海外贸易和交通通信手段尚欠发达的古典城镇的初创时期,城镇商业发展是从服务于宗教体制起步的。除奴隶之外,普通手工业者和熟练工匠也参与到宏大的建筑群建设之中,这给古典城镇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同时,早期的宗教设施,如神庙等也在非祭司时期起到了“购物中心”、“社交中心”的作用[9](P7),“它为各种各样的货物和人群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交易场所,从植物油、动物油脂、芦苇到沥青、席子和石料”等,这相当于早期的“市”;另外,神庙还拥有自己的工场加工衣物和器皿[10](P7),这相当于早期的城镇手工业。这些活动间接地促成了城镇分工的深化。
(3)古典城镇运作的文化体系源自宗教崇拜。早期的古典城镇几乎都是由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演变而来的。因此,其城镇的文化也由此逐渐兴盛。一是城镇的建筑规划文化。初创时期的古典城镇,其建筑格局总是让宗教仪式标志性建筑作为城镇中心之一,其他的手工业作坊、商市等围绕其渐次展开。到了各国封建王朝发展的成熟时期,不少城镇的中心都有用于宗教活动的广场、剧院、神庙,其他大型公共工程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围绕这些中心扩建。典型的例子是古罗马。它“把城市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罗马修建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道路、引水渠、排水系统,以使城市有能力承受不断增长的人口”[11](P52),这些公共工程,几乎都指向奥古斯都广场上宏伟的神庙建筑。而近现代能看到的代表性例子则是巴黎和北京,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和长安街的建筑布局,真正体现了城镇建筑文化的传承。二是城镇的人文文化。宗教体制对城镇文明的推动,使得大量不同背景的人口汇聚于像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大城镇,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共同生活,文化冲击与交融不断进行,一个属于古典“神圣”城镇时代的城镇文化由此诞生。
3.古典宗教城镇模式之得失评价
宗教型古典城镇模式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与依托需要宗教与城镇相结合。宗教既起到了调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们对宗教的虔诚自律不断改善着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城镇生产力。“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更高超、更恒久、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威力,因此它们能把许多家族或氏族团体的人群在不同季节里吸引回来”[12](P9)。宗教城镇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以宗教势力凝聚人气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在封建时代开启后,影响逐渐式微。除了封建皇权更加强调城镇文明服务于皇权,导致宗教势力不再主导古典城镇化运作这个原因外,还与宗教型城镇自身的运作模式有很大关系。
第一,宗教体制下城镇商业发展相对缓慢,充其量只是一个服务手段。古典城镇的商业发展起步是服务于宗教体系的,但随着城镇商业阶层拥有财产权利的增加,以及私有制、交换、财产差别的出现,商人阶层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充当宗教的“配角”。但宗教与权力的紧密结合,却压抑着商人阶层发展壮大的冲动,这使得城镇虽然出现了宏伟的神庙、祭祀等建筑,但商业的不发达却使多数人生活在“城镇贫民窟”。典型的例子是古罗马城:精美的大理石材料覆盖了新奥古斯都广场上的宏伟建筑和马尔斯神庙,但罗马城内仅有26个住宅片区为个人提供住处,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恺撒已经立法,但是大多数住宅建筑破烂不堪,有时会倒塌,并且经常失火[13](P53)。商业本身具有向外扩张的特征,但宗教却意图把人群及思想体系收敛于一处,这种聚集并不是服务于生产或规模经济的目的,因此,就形成了持久的宗教与商业发展的矛盾。虽然城镇蔓延发展并不见得都是好事,但是故步自封的城镇注定是缺乏创造力和活力的。
第二,不同宗教体系的冲突,使得人口迁移、战争时有发生,破坏了古典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古典城镇创制、发展的年代,宗教体系因国家、地区、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不同,不同宗教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并引发相互之间的战争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曾经因宗教而恢弘一时的古典城镇典范,如雅典、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比伦等,均遭遇到了这种冲击,使其“盛极而衰”。这也给今天城镇建设中宗教功能的使用提出了重要课题,即如何有效地限制宗教发展的内在冲突,避免因为教义和信仰差异带来城镇化发展的剧烈震荡,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要求。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逐渐丧失。宗教的兴盛及其与特权阶级的紧密结合,使刚刚兴起的商业激励机制受到压制,这在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埃及的早期最为明显:其资产阶级力量与商业激励机制始终受到抑制。[14](P101)宗教与专制政权任意征税、没收财产、以宫廷喜好行事,破坏了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但财富的创造有其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终究不能依靠对某个神明的祈祷来实现,这是宗教城镇难以从经济上自我维系的关键。伊本·郝勒敦指出:“对民众的财产的侵犯封杀了获取财富的动机。”[15](P101)这种对激励机制的抑制削弱了城镇发展的创新机制。跬步不前,古典宗教城镇的衰落必然是历史之定数。
(二)以安全拱卫保障“人气”的“安全之城”
古典城镇模式的特征之二,是以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包括安全的城镇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聚拢人气的“安全”之城[16](P4)。古典城镇的重要建设依据是为躲避游牧民族的劫掠及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而聚集并促成的生产生活区域。古罗马是这种安全型城镇的典型代表。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达到全盛,总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为了安全的需要,罗马城修建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道路、引水渠、排水系统等,使城镇有能力承受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17](P52);它建立了庞大的军队系统,通过对外战争来保证财富与生活要素源源不断地涌入罗马;它还将城墙与防御堡垒的作用发挥到冷兵器时代的极致。“安全之城”的时代因此而兴起。
1.建设功能首先考虑安全需求
罗马、约克、伦敦、特里尔、巴黎、维也纳、布达佩斯等欧洲古典城镇都十分重视古代城防工事。追求“安全之城”时期城镇居民所看重的,是城镇常备不懈的城墙及其带来的那种力量与安全。早在913年,建筑要塞与城墙保卫居民区便成为国王军队的主要任务之一。[18](P268)梅特兰指出,古典“安全之城”盛行的时期,把是否有能力供养一支永久性的军队并修建城墙当做取得城镇法人权利的条件之一。[19](P269)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中外城镇遗址,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这些城镇大都有出于守卫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措施——城墙;二是这些城镇的功能以政治、军事为主。[20]
古典“安全之城”兴起后,居住于乡村的居民会被其稳定、安全的功能所吸引。这种“磁体功能”最重要的作用是把“商人阶级”庇护并固定在城镇的保卫圈里,并直接促成了固定集市或市场的持久运作,城镇通过安全保障措施的完善,开始拥有了商业贸易的“内燃机”和稳定的人口规模。“当时城市的最大经济利益是每周定期一次的市场交易,它吸引附近地区的农民、渔民、工匠都来进行交换,而这种经济利益须有一个安全环境和合法制度作保障。”[21](P269)
稳固的安全保障为城镇发展创造了条件。罗马城不仅把罗马军团布置在边界、城墙和道路附近以保卫各个城镇,而且还允许独立城镇实行相当程度的自治[22](P55),城镇的基层力量对城镇安全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使得古典“安全之城”发展壮大的辉煌时代到来了。
2.能否维持安全制度是古典城镇兴衰演变的重要标尺
建成一个古典城镇(镇)相对容易,但维系一个古典城镇(镇)的安全制度长期运行则困难得多。历史上的罗马、君士坦丁堡均是城镇安全的代名词,但再高再厚的城墙、再坚固的防御堡垒与强大的军事机器,也经不起帝国内部的消耗和折腾,随着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内耗及外部安全形势恶化,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相继受到安全制度不牢固的影响而走向衰落。
其他的力量也可能削弱城镇的安全机制。以君士坦丁堡为例:“自然灾害(如地震)和紧随其后的公元6世纪晚期的大瘟疫,夺走了君士坦丁堡1/3~1/2的人口,有些小城镇甚至全城灭绝。灾害和内乱让帝国疲惫不堪,人口减少;面对公元7世纪和8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帝国无力与之抗衡”。[23](P67)另外,“帝国已经日渐退化为由永久防卫性的军事堡垒所组成的一个相当小的区域。拜占庭的防御潜力、外交和明目张胆的行贿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纷争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君士坦丁堡幸免于被彻底征服;直到公元1453年,才在土耳其人重炮的攻击之下沦陷。”[24](P67)
总体看来,古典安全城镇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其“安全观”没有与时俱进。城防与城墙固然重要,但维系安全的根本因素还是城里的“人”,“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城镇“堡垒”往往会从内部被攻破。近现代许多新兴城镇没有围墙、不驻扎军队,甚至连居民小区都没有围栏以及电子眼等监控设备的纯粹开放的做法,从根本上颠覆了古典城镇曾经引以为傲的城防体系。真正的安全城镇,不是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锁住城镇居民、画地为牢,而是以柔性的管理体制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容纳各种各样的人。“安全”得益于城镇居住人群的基本素质、相互信任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
3.古典安全城镇之得失镜鉴
古典城镇之兴衰演变,确实受到了安全体制变化的影响。人口的流入,城镇经济的繁荣,城镇可持续功能的强化,都必须在相对安全的城镇保障体系下得以充分扩展。古典城镇虽然已经消亡,但其对安全制度设计的经验教训却延续至今,安全因素在今天各类城镇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表现形式不再是围绕着城墙和防御工事这类传统安全问题展开了。“进入现代后,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仍有明显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圣路易斯及底特律等城市因此人口剧减,几十年未能恢复元气,纽约城也一度因为安全问题而严重影响其现代名城的形象。”[25](译者序P5)到20世纪末,美国一些城镇社会治安状况改善,犯罪率明显下降,这就为某些大城镇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镇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1992年经历了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兴。不幸的是,对城市未来的新威胁在发展中国家又浮出水面。20世纪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巨型城市,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更加恶化,对全球城市的安全构成最致命的直接威胁。‘9·11’事件是最极端的表现形式。”[26](译者序P5)
(三)以繁忙务实推动城镇商业发展的“商贸之城”
古典城镇模式的特征之三,是以商业发展推动城镇扩张、市场秩序建立的“商贸之城”。繁忙主要是指经济基础坚实、商业市场完善、城镇的社会基础即中产阶级发育比较成熟的状态。[27](译者序P5)而商业繁荣的关键,不是依靠居于神圣之地(宗教势力)或政治军事权力(安全保障),而是依赖由“重商主义”慢慢演化而来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一切只为追求财富增加的市场化体制。13~14世纪,威尼斯因重商主义而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贸易与金融中心,而且还是西方的主要生产车间,商业与工业得到巧妙的结合。[28](译者序P6)但是,“到17世纪时,资本主义才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从那以后,城市扩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人、财政金融家和为他们的需要服务的地主们”[29](P427)。到19世纪,城镇扩张的力量才逐渐由商业资本家过渡到工业资本家手中。
亚当·斯密分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商业城镇(镇)的发展情况。他指出:“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资料基金,仰给于农村的原生产物,而以一定部分制成了的、适于目前使用的物品送还农村,作为原生产物的代价。这两种人之间的贸易,最终总是以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与一定数量的制造品相交换。”[30](P251-252)这个结论,基本上就是现代任何一本《城市经济学》教材关于“城镇起源”的前两个重要假设条件的“古典描述”:“第一,农业生产过剩。城镇以外的人口必须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自己和城镇居民。第二,城镇生产。城镇居民必须从事生产,生产出某种产品或服务,以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去交换农民种植的粮食。”[31](P3)
关于城市经济学的第三条假设,即“城乡间要有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多次提及。他指出:“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僻远地方与都市附近地方,更接近于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僻远地方,必是乡村中范围最为广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促进这广大地区的开发。同时,又破坏都市附近农村的独占,因而对都市有利。连都市附近的农村,也可因此受到利益。交通的改善,一方面虽会使若干竞争的商品,运到旧市场来,但另一方面,对都市附近农村的农产物,却能开拓许多新市场。”[32](P141)由此可见,现代城市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起点可以从斯密对商业城镇的分析中找到雏形。
1.重商主义把古典城镇的发展聚焦到了“贸易兴城兴市”的地位
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这样一个商业城镇的兴衰来看,商人阶层对财富的追求并进而导致的重商主义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腓尼基商人依托海岸,利用黑色帆船探索从遥远的非洲海岸到塞浦路斯、西班牙甚至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地方,并凭借与强大的领邦进行货物贸易(有时是服务业)来丰富他们的城镇生活并获取城镇发展所需的丰厚利润。[33](P23)同时,商业行会控制了城镇运作,它们最关心的是扩展贸易。[34](P23)与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相适应的是,从复式簿记、商业汇票、股份公司到三桅帆船、码头、灯塔与运河事业的快速扩张,信用经济和交通经济因之而伴生。继腓尼基之后,一些港口城镇,如布里斯托尔(Bristol)、哈佛(Harv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奥格斯堡(Augsburg)、伦敦、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纷纷因商业和贸易的便利而崛起,这是13~18世纪重商主义在城镇发展史中所显现的必然过程。
2.商业发展推动“古典城镇”不断向外扩展蔓延
(1)都市商业发展对农村的城镇化改良。古典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对与其相邻或蔓延所至的农村的改良与开发亦有贡献。根据斯密的分析,其途径有三:
第一,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从而刺激农村的开发与改进。古典城镇商业的发展壮大,不仅拆除了困厄已久的城墙,还不断地开辟自由天地,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到郊区、农村实行城镇化开发。但这一过程是从城镇商业市场用强大的磁力吸引农村各项要素向城镇聚集开始的。结果,凡是与都市通商的农村都受其实惠。在中世纪,商业城镇的优势是通过商业垄断、行会的“存福特强制”*存福特强制指的是,凡属于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必须加入本行业的组织,否则便不许在同一城市内开业。加入者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并在生产和经营上服从行会的统治。、道路强制和互市强制来强迫农村向城镇提供粮食和农产品,以换取城镇的商品[35]。尽管如此,与城镇临近的农村依然获得了发展的“优先权”,其原生产物的运输所费较省,城镇商业市场又能吸纳这些产品与要素。因此,伴随着农村的产业发展与改进,农村渐渐地与城镇产生了紧密的商业关系,“城乡”一体化趋势增强。
第二,都市居民、企业通常将获得的商业财富用以购买待售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从城郊向农村蔓延开去的未开垦土地或农业用地。斯密比喻道:“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业家,乡绅往往是胆怯的事业家。就商人说,如果他觉得投下大资本来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费用的比例增大它的价值,他就毫不迟疑地马上去做。但乡绅很少有资本,即使有些资本,也很少敢如此来使用。”[36](P372)“此外,商人由经商而养成的爱秩序、节省、谨慎等各种习惯,也使他更适合于进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获利。”[37](P372)芒福德指出:“在商业城镇郊区,这一进程也在加速进行。通过把边沿地区的农庄土地分划成许多建筑地块,城市也就开始瓜分成一片一片。从19世纪开始,对城市来说,自由放任意味着‘让那些投机提高土地价格和租金的人放手去干’。随着军事防御城墙的拆除,城市就失去社会控制,向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38](P435)由此可见,从英国“圈地运动”肇始并延续至今的各国城乡工商资本下乡活动,主要就是围绕征用农业土地展开并实现城镇化的。
第三,农村居民一向处于在与其邻人的利益争夺和对其管理者的依附之中。工商业的发达,逐渐使农村居民过上符合商业与城镇秩序的生活,并更加关注政府行为是否妨碍其商业上的安全与自由。斯密指出,“就欧洲地区的农村、农业改良而言,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结果。”[39](P379)因此,商业资本既为古典城镇发展注入活力,又不满足于城镇框架的限制,它力图把触角伸向那些未经商业化开垦的农村土地,从而把城镇化自古典时代的传统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2)都市商业发展推动古典城镇化走向公交导向。对于商人阶层来说,理想的城镇应该设计得可以迅速地分成可以买和卖的标准货币单位。“这类可以买卖的基本单位不再是邻里或区,而是一块一块的建筑地块,它的价值可以按沿街英尺数来定,这种办法,对长方形沿街宽度狭而进深的地块,最有利可图。”[40](P438)但是,一旦古典城镇按商人阶层的价值要求来开发,就必然造成商业用地之间的通达用地(街道)日渐紧张,而且,随着城镇土地开发密度的提高,以及商业对外拓展(向农村或其他城镇)的需要,车辆及交通设施的使用更加频繁,快速的公共交通及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这类古典城镇发展到商业主宰阶段所不可或缺的通勤手段,以至于“每条街道都有可能成为车辆交通街道,每个区都有可能成为商业区”[41](P438)。
但这种以公交导向为基础的古典城镇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公交承载力永远跟不上城镇开发密度增加带来的人口增加的压力,以及城镇蔓延广度增加带来的通达距离及容量的新增需求。换句话说,在工业化时代的地铁、轻轨尚未发明和普及的年代,商业主导的古典城镇化发展,既需要公共交通有一个大的改善以助推其“再造古典城镇”,同时其发展也大大地受限于公共交通本身扩展的难度与成本。“拉链路”(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在西方古典城镇化的商业发展时代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芒福德曾形容道:“这种规划常常不明确区分主要交通干道与居住区内街道,交通干道不够宽,而居住区内街道按其功能要求,又显得太宽,这就要浪费许多钱来铺设路面,并设置很长的市政管线和总管道”[42](P439)。这并不是当时的规划者不知道“经济”地利用、开发城镇及其公共交通系统,实在是由于古典时代城镇模式的商业化扩张速度超过了决策者的预期。即便是快速的公交系统建成了,其目的也不是减少人们通勤的路程时间,相反,由于其扩大了城镇可通达的范围,反倒增加了人们通勤的距离与路程费,而交通时间一点都不省。[43](P446)
(3)古典重商主义城镇带来的两极分化与拥挤。古典重商主义城镇首先影响的是贫穷人口的居住区。由于对利润与土地价值回报的追逐,商业资本不允许城镇贫苦人民拥有相对宽敞舒适的住宅区和活动场所,廉价公寓及出租房成为重商主义城镇中贫苦阶层居民的“收容站”。古典城镇所发生的拥挤与两极分化就此出现。这种“拥挤”情况从16世纪商业和无产者涌向欧洲大陆的首都城镇时开始,就变得长期化了。[44](P447)“从1550年起到18世纪中,被雇工人每年工资不超过675法郎,而当时巴黎最坏的住房每年得花350法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为何工人们不得不放弃单独借住一处房子,而宁可与人家挤在一起合住一处房子了。”[45](P448)“无依无靠的穷苦移民竞相争取一个立锥之地,其产生的影响,对17世纪的巴黎或爱丁堡,18世纪的曼彻斯特和19世纪的利物浦与纽约,都是一样的。”[46](P447)
这些现象是重商主义导致的资本主导城镇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城镇或商业城镇的资本积累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越坏。“在伦敦,随着城市不断‘改良’,以及与此相连的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最后,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中了。”[47](P759-760)
这和芒福德所描述的现象完全一致:“据估计,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里,多达城市总人口1/4的人是乞丐和靠救济生活的:正是这种剩余劳动力被经典的资本主义认为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资本家可以按其自己的条件雇用工人,并且不用事先通知就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不必考虑工人今后怎样生活或是在这样不人道的情况下城市将会怎样。”[48](P448)可见,古典重商主义时期的这种城镇化结果,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聚集时期城镇的前身,正是由于有对财富、土地、利润的无限度追求,才使得重商主义城镇达到了古典城镇化发展时期的顶峰。从这个角度说,商品化、市场化和城镇化本身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商业触角延伸到多远,城镇化就可以发展到多远。
3.中国商业城镇化模式发展的滞后
斯密对同时期中国的城镇发展情况作了分析:“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49](P246)这说明,中国在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不仅工业城镇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潮流,就连商业和贸易城镇的发展也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整个国家就是农业立国的思路主导着发展。对此,郭廷以曾指出:“19世纪以前的中西贸易,双方均采独占制,在欧洲为各国的公司,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为广州的洋行,特别是洋行合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为互市的自然结果,然后得官府认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独占性与之相似。”[50](P24)但是,到1759年,出于控制外夷及其商贸的目的,“广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对于夷商的管制更严,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们除非不与中国贸易,否则唯有听从广州官府及行商的摆布”[51](P26)。这种锁国政策,大大滞缓了中国近代以来商贸型城镇化的进程。换言之,斯密眼中极具商业城镇化发展禀赋的中国,没有利用好市场、交通、资源、技术和产业的优势,致使其城镇化发展从18世纪末期脱离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潮流。
4.古典重商主义城镇之得失镜鉴
重商主义将古典城镇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城镇不再囿于一个固定的、有界的范围。城镇蔓延、农村的城镇化开拓、贸易与交通格局的快速展开以及伴随而来的城乡二元分化,都隐含着一个可能的新的时代的到来。在阐述那个新的时代之前,我们简要总结一下重商主义城镇的得失镜鉴。
第一,古典重商主义城镇打破了之前“一城一市”的格局,城镇蔓延问题在贸易扩展、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愈加严重。但这种问题在“重商主义”框架下很难得到彻底解决。“城镇群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立体公交导向的城镇模式”则是在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才逐渐出现的克服城镇蔓延模式的城镇化思路,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如何在商贸发展、城镇扩张与限制城镇过度蔓延之间找到平衡点,有待于更加创新的城镇化模式出现。
第二,古典重商主义城镇使农村城镇化问题“被迫地”卷入到城镇发展史的历史洪流之中。重商主义不断地向农村进军,农业、农民、农村全部“商品化”了,但这种“商品化”的开拓是否真的能促使农村健康、有序、科学地“城镇化”?在我看来,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难以企及上述三大标准。相反,更多的农村地区的商品化、城镇化过程,可能是与杂乱无章、极不科学相联系的。这也为重商主义之后的时代是否能有效处理城乡关系、解决农村城镇化模式敲响了警钟。客观地讲,这一问题在后续的工业城镇时代不仅未能得以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也许可以促使我们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契机:工业城镇时代确实解决了商业城镇时代的一些技术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对古典城镇的工业化改造未必都是真的实现了城镇化对“人”的关切。
第三,商业城镇的大发展使得劳动力供给日趋出现“过剩”状态。适龄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化地区所带来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和商业资本要求控制成本并获取最大利润的目标相冲突,这使得贫困、拥挤、不平等、二元分化等问题渐渐具有了“当代城镇化”的特征。这种历史的延续性,为今天仍在强调招商引资的那些城镇提出了一个自13世纪起就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安置这些劳动力?这是城镇化模式由古典向现代跃进所面对的一个难题。
二、新古典城镇化模式的历史沿革
18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催生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模式的革新,而且还有在这种生产模式下的城镇化变革。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他举例指出:“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52](P762)。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像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这样的工业城镇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会变得恶劣不堪。或者,市政官员终于可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像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53](P762-763)。
但本文认为,工业城镇之所以被冠以“新古典城镇”的名称,根本上说,还是在于其把城镇也当做一个生产函数,城镇的一切资源、资本、劳动力几乎都为这个“生产”服务,从而使它在城镇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它确实是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业城镇就是18~19世纪的一种潮流;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像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那些弊端,需要更新理念,清除工业城镇模式的“病灶”。因此,笔者将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新古典城镇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得失镜鉴。
(一)从“兰开夏发源”到“工业纽约崛起”:工业城镇的新古典革命
1.兰开夏发源
英国工业革命所带动的“新古典城镇革命”的“震中”位于兰开夏郡。[54](P144)曾经是英国最贫困地区的兰开夏,到19世纪早期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不同于伦敦以煤炭和羊毛等商品执英国经济之牛耳,兰开夏郡等工业城镇革命发生在远离首都(大都市)的地区[55](P144)。它们与伦敦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城镇中心依靠大规模的产品加工推动资源、人口聚集。马克思用一个数据说明了这种变化的结果:“19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五个城市超过50 000人。而现在,超过50 000人的城市已有28个。”[56](P761)马克思所说的“而现在”,指的就是以兰开夏郡为代表的一批工业城镇的崛起时期。狄更斯在小说《艰难时世》中将这种城镇称为“焦炭城”(Coke Town)。而芒福德指出:“西方世界中每一个城市,或多或少,都有着焦炭城特点的烙印。”[57](P462)其中,兰开夏郡的主要城镇“曼彻斯特的人口飞速增长,在19世纪的第一个30年,人口由原来的9.4万上升到27万。到19世纪末,曼彻斯特人口增长了两倍多”[58](P145)。又据芒福德的研究:“曼彻斯特在1685年时约有人口6 000;在1760年时,发展到30 000与45 000之间。伯明翰在1685年时约有人口4 000,而到1760年时,几乎增加到了30 000。1801年时,曼彻斯特人口是72 275人,而1851年时达到303 382人。”[59](P469)一个镇竟能支撑起几十万人的生产生活,这种近代工业城镇的生产力跃升能力确实令以往的城镇化模式大为逊色。
有学者指出,“18世纪到20世纪由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席卷全球,由此推动的城镇革命普遍使城镇由旧质向新质转变,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城镇向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城镇转型,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城镇的功能和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60]英国的重商主义积累、自由竞争经济加上工业革命的洗礼,在18~19世纪把城镇化顺利地引入了工业推动的轨道,创造出了一批内生发展动力极强的工业城镇,城镇化生产力在工业车轮的运载下达到了以前时代无法企及的水平与速度。从这一点来讲,以“兰开夏”发源为代表的英国工业城镇模式是成功并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城镇化潮流的。
现在需要剖析的是,工业城镇成功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是什么?马克思是用相对人口过剩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来阐明这一工业推动城镇化的新进程的,他所揭示的是“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所助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农业过剩人口不断地被吸引到城镇工厂,劳动力呈现无限供给态势;另一方面,这些劳动力必须忍受最低工资率,以贡献剩余价值给工业资本家及其主导的工业城镇化模式。劳动和资本在工业城镇化时代分工十分明确,但同时,劳动力的从属地位也在这一时期被完全固化了,工业城镇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呈现两极化发展的趋势,劳动力尽管人数众多,但只能受工业资本的驱使,并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不利位置。芒福德将这种生产关系基础总结为三个方面:“废除同业公会,为工人阶级创造一种永远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为出卖劳动力与出售商品建立一种竞争性的公开市场;保持在外国的属地,以攫取新工业所必需的原材料,同时作为吸收机械化过剩产品的现成市场。”[61](P462)而其经济基础“是开发煤矿,大量生产铁和利用机器力量的可靠资源(即使效率非常低):蒸汽机”[62](P462)。机器“战胜”劳动力的时代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本质上,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什么“机器”战胜劳动力,而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全面控制和“胜利”。
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这场“兰开夏”发源,直接导致劳动者成为当时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的主要客体;其技术依托是依赖矿石燃料的自动化机器革命;其生产关系则是资本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制度;其财富(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积累,来自重商主义城镇发展中后期商业资本对海外贸易和农村的深度开拓,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我们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积累确实催生了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且只要有源源不断的燃料、原料、劳动力供应,城镇便可自我循环的内生化城镇模式,这是以往的古典城镇化时代所不具有的特征。此时,城镇化发展拥有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约束条件,这个条件保证了资本主义开启的工业城镇模式“一帆风顺”。
2.工业纽约的崛起
19世纪上半叶,新的工业热点发生在落后的北美的辽阔土地上。工厂城镇在这里生根发芽,而且以超过英国本土工厂的规模蓬勃发展。[63](P152)工业纽约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变化,最终把这片以乡村为主的土地变成了大城镇云集的地方。1850年,美国仅有6座人口超过1万人的“大”城镇,不到总人口的5%。这一数字在以后的5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900年,美国人口过1万人的城镇达38个,大约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城镇。[64](P152)以至于“亚当·斯密的声音在世界的耳朵里响彻了60年,但只有美国听从了这个声音,并推崇和遵循它”[65](P315)。而具体到美国工业时代的代表性城镇纽约,其特征表现在:
(1)城乡移民和外国移民迅速涌入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东北部工业重镇。据诺克斯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短缺,‘大迁徙’使黑人大量流入东北部工业城镇。”[66](P83)19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爱尔兰大饥荒、英国的“放任主义”政策以及因农场土地大面积经营带来的农业合理化等,都推动了移民运动。这种国内外的移民潮解决了纽约等工业城镇崛起所必不可少的劳动力需求缺口,同时,也不断地形成美国工业城镇的“贫民聚集区”与“产业后备军”积累。由此看来,美国的工业城镇化也经历了由劳动力过剩供给引发的城镇发展困境——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城镇发展拐点。
(2)能源地、矿业镇、交通枢纽型城镇相继兴起。例如,“在燃煤蒸汽机技术和之后的电力大量使用前,水能尤其重要。这一因素导致沿着新英格兰的瀑布线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部边缘形成了一系列的工业城镇,如宾夕法尼亚的阿伦敦和哈里斯堡”[67](P69),而“矿业城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煤田城镇如弗吉尼亚的诺顿则为工业经济提供煤矿”[68](P69)。又如,“弗吉尼亚的罗阿诺克作为铁路枢纽镇的崛起,则是因为其出现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因航道和铁路系统而形成的战略性位置上”[69](P69)。在美国西部城镇崛起的过程中,由于政府决定将公共土地向广大移民开放,允许人们以不同价格购买联邦土地,以及美国西部地区采矿业、交通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出现了“投机企业的市镇”(如马里塔、辛辛那提等)、“采矿城镇”(如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和科罗拉多的丹佛等)、“牛镇”(如阿比林)和“铁路城镇”(如奥格登、奥马哈、苏城等)[70]。
(3)城镇增长主要发生在工业集聚的大城镇(镇)。这被解释为“工业城镇的先发优势”[71](P72),其外部经济与集聚经济,使工业城镇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工业企业以外的行会、特殊技能与经验的劳动力市场、各类供应商、转包商、分销机构、法律顾问、储存公司等纷纷涌入工业集聚的大城镇,城镇的增长呈现出人口与产业双重聚集的特征。到1875年,“工业城镇体系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超过15座城镇,每一座城镇连同它们的临近乡村都有10万以上的人口。拥有130万人口的纽约位于城镇等级的顶端,紧跟其后的是五座拥有35万~50万人口的城镇:巴尔的摩、芝加哥、费城、匹兹堡和圣路易斯。拥有10万~15万人口的城镇包括雅典(佐治亚州)、波士顿、布法罗、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底特律、曼彻斯特(新罕布什尔州)、新奥尔良、普罗维登斯、罗切斯特和锡拉丘兹”[72](P72)。而从产业集聚角度讲,匹兹堡对于“钢铁制造业的吸引,阿克伦城对于橡胶制品工业的吸引,代顿对于金属制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吸引等”[73](P72)引领了美国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工业城镇增长浪潮。
(4)工业城镇呈现出城镇创新的规模效应。由于工业城镇增长对企业、人力资源的高聚集作用,城镇规模的增长对创新扩散的助推作用越来越明显。“城镇越大,其拥有的规模经济也越大,也易于产生更多的创新,从而吸引移民前来并确保居民不移居至其他城镇。因此,大城镇的绝对规模,保证了强大和稳定的创新,而这又能促进人口的稳定增长。较小的城镇则必须更多地依靠其他城镇,一般是较大中心的创新扩散作用。”[74](P74)
(5)工业产业链的上下游联系及成本控制促进城市(镇)群的形成。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制造业带的形成需要产业链的联系效应予以支持。这是因为,城镇再大也不可能涵盖工业链条的所有上下游产业,这时,城镇群即以中心城镇发展制造业中心区,其周边较小城镇为高度专业化和极度盈利的制造业行业提供支持。通过银行系统、电讯系统和邮政系统的整合,使城镇群的商品流动、要素流动更加合理。例如,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五大湖的匹兹堡、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密尔沃基,以这些城镇群为基础形成了城镇制造业带。[75](P79)
(6)核心—边缘的工业城镇模式逐渐形成。“非均衡发展”是工业资本主义城镇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76](P81)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核心—边缘”模式(core-periphery pattern),即城镇制造业“中心”高度工业化、城市化,而“边缘”即农村或其他非能源、矿产、交通枢纽、非制造业的地区的发展则相对滞后。核心城镇通过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带动边缘城镇以及农村的发展,“边缘城镇农业机械生产的增长来自于核心城镇需要供给数量更多、要求也更多样的人口”[77](P81)。
(7)工业城镇人口增长带来失业率的陡增。纽约等城镇及城镇群的崛起带动了一批以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城镇,城镇的经济增长聚集了大量从农村和其他边缘地区乃至国外涌入的移民。但城镇自动化技术的日趋成熟必然导致进城务工人口无法找到工作。西方的城镇化理论倾向于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造成的间歇性危机,认为是可以克服、治愈的。但事实上,工业城镇发展所引起的失业从根本上说是个持久的“技术”现象,经济周期的繁荣或衰退至多只能减缓或增加失业,但不能“治愈”或“根除”失业。工业城镇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即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从此意义上说,工业城镇化历史进程的伴生物之一便是失业大军。
(8)工业城镇在聚集资源、人口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聚集着污染。除工业纽约所带动的美国东部沿海平原城镇群外,19世纪著名的工业城镇(区)还包括:“法国的里尔区,德国的梅泽堡区和鲁尔区,英格兰中部以伯明翰为中心的工业地区,阿勒格尼—大湖地区”[78](P471)。这些新兴的工业化增长中心在带来城镇的集群化发展与增长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影响。“一个工厂的烟筒,一个鼓风炉,一座印染厂所排放的臭气和污染物,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吸收而消失。但是,一块狭窄的地块内挤上20座工厂,就能把空气和水污染得难以治理。所以,有污染的工业,一旦在城镇里集中后,情况必然会比它们小规模地分散在农村时严重得多。”[79](P473)另外,工业城镇把聚集效应发挥到极致,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者混杂在一起,噪声、雾霾、垃圾的污染接踵而至,工业城镇产业人口(包括婴孩)的疾病比率和死亡率非常高。工业城镇增长的繁荣很难掩盖这些实际的恶劣情况,更不要说这种生产上的收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残酷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牺牲。
(二)新古典城镇之得失镜鉴
第一,工业城镇的新古典特征是效率导向的,工业集聚带动工业与城镇增长是这一效率的集中体现。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最经典的生产函数假设一样,新古典工业城镇虽然是由工业企业的产业集聚形成的,但是从整体上看,工业城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企业和生产函数,这是它选址、存在、增长、演变的根本推动力。这也为那些尚未经历工业化洗礼的国家或城镇提供了某种模仿的机制——采用工业企业聚集的方式来推动城镇化,效率显著。
第二,工业城镇的新古典特征要求劳动力对城镇增长和工业发展形成无限供给。具体表现为:(1)工业企业的集群式聚集在形成工业城镇时,也吸引劳动力不断进入城镇的工业企业就业,这种劳动力要求在城镇工业企业获得高于农村的收入(工资),以便抵消城镇较高的生活费用,因此,工业城镇必须提供相对于农村更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以吸引劳动力。(2)涌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之后,必然导致城镇工业部门(企业)就业竞争加剧,就业岗位的稀缺使工资率逐渐下降到一个制度性的低工资水平。(3)低工资率尽管可以覆盖相当比例的进城劳动人口,但城镇工业部门就业增加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劳动力进城的速度,所以,工业城镇发展的重要成本就是造成日渐高企的城镇失业率,这个成本的消化,迄今都未得到妥善解决。这也是从工业革命所引致的工业城镇发展至今一直存在的“常态型”问题。
第三,工业城镇新古典聚集也会造成污染、拥挤及各类城镇病的聚集。兰开夏与工业纽约在崛起的早期,均经历过聚集型工业城镇所挥之不去的污染(噪音、粉尘、雾霾、水质恶化、空气污浊)、拥挤(道路拥堵、河床堵塞、就业场所人满为患)、疾病流行和犯罪迭生。在环境方面,芒福德一度把这种工业城镇形容为“焦炭城”,这种城镇对能源、资源的聚集能力超过了以往时代的城镇。城镇的核心区全部是工厂与烟囱矗立,一切均被淹没在工厂排放的烟尘与污染物之中。从治理的角度看,发达国家花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才将工业城镇的污染源迁出,治理成本十分高昂。而拥挤、犯罪等工业城镇发展的社会性成本一直延续至今,这些成本如何治理,西方国家至今也在不断探索之中。
第四,工业城镇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加重。分配的不均等并不是工业城镇的独有特征,只是与商业、贸易等早期的城镇相比,工业城镇加剧了这一分配不均的社会化进程。在拉佐尼克[80](P4-7)看来,工业型城镇的微观载体就是工业企业的一个个“车间”,车间里的劳动生产关系存在等级制、雇佣制;由于产业后备军大量涌入城镇,低工资的劳动者逐渐沦为工业城镇的无产阶级,他们只能从城镇发展和增长中分享到少数剩余,城镇发展与增长的多数剩余被工厂资本家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拿走,社会财富的贫富分配差距又被工业资本主义体制进一步拉大了。皮凯蒂针对近20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指出:“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81](P22)。城镇化的工业推动模式和财富积累机制,至今仍在助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劳资分配不平等的趋势加剧。
三、小结与启示
本文试图从古典模式的精华和新古典模式的弊病中寻找城镇化后续的发展思路。笔者认为,古典城镇化虽然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其某些城镇化的建设思路却历久弥新,甚至超越了今日的新古典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模式在新古典之后,很可能部分回归古典范式,这也许让人始料未及,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当代新古典工业城镇化给予理论研究者和城镇居民的“集体焦虑”,不能亦不应该把城镇都建成工厂、车间和钢筋水泥丛林。寻求城镇化在新古典之后的“古典”出路,应当是比较研究古典和新古典城镇化模式的关键所在。
另外,通过模式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城镇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进步,但城镇生产关系却经历了古典阶段到新古典阶段的历史变迁。古典城镇因为生产力尚未达到驱动城镇内生发展的阶段,因此其治理与发展城镇的手段依赖宗教、安全与商业贸易,但并不是说这些治理和发展古典城镇的手段就注定是“落后”的,虽然它们在发展“城镇生产力”方面不及工业时代的新古典城镇,但是,它们在凝聚人口、保障城镇安全秩序以及扩展城镇商贸规模方面的确有许多方式方法值得今天的城镇发展借鉴。而新古典工业化城镇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把各种古典城镇推倒重来,美其名曰“工业改造”,可事实上,新古典工业城镇模式发展到极端时带来的是一系列“城镇病”,以至于后续的城镇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构想出“田园城镇”、“服务型城镇”、“智慧城镇”、“多中心城镇”、“逆城镇化”等方式来治理工业城镇的弊病,其结果是,一些城镇回归古典模式,一些城镇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镇发展的历史由此掀开新的篇章。中国当下正在经历新古典工业城镇建设的洗礼,尽管这个发展阶段不可或缺,但此时尤其需要对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古典和新古典城镇发展史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出最适宜我国国情的各类城镇。本文的分析即是为那些还在追求“高、大、上”的工业城镇提供一个往昔的城镇发展参照系,以方便它们重新定位自己的发展轨迹。
[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3][4][5][6][9][10][11][13][14][15][16][17][22][23][24][25][26][27][28][33][34][54][55][58][63][64]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18][19][21][29][38][40][41][42][43][44][45][46][48][57][59][61][62][78][79]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0][60] 何一民:《第一次“城市革命”与社会大分工》,载《甘肃社会科学》,2014(5)。
[30][4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1] 阿瑟·奥莎利文:《城市经济学》,第6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2][36][37][3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务馆,2011。
[35] 张冠增:《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商业垄断》,载《历史研究》,1993(1)。
[47][52][53][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0][5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5] Arthur M.Schlesinger,Jr:《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纽约,寻书俱乐部,1945。
[66][67][68][69][71][72][73][74][75][76][77] 保罗·诺克斯等:《城市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0] 何顺果:《美国西部城市的起源及其类型》,载《历史研究》,1992(4)。
[80] 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1]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武京闽)
The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Model of Urbanization
WU Yi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Sichuan 610031)
In the short term,i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of the classical model and that of the neo-classical one.Therefore,it needs to be explored from the long term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ough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level,the classical urban pattern,which emerged as a result of religion,security or business factors,can not match the “Neo-Classical Urbanization Model” initiated in the industrial age,thei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in the history need precipitation.By contras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Neo-Classical Urbanization” model has come to its declining period as far as its historical task is concerned.Therefore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particularly its malpractice,serves as a warning for the industrial towns in the making.To construct a new urbanization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e need to draw on both the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model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so as to reshape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t various levels.
urbanization;classical model;neo-classical model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理论、模式与政策研究”(14CJY023);四川省教育厅四川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四川特色的区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2015]3036号)
吴垠: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