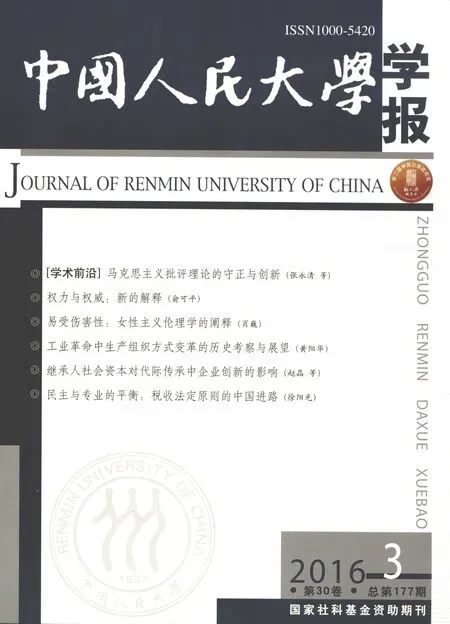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事件论
张 进
马克思主义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事件论
张 进
作为20世纪诗学的轴心概念,“作品/文本”承载着巨大的理论负荷并成为不同文艺观念和批评方法的试金石。21世纪以来,“事件”作为其替代表述与之构成一种“作品/文本/事件”的“三元辩证”关联。“事件论”视作品/文本为话语行为事件、历史文化事件和社会能量事件,凸显出文学活动主体的具身性、行动过程的历史性以及事件本身的连通性和物质性。受马克思主义有关美学与史学、文艺与社会之间关系思想沾溉的学者参与了文学事件论的塑形过程,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文论中的回归和衍生。作为事件的文学不仅“解释世界”从而成为社会历史的“前景”,同时也参与历史进程并成为实际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进而以特定方式“改变世界”。
文学事件论;连通性;物质性;具身性;历史性
“作品/文本”作为20世纪诗学的轴心概念承载着巨大的理论负荷,人们在这些基本术语上的取舍,可能意味着对不同理论观念和批评方法的选择。“从作品到文本”被视为“方法论”的深刻转换[1],“给其他许多广为接受的解释成规带来了问题”[2](P3)。众所周知,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实证主义方法中,文学作品被看成“历史文献”[3](P153);新批评把自足的“作品”视为无关作者意图、读者反应和社会环境的“超历史的纪念碑”;结构主义将“作品”看成能指与所指的完整统一,但忽略了其中的差异性和历史具体性;后结构主义以“文本”代替“作品”,视之为能指碎片或能指游戏,却仍以拒绝确定意义和历史内容为代价。21世纪以来,一种旨在将文本“内外”关联结合的“事件论”逐渐成为解说作品/文本的关键术语,形成了“作品/文本/事件”三元辩证的阐释格局。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沾溉的巴赫金、福柯、广松涉、巴迪欧、伊格尔顿等人参与并塑造了文学事件论的形成过程,而这一进程也始终处在马克思主义有关美学与史学、文学与社会、文本与实践关系问题的“问题阈”之中。
在从作品到文本、从文本到事件的理论演进过程中,最成问题的仍然是文学与历史、前景与背景、文本性与历史性、美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作品/文本理论断然排拒历史,但这些理论也都或多或少地开放着朝向历史的窗口。新批评认为文学作品可将意识形态化世界中的教条信念暂时悬搁,但作品似乎仍以某种方式谈论着它之外的历史现实。结构主义在推开历史和所指物之时,也“使人们重新感到他们赖以生活的符号的‘非自然性’,从而使人们彻底意识到符号的历史可变性。这样结构主义也许可以加入它在开始时所抛弃的历史”[4](P155)。尽管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同样是在形式主义内部进行的,但诚如巴尔特所说,它意味着部分地从“作品”(work)转到“文本”(text),从视诗歌小说为确定的封闭实体转向视其为“无限的能指游戏”。文本不同于作品结构,而是一个“抛弃了中心,没有终结”的结构过程。[5]这个动态开放过程依然与社会历史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牵连。
然而,当其宣称“文本之外无一物”并摆向“文本主义”的极端立场时,无所不包、无时不在的文本最终走出象牙之塔,按照自己的形象改写并占领了历史。这使文本“脱域”而成为了“TOE”(Text of Everything),变成了“文本巨无霸”(笔者仿用齐泽克的Theory of Everything)。[6](P14)这个文本似乎“吞没”了历史,然而,现实情况是,总有一些历史内容逸出了“文本”边界。人们不得不采用“非文本”概念来命名那些属于“活态过程”的历史[7];不过,这个术语与其说挽救了,还不如说进一步瓦解了文本主义的合法性。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活动无法摆脱文本性,人们从文本性去看待社会现象,可以“认识它们的无确切性、因其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必然具有的武断性,以及对各种文化影响渗透的吸纳性”[8](P3)。但是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如何制衡呢?如果说文本主义是将“历史”整体纳入“文本”来审视,那么有没有可能将“文本”纳入历史过程,视之为“历史事件”,将文本事件视为历史本身而不仅仅看成历史的“反映”呢?正是在这个向度上,“事件论”逐步代替“文本论”而成为解说文学作品的轴心概念。
一、事件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
“事件”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理论术语,不同思想谱系的理论家对之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形成不止一种“事件论”。然而,其理论要旨仍然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阈中得到揭示。
首先,事件论是在批判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非实体的关联本体论立场,这个过程延续了马克思的思想洞见。在旧唯物主义的实体世界观中,世界由诸多直观可见的实体构成,感性的直观为抽象思维的基础。马克思批判其“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考虑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维度,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P499-501),实践将人与事物关联起来,这种关联乃是基础性的。只有“通过实践,思维与存在、意识与感觉或者物理物质、精神与自发性被重新统一起来”[10](P38)。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构成了“事件”理论的基本立场,“事件”与“实践”一体两面。巴赫金强调,“存在即事件”,事件作为“现实存在”的“唯一性”和“统一性”整体,是将各种知识活动关联起来的根本所在。人的行为唯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是真正实际存在的,才能参与“这一唯一的存在即事件”[11](P3)。因此,他反对静态的、非历史的对世界的思想理论考察,强调认识活动“每次都必须体现为某个现实的、真正的思考着的人,以便他连同他的内在生活的整个世界(这是他认识的对象),能够与实际的历史和事件的存在(他只是这个存在中的一个因素)联系到一起”[12](P9)。巴迪欧认为,“事件”的发生乃是存在得以在世呈现的良机,事件在本质上并不是作为“是什么”而现成地存在,事件总是作为“正在发生”而活生生地到来,它是正在生成中的那个“到来”本身。正因为这样,事件就成了存在的条件,事件使一切存在成为可能。[13]事件是正在生成并随时变动的张力关系,每一个“独特的真理都根源于一次事件”[14](P7)。怀特海认为,事件就是“通过扩延关系联系起来的事物”,事件“展示其互相关系中的某种结构和它们自己的某些特征”[15](P138),不存在静止的、稳定的事物,只有动态的、连通性的、时间—空间扩延关系中的“事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具体事实就是“事件”,牛顿机械物理学的立场是不成立的,机械唯物论的立场应该被纠正,而代之以一种“关系”实在立场。广松涉则试图确立一种新的关系主义的“事的世界观”,认为所谓“事”并非指现象或事象,而是存在本身在“物象化后所现生的时空间的事情(event)”,关系性的事情才是基始性的存在机制。[16](P15)这种关系主义存在论将“实体”放置到一个连通性(connectivity)基始之上,而所有的“物”,事实上是与其他物共生共在、关联互渗的“事”或“事件”。
其次,事件论是在批判近代以来将历史过程与历史认识二分对立的史学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过程性的观念。福柯将“事件化”(eventualization)视为一种“反结构主义”的历史研究路径,在他看来,结构主义“不但要从文化人类学中,而且要从其他一系列科学乃至历史学中排除事件概念,并为此做了最系统的努力”,他反对将历史视为具有自身理性规律的进程,其历史研究的核心思路在于抓住历史转型期和断裂处,澄清其中的复杂机制,将其充分事件化,“对事件所属的网络和层次加以区分,同时要重构将诸事件联系在一起并促使它们相生相成的纽带”[17](P432),以一种考古学或谱系学的方法,对事件的复杂历史性和多维关联性,对事件的影响和效果、事件的生成和断裂所构成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建立一种历史的事件过程论。德里达将其思想的核心概念“解构”视为一种“‘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强调“从一开始,解构就不仅仅要求关注历史,而且从历史出发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待一个事物。这样的解构,就是历史……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他认为,“事件”的经验是一种“可能”的经验,它与“偶然”、“事故”等范畴亲近,“事件不应该是可预见的,而是不能计划的,没有方向的”,是“无理由的”。[18](P69)
再次,事件论是在弥合美学与史学、文学与社会、文本与实践二分对立的文艺美学观念演替中形成的,强调文艺活动的历史性、物质性和“具身性”的观念方法。在海德格尔那里,“事件”意味着“缘构发生”,真理、艺术作品都可以是一个个事件。“艺术作品的存在不在于去成为一次体验,而在于通过自己特有的‘此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事件,一次冲撞,即一次根本改变习以为常和平淡麻木的冲撞”,因此,作品“不仅仅是某一真理的敞明,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事件。”[19](P107)事件(event)是发生之中、时间之中的事实(fact)。从视艺术作品为“事实”走向视其为“事件”,也就将作品放置在时间和发生之中。[20](P145)这种事件观念广泛渗透在文艺美学领域。伊格尔顿指出:“总体说来,有可能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看待文学作品的方式:视作品为实体(object)和视作品为事件(event)。前者的典型个案就是美国新批评,对它来说,文学文本是一个有待切割的符号封闭系统。”[21](P188-189)而“事件”则与“行为”(act)、“策略”(strategy)、“表演”(performance)含义相近,彰显的是动态性、开放性和历史性。在他看来,“文学作品自身不是被视为外在历史的反映,而是一种策略性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为了接近现实,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为现实所包含——由此阻止任何头脑简单的内在与外在的二分法”[22](P170)。文学作品悬挂于事实与行为、结构与实践、物质与语义之间,它们是“自我决定”的,但这种自我决定活动与它们对其环境的“行动”方式是无法分开的。因此,“文学事件”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语境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它通过行为和表演而与历史和语境相互构成、共生共荣。
总之,“事件论”是一种渗透在人文学科各分支的理论学说,过程性、生成性、连通性、历史性、物质性、具身性等一系列观念方法聚合在它的周边,从而为审视文学作品/文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参照。
二、作品/文本作为话语行为事件
作品/文本永远与它的“制作者”之间存在着关联,然而,这种关联却不只是“记述性”(constative)意义上的,更是“述行性”(performative)意义上的。自奥斯汀开辟出语言之“述行”维度之后,文学研究者很快发现,“文学是述行语言”[23](P37)。述行语的首要功用是“施为”,而不是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24](P5)德里达将言语的“行为”视为一种“事件”的制造,“‘行为句’就是在特定时间制造事件的语言行为”[25](P68-69),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够制造事件,是因为与权力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强力、合约和机构建立的权力。文学作品/文本是作家“以文行事”的基本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文本是作为话语行为事件而存在的。
文本作为话语行为事件的观念植根于话语概念,话语关联着文本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本是“话语”的集积。利科尔认为:“话语是作为一个事件而被给予的:当某人说话时某事发生了。作为事件的话语概念,在我们考虑从语言或符号的语言学向话语或信息的语言学的过渡时具有本质性的意义。”[26](P135)在他看来,“事件”意味着话语是一种说话的事件,它是瞬时和当下发生的,而语言学的体系却在时间之外。说话的事件包括说话人、听话人、指称物和语境,它是瞬时的交换现象,是建立一种能开始、继续和打断的对话。因此,作为事件的文本总是与历史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关联。更进一步说:“小说是一种话语事件。它不反映历史;它就是历史。”[27](P38)不止小说,所有的文学作品/文本都是作为话语行为事件而存在的,而不仅仅作为历史过程的“反映”而存在。
福柯将文本放在话语活动中去考察,这引起了文本观念从“语言”(language,包括结构主义的“语言”和“言语”两方面)向“话语”(discourse)的转移,从视语言为无主体的符号链,转向视它为包含说写者(潜在地包含听者和读者)的个人话语[28](P126),变成了与历史语境相关联的具体话语。福柯的话语理论实际上就是其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理论,它集中体现了福柯的知识观和历史观。“实践”一义本来就包含在其“话语”这一术语之中,“话语”指的就是“实践的语言”。然而,“话语有其自身的作用规则,有其自身的形式,这些都不是语言规则和形式所能代替的。话语是一种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的语言使用……话语分析同社会生活的诸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医疗、教育、司法等等)”[29](P154)。因此,实践既是知识的对象,又是知识的形式,无远弗届的文本总是与无处不在的权力关联结合在话语行为事件的历史具体性之中。
作为话语实践的作品/文本是具有历史内涵的“话语事件”(discursive event),它是权力运行的场所,也是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发生交汇的场合,更是历史现实得以现形的所在。[30](P16)它负载着种种矛盾和价值,是对作家话语行为及其施为效果的概括,也是对读者话语行为及施为效果的概括。它并不只是在“说”什么的意义上来确定话语行为主体的价值,而主要是从话语“做”什么以及产生了什么效果的意义上来确定其价值。因此,“话语事件”观念消解了话语主体的意图作为“意义之源”的地位。事实上,“文学作品的写作和出版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或文化斗争。《失乐园》不仅(部分地)是弥尔顿的时代的产品或是‘关于’这种斗争的:它的写作和出版本身就是这些斗争的方面”[31](P56)。而这些话语行为事件的主体,包括作者和读者,则通过话语行为事件而参与到这些斗争之中。
既往的作品/文本理论,总是将文本话语之“所说”(saying)与“所做”(doing)分离并对立起来,视前者为作品/文本的“内部”而后者为“外部”。话语行为事件理论,则以其对“所说”与“所做”、记述性与施为性的统合,拆除了文本“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樊篱,消解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将记述话语和施为效果统统纳入话语行为事件的过程性之中。
既往的作品/文本理论,大多将创造性归结为作者或读者的一种能力,话语事件理论则将其归结为“事件”的特殊功能。格里芬指出:“一个事件的创造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事件从原有的前提中创造了自身。这个自我创造的侧面又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事件要接受、吸收来自过去的影响,并重建过去。这是事件的物理极。事件创造的第二个环节是它对可能性的回应。事件因而是从潜在性和现实性中创造了自身的。事件的这一侧面可称之为心理极,因为它是对理想性的回应,而不是对物理性的回应。由于这是对理想的可能性的回应,因而事件完全不是由它的过去决定的,虽说过去是其重要的条件。”“事件的创造性的另一方面,是它对未来的创造性的影响。一旦事件完成了它的自我创造行为,它对后继事件施加影响的历程就开始了。正如它把先前的事件作为自己的养料一样,现在它自己成了后继事件的养料。”[32](P66-67)“事件”总有其具体的时空方位,并向各个维度施加和接受影响。这样,事件就像一种行为,对于文学来说,事件就是话语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将文学作品创造为一个事件,它还可以通过“施为”而对后继的事件产生创造性影响。这种创造性或可称之为“小写的创造性”,它“是人类行动的必不可少的特性,因为,我们需要运用有限认知的、肉体的和物质的资源来应对动态的环境”[33](P8)。
与此同时,尽管作家作为文学话语行为事件的主体,其作为话语意义之源的优越地位被取缔了,然而,话语行为事件的观念却突显了行为过程的“具身性”。“具身认知”观念强调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认为认知是被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塑造出来的,身体的特殊细节造就了认知的特殊性。同时,它还强调“构成性”观念,“根据‘构成’主张,身体或世界是认知的一个构成成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对认知的因果作用的影响”[34](P5)。在这一观念视野中,认知不再被视为一种抽象符号的加工和操纵,而成为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活动。作为一种活动,认知、行动、知觉是紧密的联合体。
三、作品/文本作为历史文化事件
“事件论”的作品/文本观念,试图对文本主义和传统的历史主义进行会通融合,它不再在文学与历史、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设立等级秩序(如“背景”和“前景”等),而是将文本和历史放在事件的话语平台上等量齐观。进而言之,事件论的观念,也不再在文学学科和历史学科之间设立等级秩序(如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而是在文化的话语平台上,寻求其间的平等共存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有一个大致趋同的认识:文本是对符号设计的固定安排,它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这些文本被认为是那些在时间空间上与文本生产者相分离的人能够接近的。[35](P11)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样的文本观念深信不疑。然而,接受反应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将这一观念“问题化”了。我们知道,文本一旦形成,就与日常谈话的语境分离了,这使文本面临着被无限阅读的可能性,因此文本“构成了一种新的间距”,间距“对于作为书写的文本的现象具有建设性”[36](P143)。间距的不可抹杀性使人们再也无法回到文本创造者的思想、文本的原初指称和语境。当代理论克服间距的努力,使文本从两方面丧失了独立性而走向开放的“互文性”。[37](P125-127)在接受反应理论看来,由于带有不同“期待视野”的读者源源不断的阅读活动,文本在每一次“语境化”过程中都发生着变化,因此几乎不存在那种“符号设计的固定安排”,即便是伊瑟尔所说的大体稳定的“召唤结构”,也会在阅读活动中发生变异,这样,接受反应理论就部分地取消了作品的独立意义。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由于文本可以独自衍生和开拓自己的语境,因此,单个文本总是处在“解语境化”过程中,既没有什么“固定安排”,也非人们所能“接近”;与其说文本独立于时间和空间,毋宁说文本“占领”了时间和空间。如上两种理论在文本非确定性和开放性问题上殊途同归,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文本是一个动态存在,文本从未彻底独立于时间和空间。
尽管后结构主义视文本为“结构过程”,但这个过程只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也不是历史性的。文本的结构过程所形成的只是一个平面网络,无法包容真实历史过程。这种缺憾最终导致其走向了“文本主义”,它参照共时语言学模式,主要在文本层面(不管关涉多少文本)展开,未能突破文本的牢笼而指向文本之外的历史和现实。这种文本之间的穿行镶嵌和“秘响旁通”[38](P65),始终无法突破“文本”的牢笼,因而总是与真实的历史过程隔着一层。当然,在打通历史与文本之间的传统界限方面,文本主义也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探索,与之声气相通的文化诗学,即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了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的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时性的文本”[39](P156)。在最根本的文史关系上,“从将历史事实简单运用于文学文本的方法论,转变为对话语参与建构和保存权力结构的诸层面进行错综复杂的理解”[40](P81)。进而,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开辟出一种对话关联。
如果沿着文本的“无边界”和“非等级”开拓文本的历史维度,那么,法律、医学和刑事档案、逸闻逸事、旅行记录、民族志和人类学叙述以及文学文本都可以用来构筑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诗学”在这个维度上进行探索,“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都当成是历史话语的构成成分,而历史话语既处于文本之中又外在于文本。”在追寻文本、话语、权力和主体性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时,“并不确定因果关系的僵硬等级制”[41](P162)。仅止于此的话,那只是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建立了往返沟通的二维的文本网络,而“事件论”则力图在那种文本网络与历史现实之间画上连线,使其变成三维立体的网状结构,其基本方法就是将文本视为具有历史内容和文化含量的“事件”。这当然也是近30多年来“历史转向”运动的思想成果之一。批评家指出:“我们可归功于历史转向的最重要的成就,也许就是,它承认文本是一个事件。对新历史主义者及其他批评家来说,文学文本占据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所,各种历史力量在这些场所并通过这些场所而相互碰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得以上演。文本作为事件的观念让人们承认文本的暂时的具体性,承认处于特定历史情境的特定话语实践中的文本的确定的和临时的功能。它也承认文本是历史变迁过程的一部分,而且的确可以构成历史变化。这使批评家从将文本仅仅作为历史趋势的反映或拒绝的研究方法中转移出来,而引导他们探索蒙特洛斯所说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42](P203)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上,文本既是社会政治形成的产品,也是其功能性构成部分。文本作为事件,不只是历史进程的被动反映,而且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
作品/文本作为历史文化事件,它“不是由某个学科的普遍性的法则、价值标准所构成,而只是具有逆转偶然性的‘事件’”[43](P155)。文本事件的意义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内在规律,而在于使其作为事件成为可能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力量。它将对事件的关注引向对事件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的考察。作为“事件”的文本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实践活动。拿戏剧来说,作为事件的戏剧不仅指由文字所固定下来的戏剧脚本,而且指其演出和观看活动的整个流程,以及这个过程所牵动的社会规约和各种政治经济机制的运转。
文本作为历史文化事件的观念既区别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主义”,也区别于传统历史批评的“旧”历史主义;前者将文本看成脱离历史文化的语言编织,后者则将文本看成社会历史的镜像或文献记录。“事件”则既是与历史相交织的文本和实践,也是塑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事件论”填平了(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鸿沟。“旧唯物主义美学”设定文学前景“反映”历史背景,物质存在“决定”观念意识。“事件论”则另辟蹊径,它不否认物质性的历史语境即是一部作品文本得以诞生的基础,但它同时也看到作品文本不只是思想观念而同时拥有一个自身的物质性存在,如语言文字、装帧设计、媒介载体等,这些物质性的因素与包含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同时运作,并肩生产出作品文本的意义。这就将文本的思想观念与物质要素放在了同一个事件的操作平台上,也就打消了物质“背景”与“观念”前景之间的界限,这种路径可称之为“美学唯物主义”(aesthetic materialism)。[44](P10)
“文本事件论”打通“历史背景”与“文学前景”隔离的尝试,也在新兴的“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中得到了印证。面对一个认知图像,人们可以通过将自己的知觉从一个视点调换到另一个视点,从而翻转所看到的图像,完成“背景”与“前景”之间的转换,“将一部分视为轮廓而将另外的视为背景”[45](P14)。人们究竟应该将哪部分视为“背景”哪部分视为“前景”,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其实,背景与前景之间的设定,只是理论批评的权宜之计,在本质上,二者同属于历史文化事件。
四、作品/文本作为社会能量事件
作品/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核心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种形式主义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能量”概念的引入,开辟出解决争端的新路径,有助于“突破形式主义的静止模式”,突出“形式通常是关系性的,是文本与读者、文本与语境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46](P125)。
在当前语境中,“能量”主要是一个物理学概念,一般指物质做功的能力。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能量只能转化,人类通过掌握和运用它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美国新进化论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较早提出文化演进的“能量说”,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三个层面,认为“技术层面处于底层,哲学层面则在顶端,居中的是社会学层面”[47](P361)。能量贯通于三个层面,而流通于社会学层面的能量,或可称为“社会能量”。但他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提出并阐发这一术语的,是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他认为“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是一切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而文学文本则既是社会能量流通的场所,是社会能量增强、转换或疏散的场合,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得以上演的舞台。“社会能量”与“事件”相辅相成:事件是社会能量显形的场所,而社会能量则是事件背后的推动力量。
据格林布拉特考证,人们为了解释莎士比亚剧作缘何拥有“强制性力量”的问题,从古希腊修辞学中撷取energia一词(这个词也是英语中energy的本源),来描述修辞语言的那种“摇荡性情的力量”。从词源学上看,该术语的重心并不在其物理学意义,而在其修辞学意义。因此,这个词的意义主要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可见,energy这个术语,在根源上本来更接近怀特所说的“社会系统”的能量,原初就与语言修辞等文艺问题相关,并非文学批评借自现代物理学科的“比喻”,因而需要做切实的探究。
然而,“社会能量”概念却殊难界定,格林布拉特在提出这个术语之后,很快就遭遇了定义之难。他说:“这个术语包含可测量的东西,但无法提供一个便捷可靠的公式,用来剥离出一个固定的量化指标。人们只能从社会能量的效果中间接识别出来:它出现在词语的、听觉的和视觉的特定踪迹之力量中,能够产生、塑造和组织集体的身心经验。”[48](P6)它是某种只能从其效果中感受到的“力”,贯通于各种“踪迹”之中,与快乐和趣味的可重复的形式相联系,与引起忧虑、痛苦、恐惧、心跳、怜悯、欢笑、紧张、慰藉和惊叹的力量相关联。勉为其难的正面界定是:社会能量是“权力、超凡魅力、性的激动、集体梦想、惊叹、欲望、忧虑、宗教敬畏、自由流动的强烈体验”[49](P19)。它是流通于各种相互关联的事件经验中的力量。
社会能量作为一种“力”,相较于怀特所说的“哲学层面”或“思想意识系统”的能量,是“下倾”并沉降到具体社会生活层面的力,在这个层面,一切都作为一个个“事件”而到来,并非以真理或知识系统的形式而显现。社会能量是一些分散在踪迹之中的流动的情感能量或力量碎片,这些社会经验是零散的、粗朴的和原生的,是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这种经验并未经过沉淀或蒸馏,并不具有“更明显更直接的可利用性”[50](P133-134)。
这种能量碎片拒绝单一化、连贯化、系统化和整体化,即使在它流通到艺术领域之时,也无法被“整一化”。
在戏剧表演中,借助并通过舞台而流通的社会能量并非单一连贯的整体系统,而是局部的、零散的和彼此冲突的。各种要素之间交叠、分离和重组,相互对立。特定的社会实践被舞台放大,另外的则被缩小、提升和疏散。因此,对戏剧文本的阐释,最终就必须落实到那些独特的、活态的、具体的社会能量。这种能量才是基础性的,它生产出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这种将社会能量落实到事件的方法,与福柯的“事件化”异曲同工,只是“社会能量”较之福柯“权力”概念,“使权力不再是一个中心化的范畴,而成为由流通中的社会能量构成的众多片断”[51](P180)。这也说明,文艺与社会相互塑型,既不是某种先在的、可定义的社会生活“生产了”相应的文艺,也不是某个单一的集权化的“权力”、“世界图景”或意识形态“决定”了文艺,而是不仅流通于社会现实的能量构成着文艺,而且流通于文艺中的社会能量也参与了社会生活自身的构成过程。
因而,社会能量既是“被”社会生产出的东西,也是生产社会的集体经验的东西,它帮助生产出那个产生社会能量的社会;社会能量与社会相互生产,作为社会能量的文艺也与社会彼此构成。
社会能量作为一种流通中的“力”,相较于纯然“个人的”心理能量,又往往是超出个体界限的“社会的”能量,因其“流通性”而突破了个体边界,因而不只是个体情绪意义上的“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52],或者反之,一种低落消沉、消极悲观的动力或情感。社会能量一旦进入审美领域,它就必须满足最小限度的范围或“射程”,也就是说,它必须足以超出单个主体而通达特定的群体。有些时候,它能达到十分巨大的范围,引发社会阶层不同、观念信仰歧义的人群悲泣欢笑,体验忧喜交加苦乐相杂的混合情感。社会能量的审美形式通常必须具备最小限度的适应性,足以使这些形式历经社会环境的沧桑巨变和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而留存下来,而那些未经审美锻造的日常的社会能量话语则会因之而湮没无闻。在从其初始环境旅行到新时空的过程中,大多数集体表达都会遭到废弃,而经过艺术作品编码的社会能量则会持续千百年地制造生活幻想。
这种现象足以说明,文艺和审美中的社会能量得到了扩充和形式化,可以为不同的主体重复利用;也得到了放大和强化,能够冲破特定个体的界限而到达范围广大的社会群体;而且还拥有某种在新的时空语境中产生影响的潜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穿行回响。因此,个体能量必须在流通中与范围更大的社会群体能量相摩相荡,才能成为更有冲劲、也更具流通力的社会能量;个体意义上的经验事件,也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能量事件。在此过程中,文艺审美通常发挥着重要的能量流通和能量转换作用。
在文艺审美中,戏剧因其具有更突出的“表演性”而成为社会能量及其流通过程的集中体现。“每一部戏剧,通过各自的手段,将社会能量的负荷带上舞台;舞台修正这些能量,又将其返回给观众。”[53](P14)借助舞台并通过舞台表演,特定的社会实践被放大,另外的则被缩小、提升和疏散。通过舞台表演,社会能量的流通“构成一个螺旋而不是一个圆圈”[54](P184)。在戏剧表演中,社会实践得到转化和再造,又重新流通到非戏剧世界。这种流通中包含着变形和重塑,社会实践和戏剧表达在交叉互动的关联中持续改变。戏剧事件包含着多种多样的能量交换,戏剧通过交换而在新的情境获得新的力量。这种交换通常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共时性上,社会能量冲破文化实践之间的界限而在不同文化实践之间产生“共鸣”[55](P178);历时性上,社会能量通过作品/文本而从特定时代走向另一时代,并因之而发挥其历史作用。因此,相关的研究就要“追问集体的信仰和经验如何形成?如何从一种媒介转向另一媒介?如何凝聚于易处理的审美形式?如何供人消费?我们可以考察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与其他相邻表达形式之间的界限是如何标示的?我们试图确定这些特别标示出来的区域是如何被赋予权力,使其或提供愉悦、或激发兴趣、或产生忧虑的?”[56](P5)而这种研究,即是将文本事件沉降到社会能量层面,对其流通交换过程的揭示。
总之,社会能量流通穿行于社会历史与文本事件之中,使二者连通并相互生产,不仅社会历史生产文艺作品,而且文艺文本也“生产”社会历史并成为塑造社会的实际力量。
五、结语
“作品/文本/事件”形成了一种“三元辩证”关联。“事件”作为特殊空间,是有别于“作品空间”和“文本空间”的“第三空间”,它具有“元空间”的气质。事件空间是文艺成品之“内”(作品空间)与“外”(文本空间)得以界分的第三空间,它是一个不断生产“内”与“外”的“元过程”(metaprocess)和“活态空间”(lived space)。[57]事件空间彰显了前景与背景、内部与外部、所说与所做、文本与实践之间的连通性。马克思所希冀的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要能解决“改变世界”的问题。文学事件论强调,作为事件的文学不仅“解释世界”,它同时也在参与历史并成为实际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进而以特定方式“改变世界”。面对当前的文艺现实,卡勒发现,电子文本发展的一个结果是,“文学最终被认为更像是一个事件而非一个固定的文本……这样,表演研究或许就要在文学研究中具有某种新的重要性,因为它不再只是将文本当做是需要阐释的符号,而是更将其看做是各种表演,这些表演的可能性条件和成功的条件可以被明晰地阐发出来。那么,在电子时代里,对事件和评价的更加关注将会导致文学美学的转变吗?”[58]作为对电子时代文艺现实的回应,作为21世纪文艺美学转变的一部分,文学事件论庶几近之?
[1][3] 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5)。
[2] Greenblatt,S.,and G.Gunn.(eds.).RedrawingtheBoundaries.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1992.
[4] 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28]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 Slavoj Zizek.TheFrightofRealTears:KrzysztofKieslowskibetweenTheoryandPost-Theory.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1.
[7] 高小康:《非文本诗学: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载《文学评论》,2008(6)。
[8] 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研究文学研究》,载《文艺研究》,1993(3)。
[9]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1][12]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3] 高宣扬:《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14] 彼得·霍尔沃德:《代序: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载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 怀特海:《自然的概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6] 广松涉:《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7] 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18][25]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19]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20] 叶秀山:《美的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21][22] Terry Eagleton.TheEventofLiteratur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23] J.Hillis Miller.On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2002.
[24] 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6][36] 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7] Claire Colebrook.NewLiteraryHistori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29][43]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0] H.Veeser(ed.).TheNew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89.
[31][35] Jeremy Hawthorn.CunningPassages:NewHistoricism,CulturalMaterialismandMaxismintheContemporaryLiteraryDebate.London:Arnold,1996.
[32]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宗教》,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33] Beth Preston.APhilosophyofMaterialCulture:Action,Function,andMind.New York:Routledge,2013.
[34] 夏皮罗:《具身认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37] John Frow.MarxismandLiteraryHistory.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6.
[38] 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39]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0][42] John Brannigan.NewHistoricismandCulturalMaterialis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
[41] 伽勒赫:《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44] Paul Gilmore.AestheticMaterialism:ElectricityandAmericanRomantic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45] Peter Stockwell.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2.
[46] Jeremy Hawthorn.AGlossaryof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London:Arnold,2000.
[47] 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48][49][53][56] 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Negotiations:theCirculationofSocialEnergyinRenaissanceEngla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50] Raymond 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51][54] Brook Thomas.TheNewHistoricismAndOtherOld-fashionedTop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52] 理查德·怀斯曼:《正能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55] Jurgen Pieters(ed.).CriticalSelf-fashioning:StephenGreenblattandtheNewHistoricism.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1999.
[57] 张进:《论“活态文化”与“第三空间”》,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58] 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4)。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Problem Domain of Marxism
(责任编辑 张 静)
ZHANG Jin
(Center for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Guangdong 510420)
Work/text,as an axial concept of poetics in the 20thcentury,has been loaded with enormous theoretical burden and meanwhile has become the touchstone of various literary ideas and critical approaches.“Event” has come to be an alternative term that constructs a trialectics of work/text/event since the 21stcentury.The philosophy of event considers work/text as an event of discursive performance,an event of historical culture,and an event of social energy,which highlight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ubjects,the historicity of literary action,and the connectivity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event itself.Those schol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rxist theory about aesthetics and history,literature and society,participated and reshaped the conception of event.Such a phenomenon may be regarded as a return and reproduc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Literature as event not only “interprets the world” and becomes the foreground of the history and society,but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shaping of history and becomes a par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Therefore,literature as event “changes the world” in its own way.
the event of literature;connectivity;materiality;embodiment;historicit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15FZW027);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项目(GWIP-YJ-2014-03)
张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云山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