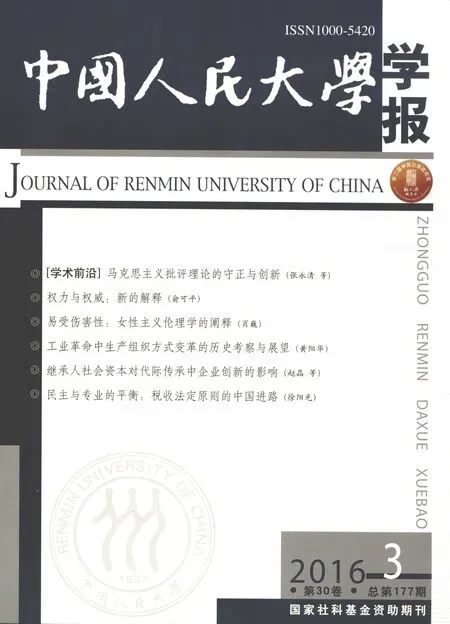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
胡亚敏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
胡亚敏
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需要对“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作重新审视和辩证研究。首先,对“民族”概念加以考辨,厘清不同术语的边界;其次,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不同声音,提炼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再次,为“民族”概念正名,“民族”不等于闭关自守,也不是回到过去,更不是用集体压制个人。基于此,赋予中国形态的民族观以新的理论特质: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民族与人民同构,中国形态民族维度的视域即文化身份和价值尺度。总而言之,对“民族”的重新阐释和民族之维的提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特质。
民族;民族之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逐一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民族”这个维度却长期被忽略,沦为一个被社会、文化、政治遮蔽的概念①“民族”概念历来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中多有讨论,且争论不断,本文主要指中国文学批评中缺乏明确的民族维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和评价有关。“民族”这个概念看似不言自明,实则有很多陷阱②吉尔·德拉诺万说:“民族是比国家或市场更为难以把握的实体,其难以把握尤其源于看似自然实则难解。”参见德拉诺万:《民族与民族主义》,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且长期以来评价不一、毁誉参半。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有必要对“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作重新审视和辩证研究。
就中国文学现状而言,尽管“民族”是一个颇为纠结的概念,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民族”因素一直没有缺席过。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民族意识勃发的土壤,民族情怀已经深深镌刻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之中。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启蒙和救亡的主题表达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文学批评领域围绕民族问题的论争也绵延不断,中西体用之争、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均与“民族”概念相关。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遭遇的诸多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民族”及相关问题。事实上,若离开“民族”这个因素,我们已经很难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了。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民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再次凸显出来,没有独立的民族意识已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浪潮,警惕文化和语言被殖民,已成为民族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民族及其相关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沿问题和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文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均简称为“中国形态”。引进民族维度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须。
一、“民族”概念辨析
在汉语运用中,由于“民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翻译以及“民族”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明确区分,故容易造成用法上的混乱。要确立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首先需要对“民族”概念加以考辨,厘清不同术语的边界。
(一)Nation及其相关概念
汉语的“民族”一词译自英文Nation,Nation由拉丁文“natio”(出生、出身)衍生而来。*关于英语Nation与中文“民族”的词源考辨已有诸多先行研究,这里主要阐述民族及其相关概念的边界。Nation在西方主要指现代民族,是现代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孕育于中世纪,而工业革命、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等则是促成民族这一新型人类组织形式的推动力。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揭示了西方现代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语族一旦划分(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易北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1](P219)
尽管用汉语“民族”对应英文Nation已约定俗成,但汉语“民族”一词又可指代特定的族群,因此需要在进一步比较相关英文概念的基础上限定汉语“民族”的用法。作为现代民族的Nation与英文中的Race(种族)、Ethnicity(族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Race(种族)主要指人的生理特征,如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它在范围上大于Nation,而其研究指向趋于遗传学。Ethnicity(族群)主要源自古代原始社会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这个“族”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是在家庭、部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制度的基础”[2](P257)。Ethnicity内含文化传承,可视为民族的雏形。当今的Ethnicity主要指民族国家中的不同族裔,如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族裔可对应于Ethnicity,这样就可将“民族”与“族群”区分开来。不过,为了更贴近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建议直接音译为Minzu更为合适。*目前中央民族大学已译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而国内大多数民族院校校名英译仍为Nation或Nationalities,这种译法显然已不合适。
(二)Nation与中华民族
与Nation作为现代民族的含义出现在中世纪以后相比,“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产生更晚。古汉语中的“族”含矢,有保卫之意,同时古代中国早期“族”的观念强调的是正统,主要用于与狄、蛮相区别。古人眼中只有诸如“天下”“华夏”、“中土”、“炎黄子孙”等,现代民族意识是19世纪中叶传统族类意识面临西方冲击下转换变化的结果。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3](P11-12)。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展示出中国文化空间概念的延伸,近代的中国民族逐步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使用了“中华”概念:“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4](P1)如果从梁启超这篇文章算起,“中华民族”的观念问世不过百余年。此后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些历史学者试图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国家为立论点,梳理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融合的历史脉络,重建中华民族本土源流的历史体系。这种研究范式的早期例子以王桐龄撰写的《中国民族史》系列文章为代表*关于近代主体精英的历史编纂与民族(国家)书写,可参见冯建勇:《想象的民族(国家)与谁的想象——民国时期边疆民族问题话语的双重表述》,载《领导者》,2015(8)。,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日益清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空前高涨,构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为这一时代的共识,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可以说,近代中国出现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才是一个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概念,西方Nation对应的正是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
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概念的特定指向为“中华民族”而不是汉语中“民族”的其他含义,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研究对象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产品及相关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民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著述丰富复杂*参见华辛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概述》,载《世界民族》,1998(2)。这里主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著述中的相关问题,略去两人的不同之处。,人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理解和阐释上出现了不同声音,这是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需要澄清的又一问题。以往人们一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就想到《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解放学说是主张国际主义的,对民族问题持否定态度。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持怀疑和消极态度。*安德森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导论》,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维斯特里奇在为一本书撰写的述评中指出,“十九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包括在宗教、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群体意识,一直持一种过度轻视和否定的态度。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会败坏社会主义的前途。列宁和斯大林则只是意识到民族主义的策略性用途,普适性的阶级革命仍然是他们进行政治分析和想象的范畴。”参见孟悦:《〈泰晤士评论〉: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读书》,1998(6)。笔者也曾请教过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他表示未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不对其作进一步解读。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问题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并有突出的成就,不少中外学者对此已做过专门研究。这里为回应有关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非议,仅扼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中的相关部分,由此了解和把握经典作家研究民族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一)阶级问题主导民族问题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民族问题时多数情况下是与阶级联系起来的,认为阶级问题主导民族问题,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不过,任何问题都有特定语境,上面提到的“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即是在回答“共产党人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的责难这一特殊情况下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工人阶级没有特殊利益:“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5](P666)由此,马克思将人类解放的目光投向工人阶级,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6](P314)。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问题的提出会削弱阶级斗争,因为统治者往往利用民族问题掩饰矛盾,“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7](P316),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永世长存。并且他们还认为有些民族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例如泛斯拉夫人组成联盟,反对奥地利的革命者,“因此,它显然是反动的”[8](P200)。
(二)民族与阶级关系的复杂性
在研究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时,马克思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做出了有远见的分析。基于被压迫者的立场,马克思认为有些民族主义是应该肯定的,如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中爱尔兰的民族反抗就具有合理因素[9](P272)。特别是马克思还天才地看到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当爱尔兰受到大不列颠奴役时:“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他们把英国工人看做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10](P484)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不仅指出了民族和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而且看到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这一全球化时代日益尖锐的问题。
(三)民族沙文主义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对犹太民族和德国民族的批评中看出。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犹太人妄自尊大的民族观予以了批判:“犹太人对待国家也只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即把国家看成一种异己的东西,把自己想像中的民族跟现实的民族对立起来……以为自己有权从人类分离出来,决不参加历史运动,期待着一种同人的一般未来毫无共同点的未来,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员,犹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11](P164)针对那种认为德意志民族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观点,恩格斯嘲讽道,他们“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它正是通过这种漫画化的、基督教日耳曼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12](P354)。恩格斯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13](P314)他对某个民族想领导世界的幻想做出断言:“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4](P494)这一口号为当今反对霸权提供了理论的先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民族与国际主义是辩证的统一。作为世界格局的一部分,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是国际主义的前提,恩格斯明确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15](P87)并且,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就是这样一种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即各个民族的联合,它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即要求所有的人都摒弃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观念,视整个人类为自己的同胞,通过直接归属一个单一的联邦国家,摆脱由国境、人种歧视等引起的不必要的战争,达到永久性的和平。有根本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是建构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基石,这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有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民族问题上所运用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为今天研究民族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当代意义。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中有些观点需要扬弃(例如关于殖民问题的看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批判性和它的辩证思维能力将使它充满自我更新的活力。
三、为“民族”概念正名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重新观照“民族”这个概念,是建构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中,“民族”既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又是一个屡遭误解的概念,因此有必要“辨彰清浊”,以正视听。
(一)民族不是闭关自守
一提到“民族”,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独立和自主,这是民族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又恰恰是在与全球的“他者”对比和参照中确立的,“民族”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之中。中国“民族”概念的问世更不是与世隔绝的产物,它诞生于睁开眼看世界的焦虑中。中国仁人志士的民族意识正是在饱受西方列强屈辱后被激发出来的,他们所追求的民族自强并不是与这个世界对峙,而是希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本的流动和互联网的通达,世界已经连在一起,任何民族想置身于世外几无可能。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有些甚至还很尖锐,但作为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抗与依赖并存,许多问题已不可能由某个国家某个政府独自解决了。就民族的发展而言,开放已经成为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条件。
(二)民族不是回到过去
“民族”也不能与复古联系起来。有些人一提到民族复兴,就想到要发掘和保存传统技艺,甚或穿戴传统服饰,这一做法是对民族振兴的误解。民族的发展固然有历史之基,民族文化中固然有精华的东西,但毕竟时过境迁,周而复始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现代民族的兴盛在承继传统的同时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产生断裂,只有摒弃那些陈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才能轻装前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形态的“民族”所强调的不是过去和传统,而是着眼于当今和未来。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不再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评判我们,通过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这时历史法庭的动力出乎意料和辩证地被颠倒过来:不是我们评判过去,而是过去(甚至包括离我们自己的生产模式最近的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将不是的一切。”[16](P190-191)同样,中国形态的“民族”观也不是把过去作为古董保存下来,更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历史留存的东西,而是把过去视为对当代的参照,促使我们审视现在的生活。
(三)民族不是集体对个人的压制
民族与生俱来的集体性是其屡遭质疑的又一问题。民族与个人的关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国家危亡之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民族利益将高于个人利益。不过,在平时,有些宏大叙事造成对个体的压制甚至伤害则是需要反省和警惕的。在建构中国形态的过程中,“民族”概念里的集体和个人并非水火不相容,更不是排斥或压制个人,而应该呈互相支撑之势。一方面,个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发展和实现的权利是现代民族的基本条件,每个人的奋斗正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个人甚至可以为民族赴汤蹈火乃至牺牲生命。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观
基于时代和国情的差异,不同国度对“民族”的理解和实践不尽相同甚或大异其趣。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民族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在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时代的发展,中国形态将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赋予“民族”以新的理论特质,对“民族”的内涵做出新的探索和回答。
(一)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写过一本书,叫《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在书中他主要谈的是民族主义的问题,不过却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意义上的团体”[17](P6)。安德森是在面临民族定义困境的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的,也许安德森的“想象”并不是说民族这一共同体是虚构的,而是指这一共同体是凭借集体的认同的力量建构的。尽管他在书中具体阐述了民族起初如何被想象以及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模塑和改造的过程,也谈到了想象得以产生的先决历史条件,但他强调的是想象是民族国家得以创制的方式和渠道,“民族”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或者说是被叙述的文本。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历史的而不是思辨的对象。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尽管人们可以基于不同立场和观点书写不同的民族叙事,但无论怎样想象民族的起源和创制,该民族的基因始终存在,血统、语言、疆域、风俗、宗教等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同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构成了不同的民族记忆,这种记忆保存在神话、民间故事与传说以及历史文献乃至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这些神话和传说虽然是叙述,但也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基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人们的生活记录。因此,民族体现为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群体认同的社会关系,我们没有凭空想象民族的自由,能够做的是我们如何言说这一历史现象。
民族的历史性还表现为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群体认同是逐步实现的,而不是一蹴而就,并且既然民族有它的兴起,那么也必然会有它的式微。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移民遍及世界各地,未来的民族必然带有一定的混杂性。不过,无论将来民族消亡与否,相信多元文化仍会长期存在。
(二)民族的核心是文化
关于民族的基本要素,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对“民族”的特征作了系统归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8](P28-29)这一定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应该说,定义中的这些要素对民族的内涵和外延起到了规范和限定的作用,不过,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语言、人种乃至经济生活都不足于成为区分民族的根本尺度*鉴于意大利存在多种方言,葛兰西认为:“语言统一问题只是民族统一问题外在的、并非绝对不可缺少的表现形式之一,至少说,它是后果,而不是原因。”参见葛兰西:《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载葛兰西:《论文学》,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今天几乎所有自认的民族——与民族国家——都拥有‘民族的印刷语言’,但是却有很多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并且,在其他的一些民族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绘画或书面上使用‘民族’的语言。”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那么,在这些要素中,哪一种要素更为根本呢?早在19世纪,就有人提出:“区分民族的标准既非种族亦非语言。当人们是一个有相同的思想、利益、情感、回忆和希望的群体时,他们就会从内心里感到自己同属一个民族。”[19](P204)这个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内在联系就是文化,就精神层面而言,文化的核心是其历史和价值观。文化作为民族的象征和纽带,表现为群体的一整套共有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在其成员中起着沟通思想、交流情感和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存在异质性,凝聚与拒斥、向心与离心、认同与异己,但作为长期积淀的结晶,每个民族毕竟拥有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主导文化,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与中国的故宫就迥然相异,这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表征。文化像基因一样融化于其成员的血液中,且代代相传。在全球化时代,那些游走于不同国度的人之所以会出现身份焦虑,实质上是文化冲突的焦虑。可以说,文化认同是民族赖以存在的根基,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民族记忆,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
(三)民族与人民的同构
随着时代和语境的变换,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不再囿于阶级的框架,而是将民族与人民联系起来。中国形态的民族与人民同构的理念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在抗日战争期间,文艺的民族化就是与大众化结伴而行的,而这种结合实际上体现了民族和人民的统一。历史进入21世纪,阶级阵营也远不像19世纪中叶马克思那个时代那样清楚和对立,民族与人民同构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如今不仅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设想的哑铃型的阶级结构被橄榄型取代,而且工人阶级这个定义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阶级界限的模糊和变动不居已成为一种常态。特别是与全球化并行的民族意识的高涨,身份研究被置于突出位置,用阶级的集合体——“人民”来代替阶级,实现“民族”与“人民”的同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提出过“民族—人民的”这个概念,他主要是针对意大利读者热衷外国通俗小说、冷淡本国当代作品这一现象而有感而发的,他在《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一文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缘由。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不仅把民族和人民视为语义相似的概念,而且把两者联系起来,认为对人民的“教育和培养”是民族发展的前提[20](P46-54)。不过,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思想仅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而中国形态的民族与人民同构则已化为革命实践。
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强调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为一体,民族与人民同构的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利益主导民族利益的观点的突破,也构成了对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超越。在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中,人民是民族的主体,人民的解放就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就是民族发展的方向。民族与人民的同构这一民族观成为中国形态的一个鲜明的理论特质。
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维度
毋庸讳言,提出建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显然是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民族之维持有特定的文化立场,它强调文学要拥有自身的民族背景,并主张理性地看待中外关系。同时,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又是一种价值尺度,它不仅仅像后殖民批评那样保持对殖民文化的警惕和批判,而是将“民族”置于突出位置,把民族认同和民族振兴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尺度,并希望通过文学与民族精神的互塑实现民族振兴。
(一)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
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寻找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是民族之维的重要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这个世界处于何种位置?”这些正是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要探寻和回答的问题。世界文坛需要多种声音,而只有不同民族背景学者的加入才能使多声部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如何为本民族文学和批评争得更多的话语权也是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的跟踪和研究中,我们发现,西方文学批评的著述包括教科书很少提及中国的文学和批评,除极少数西方学者外,大部分西方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中国,因此扭转中国文学批评被抑制或被边缘化的现象是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倡导文学作品展示民族个性的同时,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也不是一味地追求特色,而是努力发现文学所内含的普遍价值,因为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21](P44)别林斯基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天才到处被一切人所承认,而不仅为他的本国人所承认,民族性应该是首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条件。除了是民族的之外,他还得同时是世界的,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民族性必须是人类思想之无形的精神世界底形式、骨干、肉体、面貌和个性。”[22](P93)优秀的作品和批评必然包孕多重声音,我们在其间不仅听到个人的诉说,而且还有民族的呐喊,并能感受人类声音的回响。“民族之国际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的必然性。”[23](P120)一个民族的文学若没有走出国门的雄心,不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是很难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创造既体现本民族个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和批评是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追求的目标,同时它也体现出中国文学批评的自信。
(二)文学与民族精神
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同时也是一种批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民族认同和民族振兴是民族之维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尺度。弘扬民族精神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文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体现,因为文学艺术代表着一个民族“对生活和人的观念”(葛兰西语)。一些文学巨匠正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一提到英国人们就自然想到莎士比亚,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的太阳”,被詹姆逊称为“民族寓言”的鲁迅作品也深刻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特质,这些伟大的作家被誉为“民族之魂”。
民族意识是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而民族认同首先又体现为情感认同。很多优秀的作品表达出深厚的民族情感,鲁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和激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读后令人动容。即使有些描写个人欲望和内心冲突的小说,如郁达夫的《沉沦》,“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其内在的情思仍与民族的命运相连。当然,民族认同不等于对民族文化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一些文学作品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同样是对民族精神的维护。马克思曾说:“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24](P6-7)
不过,当今文学创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民族情感并没有随着国力的增长而加强,反而有所淡薄和削弱。个别作品专注于个人感官享受和欲望表达,而对当下中国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缺乏热情和思考;有些作品一味地展示民族性中丑陋的一面,用人物的愚钝和苦难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曾对大众文化的沉沦发出警示,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同样需要有一种社会的担当和责任,应对有些文学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剖析和批判。
民族认同是民族振兴的前提,从更高的标准看,文学批评的民族之维还应该研究“文学中的民族性应当是什么”的问题,鼓励人们通过文学作品展示出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好莱坞大片中,不难瞥见美国的价值观念,如《蜘蛛侠》中的经典台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即是。,运用文学的力量激发人们的民族情感,发挥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引领和建构作用。另外,健康的民族意识将为文学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撑,由此实现文学与民族精神的互塑,共同营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总之,对“民族”的重新阐释和民族之维的提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特质。关于民族之维的理论建构和实际运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沉下心来思考和研究,我辈将继续努力。
[1]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6),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文集7),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1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波兰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1月30日》,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批判的通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6]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8]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9] 吉尔·德拉诺万:《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0] 葛兰西:《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载葛兰西:《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1] 胡亚敏:《论差异性研究》,载《外国文学研究》,2012(4)。
[22] 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第五篇》,载《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23] 冯雪峰:《民族性与民族形式》,载徐遒翔编:《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 静)
On the National Dimension of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HU Ya-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
To construct the national dimension of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and make a dialectical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 and related issues.The thesis starts with the clarification of three questions:First of all,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pt “nation” should correspond to the Chinese nation,and defines the specific orientation of the concept “nation” in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 differentiating and analyzing “nation” and related concepts;secondly,in view of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studies of Marxist national theory,it briefly sorts out and refines views and methods of Marx and Engels about national theory;thirdly,it rectifies the concept of “nation” by arguing that it doesn’t mean turning inward,nor going back into the past,nor suppressing individuals by the collective.Then the thesis elaborates on national views of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Firstly,nation is a historical concept,the core of which lies in culture,and nation is isomorphic with people.Furthermore,it specifies the particular horizon of national dimension of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namely cultural identity and measure of value.In short,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nation” and the proposition for national dimension constitut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traits of Chinese form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at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theories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nation;national dimension;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Chinese for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
胡亚敏: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