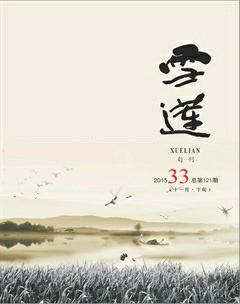浅析邦达列夫小说《选择》中两种声音的对话性
邢飞卓
【摘要】不同人生遭遇演绎着不同故事,不同人生选择决定着不同命运。20世纪苏联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在长篇小说《选择》中对主人公的命运因选择而不同的故事中展现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对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不同的选择,异样的命运所形成两种声音的对话性进行浅析。
【关键词】选择;命运;对话
“整个一生中——人都在无休止地进行选择。每天,从早晨选择早饭和领带直到选择如何度过整个夜晚——同哪个女人见面,上哪儿去,怎样消磨这该死的时间——都在进行选择。一切都在选择之后才干,爱情,战争,谋杀。近年来我常想,是什么力量支配我们一生的选择。谁知道,死后是否还有选择?地狱?天堂?幻梦?天涯之外还有什么呢?”
“在所有成千上万种生活意义和选择之中,只有一个选择是伟大和永恒的……”
邦达列夫的小说中“选择”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而“选择”一词本身又是个抽象的人生哲理命题。作家用“选择”给小说命名,同时也寄寓着其本人对人生、对世界的深沉思考和对人性、同情、理解之爱的热切呼唤。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而人的性格又具有流动性,正是这样的流动性才促成人多变的选择,选择的多变性又演绎出各种不同结局的命运。
巴赫金认为,文学作品的含义并非仅由经济、文化、语言因素决定。文学作品是多个声音对话、交流的场所,每种声音代表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文学作品是多种声音的结合体。
巴赫金的兴趣更集中于小说,他认为小说是由各种相对抗的声音所组成,在各种声音的交流及与作者声音的交流中小说获得最终意义。巴赫金把话语当作叙事作品构成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小说文本是各种声音、各种社会观点、各种社会价值观的混合体。这些声音、观点、价值观彼此互不调和,构成作品的开放性。开放性的对话形式使主人公得以同自身对话,同其他主人公对话,发现彼此的关联与区别。
一、社会环境、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各种社会观点的差异形成两种声音的对话
对于五十开外的游子,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实现多年来心中的夙愿——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亲人、朋友身旁。可当主人公伊利亚在威尼斯与老友重逢时,在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政治气候支配下,过去的老友变得貌合神离,各怀戒心的两个世界、两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不同信仰,不同的思想感情使这次会面给两个人都留下了痛苦回忆。不久后伊利亚以外国旅游者身份重返故乡,可祖国视他为外国人,他探望孤独的老母亲,但母亲不能原谅他的无情,他同瓦西里耶夫会面也再没有当年那种推心置腹的交淡了。此时此刻,他的头脑里开始像电影一样回放起当年无话不谈,形影不离的好友;当年爱着他的玛莎和疼爱他的母亲和那可爱的俄罗斯的模样。再想到那些个思念祖国,想念亲人,却无法成行的魂牵梦绕的日日夜夜……当眼前的一切与他心里刻下的美好回忆和所期盼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当这里曾经使他感到亲切、熟悉、珍视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他的心该承受怎样的疼痛?若不是二战刚结束后苏联政府对当过俘虏的官兵的严酷政策和立场,使他不敢回国;若不是要继续生存就只能选择生活在与他业已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相悖的西欧德国,过着与从前完全断裂的身不由己的生活,他的人生轨迹又会转向哪边?或许他自责,但别无选择。邦达列夫曾说:幸福就是对幸福的等待。然而伊利亚多年在异国他乡等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在千方百计与祖国,亲友团聚的时刻,反而让他觉得这幸福似乎又轻的太过于沉重,那颗装着满满幸福、满满期待的心一下子被掏空。是否眼前的一切顿时使这个年迈的游子感到绝望,是生?是死?这个1943年他曾面临的选择难题又重新出现。对于一个人来说,失去祖国和母亲的爱,失去生活的理想是多么可怕……可是,“浪子应该回到神圣的故土吗?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浪漫主义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哪里摆着佳肴的宴席,哪里就放着棺材!”被母亲不理解赶出家门的伊利亚不禁忧郁而讽刺地说。他的心痛开始蔓延,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生活使他的精神渐渐走向崩溃边缘。就像春蚕在吃桑叶,自己的身体正像桑叶一样慢慢没了血肉,一如此时的伊利亚对生活、生命的期望慢慢被吞噬,最终他选择了向生活,向整个世界妥协……
二、自主选择与别无选择的无奈——人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又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形成对话
时光渐逝,生活环境改变,尽管伊利亚变得早已不像从前,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与其后来自身的某些悲观阴郁的性格也是不无关系的。但伊利亚的命运令人同情,他不幸的一生展示了人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可悲,也见证了不同选择造就不同命运的结局。有人说,城市里有多少扇窗,就有多少种无奈,就有多少种无奈的选择,伊利亚的无奈必是其一。当时的客观环境迫使他去死,他选择了生;如今本可以朋友重逢,家人团聚,安享生活,他却选择了死。伊利亚的悲剧是发人深思的,正如作者曾对出演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演员们所说:“不管人们对选择作何解释,选择——这永远是一个难题,因为人们的本质不是单一的。”人生充满变数,选择本身就充满着多种矛盾性和不可预见性。人生的选择有时就像赌注,而对错在生活中,在这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多少人能够清楚的划开这条界线?所谓生活不能被安排,也无法按照常理出牌,或许在瓦西里耶夫看来,伊利亚悲剧的人生正是他错位的选择所造成的。可反过来想,伊利亚心中那份美好的期盼和对生活的渴望又何尝不是他最怀念的祖国,心心念念的亲人戚友给夺走的?对此,我们不禁意识到共融、理解、关怀才是对彼此最好的救赎。
三、瓦西里耶夫自身的纠结,内心的矛盾表现出的两种声音的对话
瓦西里耶夫始终以一个内心情感丰富而敏锐,善于思考的形象出现的。当得知伊利亚病情严重,他希望自己能够为他做些什么的;当伊利亚请求他陪同去探望伊利亚的母亲时,他更是一边满足伊利亚的意愿给拉伊萨·米海洛夫娜打电话,一边“责备自己不恰当地,违心地参与了这场为了使人相信而臆想出来的逢场作戏”的欺骗。尽管瓦西里耶夫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伊利亚是个胆小鬼和十足的坏蛋,却又不能理解和原谅这位朋友所选择的道路。因为他始终代表着与伊利亚对立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另一种信仰,另一种生活方式和另一种命运。然而伊利亚的自杀又给他带来不小的影响,他时常感到不安在梦中醒来,然后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大自然的真正本质?有时他甚至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想痛哭一场,却没有眼泪,但又感到痛苦难忍。因为他知道“伊利亚深信的也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上帝的意志,而是宇宙中的最高威力,宇宙的理智能力……”究竟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瓦西里耶夫不得不带着种种疑问在人生旅途中继续寻觅。
四、结语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选择的年代,“选择”俨然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每天每时每刻不得不面对各种或大或小的选择,看似简单,实则蕴理无穷。小说所把握到的时代脉搏,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对人性的思考,对真理道德的探寻所形成两种声音的对话在这个多极化、共融性发展的当下依然值得关注和深入挖掘。(上接第19页)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
三、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
作为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和伟大的反封建战士,鲁迅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在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祝福》中,他又挑开了很少为世人所知晓的生活一角——农村妇女创伤累累而又麻木愚钝的心灵世界,向读者提供了祥林嫂这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与残害的悲剧典型。可是,究竟怎样认识祥林嫂的悲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祥林嫂是一个朴实、淳厚、善良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勤恳、诚实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诚如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种“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浮沉。自觉的奴隶性格,正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内在原因。
祥林嫂的悲剧,还表现在她不仅受到封建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更遭到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但封建族权又允许出卖守寡的媳妇。祥林嫂要遵奉的礼教守寡,可宗法势力又强迫她再嫁,她无论如何行事都是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的极端虚伪。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摧残虐杀,正是祥林嫂悲剧的根本所在。
祥林嫂的悲剧还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礼教活活吞噬;她受尽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却又被摧残麻木得自觉和不自觉地去维护封建礼教与迷信。比如,她反抗再嫁,固然表明不愿被婆家当作牲口一样地出卖,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但支配她采取“出格”的反抗的内在原因,还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祥林嫂花了极大的代价去指门槛,也表明她信服了神权迷信,要以门槛作为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好赎了自己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到阴间再受酷刑。封建势力的高压与愚弄,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通过这一完整的悲剧性格,《祝福》异常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道德极端虚伪、残酷的性质,向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