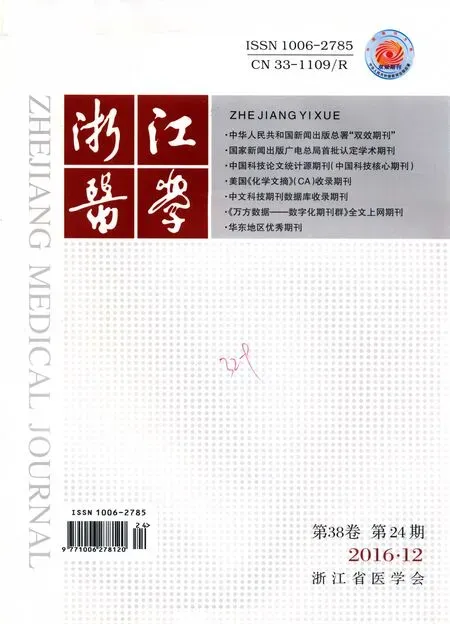我国肺移植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反思
王兴安 姜格宁
我国肺移植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反思
王兴安 姜格宁
发展很快、差距很大,是近年来国内肺移植给人的总体印象。截至2015年底,全国肺移植例数累计734例;2015全年149例,比2007年低谷期的13例增加了10倍[1]。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内肺移植不仅数量上与庞大的人口基数极不相称,而且供肺利用率极低,围手术期医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在绝大多数临床学科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大背景下,国内外肺移植发展的巨大差距值得我们反思。
1 国际肺移植的发展现状
截至2014年6月,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and Lung Transplantation,ISHLT)登记的成人肺移植已累计51 440例,年手术量稳步攀升;2013年度3 893例,较10年前增加1倍[2]。肺移植已经成为终末期肺病确切的、成熟的治疗方法。供肺短缺、原发性移植肺功能障碍(primary graftdysfunction,PGD)近10年来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4];肺移植手术环节最为稳定,术式变化不大;慢性排斥反应仍是严重影响远期生存和移植肺功能的主要因素,但治疗进展不大。
1.1 供肺短缺理想供肺标准在临床上其实早已不被严格遵守,为扩大数量,边缘供肺的底线被一再突破。这可能是ISHLT登记的手术量得以逐年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2001年之后,体外肺灌注(ex vivo lung perfusion,EVLP)技术兴起,临床应用结果显示,EVLP可通过缓解肺水肿、促进肺不张区域复张、抗炎和促进排痰等措施,明显改善边缘供肺或原本要丢弃的不合格供肺的质量,使其达到要求后用于肺移植,并取得与理想供肺接近的效果[3-4]。EVLP不仅可增加脑死亡供者(braindeath donors,DBD)供肺利用率,还能扩展心脏死亡供者(circulatory death donors,DCD)供肺来源,供肺短缺将有望得到明显缓解。
1.2 PGD PGD是肺移植术后医疗最核心的难题,其他并发症多与之关联。近10年来,边缘供肺的广泛使用和受者状况的变化都增加了PGD的防治压力。肺移植受者年龄上限从65岁调至75岁,重病患者比例也明显升高[2-4]。美国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供肺配给评分”使一些病情较重、发展较快的患者得以优先手术[5]。在其他国家,挽救重病患者同样有临床上的现实需求[6]。供、受者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使当前肺移植中PGD及其他并发症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历史时期,但围手术期医疗的整体进步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不利影响。ISHLT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2009—2013年肺移植术后2年生存率仍较1999—2008年略有提升,远期生存率则无差异[2]。需要指出的是,PGD主因——再灌注损伤的防治措施并无大的进展。一氧化氮、表面活性物质、C1酯酶等在动物实验中有效的方法,在临床试验中并未取得令人振奋的结果[3]。
1.3 手术方式近年来没有太大变化。多数情况下双肺移植较单肺移植有明显的生存优势,近10年ISHLT统计的单肺移植基本稳定在每年900例左右,增加的部分几乎全部为双肺移植[2]。
1.4 慢性排斥可引起不可逆阻塞性通气障碍,称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ronchiolitisobliteranssyndrome,BOS)。根据肺功能下降幅度分级诊断,成年受者在肺移植术后5年内发生BOS的比例约50%,术后10年内则高达76%[2-4]。免疫抑制治疗方式变化不大。在8个较常用的维持治疗方案中,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糖皮质激素三联方案使用比例相对最高,术后第1年约55%、第5年约45%;他克莫司+硫唑嘌呤+糖皮质激素方案次之,术后第1、5年使用比例约为20%[2]。术后早期增加引导治疗(单或多克隆抗体),理论上可强化免疫抑制效果,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受者生存超过2年后才有微弱的生存率优势。近10年有50%~70%受者加用引导治疗,约40%的受者使用白细胞介素2拮抗剂[2]。尽管治疗上没有大的进展,但学界对慢性排斥的认知正不断加深。近期研究结果显示,部分诊断BOS的患者经阿奇霉素治疗后肺功能改善超过10%,且有一类限制性通气障碍的病例表现为肺泡纤维化而非小气道闭塞,故有学者提出慢性移植肺功能障碍“chronic lungallograftdysfunction”这个更为笼统的概念,涵盖慢性排斥反应和非异体免疫原因导致的肺损伤[7]。
2 国内肺移植的问题和反思
国内曾有多家医院尝试开展肺移植,但发展为肺移植中心的屈指可数。2002—2006年,至少有32家医院报告了肺移植成功的经验。2007年我国推行器官移植准入制度后,取得肺移植资质的医院也有20多家。然而,到2015年底,活跃的肺移植中心已不足5家。国内数家肺移植中心报告的术后1、3、5年生存率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从受者入院到康复出院的过程中,肺移植团队面临的并发症压力仍十分沉重,需全力以赴,远不及国外同行轻松[8-10]。也正是由于这种压力,许多曾成功进行肺移植的医院浅尝辄止,导致肺移植总量低迷。
首先,问题不在手术本身。肺移植手术定型已有20余年,难度甚至低于一些肺癌根治术。在国外的肺移植中心,接受专科培训的年轻医师也在主刀肺移植。国内肺移植由最优秀的胸外科医师主刀,通常有国外进修学习的经历,在手术技术上至少不低于美欧平均水准。2002年之后数十家医院井喷式肺移植成功,也说明手术不是阻碍国内肺移植发展的因素。其次,也不是物质条件所限。国内有肺移植资质的医院不缺先进设备和高档药物,免疫引导和维持治疗均采用国际最主流的方案[8-10]。国内肺移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多学科团队协作凡观摩过美国肺移植中心的医师,对他们的团队协作都有深刻印象。受者仿佛被置于一条流水线上,每个环节都能得到最专业的医疗,且环环相扣。国外肺移植团队主要由全职肺移植内科医师、胸外科医师、专职护士、呼吸治疗师等组成。终末期肺病患者先由全科医师推荐至肺内科医师,疗效不佳时请肺移植内科医师评估,进而由包含胸外科医师的肺移植团队集体评估,符合条件者进入等候名单。术前过渡性治疗由肺内科医师负责,进入手术阶段后肺移植内科医师负责手术以外的所有围手术期医疗。团队中的护士负责协调检查、治疗和专科会诊事务,胸外科医师负责手术和支气管裂开、伤口不愈合等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处理。受者康复出院后全科医师接手一般随访工作。国内肺移植团队由胸外科手术组演化而来,胸外科医师一专多能,仅在必要情况下寻求相关学科的协助。近年来,一些团队已有呼吸内科医师加盟,但分工仍远不如国外细致。肺移植基本上沿袭了其他胸外科手术的诊疗流程,以胸外科医师为核心展开术前评估、手术和术后随访。术前过渡性治疗、围手术期呼吸康复治疗或被忽视,或不专业,围手术期风险相应升高。一些术后并发症为肺移植所特有,即使呼吸科、胸外科医师合作,处理起来往往也不如专职的肺移植内科医师专业。另外,国内在呼吸、康复治疗上也未专职化。终末期肺病患者因长期缺氧而活动减少,易伴发神经-肌肉功能不良。这类患者易发肺部感染,迅速恶化的缺氧状况及机械通气等治疗措施又使患者更加虚弱,感染难以控制,甚至继发真菌感染[5]。国内在胸外、呼吸、重症医学等肺移植相关学科都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果能构建多学科肺移植团队,围手术期医疗水平会有较大提升。
此外,协作机制也不够完善。我国已全面实行器官捐献制度,器官移植走上正轨,但同时也出现新的挑战。供者所在医院往往缺乏DBD管理的经验,难以有效保护供肺;现阶段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给捐献过程带来许多不确定性;跨医院、跨地区协作机制尚不够畅通、高效,也给供肺转运造成很大的压力。凡此种种,造成目前供肺利用率低下、质量不高的局面[1]。2013年美国供肺利用率约20%,而2015年我国全国可用于移植的捐献者为2 766例,供肺利用率仅约5%[1,11]。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器官移植登记和协作网络初具规模,器官移植已家喻户晓,器官捐赠观念也开始被国民接受,有利于肺移植发展的大环境正在形成。随着协作机制的成熟,国内供肺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如果说传统的胸外科手术类似个人竞技,那么肺移植就像团体赛。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是一支球队制胜的关键,也是肺移植团队运作的核心。
2.2 学科前沿从个人知识结构上看,中美肺移植医师之别在于博与专。中国胸外科医师一专多能,知识结构大多向肺内科、重症医学等相邻学科平面延伸;而美国则着力培养“医师-科学家(physician-scientist)”,知识结构向基础医学纵向延伸。应用型人才是高质量医疗的基石,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也需要一定数量的创新型人才紧跟学科前沿,把新技术及时整合到诊疗方案中。未来肺移植领域胸外科医师或可参与并主导以下两个热点领域的研究。
2.2.1 体外肺支持(extra corporeal lung support,ECLS)技术旨在提供类似透析之于肾移植的短期支持,主要有改良体外膜式氧合(extracorporealmembrane oxygena tion,ECMO)和ECMO微型化装置两个方向。30年前ECMO即被用于成人肺移植术前过渡性支持,然而受者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国内实践也遇到类似问题,此项应用旋即停止[6,12]。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也显示,传统ECMO治疗成人呼吸功能衰竭的效果比机械通气更差。近十几年来,技术和策略改进让ECMO重新进入肺移植领域。Chiumello等[6]检索2010—2014年文献,筛选出14项ECMO作为肺移植过渡期治疗、样本量较大的临床研究,这些改良ECMO技术获得程度不等的效果:441例成人患者过渡期病死率10%~50%,肺移植后1年生存率50%~90%。在众多改良技术中,“可走动(ambulatory)ECMO”最引人注目。成人ECMO效果不佳可能和大剂量镇静剂、卧床制动所致的肌肉功能不良有关,故反其道而行,让患者保持清醒和自主呼吸,接受康复训练和物理治疗[3,13]。最近几项研究结果显示,这个ECMO策略让大多数呼吸功能衰竭急性发作的患者得以过渡到肺移植,与同级别重症患者相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和住院天数等明显降低[5,13-15]。ECMO微型化装置有部分气体交换功能,不明显影响患者活动,目前较受关注的主要有体外CO2清除装置(extracorporealCO2removal,ECCO2R)和肺动脉-左心房Novalung技术。ECCO2R包括一个静脉双腔插管、血泵和膜式气体交换器,清除CO2的效率由过膜气流速决定,为90~100ml/min,但因血流速度慢,不能改善氧合[16]。一项包含20例患者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动脉血CO2分压(Pa CO2)在ECCO2R开始2h内从109mmHg(70~146mmHg)(1mmHg=0.133kPa)降至57mmHg(45~64mmHg)(P<0.000 1),95%的患者过渡到肺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72%[17]。Novalung技术利用肺动脉-左心房之间的压力差,将病肺旁路化,可降低PaCO2、改善氧合和右心功能,需开胸置管,将低阻力膜式气体交换器置于体外[16]。Patil等[18]最近报告1例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伴发顽固右心功能不全,在Novalung技术协助下成功过渡到肺移植。
ECLS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重症医学,也必将给肺移植围手术期医疗带来巨大影响,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领域。需要指出的是,ECLS团队同样应高度专业化,如果每年ECMO支持患者少于6例,病死率会明显升高[5]。
2.2.2 EVLP是最有望提高供肺利用率和质量的一项新技术,目前有三大分支:Lund技术、Toronto技术和Hannover-Madrid技术。EVLP源于生理学研究中采用的孤立肺灌注模型,2000年瑞典隆德大学Steen将其改良,模拟肺再灌注之后的生理状况,为首例DCD肺移植进行术前供肺评估[19]。2005年,Steen等[20]利用Lund技术将1例不达标供肺“再调理”(reconditioning)后成功用于肺移植。再调理包括:机械通气促进肺不张区域复张,富含清蛋白的灌流液Steen SolutionTM保持胶体渗透压、促进水肿液的吸收,抗生素控制感染,糖皮质激素抑制炎症反应,白细胞滤器降低炎症负荷等。灌流1~2h后初评,若达标则立即重新冷藏后移植,不达标但有望改善者则继续灌流,改善无望则丢弃。多伦多大学Keshavjee等在2008年及以后报告的研究中,将EVLP的重点进一步向再调理延伸,发展出Toronto技术。Toronto技术灌流时间明显延长,人肺EVLP至少3~4h,并大幅修改技术参数:灌流液不加红细胞以免溶血引发损害,灌流速度从Lund技术的100%正常心输出量减至40%以减少血管损伤和水肿,闭合肺动脉-左心房回路以维持左心房正压等[19-21]。2012年起见诸报道的Hannover-Madrid技术以便携、常温为特色,供肺不经冷藏,直接置于OrganCareSystemTMLung系统(美国TransMedics公司),在转运中保持机械通气和正常体温[19]。此系统采用改良低钾右旋糖酐液灌流,灌流液含红细胞和左心房开放似Lund技术,但低速灌流则取自Toronto技术。
3种EVLP技术各有千秋,争议和有待完善之处还很多。不过,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临床研究结果的证实[22]。2013年底,仅多伦多大学EVLP肺移植就超过100例,其他中心累计报告例数也有百余例[19]。2011—2015年,共有4项多中心临床试验在美欧展开,估计很快会有相关报道[21-22]。在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中,EVLP已经成为供肺保存、评估与再调理、修复、免疫调整的平台。
EVLP技术国内应用前景很好。国内DBD供肺质量总体偏低,且DCD因更易被国人接受而有望成为供肺的重要来源。4种EVLP系统目前均已商品化,Organ Care SystemTMLung是专为Hannover-Madrid技术设计的便携装置,XPSTM(瑞典XVIVO Perfusion公司)基于Toronto技术开发且高度集成LS1(瑞典VivolineMedical公司)多为Lund技术采用(荷兰Organ Assist公司)有更多个性化调整空间,且特别设计了不可控DCD供肺的原位评估功能[19]。
3 总结与展望
与国外相比,国内肺移植严重滞后,但并非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国内许多大学附属医院的胸外、呼吸和重症医学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我们能发展专业化多学科团队、建立高效协作机制、紧跟发展前沿,那么围手术期医疗和供肺获取方面与国外的差距会迅速缩小,肺移植中心的数量也会很快增多。另外,DCD肺移植较DBD在国内更有发展潜力,如果我们能参与到EVLP等相关研究中,凭借DCD肺移植数量优势也有望后来居上。
[1]毛文君,陈静瑜.中国肺移植面临的困难及对策[J/CD].中华胸部外科电子杂志,2016,3(1):1-6.
[2]CypelM,Levvey B,Van Raem donck D,et a l.Lung transp lantation using contro lled 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 donors:trials and tribulations[J].J Heart Lung Transp lant,2016,35(1): 146-147.
[3]Nathan SD.The future of lung transp lantation[J].Chest,2015,147 (2):309-316.
[4]Yeung JC,Keshavjee S.Overview of c linical lung transp lantation [J].Cold Sp ring Harb PerspectMed,2014,4(1):a015628.
[5]Lehr C J,Zaas DW,Cheifetz IM,et al.Ambu latory extracorporea lm emb rane oxygenation as a b ridge to lung transp lantation: walking while waiting[J].Chest,2015,147(5):1213-1218.
[6]Chiumello D,Coppola S,Froio S,et al.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as b ridge to lung transp lantation:a system atic review[J].Crit Care,2015(19):19.
[7]Verleden G M,Raghu G,Meyer K C,et al.A new c 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hronic lung allog raft dysfunc tion[J].J Heart Lung Transp lant,2014,33(2):127-133.
[8]毛文君,陈静瑜,郑明峰,等.肺移植100例临床分析[J].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13,34(1):28-32.
[9]陈乾坤,姜格宁,何文新,等.42例肺移植单中心8年临床经验总结[J].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11,27(10):594-596.
[10]苗劲柏,侯生才,李辉,等.肺移植手术28例[J].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12,28(3):138-140,151.
[11]ValapourM,Skeans M A,Heubner BM,etal.OPTN/SRTR 2013 Annual Data Report:lung[J].Am J Transp lant,2015,15(Supp l 2):S1-S28.
[12]毛文君,陈静瑜.体外膜肺氧合在肺移植前支持过渡中的应用[J].器官移植,2011,2(4):209-212,236.
[13]Turner D A,Cheifetz IM,Rehder K J,et al.Active rehabilitation and physical therapy during extracorporeal mem b rane oxygenation while awaiting lung transp lantation:a p ractical app roach[J].Crit Care Med,2011,39(12):2593-2598.
[14]Inci I,Klinzing S,Schneiter D,et al.Outcom e o f extracorporea l mem b rane oxygenation as a b ridge to lung transp lantation:an institutionalexperience and literature review[J].Transp lantation, 2015,99(8):1667-1671.
[15]Hoopes CW,Kukreja J,Go lden J,et al.Extracorporealmemb rane oxygenation as a b ridge to pulmonary transp lantation[J]. JThorac Card iovasc Surg,2013,145(3):862-868.
[16]Reeb J,O lland A,Renaud S,et al.Vascular access for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tips and tricks[J].J Thorac Dis,2016,8 (Supp l4):S353-S363.
[17]Schellongowski P,Riss K,Staud inger T,et al.Extracorporea l CO2 removalas b ridge to lung transp lantation in life-threatening hypercapnia[J].Transp l Int,2015,28(3):297-304.
[18]Patil N P,Mohite P N,Reed A,et al.Mod ified technique using Novalung as b ridge to transp lant in pulmonary hypertension[J]. Ann Thorac Surg,2015,99(2):719-721.
[19]And reasson A S,Dark JH,Fisher A J.Ex vivo lung perfusion in c linical lung transp lantation--state o f the art[J].Eur JCard iothorac Surg,2014,46(5):779-788.
[20]Steen S,Ingemansson R,Eriksson L,et al.First hum an transp lantation of a nonaccep tab le donor lung after recond itioning ex vivo[J].Ann Thorac Surg,2007,83(6):2191-2194.
[21]Van Raemdonck D,Neyrinck A,Cypel M,et al.Ex-vivo lung perfusion[J].Transp l Int,2015,28(6):643-656.
[22]Rom an M A,Nair S,Tsui S,et a l.Ex vivo lung perfusion:a com p rehensiv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xp loration of future trends[J].Transp lantation,2013,96(6):509-518.
本文转载自《中华外科杂志》2016年第54卷第12期
200433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
姜格宁,E-mail:jgnw p@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