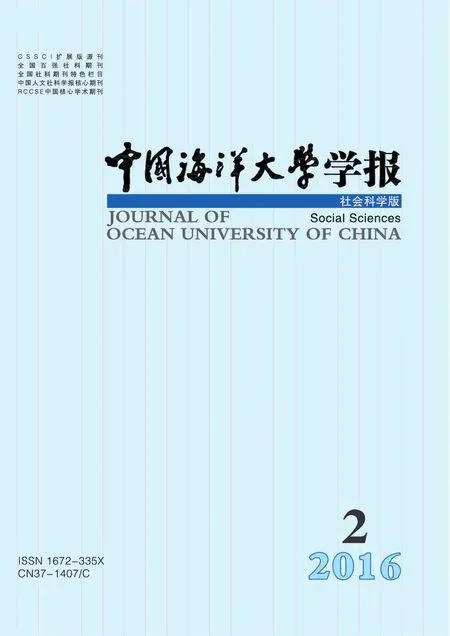明洪武十九年前的“御海洋”击倭战略
刘璐璐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明洪武十九年前的“御海洋”击倭战略
刘璐璐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有关洪武十九年以前海防建设的成效,学界往往多为忽略或估量太低。事实上,明太祖在早年征战中整合了内陆水军以及元末的海上力量,并在“御海洋”的战略下组建成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洪武朝前期的海军力量不仅保障了海运的开展,而且在击倭上也能采取主动巡捕、御之于远洋的军事行动,使得沿海终于基本无事。但遗憾的是洪武十九年以后因海防战略的转变,这种主动进取的海洋精神随之颓废,明初海防在“固海岸”的战略布局下从海上退缩到海岸线一带。
洪武十九年;御海洋;海军力量
长期以来,学界对明初海防建设的讨论,普遍是从洪武十九年(1386)以后开始的,对洪武十九年以前的海防建设则较为忽略。因为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视浙江、福建要地,十九年采纳方鸣谦提出的“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人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无可烦客兵也”[1](卷126,P3754)的建议,命汤和“往浙西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倭寇”[2](卷187,P2799),二十年(1387)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择要地筑城,添设沿海防御卫所。由是学者们多认为明初沿海防御体系从此时期开始,得以加强,形成了海陆结合,极为整肃的格局,并对其多持肯定的态度。*卢建一:《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尽管也有学者提及洪武十九年前的情况,但多比较零散,没有专门的讨论,且对这两个不同阶段海军实力的评估也值得再商榷。范中义先生在《明代海防述略》中提到“随着沿海卫所的设立,直属水军自洪武七年以后,未见其担任海上巡逻任务。这支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较强大的水军,不但没有继续发展,且逐渐失去其战略预备队作用……再无力追敌于琉球大洋”[3],这无疑肯定了洪武前期海军力量的强大和战略上的积极性,但纵观其全文,他对洪武十九年以后的海防建设也保持肯定的态度。《中国海防史》基本承袭其说。王日根教授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一书也认可此说,且在《明初海权扩张与朝贡体制重建》一文中对洪武初期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也有所保留。*王日根,何锋:《明初海权扩张与朝贡体制重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但事实上,是否洪武十九年以后加强沿海卫所等的修筑,就形成了水寨、卫所与巡检司、城堡相互支援,水陆兼备的三重防御体系的布局,就能表示海军力量增强,其防御效力就比洪武十九年以前更有效呢?
对此,杨国桢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东亚海域漳州时代的发端:明代倭乱前的海上闽南与葡萄牙(1368—1549)》一文中指出《汤和传》所记方鸣谦献策一条,朱元璋并非就采纳了“水具战舰”,“海上御之”的建议,事实上强调的只是沿海筑城置卫,并未形成陆海结合的防御体系。方鸣谦的献策和洪武十九年以后的转变,尽管卫所等修筑愈加严密,但“停止出海巡倭,意味着放弃对海洋安全的保卫,从海上退缩到海岸线一带”,是“从海上退缩,而不是向海上进取”,在战略上并不值得肯定。[4]有所启发的是,王日根教授《海防地理视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内迁》一文中,曾指出水寨内迁并不应该视为明海防衰落的标志,海防成效的关键在于巡海,在于能否取得制海权,能否巡海击倭比水寨等的布局更为重要。*王日根,黄友泉:《海防地理视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内迁》,《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此外,在《明初琉球洋海战与后世的社会反响》一文中,杨国桢先生再次肯定了洪武前期击倭琉球洋时海军力量的强大,以及洪武十九年后不再主动击倭,这种战略上从进取到退缩转变的不良影响。*杨国桢,刘璐璐:《明初琉球洋海战与后世的社会反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待刊。
由是,拙文试图对以往比较忽略的明洪武十九年以前的海防战略和海军力量,重新评估。认为洪武十九年左右是洪武朝海防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十九年以前采取的“御海洋”击倭战略更值得肯定。
一、“御海洋”战略与巡洋舰队的组建
明初的海防是与御倭息息相关的,明洪武年间海上的动乱因素主要是来自日本倭寇,这与嘉靖倭患时期的成分有所不同。“御海洋”战略指的是“御之于海”,即强调海战的作用,主要利用海军船舰的力量,积极主动出击将倭寇剿灭于海洋,与之相对的战略布局是“固海岸”,即通过严密的沿海防卫,比较被动地应对倭寇近海上岸,陆军的防守更为重要。如举人归有光指出:国家祖宗之制,沿海自山东、淮、浙、闽、广,卫所络绎,都司、备倭指挥使俟贼之来,于海中截杀之。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矣。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海中,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丕复祖宗之旧,责成将领,严立格条,御贼于外海者,乃为上功。[5](卷12,P746)防御倭寇的地点有外海、内海、海口、陆岸、城池之分,而大抵前三个是属于“御海洋”范围,而巩固陆防则为“固海岸”范围。有明一代对“御海洋”战略的集中讨论,最明显的是在嘉靖倭患时期,在胡宗宪幕僚郑若曾所撰的《筹海图编》中就特意集结了当时御倭将领们对“御海洋”与“固海岸”两种不同战略间的争论。虽然对两者孰为第一要义,更为可行,官员们争执不下,但对“御海洋”的重要作用和有效性谁也不能否认。针对倭寇,“御海洋”更为有效,在京各衙门都明白“倭长技利于陆,我兵长技利于水”,也就是说在海上作战倭寇的造船技术、火器装备等不如我,亦是众所皆知。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就曾提到福船高大可御倭,“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6](卷18,P345)经过嘉靖倭患后,“御海洋”为灭倭上策在诸将领心中多已得到认可,“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正如清末魏源《海国图志》总结的,“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由其入寇皆穷岛亡命,无力置大艘大炮,惟恃其胆力渡洋,恃其刀枪豕突,故登陆则不可敌。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则如石碾米也。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则如狼驱羊也。明代剿倭名将,亦惟唐顺之、俞大猷始惓惓于击贼海中,且谓击归船不若击来船,深得治倭要领,而戈船水犀之备,亦未及见施行。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短。”[7](P8-9)由是可知,对付倭寇,“御海洋”无疑比单纯的“固海岸”更为有效。但是要实现这种战略,非一蹴即就,于是也引发了嘉靖抗倭中对明初尤其是洪武朝“御海洋”战略的普遍追溯和怀念。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博云:“平倭长策,不欲鏖战于海上,直欲邀击于海中……国初更番出洋者,极为至善。至于列船港次,犹之弃门户而守堂室,寖失初意,宜复祖宗出洋之旧制。”[5](卷12,P764)俞大猷在呈揭胡宗宪《请多调战船》时说:“倭贼虽勇悍,然用功海上,定靖可期。国初靖海侯吴祯追而捕之于琉球大洋,由是不敢复来。”[8](P214-215)指明“御海洋”战略早在明洪武初期就已采纳,并十分有效。事实上,在洪武十九年以前,朱元璋对于沿海的日本倭寇不仅采取“御海洋”的积极战略,而且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
元末明初海防未备,日本倭寇经常侵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即位后,辽东一带尚在元的控制之下。为解决北征的军粮问题,“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1](P1915)通过海运将江南的粮米等运至北直隶附近。与此同时,洪武二年(1369),“倭人入寇山东濒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2](卷38,P781)八月,“倭人入寇淮安”,[2](卷44,P866)洪武三年六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2](卷53,P1056)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明初倭寇在沿海一带不断为患,显然会影响到海运的顺利进行。洪武朝的海运一直持续到洪武三十年(1397),而明沿海防御诸卫所的大规模设置是在洪武十九年(1386)方开始,这就意味着至少在防御体系完成之前,为保障海运的正常必须积极地出海捕倭,“御海洋”战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在洪武朝前期可以看到不少主动出海捕倭,积极造船的事迹,朱元璋对此是持十分鼓励的态度,这完全不同于后来以被动的沿海设防为主,御之于海岸的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明初海军的强大。洪武二年(1369)四月,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诏以德有功,故升之。其官校千二百四十七人,赏绮帛五千匹,银二千五百六十九两;战溺死者,加赐钱、布、米,仍命德领兵往捕未尽倭寇。遣使祭东海神曰:予受命上穹为中国主,惟图人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屡肆寇劫,濒海郡县多被其殃。今命将统帅舟师扬帆海岛,乘机征剿以靖边氓,特备牲醴用告神知。[2](卷41,P824)
对东海倭寇之害,明太祖是非常鼓励扬帆海岛,积极追剿,与其海战而平之于远洋的。洪武三年六月,倭寇福建沿海诸郡,“福州卫出军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2](卷53,P1056)七月,“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八人缮理,遇征调则益兵将之。”[2](卷54,P1061)从新置直属京师的水军等24卫,占到京师48卫的一半,每卫配置战船50艘,而明洪武七年之前卫所之制是一卫统10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若按1120人算,这是一支由都督府统一管辖的拥有千余艘战船,数十万军士组成的庞大的海军。朱元璋依靠其力量,足够入海歼敌。十二月,“诏赏福州捕倭军士文绮、金帛。”[2](卷59,P1161)洪武五年六月,“命羽林卫指挥使毛骧、于显,指挥同知袁义等,领兵追捕苏、松、温、台濒海诸郡倭寇”[2](卷74,P1360),结果是:
指挥使毛骧,败倭寇于温州下湖山,追至石塘大洋,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及倭弓等器送京师。诏令中书定赏格,凡总旗军士弓兵生擒贼一人者,赏银十两,斩首一级,银八两;民人生擒贼一人,银十二两,斩首一级,银十两;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于班师之日验功赏之。[2](卷74,P1371)
明太祖的远洋击倭取得胜利,并且对捕倭赏格的高额规定,举朝形成积极造船备倭之风。八月,因考虑官军逐捕倭寇,海舟不够,为实现海上追击,“诏御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2](卷75,P1390),如此大规模的新造海舟,朱元璋担心给民众重科之负担,但得到中书省臣的答复是,“倭寇所至,人民一空,较之造船之费,何翅千百,若船成,备倭有具,濒海之民,可以乐业,所谓因民之利而利之,又何怨?”[2](卷75,P1391)足见当时官员们普遍赞成积极出海御倭。是月,“明州卫指挥佥事张亿,率兵讨倭寇,中流矢卒,上闻而悼之,遣使致祭。”[2](卷75,P1393)九月,“诏浙江、福建濒海诸卫改造多橹快船以备倭寇。”[2](卷76,P1404)正是在这种举朝积极造海舟主动追捕倭寇,鼓励海战的氛围下,熟悉水战、海运的德庆侯廖永忠重申了“御海洋”的主张,并提出在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的基础上建立起拥有足量多橹快船、大船,可以海上剿捕倭寇的巡洋舰队。洪武六年(1373)正月,廖永忠上言曰:
陛下命造海舟翦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窃观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请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舡,命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欲退不可走,庶乎可以剿捕也。[2](卷78,P1423)
朱元璋听从了廖永忠“御海洋”的建议。当时的广洋卫指挥使是于显,方国珍的儿子方礼是广洋卫指挥佥事,横海卫指挥使是朱寿,后因督辽东海运功被封舳舻侯。三月,广洋卫、横海卫依旧出海巡倭。七月,倭寇墨诸城等县,近海诸卫照旧分兵讨捕之,“台州卫出海捕倭,获倭夷七十四人,船二艘,追还被掠男女四人”[2](卷83,P1490)这一年,福建都司都指挥同知张赫“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2](卷203,P3042),充分显示了洪武前期海军远洋作战的能力。
洪武七年(1374)正月初八日,明太祖朱元璋“诏以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所统在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泉、潮州沿海诸为官兵,悉听节制。”[2](卷87,P1546)建立起一支中央直属,节制沿海各卫的巡洋舰队。同年七月,“海上警闻,公复领沿海各卫兵出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上益嘉赖之。”[9](P142)在总兵官吴祯的指挥下,这支组建不久的舰队追击倭寇至琉球大洋,取得海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洪武前期海军有远洋作战的实力。洪武八年(1375)九月,吴祯、于显“率备倭舟师自海道还京”[2](卷101,P1708),说明这次大规模的巡海击倭活动持续了长达一年半以上。此后,海军舰队每年春季巡海捕倭,秋季撤回,远洋击倭成为常例,这充分显示了洪武朝前期海军力量的强大。
其后,造船捕倭继续得到鼓励,并对不能及时出海捕倭导致倭寇上岸者予以极重的处罚。洪武八年四月,“命靖宁侯业昇巡行温、台、福、兴、漳、泉、潮州等卫,督造防倭海船。”[2](卷99,P1680)十二月,“诛潮州卫指挥佥事李德等。先是潮州濒海居民屡为倭夷劫掠,诏德等率舟师沿海捕之,德等逗留不出兵巡御,贼遂登岸大肆劫掠,上闻而怒逮德等至京师诛之。”[2](卷102,P1725)正是在这种积极的御海洋战略下,洪武九年到洪武十二年,海上基本无事。
洪武十三年(1380)倭寇出没之地,多转向广东。在江、浙一带多年平静的情况下,朱元璋开始改变其御倭策略,洪武十五年(1382)一月,“山东都指挥使言:每岁春发,舟师出海巡倭,今宜及时发遣。上曰:海道险、勿出兵,但令诸卫严饬军士防御之。”[2](卷141,P2226)同时备倭将领们的积极性也不如早期出没波涛的宿将们了,四月,浙江都指挥使司要求更改巡御的地点或缩小各卫巡御的范围。[2](卷144,P2268)各卫巡海的负担减轻,海军操练、巡防的难度也降低,给倭寇留下更大的海洋活动空间。十一月,“福州左、右、中三卫奏请造战船,上曰:今天下无事,造战船将何施耶?不听。”[2](卷150,P2365)尽管在洪武十六年、洪武十七年明太祖依旧奖赏慰问出海捕倭者,“赏温州、台州二卫将士擒杀倭寇有功者,凡一千九百六十四人文绮、纱布、衣物,有差”[2](卷156,P2426)、“镇海卫百户王庭,出海运粮,遇倭寇战殁,广洋卫百户周清,出海捕倭溺死,诏庭加三等追赠,清加二等追赠,俱以米、布给其家”[2](卷166,P2555)但显然其奖赏的规格已大不如前。洪武十七年(1384)十月,朱元璋仍告诫运粮辽东的军士“海道险远,岛夷出没无常。尔等所布将校毋离部伍,务令整肃,以备之舟回登州就被巡捕倭寇,因以立功也。”[2](卷166,P2550)但其备倭战略已不再是“御海洋”,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和二十年分别令信国公汤和与江夏侯周德兴往沿海择地筑城建卫,这就代表其战略已有很大的转变。*关于其战略转变可参考杨国桢:《东亚海域漳州时代的发端:明代倭乱前的海上闽南与葡萄牙(1368—1549)》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2002年春。从此,比较被动地“固海岸”成为他后期的防海之略。
二、洪武前期海军力量的来源
洪武十九年前“御海洋”击倭战略能够实现,亦是时势所趋,一是因辽东海运的存在必然需要远海海军的保护,光凭陆防是保障不了的,“固海岸”也尚未得以推崇与实践;二是洪武前期有能力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而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水军将领们也有击倭海上的思维。那么,洪武朝前期海军的来源是什么呢?朱元璋是如何整合组建成这支强大的海军的呢?大致来说,主要来源于早年征战中的内陆水军,元末方国珍等海上力量的整合,以及明初为发展海运和击倭的造船建军。
朱元璋第一支水师力量,是巢湖水师的来附。至正十五年(1355),“上与诸将谋渡江,患无舟楫”,[2](卷3,P29)但当时巢湖水寨盘踞着叛元的水师万余人,有船近千艘,五月,巢湖水师取得与朱元璋的联系后,除赵普胜带领其部下离走并投奔了陈友谅,余下的舟船到和州后归顺了朱元璋。后又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令其教诸军习水战,命廖永安、张德胜、俞通海等将之。因为巢湖水师俞、廖两家的投靠,加上从元军水师中得到熟悉水战的十九人的教习,朱元璋从无舟楫到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水师。顺利渡江攻占南京后,至正十九年(1359),与赵普胜在枞阳水寨相战,打败之,获艨艟数百艘。至此巢湖水师几全归朱元璋所有。一大批从巢湖出身懂水战的将士,包括廖永安、廖永忠兄弟,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兄弟及其子弟,还有张德胜等人,在以后征伐南方的水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还训练了一批原来不习水战的人员,水师的规模和作战能力也在征战中得到提升。
其后,朱元璋的舟师在与陈友谅、张士诚等的较量中得以扩充。陈友谅盘踞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拥有在当时颇为强大的内河舰队。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试图以其舰队的优势攻打在南京的朱元璋,但最终失利。明军“俘其卒二万余人,其将张志雄、梁铉、俞国兴、刘世衍等皆降,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舰数百,”[2](卷8,P105)并追击汉军至慈湖,纵火焚其舟,在采石又大败之。通过这次较量,朱元璋获取了一百多艘大船和数百战舰,这应该是一支完整的内河舰队。次年决意主动讨伐陈友谅,经过湖口、鄱阳湖水战后,吸收了剩余的汉军舰队——总数有5万人*牟复礼,崔德瑞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6页。。破除陈友谅后,明军开始转向江浙一带的张士诚。张士诚是以操舟运盐起家的,名义上归附元朝并负责供应元海运所需的粮食等物资,有不少舟师。至正二十六年(1366),在与朱元璋的水战中打败张士诚,获其楼船。明水军不仅在船舰上越来越多,作战能力也越来越强大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年准备取淮安,徐达提出,“兵不在众,宜以步骑一万五千,舟师一万,水陆并进。”[2](卷19,P274)这说明当时组建一支万余兵力的水军已不在话下。接着,四月徐达率军至淮安,破其余部水寨军,获船百余艘。
经过长期的征战,内陆水军已经成熟,但拥有真正海军的开始是来自对元末方国珍等海上力量的吸收。至元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命参政朱亮祖帅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讨方国珍”[2](卷25,P361),十月,又“命御史大夫汤和为征南将军,佥大都督吴祯为副将军,帅常州、常兴、宜兴、江阴诸军讨方国珍于庆元”[2](卷26,P387)。在盘屿大战,“斩首及溺死者甚众,擒其伪副枢方惟益、元帅戴廷方等,获海舟二十五艘,马四十一匹”。[2](卷27,P410)还师庆元后,马上往定海、慈溪等县,又“得军士二千人,战舰六十三艘”。[2](卷27,P410)尽管通过战争从方国珍处得到不少海舟,但毕竟在内河、内湖作战不同于海战,明水军对海上的航行和作战情况也不了解,更无多少海战的经验。而这时方国珍已遁入海岛,在朱元璋尚未有真正海军的情况下,他颇为担忧,于是举行了祭祀海神的仪式。据载,上乃命中书平章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帅师自海道会和讨之,祭海上诸神曰:“近命御史大夫汤和为征南将军,领兵取庆元、温、台等郡,今复遣中书平章廖永忠为之副,往庆元招抚军民,惟兹军士未尝涉海,兹经海上,惟神鉴之。[2](卷27,P413)
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朱元璋任命内陆水师出身且在水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的廖永忠为副将军,实为权宜之举。虽然最终是以招降来解决这一难题的,但也说明内陆水军的成长对向海军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有相当的人员、舰船可以用诸海上,尤其是通过海上训练后可能成为很好的海上力量。同时,内陆水军与海军存在很大的差别,未有海上经验的水军难以真正熟悉海上事务。方国珍等元末海上力量的加入、被整合,才是朱元璋拥有海上力量的真正开始。
方国珍(1319—1374),原名珍,字国珍,避庙讳更名真,因字谷贞、谷珍,元末浙江台郡黄岩洋山澳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1](卷123,P3697)方国珍入海为寇的时间在至正八年(1348),原由是被怨家诬告与海寇通所致,《明太祖实录》记载:
元至正中,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诛连平民。国珍怨家陈氏诬构国珍与寇通,国珍怒杀陈氏,陈之属诉于官,官发兵捕之急。国珍遂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亡入海中,旬月间,得数千人,劫掠漕运粮,执海道千户。[2](卷88,P1560)
宋濂在洪武九年奉诏所作的《故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铭》中亦有记载,虽其言辞为方国珍入寇实为无奈之举有所辩护*左东岭:《<方国珍神道碑铭>的叙事策略与宋濂明初的文章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但对其前因后果的描述更为详尽:
至正初,李大翁啸众倡乱,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舟。剧盗蔡乱头闻其事,谓国家不足畏,复效尤为乱,势鸱张甚,濒海子女玉帛,为其所掠殆尽,民患苦之。中书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发郡县讨蔡寇。公之怨家诬构与其通,逮系甚急。公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公度不能继,且无以自白,谋于家曰:“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藉之为奸,媒蘖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咸欣然从之。郡县无以塞命,妄械齐民以为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数千,久屯不解。[10](P1255)
从这两段材料来看,元末温州、台州一带濒海之民入海为寇者并非特例。从地理环境来看,这一带岛屿丛生,出入海上贩盐为生之民不在少数,在朝廷眼里这些人确是难免通寇、为寇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元代兴海运,运送漕粮的重要起点太仓诸港与台州的距离也很近,故海寇李大翁等劫夺漕运舟,而方国珍入寇后也劫掠漕运粮,这不仅为海寇的补给提供便利,且有利于扩充自己的船舰数量。方国珍入海,得到家人、邻里的支持,并且才十多天跟随者就多达数千人,其部下应该就有不少贩私盐者,据有关研究指出,*陈波《海运船户与元末海寇的生成》,《史林》2010第2期。方国珍完成武力积累的重要社会基础,多为元末生计窘迫承运海漕的船户,他们中间很多人为逃避赋役而逃入海岛加入方国珍的队伍中。
因方国珍的行动破坏到海道运粮的正常,不久元朝诏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总舟师捕之,但“兵败,反为所执,国珍因迫使请于朝,下招降之诏。元主从之,遂授庆元定海尉。国珍虽授官还故里,而聚兵不解,势益暴横”。[2](卷88,P1561)方国珍受招降后,至正十二年(1352)元征徐州,命江浙省募舟师守大江时,他怀疑元会乘此剿灭自己,复入海为叛,于是,元再次命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花讨之。“泰不花率舟师与战,众溃,泰不花自分必死,即前薄国珍船,手刃数人,遂为所杀。”[2](卷88,P1561)次年(1353)三月,元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儿、南台侍御史左答里失前往诏谕授官,方国珍“疑惧不赴,拥舟千艘,复据海道,阻绝粮连。元复遣江浙右丞阿儿温沙与庆元元帅纳麟答剌会兵讨之,皆败。元无如何,复招安,从其所欲,以国珍为海道漕运万户,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在此期间元还曾招募海上壮士击国珍,如“海上赵士正诸家起义兵与方氏战,子弟多创死,不获沾一命”,而“方氏累叛累进,秩功罪反,人无以拳,于是上下解体,多甘心从乱而方氏益横。国珍既受官,不听调,时汝颍兵乱,四方多故,元益羁縻不能问。”[11](卷90,P217)方国珍势力愈益扩展,甘心跟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时海内大乱,江淮南北诸郡纷纷聚众割据,元已无余力消除方国珍,只好任其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方国珍攻据台州。至正十五年(1355),方国珍攻下温州、庆元。至正十七年(1357),元朝希望借助方国珍的海上力量来讨伐在江浙一带割据的张士诚,“国珍率兄弟诸侄等以舟师五万进击士诚昆山州,士诚将史文炳等御于奣子桥,国珍七战七捷,会士诚亦送款于元,愿奉正朔,元从其请,遂命国珍罢兵。”这时候,方国珍拥有舟师五万,迫使张士诚称臣于元。国珍还师后,“开治于庆元,而兼领温、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侄明善居温,而留弟国珉自副。”[2](卷88,P1562)依靠海上舟师力量兴起的方氏,俨然已是一方强有力的割据势力。
当时,“元每岁遣官督国珍备海舟至张士诚所,漕米十万余石,渡海北输元都”,[2](卷88,P1562)由张士诚负担海运中的粮米,而具体的海上运输则由方国珍负责。元末海运的路线,在朱清、张瑄开辟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自至元三十年(1293)后常走的是千户殷明略所开的新道,“从刘家港开船,由长江口出海以后即直接向东进入黑水大洋,经由黑水大洋又直接向北航行到成山角,再转西仍由渤海南部到达界河口”。[12](P61)这条海路中很长的一段远离海岸,进入深海中。方国珍自海道运粮,应该也是常走此线,这就对其航海造船技术和防御海寇能力的要求更高,正因为如此,方国珍更加多造大船,其部下也积累了相当的海运、御敌经验,其海上势力应该是元末最为强大的。
至元二十七年(1367),方国珍遣使奉表谢罪乞降后,朱元璋接受了他的归顺。十二月,方国珍及其弟国珉率所部谒见汤和于军门,得其步卒九千二百人,水军一万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粮一十五万一千九百石,他物称是。[2](卷28,P428)至此,明水军的人数至少达到两、三万,获取了数百艘海舟,方国珍的子侄及其部下也加入到明军中,自此,明从海道往来已不是问题。除了方国珍的海军主力外,继而,“元昌州达鲁花赤阔里吉思亦来降,得其粮六万九千石,马五十匹,船四百八十二艘。”[2](卷28,P428)紧接着,同月,征南将军汤和、征南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率舟师直接由海道自明州进入福州,不数日至城下,一鼓克之,“获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2](卷28下,P473)洪武元年(1368)陈友定在延平被擒,闽海平,其海上舟舰等也归明太祖朱元璋所有。
明太祖整合了这些海上力量后,在接下来的南征北伐中都充分利用海道,洪武元年(1368)二月,“诏御史大夫汤和还明州造海舟,漕运北征军饷;命平章廖永忠为征南将军,以参政朱亮祖为副帅,舟师由海道取广东。”[2](卷30,P514-515)五月,昌国州兰秀山海寇入象山县作乱,对其经过和海寇身份,学界有所研究,*藤田明良:《兰秀山之乱与东亚海域世界——14世纪舟山群岛与高丽、日本》,《历史学研究》698号,1997;陈波:《兰秀山之乱与明初海运的展开——基于朝鲜史料的明初海运“运军”素描》,《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多认为这些人是方国珍的余部。洪武二年(1369),吴祯调兵剿捕之,得到明太祖的嘉奖。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之民不得私出海。”[2](卷70,P1300)曹永和先生解释这一段材料时指出,“这一段记述说明太祖的扩张海军,增强了海防的措施”。[13](P42)
此外,为保障辽东海运又大造海舟以补海运中舟船不足。洪武元年二月,“诏御史大夫汤和还明州造海舟,漕运北征军饷。”[2](卷30,P515)八月,“上命造海舟运粮往直沽,候大军征发。”[2](卷34,P620)《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中亦载,“大军方北伐,命造舟明州,运粮输直沽。海多飓风,输镇江而还。”[1](P3753)《明史》卷一三一《郑遇春传》中也提到,洪武三年,“还京,督金吾诸卫,造海船百八十艘,运饷辽东。”[1](P3854)为满足海运的需要,明到底新造了多少海舟,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这些海舟的增加有益于增强运军的实力。洪武五年,诏吴祯“分总舟师数万由登州转运以饷之”,[9](卷5,P142)说明当时运军的数量达到数万。陈波引《名山藏》、《国朝宪章类编》和《明太祖实录》中关于漕运的材料指出洪武中海运人数达到八万余人。*陈波:《试论明初海运之“运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海运之兴,不仅增加了舟船,锻炼、培养了一批熟知海洋事务的将士,也促成了积极主动的御倭战略,海运军将领中也不乏捕倭能将,包括汤和、廖永忠、郑遇春、吴祯、张赫、朱寿、朱信、宣信等人。*关于海运与御倭的关系,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海运兴起是有利于发展海军和御倭的,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中研院”史语研究所,1961年,第25-31页。
总的来说,明太祖对方国珍等元末海上力量的整合,不仅使自己拥有了众多海舟、船舰以及熟悉海洋的将士,而且在以后的海运、御倭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些力量。明太祖在早期听取了这些人中要求“主动击倭,御之于海洋”的积极海防战略,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巡洋舰队,显示了洪武前期海军的力量。
三、结语
事实证明,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明初海军,不仅规模宏大,有一批熟悉海战的将士人员,而且有远洋作战的实力,能够保障明初海运的顺利进行,且在击倭上采取主动出击的态势,“御海洋”的战略也因此得以实践。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辽东海运的顺利,“御海洋”在洪武初期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遗憾的是洪武十九年以后明太祖海洋战略的转变,强大的海军力量被固守海岸的战略制约,尽管沿海的军事设置取得一定成效,但出海主动击倭的战略被渐渐放弃,直到嘉靖倭患时又被击倭将领中的有识之士们重新思考和实践。虽然在永乐下西洋的庞大船队里仍可看到许多出身洪武朝水军、海运,在洪武朝锻炼出来的那批熟知海洋事务人员的影子,这些无疑显示了洪武初期海军力量的强大。但可惜的是朱元璋禁海、防海等保守的海洋发展战略随之而来,成为祖宗成法为后世遵循。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也多是其沿海筑城建卫之后的历史。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七年组建的那支强大的巡洋舰队,和在“御海洋”战略下的击倭功绩,则往往被后世学者们忽略。
同时,在对有明一代海防建设的划分阶段和内在逻辑上仍值得商榷。沿海卫所、水寨等的修筑严密,并不一定就代表在实际海防中更有效,并不能作为评判明海防建设成功的主要标志。相反地,可能是海洋防线从海上到陆地的退缩。是否采取“御海洋”的战略可能在实际御倭中更为重要,这不仅意味着海军是否有足够的远洋行动力,也是对制海权的争取。重新审视洪武前朝的海防建设,或可纠正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些偏差。
[1]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明太祖实录[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3] 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J].历史研究,1990,(3).
[4] 杨国桢.东亚海域漳州时代的发端:明代倭乱前的海上闽南与葡萄牙(1368-1549)[J].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 2002.
[5] 郑若曾著,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 戚继光.纪效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
[8] 俞大猷.正气堂全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9] 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录[M].新北:文海出版社,1870.
[10] 宋濂.宋濂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1] 傅维麟.明书[M].四部全书存目丛书本.
[12]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3] 曹永和.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A].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辑[C].广州:“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1984.
责任编辑:高雪
The Positive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aval Forces in the Early Ming Hongwu Dynasty
Liu Lulu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Scholars have often underestim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aval forces before the nineteenth year during the reign of Hongwu Empero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 f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ing Taizu Emperor's reign, he had formed a powerful cruiser-fleet under the strategy of coastal defense by integrating inland navy forces with the former ones affiliated to Yuan Dynasty. The navy forces could not only protect the sea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Japanese pirates' attack, but also ensure the safety of coastal areas and territorial seas. However, the positive maritime strategy was changed later, the initiative and enterprising maritime spirit were on the decline. The coastal defense retreated from the sea far from the coastline to the coastal line proper.
Ming Hongwu Dynasty; the positive maritime strategy; naval forces
2015-11-15
刘璐璐(1988-),女,湖南湘乡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海洋史。
K248.1
A
1672-335X(2016)02-0084-07
——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