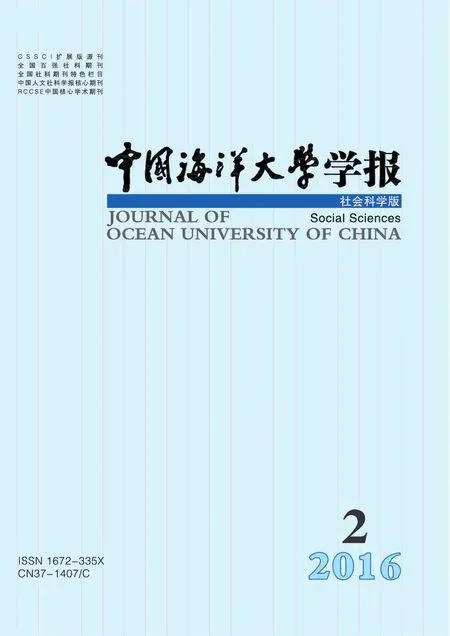日韩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邓妮雅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日韩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邓妮雅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日本——韩国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案是继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后,在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的第一案。日韩东海大陆架油气争端产生于两国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初,东海具有广阔石油前景的预测推动了两国在重叠区域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活动。日韩共同开发从谈判到协定生效这个过程中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日韩共同开发协定是一份全面而务实的法律文件,规定了共同开发区域、联合委员会、特许权人确定方式、法律适用、争端解决等内容。虽然经过两轮开发,并未发现有商业价值的油气资源,但是该案也对中国与邻国进行共同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影响因素;法律框架;对策与启示
日本——韩国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案(以下简称日韩共同开发案)是继1969年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之后,在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的第一个案例。1974年1月,日本和韩国草签了《日本和大韩民国关于共同开发邻接两国大陆架南部的协定》(以下简称《1974年协定》),该协定于1978年6月生效。根据该协议,日韩两国将建立面积为24.101平方海里(后调整为24,092平方海里,约8.2万平方公里)的共同开发区,该开发区位于日本主张的大陆架“中间线”与韩国主张的大陆架延伸线之间的争议区。迄今为止,日韩共同开发区并没有发现有商业价值的油气田。但从共同开发的功能性角度来看,它却是一个较成功的案例,协定的文本也为研究共同开发提供了一份全面而务实的法律文件。[1](P37)
一、日韩东海大陆架油气争端的产生
1969年5月,亚洲近海矿物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发表了东海具有石油远景的报告(也称《埃默里报告》),引起了日本和韩国的注意。从1969年4月至1970年9月,韩国先后与美、英等四家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租让合同,开展了大规模的地球物理和石油钻探工作。韩国政府1970年的《海底资源开发法》(Submari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Law)生效,同年5月发布的执行《海底资源开发法》的法令,宣布了韩国大陆架的界限。韩国将海底开发区域划分为7个区块(区块命名为K1至K7),其中1-4矿区在黄海,其西缘大致靠近我国的中间线;第5-7矿区的南缘和东缘则按自然延伸原则,大体按东海的200米等深线,第6矿区位于日本海。*韩国授予几个外国石油公司在黄海和东海开发大陆架的许可权:1969年4月15,韩国政府在K-2和K-4区块与Gulf Oil CO.ltd石油公司签订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合同;1969年12月,韩国政府在K-3和K-6区块与Shell CO.ltd石油公司签订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合同;1970年 2月,韩国政府在K-1和K-5区块与Social & Texas CO.lt石油公司签订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合同;1970年 9月,韩国政府在K-7区块与Wendell Phillips石油公司签订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合同。[2](P281-282)这个授权开发区的南部超过了理论上的日韩中间线,并与日本石油公司开发的区域相重叠。
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视东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展了大量活动。*1967、1968、1969年,日本三家石油公司分别申请了海底资源开发的许可权。1969年至1970年,日本有关机构在政府资助下对东海大陆架,特别是钓鱼岛周围海域进行多次调查。1970年后半期,日本还制定了东海大陆架寻油5年计划,后由于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的严正立场、中日关系正常化等因素,该计划未真正实行。[3](P109)自从《埃默里报告》预言这里存在石油之后,日本在这一带也划定了4个租让区(区块命名为J1至J4)。日本的J2和J3与韩国的K5和K7租让区重叠,形成了海上争议区。
在韩国宣布在东海、黄海建立大陆架矿区后不久,日本要求日韩双方谈判划定两国大陆架界限,但谈判无果。1974年1月日韩签订了《1974年协定》。韩国于1974年12月批准了该协定,而日本直到1978年6月才批准。
二、日韩共同开发的谈判过程
从1972年开始,日韩两国就准备进行东海海域的共同开发,但双方在利益协调和法律规则调整等方面的谈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日韩共同开发从谈判到生效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阻碍因素和促成因素两个方面。
(一)阻碍谈判的因素
《1974年协定》签订后,韩国于当年12月就通过了该协定,而日本用了4年多的时间才通过,因而阻碍因素主要来自于日本。
1、日本《采矿法》(Mining Law)与共同开发协定的冲突
日本石油开采受到1950年《采矿法》(Mining Law)的管制。例如,《采矿法》规定矿区规模不能超过15公顷(约0.00044平方海里),而日韩共同开发协定所管辖的开发区面积为24,092平方海里;属于国家的矿产资源不能由私人享有,矿产资源不能无偿产出;采矿法的申请核准以先来先办原则处理,而对申请人能力的审核无经济规定,而日韩共同开发协定则以竞争原则对采矿执照申请加以筛选等。[2](P279-280)为了促进共同开发的实施,日本于1978年6月颁布了《特别措施法案》(Special Measure Law)。
2、日本和韩国海洋法律政策的差异
日本与韩国在大陆架制度和重叠海域划界原则上的差异,以及日韩两国在渔业有关的海洋法律政策上的较量,阻碍了谈判进程。
第一,大陆架制度与划界原则不一致。日韩共同开发案谈判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还处于第二轮谈判之中。日本一直坚持中间线原则,韩国在东海北部与日本大陆架坚持陆地自然延伸原则,主张其大陆架延伸到冲绳海槽,日本男女群岛南部大陆架是朝鲜半岛的自然延伸。1969年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中否定了等距离线原则构成了习惯国际法,并立足于大陆架应该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来做出了最终裁决。[4]若将之运用于东海海域,则中国和韩国的主张会得到支持。1969年2月,北海大陆架案判决做出仅几个月后,《埃默里报告》出台。这使日本政府高层对《1974年协定》的态度分化为两派:一派主张不能放弃中间线原则,应在新的海洋法公约达成之后再划分大陆架界限。[5]日韩共同开发区完全包含在两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坚持中间线原则完全合理。另一派则主张尽快通过《1974年协定》,该协定通过耗费时间太长,韩方会单独推进共同开发,情况会更加不利。
第二,海洋污染与渔业问题。日本本土附近海域是世界上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渔业和航运是影响日本海洋政策的两大核心因素。近海石油开发可能会对海洋污染和对渔业活动均带来影响。*由于国土面积小,日本的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日本民众90%的动物蛋白质来自于海洋,在日韩共同开发区内,日本渔民的年捕鱼量为5,700吨,占日本整个西部水域捕鱼量的28.5%。这不难看出共同开发区在日本渔业的重要地位。渔业产业也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在该区域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建立的油气设施将对渔业和自由航行造成影响;石油开采活动也可能造成海洋污染。但是,日本渔民也担心日韩共同开发区不建立或者延期建立,韩国会废除《日韩渔业协定》,或者建立200海里专属渔区,这对日本西部的渔业也会是沉重的打击。[2](P308)日本国会迟迟不通过《1974年协定》,韩国政府也不断抗议并声明会建立200海里专属渔区。
3、国内政治派别之间意见的分歧
日本自民党坚持要求核准《1974年协定》,而其他政党及自民党部分议员则持反对态度。日本国会内部就《1974年协定》的批准问题就争论了3年多的时间,牵动了整个日本国内社会。直到1977年6月,日本国会才正式批准《1974年协定》。1974年5月,《特别措施法案》提交国会讨论,但是从第75次议会至80次议会都没有得到通过。《1974年协定》提请批准过程中,同样也遭到了自民党内部部分成员的反对。甚至在这两项议案通过后,反对该法案通过的自民党成员离开了自民党,组成了新的党派——新自由俱乐部(New Liberal Club),并继续在第80次议会中通过分化选票和煽动公众舆论以反对通过该议案。[2](P306)
4、中国和朝鲜的抗议
《1974年协定》的签订不仅遭到了日本内部的反对,也引起了朝鲜和中国的强烈抗议。*中国的外交抗议主要参见:《人民日报》1974年,第2.5卷,第1页;《人民日报》1977年,第5.28卷,第3页;《人民日报》1977年,第6.14卷,第1页;《人民日报》1978年,第6.27卷,第1页。朝鲜的外交抗议转载于《人民日报》,1974年,第2.10卷,第5页。东海是中、日、韩三国所围成的半封闭海,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划界应由相关国家首先协商确定,无协定则依据“特殊情况加距离原则确定”。[7]日韩共同开发协议中无视中国在东海的权益,在还未进行海洋划界的前提下,开发区的面积延伸至中国可依据自然延伸主张的大陆架区域。协议签订后,中国有3次强烈抗议和7次低层次的外交抗议。中国政府在抗议中多次提到日韩共同开发协议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利,日本政府实际的开发活动会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这是1972年9月中日建交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措辞强烈地谴责日本政府的政策。在中日邦交刚刚恢复的初期,这也是日本府必须要考量的因素。
(二)促成谈判的因素
《1974年协定》虽然阻碍重重,但国际环境的影响,石油资源的潜力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吸引力,政府以及非政府成员的推动,在历经4年半之后最终通过。促成谈判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环境的影响
第一,政治关系缓和。20世纪60年代,日韩两国关系走向缓和,并于1965年6月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为两国共同开发合作的开展酝酿了较好的政治环境。
第二,两国经济发展需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实行“重化工业立国”的战略。[8](P271-272)但是韩国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大部分依赖于外国,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这种对外依赖性进一步加深。[9]日本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能源消费的巨大增长。*统计数据发现,日本1955年消耗的总能源数量为644兆大卡,其中将近79%是国内生产的,而煤占了将近一半。1975年消耗的总能源为3435兆大卡,国内生产的能源只有445兆大卡;而原油为2436兆大卡,占总能源的将近80%。到1990年,国内总能源消耗为4663兆大卡,国内生产的能源只有816兆大卡,只占总能源的大约17%;原油为2158兆大卡,占能源消耗近50%。[10](P578)日韩共同开发谈判时,两国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石油是两国工业化建设中重要的能源构成,两国需要稳定的石油供应以支持高速发展的经济。
第三,石油危机的影响。1973年以及1978—1980年,中东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引发了石油危机。市场上石油短缺,油价从1973年的每桶大约2美元跃升至1980年每桶30美元左右。日本当时作为一个主要的石油使用国,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其80%的石油供应来自于中东。[10](P478)石油危机日本感到确保石油来源稳定性的重要性,因此日本积极寻求石油供给来源的多元化。[11](P163)韩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很高,因而开发近海石油的愿望较为迫切。
2、对潜在资源的评估
1969年《埃默里报告》出台,预测中国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石油储藏地区。该报告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该地区油气资源的关注,也引发日韩和中国台湾三方纷纷划定矿区,客观上促成了三方之间就东海进行共同开发的讨论和谈判。大陆架潜在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对于石油资源严重短缺的日韩两国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在石油危机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更加速了两国挖掘近海油气资源潜力的意愿。
3、日韩合作委员会的努力
当日韩在共同开发前期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人士在非政府层面上做出了不少努力,其中核心就是日韩合作委员会(Japan-Korea Cooperation Committee)。[2](P286)
1970年8月,在日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矢次一夫(Kazuo Yatsugi)提出了离岸共同开发议案,议案的目标不仅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开发,也包括海底资源的全面开发。正是这个提案促使了大陆架共同开发的产生。[2](P286)1970年9月,日本—韩国合作委员会和日本—台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包括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日本经济组织联合会副主席堀越祯三(Teizo Horikoshi)、国家政策协会的常务理事矢次一夫,提出了日韩台三方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方案。虽然三方共同开发案最终流产,但在第六次日韩合作委员会常规会议,以及1971年1月19至1月20日召开的日韩离岸开发协调委员会提交报告的基础上,日韩共同开发案的讨论仍在继续。
4、自民党的推进和民社党的支持
日本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工业主义经济所决定的。自民党在日本国会中是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纵观1950至1990年日本众议院的选举情况,自民党的选票,虽然从最初占70%以上有所下降,但即使在选票最低的70年代,自民党的选票仍然占40%以上。[10](475)自民党内的亲韩派认为,日本已经签订了共同开发协定,则需要通过该协定以遵守国际诚信原则;况且,即使日本不进行共同开发,韩国方面也会实行单独开发。正是这部分主导力量的推动,《1974年协定》才可以最终通过。民社党是日本众多政党中(除了自民党)唯一支持日韩共同开发的政党。在民社党的支持和帮助下,自民党最终在议会中通过了共同开发议案。
5、日本和韩国政府在渔业和海洋污染政策上的协调
日本政府对可能产生的海洋污染做了更加详细的安排。第一,日本政府主张在共同开发安排中,消除日韩政府在防止和处置海洋污染中明显不一致安排;同时规定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不能影响航行和渔业;需要采取措施阻止爆炸,防止和处置海洋污染;同时也规定了如何处置污染带来的损害。[2](P300)第二,为了减轻渔民对海洋污染的担忧,取得渔业部门对共同开发案的支持,日本外务省与经济产业省、天然资源与能源厅、农林省(现为农林水产省)、水产厅、海上保安厅和环境省等部门交换意见。日本经济产业省和水产厅成立了协调办公室,做出了确保海底勘探开发最大程度的安全进行,建立了海洋事故引起的全额渔业赔偿制度。[2](P308)
日韩双方政府在《1974年协定》及相应的会议纪要和外交换文中对海洋污染和渔业问题做出了具体协调。如在会议纪要规定,双方政府要对需要给予各国特许权方行政指导,尽最大努力调整平衡双方的渔业利益。[12]1974年1月30日,日韩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外交换文中,双方对于如何防止共同开发区内勘探和开发活动产生的海上碰撞,防止和消除海洋污染的具体措施达成了一致。[13]同时在《1974年协定》中还规定:为了保护共同开发区重要鱼群,对石油开采和相应措施施加了某些限制;对渔民要进行补偿。[14]
6、韩国政府的压力
韩国政府对日本不断施加压力,促使其通过《1974年协定》。韩国政府发表声明,声称正在准备单边开发,准备建立200海里专属渔区,将日本渔船驱逐该区域。1974年3月共同开发协定签署仅仅40天之后,韩国在野党民主共和党、政策制定委员会的主席朴俊奎就公开抗议日本政府拖延日韩共同开发进程,声明如果日本不批准共同开发协议,韩国将进行单边开发。1977年4月,韩国总统朴正熙和其他韩国官员的后续声明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警告。[2](P303)韩国政府持续的声明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压力,使得日本自民党产生顾虑,害怕韩国将进行单边开发,因而积极推进共同开发。
三、日韩共同开发协定的主要内容及其后续进展
日韩共同开发的法律框架包括:两个协定《日韩北部大陆架划界协定》、《1974年协定》,四个外交换文和一个会议纪要附件。
(一)日韩共同开发协定的主要内容
1、共同开发区域
《1974年协定》确定了共同开发区,并在附件中详细标示了7个分区的坐标。日韩共同开发区的具体位置在北纬28°36′至北纬32°57′,东经125°55′5″至东经129°9′之间,面积大约为24,101平方海里(后调整为24,092平方海里)。共同开发区共划分为9个区块,划分流程附在《1974年协定》附录中。*1987年5月第一轮开发结束之后,日韩共同开发区被重新划分为6个大致相等的区块。1987年8月,第一轮开发结束后,日韩双方协议将区块重新划分为面积大致相等的6区块。
2、日韩联合委员会
《1974年协定》要求两国成立日本—大韩民国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以对涉及《1974年协定》的问题进行磋商。该协议第24条、25条对委员会的组成以及职责做了规定,委员会主要的职责为审查报告、监管开发区内的活动、提供法律政策建议等,该委员会的所有决议、建议及其它决策,均只能通过国家部门之间的协议达成。日韩两国对特许权受让人许可和管理权限的保留,将委员会的角色限定为咨询和进行合作的论坛式结构。[15](P117)委员会缺少权威性,它的许多职能仅限于向两国提供建议。
在共同开发后期,委员会也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1974年协定》规定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而早在1985年3月东京会议后,委员会便没有再召开过会议。但是,日韩共同开发区的活动直到1989年9月才最终停止。[16](P97)虽然,共同开发区联合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取决于国家协商采用的模式,但委员会也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职能。具体而言,联合委员会至少具有三个基本功能:首先,对共同开发区活动,它具有最低限度的监管功能;其次,它是一个永久性的论坛场所,共同开发的双方可以进行常规性的会议;再次,当共同开发的双方或者多方之间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出现的时候,联合委员会可以作为咨询和协调的媒介。[17](P146)虽然在日韩共同开发案中,委员会仅具有咨询和协调的功能,但是在共同开发活动还没有终止之前委员会就停止其职能的行使,委员会的价值和功效并没得到充分的体现。
3、分区块特许权人的确定
《1974年协定》第4条规定:日韩共同开发区内,每个分区的石油勘探工作均由两国的特许权受让人一同进行。每个国家针对各个分区必须至少授予一个特许权受让人。如果特许权受让人或分区出现变更,有关国家必须尽快授予新的一个或多个特许权受让人。第5条规定:一个分区工作的特许权受让人必须携手合作,应签署联合作业协议。协议内容必须包括:有关自然资源共享及费用分摊的详细情况、指定作业者、对独承风险运作的安排、渔业利益的调整、争议解决。第6条设立了作业者选择的僵局机制(deadlock mechanism):双方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选定作业者,如果无法确定将采取抽签的方式决定。
共同开发协议中,分区内特许权受让人的选择权留给了日韩双方。双方只需要通知另一方其特许权受让人,而无需另一国接受(但是特许权转让时需要其他特许权受让人的同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制度类似于强制性的一体开发,参与者对于合作者没有选择。这种制度的优点是双方无需达成共同的选择程序,可根据各自经济倾向性选择特许权受让人。[15](P118)双方政府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且能依据各自国内法律更快地确定特许权受让人。
4、开发区的法律适用
《1974年协定》第9条规定了开发区的法律适用,由不同分区块中进行作业者的所属国行使管辖权并适用其法律,即“作业者准则”。这种法律适用带来的后果是,共同开发区不同地区适用的法律和规定可能不尽相同,如果受让人组合情况发生变化,某个地区的适用法律也可能变化。这样的方式有其便利性,日韩不用为了协调不同的法律规则,或者制定一套新的法律规则,而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样,这也会带来一些复杂的情形。根据《1974年协定》第10条,基于商业性开采价值的自然资源的发现,双方租让权人的申请勘探权可以转化为开发权,此时分区内的作业者如果发生改变,法律的适用也会发生改变,这样同一个分区内勘探和开发期间需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
以上法律适用规则只适用于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事项,其他事项上存在例外。第一,共同开发区内的刑事法律规则的适用,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只在《1974年协定》中规定委员会可以提出适当措施的建议的原则性规定。第二,征收捐税和其他费用问题也是作业者规则的另一个例外情形。《1974年协定》第17条,规定了各方征收税收的情形以及一方不得向另一方征收税收的情形,会议纪要中也对各方征收税收的情形做了补充规定。第三,根据《1974年协定》,租让权人在共同开发区内开采出来的自然资源应视为该方在享有主权权利的大陆架上开采的资源,应当适用该方的法律法规。
5、争端的解决
《1974年协定》第26条规定,双方因解释和执行协定引起的任何争端应当首先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无法解决时应当提交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具有约束力。该条款对仲裁员的组合和权限做了规定,但是对于仲裁规则的适用并未做出具体规定。此外,该协议并未就受让人与国家间、或分区内共事的受让人间,争议解决方式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要求共事的受让人间达成的联合作业协议必须包括争议解决条款。
《1974年协定》中还对退还面积、权利移转、环境与安全保护、单一风险条款等事项的做了相关规定。
(二)共同开发的后续进展
《1974年协定》生效后,日本和韩国政府即正式发布共同开发区区块划分公告,授权有关公司可以进入共同开发区经营。第一轮开发至1987年5月结束,共八年,但未发现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油田。此后,日韩政府进行了磋商,双方对矿区的分配和钻探义务进行了协商。1987年8月,日韩双方根据《1974年协定》第3条第2款的规定,将9区块重新划分为大小大致相等的6区块,钻探义务从原来的11条减少至7条。1987年5月,日本新石油公司(Nippon Oil Exploration CO.)向日本政府申请了勘探权,但是直到该公司权利的最后有效期间(1989年9月),韩方都没有有效授权的石油公司。此后,没有进一步的勘探开发活动。
四、日韩共同开发案对中国的启示
日韩共同开发案虽然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但该案的法律框架和实施效果对中国与邻国共同开发仍具有启示作用。结合东海海域的周边环境、国际形势和海洋法的发展,中国与东海邻国海洋资源的开发面临挑战,但也存在机遇。
(一)进行海上共同开发之前,要充分评估拟开发区实际的经济效益
海上共同开发直接和最大的目的,就是及时有效地获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油气资源。日韩共同开发区勘探与开采工作进行了近10年,没有发现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最终搁浅。我们在进行海上共同开发之前,要充分评估拟开发地区的资源,以保证进行共同开发的经济效益。
我国周边海域政治环境紧张而敏感,首先,拟选择的区块应为双方主张重叠的区域,同时区块的选择宜小不宜大;其次,对拟选择的区块应提前做好科学评估,却有可开发的商业油气资源,否则共同开发协议签订后既没有发现商业价值的油气资源,又招致周边国家外交上的抗议,得不偿失。
(二)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国家间关系,对共同开发协定的达成有重要影响
日韩共同开发案的达成,是两国战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实现的。日韩同为美国的盟国,美国因素作为影响两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发挥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国家间关系,使得国家之间进行海上共同开发时更容易达成共识,也能较好地解决或者缓和共同开发过程中的争议和分歧。
因此,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在选择共同开发的国家时也要率先选择冲突和争端较小的国家,从易到难。在东海海域,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主要为三个方面:海洋划界的原则、海洋划界的方法、钓鱼岛的地位及其在划界中的作用。这三个问题短期内都不能解决,加之中日之间政治关系比较紧张,中日之间短期内实现共同开发难度较大。较之于中日关系,中韩关系较为缓和,中韩双方政治环境较为良好。2000年中韩签订了《中韩渔业协定》,协定在暂定措施水域共同开发渔业资源,虽然争端不断,但也是共同开发渔业资源的尝试。在南海海域,中国与文莱的海域主张重叠区较小,海上主权争端也只涉及南通礁,没有岛屿争端,从文莱着手将会是南海共同开发可能的突破点。
(三)充分利用联合委员会的职能
在共同开发中,联合委员会的职能范围随着选择开发模式的不同会有差异。但是,在共同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联合委员会这样一个平台,增强其常设性,发挥其监管功能、咨询协调功能。联合委员会成员可由双方政府高层、石油产业的代表、渔业环保等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并可包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组织的成员代表列席。双方可将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场所和机构,双方进行协商和协调,对共同开发的安排进行修改,协调解决开发活动中的争端。
国家可以授予联合管理局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开发区内作业活动的监管权、完善国家政策和协议修改的建议权等。这不仅有助于共同开发内日常活动的有效运行和监管,也可增强国家间合作和交流的紧密性和及时性,保证共同开发区内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顺利进行。
同时,可以借鉴马泰共同开发案中建立法律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的做法,由专家来讨论和设计具体的法律规则,送交两国政府审批。[18]此种方法制定的开发区规定,能与各自国内法律规定冲突达到最小化,并且更具有时效性。
(四)允许与不同国家间利益与义务分配机制的差异
在日韩共同开发案中,双方为石油开发的承包方设定了一系列详尽的渔业、环保、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尤其是对渔业利益的让步,对石油开采活动的限制。在石油资源开发的前景不甚乐观的情形下,石油公司作为一个追求盈利的私主体是否仍然愿意承担如此繁重的责任?这也是日韩共同开发的第二阶段,韩方没有石油公司提交开发和勘探申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设计共同开发方案时,我们应该注重利益分配与义务的协调,将不同层次的利益进行区分。海上资源共同开发不仅包括油气资源带来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潜在的利益,如海上基础设施的建设、雇佣机会的增减、能源安全的保障等。[19](P148)国家作为最终的受益方,更要考虑这种潜在收益;石油公司作为直接执行者,也需要得到其私主体应该分享的经济利益,因而国家之间、国家和承包商之间,都需要协调好彼此的经济利益和义务的分配。
在石油开发活动中,进行共同开发的国家可分享的利益包括直接和间接利益两个方面,前者包括授予石油合同、税收、矿区租赁的收益,后者包括国家通过上游和下游产业的经济链条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一个国家的石油产业越发达、市场越开放、地理位置优越,这种间接受益就会更多。[20](P158-159)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说,在共同开发协定中,我们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可以规定一个较为灵活的利益分享机制,并且根据我国与邻国国家情况的不同做出调整,这样才能吸引邻国与我们进行共同开发。
(五)中国在东海与邻国进行共同开发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四十年来国际海洋形势和海洋法规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约》大大扩张了国家管辖权的范围,造成了相邻和相向国家间加剧争夺有限的海域。国家间海洋利益的冲突加剧,以及立场的不退步,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决定了中国与东海邻国共同开发困难重重。
第一,海洋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韩签订共同开发协议时,《公约》还处于第二轮的谈判中,且经济区制度为讨论议题之一。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和随后发布的《埃默里报告》对日本的立场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影响。而《公约》已经成为了海洋法“宪章”,赋予了沿海国家“新”的权利,建立了完整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海洋法律意识的觉醒、对海洋油气资源的需求、海洋战略地位的重要,各国先后依据《公约》赋予的权利,主张最大范围的海洋权利主张。有限的海洋范围内权利主张的冲突和重叠愈加复杂,各国对海洋主张的立场也鲜有后退。
第二,日本海洋政策不断完善,建立起了完善的海洋法律体系,不段加强其海洋主张。1996年,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关于在专属经济区行使渔业等主权权利法案》以及《养护及管理海洋生物资源法》。此后日本又陆续制定了《水产基本法》、《无人海洋岛的利用与保护管理规定》。[21]200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根据《公约》第76条第8款的规定,向联合国外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日本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其中将“冲之鸟”礁作为岛屿处理,主张200海里的大陆架和外大陆架。此后日本为了巩固“冲之鸟”的岛屿地位,擅自在周围搭建防护设施,构筑离海面约7米的海上观测平台,并通过国内立法来进一步确保冲之鸟礁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律地位。[22]日本的这一系列举措都使得中日之间海洋争端更加复杂。在钓鱼岛问题和海洋划界原则问题上,中日立场仍然不可调和,且短期内无法解决。2008年中日公布了《关于中日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初步确定了中日在东海划定区域内进行共同开发的意愿,但是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近几年来伴随着钓鱼岛问题、南海局势,中日政治环境依旧十分紧张,中日共同开发困难重重。
(六)中国与东海邻国进行共同开发的出路
中国与韩国开启了海洋划界的预备谈判会议,共同开发阻力较小。中韩于2015年1月29日举行了中韩海洋划界的预备会议,中韩争议的苏岩礁问题是其中议题之一。[23]但是中韩划界协议在短期内达成的可能性不大,若中韩在划界期间进行海上资源的开发,既可以缓解两国渔业争端,也能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符合《公约》临时性措施的规定。[24]中日之间在领土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难以解决的前提下,虽然实现共同开发困难重重,我们仍可以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充分利用《共识》所达成的一致。中日在岛屿争端上仅涉及钓鱼岛,在区块选择上受岛屿争端影响较小,且《共识》中划出的合作区域不涉及中日双方争端。因而,有学者指出“共同开发”在这部分海域率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推行“共同开发”政策进展中,《共识》毫无疑问是走在了前面。[25]
第二,加强非政府层面和低敏感度层面的合作。日韩合作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政府机构,在日韩协定谈判和达成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中日两国的政治环境不利于海洋合作的开展,但是双方可以通过非政策层面的交往,加强两国往来和经贸合作,以经济合作的推动带动政治层面的合作。在低敏感度层面,双方可以在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的基础上加强渔业、海洋环境等方面的合作。双方经贸往来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推动两国政府层面合作的加强。
第三,继续在中间线中国一侧加强油气开发。日本和韩国共同开发侵害了中国和朝鲜第三国的权利,双方仍然强行推动双方共同开发的进程。反观中日之间的争端,焦点仍在于油气资源争端,而且东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主要在中间线中国一侧和钓鱼岛附近。中国已经在日本主张的中间线中国一侧成功开采出了石油,而日本并没有大的收获。若双方共同开发无法实现,我们仍应当继续在中间线一侧加强春晓等油气田的开采,给日方施加压力。中国与周边邻国进行共同开发,一方面要考虑第三方争议国家的利益并进行安抚,但同时也要勇于推进开发进程,以先行开发带动共同开发。
[1] 萧建国.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
[2] Takeyama Masayuki, Japan’s Foreign Negotiations over Offshore Petroleum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in the Japan-Korea Continental Shelf Joint Development Program, Robert L. Friedheim et al., Japan and New Ocean Regime, 1984.
[3] 蔡鸿鹏.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Germany v. Denmark and Netherlands), I.C.J. Judgment of 20 February 1979, 33.
[5] Choon-Ho Park, The Sino-Japanese-Korean Sea Resources Controversy and the Hypothesis of a 200-Mile Economic Zone[J].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75 Vol.16: 27-46.
[6] Akaha Tsuneo,A Cybernetic Analysis of Japan’s Fishery Policy Process, Robert L. Friedheim et al., Japan and New Ocean Regime, 1984.
[7] 1958年《大陆架公约》[EB/OL].http://www.un.org/chinese/law/ilc/contin.htm, 2015-01-30/2015-09-27.
[8] 曹忠屏,张琏瑰等.当代韩国史(1945-2000)[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9] 朱凤岚.“日韩大陆架协定”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亚太.2006,(11):32-40.
[10] (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 Ian Townsend-Gault, Rationales for Zone of Co-operation, in Robert Beckman et al., Beyond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2013.
[12] Agreement Minute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cerning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ntinent Shelf Adjacent to the Two Countries[EB/OL].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225/volume-1225-I-1 9778-English.pdf, 2014-12-25.
[13] Exchange of Note, January 30, 1974, Note b and Note c[EB/OL].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225/volume-1225-I-1 9778-English.pdf, 2014-12-25.
[14]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ncerning Joint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ntinent Shelf Adjacent to the Two Countries[EB/OL].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225/volume-1225-I-1 9778-English.pdf, 2014-12-25.
[15] Hazel Fox et al., Joint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989. Vol.I.
[16] Miyoshi Masahiro, The Japan/South Korea 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 of 1974", Hazel Fox et al., Joint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990, Vol.II.
[17] Clive R. Symmons,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Joint Development Zones, Hazel Fox et al., Joint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990, Vol.II.
[18]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laysia- Thailand Joint Authority, done at Kuala Lumpur on 30 May 1990[EB/OL]. http://cil.nus.edu.sg/1990/1990-agreement-between-the-government-of-malaysia-and-the-government-of-the-kingdom-of-thailand-on-the-constitution-and-other-matters-relating-to-the-establishment-of-the-malaysia-thailand-joint-autho/, 2015-7-3.
[19] Gavin Maclaren & Rebecca James, Negotiating 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s, Robert Beckman et al., Beyond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bon Resources, 2013.
[20] Thomas H. Walde, Financial and Contractual Perspectives in Negotiating Joint Petroleum Development Agreement, Hazel Fox et al., Joint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II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990, Vol.II.
[21] 杨洁,黄硕林.日本海洋立法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12,(2):265-270.
[22] Japan’s Submiss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pursuant to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Executive Summary[EB/OL].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jpn08/jpn_execsummary.pdf, 2015-3-10.
[23] 双方举行海洋划界谈判的预备会议[EB/OL].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5-01/29/c_127434969_2.htm,2015-3-10/2015-09-27.
[24] 傅崐成.海洋法相关公约及中英文索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25] 罗国强.“共同开发”政策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实际效果:分析与展望[J].法学杂志,2011,(4):14-17.
责任编辑:周延云
Japan and Korean Offshore Joint Development in Continent Shelf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Its Inspirations for China
Deng Niy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s offshore joint development is the first joint development case in the disputed sea area since th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 in 1969. Although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progress, yet it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Chin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s oil and gas dispute i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 shelf arose in the burgeo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1970s. The prediction that the East China Sea had a broad prospect of oil promoted the two countrie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ctivities in the overlapping area. During the progress from the negotiations to the effect of agreement, a number of factors exerted influences on it. Th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s joint development in continent shelf is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legal document, in which provides for joint development zone, joint authority, concessionaire and operator, application laws, dispute settlement and so on. Even there is no commercial oil and gas resources found in the zone after two rounds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is case gives some inspirations for China to propel joint development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continent shelf in the East China Sea; joint development; influential factors; legal framework; measures and inspirations
2016-01-1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海上共同开发国际案例与实践研究”(13JZD039)
邓妮雅(1988-),女,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海洋法研究。
D993.5
A
1672-335X(2016)02-006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