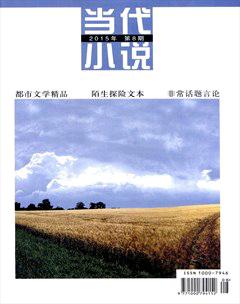歹人
项中立
1
枪毙我二爷爷那天,飘着细密的雨星子,但这丝毫不影响西水镇人看热闹的兴致。他们将西坨团团围住,在雨雾中眯起眼,一邊注视着坨子上被五花大绑的我二爷爷,一边耐心地等候那声结束一切的枪响。
我奶奶说,那场雨是那个春天的头场雨,架势拉足两三天,却始终下得不像一回事。西坨上几株野梨树,和我二爷爷枯瘦的身影,构成了那个雨天最动人的风景。
枪声响起之前,我二爷爷突然抬起了他的头,最后一次向人群里企望。
“我在这个时候走了过去。”我奶奶说。我奶奶迎着二爷爷企望的目光,庄严地走过去,像走在多年前的那个黑夜里,四周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死亡在河水中默默地含笑相迎……我奶奶走到我二爷爷跟前,旁若无人地搂过我二爷爷的脑袋,让他的嘴脸和鼻子埋进她的胸前,紧紧挤着她的乳房……
枪声终于爆响。我二爷爷徒劳地蹿了一下身体,旋即倒地。他的半个脑瓢被子弹掀碎,红红白白的东西泼到野梨树上,顷刻间被无数蝇虫覆盖。
我二爷爷倒地的同时,人群里也有个人应声栽倒。他叫罗嗑嗑,村革委会主任。在西水镇,他是惟一一个被枪毙我二爷爷的场面吓倒的人。
很多人围住罗嗑嗑(我奶奶说,围住罗嗑嗑的人,远比围住我二爷爷尸体的人多)。有人急迫地呼喊罗主任醒醒,有人狠命地掐住了他的人中。片刻,罗主任缓缓苏醒。他骨碌着两只大眼,茫然呆视着面前的人……突然,罗嗑嗑甩出个“八字指”,冲面前的人一点,同时嘴里“嘭”的一声响,在所有人诧异的瞬间,罗嗑嗑蹿起身,亡命而逃。
人们才晓得罗嗑嗑吓疯了。多年以后,我在西水镇念小学,常见一个衣衫褴褛、长发像松树鬃一样交错粘连在一起的人,极不耐烦地翻腾着街上每一个垃圾箱。找到可吃的东西,胡乱嚼几口,扔掉,继续翻腾,不知疲倦——这个人就是罗嗑嗑。在罗嗑嗑翻腾垃圾箱的时候,我们喜欢悄悄靠近他身后,用“八字指”点住他肮脏的沾满碎草屑的脑袋,嘴里突然爆出“嘭”的一声。这时的罗嗑嗑,慌张着扔掉他找到的任何可吃的东西,蹿起身,头也不回地亡命而逃……
罗嗑嗑最终死在了西水镇南面一个废弃的涵水洞里。那是个冬天,人们无意中看见他时,他早已冻成了一根硬木棍。
我奶奶说,那个哀伤的雨天,她孤独地驾着一辆排子车,将二爷爷的尸体从西坨上拉回老坟葬了,没人给她搭手——我爷爷多日前不知去向;整个西水镇的人,在枪声响过之后,一哄而散……“我们家是右派,老二又是被镇压的人,”奶奶说,“没人愿意帮我一把。”雨中的西坨,土地愈加松软,深深陷住单细的车轮,我奶奶每走一步,都得付出巨大的体力。奶奶走下西坨的时候,罗嗑嗑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他跟在排子车后面,拿“八字指”点着我二爷爷血葫芦一样的脑袋,唇间“嘭嘭”地乱响。每响一声,奶奶背上,都像有根针,尖锐地刺进脊骨……
二爷爷被枪毙后的一天夜里,我爷爷才回来。奶奶歇斯底里地哭嚎着,她让自己的手指变成了锋利的刀尖,在我爷爷脸上留下无数道血口子。
“老二死了,”她说,“二国他……枪毙了……”
奶奶说,“他的罪名是破坏军婚……破坏军婚……”
爷爷沉默着站在黑夜中,呆着脸,任我奶奶疯狂地抓挠。血顺着下颏缓缓流淌,新鲜的血腥味儿招来无数黑暗中的蝇虫。他不去惊扰它们,他默认它们在他脸上频繁地滑行和吸吮……
那夜之后,我爷爷断绝了和林孔雀的揪扯。
2
二爷爷耳朵灵怪。在安静的夏夜,他蹲在堤坝根下,能听见鱼群在西水河里游泳。他把网撒下去,总能捞上些白瓷瓷的鲢子鱼。奶奶将鲢子鱼刮鳞去内脏,撒些粗盐腌好,等着我爷爷从柳寨回来一起吃。那时候,爷爷在相距六十多里的柳寨教中学,每个星期都要回来拿些换洗衣物。爷爷步行六十多里,要两三个时辰,黄昏到家,住一宿,翌晨返回。爷爷前脚进院,奶奶就把灶火点燃了,然后,将腌好的鲢子鱼放进锅里,再淋上几滴油,不消半袋烟工夫,煎鱼的香味就盈满三间老瓦屋。爷爷和二爷爷喜欢在我奶奶把煎鱼端上桌时喝一点酒。爷爷在酒后喜欢卖弄地背诵古诗。爷爷背诵古诗的时候,二爷爷低着头默不作声,我奶奶却把脸仰得高高的,眸子闪着兴奋的亮光。她佩服爷爷的才气。当初,奶奶正是看上了爷爷的才气,才选中了比我二爷爷大了七八岁的我爷爷。
吃完饭,天完全黑下来,二爷爷孤独地穿过堂屋,回他屋里睡了。二爷爷睡觉鼾声如雷,但是我爷爷回家这一夜——至少是前半夜,二爷爷屋里是安静的,二爷爷连他的呼吸都放得轻柔。
爷爷走后,奶奶满面春风地给二爷爷挤媚眼。二爷爷哼一声往外走:“你骗不了我!”
奶奶悻悻地皱皱她的眉,然后,她变得若有所思,常常让手里的东西找不到该放的地方。
其实,奶奶一条命,是二爷爷从西水河里抢回来的。
那年,二爷爷被村里指派护瓜田——这得益于他的灵怪耳朵,他总是在偷瓜贼还没有靠近瓜田时就捕捉到动静。于是,二爷爷和另外一个看瓜人提着胳膊粗的枣木棍,在瓜田里气势汹汹地巡视,致使那些偷瓜贼恨恨地望风而逃。
有天夜里,二爷爷突然从熟睡中惊坐而起。他说听见一个女人喊救命。另一个看瓜人仄着耳朵倾听一番,什么也听不到,他说罗二国你是吵惊吧?二爷爷肯定地说没有。他循着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的喊声,寻到半里路外的西水河边。半个时辰之后,二爷爷抱了个湿漉漉的女人来。女人身子软塌塌的,但她没死——当她被河水冲入那片小柳丛时,她突然不想死了,她虚弱地呼喊……柳枝把她衣服上所有的纽扣都刮脱了,她的白瓷瓷的乳房裸露无遗。我二爷爷是个腼腆男人,他几次抖着手,想帮她把衣服抻一下,但最终也未能鼓足那股勇气。
这个流浪的女人,吃过我二爷爷为她摘的瓜,说,你们这地方瓜真甜。她最终成了我奶奶。对于这桩婚事,教中学的我爷爷颇有些意见,但他招架不住我太奶奶的目光——那时候,我爷爷的母亲,我的太奶奶还活着。她凌厉的目光不容置疑地告诉我爷爷:你别无选择。在她老人家看来,随便一个蹲着撒尿的,都配得上一个右派的光棍崽子!
我爷爷跟我奶奶成亲之后,我二爷爷的耳朵突然失聪。他不光听不见别人听不见的动静,连对面讲话,也不应声。也许他是听见了,他只是固执地不肯说话。他总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走路。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半年,他的耳朵才恢复了从前的灵怪,脸上也有了表情,有时候,还大着胆子,跟我奶奶开句玩笑:
“两个馒头热不热呢?”他指着我奶奶一对鼓突的乳房。
“摸下才晓得哩!”我奶奶佯装解脱纽扣儿,二爷爷却慌张着溜掉了。他的慌张,叫我奶奶放荡地大笑不止。我奶奶喜欢这样笑。
有天傍晚,我二爷爷被罗嗑嗑押上了西坨。罗嗑嗑喜欢在走动时,背上他的大砍刀。他那把大砍刀和电影里洪常青的砍刀一模一样,刀柄上系了条红绸子,有风拂动时飘扬起来,像窜动的火苗子,让罗嗑嗑看上去威风凛凛。不过,罗嗑嗑的砍刀不是铁打的,是木头做的。村里拐木匠在制作这把木刀时很费了些心神,活儿来得细致。他是个巧妙的手艺人。他把做好的木砍刀涂上层白亮银粉,这让它看上去蛮逼真,有了钢铁的寒气。
西坨上盛开着野菊花和白刺苋。野梨子也熟了。秋后的晚霞热烈而神秘。二爷爷低着头,在一株野梨树下垂手而立,样子十分猥琐。这是二爷爷最熟稔的姿势。他是右派子女,他不能在革命干部面前仰着脸等待命令。
“你想不想进步?”罗嗑嗑从背上解下他的砍刀。
“想。”二爷爷仍是低着头。
“算你识抬举。”罗嗑嗑把他的砍刀在夕阳里夸张地舞着,一刀一刀地刺向树上的野梨子,仿佛那是令他十分愤慨的阶级敌人。“现在,我代表革命组织交给你一项秘密任务——”罗嗑嗑准确地刺中一颗硕大的野梨子。野梨子掉下来时,砸到我二爷爷头上,二爷爷更深地埋了埋头。罗嗑嗑说,“秘密窃听村里黑五类的谈话。”罗嗑嗑捡起那颗野梨子,粗鲁地咬上一口。
按照罗嗑嗑的指示,二爷爷在每个安静的深夜,偷偷潜伏到黑五类家院门外面,隔着长长的院落,窃听他们在各自屋里的谈话内容。只有二爷爷具有这个本事。第一次,二爷爷听见地主分子跟他老婆说“要变天了”。二爷爷把他听到的话报告给罗嗑嗑。第二天,地主分子委顿的身影便摇晃在村街上。他脖子上挂块木牌子,上写“地主分子某某某”。槐木牌子压人,他不得不把头深深埋下。他一边委顿地走着,一边懒散地击着一面炸了裂璺的破铜锣,同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某,我说要变天了,我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的受过硬伤的腿,一瘸一拐,显然疼得厉害。但是,罗嗑嗑背着他的大砍刀跟在后面。罗嗑嗑不允许他停下歇会儿,他只得艰难地走下去,直到一场大雨如约而至。
第二次,二爷爷窃听到某个右派躺在被窝里跟他老婆说“我得把它记在我的账本上”。他老婆说“这也要记?”右派说“要记。”二爷爷如实报告给罗嗑嗑。这引起了罗嗑嗑的高度重视。押着右派游街的时候,罗嗑嗑把白刺刺的大砍刀架到右派脖子上,逼迫他赤裸裸地揭露自己:“我打算把我老婆养的那只鸡下了多少蛋记在账本上,到它收窝时算算总共下了多少……我不该偷记变天账,反攻倒算,我罪该万死……”
整个秋天,村街上频繁地响着游街的破锣声。那面破锣最终被击碎了,罗嗑嗑就买了一面新锣。但罗嗑嗑想,坏分子是没有权利使用新锣的。罗嗑嗑就用他的大砍刀先将新锣敲出裂璺,听上去声音破衰,才肯交给坏分子拿去游街。所有游过街的坏分子无一例外地纳闷:他们躺在被窝里说话,罗嗑嗑怎么会晓得?后来他们慢慢弄明白,這是我二爷爷帮他窃听。再见到我二爷爷时,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打哑语,做手势。但他们看我二爷爷的目光里长了牙齿,恨不得将我二爷爷嚼碎了,像吐坨痰那样吐到阴沟里去。在他们眼里,我二爷爷是个令人讨厌的歹人。
村街上一时间安静了,那面破锣被不情愿地闲置在罗嗑嗑家。这让罗嗑嗑十分恼火。他说要农闲了,公社领导一再强调,越是农闲越要狠抓阶级斗争。他的大砍刀在我二爷爷面前胡乱地挥舞着,命令我二爷爷找根结实苇篾子,把耳屎挖干净,再去窃听。
但我二爷爷仍是一无所获。
又一个傍晚,罗嗑嗑将我二爷爷再次押上西坨。野菊花和白刺苋早已凋零。野梨树脱光叶子,瘦骨嶙峋地立在寒风里。隆冬的晚霞稀薄而脆弱。
“罗二国,你还想不想进步?”罗嗑嗑严肃地盯视着我二爷爷。
“想。”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罗嗑嗑庄严地为我二爷爷正了正军帽。那年月,几乎每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都有一顶绿色军帽,或者一件仿制品。我二爷爷是右派子弟,我敢肯定,他当时戴的是件仿制品。罗嗑嗑说,“你哥罗大国回时,及时给我报告。”
“你想让他游街?”
“我无计可施。”
“他是革命教师……”
“你没有资格跟我辩论!”罗嗑嗑不耐烦地抄起他的砍刀,在我二爷爷面前焦躁地挥舞,“记住,他和你一样,是右派子弟!”
罗嗑嗑的命令像块死沉的石头,压在我二爷爷的心口上,叫他茫然不知所措。这天夜里,他的屋里一直安静着,没有寻常的鼾声。这表明他一直醒着。这让我奶奶感到了诧异和不安。没有人比我奶奶更了解我二爷爷。他们隔着一间堂屋住了这么些年,深知这个男人没有鼾声的时候,不是遭了大病,就是窝着天大的心事。当年她决定嫁给罗大国时,他的屋里就安静了许多个夜。那时候,她晓得这个男人的心事。她一直觉得愧对这个救命恩人。但她觉得爱和报恩不是一回事。她爱的是罗大国有才气。他会背诵那么多古诗,他的眼镜松松垮垮地搭在鼻梁上的样子,让她怦然心动……
可是今夜,罗二国,这个男人,他心里又窝了什么心事呢?这个夜里,我奶奶赤着脚,在冰冷的屋地上不安地踱着碎步。她想穿过隔开他们的堂屋,去摸摸他的额头。她希望他只是病了,发烧了,没有别的事叫他闹心,叫他痛苦得丧失了鼾声。可是她最终没有足够的勇气跨过堂屋,她只是赤着脚,站在她的屋地上,向我二爷爷说:
“你怎么了?”
二爷爷沉了一会儿才说:“我得跟他谈谈。”
“跟谁?”
“罗大国。”
这个星期天,我爷爷罗大国从柳寨回来,还没进家,就被我二爷爷截去了西坨。
我二爷爷是个不喜欢绕弯子的人。他让自己隐忍了愤怒的眼睛硬生生地直视着罗大国:
“那么肥的一块地,为什么就一直荒闲着?”
“这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后来我爷爷回忆,那天他们在西坨待了半个多时辰,好像只说了这两句话。这话别人是无法破解的,只有他们自己晓得,肥地指的是我年轻的奶奶。
那天,我爷爷从西坨回家不久,罗嗑嗑就找上门,将一面破锣扔到我爷爷面前,不容分辩地说:“游街去,接受改造!”
显然是我二爷爷报告无疑。
二爷爷似乎抱定一不做二不休的念头,他总是在我爷爷从柳寨回来的第一时间,跑去给罗嗑嗑报告。所以,罗嗑嗑总是能够及时地把破铜锣扔到我爷爷面前。后来,我爷爷改变了惯常的做法,先在村外庄稼地里潜伏下来,等到夜深人静再进家。爷爷不敢从门里走,总是轻轻地从窗户里,被我奶奶接应进去。但这毫无用处,砂子粒儿掉进水缸,我二爷爷的耳朵都能捕捉到声音。当我奶奶和我爷爷心惊胆颤地听见二爷爷沉着地打开堂屋门,往外走去时,他们的心不约而同地变得哇凉。过不了半袋烟工夫,罗嗑嗑就会准时地将那面破锣扔到我爷爷面前。我爷爷烦透了他的兄弟罗二国。他们的目光不期而遇时,简直都能撞出噼噼啪啪的火星子。这让我奶奶极度不安,害怕两个男人有一天会动起手来,让村里人看笑话。有一天,我奶奶跟我二爷爷说:“想想你哥他的苦吧,六十多里走回来不容易。”二爷爷说:“他想过你的苦吗?”二爷爷用一根竹篾子耐心地挖着耳朵。现在,二爷爷闲下来就挖他的耳朵,我奶奶不用想也晓得,他是为了及时准确地捕捉我爷爷的信息。
“这么些年他碰过你一回没有?”二爷爷最终把沾满耳屎的竹篾子抛掉,掸掸他的耳朵,样子很轻松。“你不用骗我,我什么都晓得。”
奶奶是愣怔了一会儿的。她为我二爷爷不留情面地戳穿她掩盖已久的生活,而不知所措。跟着,我奶奶又大哭起来。奶奶的哭和笑是一样的放荡,听上去像个哀伤的泼妇。
3
我爷爷罗大国潜伏在茂密的庄稼地里。成群的花翅蚊子和蚱蜢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的手背上,脸颊上,脖颈上,凡是裸露的皮肤,迅速鼓起层层毒包,疼痒难忍。我爷爷在挥手阻止蚊虫们进攻的同时,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弄出突兀的动静,有社员在不远处的庄稼地锄草,倘若被他们发现,那将是件蛮糟糕的事情。
田野里到处盛开着蓝色的打碗花和黄色的芥菜花。晚霞降临的时候,打碗花和芥菜花会慢慢收拢它们漂亮的花瓣。这个时候,锄草的社员们收工回家,田野里阒无一人,我爷爷才能钻出闷热的庄稼地,到前面的树林里透口气,然后,还要等到村里的狗吠安歇下来,才能贼一样潜进村里。
“我爷爷他干嘛非要回来呢?”我小时候,这样问过奶奶。
“他怎么舍得不回来!”我奶奶把一块酸甜的野梨子填进我嘴里,“那时候,你爷爷整日惦记着林孔雀,七天回一次,那是他惟一的机会。”
那时候,我爷爷已经改变了先回家,后去会林孔雀的习惯——他在村外潜伏到深夜,进村先去会林孔雀,然后才回奶奶屋里。虽然这样仍是躲不过击着破锣游街,但是我爷爷说他心里是兴奋的,念“街文”(我爷爷管游街时念的词儿叫街文)时也琅琅上口。爷爷暮年时,曾击着奶奶的洗脸盆给全家人演示过自己当年游街的情景——爷爷慢慢地踱在屋地上,做出那种因跋涉过六十多里路,而十分疲乏的神态,击一下洗脸盆,念一句“街文”:
“我叫罗大国,
咣——
谁都认识我。
咣——
深夜来街游,
咣——
耽误大家伙儿……”
全家人都笑。奶奶和爷爷笑得尤其热烈。我从他们的笑声里,感觉出他们已经原谅了二爷爷深夜告密的行为,或者原谅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有的小人物们……
我爷爷当年在县城念中学时,和林孔雀是同学。那时候,漂亮的林孔雀担任着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主唱。她的歌唱得非常棒,总是能够赢得最热烈的掌声。很多男生都喜欢他,乐意把他们写满褒扬的信笺当做情书,偷偷放进她书包里。我爷爷也不例外。虽然我爷爷是右派子弟,没有资格给林孔雀写情书,但这挡不住他喜欢林孔雀。我爷爷中学没毕业就到乡下当了代课教师。我爷爷在乡下教书的枯燥日子里,始终没有忘掉漂亮的林孔雀,他甚至在自己的臆想中,频繁地完成着一次又一次手淫。
林孔雀中学毕业之后,放弃了保送上大学的机会,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做了最后一批下乡知青。她的事迹在当时的报纸上有过报道。后来,林孔雀经人介绍,嫁给了从我们西水镇当兵出去的罗排长,成了我们西水镇的媳妇。林孔雀做了几年随军家属之后,不明缘由地回到我们西水镇。我们县的县报在“舍弃军营,建设家乡”的大标题下,做了详尽的宣传报道。林孔雀有这个本事,她总是能让自己随时随地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那时候,我爷爷还没有娶我奶奶。我爷爷每次回来,都能看见林孔雀穿着军人的白衬衣和裤子,若有所思地在她家院里散步。林孔雀喜欢把白衬衣扎进裤腰里,这副军人的做派,是让我爷爷留恋家乡的惟一理由。
我爷爷跟林孔雀第一次碰面是一个早晨。在村口,回学校的我爷爷和散步的林孔雀不期而遇。
“你好像一點都没变。”林孔雀说。她大方地伸出一只手。
“呵呵……怎么会呢,十年都过去了……”我爷爷缩缩手,没敢迎接她。
“你真的没有变化。”林孔雀自己解围似的把她的手在空中晃了晃。她好像捉住了一只在空中飞翔的瓢虫。“你让我想起了咱们的中学时代。”
“呵呵。”
又一个早晨,仍是在村口,林孔雀截住了我爷爷。这一次,她好像是专门等在这里。
“你就没有去我家坐会儿的想法吗?每天就我一个人,我很孤独。”
“你知道我是右派子弟,让人看见对你不好……”
“你可以晚上来啊,或者夜里……夜里是不会有人看见的。”
就这样,我爷爷和林孔雀有了揪扯不断的关系。这也是我爷爷不愿娶我奶奶的主要原因。
在我二爷爷没有去报告之前,我爷爷总是挨到后半夜才借机造访林孔雀。这件事,我爷爷和林孔雀做得相当谨慎,以至于几年里,我奶奶和所有西水镇的人们一样,毫无察觉。
林孔雀跟我爷爷说,她和罗排长的婚姻早已面临绝境,原因是罗排长将要升任罗连长。“他枉穿了那身军装!”她说。她在黑暗中恶狠狠地点燃了一枝香烟。她吸烟的样子十分稳练,这表明她不是初吸。“我等着他下最后的决心。”黑暗中,我爷爷把林孔雀紧紧地抱在怀里。她已是十分消瘦了。她的胸癟到平庸,她的锁骨瘦得像木柴棍,硌疼了我爷爷的胸口。对于她和罗排长的事,我爷爷无能为力,他只能这样紧紧拥着她,让她感到还有一点力量属于她。
我爷爷和林孔雀的交往辛苦而隐秘。但在我爷爷枯燥的教书生涯中,这是件极有乐趣的事情。在我爷爷看来,跋涉六十多里土路,然后蹲在庄稼地里,忍受蚊虫叮咬,比起跟心仪的林孔雀幽会,获得半宿欢娱,实在算不得什么。
那个夏天,罗排长回乡探亲,住了半个多月才走。这半个多月里,我爷爷总共有三次回家的机会。他看见魁梧的罗排长像林孔雀那样穿着白衬衣,在他家院子里打太极,不得不把自己想念林孔雀的冲动残酷地压制住。他把自己关在奶奶屋里,孤独地喝着闷酒。那时候,他和我二爷爷相见无话,关系非常紧张,不再像从前那样邀请我二爷爷一同喝酒。他只是自己喝,这样,他很快就会把自己喝醉。
每次喝醉之后,爷爷总是满怀激情地将我奶奶狠狠压在她的炕席上……
4
因了那夜的沸腾,西水镇人记住了那夜的月光。
那夜前半夜,我奶奶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奶奶烦躁地打开了窗户和门,让凉爽的夜风从她屋里穿堂而过。是我爷爷回家的日子,可还不见他的影子。有一段时间,我爷爷总是说半路上有座桥塌了,他得多走六十里路,绕道另一座桥才能过河,所以,他总是到后半夜才进家门。我奶奶对我爷爷的话深信不疑。
街上突然有人呼喊。我奶奶听不清喊什么,就问那屋的我二爷爷。我二爷爷说,林孔雀被强奸了。我奶奶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爷爷。我奶奶至今都弄不明白,那一刻怎么就成功地把我爷爷跟林孔雀揪扯到了一起,她原本是不晓得他们的事的。我奶奶一直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
我奶奶赤着脚跑到外面,她才发觉那夜的月亮出奇的圆,出奇的大,白瓷瓷的,亮得灵怪。街上已经沸腾了,到处都是人,民兵们紧急集合,满街上响着拉枪栓的“哗啦”声。我奶奶一屁股坐到了白瓷瓷的月光里。
我二爷爷也跑出来。他竖着灵怪的耳朵,在村里背人的角落谛听。他终于听见某个草垛里面有异常动静,像胆怯的小鼠在颤抖。
二爷爷说:“哥,你出来吧,没有别人。”
我爷爷从柴垛里钻出来,浑身都在颤抖。二爷爷说:“到底怎么回事?”我爷爷说,他刚从林孔雀家出来,就撞到了罗嗑嗑。二爷爷说,哥你不能回家了。二爷爷拉起浑身筛糠的我爷爷,曲里拐弯地绕着街巷走。二爷爷把他的耳朵机警地竖着,一路上,他们总是能够先知先觉地绕开巡逻的人们。
二爷爷最终成功地把我爷爷送到村外面。二爷爷脱下自己的鞋叫我爷爷穿上。一路走来,他听得清我爷爷脚上只有一只鞋。二爷爷说:“哥你也不要回学校了,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躲,风声过了再回来。”
二爷爷穿着我爷爷的一只鞋往回走。他听见街巷深处响着嘈乱的脚步,晓得那是罗嗑嗑率领的巡逻队在搜查。二爷爷定定神,从容地迎着他们走过去。
白瓷瓷的手电光一下子照在二爷爷赤着的那只脚上。
“绑了他!”罗嗑嗑突然叫道。
二爷爷就被结结实实地绑了。后来二爷爷才晓得,罗大国和罗嗑嗑在林孔雀家门口相撞时,脚下慌张,甩丢了一只鞋,顾不得找,便向西而逃;罗嗑嗑手里是提着那把砍刀的,被罗大国一撞,飞出手去。罗嗑嗑当时以为撞上猛鬼了,妈呀一声,抱头向东而逃。后来,罗嗑嗑带人回去寻刀时,意外捡到了那只鞋。罗嗑嗑断定,强奸林孔雀的歹人赤着一只脚逃不远,率人沿街搜查,就把二爷爷擒住了。
因为林孔雀是军官家属,又被报纸多次宣传报道过,有关部门对这起案件十分重视,连夜组织突审。西水镇革委会的院里院外,白瓷瓷的月光里,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林孔雀是受害人,自然被请到了审问现场。她坐在一把椅子上,我二爷爷五花大绑跪在地上。
调查人员问林孔雀:“是罗二国强奸了你吗?”
林孔雀说:“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二爷爷说:“是我。”
林孔雀说:“是他。”
又问:“罗二国怎样强奸的你?”
林孔雀说:“心太慌,记不清。”
二爷爷说:“我把她压在炕席上。”
林孔雀说:“他把我压在炕席上。”
二爷爷最终被判死刑,两天后执行,罪名是破坏军婚。
二爷爷被执行前一天,我奶奶去监所探视了他。隔着那面厚厚的玻璃墙,她看到我二爷爷精神蛮好,一点都不显得哀伤。
奶奶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二爷爷说:“这事总得有人出来挡,不然没个完。”
“你只是为了那个男人?”
“我是为了你,还有他(她)。”二爷爷指了指我奶奶的肚子,“我晓得罗大国动了你三回,你肚子里有了……”
我奶奶的眼泪,顷刻间夺眶而出。
我奶奶哀伤地凝视着我的二爷爷。他在用他的手指徒劳地挖着耳朵。这是他久已形成的习惯——在他觉得无所事事的时候,用一根竹篾子有一搭没一搭地挖他的耳朵。可是,监所里连根竹篾子也没有,他只能用粗笨的手指头在耳朵上做着那个熟练的动作,看上去固执而机械,一点都不生动。
“我觉得他心里其实特别空虚。”多年以后,我奶奶在回忆那个情景时,总是这样说,“透过泪水,我发现这个傻男人的目光躲躲闪闪,是那样的不自在。有好几次,我看见他把目光不自主地搭到我日渐鼓突的乳房上。我懂这个男人,我晓得他在想什么……在他被执行的前一刻,我走向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他湿漉漉的嘴脸挨紧我的乳房……那个傻男人,在枪声响起来的刹那间,我看见他笑了……”
5
枪毙我二爷爷的枪声,在西水镇的天空回响了好些时日。
林孔雀被强奸的案子了结以后,有关部门把严惩歹人罗二国的情况通报给罗排长所在部队。部队领导命令罗排长立即将林孔雀接回了部队。林孔雀走的那天,西水镇凭空起了一场风暴,刮起来的砖石瓦砾,将罗排长开来的军车玻璃都砸碎了。罗排长说,要不等风煞了再走吧。林孔雀摇摇头。军车就顶着猛烈的飞沙走石开走了。从此,西水镇人再没见过林孔雀。
奶奶生下我父亲时,二爷爷坟头已经被茂盛的燕子草和苋齿菜覆盖。爷爷辞了教书的工作,终日与妻儿相守。但是爷爷却是沉默寡言的,喝过酒了,也不再背诵古诗。有时候我奶奶逼他背一首听听,他说:“我都忘记了。”
每逢二爷爷忌日,爷爷总忘不了到他坟头烧些纸钱。爷爷会看见一束祭花早在他到来之前,就安静地放在那里。祭花染着晨露,栩栩如生,显然来自城里。爷爷晓得是谁来过了,也晓得她离开得不会太久,但爷爷从没有找过她。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