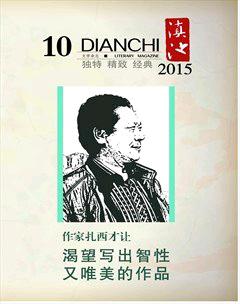长河(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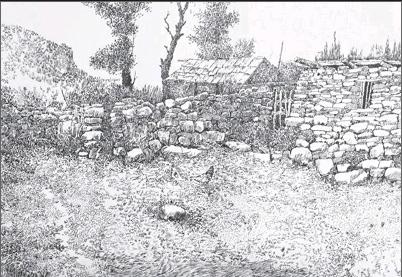

李达伟,作家,现居云南大理。
河流:文明与灾难共存。从一条河流上能够清晰地看到:孤独即死亡。
在文明与灾难面前,我们能看到佛的样子,神灵的样子,以及魔鬼的样子。就像那头被洪水冲走的老水牛,洪水翻腾汹涌,但它丝毫不慌乱,借助水的浮力漂着,显得很安静。那些浑浊的河水,是那头老水牛所喜爱的。最终,那头老水牛,被洪水冲了有两公里后,安然无恙。那次洪水,有无数的牲畜被冲走,有些成了浮肿的尸体,有些下落不明。
那次洪水,上游冲下来了许多木头,同时还冲下来一些动物,人们纷纷去打捞那些木头,人们纷纷去棒打那些落水的动物。那个民间,在那次洪水中,收获了无数的动物和植物。人们在那个夜间,啖野生的肉吃大碗的酒,那些打捞上来的湿材,在火中吱吱地响着,所升腾出来的烟雾熏得人们直咳嗽。烟一直熏了好几天,把那个民间的白日熏成了黑夜。
那个民间,面对那次洪水,对冲走的良田,很不是滋味。在啖肉饮酒时,那样的滋味早已不在,更多的是感激竟有这样一场多年不遇的洪水。村寨里的那个模样像傻子的木头,把一口野猪肉放入嘴里后,把内心里面的想法吐露出来,希望明年还有那样一场大的洪水,或者比那场洪水还要大的洪水。那个民间听到木头说出那样的话后,面面相觑。到底是再来一场那样的洪水好呢,还是不来好呢?当时,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再次想到了冲走的良田,以及良田种植的那些玉米,长势正好的玉米,不出意外这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又可以有许多的玉米粑粑了。玉米粑粑和肉类之间,那个民间不知道到底该认可的是玉米还是肉类?悖论横生的世界。目光清澈,抑或目光短浅,抑或是无法定义。
洪水消退,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捡拾那些搁浅在河谷中的木头。那次人们捡拾的木头,够那个常年都烧柴火的民间,烧很长一段时间了。在那个春节,那个民间比往年清闲很多。往年的春节,人们休息两天后,便提着斧头朝群山深处走去,为了砍伐至少要够一年烧的柴。那个民间,便是在清闲的日子里,发现了那条河流便是神便是佛。河神、山神、植物之神以及那个民间的佛,出现在了那个河谷。人们纷纷拿出了供品,那个民间的巫师带领着村寨里的男女老少出现在龙王庙。巫师是那个民间意识形态的代表,那个巫师在庙宇里悄声地和神灵鬼魔对话,所有人都听到了巫师的念念有词,由于太过轻声,没有人听清楚,但没有人会怀疑巫师。那个民间在巫师的指点下纷纷跪下了,并磕了三个虔诚的头。祭祀仪式结束后,人们坐于庙宇前的空地上,轻松愉悦,然后开始大口喝酒大口啖肉。到了下一年,洪水再次来临,比往年更加迅猛,那年再次冲走了许多的良田与庄稼,木头依然还从上游冲下来,但没有任何野生动物。只有作为人的木头按捺不住内心里的欲望,说出了内心的渴望,怎么就没有去年那么多的野物呢?人们再次面面相觑。
在河流里,可以见到佛的样子。可以在一块岩石上看到佛的样子,也可以从河流里的倒影里看到佛的样子,也可以在一条鱼身上看到佛的样子。而在那个民间,现在看到更多的是恶鬼和魔的样子。
河流里注满了灾难与文明。某个诗人如是说。
2
雕刻:手艺的发源伴随着的往往是手工艺人生存的艰难,雕刻可能也是源于这个原因。当然,源于民间的智慧,也应该是原因之一。民间艺人的生活,某个群体的生活,只是民间艺人生活得比常人丰富些或者枯燥些而已。更多时候,民间艺人丰富了一群人。民间艺人,很多时间里是在一个创造的世界,创造了音乐,创造了神灵(像甲马)。
民间艺人,用心灵观察民间,长时间这样观察。民间艺人,爱一切,特别是自然。然后,才是民间的手工艺,才是日益精湛的手工艺。那是多年以前,我读高中,出现在滇西北的某个村寨,那个寨子的名字,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不清。那样模糊的背后,是那样的村寨存在着很多。在那些村寨,几乎家家都有木匠,有时甚至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参与到木匠活中。这些村寨里的木雕,经过了变迁,从纯粹的手工雕刻演变到了机器介入,但其中一些部分,还需要人亲自去做。我有一些高中同学,生活在那样的村寨中,他们读书的同时,脑子里回响的是雕刻的声音,其中某个人跟我们说起过他的想法,他不想读书了,他要回去帮家人,更何况回家成为一个木匠收入也是很可观的。有许多这样的人,靠手艺生活,还生活得很好。我曾多次跟着那个同学进入那个村寨,他的两个姐姐初中毕业后,就回来家里成为女木匠。木头的香气,在那些空间里缭绕,我深吸了好几口气,感觉很舒服。那样的舒适感,让我心生羡慕,我想成为一个木匠,而最终一些原因的阻挠,我没能成为一个木匠。有些民间手艺人的生活,却不如意。一些民间手艺,正处于被淘汰的边缘,工业化对于民间的侵吞,迅疾,泥沙俱下。
雕刻,这里主要是木雕。窗格子,以及上面的雕刻,自然物象居多,主要以花鸟虫鱼兽为主。这条关于木雕的河流,里面融汇着真正的一条河流,以及河流两岸的生命。有一只鹿,在一棵大树下安静地站着,它的眼睛里,盛满了一个天空的湛蓝清澈。那些民间,以物寄托一些美好的东西。
在木雕上,可以发现一个民间的想象力。民间手艺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即便在那么一段时间里,他们为生活所困,但在制作一个手工艺品时,依然能感受到他们超人的冷静与安静。他们把思想的空间打开,让思想在天地之间遨游。思想在天地间的行走,所带来的便是艺术品被自由
逝水无痕(线描) 桑子
的因子被自然的因子所滋养,然后便是手工艺品的浑然天成。刀法,是经过练习的过程,我为何最终没有成为一个木匠,主要就是刀工不行,在平时我也没有多少兴致去练习刀法,也没有人强迫我去练习刀法。而我的那个同学,以及别的许多人,首先是在一种环境的濡染下,从小就自觉不自觉地练习刀法,他们成为了一群小小的刀客,他们从小面对着的便是一片森林的局部,并感受着一片森林的气息。森林便是一个宏大的自然界,一片又一片的密林,里面有着花鸟虫鱼兽,便有着万物众生的自由。自由,他们应该是感受到了来自一个民间的自由。
在雕刻的过程中,顺着木质,并不刻意。这里提到的木雕,主要集中于剑川那个小县城的各个民间里,县城的建筑里,木雕是最有特色的。而从那个小县城往外扩散的别的民间里,依然看到人们对于木雕制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对于木雕的坚守,似乎暂时也没有什么新生事物对那些民间里的木雕进行冲击,这与一些民间里的别些手工艺不一样,一些手工艺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有些甚至已经溃不成军。
洱海边的老木船客栈,很精致,里面同样有着木雕的介入,那又是一个浓缩的民间,里面更多的元素是白族木雕、白族文化以及白族民间的东西。在大理,真正的民间,里面注满了并不变质的手工艺。
一个建筑,包容了多少民间的手艺。一个建筑,同样在比照着各种手工艺的生死存亡。在那些民间,大部分的建筑,便是手工艺制造的物。
雕刻史,也是一条长河,某个诗人如是说。
庙宇:似乎在我的文字里,不断被重复,而其实是不断被我认知的过程。在那么一段时间里,庙宇里,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的真实,特别是作为人的隐秘的真实外露。人们在庙宇面前,在一个巫师面前,都会把内心的想法以及自己的过往真实袒露,一个又一个民间,面对着庙宇和巫师忏悔。庙宇,成为一种思辨和反省的场所。一个民间,面对着那些鸡头鸡尾,思考着一个民间的过往、现在以及未来。即便到了现在,在某个节日里,一个民间依然信奉着来自鸡头和鸡尾里的暗示。面对着那些鸡头鸡尾,只有一些人懂,更多人是半懂不懂。
曾经,一个又一个民间里,最不能缺少的是庙宇。人们在一个约定的日子来到庙宇,经过几代人的坚持,把那个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像是四季轮回,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转动,凌晨的鸡鸣一般,必将会到来,除非是某个季节里某棵树上有那么一片叶子不坠落,要留住某个季节,或者是那只鸣叫的鸡,没有醒来。
看到过这样的观点:宽容宗教,宽容鬼神的存在,人们在宽容中,收获了心安。深以为然。人们同样在宽容那些巫师,那些巫师在给一些人讲述着,每到夜间,许多死去的人就会活过来,他们会在那些墓地里吵闹不休,为了那口直到死去还没有咽下的那口气。一些人是被一口既无法喷吐也无法下咽的气憋死的,直到死后很久,尸骨腐烂,那股气才融入腐烂之中。那口气是人们的生活或者是生存中累积下来的,更多时候是怨恨之气,有时候是一种欲望之气,还有一些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之气。村东的李来到村西的李家,那时候,村西的李正被肝癌晚期所折磨,他将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而村东的李不管那股刺鼻的恶臭把嘴巴伸向了他的耳朵,并轻轻地说了什么,村西的李便怒目圆睁手脚抽搐,口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就那样离开了人世。而村东的李,到底在村西的李耳边说了什么话?这是我们所最想知道的,而那个巫师,只是诡异地笑了一下,并不道明。在那些民间,人们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宗教的一部分。而有许多如我一般的人,只有在一年的那么几天里,宗教意识才会很强烈地出现在我们身上,在别的时间里,宗教意识会自然消失。在民间,宗教意识并不是以这样断断续续的状态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导引到宗教意识上。我
不知道有着强烈宗教意味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弊端,但我总觉得人有点宗教意识还是有意义的。庙宇的内涵是异常丰富的。就像是民间本身的内涵。在不断深入民间后,我才发现民间不是只有庙宇,还有别的许多东西,在民间的一些角落里,宗教意识已经变得很淡薄,人们开始变得不再宽容宗教,人们开始变得只宽容自己。庙宇消失,在民间,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真实的生活。庙宇的劫难,以及灵魂的劫难,也是某种民间艺术的劫难。
美,是一种习惯,而那些变形的面具和那些塑像,却很难让人习惯,但它依然很美,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说,某些时候的美,是变形的。
丢了魂魄,都要去庙宇里寻找,而找出的只是一只最微小的类似蜘蛛的东西,这便是自己的前世今生。在一座庙宇里,可以找到诸如此类的东西。
在那些民间,人的成长便是对一个地域与庙宇熟悉的结果。
一种在高处看万物,或者在高处反观自己。这是一种被过滤的温暖。庙宇还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抻拉关系,某个巫师如是说。
殉道者:民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殉道者。
生命。万物众生。在一片荒漠里,奄奄一息。一些蝴蝶在荒漠里,飞着,让人惊讶地飞着。飞过荒漠,像电影的镜头,转换到了某个民间。以大理的蝴蝶泉为背景,一些枝干虬曲的树木,一些水塘,在时间面前,并不静止,枝叶摇晃,水面涟漪轻泛,有许多的蝴蝶,那只荒漠中的蝴蝶赫然在里面,在那些枝叶间,在那些草木间,飞着,停着,这样的民间,不再荒漠。而当真正的蝴蝶消失,那某种程度的荒漠会不会又将诞生?过渡,地点在这里过渡着,时间在这里过渡着,那只蝴蝶通过这样过渡着。最终,蝴蝶必然要成为一个殉道者,或者是作为殉道者一般地
死去。毕竟,时间能带走一切,也在淘洗着一切。殉道的蝴蝶。殉道的植物,还有一些殉道的神灵。
莫非,在更多时间里,我笔下的民间,是我所熟悉的故土。那么那些鬼神故事是我从小就开始耳濡目染的吗?回答必然是被否定的。有许多鬼神故事,往大里说是一些民间的故事,我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听到的,甚至是看到的。鬼神故事里,有着许多殉道者。民间。消亡的民间。现存的民间。
消亡,民间的一种热闹,民间在现实面前的大溃退,以及民间殉道者的集体消亡。某个人如是说。
5
长剑:互相仇恨的民间。长剑,只是一个工具。而当长剑,有了灵魂,民间就有可能被长剑所控制。长剑的灵魂,有时是那些沾染的鲜红血液所赋予的,有时是一个隐秘的民间所赋予的。这样一把长剑的存在,让某个民间感到了隐隐的不安。一个民间必须面对那种不安,一个群体必须要面对那种不安。
他拿出了家中的长剑。经过了几代人的淬火打磨,经过了没日没夜的努力,一把长剑终于被铁匠世家打磨了出来,这于这一家人是绝无仅有的,毕竟他们在更多时候,要制造的就是独一无二。一把长剑,刀鞘上面雕刻着一条龙,有阴刻阳刻的混合。用途:在那个民间,说实话,不需要那样的长剑,如果作为艺术品,在那个民间,同样很少有人能够欣赏,或者说是更多时间里,那个民间总是在与饥饿温暖做抗争,而暂时还没有多少余暇来欣赏美。一把长剑,至少要有一个主人,而当一把没有主人的长剑出现了,它便会去寻找它的主人,以它的嗜血性。某一天,那个民间的王某,来试剑,王某拿起了那把长剑,他挥手朝铁匠铺门前的那棵松树砍去,砍中的是其中的一棵枝桠,枝桠瞬间掉落,声音清脆,松树枝桠间的油脂香,清香,扑鼻。王某,买下了那把长剑。铁匠,在王某背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王某,用那把长剑,在一些田地边挥舞着,披荆斩棘,许多的荆棘纷纷坠落,如果是慢镜头的话,荆棘的坠落过程,美得异常炫目。当王某把田埂上的杂草,纷纷劈落后,王某看到了刀尖上的血,鲜红的血滴,不是王某的,王某想用手把刀尖上的血擦掉,他很清晰地感受了血液的粘连,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血液瞬间变得湿滑,食指瞬间滑向了刀尖,食指瞬间被切掉了一截。血液,一滴一滴往下落,被尘埃淹没,王某的血液,最终比那些尘土还暗。王某,面颊上的冷汗一阵阵往下渗,眼泪沿着面颊往下流,与冷汗汇在一处。长剑早已被王某丢在地上,王某,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着那把长剑。那把长剑,没有在王某面前消失,也没有在王某面前突然从地上直立,没有任何成灵的征兆。王某从那些被刀子削落的杂草间,找到了艾蒿,是猛然间,王某发现了,在那个空间里,到处蔓延的是那种植物的气息,与鲜血的腥臭气味不一样。王某,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用那把长剑,几乎砍倒了一片广阔的植物地。王某,必须要砍掉田埂边上的那些杂草。如果在那个角落里,把所有的杂草留下,王某留下了一片广阔的植物地,却无法收获一片好的庄稼地。王某,不知所措。民间,需要一把精致的长剑吗?王某可能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讲述者如是说。
乌托邦: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形式的民间,将出现在我的笔下,这主要源于许多时候,乌托邦在我的思想里不断出现,交杂,并发酵,并让我异常难受。那我就制造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吧!
我的这种有意的歪曲,有一定目的,首先是要满足我内心深处的一点点私心,我不想被过多的苦痛所折磨,现在的民间,过多显性的苦痛折磨着民间。而乌托邦,似乎永远只存在于民间的念想里,或者最多只能落实到角落,或者是具体的某个人与物身上。我过多的是以悲情的眼光,看待着民间的一切,这样我便看到了过多悲情的民间。当我在泥泞不堪的公路边等车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裹着毛巾的老奶奶,她也在搭车,她旁边是她的儿子或者是孙子。随意与他们说了几句话后,知道眼前的这个老奶奶要去市上做化疗,这已经是她第五次去做化疗了。病痛是折磨人的。有些病痛必须要去化疗。这些常识,正侵蚀那个民间,而过去,更多时候,民间的观念便是患有绝症就没必要再去挣扎了,而是好好回家吃上几顿饭,好好用医疗费用打造一口好的棺材。而现在的民间,大部分人认为在一些时候,还是要适当挣扎一下,反抗一下,抗拒一下,而现实的残酷便是那样的行为往往是徒劳的。那个民间依然在苦苦挣扎着。
民间的童年,独属于童年的民间,一种乌托邦的民间,一些壁画,都有童真的特点,似乎那些是所有孩子的突发奇想与宏伟构思,把那个民间染成想象的蓝色,深邃而单纯的蓝色。以童话来填充那些墙壁的空白,这是不可思议的,似乎这个民间永远活在民间的童年,永远活在童话中,在这些童话中,民间远离了仇恨,远离了自戕,远离了饥饿,远离了疾病。有鱼,有虾,有蚌,这是一个沿海居住的渔村,但在一些深山峡谷中,我同样看到了这些鱼类的身影,一种暗示,也可能是对海或者是一个高原湖泊的渴念。
有时我会渴念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一种回归童年一般的乌托邦,我如是说。
7
释梦者:顾名思义,解释梦,曾经在一些民间里,成为一种职业。
许多的释梦者存在于民间,现在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有些在很长时间里不给人释梦后,便失去了给人释梦的能力,而一些人还有这样的能力,但这些很少的一部分人,需要用鸡血来唤醒,一只鲜红的公鸡,找准它的动脉血管,可以轻割,用锋利的刀子,轻轻一割,鲜红的鸡血,以及一种鲜红地死去,那个需要被唤醒的释梦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种鲜红的死亡,当那只公鸡死去,一个释梦者就会活过来。
我做了一个梦,又做了一个梦,都是噩梦,时间是连续的,情节也是连续的,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好是坏?这是我自己无法把握的。反正梦的内容不是很好,里面充满暴力,充满血腥。白日里的我,似乎因为梦境已经把我掏空,这样,白日里的我,时而会觉得四肢无力,幸好没有幻想迭出。到后面,才知道那是脑神经衰弱了。我便去医院里,开了一些药,每天按时服用。后来,我见到第一个释梦者时,他却并不这么认为,他拍了拍我的脑袋,这是好的征象,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样的我并不好。那个释梦者,偷偷地跟我说,那个民间里的所有人都做了那个梦,那个民间被噩梦折磨了一个月。当我问了那个民间的其中一个,然后几乎都是一路狂奔地寻访了那个民间,原来确实是一个民间都在做梦。那个月,那个民间在白日与黑夜里来回穿梭,更多时间里,是他们在更多的夜间模糊了黑夜,有那么一会,那些被噩梦折磨的人,对梦没有任何怀疑,是突然间惊悸了一下,才猛然惊醒,浑身汗涔涔的,庆幸那只是梦。一些释梦者,接连出现在那个民间,吉兆还是凶兆,那些驻扎在那个民间的释梦者,争论不休。民间,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些释梦者。也许,只有不用去理那些释梦者。但在关于那个民间的很长一段历史里,释梦者是重要的,那些释梦者往往还是巫师,或者是在那些民间里唱戏的人。在那个民间的文明史的构建中,庙宇与戏台是最重要的,也即巫师和唱戏的是很重要的。庙宇和戏台,起到了娱人和娱神的作用。一个民间的文明,一个民间里的那些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便是在庙宇和戏台的双重濡染下,在那个民间慢慢形成,并一直延续,成为一条河。但河流,会出现断流,这是一个民间不曾想到过的。释梦者,对于梦的解读,不再准确,民间也是不曾想到过的。我在一些老人的
天青色等烟雨(线描) 桑子
讲述中,见到了一些奇异的释梦者,他们能根据梦来断定许多东西,他们同样在面对一些人的时候,能轻易说出这几日那人曾经做过的梦,甚至一些释梦者,会诡异地一笑,我曾进入你的梦中,你的梦便是我制造的,我便是推动你梦境不断发展的主要因子。那个折磨了民间很长时间的噩梦,在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那些怪异的释梦者,在某一天,也突然从那个民间消失,就像是不曾存在过一样。在某一天,那个民间突然就忘记了曾经做过那么一个梦。
在某个老人的讲述中,有这样的说法:释梦者,衣袖里还藏着一把锋利的剑,他们用那把长剑的寒光一照,什么样的梦有什么样的征兆可以解释。但我还不曾见到一把锋利的长剑。莫非来到那个民间的那些释梦者,都是假的?一个真实的民间,在真假不明的释梦者面前,变得已经不再真实。
我曾经很信任释梦者,那个老人如是说。
民间:过去与现在交杂。
在那个民间,没有河流的存在,似乎也就不会有文明史的存在。毕竟河流与文明,联系紧密。一些研究村庄史的专家学者,接连出现在那个民间,对流落于荒野的墓碑、故事传说、巫术史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多种研究方式,对那个民间的前世今生进行了剖析。那些专家学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可以用词典 (让外来者异常陌生的词典 )归纳的民间。但那些词典往往只存在于口头,几乎不能用汉语来记录它们。
当我出现在那个民间,到处充斥着陌生的土语。在我成长的那个民间,同样有只能用我们的土语才能定义的物。于坚很推崇海德格尔对于土语的定义,“土语是任何一种语言生成的秘密泉。任何蕴含在自身中的语言精神都从此一秘密源泉流向我们。……恰恰是瑞士山区与河谷地带完好无损地保留住了土语这种高贵的财富:在他
们的土语中,他们不只能言说,而且还能思想和作为。”在那个民间,那些物的存在以及那些生活方式,便是以土语的方式、作为和思想存在着。那是在别的语境下,所不曾有过的形式,也就不可能有着围绕那个形式而作为而思想的人群。
直到现在,我还依然找不到表达那些特定土语的办法。我无法直接切中它的内核,也就无法真正抵达它的真实。我只能在这里隔靴搔痒,只能在这里泛泛而谈,或者直接是简化。被我简化的民间,还有被我简化的土语,以及被我简化的语境。也许,某一天,将会有那么一部关于土语的词典,那时民间的视角借助土语,而语言又依赖民间的视角。最终的结果,那些专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那个民间,从出现人类的那天开始,或者时间再往前推一些时间,就没有河流的存在。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做出了如此推论:或者河流曾出现在某些土语存在的时间里。
河流能孕育属于农耕文化的文明与富庶。那个民间没有河流的存在,竟能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段文明史。这样的结果让我多少感到惊讶,毕竟我的思想一直僵化在河流与文明的纠葛中。
是在某一天,在我那间狭窄的卧室里,我听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话,顿时让我僵化的思想空间不断扩张,并最终冲破牢笼。我的思绪,真正破窗而出,在那个民间的一个又一个山间驻足,攀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我发现了一个深藏在那个民间的秘密,有一些井水的存在(这就够了,够那个民间饮用),有一些盐井的存在(这满足了那个民间对盐的需求,但最主要还是满足了另外一些世界对于盐的需求),盐同样也能制造一段文明。其实,这些秘密,是那些专家学者所发现的,也是那个民间的口传史一直流传着。废弃的盐井,废弃的井,以及依然是被运用的井,佐证着人们的观点。
那个民间的文明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现在看似贫瘠的土地上,曾经繁华异常。如果不是还有一个掌握着那个民间口传历史的老人生活着的话,一段文明史,一个村庄史可能会随着口传的中断而中断,甚至会消失。口传的历史里有着活的物与人,诸如在那个寨子里,曾经有一些奇人,用奇异的办法给一些人治病,还有一些人说着奇异的话,唱着一些奇异的音乐。在那些依然能唱出村庄史的老人口中,我听出了那是创世的神话传说,往往开头是用土语唱出的“创世之初,天地混沌”之类。
那些歌者的存在,让民间充满了混沌的意味。走入那样的民间,会在一段时间里,分辨不出时间的具体间隔。在那个民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口传史的继承人往往需要一些机缘,一些人会因为自己成为继承者而觉得那是一份荣耀,毕竟自己成为传人便意味着自己对那个民间有了担当。而现在,那个民间的很多人,已经不相信机缘,在很多年以前,那个民间的口传史遭到了粗暴的冲击?
那个民间,在一个高山峡谷之中,那样的生存环境,无疑是艰辛的,也无疑是落后的。那样的艰辛与落后,在我一直以来的想象中,是无法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文明史的。在这里,我再次把自己的疑问抛了出来。在很多时间里,我在那个民间里到处行走,以童年的眼光,以成年的眼光,在更多时间里,我看到更多的是民间的荒漠,如果是深入民间的话,应该是精神的荒漠。
是在那天的那次对话后,我才真正开始对那个民间的一切物事进行了梳理,在梳理中,我发现了以前的认知是属于自己的荒漠化。那个民间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有着高度文明史的渗入。
一个现在看似穷乡僻野的民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贫穷,相反还相当富庶。这样的富庶,要借助于一些民间野史的补充,同样还要借助一些学者的研究。我的面前,摆着一本关于盐井方面研究的书,另外在我脑海里还摆放着从许多老人那里搜集来的野史。那个民间,在它最繁华的年代里,主要是借助盐井的支撑,不仅那里有盐井的存在,它恰好处在一个背盐必经之地(经过那个民间,又可抵达一些有盐井的民间)。没有一条真正的河流,只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土路,还有到处密布的森林(这又是一个疑问,往往是一个密林必然能涵养一条河)。
那个民间开始出现了一群背盐人,他们嗅着盐的味道而来。他们通过那些密集在空气里的盐味跨越了很长的路,这段路必须要披荆斩棘,这些地方原先并没有原始居民,他们甚至看到了一个全部由竹子组成的角落,远远望去,那片竹林编织出一个院子的形式。院子的形式,对于那群人而言,并不陌生。人们抽出了手中的长剑,把那片竹林砍掉,并用土木替换,一个简陋的居住地就这样形成了。这是雏形期,这造就了一条通向盐味的道路。那个简陋的民间,有一段时间是孤独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去寻找盐的味道后,那个民间便开始变得喧闹,但更多时间里,依然还是一个浮肿的喧闹,只有人声的鼎沸,只有骡子的叫嚣,只有鸟类与人之间的交谈,还缺少了些什么东西?
当一个民间发现了自己的浮肿,源自于只是过客的身份定位。只有抛掉过客的漂泊感,那些浮肿的东西才会被真正充实起来,进而变得丰腴肥美。这样出现了第一个戏台。来了第一个唱戏的人。出现了第一套戏服,华丽的戏服,与那些密林里的一些动物身上的毛皮,有着同样的质地与形式,像虎豹的纹理,像那些鸟的羽翼,像地上爬动的虫类。那个民间看到那套戏服时,脑海里的第一反应便是这样。然后是第一句唱词,以及第一个身段,这些给那个民间同样也带来了猛烈冲击。那些唱词,以及那些身段,是那个民间所陌生的。那些赶着马帮的人,熟悉的只是苍凉的赶马调的唱词,而戏台上出现的调子,有时像极了动物的长啸悲吟。当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唱戏的人之后,人们在那些唱词里找到了一种依托。一个民间的向善品质,在那些唱词里随处可见。那些唱词制造了那个民间一部信仰史。唱戏,那是对下里巴人最好的塑造方式。因为那些戏的存在,那种言说方式里几乎就很少有说教的意味。然后是纸张出现在了那个民间,然后是一个教师出现在了那个民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塑像(孔子的塑像)出现在了那个民间。这样一个尊师重道的民间,不再是雏形。
现在,在那个民间里,有着许多建筑物的遗留,可以在那些斑驳与细微的细节中,找到关于儒家文化的痕迹,也在一些庙宇里,可以发现有着道家文化的濡染,同时还有着别的多种宗教的杂糅。这个民间,信仰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宗教。
这便是一个民间基本的文明史的出现与正式确立的过程。这一定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诸如第一句唱词能被多少人接受,从接受到依赖,同样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从现在许多人对于戏曲的认知上,就能感觉到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些戏曲。但在那个年代里,戏曲是受到那个民间欢迎的,毕竟它带来的是一种过往民间所不曾有过的喧闹。那个民间可以在茶余饭后田间野地,谈论着那些戏曲。一个民间需要这些东西的介入,也只有这样介入后,一个民间才从最丑陋的建筑开始,慢慢被建成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民间没有把一些东西道明,一直以来民间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它只是用物的方式在暗示。暗示,即不明说,即需要参透。参透人生,参透人性的世界。当那些盐井先后废弃,一些人先后离开,但由那些物事人所构建起来的民间,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它并没有在众多的贫瘠面前垮塌,而是相反,在那个民间,现在依然在坚持对一个文明史的坚守以及延续,那个民间依然坚持唱戏便是明证。
文明史是一条河流,需要许多的支流。那个民间的文明史的支流,茂密且繁密。我开始出现在那个民间,就为了看一场戏,戏词转变为当地民族语言(一种土语)。这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转变,那个民间里的一些人没有接触过文字,却能通过口头语言知道一场戏的内容,以及一场戏的内涵。
在那个民间,看戏的人群与去庙宇里的人群一样多。而庙宇,同样是一种言说方式,或者直接就是一种说教方式。在庙宇面前,说教的人是一个又一个巫师,而在戏台上就是一个又一个唱戏的人。一个民间便是以这样的方式,有了自己的文明史。庙宇和戏台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庙宇就必须要有戏台,有了戏台就必须要有庙宇,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载体,戏台除了说教意味而外,还有娱人娱神的作用。在那些观看戏剧的人群里面,还有一些已经逝去的人,他们重新回到民间,并感受着一个戏台所带给一个民间的韵味。戏台上的身份是可以替换的,那些演戏的人就在不停地更换着自己的身份,那时他们已经不是自己,而是那个民间的一个部分。在戏台上,似乎不需要寻找自己的身份,只需要把民间的身份定义好就行了。
那个民间的那些老艺人,许多已经相继离世。如果后继乏人的话,那个民间的文明史,就会出现断层的危险。在一些民间,我看到了一些闲置着的戏台,没有人来修缮,破败就由它破败,空着就由它空着。而恰好戏台旁边还有一些古木,枝杈庞杂,人们可以在下面乘凉闲谈,那些乘凉的人群,都是一些老人,他们是那些戏台的见证者,也曾是那些民间戏曲的狂热者。而一曲早已终了后,只剩下面对面的尴尬。幸好在那个民间,在平日里还有一些老人,在练习着身段以及唱腔唱词,他们知道那个民间依然需要一个戏台,如果没有戏台,一个民间的思想教育该如何进行,只借助于学校是不行的,而演绎一段人生,这才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思想的冲击。
我想成为一个会唱戏的人,有着自己的戏台,有着自己的观众,而真实的自己似乎永远也成为不了一个会唱戏的人。那个民间,在唱戏中不断修复自己,而作为一个唱戏的人,同样也在不断修复着自己。那些庙宇里供奉的是民间的神。一个成神的人,一个成神的物。那个神化的过程,是整个民间靠神话传说以及现实糅合的过程。那个民间的那个戏台,所正正对着的是一个石崖,石崖中间有着一个半月形的图案,有一些人还崇拜那个半月形图案。而那个半月形图案是如何出现在那个石崖上的?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民间有许多这样的传说。传说是动人的。一个民间的繁华,被不断推进的时间所遮蔽,当一个又一个老人离开那个民间,当一段又一段口传的历史与故事没有被传承下来,一个民间的繁华几乎
很难展现在又一个民间面前。多少繁华的民间,被遮蔽?
后来一些专家继续深入那个民间走访调查。那个民间有河流,只是早在多年以前就干涸了,其中某个人如是说。
一个传说:在另外一个民间,有那么一条河流。这条河流里,有着神话史的存在。神话史在河流的两岸生长着,以生命的方式生长着。在一个壁立千仞的石壁上,有着一个天然的塑像,被人们供奉为本主,本主即神。这是对一个自然物的崇拜,这同样是对一个自然物的神话。在多年以来的神话之后,那个民间的精神史,与那个神物脱不开干系。祭祀天地的场景,便是在那个神物之下的场地里。场地里,砾石遍地,艾蒿遍地,这些都是祭祀天地时必不可少的东西。人们是在那个自然物里找到了神灵的影子,神便是一个自然物,一个让人惊讶的自然物。那个民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见着一些自然物,就会心生崇拜之情。那个民间流传着关于那个自然物的故事。可以算是一个传说,但故事里面的一些人还健在,这样便增添了故事的真实。真实与不真实,在那个民间,已经不是很重要,也有可能那个民间也害怕有人会推翻真实。那些健在的老人,更多时间里沉默不语,在一些时间里,却又绘声绘色地跟人们讲起那个故事。
这可以算是一个关于打猎的故事,它的主题在一开始,我以为是关于打猎的,而在听完后,才发现并非是关于打猎的,打猎只是引子,这是关于神的故事,神灵才是主题。打猎的人有三个,而猎狗有六条甚至更多。他们带着猎狗,经常出现在那个石壁旁,一些野生动物生存在那些岩壁间。而岩壁上的神物,似乎会忍受不住在那个石壁上的枯坐修行,而诙谐地和他们开一些玩笑。那个神物,最爱做的一件事情,便是用神力把那些猎人的头狗藏起来。神,制造了一座又一
我新近的日子沐浴着阳光(线描) 桑子
座交叠的山,也制造了一片又一片缠绕的密林,那条头狗就再也走不出来。有时,在那个民间,同样会有一些人遇到类似情形而走失,有些人会在好多年后再次出现在那个民间。神为何会把他们的头狗藏起来?他们只是在谴责神灵的顽皮,而忽略了神灵的另外一层用意。神灵的用意,最终被一个巫师说出,只是被那个巫师说出来的时候,那个神像已经被那些人从石壁上凿掉,已经被人丢入那个民间的那条大河里。
神像被丢入河的那晚,天大雨,发洪水,塑像被水冲走。这里把那个巫师道出的原因补充一下,再接着复述故事。巫师告诉那个民间,神灵把猎狗藏起,只是为了告诉那些猎人,不能过度捕猎,不能捕杀怀孕的动物,要在一些季节才能捕猎。人与自然,最素朴的道理,通过巫师的口传出来,便有了神祗的意味。那个民间,在一个又一个巫师用神祗一般的语言说教面前,似乎在正确地处理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直到巫师消失,直到神灵消失。
塑像丢失,报应开始,洪涝灾害接连不断,曾经的富裕,已无处寻找。那个民间似乎明白了为何会出现那样的情形:是神灵的丢失。一个又一个的巫师,开始审判那三个人,那三个人承认是他们在一个暗夜,把雕像丢掉了。而在另外一个民间里的赵某,同样在那个暗夜里,出现在了那条河的下游。暗夜,洪水,只有喧腾的声音,赵某感到了内心里泛起的阵阵凉意,但赵某从那个几条河汇聚的岔口回家,还需要爬过一座山。赵某,在暗夜里,停在了那个三岔口,他掏出了怀中的旱烟,吸了三口时,他突然看到了河中泛起的金光。赵某,感到惊诧的同时,也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奇异的天象。一条金黄的大道,分明就在那个三岔口展开,洪水被金光分开,那时河道变得空阔无比,赵某战战兢兢地走上了那条大道,如果金光突然消失,洪水又将泛滥,那赵某可能就要魂丢三岔口了。而最终,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赵某在河水交汇处见到了那个塑像。赵某当即下跪磕了三个头,然后小心地把塑像放入背篓里,背回了另外一个民间。神很轻,赵某走得轻盈。
这是上天对于另外一个民间的眷顾。从此,这个民间多了一个神灵。赵某把那个塑像带回那个民间后,村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迎接礼,那天全村男女老少虔诚地跪在庙宇前面,看着一个巫师给那个神净身,并在塑像外面镀上一层金光,然后放在庙宇中间。从此,那个民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这与神像原来存在的那个民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过去,这样的好情形应该发生在那个民间。一个民间的富裕,开始出现流言蜚语。
那三个人,再次出现,出现在了这个民间。是在一个夜间,他们出现在了那个庙宇前,庙宇被上了锁,他们从门缝间往里探,那个塑像在夜间爱闪闪发光,夜的黑暗无法遮蔽它的闪光。他们三个人,竟大言不惭地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你真是我们的神的话,你就把这扇门打开,我们接你回家。那三个在说着这话的同时,也跪倒在了夜色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开始发生,那个门自动开了。他们抱着那个塑像,消失在夜色里。第二天,发现塑像已经丢失的那个民间,许多的老人痛哭流涕。人们只好用木的塑像代替。从此,那两个民间,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当我在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我把内心的不理解表达了出来,这个故事,经过了多少人的加工制造?许多民间的故事,就是许多人进行加工的产品。而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那两个民间,几乎所有人都坚信,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故事的。当我在某个民间,见到了那三人中还活在人世的那人,他把这个故事详实地再次说给我。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在许多个民间,就是这样,神话与现实杂糅,现实在不断制造着故事,故事也在不停地反证着现实。特别是在一个人神共居的世界里。而无疑,在许多民间里,一直有着人神共居的传统。如果梳理那个民间的神史,就可以看到许多光怪陆离的人,人性的善与恶,在神史里一目了然。民间的丰富,源于民间的现实与故事,也源于民间的成长与创造能力,一些民族文化
研究者如是说。
诅咒:在一些民间,存在着形式各样的诅咒。
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走路,终身吃土。”(引自《圣经·创世纪》)神说的可能是土语,如果神不会土语,神将无法深入民间,神只能孤独地高高在上。而这里,神用蛇的语言与蛇交谈着。在那个民间,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现在,神必须用那个民间的土语,那个民间才知道神的意图,那个民间也才会去崇拜自我认定的神。
那个民间,所有人与物,都被神审判。神对那个民间说:“你们这个民间太过荒漠,就必须受诅咒,必须深入密林,终身与鸟兽为邻。”似乎神说话的方式都是这样的。区别只是用什么样的土语在表达它而已。
那个民间,接受了审判。那个民间,深入深山,与草木鸟兽为邻。那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密林。密林里有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它们不分白天黑夜出来叫嚣,有时是在嬉戏游玩,有时甚至是不同种类的动物在一起嬉戏。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仇恨与惧怕,在那片密林里不再存在,那片密林里的所有动物,都是食草动物。而在那片密林里,长着繁茂的草,各种各样的草,繁殖速度异常迅猛的草。审判的过程,只是神出来说了一句话,神便不再出现。但那个民间突然意识到,神存在于任何角落,也能幻变为各种动植物。当那个民间,从那片密林出来,他们的神便不再是单一,有时可以是神,有时也可以是物。再后来,我便是出生在那个民间,那个民间的神便是我的神,我便有了各种各样的神。我想在那些墓地里找到一点点信息的,最终我只收获了那个民间大致出现的时间(更准确的说法,是第一座坟墓出现的时间,而关于那个民间出现的时间,根本就无法推测)。
那个民间,要在密林里反思。原来,神审判了其中一个巫师。那个巫师,一个人来到了密林中,抄录经史,在抄录的过程中,那个巫师感受到万籁俱寂,身体通透。那个巫师,用一种土语,记录着那个民间的诞生以及生长。据说,他同样在神的启示下,写下了那个民间的结局。只是那个巫师所抄录的经书,并没能留下来,当那个巫师死在那片密林时,那个民间没有一个人来把他接回家,而是任由他的尸体腐化在那片密林里,随之腐化的还有那些经书。巫师的尸体,在腐烂的过程中,并没有散发出恶臭,那些经文的腐化,同样没有任何的恶臭,散发出植物叶植物根腐烂的气味,似乎经文便是植物叶,尸体便是植物根。据说,那个巫师在离开人世之前,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何要被神审判,他在那么一些时间里并没有真正履行一个巫师的责任。作为一个真正的巫师,他没能把那个民间的文化熟稔于心,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某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了那个民间里庸碌的一员。他同样已经预料到神会像审判他一样审判那个民间,只是方式上不一样而已。当神要结束对他的审判时,巫师染上某种当时无法医治的病疾,他没能对那个民间进行再次言说,也没能在那个民间建立起庙宇以及戏台。是神在启示他,庙宇与戏台必不可少,两者所对民间起到的言传暗示作用,在民间是不可估量的。在那个民间,很长时间里,只是把那个巫师无缘无故进入密林,当成是一个笑话。神灵竟然无法医治那个巫师的病疾?这似乎无法解释,那个民间,最终明白了那时神的无奈。
民间开始走在重生之路上。更多时间里,那个民间与那个密林之间总是有着冲突的发生,但神下旨不能砍掉密林里的任何一棵草木,那个民间只能寄居于密林之中。那个民间,在各个季节里,感受着来自自然界的冲击,那个民间同样感受到了来自一片密林的侵吞。密林,不断繁殖,繁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那个民间的想象力。在那个民间的思维里,绿意缭绕的世界,总是不好的。现在,那片密林,正用冲击力很强的绿意冲击着那个民间,那个民间从视觉开始从触觉开始感受着密林。那片密林,已经不允许那个民间有着任何喘息的机会。那个民间,在绿意中生存着。荒漠,必须被填充。生存环境的荒漠,更多时候,也会滋生灵魂方面的荒漠,这是神灵在审判那个民间时,说得铮铮有声。那个民间,被神审判终生。在那个密林里,那个民间重新找到了原始的庙宇以及原始的戏台,自然便是庙宇,自然便是戏台,自然界里的那些动物植物便是巫师,便是戏台上的主角。那个民间里的人们,甚至变成了鸟,变成了植物,变成了动物,他们同样也习惯了夜的黑,他们同样赶跑了夜带来的恐惧。当某一天,神决定赦免那个民间时,神发现了那个民间中出现了一些异类,他们又开始砍伐着那片密林,他们又开始捕杀着那些鸟类动物。在那个民间,这样的人,迅速增加,民间里原来通灵的人,已经完全消失了。神的审判,最终竟然是失败的。神异常恼怒。
现在,神又再次出现在那个民间。神对那个民间说:“你们这个民间太过荒漠,就必须受诅咒,泥石流将会泛滥,山体将会坍塌,人心的欲望将会膨胀到极点,最终你们将被自己埋葬。”但那个民间,听不到神的话语,那个民间,已经没有任何戏台以及庙宇。那个民间,已经没有自己的神灵。在那个民间,现实正日渐明晰。几乎很少有人能说得出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民间的一些人事。为何会没有释梦者的出现?释梦者能通过一些梦,来给那个民间一些启示。其实,是有那么一些释梦者来到那个民间,只是那个民间没有人做梦。这是一个梦缺失的世界,诅咒者如是说。
长河:记录某次对话。对话不是长河式的对话,而是此次对话谈到了长河式的东西。民族文化是一条长河,里面有很多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对话者之一是我老师赵敏。我是旁听者。他们谈论的不是文学,而是民族文化。我老师现在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以前曾经写过一段时间的文学作品,文字独树一帜,但接触民族文化后,他便暂时把文学放下了。赵敏老师和我从不谈文学,只谈宗教(儒释道等等),谈宗教所要探讨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谈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以及如何相生,我们还谈民族文化(宗教其实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罗兰·巴特《文之悦》里曾如此谈论文化:古典作品,文化,愈是文化的,悦便会愈强烈,愈多彩。民族文化都是一些古老的作品,在真正涉入民族文化这条河,那种属于罗兰·巴特的悦,或者是属于我的悦就真正变得很强烈),他总觉得我应该找到文学与民族文化之间最好的契合点,也即应该寻找那种最古老又最强烈的悦。他们谈论的内容简要摘录如下:
人更多时间是通过求之于内的方式来完成作为人之成为人(即修身),而求之于内遇到困境之后,人必然要求之于外,找一些寄托物(象征意义)来解决思想世界的恐慌与荒漠化。庙宇与戏台以及神树,都是象征物,象征着某些根性的东西,当把这些熟悉的物消除,民间就会变异。那些象征物的消失必然会给人带来苦痛,毕竟那些象征物是那些人精神世界的依托。这样的依托经过时间的过滤之后,便成为一种平衡的方式。宗教世界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平衡,应该是最重要的,有些失衡会带来让人意想不到的毁灭。
此次对话还谈到诗歌的起源是宗教,赵敏老师多次听到过那些祭祀时的祭词,甚至比好些诗歌都精彩。诗是宗教,宗教仪式中的某些祭文中,有着强烈的诗歌的韵味和节奏。我想真正聆听一些祭文。我想真正听某个毕摩念一段指路经,那些逝去的灵魂,要回归,要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据说要涉过高山和峡谷,要对抗瘴气与荒芜,还有那么几条路……但从一个毕摩口中念出来,就不会是这样的意味了,还有神性的意味,还有诗性的意味……他们如是说。
责任编辑 段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