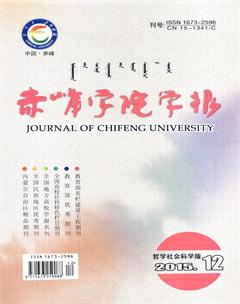自我的觉醒与人文理想的失落
李再红
摘 要:《儒林外史》塑造了一批市井奇人形象,孤高狷介构成了这一群像的基本特点。这些形象虽然着墨不多,艺术上也存在主体观念表达过于直露的弱点,但这些形象却是作者人文理想的体现,且作为小说对社会认识与探索的一个重要环节,体现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解码,表现出作者对社会出路的探索与指向,因而有着特殊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品味与探究。
关键词:《儒林外史》;市井奇人;自我觉醒;人文理想;失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53-02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是一部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王冕的故事开宗明义,隐括全文,用市井奇人压轴,以述往思来,中间描述以名利为中心的科场、官场、市井等生活场景,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在名利场中的不同观念、态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封建末世儒林的生活精神状貌,其针砭时弊、寻求社会出路的布局意图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尽管奇人们的思想言行体现出社会良心的苏醒,凝结着作者的人文理想,但他们能否成为社会的未来希望,却很值得思考。
要弄清这样的问题,关键要搞清市井奇人究竟代表了一种怎样的社会力量,这样一种力量是否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导,能否得到时代的“认同”进而引领潮流。为此,我们不妨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试图在作者对社会总体的观察认识和理想追求的表达与诉求中,去考量市井奇人的主观价值和客观意义。
奇人出场之前,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科举制度影响下的社会风尚与儒林的生存状态。被儒家所标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在“官本位”思想的冲击下,在“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的现实熏染下,已经失去意义而只存用法,追名逐利成为时尚潮流。于是,尚存一丝古朴的周进、范进等则偃仰反侧,饱尝辛酸。他们失意时尊严扫地,得意时备受趋奉,成为世俗警顽发聩的一面镜子;而王惠、严贡生之流,则道德尽丧,贪鄙无耻,显示了功名官场怎样膨胀野心,伞护不法。由于仕进之路的狭窄,谋生手段的缺乏,大批的士子沦落,他们已经顾不上“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古训,使尽浑身解数谋利,于是招摇撞骗,诈世欺人与自欺自慰的表演花样迭现。莺脰湖畔的高士,西湖沙龙名士,莫愁湖畔的无聊群体,就典型地体现了大多数士子的生存现状以及精神日益走向衰落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急需一种道德支撑力量,因而真儒贤人们就在千呼万唤中出场。但是,“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虞育德为代表的贤人们恪守圣人训教,讲究“文行出处”,明察政治黑暗,感叹“我道不行”而拒绝走入官场,纵有济世之才,“国情”也不允许他们去实践挽狂澜、扶大厦的使命。但贤人们血管里毕竟流淌着传统主流文化的血液,匡社稷、救民生的使命感,还是让他们修泰伯祠,搞祭祀大典,企图以远去的亡魂唤回社会良知。然而,封建文化早已僵死,礼乐盛典这剂复古药方,岂能救治社会腐烂的肌体,助政教一臂之力的盛典,连同贤人们的美好愿望一起,很快冰消瓦解,影响难追。而像虞博士那辈人,也老的老,死的死,散的散,留下来的也许只有空谷流音了。而后整个社会更加利欲熏心,“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季遐年等市井奇人们次第登场了。称他们为奇人,倒不如称其为狂狷之人更为准确。季遐年本为一介寒儒,但并没有读书人的“体面”,他不修边幅,服饰寒酸,竟混迹于僧舍“随堂吃饭”。他以写字谋生,字如其人,弃古人法帖,任性而为,格调孤傲无群,连书写工具亦俱为秃笔废翰,可谓古怪。人请他写字,他也完全依情绪而定,如不情愿,任你王侯将相、乡绅大佬,一概不给面子;对上孔方先生、润笔银子,正眼不瞧。施乡绅请他写字以堂皇门面,反招其上门骂了个痛快淋漓,表现出一种恣情任性的狂狷。王太是个围棋高手,但并不以此沽名而博取丰衣足食,而是安于卖火纸筒的生意。他去看大老官下棋,受到轻视,他绝不忍辱逢迎,而是凌厉出击,杀得不可一世的大国手落花流水,出了一口恶气,足见其任侠使气的个性。盖宽能诗善画,但不以此招摇过市,争名逐利。他原为富有,为诗画朋友散尽浮财救困解难,又为小人谋算丧尽家产。但他有贫富无改的淡定,操持茶馆“贱业”,自力更生,且始终困穷而未攀结当年的“同贵”,有一种维护个体尊严的孤傲。以裁缝技艺养身,又以诗书琴趣怡情养性的荆元,从来没有感到业贱人低,而是人也悠然,情也淡然,其言其行、其情其性,虽不惊世骇俗,但也见出独立的自尊……总之,市井奇人们的个体生命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贱业自守,情趣自乐,自我与自尊。和贤人们相比,他们更清醒一些,且少了一些迂执与颓废。
奇人出世,面对着文明的僵死,庸俗的横生。以科场、官场为代表的社会名利场,充斥着腐败、罪恶。贤能与英名无缘,伟业与利益错位,钻营被时尚推崇,逢迎为社会青睐。弃珍珠而宝鱼目的时代,卑鄙必然成为名利场上的“绿卡”。奇人们良知未泯,粪土名利,因而决不巴结逢迎,沽取名利;他们看破世情,精神出尘,因而决不虚妄骛远,蝇营苟且;他们看守心灵的自我,孤芳自赏,因而决不灵魂待沽,良心待染。他们以孤傲之性,对抗世俗冷遇;以狷介之行,釋放不平之鸣。宁静,化解了物欲躁动;淡泊,驱散了财迷心性。他们并非圣人,没有时世之忧,也没有救世之责,他们只是以率性自为,保持了自我人格的尊严和独立。这种品格无需去拔高评价,更不值得去树碑立传,但它体现出一种人本的复苏、个性的觉醒,有这样的意义就足够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奇人身上,体现出作者对当时背景下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我们不妨代作者进行一下推想:社会官场腐烂,世俗利欲熏天,士子沦落且堕落,贤人迂阔,礼乐无补,兵农救世更是徒劳……面对行将就木的社会,作者彷徨苦闷,无方施救,也只能寄希望于士子的道德自救,以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无羁、完满自足的人格作为士林解放的出路,这虽然很有点迂,但也是出于无奈。
独立无羁,首先是无欲。无欲无求,方能至大至刚。像季遐年不贪财,不慕势,不沾光,方能傲气十足;像荆元不图人富贵,不伺候人颜色,才能淡泊宁静。这当然需要自我意识作支撑。人性的觉醒让奇人们不再为功名而活,而是为自己、为真实而活,由此他们摆脱了封建统治的名利诱惑,所以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但这种观念的稳固,同样需要物质的保障。此前士子的蜕变除了进身通道狭窄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谋生能力的低下,谋生手段的缺乏。缺乏物质保障的心灵,是很容易扭曲的,希求按个人愿望选择生存形式就更加艰难,这是依附性、寄生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士这个阶层的分化瓦解、屈节从俗就是最好的证明。因而,要导引社会走出迷局,首先要复活士这个阶层的本性,而本性复活则靠道德自救,但前提是让士人能够独立谋生,能自食其力。作为手段,做生意也好,卖文也罢,总须有操持的“贱业”和技艺。只有这样,才可以安身立命,否则,奇人是很难“奇”起来的。有了这样的基础,奇人们的风雅与假名士的附庸风雅才有了本质的区别,骨子里没有了贪欲,人格才会坚挺,琴棋书画才真正与“性相近”。
刘咸炘在《小说载论》中说:“四客各明一义:季忘势,王率性,盖齐得丧,荆蹈平常。四者合则大贤矣。”评论颇有见地,但“大贤”之说不为得体。因为奇人们既无济世之志,也无经邦之术,更没有扶倾挽颓的责任心与紧迫感。只是他们心态比“贤人”“名士”们都悠然坦然,因为他们没有生计艰难的忧戚,也没有名利不全的焦虑,这也许正是作者心中理想的人生。由于坦然,奇人们能随遇而安;由于自觉,他们没有地位卑下的不平和操持“贱业”的羞愧;由于独立,他们蹈雅践俗,一任性情,从容自如。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封建正统文化对人的异化,避免了仰人鼻息的耻辱,告别了奴性人格,维护了人性的完整。
奇人们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支点,应该可以安之若素了。然而,现实和理想本来就有距离,叛逆性的人文理想,只能被专制社会视为异类,也为世俗所不容,奇人们的“空中楼阁”注定难以长期存在。因为,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实现,有赖于社会革命性的进步,而非靠奇人的狷狂就能实现,正如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指出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奇人们绝不是能够担当和实现“历史的必然要求”的阶层,他们不满现实,但不去也无力改变现实;他们不欣赏贤人的迂阔,厌恶假名士的虚荣钻营,痛恨社会的不公,但只能遗世高蹈,根本找不到士林解放的通途。奇人的悲剧正在这里。因而,奇人们不過是啸傲市井的隐士,带着魏晋名士任诞的因子。他们狷介狂放的行为虽有自醒成分,但和古代隐士的放浪形骸无本质的区别。他们可以狂傲地回击世俗的冷遇,像天马行空般将丑恶庸俗置于马蹄下无情践踏;他们还可以“齐得丧”,傲视富贵,以卑贱者的不平向传统世俗挑战。然而这一切,都因缺乏目标指向性而与现实脱节,甚至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古君子风度都相去甚远。像荆元那样,让朋友都“不和他亲热了”,就成为必然结果。这足见独立就是孤立,何况他们的言行虽不迂阔,但也不厚道!奇人们像魏晋名士一样逍遥放诞,在令人窒息的黑夜中挣扎,却很难见到曙光,这是奇人的悲哀,也是作者人文理想的失落。作者以愤激的笔调写奇人的傲岸狂放,以欣赏的笔调写他们的风度,更以悲凉的笔调写其梦醒之后的无路可走。特别是全书在荆元凄清的变徵之音中收束,更传达出作者无尽的怅惘和忧伤!
——————————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华夏出版社,1994.
〔2〕李汉秋,胡文彬.儒林外史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