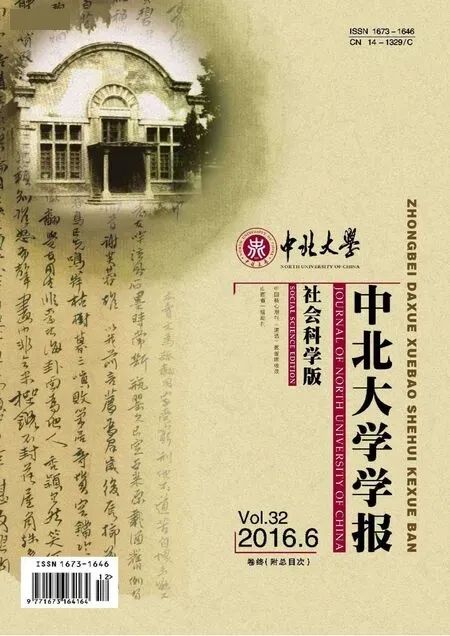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莫言文学作品中的“色彩变异”研究
纪 燕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莫言文学作品中的“色彩变异”研究
纪 燕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色彩的隐喻意义是人们基于生活体验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 基于人类共享的文化、 知识和经验, 人们对颜色的认知存在共性。 然而, 莫言对颜色有浓厚的意识倾向, 其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色彩感知存在着明显有别于传统意义的 “色彩变异”: 红色被赋予残暴、 恐怖、 性等隐喻意义; 绿色充满邪恶、 肮脏和鄙俗。
认知语言学; 莫言文学作品; “色彩变异”
莫言曾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人, 创作每部作品都尝试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 所以莫言灿烂的语言也得到国内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关于莫言的语言浩瀚如海、 林林总总的研究, 大致可归纳整理为: 对莫言作品中的词语研究, 比如方言特色(从语用的角度分析莫言小说中方言使用的情况, 论述了方言的文学功能及审美效果, 并试图探询小说作品中使用方言的原则); 民间熟语的特点(重点探讨谚语与歇后语的文学功能)等; 对莫言作品艺术特色的关注, 即从作品的多重视角叙事、 主题的象征意义、 寻根意识, 到文章叙述的复调结构、 狂欢场景、 再到作品的现代性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技巧﹑修辞艺术等方面; 综观学界对莫言文学作品的研究现状, 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创作风格、 人物形象、 叙事手法、 词语研究、 艺术特色等方面, 分析莫言作品语言特色的研究大多将文学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 较多地呈现出对作品主题的解读; 尚且没有学者从认知的视角, 把莫言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隐喻的语言现象来思考其价值和意义, 更没有对莫言文学作品中色彩词做系统的研究。 据统计, 莫言对“色彩”有着明显的偏好, 其17部文学作品标题中颜色的出现频次分别为“红色”5 次 、 “白色”3 次、 “金色”1 次、 “黑色”1次, 作品中颜色词出现频次为8 534 次。[1]莫言文学作品中的色彩词不仅是对事物原本的忠实描写, 也是利用色彩词的隐喻意义构建一个文学的色彩空间。 隐喻是两个不同概念相互映射的过程, 从概念隐喻视角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2]在文学作品中选用恰当的色彩词是达到语言美感、 产生艺术魅力的重要途径之一。[3]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探究颜色隐喻是欣赏莫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
1 认知语言学视域的色彩研究
隐喻是人们思维、 行为和表达思想的认知方式, 是基于身体感知去描述和认知那些抽象的和难以理解的事物。 在《隐喻学概论》中, 赵艳芳认为人们总是通过寻找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似点去认识和理解所处的世界, 这种跨领域的“映射”是一个隐喻性的认知系统, 语言正是由此发展。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工具,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修饰。[4]106颜色广泛出现在我们的语言中, 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认知域如情感、 性格、 心智等抽象的范畴存在着内在特征或外在表象联系的关联, 被广泛用于映射其他事物, 通过颜色认知和理解原本没有颜色的事物或者概念便形成了颜色隐喻, 体现出人类社会生产、 生活的印记, 是人们更好地体验、 认识世界的一种主观方式, 是人类重要的思维工具和认知工具。
回顾色彩研究的历史, 就基本色彩词汇系统而言, 无论何种语言都体现出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和普遍原则。 颜色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被广泛应用于映射其他事物而具有了千变万化的比喻和联想意义, 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 自古希腊时期开始的语言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聚焦不同语言系统中的颜色范畴及其分类。 语言是思维的外衣, 人类对赖以生存的世界的认知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 语言中的范畴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范畴呈现出对应关系。 学界最早研究颜色词中语言认知问题的学说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 该理论对颜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生理性的、 物理性的、 感性的、 视觉的知觉形式, 而从心理出发, 与其他事物相联系, 成为一种观念性的阐释和象征性的比附。[5]446-447色彩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 感性的知觉形式, 而是与文化、 心理相联系, 与语言表达息息相关。 色彩认知域是人类的基本认知域。 在人的认知体验中, 人们能够体察到一种颜色与一些抽象范畴中事物的非客观相似性。 颜色词源于他们的初始意象, 当我们把颜色词与抽象概念相联系的时候, 颜色词常常具有了隐喻色彩。 比如人类对黑色往往产生恐惧和绝望等消极的联想, 缘由可追溯到人类对世界和自然知之甚少, 对未知事物怀有恐惧的原始时期, 尽管黑色和所寓意的事物之间没有直接的语义联系, 但是基于人类自身生活经验而对黑色所产生的联想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思维。 颜色隐喻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 色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起着不同的作用, 成为文明世界中必不可少的构成形态。[6]
2 莫言文学作品中的 “色彩变异”
颜色与隐喻的有机结合是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创作手段之一。 运用色彩意象可突出作品主题、 塑造人物形象、 渲染作品格调, 可见, 注重对色彩的运用是莫言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 莫言不但偏爱红色, 还刻意调配青、 粉、 紫等其他色调, 描写与之相呼应的其他物体的红色, 如暗红色的蚂蚁、 鲜红泪珠、 深红的嘴唇和赤红的皮肤等。 他把一连串色彩或对比或累加起来, 形成扑面而来的视觉效果。 色彩在莫言的笔下犹如画家手中的颜料, 或粗描或淡写, 或浓妆或艳抹, 以色彩斑斓的颜色关联作品的多重意义, 赋予色彩不同的隐喻内涵。 颜色就像桥梁沟通了文学世界和莫言的内心世界。[7]莫言对颜色有浓厚的意识倾向, 以充满魔幻色调的叙述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其文学作品中建立了一个色彩的艺术王国, 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色彩感知有着明显的“色彩变异”。
2.1 “红色”的变异
红色在我国最早的汉语辞源学词典《说文解字》中指的是火与血的颜色。[4]106以红色原本的物理特性为基础, 高度抽象、 升华, 体现出 “生命、 光明、 战斗、 活力、 激情、 温暖、 力量”等非颜色指称的文化意义。 汉语中红色被赋予幸福、 喜庆、 吉祥、 兴旺、 好运等隐喻意义, 人们往往从红色联想到战争(如红心、 红军、 红色政权、 红色根据地)、 福利(如红包、 红利、 分红)、 成功(红榜、 红运、 开门红)等。 总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红色令人觉得温暖, 感到热情。[8] 86
然而, 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 红色却充满残暴、 邪恶、 性等意义。 例如: 《红高粱》中的“红高粱” 是具有深刻寓意的象征实体, 红色充斥着整部作品, 是突出渲染的主色调。 罗汉大爷誓死不屈服日寇而被活剥人皮呈现出血染的风采。 一望无边的火红高粱地变成了鲜红血液的大海: 罗汉大爷、 我爷爷的、 我奶奶的、 单氏父子的、 日本鬼子的等等, 血腥弥漫、 惊心动魄。 鲜红如血的红色高粱里, 激活了原始欲望的诉求, 性欲象脱缰的野马, 成就了“我奶奶”叛逆自由的性格。 火红的高粱宣泄了他们的性爱, 一望无际的红色高粱表征了人类原始的、 粗放的生命力。 《金发婴儿》中单从小说附带插画就可以看到浓浓血红色的背景、 半裸的男人和白花花肥硕的女人共同渲染了赤裸裸的性欲。 火红的公鸡鸡冠唤起了紫荆对性爱的渴望, 红色成为原始的性冲动的诱因, 这个长期遭受性压抑的女人在红色的刺激下最终冲破了封建禁锢的罗网。 《红蝗》更是以红色充溢弥漫全篇, 红色承载着生命的律动和高昂的情绪, 暗示青春的躁动, 包含着美与性的暗示。 莫言后来创作《红蝗》则充分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红色演绎成为赤裸与欲望的代名词。 “蝗”是一种害虫, 红色是丑陋的象征, 红蝗意味着人类贪婪自私的本性和永无止境的欲望。 莫言通过描写这种暗红色的丑陋动物来揭示人类比蝗虫更加自私、 贪婪、 邪恶的本性。 八万字的小说中红色出现了近百次, 红色的沼泽、 红色的愤怒、 红色的欲望, 莫言以不同寻常的眼光看待红色, 以更加大胆的笔触异化红色, 揭示人性的缺失。 对丑陋邪恶的厌恶之情、 对爱情的渴望、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对社会进步的期盼、 对生命意识的呼唤在一片揭丑的红色中呈现出冷酷严峻、 发人深思的精神折磨, 寄托着作者深邃的思想情感。 这种“以丑为美, 使美变丑的独特趣味, 在表现出一种人格样式的同时使小说处处显示出狞厉的美……为中国读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9]。
2.2 “绿色”的变异
在汉语中绿色是青春、 生机、 希望、 和平、 生命力等象征意义。 比如“绿水青山、 苍翠欲滴”形容景色秀丽、 草木等绿色植物富有生机, “丹心碧血”表示誓死效忠的精神, “苍松翠柏”讴歌不畏严寒、 顽强的生命力。 绿色在英语中也有健康、 正义、 环保等积极的意义, 比如“a green old age”是老当益壮的意思, “remain forever green”意思是青春永驻。 颜色反映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整体价值取向, 绿色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却有着理想、 青春和智慧等美好的隐喻内涵。
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对绿色表现出了浓厚的意识倾向,但绿色在莫言的笔下却象征着逆境的恶劣、 现实的邪恶、 人性的肮脏和鄙俗。 例如《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以绿色强烈抨击愚昧落后的封建势力。 主人公金菊在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绿色的幻觉: 金菊眼前万点金星飞迸,接着又变成绿色的光点,那么多的绿色的光点画着优美的弧线在她的头上飞舞。 她伸出手,去捕捉些么绿光点却总也捕捉不住。 有时, 好像把一个绿光点握在手心里,但一张手, 它又飞走了。 《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脸皮被剥掉后一串一串鲜红的小血珠从他的酱色的头皮上往下流, 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 鲜血淋漓的酱红色的背景之上的绿苍蝇格外加强读者对残酷丑恶场面的心理冲击, 在强烈的恐惧中体会绿色的龌龊。 《欢乐》中莫言以回旋不绝、 长河大浪般的语言气势组成了一连串丰富的绿色意象: 披着绿浓血和粪便的绿躯体、 阴凉的绿铜臭、 绿色的谎言、 绿蛆虫的灵魂、 绿色的海誓山盟、 永远逃避绿色、 花花绿绿的云、 绿色的恶心、 碧绿的仇恨、 母亲嘴里吹出来的绿色气流、 奶奶洁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绿又染红、 嫩绿的脑浆、 绿色的臭屁。 绿色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始终象征着事物消极的一面, 充满生命力象征的“绿色”在莫言的视域中变得肮脏, 成为社会上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3 结 语
颜色的所指远离了其本来的意象, 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 人们通过联想与其相对应的物体, 从中获得在社会约定俗成下产生的特定隐喻意义。 在隐喻视角下, 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对语言本意的表现, 更多的是对这个语言的表层意思背后的一个深层次文化的体现。[10]色彩的隐喻意义是人们基于生活体验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 对颜色具有认知上的共性。 然而, 作家所处的时代、 生活环境、 个人经历、 思维方式、 宗教信仰以及创作心理等多种因素促成了颜色认知共性中的个性。 色彩词语折射出来的正是作家五彩缤纷的内心世界。 莫言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色彩变异”是基于其自身切实的生活基础和心理感受。 莫言童年时期正值中国经济萧条、 缺衣少食, 封建统治下的社会基调是压抑的、 沉闷的、 不自由的, “饥饿”和“愤怒”占据了莫言几乎全部的童年回忆。 莫言在农村生活了20年, 对土地的爱与恨、 对饱受压迫的农民的同情、 对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对人生的痛彻感悟等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他对色彩的疯狂诅咒, 歇斯底里地从他满腔愤怒的语言中宣泄出来。 莫言对客观世界的颜色感知正是经过了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渗透和过滤, 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色彩变异”, 又将其融入隐喻, 诉诸笔端, 运用色彩词来绘色赋形、 凸现主题意识、 实现文学象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色调和语言风格。
[1]潘峰, 黄健. 论莫言文学作品中的红色词[J]. 时代文学, 2012(4): 99-101.
[2]张平丽. 概念隐喻视角下对《宠儿》的解读[J]. 短篇小说, 2015(11): 51-52.
[3]程语诗. 谈文学作品中色彩词语的语言表达效果[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1(3): 213-214.
[4]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2001.
[5]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6]罗瑶. 色彩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嬗变[J]. 成都大学学报, 2011(4): 111-113.
[7]纪燕. 莫言文学作品的颜色隐喻研究[J]. 芒种, 2014(12): 27-28.
[8]朱光潜.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9]颜纯均. 悠闲而骚乱的心灵——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莫言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1988(3): 79-84.
[10]闫锐. 隐喻视角下《肖申克的救赎》的解读[J]. 短篇小说, 2015(11): 111-112.
“Color Variation” in Mo Yan’s Literatur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JI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China)
The metaphoric meaning of color is a subjective cognition based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 With shared cultur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commonness is found among people’s perception of color. In Mo Yan’s literature works a strong consciousness in color is detected to be deviated from the color perception in common sense: red is loaded with metaphoric meaning such as cruelty, shock and sex; green is full of evil, filthy and vulg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Mo Yan’s literature works; “color variation”
1673-1646(2016)06-0092-04
2016-06-12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语料库的莫言文学作品中的颜色隐喻研究(14YJC740035)
纪 燕(1979-), 女, 副教授, 硕士, 从事专业: 认知语言学。
H15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