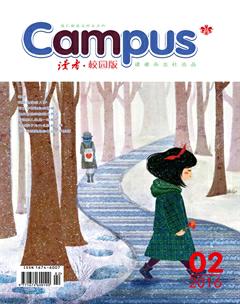像一头怪物
绿妖
我上初中时,班里转来了一个从市里来的女生,短头发,寡言。那时我经常逃课,她观察了我一段时间,然后加入我的行列。我们一起逃课去图书馆,钻进胡同买旧书、旧杂志。那条胡同是老城区磨各种调味粉的所在地,摊主会收购大量干净的旧书、旧杂志用来包装粉末。在弥漫鼻腔的花椒粉、辣椒粉中,我们一本本地挑选自己心爱的杂志。当然,新华书店里也有书,但是新书太贵了。一本《简·爱》要8块钱,得存上很久的早餐钱才够。有一次买书归来,校门上了锁,虽说翻墙是我俩的家常便饭,但我们那天去了学校门口的池塘边,天下着大雪,我读书,她在雪地上写字。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我们的头发上。
我们的学校是由退伍军人办的私立中学,实行军事化管理。有几个男生犯了错,校长就把他们单独关在地下室里,关了8个小时。我对这种粗暴的管理方式生出极大的反感,进而判断校长已经不值得我尊敬,所以,我不再上他的课。这是我少年时期第一个主动的“选择”。
但那个女生不同,逃课只是她缓解压力的途径,大部分时间她还是会像鸭子一样,排着队缓缓步入教室。在20世纪90年代,小城市里是不流行念高中的,因为读3年出来如果考不上大学,这3年就是白费。她上了水利技校,其实她的分数上重点高中没有问题。在技校,她仍然拼命念书,考第4名会让她崩溃。她拼命考试,就是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但无论她考第几名,都会被弟弟的顽劣抵消,家人都为在学校打架、被学校叫家长的弟弟叹息。她和母亲形同陌路,母亲当着全家人的面把她说得一文不值:“捡破烂的人都不捡你!”她学会了沉默。等到她17岁时,母亲又想知道她为什么沉默,围着她打转,想撬开她的嘴,这迟到的关注比一贯的忽视更令人痛苦。
现在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原生家庭的缩影,粗暴的父亲或者控制欲强的母亲使家中没有温柔,要么是忽视与冷漠,要么是粗暴和讥笑。这对于神经敏感的孩子来说是极大的煎熬。她抱怨完母亲,又为自己的抱怨害怕。我们受的教育是“子不嫌母丑”,我们怎么能抱怨自己的母亲呢?于是,她说自己自私——正常的表达迅速变成自我攻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和我们的真实感受是隔绝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爱情、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青春是一场漫长的内耗。原生家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厚壳,我们用十几年的时光去凿穿它。
毕业后,她一度在市火电公司吊车班上班,开45吨的吊车。她说那是工地上最好的工作,仅次于坐科室。那时她刚刚17岁,对于小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成长来得格外迅猛,读大学的孩子22岁才需要面对社会,我们在十六七岁时就开始面对。那个年纪,按照华德福的教育理论,孩子们刚刚从精神世界被扔出去,扔到了物质世界。我们发现,身边的这个世界不符合我们的想象,并不美。同事们很少看书,反而对八卦琐事津津乐道,这趣味在我们看来庸俗无比。
我不知道在她心里经过了怎样的斗争。我在那个时候,忽然说起了普通话,这在所有讲河南话的亲人当中像个笑话。而当我和她再见面时,她已放弃了火电厂的工作——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大逆不道的事情——在一个小区里开了一间裁缝铺。于成人而言,我改说普通话只是因为性情乖戾,但她的举动脱离了生活的轨道。那间设在煤矿工人小区的昏暗的小小的裁缝铺,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自我觉醒,作为一个人去主动选择,而不再是作为父母的女儿和财产而存在。那间裁缝铺后来不知所终,我和她也失去了联系。在一个衰败的工人小区,一间裁缝铺无力抵抗整个矿区煤被挖空的大势洪流,即使它承载了一个少女全部的希望与梦想。
17岁的时候,我看中了爷爷的床单,是那种老粗布的布料,黑白格子,铺了很多年,手感仍然挺括。跟爷爷要了,洗干净,一个春天的周末,我带着这条床单,坐了30分钟的小巴到市里去找她。改说普通话的我和本来就讲普通话的她,两个叛逆者在一间裁缝铺会合。她兴奋地用床单给我做了一件衬衫。现在回想,那是一次并不高明的设计,那种生硬的色块架在我身上,凸显了衣服和我所有的缺陷。就像正青春的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面对社会,索性放大并强调自己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并以此抵挡世俗。我穿着那件衬衫,像一头怪物在街上走着,充满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