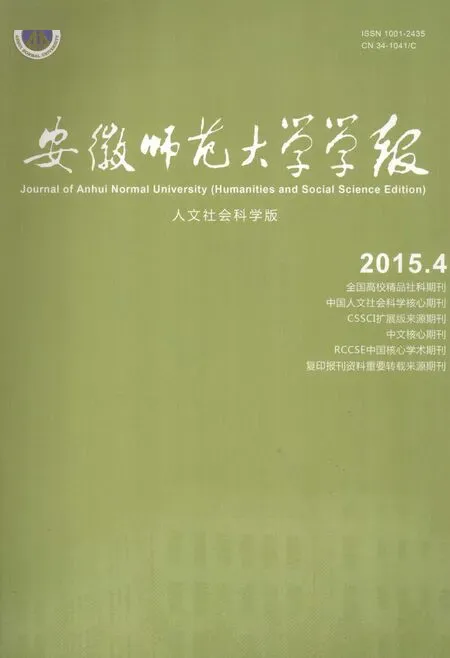《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
关键词:庄子;《天下篇》;圣人;内圣外王 出现在《天下篇》的开篇中的两个是“方术”与“道术”:“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而在方术与道术对照的背后,隐含着今学与古学的对比:后文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的古之人,则是古之道术的人格体现;以六家之学所代表的百家学(或称诸子学),可谓典型的方术,“天下之治方术者”所指称的正是百家之学。不过其中的前五家对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皆能闻其风而悦之,因而未尝不是古学的绪余与延续,第六家惠施之学则与古学完全隔膜,不再能上承古学的本根。
摘要:《庄子·天下篇》之关切并不在于六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其对六家的评述实际上指涉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中国政教生活最为核心的问题。通过“道术”与“方术”之辩,庄子揭示出从方术中开出道术的可能性。道术的通达要求天道(神)、地道(明)与王道、圣道四者的连接与整合。《天下篇》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下将人分为七类,揭示了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在这七类人中,惟有圣人能够通达天人,承担圣王的事业。因此在人类的政教文明系统中,圣人具有中枢性的地位。
Abstract:The concern of Chuang Tzu·Under Heaven is not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six schools. Chuang Tzu's discussion on the six schools in fact refers to the way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which is the key problem of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B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aoshu” and “fangshu”, Chuang Tzu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of exploring daoshu from fangshu. The acquirement of daoshu demands the connec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ways: the way of heaven, the way of land, the way of king and the way of sage. Chuang Tzu·Under Heaven divide the human beings into seven species in the sight of “spirit, brightness, sage and king”, and reveal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nature of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 species, only the sage can link up heaven and human, and burden the enterprise of a great king. So the sage is the pivot in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 of human beings.
引言
《庄子·天下篇》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收入《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系最早从总体上综论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大文字”,三者之中尤以《天下篇》为重。《天下篇》对天下学术的讨论有本根与枝叶贯通的整体感与透彻感,且立意极高,其对六家学术的论述本身就是在探讨内圣外王之道,而后者乃是开通天下作为“天下人的天下”的可能性的根本。
今人往往视《天下篇》为我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这当然不错,但这种看法里包含了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作客观研究以还其本真面目的现代眼光,在这种为求真意志所主导的现代目光中,《天下篇》的写作动机,只是纯粹的学术动机,即客观地展现周末学术的状况。其实,与老子、孔子、孟子、荀子一样,庄子并不是职业学者,其著书立说的活动并不能放在现代的分科性与专业性的研究体制中加以理解。相反,学术本是经纬天下的一种方式,其与世道人心、风俗政教相为表里,此诚如张之洞所言:“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157故而皆系有所为而后发,学者之学术关切只是政教关切的内在部分。而现代意义上以客观性为其追求的“学术史”,则是职业化学术建制的产物,当然也是学术之去政教化的后果。显然,庄子的关切并不在六家学说客观的本来面目,其讨论六家学术的方式本身就是在展开他所关切的政教问题,或者说,对六家学术的探讨本身成了他直面政教生活最核心问题的方式。

然而,这篇“庄子自序”却冠名为 “天下”,这究竟如何理解?当人们以学术史或学案为出发点面对《天下篇》时,自然“天下”这个命名不再重要,而以文本首句字词名篇的古文义例,似乎可以给出一个切实的理由,以终止在“天下”的篇名与《天下篇》这一“大文字”之间进行任何义理关联的追问。在这种情况下,陆德明的“以义名篇”*按《经典释文》对《天下篇》篇名的理解是“以义名篇”(参看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65页),但后代的理解中,却越来越偏向于它的反面。说,遭到现代学者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方光在其《庄子天下篇释》中断言:“惟篇中历述诸子,论列是非,陈义立言,专指道术,定名‘天下’,不过举篇端二字,以冠篇名耳。所谓义者,果恶乎在?陆氏于‘天下’义无所发明。”*严灵峰编《无求备斋老列庄三子集成补编》第55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问题在于,对于现代学者所谓的古文篇名的义例,陆德明岂能无闻,然而其着意突出“以义名篇”者,用意何在?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在提醒人们,“天下”二字并不是作为一个无关紧要、可以省略的辅助性语词,而是作为一个直指主题、点名宗旨的中心词语,进入《天下篇》的结构整体的,这意味着《天下篇》之所以命名为“天下”,并不能脱离《天下篇》的总体内容来加以思考。换言之,如果《天下篇》果为庄周自序撰作宗旨,那么其名篇之义例应该与内七篇的命名关联起来加以考察。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这样一些直接切入宗旨的篇名,对于这七篇文本的理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古往今来,人们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离开篇名,来理解这七个义理深邃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天下》的“以义名篇”,其实是提醒人们,恰当的切入点是将它与内七篇放置在同一个系列——而这意味着,“天下”,并不仅仅是篇首的一个词,而是如同“齐物论”之与《齐物论》一样,它深层地渗透在《天下篇》的每一个细节与角落里,既构成理解这一文本无法绕开的出发点,又成为这一文本所指向的目的地。
《天下篇》所谓的“古之道术”,说到底不能脱离“天下”这个词语来理解,它应该被理解为《大宗师》所揭示的“藏天下于天下”之道,也就是将天下交给天下人、让天下成为天下人的天下的道术,而这一道术被《天下篇》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惟有通过内圣外王之道,天下作为天下人的天下的可能性,才能被贞定。而在“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情况下,内圣外王之道如何重新开启?这个问题构成了内在于《天下篇》的隐蔽线索。正如《齐物论》全篇没有一处提到齐物与齐论,但整篇却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对于那些习惯于从词语、范畴或概念出发,并且以概念出现之统计频率来试图抵达内容本身的现代探究方式而言,的确《天下篇》中天下的主题并没有得到概念化与范畴化的处理。但是从思想的深层维度去理解,不难看到,陆德明揭示的“以义名篇”,实际上昭示着一种贯通《天下篇》的可能途径。
从内容上看,《天下篇》分为两大部分:一,总论;二,论六家之学。总论部分包括以下若干问题:道术与方术之辨、神明圣王原于一、人性七种类型(生命存在方式或类型)、内圣外王之道的裂变与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即从古学到今学的演变)。第二部分论六家之学:(1)墨翟、禽骨离;(2)宋钘又称宋子,庄子作宋钘,孟子作宋牼,韩非子作宋荣子)与尹文;(3)彭蒙、田骈、慎道;(4)关尹、老聃;(5)庄子;(6)惠施。在六家学术中,前五者都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发端,而《天下篇》独不以之许惠施,则在作者看来,惠施之学已经失去了与古之道术的连续性,因而并不是古之道术于今仍在的绪余或支脉,而是彻底的“今学”。它以天下万物作为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而失去了根本的政教关切,既脱离了个人的修身完生,也与政治-社会的改良了不相干。因而由之再也无法上通到神、明、圣、王原所自出的“一”,而是下降到彻底地以支离方式去理解天地万物然却不通人道之方术。无论是对惠施的评价,抑或是对其他五家的理解,《天下篇》都站在古之道术的高度,而不是现代学者所追求的对六家之学的客观甚至中性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设若自序之说成立,那么,《天下篇》对其余五家之学的介绍,就不是为了讨论五家之学本身,而恰恰是为了给出庄子的撰作宗旨,因而实在只能是庄子之学自我理解的一个导引。对此,清代学者宣颖(生卒年不详)的如下理解值得重视:“一般溯古道之渊源,推末流之散失。前作大冒,中分五段,隐隐以老子及自家收服诸家,接古学真派。末用惠子一段,止借以反衬自家而已。”[2]197我们虽然无法完全同意宣颖隐含的庄子归宗老子、并以自己与老子作为百家学之终的意见,*与宣颖近似,朱得之以为《天下篇》“序其祖老而不同于诸子之故”,陈寿昌谓:“此为《南华》全部后叙,上下古今,光芒万丈,以文妙论,自是得漆园之火传者。”见方勇《庄子纂要》第六册,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0-822页。但宣颖指出《天下篇》讨论五家之学的目的,在于“推末流之失”以与“溯古道之渊源”构成对照,从而引申出庄子以其学“接古学真派”的醉翁之意,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王夫之对《天下篇》讨论五家之学的用意之概括,无疑更为到位:“乃自墨至老,褒贬各殊,而以己说缀于其后,则亦表其独见独闻之真,为群言之归墟。”[3]462更为重要的是,船山指出《天下篇》追溯古之道术的分化时强调六艺之学的意义:“若其首引先圣六经之教,以为大备之统宗,则尤不昧本原,使人莫得而擿焉。”[3]462庄子之学与六艺之教的关系,实在是庄子面对的大问题,而以学术史定位《天下篇》的类型的现代学者,却无法对此进行追问。问题在于,不独对庄子以外的五家之学的勾勒,而且对于六艺之学的叙述,以及对于旧法世传之史的叙事,是否都在一定意义上标画了庄子之学得以立身的位置?古之道术、旧法世传之史、六艺之教、百家之学,所有这些被《天下篇》在内圣外王之道的高度被结构化之后,对之的刻画,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以学术经纬天下的方式,最终又在什么意义上这种刻画本身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当下展开方式?
一、道术与方术之辨*
问题是当学术完全陷落到方术里而失去了对道术的开放时,它还能承付“天下”吗?《天下篇》以道术与方术之辨开篇,而开篇的“天下”一词*“天下”就其内涵而言,固然可能如顾实所言的那样,是“天下之人”的略词(张丰乾主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但这里使用“天下”可能另有深意。比如后文对墨子的批判即在于,虽然墨子真的可谓是“天下之好”,但更重要的是他“离于天下”“反天下之心”,终至于“天下不堪”,其学能“奈天下何”!对宋钘、尹文等等的评价,“天下”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天下”并非仅仅作为天下之人的集合,而更是一种评价学术之尺度,内圣外王之道所承担的不就是天下吗?事实上,《天下篇》总论部分“天下”一词出现6次,其中第5次是“天下之人”。若果如顾实所言,第一次出现仅为“天下”,第5次出现为“天下之人”,则意思无差别。但恐怕未必如此,因为整个《天下篇》用词考究、书法之密,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分论部分,墨子节“天下”出现7次,宋钘、尹文部分出现3次,彭蒙、田骈、慎到部分出现2次,关尹、老聃节出现3次,庄周节出现1次,惠施公、孙龙节出现4次。总计《天下篇》,“天下”一词出现26次。,似乎在提示,道术与方术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关联着“天下”这一核心主题,并且只有当这一问题成为“天下”主题的切入方式时,我们也才获得进入《天下篇》的适当路径。换言之,天下的主题构成一种指引,它规定着道术与方术之辨所内涵的问题意识及思考方向。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不可加”意味着达到了极致,达到极致是道术的特性,而不是方术的特性。因而,对治方术的人们而言,他们所治的并不是“方术”,而是“道术”。但一旦从古之道术的视野来看,则他们“所谓”的“道术”不过“方术”罢了。庄子在这里提供的乃是一种必须被认识的现实状况,这就是以“方术”替代“道术”——这一现象构成了一个时代性的人文状况,“百家异说”以及与之相应的“诸侯异政”,正折射了这样一种人文状况:对道术的言说并没有触及道术,而是停滞在方术的层面上。由此发生了“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的诘问与感慨,从对“古之所谓道术”的追问,传递的恰恰是“今之所谓道术者”在实质上远离了道术的现实认知。
古之“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无封无畛,而今人所治方术则为道术之一偏,“方术,道术之局于一方者也”[4]447。“方术,一方之术,有在有不在者也。道术,大道至术,无在无不在也。”[5]827因而方术与道术的区别是很明确的,“治方术不可竟说是道,道本无方也”[6]777。但既然古之所谓道术无乎不在,因而它未尝不在方术之中,通过方术而呈现自身,“亦不可说(方术)非道,道在方术中也”[6]777;但因道术无所不在,故而并不能为某种特定的方术所穷尽。即便从方术的层面去理解道术,道术也必然开放在作为复数的诸种方术而不是作为单数的一种方术之中。道术虽可通过方术而呈现,但并不因此而仅仅呈现在某种特定的方术之中。方术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是古之治道术者通过治方术而治道术,其必不“以其有为不可加”,相反,却时时刻刻注意到此方术自身适用的有限边界。因此,任何方术都同时包含着通达道术与远离道术的双重可能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方术的消除与瓦解,而在于从方术中开出通达道术的可能性,这就是认识到方术的边界。
钟泰云:“全者谓之‘道术’,分者谓之‘方术’,故‘道术’无乎不在,乃至瓦甓尿溺皆不在道外。若‘方术’,则下文所谓‘天下之人各自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者。既有方所,即不免拘执,始则‘各为其所欲’,终则‘以其有为不可加’。‘其有’者,其所得也。所得者一偏,而执偏以为全,是以自满,以为无所复加也。此一语已道尽各家之病。”[7]756“若学虽一偏,而知止于其分,去声不自满溢,即方术亦何尝与道术相背哉!”[7]756将方术本身作为方术来看待,本身就已经包含着某种道术的因素,如同知俗之为俗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俗。还方术于方术、知方术之边界,这本身即通道术。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即便方术自身拒绝了向道术的开放,但无所不在的道术也照样将自身开放在方术中,就“方术”的本身而言,它就是“道术”之局于一方者。[4]477当成玄英以“道”释“方”时,他无疑注意到方术与道术的关联。*将“方”理解为“道”,并非孤例,因而值得重视。韦昭《国语注》卷十六《郑语》云:“方,道也。”杨倞《荀子注·礼论》云:“方,犹道也。”《吕氏春秋》卷十七《君守》高氏训解云:“方,道也。”等等。方勇以为《天下篇》的旧注(如成玄英)以“道”解“方”为误(《庄子纂要》第六册,第825页),没有看到方与道的复杂关联。的确,方术提供的同样是道路与真理,但“方术”所揭示的“道”与“道术”之“道”毕竟有所不同。
如何认识方术中的真理与道术中的真理的差异?王博根据《说文》段注与《经籍籑诂》对“方”的字义加以总结,分析出14义。*详参见王博《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方”字》,《简帛思想文献论集》,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74-275页。“方”的若干义项,大体理解为一棵语义树,有本根、主干与枝叶,彼此相关,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语义树的高度,可以看到,当吾人以“道”释“方”时,这里的“道”有其限定,它不是那种无方无体意义上的本源之道或绝对之道(这种本源之道在《天下篇》被刻画为“一”),而是有条件的道,呈现出明确规则、有封有畛,而且它是以复数方式出现的。当吾人说齐家、治国、修身、平天下各有其“道”时,这个意义上的“道”就是“方”。“方”之为“道”有其适用的条件与边界,而这正是它所具有的“处所”与“廉隅”之义的根据;“方”之为“道”,只有在某种处所、场域、情境、维度、脉络下才是可能的,过此以往,则不再适用。因而对于“方”之为“道”而言,存在着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这就是“方”被理解为“义”的原因,而“义”本是适宜、合适的意思。这说明,“方”所呈现的真理,与作为“一”的“道术”所呈现的无条件、无方所的真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也就是说,“方”所表现出来的“道”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之道,而是根基于地方性,因地制宜,因而需要拷问其适宜性。它的真理性是立足于它的条件性之中的,而它的条件性就是它的处所性、地方性。也正因为与处所性、地方性相关而有适宜性的问题,故而它有“正”与“不正”的问题,即在特定处所、脉络下合于“义”(适宜),即为正。设若是无方无体的道,则并无所谓“正”与“义”与否的问题。这样,当“方”被理解为道(道路与真理)时,它与大地(地方、处所)的关联成为它的内在规定。钱穆以“居地”解“方”,恰好触及了这一点。*详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方”之为“道”,其所具有的界别性其实也来源于地道本身的规定,“四方”“土方”“方向”等语已经将我们带入这种界别性之中,所谓的“四方”一词正是这种分别性的体现,而《周礼·天官·冢宰》所谓的“辨方正位”、《易·未济》所谓“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也正显示了“方”与“地方”的关系。事实上,汉语的“地方”一词,直接展示了“地”与“方”的内在关联。《周易》“坤”卦取象于地,而《易·坤卦》六二“直方大”,王弼《注》谓“地体安静,是其方也”,这就是将“方”作为坤德,即大地之道的品质。《周易·坤卦·文言传》以“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来表述“坤”的品格,此与所谓的“地道曰方”形成义理上的连接。*关于地道与天道的分别,参见陈赟《〈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周易研究》2015年第1期。另外关于地方性的讨论,参见陈赟《世界与地方:政治生活的伦理境域》,收入陈赟《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8页。在该文中,笔者从形而上的角度讨论“地方性”的本体论意义……世界固然是存在者共有的公共敞开区间,但同时它又是界域性的,“世”是在“界”中显现它自己的。由此,汉语思想对世界的理解,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共有空间,相反,不同的“地方”,构成了“世界”的不同“界域”。对“世-界”的经验总是发端于某一地方,而在此地方性的经验中,世界才得以真正作为世界而敞开。人的栖居固然是在“世界”中,但总是发生在某个“地方”,而不是一个没有“地方”的“世界”。“地方性的世界”,或者“世界中的某个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是古典思想的一个共识性信念,《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对于它的内涵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天道圆,地道方,圣王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这就是说,天道是运化的,圆融的,不可测度的,“神无方而易无体”正是对天道的揭示。天道虽然无方无体,没有明确的区域性的规则,“道无定在,而实无所不在”[6]777,但它又是无所不在的,贯通表里精粗的,天道的真理因此常被表述为“天之经”,所谓“经”意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常道,作为大经大法,它不受具体情境与条件的限制,所谓“道本无方”[6]775,天道的真理由于它的普遍性因而没有所谓适宜性的问题。适宜性即“义”,意味着必须与具体的状况、特定的情境、相应的条件相适合、相配合,它是地道的规定,故而汉语有“地之义”,以与“天之经”相对。大地则被区隔为不同的地方,在自然的意义上,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地理、地貌,因而也有独特的天气,甚至特有的生物圈;在文化的意义上,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风俗、习惯、传统、历史、生活方式,乃至文明系统。“地道”作为真理恰恰根基于一个地方的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因而,与无方所、无定在的天道相比,地道一方面是有方所、有定在的,因而它是确定性的真理,但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相对性,它总是具有一个适用边界或条件的问题。方术之“方”根植在大地的风土性之中,方术既是接地气但同时又是囿于地气的。汉语说“因地制宜”,而不说“因天制宜”,就是因为地道、方术因应着区隔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对性,但也正是这种区隔性与相对性,使得地道的真理有着明确的规则。
基于方术与地道的关联,可解庄子所提出的“方内”与“方外”的分辨。《庄子·大宗师》:“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这里的“方”即意味着大地上或人间的礼法,因而,《荀子·礼论》《礼记·经解》将“不法礼”、“不足礼”或“不隆礼”、“不由礼”的人叫做“无方之民”,而将“法礼”“足礼”“隆礼”“由礼”者叫做“有方之士”。*孙希旦亦云:“惟礼达分定,而民知向方。”《礼记集解》卷二十二《礼运》,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6页。钟泰由此而正确地指出:“方内”与“方外”的“方”指礼,“游方之外”谓游于礼法之外,“游方之内”谓游于礼法之内。[7]155礼之所以为“方”,正在于礼之与地道的关联,《礼记·乐记》云“乐由天作,礼由地制”“乐者天之和,礼者地之序”,这里表述的正是礼与大地的真理的内在联系。显然,方之内即大地的法则特别是人间世的真理(礼法就是这样的有条件真理)之内,方外则意味着在地上的真理之外,直接与天道的真理为体。*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说法可以作为参考:“当我着手写‘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时,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讲的是天上的真理,多神教讲的是尘世的真理;将来,这两个真理结合起来,那宗教真理就完满了。但是,当我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要把基督与反基督者结合起来,乃是渎神的骗局;我知道了:两个真理——天上的,尘世的——已经融合在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身上了,融合在那个为普世基督教所信奉的人身上了;我知道了:在他——唯一真神身上的真理不仅是完备的,而且还在不断被完善、不断成长、永无止境,除他之外,再不会有其他。但是,我现在还知道,我必须把这个骗局延续到底,以便看到真理。从一分为二到二为一——这就是我的路……这唯一的、涵盖一切问题的问题,就是关于两种真理——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真理在神-人现象中的关系。”《〈梅烈日科夫斯基全集〉自序》,收入《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卷一《生平与创作》,杨德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虽然《大宗师》指出,方内与方外,“内外不相及”;但无论是孔丘之游方内,抑或老聃之游方外,都使用了一个“游”字,刻画了一种越界的自由,即孔子虽然逍遥于方内,但却由此通达方外,老聃虽然逍遥于方外,但却并没有与方内隔绝。
总之,道术意味着全体的真理,方术则是局部的真理,因而它具有相对性。但全体的真理不能不显现在局部之中,因而方术本身的限制就在于它是道术的一端、一曲或一偏,并囿于这一偏而不能上达全体。但若从方术出发,认识方术的局限,超出方术,则可以上达道术。
二、神、明、圣、王与道术的进路*
在讨论了方术与道术的分别之后,《天下篇》对道术的性质又做了新的规定,这就是“一”:“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显然,如果方术是“多”,则道术是“一”。*《老子》第三十九章曾如是描述“一”:“天一以清,地得一以灵,神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第二十二章则云:“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庄子·在囿》:“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庄子·天地篇》:“《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对《庄子》而言,“道术”之“无乎不在”表述的就是道术之为“一”的品质,只有“一”才是古之人所以备的根据。道术当然是原于一,或者说它自身就是“一”,“原于一,则不可分而裂之。乃一以为原,而其流不能不异,故治方术者,各以其悦者为是,而必裂矣。然要归其所自来,则无损益于其一也。”[3]463道术以“一”为特征,因而任何方术一旦溯其本源,无不本于“一”,但同时又是对“一”的分裂,但不管方术如何陷落到一方之见中,它仍然对道术之“一”的品格无所损益。
关于“神”“明”“圣”“王”与“一”的关系,张文江有一个精妙的观点:“道术从五个方面来讲,有四条进路,一个归宿。四条进路就是神、明、圣、王。其中神、明相应于自然领域,圣、王相应于社会领域,或者说政治领域。进一步分析,神、明相应于自然神学和自然哲学,圣、王相应于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他进而以之重新诠释道术与方术:“所谓道术,就是疏通神、明、圣、王和一之间的关系。所谓方术,就是仅从神、明、圣、王的某一段而加以发挥。”[8]104—112这一看法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也具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刘小枫亦有类似的看法:“一是道术之为道术的品质规定,而神明圣王可能是一的四种样式。”刘小枫《颠覆天下篇——熊十力与〈庄子天下篇〉》,《中国文化》第三十四期。
神、明分别对应天、地*神明与天地的关联,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荀爽《周易荀氏注》:“神之在天,明之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昼照。”《周易·系辞传》:“以体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礼记·乐记》:“礼乐偩天地之情, 达神明之德。”《老子指归》:“道德,天地之神明也。”《春秋繁露·正贯》:“德在天地,神明休集。”《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清代张隐庵注云:“神明者,生五气化五行者也。”《荀子·性恶》:“通于神明,参于天地。”,《庄子·天道篇》云:“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这里的尊、卑即指天地与上下之位的对应。郭静云在《神明考》一文中指出:古人以为,日、月、星三辰中,日和月皆出于地而落于地,属于“地”的范畴;而列星恒际玄天,属于“天”的范畴。神气降于天,明形出于地,“神”和“明”相接,成为天地交感的媒介,万物由此而化生。日久天长便结晶出“神明”的哲学概念。如果我们用两个字来揭示“神明”一词的本质的话,那它就是“生机”。古人造字,以日月为“明”,最初的取义是日出自地、光明升起之意。因此,“明”首先是一种时间的观念,在甲骨文中“明”与“昃”是一反义词,“明”指太阳升天的时段,而“昃”指下午太阳降落的时段。而当人们去试图认识和理解宇宙自然现象时,又将日和月看作是由地所产生的“明形”,日和月有按时轮流着升天的机能;在古代神话中,大地乃是日月所出与所入之处,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记录六山为“日月所出”,而在《大荒西经》纪录六山为“日月所入”;《楚辞·天问》亦云:“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日、月二者出于地而入于地,换言之,这也就是大地所出之“明”。这个观念后来也影响于《易传》思想的形成,如《周易·晋卦》曰:“《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神降而交于明,明升而交于神,神明相交是天地交通的最重要的媒介和形式;古人在尚未有抽象的“气”概念时,将天之“神气”下降与地上之日月升腾视为万物化育的生机。《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特别清楚地阐明“神明”系天地相辅之产物。所谓“天地相辅”,即是说天与地的互相辅助与交通。天地不交,则无生机。有神明,天地之间便有了生机。故在宇宙创生当中,神明乃为一关键性的阶段。*郭静云《神明考》,《中国儒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另外请参看郭静云《先秦易学的“神明”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周易研究》2008年第3期;熊铁基《对〈太一生水〉“神明”的历史考察》,《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神明既是天地之德,又是天地之用,钟泰指出:“神者天,故曰降。明者地,故曰出……皆以神明与天地相配,是言神明即言天地之用也。”[7]756神明来自于天地,是自然界的万物所得之于天地的精粹,但它又内在于万物之中,是天地的生化之机在万物中的显现。*钟泰:“‘神明’承‘天地’言。《天下篇》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又曰:‘配神明,醇天地。’以‘神明’与‘天地’对言,而神曰降,明降自天也;明曰出,明出自地也。则‘神明’者,天地之精英,故曰‘神明至精。’”(《庄子发微》,第488页)“‘神明之位’,‘神’属天言,‘明’属地言。《天下篇》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言‘降’,属天可知。明言‘出’,属地可知。故‘神明’者,天神而地明。明之为言盛也。上云‘莫神于天,莫富于地。’‘明’、‘富’皆盛义也。”(《庄子发微》,第291页)《天下篇》述庄周之学时云:“天地并与?神明往与?”,则再申天地与神明的关联,钟泰:“天地以有形言,神明以无形言。以有形言,故言‘并’,《齐物论》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也。以无形言,故言‘往’。‘往’者往来,下文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也。”(《庄子发微》,第790页)神明乃天地之精神,或更精确地说,神乃天之神化,明乃地之精粹。由于始终处于升降运作之中,故而神明并非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运作,神明是天地交通成和的关键,天地、山水、万物之中皆有神明存焉。*自然的山水鱼鸟,“皆有神明”(朱震青《虔中偶语》)。神虽然原于天,但却要下降于地;明虽原出于地,但却上升至于天。因而《天下篇》以“降”“出”状写“神”“明”。*与此相类,《鶡冠子·王》云:“神明者,下究而上际。”钟泰指出:“其举神明者,以表天道、地道。”[7]756也就是说,神的进路是研究天道,它直接探寻大全或道体;明的进路是研究地道,它研究大地上的万物,通过大地的真理而上达道体。天道与地道的进路合在一起,构成了张氏所谓的自然神学或自然哲学的进路,总之是对自然领域的研究。
神与明的差异,对应天道与地道的差异。在《庄子》全书的脉络中,知不胜明,而明不胜神。《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以其“神凝”,而“使物不疵厉而年谷熟”,走“神”的进路。《齐物论》中对于执着于是非的作为人籁的物论,提出“莫若以明”,走“明”的进路。但《庄子·列御寇》对神、明两条路线进行了总结,最终提出了明不胜神、以神主明的观点。“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成玄英疏云:“明则有心应务,为物驱役,神乃无心,应感无方。有心不及无心,存应不及忘应,格量可知也。”(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59页)陆树芝的解释更为简洁:“知有予夺,亦人心之明也。而有知之明,不免逐物而为所使,不若如神之气,可以坐照而征之。明之不胜神久矣,而愚者莫知所谓神,独恃所见以入于人,则用功于外,无望乎其人而天矣,岂不悲哉!”(陆树芝《庄子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明与神本身就有相互蕴涵的关系,但以神主导明与以明主导人却极为不同。王夫之对此的分析极为深刻:
明者,神之所函也。神者虽发见于明,而本体自如,虽未明而固无所诎者也。繇明有知,神则非不知而固无知也。繇明有知,则见为有征,而欲以画天下而平之,故曰“莫若以明”。而不知明随外谍,则与神相离,徇耳目以外通,而不丧其耦;其流也,乃至为苞苴竿牍,用以成兵刑之害。夫内以自葆其光者,神也。外以凌大火大浸,而不害其逍遥者,神也。使人之意消而化,以其神而通物者,神也。神葆其光而天光发,虚室之白,无不照也。如是以为明,则固可使照物之天矣,故又曰“莫若以明”。神使明者,天光也;明役其神者,小夫之知也。故至人以神合天。神合天,则明亦天之所发矣。神与天均常运,合以成体,散以成始,参万岁,周遍咸乎六宇,而明乘一时之感豫以发。其量之大小,体之诚伪,明之不胜神也明甚。而愚者恒使明胜其神,故以有涯随无涯,疲役而不休,而不知其非旦暮之得此以生也。故休乎天均者,休乎神之长运者也。神斯均,均斯平,平斯无往而不征。缘守督以怀诸独,而葆其光,出乎险阻而不伤,凝神其至矣。故曰,此庄生之学所循入之径也。[3]461
简单地说,一方面,以神主导明,是“天而不人”,上升到“天”的机制中;而以明使神,则是“人而不天”,最终下落到人的机制中,逐于外物而不能自返,最终丧其真神*例如王雱云:“人神之所用,见独也;明之所用,见有也。见独则所以入于天,而见有则所以入于人。”(《南华真经新传》,方勇《庄子纂要》第六册,第810页)林自云:“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胜神。”(方勇《庄子纂要》第六册,第810页)另外,陶崇道说:“神者天也。”(方勇《庄子纂要》第六册,第812页);另一方面,神者本为天性自然之灵觉,因而为内,而明者依赖形之可见者而为之征验,故而为外*褚伯秀:“明谓形之可见者,必藉形中不可见者主之,欲动而动,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谓‘征’也。不平者,形形有贫富寿夭之殊,神之在人则一。以神观物,无有不平;以形观物,则不平矣。‘征’者,扣之而应,感之则通。若以不信视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无征,取征于神,以外求征于内,内重而外轻也。若以内求征于外,则‘其征也不征’;其征也不征,则‘其平也不平’矣。‘明者为使’,动用有限;‘神者征之’,静体无极。故曰‘明不胜神也’。”(《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102《列御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5页)陈深:“明,外也;神,内也。”(方勇《庄子纂要》第六册,第812页)陆西星:“神则天性自然之灵觉,有不可以丝毫知力与乎其间。‘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顾恃其所见,以外为功,不亦悲乎?’外,谓己之干慧黠识。”(《南华真经副墨》,第474页)。故而,神、明的路线,由于神、明之间彼此牵涉、互相蕴涵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以神主明的路线与以明使神的路线。
在《天下篇》所探讨的六家之学中,只有关尹、老聃一系的“澹然独与神明居”与庄子一系的“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与天地之道或神明的进路相应,从而与古之人的“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相应。墨子之学,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慎到之学虽然并非没有涉及到万物,*虽然墨家之学“不靡于万物”,宋钘、尹文之学“不饰于物”且“接万物以别囿为始”,彭蒙、田骈、慎到之学“趣物而不两”“泠汰于物”,“与物宛转”且“齐万物以为守”,可谓以不同形式皆涉及到“物”,但对物的涉及仍然是在人间的方内世界的视域内,物仍然是作为人的有用物而被思考,作为经营天下的政教事业之所及者而被思考,而没有上升到天地之道的本身。但却是在人间的礼法世界,是从利用厚生的政教事业而涉及到万物,而不是直接从天地之道的层次与物打交道,因而无法触及天地神明。惠施、公孙龙之学虽然撇开人间政教研究天地万物,却逐于万物而不反,强于物而弱于德,是对天地万物的对象化研究,它最终无法契会天地神明,《天下篇》所谓“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可以用来概括惠施公孙龙之学。这一系的学问,与关尹老聃之学、庄子之学的差异就在于它是以明使神的进路,因而其对天地万物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下落到人的机制中,是以人的认识的逻辑来结构天地万物,从而使得神明隐遁;而关尹、老聃与庄子却是以神主明的进路,其对天地万物的研究上升到天地之道,既是对人的存在维度的提升,也是对天地之道的接近。
与神明的自然进路比较而言,圣与王的进路相应于人道:“万物之中,最灵秀者人。人之德盛者莫如圣,人之功大者,莫如王……举圣王者,以表人道。”[7]756人道有两大领域:一是教化领域,相应于“圣”;一是政治领域,相应于“王”。因而,这两大领域又名之为教统和治统,圣的进路是教统的进路,而王的进路则是治统的进路。张文江所谓的社会与政治,实际就是教统与治统分别针对的领域。《荀子·解蔽》对圣、王做出了经典的区分:“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圣的进路的实质是尽伦,即充分地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能性,它着眼的是人性的提升;王的进路是的实质是尽制,即为人的行为设立可以遵循的制度,它给出的是人的公共活动的最低限度的规则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制度。圣、王的进路不同点在于:一方面,圣的进路是提升性的、引导性的,而王的进路是限制性的、防御性的,前者着眼的是人性的上行路线,后者立基的是人性的下行路线;另一方面,正如张文江曾经指出的那样,王者的进路是由外而内,通过影响人的外在行为而转化内在心性,圣的进路则是由内而外,通过提升人的人性而转化人的外在行为。[8]
圣与王所对应的教与治这两种不同进路,彼此也有深刻的牵涉关系。但在总体上,《礼记·学记》对于二者的结构有一个回答,这就是所谓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以教为里,则治为表;以圣为内,则以王为外,这就是《天下篇》所谓的“内圣外王”,它代表了中国思想对治教结构的终极回答。这一回答不同于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1884-1976)总结的西方治教结构的三种形态:政教合一、政教分离、政教协定。布尔特曼所总结是西方文明中曾经出现的治教关系的三种历史形态,但他并非给出治教关系的最高可能或终极形态。《天下篇》对治教关系的回答,显示了最佳最优的“政治体”在其理想性乃是一所“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自天子至庶民皆以修身为本的“大学”,或如梁漱溟所云,中国思想所理解的国家在最终意义上是一所大学校。*梁漱溟说:中国式的人生,其特点是向里用力,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支持了这一点,使得“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成为对这一政治-社会构造之理想的恰当描述。《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216页。钱穆阐发的“学治”的观念,*钱穆云:“今就中国传统政制与学术文化事业相联系相融洽之要义,再扼要言之。一者在有考试之制度,专为拔取学人使之从政,故其政府僚吏乃全为学者。此种政制可名为学人政治,或简称为‘学治’,以别于贵族政治或富人政治。”“‘学治’之精义,在能以学术指导政治,运用政治,以达学术之所祈向……学术者,乃政治之灵魂而非工具,惟其如此,乃有当于学治之精义。”钱穆《道统与治统》,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政学私言》上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87-88页。就与中国文化的这一理想密切相关。
圣王的进路虽然从人道的政教领域出发,但在它终极的境地,也必须通达天地之神明。“聖”字甲骨文未见,金文中或省作耳/口,是会意字,意谓声入心通,入于耳而出于口。《风俗通》提供了一个文献上的根据:“聖者,聲也,言闻声知情,故曰聖。”*按顾颉刚所引《风俗通》之言乃《广韵》四十五叙“圣”字引。《太平御览》“人事部”四十二“叙圣”所引应劭《风俗通》为:“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调畅万物。”《韩诗外传》卷五说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并引《传》说:“闻其末而达其本者,圣也。”这是说从耳闻的具体事物而通晓其根本,就是“圣”。《白虎通·圣人》对圣人的解释,特别强调身体的不同官觉的彼此通达,以及由此身体自身的通达而导致的与万物的通达:“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徳,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自身的通达以及与万物的通达,使得圣人能测万物之情性,能在其存在中给出或接纳万物之情性。“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戴礼记》卷一)《哀公问五仪》《荀子·哀公》:“哀公问:‘敢问何如斯可大圣矣?’孔子曰:‘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所以理然否取舍也。’”可见,圣不仅仅贯通人与人,而且贯通人与物,以至于与天地合德。
《说文解字》对“王”的理解:“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古文王。李阳冰曰:‘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这个理解受到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启发,后者云:“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者,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之?”
由上对圣王的理解,均可看出贯通天地或通达天地之德构成圣王的品质。扬雄《法言·修身》云:“或问‘众人’。曰:‘富贵生。’‘贤者’?曰:‘义。’‘圣人’?曰:‘神。’观乎贤人,则见众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从天地而见圣人,则圣人之德实通达于天地之德。《庄子·知北游》明确地指出圣人与天地的关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所谓的“大圣不作,观于天地”实与扬雄所谓的“观乎天地,则见圣人”,异曲同工。王者与天地的关系,《庄子·天道》亦明确指出:“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综合二者可以说,圣王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其体现了天地之德,此正如顾实所云:“中国群经百家言,大本大宗,无不取象于天地神明之德,以成其内圣外王之业。”[9]4在《天下篇》的脉络里,圣、王实为道术的承担主体,而神、明则为圣王所以能够生成、可以承担道术的根据。*陶崇道的理解:“道术,大道之术,无在无不在这也。道术成于谁?此皆天上神明降下,生出圣王来所成者,是一直语。”见方勇《庄子纂要》第六册,第827页。因而,圣、王与神、明之间具有某种承接关系,圣承接的是神,王承接的是明。谭戒甫说:“圣王分承神明,亦即分承道术;生成亦即分承降出耳。”[10]刘凤苞甚至断定:“圣即神,王即明。”[6]776这当然不是在神与圣、明与王之间画上等号,而是说圣必须就着神来达成,王必须就着明来理解。王弼指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28《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5页。这就是说,圣王所以能够以其生命体现天地之德,正在于他茂于众人的神明。神明既是天地之精神,又是人之精粹,是人所以贯通天地的根本。人以其神明与天地之神明相接,是以有圣王之道。
从神(天道)、明(地道)、圣(教统)、王(治统)去探讨以“一”为品格的道术,皆为可能之进路,但从任何一者出发,都必须通达其他三者,并会通、协调、平衡,而后有四者之和谐,由此而有“一”。事实上,四者构成一个文明的四大板块,神、明意味着天地万物在其中自行运作的自然境域,圣、王构成人道领域,圣、王之道分别意味着着眼于人性改良、以引导性为指向的教化系统和着眼于秩序、以防御性为指向的政治系统。换言之,不管是从天道(神)出发,还是从地道(明)出发,不论是从教统(圣)开始,还是从治统(王)开始,只要局限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就无法摆脱下降到方术的命运,而道术则开放在对天道、地道、教统、治统四者的整合中。治统与教统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干,而天道与地道构成了自然的宇宙。如果仅仅研究天道与地道,而不能通之于教化与政治,那么正如扬雄《法言·君子》所谓:“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伎。”也就是说,研究自然领域而失去了政教关怀,而只是出于纯粹的兴趣,就会下降为纯粹的技术(技术又称方技)而远离道术,惠施、公孙龙之学就是这样。反过来,如果人类的政教不能与天地之道配合、协调,则此政教文明即为一病态的没有生命力的文明。比如现代政教体制,在一定意义上是反神明的,它不断增厚的人为的观念与价值,构成了对神明所寄身的自然运作方式的压力。也就是说,基于精神性与理性的社会-政治建制,通过对人的生物性的压迫与扭曲,因而形成了现代个人的神经官能症状,*就人身而言,神明呈现的是生命中那种自然而然不知其然的运作机制,比如脏腑与经络的自发运作与彼此配合,皆由神明主导。生物钟的运作机制也是天地之神明的显现,生物钟相应于主观内在时间,动物植物以此了解与自身存在相应的一天中时间之变化、一年中之时节,以便预期环境的日常变化与光照、温度、雨量、湿度的年度变化,从而让自己在适当时地迁徙、冬眠、交配、开花、生殖等等,最终实现其生活周期与地球公转之间的同步,以达与物理时空之和谐。(参见罗素·福斯特、里昂·克赖茨曼《生命的季节:生生不息背后的生物节律》,严军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这与政治-社会中基于主体的目的性活动而发生作用的机制具有不同的性质。人与其他存在者不同,他不仅具有意志、欲望、情感与理性等主体结构,而且能借助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例如科学、宗教、艺术与哲学等等诸种活动,超越了神明运作的自发节律,而获得了向着更高更复杂的时空数量级不断开放自身的可能性。但这意味着他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具有遮蔽神明机制的可能性。这一症状实由文明的病态机制所生发而最终又要个人来承受它的后果。故而道术的通达其实要求在天道、地道与治统(王道)、教统(圣道)之间加以连接,四者构成有机的“一”体。钟泰云:“天道、地道、人道皆原于一。以见人与天地无二道也。”[7]756故而陆贾《新语》卷上《道基》:“《传》曰:天地生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道术的生成意味着将由一本而生成的神、明、圣、王重新整合为一的方式。
三、生命存在类型与政教的人性基础*
神、明、圣、王不同的进路,构成通达“一”(道术)的不同方式,这种不同的进路与通达“一”的不同方式,实际上刻画了人的基本类型,而对人的不同类型的理解本身又是政教文明自我奠基的核心。《天下篇》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内将人性予以类型化,分为七种:“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正如顾实所云,其“所记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万民之七等人,具见上世政府社会之运行组织,相维相系,大纲尽是矣。”[9]4对七种人的刻画在《天下篇》的脉络中并非可有可无的,而是意在揭示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注家皆以为此不过呆叙七等人而已,以致上下文气阻融难通。不悟此正叙内圣外王经世之方术,并非呆叙七等人。苟明乎此,则上下文气,自无不贯穿者矣。”[9]6张文江以为对人的类型化刻画,是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8]但这一刻画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社会阶层的范畴,与其说它是在社会的架构下还不如说是在天地之间的架构下,对人的所有可能类型的结构性分析,一如陈柱《阐庄中》所云:“庄子之意,盖以此七等人别天下人之品类,以谓道无乎不在,而为人之等不同,则亦各道其道而已。”[11]
(一)天人、神人、至人
《天下篇》对七种人的刻画有着谨严的“书法”:天人、神人、至人的书法相同,皆以“不离于”+“谓之”构成,从而与圣人、君子皆以“以…为…”+“谓之”有所区别,也与百官、万民皆以“以…为…”不同。*张文江最先注意到七等人的语法问题:“进一步分析三、二、二的分类,可以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三、二和二,或者说前五后二,其语言标志为结束于‘谓之某某’。一种是三和二、二,或者说前三后四,其语言标志为开始于‘以某为某’。在七种人中,三种人所占的位置最高,追溯本源,超然于世,其语言标志为‘不离于某’。由此引申,圣人和君子居于中间阶层,从事于思想文化,观其结束于‘谓之某某’当属上,然而开始于‘以某为某’当属下。而殿后的百官和民,切实于日常生活,其象分散于人群,开始于‘以’,结束于‘以’。整段最终以‘民之理也’,对应于开篇的‘古之道术’,这也就是贯通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和‘理’。”见其《〈庄子·天下篇〉讲记》 ,《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第105-106页。表述的方式本身就内蕴着将七等人类型化的方式,而且七种人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的组合。天人、神人、至人作为一种类型,它分别不离于“一”的“宗”“精”“真”,而被谓之为“天人”“神人”“至人”,就它们自身而言,并无天人、神人、至人的自谓。他们生活在“一”中,实享“一”而忘“一”,不知有“一”,“一”不再以名而立,他们的生活本身成了“一”的流行发用,因而他们不追求“一”,“一”并非有意寻求的对象。三类人完全生活在“天的机制”之中,生物性与精神性、感性与理性如同“天乐”那样自然而然地处在高度和谐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与天和者”。*《庄子·天道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张文江指出:“相应神明的三种人,是天人、神人、至人。”“相应于神明的三种人,和‘一’大体不隔,就在‘一’之中。”[8]“天人”相应于“天”,按照《庄子·天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的叙述,则“天”在“道”“德”之先,并为“道”与“德”之根源,故董仲舒《天人三策·第三策》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之所宗者为“天”,是故吕惠卿有谓:“古之语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则天者所宗也,故不离其宗,谓之天人。”[12]585神人的特点是“不离于精”,精意味着“一”之精微、精粹,由天地之精粹而有神妙之用,是故顾实谓“精亦神也,《知北游篇》谓‘观于天地,神明至精,与物百化’,是也。”[9]13神人因其能神妙万物而不见其功,不知其所以如此,故被谓为“神人”。陆西星云:“不离于精者,凝聚精神,万古不朽,能感天动地,能贯金石,如鬼神然,是则所谓人而神者,故谓之神人。”[4]477至人的特点是“不离于真”,这意味着“真宰内充”而不可以已。不离于真不等同无妄之真、无假之真,因为无妄、无假已经意味着与妄、假的对立,而“至人”则超越了这一对立。天人、神人、至人是《礼记·中庸》所谓的“自诚而明”者,而不能理解为“自明而诚”者。
天人、神人与真人的书法,以“不离于…”而不以“以…为…”来刻画,这表明三类人均超出了“有以为”所表述的“人的机制”,而直接成为“无以为”所表述的“天的机制”之呈现。《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以……为”发生在“人的机制”中,其所刻画的人,不免有意,其于物也不免有相,其所行也因此不免有迹。而由“不离其(宗+精+真)”,呈现的“天的机制”,无意、无相,且无迹。刻画三类人的“谓之”,*“谓之”不同于“之谓”,它意味着“A被C称作B”、“A被C看作B”,但B并不是出于A的自身规定,而是出于称作、看作的主体C的认定。参见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第二章第一节“谓之与之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乃是外在的命名,不是出于其自身的规定,至于其本身,完全是“无名人”。*《庄子·应帝王》有“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一段,无名人与天根不期而遇,绝非偶然。因为无名人“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又,《应帝王》蒲衣子谓泰氏:“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天道篇》老聃曰:“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皆相应于无名人之相。而天人、神人、至人也是无名人。天人、神人、至人(甚至圣人、君子)其名出于他人的命名,而非其本有。谓之而有,则其区分,并不能尽其实际,而只是出于理解的方便。*但圣人、君子又与三种人不同,有“以……为”的书法,则其所以为君子、圣人,有以之自励,修而至之。“不离其(宗、精、真)”中的“其”,可以理解为神、明、圣、王皆原于“一”的“一”。这三种人是“无翼飞”者、无迹行者,只见其效而不见其功,是以其对他人而言,为“天”、为“神”、为“至”,但其所造之境,由何而来则不可得而述。
(二)圣人
第四种人——圣人——的“书法”,不再以“不离于……”,而以“以…为…”来刻画,而“以…为…”反显出可行之方,因而其所彰显的是“可道之道”。或者说,天人、神人、至人不可由学而至,只是在圣人之境,继续上达,圣而不可知谓之神人,圣而至于其极谓之至人,圣而纯乎天而无乎人谓之天人。是故刘凤苞云:“‘为’字是圣人实际,若止说上三层,则无从著手,恐落空虚也。上三层是圣人顶上圆光,下一层乃显出庄严实相。”[6]778《天下篇》以“宗”“本”“门”三者彰显的是圣人之道的着手处,是成为圣人的道路,因而圣人可以由学而入。
对圣人的刻画首先用了三个概念:“天”“道”“德”。这与《老子》二十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天者同于天。”“天”“道”“德”三者并举,且三者皆系自然之物,于人须以无为法接引之,以使其自行来到自身。但在圣人这里,这一自己来到自身又是在“以…为…”的架构下发生的。这一点与“天人”“神人”“至人”有所不同。“以…为…”是圣人的下降,下降到君子、百官、民的行列,这就叫做“与人与徒”,于是与天人、神人、至人的无意无相无迹因而也没有下手处相比,圣人则有了“宗”“本”“门”,换言之有了可以切实遵行的道路。“以…为…”传达圣人所行的是“有为法”,此与“天人”“神人”“至人”那里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圣人的“以…为…”结构却又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其所为者,不过是让“道”“德”“天”自行来到自身,故而其有为本身即是对无为的接纳。以“作为”的方式去抵达“无为”,以“无为”的方式去“为”,这样,圣人以其性之德与天之德合一。圣人以其“天”“道”“德”分别承接“天人”“神人”“至人”,是故吕惠卿云:“圣人者,以天为宗,则天人也;以德为本,则神人也;以道为门,则至人也。兼此三者,而兆于变化,是为圣人而已。此神之降而为圣也。”“由圣人而上,与天同者也。”[12]585这样看来,“圣人”既可以视为与“天人”“神人”“至人”并列的一种人,但同时又是三种人之集大成者,至少“圣人”可上通于三种人。“圣人”的“宗”“本”“门”似乎有意、有相、有迹,但由于其所“宗”“本”“门”者是“天”“德”“道”,因而又恰恰保持了与天人、神人、至人的连续性,可以跻身于三种人的行列,这就叫做“与天为徒”。由此,圣人是“与天为徒”和“与人为徒”的统一。“与天为徒”与“与人为徒”的区分见《庄子·人间世》:“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然而“圣人”既“与天为徒”,由此而与“天人”“神人”“至人”归为一类,但同时又“与人为徒”,因而与后三种人(“君子”“百官”“万民”),可归为一类。这样,圣人既可上达于前三者,又可下通于后三者,但正因如此,圣人最终既有别于前三种人,又有别于后三种人。
对“圣人”的刻画的另一个关键语词是“兆于变化”。由于对“兆”的理解不同,故而“兆于变化”可以有三种解释:其一,《经典释文》以为“兆”本或作“逃”,逃即避,兆于变化,即顾实所谓“超离乎穷通死生之变化”。逃于变化,即“化化者不化”之意。其二,兆为征兆,预知吉凶,隋代萧吉《五行大义》五引“兆”作“明”,兆于变化,即“明于变化”。其三,兆于变化,即《天运篇》所谓的“与化为人”,或郭象所谓的“与化为体”。*见陈赟《从“无体之体”到“与化为体”——船山庄子学的本体与主体》,《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第三种含义无疑更具有思想的诠释潜能。《吕氏春秋·下贤篇》云:“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其与《天下篇》出于同一机杼。[13]1293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即观于机兆,唯变所适,随时而中,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它刻画的是圣人在方之内而不囿于方,以圆行方,以方行圆,因而与天相通。圣人的“兆于变化”,与前文的“无乎不在”,后文的“其运无乎不在”构成深层的对应,显出圣人对于“以…为…”架构所显现的“人的机制”的超越。钟泰云:“与化为人,即与天为人。而不言天而言化者,化则兼天与运二义而有之。天道之活泼泼地,于是全盘托出。”[7]308“兆于变化”也是圣人成为七等人的中枢之关键,顾实业已指出:圣人上通于天人、神人、至人,下通于君子,更下而又以齿百官、理万民。[9]15
(三)君子
“君子”的“书法”与“圣人”同,皆由“以…为…”+“谓之”构成。这是由于“圣人”与“君子”为一路,是“教统”(对应于“神明圣王”中的“圣”)的承担主体;二者没有形式的差异,却有内容的不同,即彰显圣人的人格内容的关键词是“天”“道”“德”以及“变化”,刻画君子的却是“仁义礼乐”: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钟泰指出:“圣人之后,继之以君子者,君子者,圣王之佐。非仁无以惠民,故曰以仁为恩;非义无以治民,故曰以义为理。非礼无以教民,故曰以礼为行;非乐无以和民,故曰以乐为和。而又曰熏然慈仁者,仁义礼乐,仁为之本。临民为治,仁尤其要也。以不忍之心,行太和之治,如南风之化物,故曰熏然。”[7]308无疑,构成君子人格的关键是仁义礼乐,尤以仁为四者之统摄。*《庄子·骈拇》:“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从这方面来看,这里恰恰显示了君子与仁义的内在关联。
圣人与君子之别关键在于道德与仁义礼乐的区分。仁义礼乐落实到君臣、父子、贵贱、名分、上下等政治-社会的秩序中,故而以仁义礼乐为教为学者,特别重视人伦,甚至大有以人伦为政教之全部或核心。比如礼学大师凌廷堪(1757-1809)说:“夫其所谓教者,礼也,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经释例》卷首《复礼上》,《凌廷堪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5页。人伦本义为人之为人的类性规定,但对于君子而言,“人伦”的这一规定被定格在“人间”(人与人的“之间”)的地基上,*正如顾炎武所云:彝伦与人伦不同,彝伦可以包含人伦。“‘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彝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5页。因而人在这里被视为具体的角色或关系的体现,例如人成为父亲、儿子、兄长、弟弟、君臣、朋友等等人伦角色的总和。成为一个人,于是就被理解为尽自己的角色所规定的“名分”及其相应的义务或责任,而礼恰恰将这种来自社会—政治的“名分”固定下来,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
可以说,对于君子之学而言,其精神在于仁,即在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生活场域,相与成就人之所以为人者;其道路在于礼,“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彰显了君子与礼的关联。“礼”虽有“天之经”的向度,但更有“地之义”的层次,它意味着因顺大地的风土性而自发产生的习俗制作的礼仪,*《慎子》云:“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有长幼之礼,无勇怯之礼;有亲疏之礼,无爱憎之礼也。”俗,《说文》解释为习,段玉裁注云:“习者,数飞也,引伸之凡相效谓之习。《周礼大宰》:‘礼俗以驭其民。’注云:‘礼俗,昏姻丧纪,旧所行也。’《大司徒》:‘以俗敎安。’注:‘俗谓土地所生习也。’《曲礼》:‘入国而问俗。’注:‘俗谓常所行与所恶也。’《汉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故而当归属于政治-社会的方内之道。*《庄子·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因而经由仁义礼乐所彰显的人性理解,并不是天与之人性的全部,而且对于圣人及以上三种人而言,这一对人性的理解却仍然是不充分的。《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观念,《礼记·礼运》则有基于道德的大同与基于礼义的小康之辨,这个分辨将道德与仁义礼乐所处的不同维度勾勒出来。仁义礼乐仍然是政治-社会的方内之道,因而它最终归属于“人的机制”,但道德则归属于“天的机制”。*《庄子·骈拇》:“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又《马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刘凤苞云:“圣人、君子,皆有功用可见,但圣人不落边际,君子仅得其绪余,是以圣人仍合乎天,君子只尽乎人而已。”[6]778对庄子而言,“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庄子·在宥》)*《天地篇》云:“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道、德出于自然,就其根源而言,无不本于天地之神明,但它在人这里则必须经过后获性的努力予以开发,而后方能彰显。就此而言,这种意义上的“道德”绝不是现代汉语中的道德,更不是morality或virtue的对等义,《庄子·庚桑楚》说:“道者,德之钦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这就是说,德之所尊所仰者是道,也即德可兼于道,而道则兼于天。就先天的造化过程而言,由道而有德,由德而有生,由生而有性,由性之动而有为,由为而有伪,由伪而有失其性。德是天德、天光所发者,对庄子而言,德一落形质则谓之性,故言性者生之质,生之谓性,性与生本来相通。性之动出于自然是“为”,出于人为则是“伪”,“伪”意味着脱离了“天的机制”而下降到“人的机制”。就后天学习过程而论,“动以不得已之谓德”,“不得已”意味着在“为”(性之动)中减损“人的机制”(伪),它是为“无为之天”让出空间,由性而德,由德而道,由道而天,《天地篇》所谓“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也”[7]545—547。
因而,就从庄子意义上的“道”“德”高度来看,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悉皆为天所赋予人的人性之内容的表现——即所命之性,但君子却在大体(精神性与理性)与小体(生物性与感性)的对立中确证人的人性,即将精神性、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特性——性,而将人的生物性作为人与禽兽的共同特征(命)而视之为对人之为人之性的否定。这种在“性”“命”之间的选择是通过“谓之”(主观性的看作)而实现的。《孟子·尽心下》云:“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味、色、声、臭就其本身而言未尝不是人之性,但“君子”(当然不是“圣人”,在圣人那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却“谓之”为“命”,而不“谓之”为“性”;一如仁、义、礼、智就其本身而言,与味、色、声、臭一样皆为天之命,但君子却“谓之”为“性”,而不“谓之”为“命”。故而对于君子而言,人性永远是人之所以别于动物或禽兽的特征,这种特征只有通过减去人的生物性或感性才能达成。这就将生物性与感性确证为“非人”者,而将人性确立为精神性、理性,而其所谓的人性因此而具有反自然、与生物性相对立的特性。本来天赋于人的禀赋才情,皆能得以畅快淋漓的发挥,充分施展,是道德的内在要求;但在君子那里,道德被下降为伦常所规定的政治-社会性的规范,人的才、情从性中被分离出来,于是政治-社会所赋予的规则、条理、秩序、规范,被视为道德性本身,而后者往往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设定。比如平等、人权、消极自由等等,只是人道(政治与社会)架构下的秩序原理,放乎自然天道的架构下,则就会失去其意义。正如教育在道德的意义上是个人所得于天的禀赋才情以及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充分实现,是完全必须由个人自己来承担的事业;但在政治-社会的架构下,它往往被降低为抵达上述事业的条件,稳定与公正等等基于社会-政治的架构本身而产生的问题却占据了教育体制的全部,而人之才情禀赋等的实现,却从这种体制的关注中被移除。
因此,庄子看到,一旦道德被政治-社会性的结构所凝固化,那么它实际上就只能下降为抵达道德的条件,而不能被视为道德的本身,而道德只能在自得的意义上获得,道德的获得只能是它自身,而不可能通过它的条件的改善而来到;而且每一个人的获得的方式与内容也都因为其自然禀赋而各不相同。故而陆西星云:“若夫以仁义礼乐为事而熏染纳天下于慈仁之中,则谓之曰君子。盖仁义礼乐皆失道而下之事,贤人君子治世之法无过于此。”[4]477君子之学的特点在于守住人道(人之所以为人)的界限,而这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出于人道的规定,而非天道的规定。正是基于人道,君子之学在大体与小体之间划出分野,由形(小体)而上,不断突破小体的局限,这就是内在于君子之学的形而上冲动,正是这种冲动规定了“君子不器”“下学而上达”的品格。*“下学而上达”即所谓立足于学习过程的上升之路是针对万民、百官与君子的。刘小枫注意到:论语所谓的“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皇侃解释:“上达者,达于仁义;下达谓达于财利。”还是与《天下篇》相通的。《后汉书·张衡传》:“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有云为者也。”这些都体现了以仁义礼乐刻画君子的品质的说法。刘小枫《颠覆天下篇——熊十力与〈庄子·天下篇〉》,《中国文化》第34期。可见,君子之学成立的基础是人禽之辨,人禽之辨的核心是区分大小体。*《孟子·告子上》:“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由此而有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通过“属”与“种差”方式获得的人与动物相异的本性,作为人性;因而对于君子之学而言,大体与小体的张力始终存在,至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则并非君子之境所能涵盖,它应归于唯圣人才能抵达的“践形”。君子的生命彰显的理性或精神性,后者区别于人身体上与动物性、植物性相通的“本能”。对于君子,人的本能是被接受下来的,是被给予的,而不是功夫修养变化的对象,但对于圣人、神人、至人、天人等,即便是所谓的本能,也可以变为功夫的成就。例如《庄子》所呈现的至人之寝无梦、觉无忧、息之深,就是通常状况下被人们称为“本能”的地方也变成了人自己的成就。而君子之学所理解的人性就被归结为精神性与理性,后者成为尽性的内容。*《庄子·天道篇》:“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可以看出,对于仁义礼乐的超越,而直与道德为体,乃是至人(其实还有神人、天人)的特点。君子“尽性”却不能“至于命”,圣人则能“至于命”。君子之尽人性,犹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以前事,圣人之“至于命”,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后事。尽性,即尽人之所以为人者,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注意这里的主体是“君子”而不是“圣人”。故而当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时,他所说的主体也应为君子而非圣人。是典型的为己之学,它以安守在被政治-社会所结构的人的分位之内,素其位而行为特征。正因如此,君子的尽性只是尽己之性,而不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圣人由于至于命,故而其尽己之性,同时也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换言之,在君子那里,由于人性被视为属加种差所获得的与他者的相异性,因而己性、人性、物性是不同且不通的,然而在圣人那里,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一样成为人所以为人的特征,故而他经由“至于命”而所抵达的人性概念,触及到人性与物性成为它自身的总根源——天道。故而上文所谓“圣人仍合乎天,君子只尽乎人”的确显示了圣人与君子的分野。
(四)百官
如果说刻画君子的是“仁义礼乐”,那么百官则是“法名参稽”。《天下篇》如是叙述百官:“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正如钟泰所指出的那样,*《庄子·天道篇》:“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由此,钟泰指出:“明道德以上为圣人,明仁义以上者为君子,明分守形名以下则为百官。”见《庄子发微》,第757-758页。君子是贤者而百官是能者,君子所守者为(人)道,百官所守者为法。如《荀子·君道篇》云:“君子守道,官人守法。”君子以“教”化民,其所依在礼;百官以“治”制民,其所依在法。形名法数,百官守之,陈其数而未必知其义,循法而不违之而已;*《荀子·荣辱篇》:“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王闿运亦说:“此即事为治,不求有道,但为其法。法不出奇偶参倍,尚不必至五而数穷矣。自周衰用之,至今百官以治天下,但有差贤耳,不能相绝也。”见王叔岷《庄子校诠》卷五《天下篇》,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95页。但君子则必须知其义而后能行其教化。百官既为官守,则各有分职,分官设职,可使百官各守其业,不必通达于其分守之外,是以百官的职守反而强化了政治-社会的方内体制,但君子之教,则以通达、引导为尚,虽然以礼化民,但未尝不具有超越方内体制的机杼。
《荀子·富国篇》谓:“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百官以法为分,以客观性的法度而不以主观性的人为根据分别人的等级尊卑上下之序,分配物品财产等。《管子·七法》谓:“尺寸也,规矩也,绳墨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是客观性的尺度、标准、规范。《管子·明法》:“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常之数,不可差以长短。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以法为分,意在避免主观的任性,如果说礼制重在对差异的开放,因名位的不同而以相应的礼数固化这种名位,那么法则以其同质化、均匀化提供一致性且更方便操作的准绳。《慎子·威德篇》:“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群书治要》引《慎子》:“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赐,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这就是说,即便是以“抓阄儿”,即抽签的方式分发物品,得到与得不到都不会抱怨,因为得与不得一皆系之于法,而无关于人,因此这里没有哪个人可以成为感恩与怨恨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法本身超越了个人的情感、意志与欲望,因而也杜绝了人的私心,而呈现为以同样方式向着每一个人开放自身的客观性。《尹文子·大道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则顽嚣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能鄙齐功,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韩非子·制分篇》说:“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由此,法避免人的主观随意性,因而也是任性的欲望与意志的防御工具与解毒剂,是形成客观性秩序不可或缺的规范。
百官,是佐王者以治民的人,但作为官僚阶层或科层制的官吏,他们彼此之间亦不得不按照一、二、三、四的品位次第序官颁爵,以此厘定百官之间的等第与层级,以使得官僚集团内部有森严的等级秩序,从而形成逐层逐级性的支配与管理的机制,任何一种官吏的名位都被他的层级限定,因而必须在言行等方面遵循被规定的分位规定。《荀子·王制篇》:“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这里所讲的“制”“度”“数”“等宜”,均是对百官、君子的规定。这里似乎是对礼制的刻画,但只要达到规定的条件,就可以有相应的“等”“宜”,故而礼本身就包含法的向度。只不过,“礼”与“法”分别对应于圣人之教、王者之治,其执守的主体分别是君子与百官,其施对的对象也有所不同。《荀子·富国篇》:“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西周王制精神相应。
从君子之仁义礼乐到百官之刑名法术,分承圣者之教与王者之治。君子基于人的由形而上的冲动予以启发、引导,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为目标;治则是以标准、尺度防御人性的下陷、堕落,百官成为法度的执行者。《礼记·学记》对教(礼乐教化)与发而后所立之法的比较:“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针对已经发生的某些问题而立一法,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又由所立之法而滋生出新的问题,于是,又需要建立新法予以救治。如此环环相扣,在上者法度日益繁琐而在下者总有应对之方,但除弊与生弊之共生的机制,却根深蒂固于法之中。相比之下,礼之为教,虽然也无法根除上述除弊与生弊的共生机制,但它指向的是完整的人格之构建,此与法之因事而立不同;法之因事而立,故而其所制者毕竟有限,礼因人而制,故其所向者无穷,并为人的主动预留余地。礼可以弥漫贯通公私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法却注定只能施行于人与人交接的公共地带,如饮食穿衣、举手投足等等法所不至之地,皆可由礼为之节文。法之立,必依赖于执法者,方能保证法度的遵行;但礼之立虽也由刑担保,但最终却依赖于人之自觉之实行。故而礼、法分别针对既可由之又可知之者、但可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者。故而,对于那些礼不能用的阶层而言,法则是不得已的选项。*陈景元:“道不足则用法,法不足则用术,术不足则用权,权不足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反术,术反法,法反道,道则无为而自化也。”见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103《天下》,第1001页。
(五)民
无论是百官,还是君子,所治所教,皆指向“民”。民是七等人的末端,是治教的对象,但同时也是圣王见天必由之出发者。《天下篇》对民的刻画是:“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农、工、商之民各以其耕作、制作、经贸之业为其日用之常事,故而财货之积累、生息之繁衍、生存需要之满足为其意欲之所在,老弱孤寡皆能有养则为其所期待者,换言之,庶民谋求生计,以衣食为天。与君子、圣人及以上相比,庶民所关注者,更多为日用生活之满足,既无君子精神性的上达要求,也无圣人以上将生物性作为工夫之成就的企望,但同时也无因过度社会性-政治性的机制而催生的奢华欲望,因而其生活呈现出那种自发的贴近自然的淳朴性,因而在政治-社会的架构下,在君子、百官与民三个层级中,民可谓最接近“天”。民间(民与民之间)自发形成的各种行事的机制,内化为习俗、习惯、风气、传统,也是最接近“天”的,因而圣、王可从庶民及其生活中以见天道。但另一方面,庶民本身之所以需要被治理、被教化,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自然的朴素性之中,不能上升到文明的层次。虽然王者可以由民心、民情以见天道,但庶民对于天道的呈现却是日用而不知的,是偶然的遇合,而不是他们自身的成就。因此他们需要被治理、被教化。
四、圣人何以是人类政教文明之中枢*
(一)君子、百官、民何以无“人”之称
刘小枫注意到,前四种人格类型,天人、神人、至人、圣人中,皆有“人”字,而天、神、至、圣则是人达到的层次或类型,但君子、百官、万民三者无一用“人”之称。*刘小枫《颠覆天下篇——熊十力与〈庄子·天下篇〉》,《中国文化》第三十四期。的确,由“天人”“神人”“至人”“圣人”皆称名为“人”而言,四者可以归为一类。问题是:“君子”“百官”“民”为什么却无“人”之称?君子、百官、民生活在政治-社会的“方”域之内,在那里,人的自我确证是在“社会人”的彼此之间进行的。就人的自我确证而言,人只是在与人以外的其它存在者相对时,才具有将自身表述为人的可能性,而在社会-政治的架构下,人与人之间往往通过“我”“你”“他”的人称形式而得以相互定位,这种定位强化了自我的优先性,但这也恰恰说明,自我是在与他者的相互对照中交互构成的,这就是社会性向度对政治-社会中的人的自我理解的构成意义。人在这一向度下将人下降到我、你、他,或我们、你们、他们。人只有在超出人的存在时,因此也是超出社会-政治的架构时,才具有将自身表述为人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在天道的地基上,人才成为人,正如在天道的地基上,某一动物成为这一动物一样,因为只有天道才触及到某一存在者能够自己成为自己的根源。*“我是谁”的问题,是政治-社会中的人的问题;“人是什么”的问题,则是在天道层次上才能给出的问题。“人”在政治-社会的架构下不再可能享有天与的人性的全体,而是不能不简化为政治-社会建立的某种名位与角色的载体,所谓的“白马非马”所指代的正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个“军人”在残酷的战场上,只能作为“军人”而不是作为“人”来从事他的自我与他者的确证。这就发生了“军人非人”的现实,正如在病房中的病人也只是被作为“病人”而不是作为“人”被对待一样。
由此,“民”这一词语所表述的其实是一个政教社会中的阶层,其内涵与规定受限于社会与政治的结构性安排,因而“民”与“人”终有不同。同样,“百官”是技术官僚或科层制的官吏,属于国家机器的执行主体,由于被限定在某种功能与被动的分工中,其生活方式并不支持完整的人的品质的全面呈现。与此类似,“君子”与“人”的距离,恰恰在于其所谓的“人”被“仁”规定,即在人间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规定,而不由人与天的关系规定。因而君子所向往的“人”的品质,毋宁说受限于人类建构的政治-社会系统,而无与于天之所以与人的全部特性,而更多地是在自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大体(精神性、伦理性)等架构内打转的那些特征。这是一种吊诡,圣人以上的四种人,如前所述,超越了“人的机制”,其生命与生活成为“天的机制”之体现。恰恰因为对“人的机制”的超越,而使四者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君子、百官、庶民生活在“人的机制”,却无法抵达人的全体,而只是作为人的位格的某种政治-社会化了的“身位”或“名分”的载体。
(二)天人、神人、至人不愿亦无能担负圣、王之业
虽然天人、神人、真人与圣人一样,都是可以抵达天与人性之全体者,但三种人并不愿成为圣、王,以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而是以自己的完身养生为头等大事。刘凤苞说:“劈分七等人,做个榜样。天人、神人、至人,纯乎天,圣人则尽人以合天者也。老庄立言,往往超乎圣人以上,见得圣人虽以天为宗,尚在道德上著力,变化上用功,不若上三等人之浑然无迹、不见所为也。然圣人备道之全体,广大精微,仍是与天为一。”[6]779三种人关注的是如何以自己的生命体现内蕴生生之德的天道,后者并不以社会性-政治性为其主体内容,而以宇宙的精神、天地万物之神明为其品质。因而,三种人选择游于方外,生活在天地之一气而未始有物之处,一任天地万物之自然。对于自己之生物性与精神性皆能以无为而无不为方式达到贯通,更在生物性与通常无由下功夫的“本能”上有非同寻常的修为,其功力之深湛,直入无意识之域;其视人亦天地间一物,为天地之气机、生意所充盈。对三种人而言,圣、王的生活方式总是无法避免因天人之间的张力而带来的紧张感,他们自己却宁愿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宁愿自隐于无名,远离尘嚣而遗世独立。在这个意义上,三种人不是生活在人际关系中的人。爱因斯坦就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不包含人际(人间)因素的事业,这样的事业本身就给人以神圣感。毋宁说,三种人生活的处所不是人与人之间,而是人与天之间,对他们而言,“人间世”(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社会的礼法所结构化了的“方内”之域,只能成为临时性的寄居之所,而不是自我确证的真正家园;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突破各种类型的“方术”的限制而直达道术本身。
因而,社会性并不是刻画三种人的恰当概念,三等人总是“世外”的高人,对在政治-社会的方内生活的人们而言,它们无疑是真正的“天外来客”,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客人,他们总是独来独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群”或社会性并不是三种人的生存规定。这三种人是完全意义的“天地人”,正如君子、百官与庶民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一样。司马迁对老聃的刻画是,“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可以视为三等人人生取向的例证。所谓的修“道德”,即不以仁义礼乐而以道德作为其学问的归宿;所谓“自隐无名”“莫知其所终”,意味着其所追求的并不在于政治-社会中人们的承认与认可,并不追求方内的人们所追求的声名、功利与权力,因而其在政治-社会所结构出来的“人间世”,自然是隐而不显的。
三种人虽然自隐于无名,但他们往往有非同寻常的道艺,如《庄子》中解牛数千而刀不伤的庖丁、“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斫轮高手轮扁,能够“即凡天下之事,目所接触,无不若为吾艺设者。必如是能会万物于一己,而后其艺乃能擅天下之奇,而莫之能及”[7]68,他们由技而道,因而能够会通天地万物于一艺之中,其艺也因此登峰造极,其人也与其艺一样往往抵达出神入化之境。通常所谓的“诗圣”“诗仙”“诗神”“画圣”“草圣”“书圣”“书神”“棋圣”等等,刻画的都是这种人,他们外师造化而内达心源,在天地万物的神明之德中成就其艺、成就其人,其所从事的道艺本身也成了对其天赋才情与潜能的最高开发。故而天人、神人、至人实际上就是天地之子、神明之友,而不屑屑于人事。政治-社会的规则与伦常,在他们看来并不是自我确证的方式,所谓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则必然是要将天地神明中的“一”在自己生命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为抵达了神明之德,因而他们能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庄子·庚桑楚》云“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虫能天”,而鸟兽皆可包含在“虫”中,故而这三种人愿意与鸟兽同群,因为对他们而言,不知有“人”,亦不知有“天”。《庄子·庚桑楚》:“夫复謵不馈而忘人,忘人,因以为天人矣。”
三种人与圣人、君子“鸟兽不可与同群”的人道选择有所不同。《论语·微子篇》记载,孔子面对作为隐者的长沮、桀溺,发出了如下的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最终选择了与被政治-社会中的方内人生活在一起。其与三种人相比,所瞩意者终有不同,其中缘由盖如《庄子·外物篇》所云:“圣人之所以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有必要区分圣人所体之“天”与天人、神人、至人所由之“天”的内涵。三种人与天为一,游于未始有物之处,与物为春,喜怒通四时;圣人之天虽然也指向这种内蕴在宇宙、天地、万物中的神明之德,但同时也关联着社会性。尽管在道术的层次看“人间世”,它永远无法摆脱“方术”的洞穴,但这种作为洞穴的“人间世”却是天下人的共同家园,因而也是圣人由天下以见天道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其修、齐、治、平的使命所在。三种人游走于方之外,而圣人却游于方内而通达方外。仁义礼法刑名度数对于方外的三种人来说,没有意义,但对圣人来说却有意义,这里有个天下的维度。对圣人而言,天上的真理一定呈现并落实为地上(天下)的真理,真理并不离开俗谛,道术一定开放在方术之中,因而圣人以其“兆于变化”将“道术”与“方术”打通,“道术”不能不下降到“方术”中。政治-社会的共同体,往往立足于其成员的“成心”与“成见”共同构筑的共同“意见”,这些“公共意见”虽然可能蔽于一曲而于大理,与“方术”有很深的纠葛关系,但它却是一个地方、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根基。圣人正因为超越了根基于地方与风土的公共成见,通达了道术,以至于完全可以跻身于前三种人的行列,但那并不构成圣人身位的全部,圣人总是“与化为体”,因而可以有不同的变身。正是他的这种变身,使得能够以超越方术、通达道术的方式而保护共同体的“集体成见”,而政治-社会的共同体的集体成见,只有在抵达其合理性边界、明了其见与其蔽之后,才能通过消解其蔽的方式而得以保存其见。是故不到圣人地位,公共的集体成见反而不能得以保护,而这种集体成见恰恰是政治-社会得以立身的基础。因而圣人虽然如同三种人那样,同样超越了政治-社会这一方术性的结构,但却成为人间世的真正守护者。因而仅仅以天人、神人、至人三种人的集大成来表述圣人虽然是对的,但仍然不充分,用七种人的贯通与变化,来理解圣人,才是最为充分的。
一旦以圣人为对照,就会发现天人、神人、至人的限制。虽然在个人的修身上,他们抵达了七等人的最上位序,但三种人所追求的是天爵,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通达于天地万物,但未必达于人间社会。事实上,三种人往往隐身于社会中,成为政治-社会中的隐者。他们可以是民,也可以是百官,但却是客居在庶民与百官之位,随时可以弃之如敝履。他们不太愿意也不太可能成为王者,他们坚定的信念如《庄子·让王》所云:“道之真以修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这样的见识,虽然远远超出了世俗的士君子与百官,但毕竟在身与国家、天下之间执著于精粗本末之分别,故而不能无意。*林希逸云:“绪余、土苴以治国家、天下,圣、贤之论也。庄子之言如此分别,人皆谓其以精粗分两截。其意只谓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与,方可以尽无为之治。但其言抑扬太过,而心实不然。‘绪余’、‘土苴’,只就‘余’字上生,犹云‘尘垢’、‘秕糠’。近世荆公之学真把做两截看了,以此施用多举‘绪余’、‘土苴’之语,所以朱文公深辩正之。”见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第914页。例如《天下篇》对老聃的评价,就有“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的表述,本与物、精与粗、有积与不足之间的分别,显然是老聃之学“未能至极”的原因。*《天下篇》叙述老聃之学,与其他数家有同样的书法。如,“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对墨家之学总体批评,又通过虽然小有肯定。“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同样,通过虽然表达了对宋鈃、尹文的批评之意。“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对彭蒙总体否定然后通过虽然略有肯定。对于老聃,“虽未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通过虽然也表达了肯定之中有批评的态度。但后人不察《天下篇》的书法,将“虽未至极”改为“可谓至极”。关于这一点,钟泰《庄子发微》已有检讨。这样看来,天人、神人、至人虽然可以理解君子、百官与庶民,并深察其所囿的方术,因而从方内超拔而出,直契天地精神;但惟独对于圣人虽然有所知,但却不能真正理解,而圣人却是唯一可以真正理解三者,也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七等人的人。如此说来,方外的三种人于圣王所承担的天下的事业,不仅是非其所愿,而且亦非其所能。三种人虽然在个人的生命中消解了生物性与精神性的对待以及由此而来的紧张,但对社会性与政治性却缺乏充分的重视,因而也无以肯定由天下以见天道的正面意义。
(三)君子、百官、民不可承担圣、王大业
后三种人(君子、百官与庶民)也不可以承担圣、王的大业,因为其不能通于天地,而最多达于社会,对于那些上通于天地神明之德而藏身于政治社会中的前三种人却不能认识与理解,遑论通达。君子与百官是政治-社会中的显者,二者与天人、神人、至人的隐者身份正好相反。隐者往往自埋于民,藏身于茫茫人海,隐的境界越高,则对方内身份的要求越低。相比之下,散落的民是隐者最方便的身份,因为它最不容易被关注。张文江说前三种人是渔和樵,[8]那是因为渔翁与樵叟是民中的特别者,二者生活在山水中,而山水自在于天地之间。因而渔樵之生活,是在天地、山水、万物中的自然生活,政治-社会的价值污染不会及身,故而二者成为隐者的象征。《桃花源记》《富春山居图》《渔樵问对》《渔樵闲话》等等,所勾勒的隐者,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支独特的担纲者,这是隐的一条线。中国文化的另一支担纲者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君子),这是显的一条线。前者在后世被命名为“道”,后者被称之为“儒”,二者共同构筑中国文明所建构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形态:进则“儒”之君子,“退”则道之渔樵,二者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标。但毕竟如《庄子·大宗师》所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君子受限于方内的礼法,其与天道缺乏直接的契会,这也正是君子无法理解天人、神人、至人的真正原因。君子、百官、庶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受缚于根基于大地的“方术”。
如果说,天人、神人、至人,不被政治-社会的架构所限制,因而生活在“方外”,“方外”并不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之外的地方,而是对方所呈现的“人的机制”的真正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天人、神人、至人并不能理解为某一政治-社会的不同阶层,但君子、百官与庶民则被政治-社会的机制固化为这样的不同阶层,他们也的确从社会-政治的价值来展开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证。因为所处的社会-政治的阶层不同,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追求。方内的人追求人爵,即社会上名声、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财富、权力等,政治上追求仁义礼法数度,由此而建立的政治只能是“礼尚往来”与相互承认的政治,它既是以秩序与安全的追求为指向,也是以洞穴(方内)中的人间价值的肯定为目的。相比之下,方外的人追求天爵,在个人存在上追求的是生活的品质,在政治上崇尚超越礼法数度的“道德”,故而与之相应的是那种没有统治的政治,不是“相濡以沫”而是“相忘于江湖”。
进一步分析,君子、百官与民各有其不同的追求,因此也要求相应的治理形式。《荀子·君子篇》:“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荀子·正论》:“荣辱之分,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成俗,万世不能易也。”这种不同,正是政治-社会得以形成不同阶层的根据,人间政治社会因为人们心性的不同而有其天然构成的组织形质,尊重这一组织形质的政治与社会不会采取现代大众民主政治所采用的如下方式,将个人化为国家与社会政策的单元,而将其化约为抹煞了层级与差异的“平均人”概念。政治-社会的不同阶层,虽然在其表面上根植于政治-社会的固化安排,但其实却根源于人的心性与禀赋的差异。君子、百官、庶民本身就有这种差异,加上政治-社会体制的固化作用,故而不能超越阶层本身结构出来的“视野”,这一视角其实就是一种“洞穴”,由此而不能超出自身的洞穴而达成对政治-社会在更高水平上的综观,即对七等人“如其所是”的观看,因而他们无法承担藏天下于天下的圣、王事业。
《史记》记载郦生之言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案《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据《史记索隐》,郦生之言出自管子,管仲曾云:“王者以民属天,民以食属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王者的事业其最深邃的根源,当然是对天的认识。但天有两个层面:一是“人之天”,人的以治教为主体的文明,说到底是“人之天”,文明乃是人类的自然,一如生物性本身是生物的自然那样;二是“天之天”,即内在于天地万物中的天道,一皆出于“天的机制”,没有任何主观性的人为意志与私的情欲参与其间。君子与百官对天的认识大概可以到达“人之天”,但却无法进入“天之天”,正如天人、神人、至人对天的认识,深入到“天之天”,但对“人之天”的认识却不充分一样。而圣、王的事业要求对“人之天”与“天之天”均有深刻的认识,惟其如此,方能将天下藏于天下。《庄子·达生》云:“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不厌其天,不忽于人,几乎以其真!”“人之天”毕竟无法超越“以…为…”的机制,“以民属天”“以食属天”“以民人为天”等等,都显示了这一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天道依然是人之主观上认取的所谓“天道”,它仍然是人道的一个部分,因而不能不与天地万物之神明失之交臂。在这种“人之天”的架构下,人的生物性不能不被剥夺内在于自身的意义,而在大体与小体的对立架构中,成为等待着注入价值的虚无容器,从而导致治教文明与天地自然的分离与冲突,由此而远离真正的“一”。同样,民以衣食为天,不但因为较少精神性而不能抵达作为“人之天”的治教文明,而且亦不能真正达到天地万物的神明之德。总体言之,君子、百官与庶民,虽然有务内与务外之别,虽然有“从其大体”与“从其小体”之异,但他们都是既在天之下,又在地-方之内,其所及所守者乃人与人之间之价值,其关注或在人之生物性要求,或在社会性价值之满足,而无法在两者之间达成“一”。
(四)唯有圣人可以承担圣、王事业
“一”对于圣、王的事业如此关键,以至于在《天下篇》的总体结构中,它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七种人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一”发生关系。张文江说:“七种人推究其根本皆原于‘一’,其间区别在哪儿呢?相应于神明的三种人,和‘一’大体不隔,就在‘一’之中。相应于圣王的圣人、君子二种人,也在‘一’之中,但试图寻找‘一’。还有百官和民二种人,尽管也在‘一’之中,但是不寻找‘一’,也不知道‘一’。”[8]这的确是见道之言,但应该指出,这是《天下篇》在讨论七种人与“一”的不同关系的“显”的一维,《天下篇》还有“隐”的一维,其关键在于从七种人的总体重新去探索圣人与“一”的关系。*当《大宗师》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时,它呈现了“一”的更复杂层次。天人、神人、至人实享“一”而不知有“一”,“一”就在他们的生命中,不再是渴慕追求的对象,“一”是无名的,三种人自身也是无名人。君子之学以大体与小体的分别为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一”在君子那里不是生命实享的过程,而是心志渴慕的对象,即便在一定意义上说君子也在“一”之中,但这里的“一”仍然是“以…为一”的“一”。百官与民自发地在“一”中,只是由于“一”的流行发用而被动地以偶然遇合的方式与“一”照面,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事实上,百官与民既不如同君子那样有志于“一”,也不知道什么是“一”。对圣人而言,“一”既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也内在于天下(政治-社会)之中,但其存在的状态不同,在天地万物之中的“一”是现成的,是神明之德的显现;在政治-社会中的“一”永远都是没有完成的,而是等待着去实现的,它是“一”本身开放给人的空隙,人必须通过这个空隙而进入“一”,并进一步去完成“一”。在这个意义上,“一”是那种等待着圣、王的到来而必须由圣王引领人们去实现的事业。这就是圣人为什么既然在“一”之中,然而仍然还会去寻求“一”的深层原因。“一”对于天人、神人、至人而言,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但他们的身体似乎完全为“天的机制”所充满。从君子、百官、民的立场来说,“一”在“天下”,在“地上”,在“人间”,但永远是美好的理想。然而对圣人而言,“一”既在天上也在地上,“一”就是将天、地、人贯通的方式。圣人是从天人、神人、至人那里带着天道的信息下降到君子、百官与民所置身的人间世界,是以圣人与王的出生都不断地被神话化,神话化的本质就是他不是从人间到人间,而是从人间之外来到人间。但人间之外并不是一个地方,将天道以及天人、神人、至人理解为来自一个地方,仍然是从大地来理解天,因而并不能真正达到天。圣人的“一”,恰恰显示了他上通天人、神人、至人,下通君子、百官、庶民,因而他既是在政治-社会中,又是在天地万物中,皆能在“一”之中。这恰恰是其可以承担藏天下于天下的事业的根本。
在七等人中,唯有圣人可以承担圣、王的事业。*圣与王的区别:圣者本于天,由天而通地;王者本于地,由地以通天。但王道与圣道不同,圣者不必王,因而王者除了德的要求之外,还有处上、处下、退居、进为之分。钟泰对帝道与圣道的区分,可以参见《庄子发微》,第284页。顾实云:“圣人为七等人之中枢,上通于天人、神人、至人,下通于君子,更下而又以齿百官、理万民。自非兆于变化者,谁能与之。”[9]15圣人即显即隐,即隐即显。圣人是藏身于天下的人,《礼记·礼运》:“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敎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藏身于政教生活中,使得礼乐刑政皆由天出,替天行道,因而圣人隐身于天下,不隐而隐,隐而不隐。圣人的藏身于“天下”,其实也就是藏身于“天”。《庄子·达生篇》谓:“圣人藏于天。”藏于天,也就是从“人的机制”中退却,进入“天的机制”中去,由此他虽然治理国家天下,但由于隐身于“天的机制”之中,为而不为,不为而为,相为于不相为,将能量的使用所不可避免的耗费转变为能量储藏,因而圣人可以瓦解在道之真以修身的能量收藏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量耗费之间的冲突,以至于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本身就变成了养生的方式。这就是圣人的极其高明而道其中庸。而方外的天人、神人、至人尚未能抵达这一高度。其前三种人与后三种人生活的区域分别是方外与方内,“方”的核心是人间的礼法,《孟子·万章上》说:“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与不得,曰有命。”一方面这是大君子孟子对孔子的刻画,另一方面这一刻画恰恰表明圣人在君子那里,天、道、德是隐身的,隐身在仁义礼乐之中,这就是其“兆于变化”之所在。在天人、神人、至人看来,圣人受制于礼,规规于礼,但他们却不知圣人以道、德、天联通于“天人”“神人”“至人”的“宗”“精”“真”,又以道、德、天提升君子的“仁”“义”“礼”“乐”。由此圣人在君子的“仁”“义”“礼”“乐”与天人-神人-至人的“宗”、“精”、“真”之间做了连接,所以仁、义、礼、乐在君子那里与在圣人那里是不同的,在君子那里,仁义礼乐是政治-社会的方内规矩,是大地上的真理;但在圣人这里,仁义礼乐却本于天、效于地、列于鬼神的。《礼记·礼运》云:“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昬、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圣、王贯通方内与方外,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即分别在教与制上为阶层的由下而上的流动分别提供心性与制度的支持,在七种阶层之间构筑秩序,使之各从其类、个得其所。最高层的天人与最底层的民,对圣王来说,是两种见天的方式,在天人那里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天”和“一”,在民那里发现天下人的“天”和“一”,前者引导由己而见“一”,后者启发由天下而见“一”。因而,在圣人那里,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的同一的,一方面向着天人、神人、至人上升,一方面则是向着君子、百官、万民下降。这两条路均是圣人见天地、见众生的方式。圣人学于众人,在民视中见天视,在民听中见天听,这是见政治-社会的“天”;学于天人、神人、至人,这是见神明之“天”。惟其如此,而后能将政治-社会之“天”与天地万物中的神明之天会而通之为“一”。于是,对圣人而言,“一”无乎不在,既在高处,也在低处,因而在任何一方中均有“一”的踪迹。圣、王所建构的秩序,预留“阶层”之间的流动,允许并制度性地鼓励社会上(圣人以下为显的社会,圣人以上为隐的人间)由下而上的流动,比如在德上由民至于君子与圣人,比如在能上由民至于百官甚至于王者,这就意味着不能将圣人、君子、王、百官的名位凝固在某一特定阶层之中,而要具有开放性与流动性。开放性与流动性是向着人的努力修为敞开。更高的流动性比如由君子到圣人、由圣人到至人、神人、天人则是非社会性的,因为这里的向上流动背后是天爵而不是人爵,制度的支持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天爵已经属于方外的馈赠,但政治-社会必须具有向天爵开放的余地与空间,这意味着“人的机制”必须适当地加以限制,不能让其将人的心性充满、甚至占据或垄断,不能让其把人间塞满,而不留空隙。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在这个人声鼎沸的世界里为“天机”预留余地。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序[M]∥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2]宣颖.南华经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3]王夫之.庄子解[M]∥船山全书:第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4]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陶崇道.拜环堂庄子印[M]∥方勇,编.庄子纂要:第六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6]刘凤苞.南华雪心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张文江.《庄子·天下篇》讲记[J].上海文化,2013,(1).
[9]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自序[M]∥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10]谭戒甫.《庄子·天下篇》校释[M]∥经典与解释:第24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1]陈柱.阐庄中[M]∥子二十六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吕惠卿.庄子义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王叔岷.庄子校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杨柏岭
【哲学研究】
Chuang Tzu·Under Heaven and Way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CHEN Yun (DepartmentofPhilosophy,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Key words:Chuang Tzu; Under Heaven; sage;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5)04-0454-23
作者简介:陈赟;(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11JJD720002)
收稿日期:* 2015-04-08
DOI:10.14182/j.cnki.j.anu.2015.04.013
——兼与儒家道术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