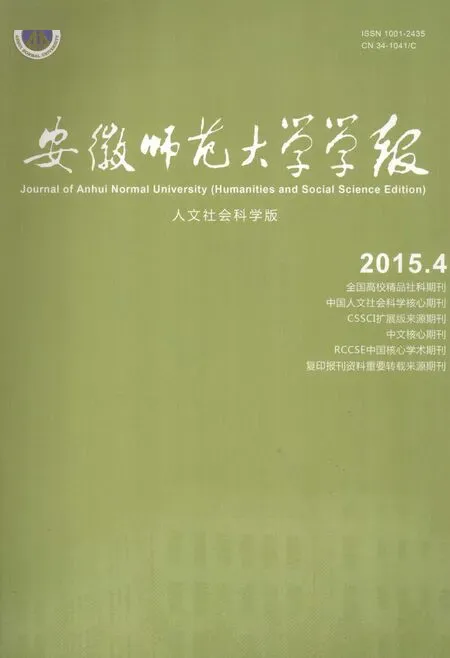论清人的“清词衰亡”说*
胡小林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441053)
词至清代复盛,清人已视之为定论,陈廷焯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1]沈曾植云:“词莫盛于宋,而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馀。及我朝而其道大昌。”[2]但是清人论清词时,也时常提出“清词衰亡”这一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质是什么?清人“清词衰亡”说对于清词复兴的意义如何?
一、清人“清词衰亡”说的提出
在清代以前的词史中,词人最早针对当代词坛提出“衰亡”说的是明代晚期的俞彦。他在谈论词的音调时说:“词全以调为主,调全以字之音为主。音有平仄,多必不可移者,间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间有必不可移者。傥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则歌时有棘喉涩舌之病。故宋时一调作者,多至数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既不解歌,而词家染指,不过小令中调,尚多以律诗手为之,不知孰为音,孰为调,何怪乎词之亡已。”[3]批评明人作词不解词音与词调,任意为之,遂致词在明代衰亡。至清代,清人对当代词坛的得失利弊尤为关注,不断提出“清词衰亡”说。
清代中叶,“清词衰亡”的观点依然存在,并且批评对象愈加明确,措辞也更为激烈。保培基在 《蓉湖渔笛词序》中斥责近世词坛堆砌数典、不审音律之陋习:“窃见今之学者,于诗工拙固不可知,而往往剽青镵白,袭彼俪此,割裂而堆砌之,曰填词,曰诗馀,无怪乎所谓文艺之下乘也……余独慨夫近世词学之几息。”[4]405瞿世寿 《徐睿贞词稿序》指出当世词人的狂妄自大:“近代诸家偭背先型,师心自是,彭亨拥肿,曤目丧心。苍耳蒺藜,罥之皆能刺足;鹿床乌喙,食之便可腐肠。复旦无期,横流难挽。古人真面目,灰丛垢集非一日矣。”[4]458蒋敦复在 《寒松阁词跋》中的批评则更为严厉:“握手论词,相叹近日词风盛行,词学转衰……时彦诧于人,辄云姜张、朱厉,其实于玉田、樊榭仅得皮毛。竹垞已不可及,若白石之一往庯峭,非貌为清空者可袭而取。”[4]1198
清代晚期,“清词衰亡”说仍在持续。谢章铤在为张惠言作 《词选跋》时指出,清词似盛而实衰:“国朝词家最盛,王兰泉 《词综》,姚茝階《词雅》,蒋子宣 《词选》,撰录不下数十百人,然自浙派流行,大抵挹流忘源,弃实催华。强者叫呶,弱者涂泽,高者单薄,下者淫猥。不攻意,不治气,不立格,而咏物一途,搜索芜杂,漫无寄托,点鬼之簿,令人生厌。呜呼!其盛也,斯其衰也。”[4]1409黄家绶 《醉吟居词稿序》认为浙西词派强调宗法姜、张,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后世词人:“余尝论本朝词家自朱、厉以后,倚声选韵者非靡即俚,迷而不知门户。真如轻烟一缕,袅空无际者不可多觏。”[4]1486谭献 《愿为明镜室词稿序》认为浙派后学之词,其实已堕入明词末流:“圣朝文治迈古,贤人君子,类有深湛之思、澹雅之学。倚声虽其一端,亦必溯源以及流,崇正以尽变,而词益大。六十七年间,推究日密,持论日高。阮亭、羡门惭其雅,其年、锡鬯失其才。乃至尧章、叔夏,亦不能匿其瑕,其升庵、元美之祧已久矣。”[4]1505文廷式在 《云起轩词钞序》中回顾清初至清末的词学流变时说:“有清以来,此道复振。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4]1877此论有褒有贬,一方面指出晚清词坛词人辈出,在格律声韵上超越前人;另一方面又指出晚清词作在寄托涵思方面则过于窘局,不能望清初词人之项背。
可以看出,明人与清人均提出过当代词坛“衰亡论”,但是,清人所谓“词衰”与明人之所谓“词衰”,概念并不一样。根本差别在于,明人提出此话题,是因明代词坛无论词作数量还是质量,均无法与词学鼎盛的两宋相比,故称其凋敝。清人在讨论清词兴衰问题时,遵循的思考路径是貌似极盛,实则极衰,是在清词复兴的前提下提出这一话题,其涵义颇耐人寻味。
清人所体认的清词之“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论词不尊词体,不追流溯源,使词沦为小道;(2)学词不肖,号曰师法古人,却因才力所限而仅得皮毛;(3)作词不工,词人词作众多而品质堪忧;(4)派系之争严重,囿于门户之见,堕于词学末流而不自知。严迪昌在《清词史》中指出:“清人之词,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与 ‘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任何‘诗庄词媚’一类 ‘别体’说均被实践所辩正。”[5]此为今人对清代词体特质及功能的定位。但是,清人对清代词体及功能的定位与期许,或许并非仅限于此。
二、清人“清词衰亡”说的语境变迁
清人提出“清词衰亡”说,并非与唐宋词相较而言。相反,在与唐宋词相比较时,清人对于清词颇为自信,亟称其盛,认为清词出入晚唐、两宋之间亦无愧也,从清初至清末,均是如此。但是,在谈及当代词坛现状时,往往话锋一转,进而提出“清词衰亡”说。根据清人“清词衰亡”说具体语境的变迁,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清初词家在明词衰亡阴影下思考清词繁盛之后的进一步走向。清初清人的“清词衰亡”说有一个共同讨论基础,那就是,承认清词的全面繁盛:词人众多、创作活跃、流派纷呈。但在清初词坛极盛的背后,隐藏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清词如何走出明词的困境,不重蹈其衰亡的覆辙?清初词人认为,明词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词之真情与词之格律的双重缺失,其典型表现,就是明人对 《花间》《草堂》词作的机械摹仿。而在清初词坛,《花间》《草堂》之风依然盛行。此外,清初词坛对于词之音韵、格律亦无定则,虽有沈谦 《词韵略》、万树 《词律》等先后问世,但对清初词人作词的指导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因此,清初词坛面临的词学困境与明代词坛如出一辙。虽然清初词坛暂时出现繁盛的局面,但是如果词学的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衰亡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二)清中叶,词家对浙西词派得失的思索。自浙西词派在康熙中叶词坛定于一尊之后,其后百余年,词人大多唯朱、厉是举。与此同时,词坛无论浙派词人自身还是非浙派词人,对于浙西词派得失的讨论也在进行。
浙西词派词人关注的焦点是,自朱彝尊、厉鹗之后,浙派后学如何将姜、张“清空骚雅”之词旨落到实处,不再仅是酬唱时的口头空谈或供人辨别词学门径时的标识,否则,浙派后学的创作将意味着清词的衰落。浙西词派后期领军人物郭麐对浙派后学的批评,最具有代表性。他在《梅边笛谱序》中说:“倚声之学今莫盛于浙西,亦始衰于浙西,何也?自竹垞诸人标举清华,别裁浮艳,于是学者莫不知祧 《草堂》而宗雅词矣。樊榭从而祖述之,以清空微婉之旨,为幼眇绵邈之音,其体釐然一归于正。乃后之学者徒仿佛其音节,刻画其规模,浮游惝恍,貌若玄远,试为切而按之,性灵不存,寄托无有。若猿吟于峡,蝉嚖于柳,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4]736但如何落到实处,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非才力过人者不办:“自小长芦竹垞以姜、张为宗,海内翕然从之,几于家白石而户玉田矣。顾世之学姜、张者或失之涩,或失之直,袭其肤末者多,得其神髓者少。浙西六家有扶衰救弊之功,由今观之,惟竹垞不愧称巨擘,其下令人有自郐之想。甚矣!词学之难也。”(王初桐 《西濠渔笛谱序》)[4]715在浙派后期,一方面缺乏如同朱、厉般能以微言传远旨的通儒巨公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浙派后学对于先贤词学理念的真正顿悟也付之阙如,其衰微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非浙派词人在肯定浙西词派振敝之功的同时,对浙西词派的不足也提出了批评。谢章铤在 《抱山楼词录序》中历数浙派兴起与衰落之成因:“国朝词学,浙最盛行,竹垞倡于前,樊榭骋于后。羽翼佐佑,俊才辈出,而派别成焉。祖宋窥唐,意内言外。竹垞以情,樊榭以格,作者莫之或先。又揭其涉猎之绪余,搜奇征僻,以相夸耀。昔昌黎之诗,时多险涩,皆其文所吐弃者,积之于诗而已矣。朱、厉体物数典,其游戏殆亦若是哉?或专效之,浙词之盛反衰。”[4]1441亦有词家则针对浙西词派之流弊,进行攻诘,如张国梁 《红豆山房词钞自序》指出:“戊子闱中……后晤李式斋孝廉、蒋澹怀茂才、孙小屏进士,纵言至词,于竹垞、樊榭诸家,攻击无完肤。”[4]1135其中,尤以常州词派领袖张惠言为代表,蒋学沂在 《藉船词自序》中提及张惠言论词之旨:“先生之言曰:‘词者,诗之馀也。词学始于唐季六朝,至南北宋为极盛。后人为之,或流于放,或伤于纤巧。故元明以下无词,国朝乾隆间始有人起而振之。’则先生自谓也。”[4]974张惠言之言,以“元明以下无词”一带而过,将清初词人及浙西词派直接忽略,可见他对以浙西词派为代表的当代词坛的批评与不满。
(三)清代晚期词坛,词家往往将浙、常二派优劣进行对比,认为作词不应囿于门户之见,才是保证清词不衰的根本路径,观点更加中允。伍绍堂 《梅边吹笛谱跋》对于浙、常二派均有所批评:“考国朝经生能填词者,近推张皋文、江郑堂,然皋文论词,往往求深反晦,如姜白石《暗香》《疏影》二词,乃指为二帝之愤,不几于钱蒙叟之解 ‘云鬟’‘玉臂’耶?江郑堂论词,于万氏 《词律》深致不满,而自诩其倚声为得古今不传之秘,余未敢遽以为然。”[4]631郑文焯也提出:“凡为文章,无论词赋诗文,不可立宗派,却不可偭体裁。”[6]此时,浙、常二派的争锋已趋平息,门户之争已经失去昔日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清代晚期词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文人学词的理想状态,应是融通诸家之长而为我所用。但当时词坛实际情况却是,学识浅陋之词人依然囿于一家而不自知。面对词坛现状,当时词家除却批驳有加,也提不出更加有效的改革办法。清代词家罗道源在 《怀青盦词序》中将清词作者繁多而佳作不多的原因,归结为清代词人误将旨在抒写幽怀要渺之致的作词,下墮为门户积习之学和派系攻讦之斗:“词之作也,由来已久。昔人谓意内言外,能陶写幽渺难喻之旨,故动荡迷离,使人不倦。以此论词,不可不为得焉。然后之作者,但取赵宋,或南或北,不一其人。抗高调者艳说苏辛,尚柔婉者竞言秦柳。其流弊之极,遂误以支涩为浑厚,浅率为清泚。夫以风月思怀之境,一变为门户积习之学,其为作者繁而佳者少,不待言矣。”[4]1782有些词家,如张祥龄在 《半箧秋词叙录》中甚至将清词之衰归结为运数所致,认为文章风气,如四序迁移,莫知为而为:“南唐二主、冯延巳之属,固为词家宗主,然是句萌,枝叶未备。小山、耆卿而春矣,清真、白石而夏矣,梦窗、碧山已秋矣。至白云,万宝告成,无可推徙,元故以曲继之。此天运之终也。”[4]1787言下之意,南宋张炎已为词运之终结,故清词运数之衰,亦属自然而然之事。
清人在不同具体语境下提出“清词衰亡”说,其合理之处在于能够及时发现当下词坛存在的弊病,提醒词人引以为戒,并顺势提出词学改革主张,使清代词学得以遵循正轨而发展;其弊端在于观点过于偏颇,动辄言过其实。事实上,囿于词人自身词学见解、流派归属或话语环境,不同词人往往对所谓“词学衰亡”的看法并不一致,此流派认为是“极盛之兆”者,另一流派却以为是“衰亡之征”。以词的声律问题为例,清代词坛对于词谱、词韵的具体性、系统性、实证性、专业性整理,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尤以万树《词律》为发力之作,但晚清词人对于 《词律》的评价却不尽一致。俞樾在其 《词律序》中指出,《词律》一书为词家正鹄,在词学中可谓学览之潭奥,摛翰之华苑,对万氏的创造之功尤为肯定。[7]同为清代晚期词人的张德瀛则认为,宋、元人制词,无按谱选声以为之者,皆形诸齿颊,非有定式。但是,从明代晚期程明善 《啸馀谱》、张綖 《诗馀图谱》开始,以至有清一代词坛,流风相扇,失去宋人作词之轨范,可谓词谱大行而词学尽废。[8]也可以看出,清代词人对于词坛盛衰的体认,常常具有其复杂性,也不可一概而论。
三、清人“清词衰亡”说的实质
清人在“清词衰亡”说中,对“近日”“近世”“近时”之倚声家严厉地批驳,表面上反映出清人对当下词坛创作现状的不满,其实质是清人对清词成就预期之高与清词发展中的病弊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焦虑心态,也是清人对于以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濒临衰亡之担忧。
清代词人对清词成就有着很高的预期,这从清人对于清词之自信可以管窥一二,最突出地表现为对清词繁盛局面的自豪感,这在清人词论中随处可见。但在清词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流弊,无论哪一种词学思想,均是如此。与明人论明词时注重本事与赏析不同,清人论清词时,对于清代词坛当下存在的弊病尤为关注,并由此引发对清词发展停滞的焦虑心态,甚至提出“清词衰亡”说的极端观点,以期引起当世词人的关注。清人唐梦赉在 《聊斋词序》中指出当世词家有二病:一则粉黛病,一则关西大汉病。[4]410江藩在 《梦隐词叙》中批评道:“予谓近日词人有二病:一则专工刻翠雕红,揉脂搓粉,无言外之意。深婉惜之,此乃不宗姜、张之故……一则铜弦铁板,引稼轩、龙洲自况,不知宫律为何物。四声二十八调,有轻重清浊之别,岂可置而不问,但求畅所欲言乎?稼轩、龙洲未必若是之妄也。”[4]631-632曾炜在 《青田山庐词钞跋》中提及莫友芝 《葑烟亭词序》中关于清词弊病的讨论:“近日海内言词,率有三病,质犷于藏园,气实于穀人,骨孱于频伽,其倜然不囿习气、溯源正宗者又有三病:服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袭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逐波忘返者也。”[4]1591金应珪在 《词选后序》中也指出,近世词坛有三弊,一曰淫词,一曰鄙词,一曰游词,前两弊显而易见,常人皆知其非,而游词之弊则似是而非,易于乱真,学词之人必破此三弊,而后才可以为词。[9]3933
清人所批驳词坛弊病,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寄托与格律难以兼美,精审格律者无所寄托,有所寄托者不审格律;(2)婉约与豪放失之过当,婉约者过于婉约,豪放者过于豪放;(3)学词而不肖,师法今人者忘却古人,师法古人者难悟真谛。清人在批评清代词坛当下种种弊端时,进而带出“清词衰亡”之论,从清词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视为清人针对清词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抛出的旨在推动词坛变革的词学策略。纵观流派众多的清代词坛,几乎每一个词学流派的兴起,都伴随着其对当下词坛弊端的指责与批驳,并以此为基础推行自己的词学主张,隐藏着开宗立派的意图,浙西词派取代阳羡词派而兴起,常州词派之于浙西词派,均采用了这一词学策略。
当然,晚清词人在远距离反思整个清代词坛的功过得失时,也会提出“弊病说”,这与以上所论清人对当下词坛的批驳相比更加理性客观,不再有门派之争的杀伐之气。如陈廷焯首先肯定清初词坛备极一时之盛,然后才指出清初词人有二病:“一则板袭南宋面目,而遗其真,谋色揣称,雅而不韵。一则专习北宋小令,务取浓艳,遂以为晏、欧复生。”[9]3775
事实上,清人在提出“清词衰亡”说之前,已经注意到明词之“衰亡”。清人认为,明词衰落的表征有三:一是治词者寥寥;二是托体不尊、大雅不存;三是失宫坠羽、音律舛误。[10]明词衰亡的表征,其实亦是明词的弊病。而这此弊病,清词亦有,清人对此更加关注,这也反映出对词坛现状的不满。
以清初为例,其弊病之一,就是主导明代词坛的 《花间》《草堂》词风在清初的延续。何士信 《草堂诗馀》的选词之旨,本为雅俗并举,但在明代文坛,“性灵说”主导一时,《草堂诗馀》中抒写真情之作便被明人奉为圭臬,以为词之准的,导致明词浅俗浮艳,有曲化之倾向。清初词人依然未能跳出这一局限,清初词家中的有识之士对于 《草堂诗馀》,尤为痛恨。对此,沙先一、张晖在 《清词的传承与开拓》中以朱彝尊为例,谈及清初词人改革词风的策略:“朱彝尊对明词及清初词坛创作颇为不满,于是倡导醇雅之格、清空之风以纠正词坛创作的弊病。”[11]朱彝尊在编纂 《词综》时,将批评矛头直指 《草堂诗馀》:“古词选本……皆轶不传,独 《草堂诗馀》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调之不振也。是集兼采……诸书,务去陈言,归于正始。”[12]679朱 彝 尊 以 《词 综》之 雅,力 挽《花间》《草堂》词风之俗,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廓清词坛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清词坛,词家对朱彝尊关于 《花间》《草堂》词风的否定,则秉持质疑态度。况周颐就认为 《花间词》不易学,即便是能够窥两宋词堂奥的、词学造诣甚深的词家,对于 《花间词》也只能望尘却步。[13]王国维也是这个意思,认为 《草堂诗馀》不能一概抹杀:“自竹垞痛贬 《草堂诗馀》而推 《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 《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14]可见,清代词人对本朝词坛弊病的认定,对本朝词学思潮的反思,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朱彝尊的继承者厉鹗,对于朱氏倡导的醇雅词风,做出了进一步开拓。张宏生指出:“他(厉鹗)之所以能够开创浙派发展的新局面,除了他本人多方面的素质之外,接过朱彝尊提倡的尊姜口号,并给以实际的阐发,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15]但是,问题在于,浙西词派后学并非均具有与厉鹗同等学力与才力,对于朱氏词学思想的领悟有深浅,执行能力亦有高低。那么,朱彝尊对于清词的革新,到底能泽被浙西后学多久?浙西后学对于朱氏词学思想的继承质量,取决于其自身才识和悟性的高低,下者往往会拘囿于朱氏词学主张、创作方法的束缚,无力创新和形成独特词风,遂成为词派的隐形人,最终导致词派的衰落。对此,储国钧在 《小眠斋词序》中指出:“夫自 《花间》《草堂》之集盛行,而词之弊已极。明三百年,直谓之无词可也。我朝诸前辈起而振兴之,真面目始出。顾或者恐后生复蹈故辙,于是标白石为第一,以刻削峭洁为贵。不善学之,竞为涩体,务安难字,卒之抄撮堆砌,其音节顿挫之妙荡然。欲洗 《花》 《草》陋习,反墮浙西成派,谓非矫枉之过与?”[4]444浙西词派朱、厉对于清词的改革,促进了清词的发展与繁荣,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弊病。孙克强认为,浙派弊病有三:强调文本文雅精致,忽略情感因素;以南宋为畛囿,师法片面;片面讲究韵律,名实难符。[16]后继词家面对词坛之新弊病,必然会提出新的词学主张,再次推动清词的发展。
清人对于清词发展兴衰的关注,除却文学层面承继和超越古人的考虑,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对以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能否薪火相传的担忧。清人对于词之起源的讨论,一直与 《诗》为代表的儒学紧密相联,认为因为诗教衰微,遂有倚声之学的兴盛。作为词派领袖的朱彝尊,同时又具有深厚的经学造诣,其对于词与儒学关系的讨论,可以视为代表。朱彝尊在《艺香词题词》中提出,就“兴会”而言,诗词应无差别:“诗降而词,取则未远。一自 ‘词以香艳为主,宁为风雅罪人’之说兴,而诗人忠厚之意微矣。窃谓词之与诗,体格虽别,而兴会所发,庸讵有异乎?奈之何歧之为二也。”[4]102在指出词源于诗的同时,又进一步强调词与诗的差别,仅在于抒情内容的不同,相对于诗,词更具有抒发隐幽之情的优势:“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12]692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将词视为以 《诗》为代表的儒学之承递,实际受到其业师曹溶的影响:“彝尊忆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倡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4]279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清初词家,将词纳入儒学统序,固然不能排除出于推尊词体的需要,但更重要和深层的目的和用意,当是面对明清易鼎、民族文化濒临灭亡时必要保护和传承策略。
并且,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清人对词体的认知,促进了清人作词的自觉意识。张宏生在谈及明末清初从 《古今词统》到 《词综》的词学思想演变时指出:“可以看出一种特定的思路,即越来越明确地在词学中确定统序,这一点,是清词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特别是清代词学流派兴盛,往往有非常系统的理论,而理论的展开,也与对前人的体认有关。”[17]因此,清人的治词思路,不仅在于确定词自身的统序,更重要的在于将词纳入到儒学道统之中,强调其佐时治世的功能。清嘉道间张惠言以经言词,亦沿袭了这一思路:“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 《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18]1
苏士枢 《石舫园词钞序》说:“(填词)上薄风骚,下关世运,非可以小道浅测之。”[4]870既然清人将词的地位提升至儒学诗教的高度,视其与世道运数相关,那么,词在清代的兴衰变迁,必然会刺激词家的敏感神经,发出清词衰亡、江河日下的警世之论。
四、清人应对“清词衰亡”:自我审视和自觉变革
面对清人清词话语体系中的清人应对“清词衰亡”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从个人角度而言,清人加强对词作的自我审视;二是从词坛总体而言,针对诸种“弊病”展开自觉变革。
清人在指责近日词家存在诸多弊病的同时,更加强对自身词作的严格审视。清代末年,端木埰在 《碧瀣词自叙》中叙述了自己漫长的学词历程: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师从金伟君时“虽从事于斯,茫然不知词为何物……惴焉惧辱家训,亟叩先生以词曲所以异……乃悉取碧山、草窗、蜕岩、君衡诸公集熟读之”[4]1751,至“偶以青蚨三百得 《词律》佳本,遂日事吟弄。从此因缘涉猎,或作或辍”[4]1752,至“甲申(1884)以后……赓和益多。幼霞尤痂耆拙词,见即怀之”[4]1752。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练,端木埰《碧瀣词》兼采王沂孙的寄托、姜夔的清空和苏轼的清雄,不囿于一家而自成体系。可是,端木埰在 《碧瀣词自叙》开篇便提出:“仆词不足刻也,且不可刻。”[4]1751这虽是自谦之语,但也足见端木埰对己词的要求之严。端木埰的经历,是清代词人刻苦学词的一个缩影。蒋澹怀也曾言:“殚精竭虑,为举世不好之物,叹息而已。”(朱绶 《缇锦词自序》)[4]806
随着清人对词学典籍的整理与发掘,词学系统日益完备,对词人的要求亦越来越高。因此,在清人学词过程中,经常会有“填词颇难”的叹息。如俞樾 《绿竹词序》曾说:“词莫盛于宋。元曲兴而词学稍衰,有明一代非无作者,而不尽合律,毛公所谓徒歌曰谣者也。至我朝万红友《词律》出,而填词家始知有律。然榛芜初闢,疏漏尤多。道光间,吴门有戈顺卿先生,又从万氏之后,密益加密。于是阴平、阳平及入声、去声之辨细入豪芒。词之道尊,而填词亦愈难矣。”[4]924即便是深谙词之格律音韵的戈载,填词也时有愧悔之意。他在 《翠薇雅词自序》中说:“予于词致力已十数年,向时所制,刊成十卷,见闻未广,校勘未精,草草问世,深自愧悔。虽舛错之处,亦多依据,然事不从其朔,非探原之举也;法不取乎上,非择音之旨也。故修改之志,无日去怀。”[4]797-798于是,戈载借 《吴中七家词》刊刻之际,重新校刻其词:“予乃就十卷中遴其稍可者,重加订正,又细考四声,必求合乎古人,且必求合乎古人之名作以为法。所选仅十之三。”[4]798
清代词学系统的日益完备,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加大了词人治词的难度,但对于清词的发展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朱祖谋 《吷庵词序》认为,在追求词律的精审与文本的骚雅之外,还应有更高的填词境界:“我朝二百七十年来,英硕辈生,博综艺事。独于斯道,颇疑晚出益工。诚以审音辨律,雅志矜慎。劬学笃嗜,或可企及。至于明阴洞阳之奥,腾天潜渊之才,接轸风骚,契灵乐祖。相如答盛览问赋,以为可学者迹,不传者心。词流精诣,殆无逾此。”[4]1927“词别是一家”,面对严格的填词格律,唯有以心体悟词道,才是清代词人薪火相传,保持清词不衰的秘籍所在。
清代词人在严审己作的同时,也针对当下词坛的弊病,积极开展自觉改革,这也是清人应对“清词衰亡”的措施之一。纵观清代词史,无论是作词、论词、选词或整理词籍文献,均显示出清人变革的决心和努力。陆世楷在 《东溪诗馀题词》中透露出变革先驱者之不易:“当开元、天宝之盛,而箫声柳色,词源已滥觞矣。是知声音之道,关乎治忽,风气将变,有开必先。所贵主持其间者未变而示之的,已变而立之坊耳。”[4]170-171而敢为变革先驱者的词家,往往具有卓越的前瞻意识。朱彝尊的词学主张,就曾一度受到当时词家的质疑。他在 《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当取诸南渡,锡山顾典籍不以为然也。”[4]338-339其《咏物词评》又言:“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实庵舍人意与予合。”[4]164雍乾词人陆培在 《白蕉词自识》中总结清初词坛变革历程时说:“词至前明,风斯下矣。国朝钜公辈出,力矫 《草堂》习气。竹垞翁自拟乐笑,谓集诸家大成。近读钱塘厉先生 《秋林琴雅》,古情异采,几跨小长芦而过之。”[4]429一语概括出顺康词坛众家及浙西词派对于革除明代词风残余的贡献。蒋敦复在 《香隐庵词跋语》中,则指出自己意欲以词话挽浙西词派后学之谬误的迫切心情:“迩年词学大盛,俱墨守秀水朱氏之说,专宗姜张,域于南渡诸家,罕及 《花庵词选》者,况 《花间》乎?敦复尝欲救之,作 《词话》,以 ‘有厚入无间’及炼字句之法告人,尊词品故也。”[4]1255而张惠言编纂 《词选》,亦体现出强烈的变革意识:“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今第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18]
清人对当代词坛的自觉改革,是以明词之衰亡为借鉴的,目的是避免清词重蹈明词的覆辙。无论词学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需要强调的是,倡导改革的词家们其主观意图都是希望清词能再次进入良好的发展路径之中,能够与唐宋词比肩。
五、清人“清词衰亡”说对于清词复兴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任何文体都有其兴衰的必然规律,词亦是如此。从词史而言,词肇兴于唐,极盛于两宋,衰落于元明,复兴于清。在清词复兴的背后,是清人对清词发展持续地关注和推动,清人“清词衰亡”说即是其中策略之一。尽管清人“清词衰亡”说看似过于极端和片面,甚至有耸人听闻的嫌疑。但是,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心理动机和时代动机,反映出清人对当代词学发展现状的关注和焦虑。面对当代词坛的发展困境或词学弊端,清代词家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有识之士会警示提醒,力图改革,有些词家则选择了缄默或回避,但更多词家或许根本认识不到这些问题,从而无意识地加重了词学发展的障碍。因此,清人“清词衰亡”说的提出,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对清词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它体现出清人复兴本朝词坛的自觉意识。在明清易代之痛的激发下,清人从清初开始,面对元、明词坛衰敝的局面,便自觉地承担起匡复词坛的历史责任,不断提出词之衰亡的隐忧,促使清代词坛自觉革除当下弊端,随时调整其词学理念和创作规范,实现词学流派的自我调整乃至相互更迭,达到词学复兴之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对汉民族文化精神和儒教统序思想的自觉传承。
第二,它是清人对本朝词学成就的崇高期许。清词的复兴,不仅仅是清人汇集前代词学遗产之大成,整理、总结前代词学资源,建构、完善古典词学体系的努力结果;同时也是清人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词学问题进行持续而深入的理论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创作实践。那么,清人对于自身词学成就的崇高期许,就成为推动清词复兴的主要动力。
第三,它是清人词史观念的充分体现。清人之所以提出清词衰亡说,往往是在与前代,尤其是两宋词学成就的比较之中得出的。这说明,清人已经自觉地将清词的发展,纳入到中国词史发展进程中并不断地加以审视,以便对清词的价值和地位能够准确地做出自我评价,促使清代词学在停滞与改革的交替进程中不断成熟和完善,从而臻于全盛。
[1]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3775.
[2] 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M]∥朱祖谋.彊村丛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
[3] 俞彦.爰园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00.
[4] 冯乾.清词序跋汇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5] 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
[6]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332.
[7] 俞樾.词律序[M]∥万树.词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
[8] 张德瀛.词征[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095.
[9]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谭新红.论清人对明词的体认和反思[J].文学遗产,2003,(6):121.
[11] 沙先一,张晖.清词的传承与开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2.
[12] 朱彝尊.曝书亭词话[M]∥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13] 况周颐.蕙风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423.
[14] 王国维.人间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263.
[15] 张宏生.清词探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5.
[16] 孙克强.清代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47-251.
[17] 张宏生.统序观与明清词学的递嬗——从《古今词统》到《词综》[J].文学遗产,2010,(1):93.
[18] 张惠言,等.词选·续词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
——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