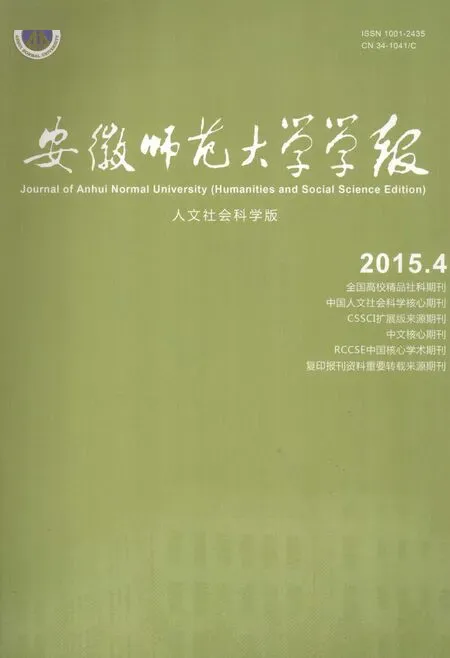从心学内涵看杨简废《序》的思想成因
叶文举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学者通常以是否尊崇 《毛诗序》为标准,把宋代 《诗经》学分为主 《序》派和废 《序》派两大阵营。如果从这个划分来看,杨简当归为废《序》一派。杨简废 《序》和他心学思想的理念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①关于此点,请参见拙文 《杨简 〈诗经〉研究的心学特色》,《孔子研究》2009年第2期。他曾在对 《召南·殷其雷》进行解读时,全面阐述了对于 《毛传》《毛诗序》及郑笺的认识:
闵其君子勤劳之心,自是正心、道心。卫宏强起其说曰:“劝以义。”诗中无此情也,毛公亦未尝有此义,雷方动、雨将至,君子亟行,莫敢少止,急趋期会,异于平时,故曰:“何此言违,莫敢或遑也。”振振,叹美其君子,爱之故美之;归哉!归哉!临违告以讫事早归,此人之常情、常言。郑康成因 《序》曰:“劝以义。”遂曲说求合乎 《序》曰:“君子为君使,功未成,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未得归也。”诗旨人情,断断乎无此,盖因夫卫宏,不知“庸常”“无邪”之即道,故穿凿其义,郑不知汉史卫宏作序之实。以为毛公之前已有序,曰至毛公乃分众义,各置篇端,意谓古作而不敢违,故曲就其说,亦郑不知道,与序同。又郑不善于文,又好穿凿故也,又诸儒多以雷生义,亦凿,非诗人本情。②杨简 《慈湖诗传》卷二,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杨简的 《诗经》研究主要体现在其 《慈湖诗传》的著作中。下文所引文字如出于 《慈湖诗传》,因为较多,不再加注。
杨简认为 《诗经》诗篇所表达的思想都是“道心”“正心”,《毛传》对诗歌的解释尚符合诗歌的正意,只是到了 《毛诗序》(按:杨简认为《毛诗序》是东汉卫宏所作)时加以了穿凿附会,背离了“本心”“道心”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杨简认为 《毛诗序》解读 《诗经》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此他提出了要全面废 《序》。笔者认为,与心学思想相关联,杨简主张废 《序》的具体原因值得探讨。
“本心”的普遍性:反对 《毛诗序》解诗的“历史化”
杨简认为“本心”“道心”“无邪”之心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他最不愿看到 《毛诗序》将“本心”“道心”“无邪”之心具体落实到某一国、某一人身上,而 《毛诗序》解诗的最大特点就是经常把 《诗经》的主旨历史化①关于解读 《诗经》的历史化问题,请参见王硕民 《试析汉代 〈诗经〉研究历史化产生的根源》,《东方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汉代 〈诗经〉研究历史化的几种表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实勾连在一起,从而使得 《诗经》的主旨具有了特指的内涵,而丧失了“道心”的普遍意义。②杨简反对 《毛诗序》的历史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杨简认为将 《诗经》按照世系进行排列根本没有多少客观的依据,他对 《小雅·黍苗》进行解读时说道:“《毛传》初未尝言刺幽王,而卫宏作 《序》则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宏盖拘于世次,故强归之幽王。且 《清人》,郑文公时诗,而置于庄公、昭公诗之前。《诗》经秦火,口诵所传,难执世次,况宏 《序》谬误良多,不可尽信。孔子所取大旨,固不在其人与世,而宏谬太甚,不得不辩。”(《慈湖诗传》卷十五)就旗帜鲜明地反对 《毛诗序》把诗篇的创作时间强行加以定位。这是杨简在心学思想上反对 《毛诗序》解诗历史化的第一个原因。他在解读 《邶风·日月》时说:
《日月》,乃深恶无礼之诗,正也。故圣人取焉,而诸儒谓之人者,庄公也。 《毛诗序》谓:“庄姜遭州吁之暴伤,已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犹未害于义也。”伤之而已,犹之可也。而《诗》曰:“德音无良,逝不古处。”“胡能有定,报我不述”,恶之甚也,非所当施于夫也,非庄姜所当施于庄公也。施于庄公,则悖矣;施于州吁,可也。且之人犹不敢明言之,诸儒拘于《序》,遂入于不义,使歌此诗者,以之人为庄公歌之,岂不长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可者。(《慈湖诗传》卷三)
杨简反对把 《日月》的主旨单一地指向庄姜、庄公,而认为它应当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就是人们追求“无邪”之心,故而杨简认为此诗“正不必究知之人为何人,惟见无礼悖乱之可恶,岂不正乎!”(《慈湖诗传》卷三)圣人的道心和凡人的道心其实同有,他在解读 《周颂·维天之命》的时候所说“文王之心,即众人之心,即千万世之心”(《慈湖诗传》卷十八),正是这个思想的表露。如果像 《毛诗序》那样将 《诗经》历史化,和具体的人事联系在一起,那么“道心”作为人们普遍存在的本体就落了空。
杨简反对 《毛诗序》解诗历史化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历史化”是“道心”外求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历史化”也成为了杨简批判 《毛诗序》的一个重要目标,他在解读 《唐风·葛生》时说道:
《诗序》曰:“《葛生》,刺晋献公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矣。”夫本诗妇思其夫也,卫宏不知夫妇之道正大,故外推其说以及于君焉,既失诗人之情,又失先圣之旨。(《慈湖诗传》卷八)
杨简的潜在之意认为,《葛生》只是单纯表达了妇人思念亡夫的正常的人伦情感,“夫妇之道”本来就是正大的“道心”。如果把 《葛生》的时代定为晋献公时期,去寻找“道心”的成因,外求诗旨,也就否认了“道心”先天性存在的特点,这和杨简道心本存的心学思想是相违背的。
再者,在杨简看来,如果仅仅从历史事实中外求诗旨,难免有曲解的嫌疑,不如求之于本心,来得明快。杨简解读 《邶风·终风》时说:“《终风》,恶其暴乱无礼之诗,正也。《毛诗序》谓 ‘卫庄姜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之诗’。诸儒不悟无邪之为道,故曲推其义,失之矣。”(《慈湖诗传》卷三)故而,杨简认为 《毛诗序》把诗歌历史化是多此一举的行为,是赘言或赘词。因此,杨简主张不必在意于 《毛诗序》历史化的解读,完全可以将其弃置一边。他在讨论 《王风·中谷有蓷》时说道:“《毛诗序》曰:‘《中谷有蓷》,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诗中初无闵周之情,卫宏赘辞也。恶不淑,正也。忧苦,非邪也。宏不达无邪平正之道,故多赘说。”(《慈湖诗传》卷五)杨简认为卫宏不懂得人心本“无邪”的说诗宗旨,故多作曲解、赘说,反而离诗歌的主旨越来越远,伤害了“本心”“道心”。杨简解读 《王风·兔爰》时说:
是诗忧苦无聊,虽有隐怨,无敢著明。是诗无邪,孰非道心?《毛诗序》曰:“《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败节容有此事。《序》多误,亦不可深信。然孔子取此诗之道心,虽无此序亦可,而 《序》文赘,反足以乱道心。(《慈湖诗传》卷六)
杨简认为 《王风·兔爰》并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感发,它只是表明“无邪”的道心而已。因此 《毛诗序》附会历史事实的曲解,是多余的赘言,从根本上于“道心”无益。《毛诗序》把 《诗经》历史化的一个主要用意,实际上是要追寻诗篇的作者,杨简认为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杨简曾说:“诗人或有感动,斐然而作,忽然而忘。他日采诗者取之,则其名未必本有,他人加之,亦未可知也。孔子不作诗序,旨在于诗无序,可也。”(《慈湖诗传》卷一)杨简认为 《诗经》中的诗歌只是当时人们情动于中,感发而作,并非刻意为之,后来的采诗者也不知道作者为谁,《诗经》的作者完全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因而 《毛诗序》通过将 《诗经》历史化的手段去探寻作者,本身就是一个谬误。总而言之,杨简反对 《诗经》历史化的目的还是为其心学思想服务的。他在 《自序》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反对 《毛诗序》历史化解读的理由:“诗之有 《序》,如日月之有云,如鉴之有尘,学者愈面墙矣!观诗者既释训诂,即咏歌之自足,以兴起良心。虽不省其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墙矣。”(《慈湖诗传·自序》)
“本心”直指:反对 《毛诗序》“支离”的解说,主张“通言”的解读
杨简对 《诗经》二 《南》有过总体评价,他说:
夫二 《南》,用于乡乐,用于邦国,周公必以经意。又孔子屡以启伯鱼,启门人,又屡言《关雎》,门弟子宜有所问,而此通言后妃之德,余篇略同,当是孔子之所诲告,不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离人心,欲后世诵咏 《三百篇》之诗,知皆正辞正情,足以感发人所自有之正心。若于本诗之外,赘曰某国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之故,则诵诗者首见其国,又见其人,又见其故,至于本诗,将诗人不知所以然,油然动于中,发诸声音,自中自正,浑浑融融,无所不通之妙,如云翳日,如尘积鉴矣!而况于置诸首而谓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慈湖诗传》卷一)
杨简反对把诗歌的主旨落实到“其国”“其人”“其故”,这样容易“支离人心”,看不到人之“本心”所在,因此他反对将 《诗经》进行细致、琐碎的解读,所以他主张废除 《诗序》,因为 《诗序》烦琐的解读,就“如云翳日,如尘积鉴矣!”看不到本心的所在。①杨简反对对 《诗经》进行支离地解读,和理学思想上的斗争有着潜在的联系。从“支离”一词,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作为心学一派的杨简,和乃师陆九渊一样,与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一派的思想有着内在的矛盾。这里的“支离”,在理学思想上显然是有所指的。乃师陆九渊曾在鹅湖之会上讽刺朱熹:“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陆九渊 《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7页。)就直指朱熹的学术是“支离事业”。也许在杨简看来,朱熹的 《诗集传》就属于“支离”的著作。故而杨简主张“通言”的解释,而反对具体阐述 《诗经》的诗旨,这也是他主张废 《序》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又说:
今 《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其人,岂亦果有所自,犹有圣人之微意邪!若其置诸篇端,又名曰序,则大乖矣。自 《邶》以下多指其人,又乖矣!至于曲推其意,穿凿其说,如于 《关雎》言哀窈窕,无伤善之心,诗中即无此情;于 《殷其雷》言劝以义,诗中亦无此情,于 《摽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时,诗中何但无此情,正言其不及时,此类奚可殚举。《东汉书》谓卫宏作 《毛诗序》,夫不闻子夏为书而毛公始有传,卫宏又成其义而谓之序,盖子夏亲近圣人,无敢支离,毛公、卫宏,益差益远,使圣人大旨,沉没于云气、尘埃之中,吁其甚矣!(《慈湖诗传》卷一)
杨简认为 《毛诗序》解读诗旨穿凿附会,肆意推断诗篇的意旨,因而反对 《毛诗序》将诗篇“多指其人”,主张“通言”的解释。杨简还认为,《毛诗序》把 《诗经》历史化,有时并不能确指具体时期、具体人物,这样 《毛诗序》所论诗歌主旨也就没有多少实在的意义。如杨简讨论《邶风·静女》时说道:
《毛诗序》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序》盖以是诗居 《北风》《新台》之间,故以为刺。详观诗辞,又非陈古。郑笺义思“贻我以贤美之妃,以易无德之夫人。”而本诗未章,辞情未必其然。然则安知是诗,非武公、文公之诗乎?诗不可以世次定,《郑·清人》,文公之诗,而序于昭公之前,观此可以通矣,矧是序,亦未能知卫君之为何君。(《慈湖诗传》卷三)
杨简认为 《诗经》诗篇的次序并不一定是根据世系年代来编排,所以关于诗篇的主旨也不能根据某一诗篇所处前后诗篇的主旨进行推断。《毛诗序》对 《邶风·静女》的解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杨简主张“通言”的解读归结一点,就是“思无邪”的说诗宗旨,他认为 《毛诗序》就违背了这样一个核心。他说:“卫宏不达平正无邪之道,其作 《序》率多赘辞,曲为之说。”(《慈湖诗传》卷五)“诸儒不知 《序》之不足尽信,率以 《序》解诗,其有阻碍,必至于委曲穿凿牵合。”(《慈湖诗传》卷七)
如果不做“通言”的解读,就容易滑入“支离”的泥潭,《毛诗序》解读方式上的弊病也在于此。这种“支离”的毛病除了上文所述,《毛诗序》经常将主旨落实到具体的人、事之外,还表现在 《毛诗序》时常割裂诗篇的主旨,比如杨简论到 《周南·葛覃》的主旨时说:
《毛诗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夫人善心即道心,妇人志于女功,躬节俭,服澣濯,念父母而归宁,方是心油然而兴,互见错出,无非神用,何本何末?而为诗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则可以,是诗初无是情,不省诗情,赘立已意,使天下后世平夷纯正质直之心,凿而穿之,支而离之。(《慈湖诗传》卷一)
杨简认为“善心”“道心”与生俱来,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不自觉地油然而生,它们并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毛诗序》务要牵强附会地阐明“善心”“道心”存在的前因后果,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是琐碎的“支离”之说。
“本心”自在:反对 《毛诗序》的“美刺”说
《毛诗序》说诗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美刺”说,这一点同样遭到了杨简的猛烈批判。《毛诗序》认为 《诗经》特别是“变风”“变雅”,是有“刺”意的,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1]271这一点和杨简“无邪”的说诗宗旨也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因为人心本善,“本心”即为“善心”,所以根本无“邪”可刺,故而杨简对 《毛诗序》以“刺”说诗心存不满。杨简解读 《郑风·丰》时说:
《毛诗序》曰:“昏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观诗意诚有之,然今悔矣。悔过之心,圣人取焉,而 《序》总曰:“刺乱也”,则差矣,此悔而作诗,求复谐者也。(《慈湖诗传》卷六)
杨简对 《毛诗序》“刺”说的批判,有时还出于对封建伦常秩序的维护。 《卫风·考槃》,《毛诗序》云:“《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对此,杨简批驳道:
《序》每失诗旨,于此又见,此诗自决于退处,岂有刺君之意,君虽有过,岂可以刺,言硕人知时而退,正也,道也。卫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说,《毛传》亦不言刺庄公,以是益验卫宏作 《毛诗序》。汉史可信,宏虽多祖毛说,而又以己意成之欤!(《慈湖诗传》卷五)
杨简一方面对 《毛诗序》的诗旨外求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又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对 《毛诗序》的“刺君”说表示了不满,带有强烈的忠君色彩,已经不单纯是从学术思想所作的品评,犹如他在对 《王风·君子于役》进行解读时说道:
《毛诗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君不可以言刺,而况于王乎?是诗,妇人思念其君子而已,初无刺王之意。卫宏不知道,不知妇念其君子之心,非邪僻之心,即道心,故外推其说,殊为害道。又何以知其非妇人作,而必曰大夫作耶?(《慈湖诗传》卷五)
杨简认为此诗就是一女子思念夫婿而作,而不是 《诗序》所认为的王朝士大夫所作。由此《毛诗序》认为“刺平王”的主旨就不能成立,杨简认为王者根本不可刺讥。我们姑且不论杨简的批评是否准确,但就这一批评的立场而言,潜藏了深厚的封建忠君思想。这样的解说在 《慈湖诗传》中时常出现,如杨简针对 《毛诗序》关于《唐风·扬之水》“刺晋昭公”的观点,提出“君言刺,大悖也”(《慈湖诗传》卷八),显然也是基于“忠君”观念所给予的批驳。
不过,杨简主张“思无邪”的说诗宗旨,并不是彻底地认为 《诗经》中所有的诗歌都没有刺意,特别是 《诗经》中的某些诗篇因为其相关本事有史书的明确记载,表明与衰乱的政治状况是有关联的,那么诗歌就有了讽刺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杨简也无法回避。但是在杨简看来,“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思无邪”的道心服务的,借以消解“刺”的重要性。如杨简在解读 《郑风·清人》时说:
观是诗,虽不知高克与文公事情之详,而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恶,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慈湖诗传》卷六)
《郑风·清人》关涉的历史本事在 《左传·闵公二年》中有所记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 《清人》。”[2]225作为诗歌的 《郑风·清人》,它不可能象史书那样完全记载历史本事,所以杨简认为,“不知高克与文公事情之详”。不过 《左传》对本事却保留了完整的记载,证明此诗内含“刺”旨是史实基础的,杨简当然就不能再回避了,所以杨简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最后,全文引用了 《毛诗序》的解读,暗示了杨简是认同《毛诗序》的看法。但为了表明和自己“无邪”的说诗宗旨相统一,杨简又认为,《诗经》“刺”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表现“无邪”之意,所以杨简才说 《郑风·清人》“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恶”,其目的则是“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仍然回到了“无邪”的说诗宗旨上。
《毛诗序》比附诗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陈古刺今①关于 《毛诗序》“陈古刺今”的方法,请参见拙文 《试论 〈毛诗小序〉的诗旨比附及其对后世“寄托”艺术的影响》,《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2辑。,这一观点同样受到了杨简的挑战,原因就在于杨简认为“无邪”的道心是不分古今的,亘古不变而恒常地蕴藏于人们的内心之中,故而就不存在陈古刺今的问题。杨简在解读 《王风·大车》时说:
周衰,淫风虽流行,而公论终难磨灭,以人性善,终不磨灭也。是诗情状非陈古, 《毛传》亦不曰陈古,独卫宏 《序》曰:“陈古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自古无淫俗,安有同穴之誓。卫 《序》非。(《慈湖诗传》卷六)
《毛诗序》解说 《王风·大车》的诗旨曰:“《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对此,杨简用“以人性善终不磨灭”,即人性贯穿古今的观点来驳斥 《毛诗序》“陈古刺今”之非。杨简认为“道”普遍地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故而“陈古刺今”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杨简在解读 《齐风·卢令》时这样说道:
《毛诗序》曰:“《卢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考 《序》及 《传》,皆谓陈古,而本诗辞情不然,曰其人其辞,指今非陈古也,苟陈古则宜每章称仁、称德,而次章曰鬈,末章曰偲,又三章皆曰美,殊非陈古之意,盖 《序》 《传》以襄公之诗不应有美,故曲推其说,以为陈古以风,不知诗不可以次序,观不可以执一观……故田而民悦之欤,民悦其君,正也,道也。不然则齐有士大夫之贤者,民悦其田也,亦正也、道也,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故不明已之道心,又不知人之道心,而况于六经之大旨乎。(《慈湖诗传》卷七)
不难看出,杨简对“陈古以风今”说诗方法的批评是相当地严厉,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受到了心学思想的影响。正因为杨简认为,“道心”是人天生所固有的,所以根本上没有古今的分别,古人的“道心”也为今人所具有,古人并不见得优越于今人,他们在主体上是平等的。杨简在对《小雅·绵蛮》解读时说:
是诗微臣感其所蒙饮食教,载之大臣而作也。而卫宏作 《毛诗序》,乃反之曰“刺者”,盖意周衰乱世,必无若此仁惠之大臣,故反之以为思古之诗,而本诗情状非思古也。观诗固不可执其世,其间大臣岂无一人,能悯徒行小臣之忠劳也。此事虽甚微然,道无大小,其恤下之心、感惠之心,皆善心、正心、即道心也,圣人取焉。(《慈湖诗传》卷十五)
诗歌并无思古之心,“道”也没有大小之别,只要能够凸现“道心”即可。他对 《小雅·瓠叶》的解读更是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毛诗序》言“不以微薄废礼”,是也。而曰“大夫刺幽王,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雝饩不肯用也,故思古焉”,则不可必也。虽至乱之世,岂无一人一事之善,而必曰古之人,是绝灭人之道心,大不可也……诚敬弥著,是谓道心,人皆有是心,而自不知其为道也。故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慈湖诗传》卷十五)。
“道心”即使在时风日衰的社会之下也是存在的,如果强调“陈古以刺今”,无疑是漠视了今人的道心。
由于强烈排斥 《毛诗序》的“讽刺”说,再加上受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杨简甚至对 《毛诗序》的用语也非常苛求。比如杨简对 《陈风·东门之池》进行解读时说:“《毛诗序》曰:‘《东门之池》,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疾’之为言,甚矣!犯矣!非诗人之情也。是诗含隐不露,讵敢曰疾之耶!”(《慈湖诗传》卷十五) 《毛诗序》用了“疾”这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字眼,杨简都认为不可,用词“甚矣”,而认为此诗是“含隐不露”的,实质是表明“道心”是普遍存在的。
余论:杨简废 《序》的得失
杨简反对 《毛诗序》的解读,完全是从其“心学”思想出发,本身就有理论先行、本末倒置的危险,其实和 《毛诗序》一样皆存在不顾诗歌文本的倾向。《毛诗序》对诗旨的解读存在着比附、曲解的弊病,显露出儒家诗教历史化、道德化的特点。杨简对 《毛诗序》的批判就方法论来说,实际上是以一种错误的批评理念评价另外一种错误的批评理念,两者都有各自的软肋。杨简对 《毛诗序》的批评通常都没有充足的文献佐证,而是极其主观臆断的批评。如他对 《小雅·伐木》解读道:“是诗,燕群臣之乐歌也。而《毛诗序》曰 ‘燕朋友故旧’,盖失其情矣!夫君以臣为友,乃其常言。”(《慈湖诗传》卷十一)《伐木》诗显然是表现友朋之情的宴飨诗,但杨简强解其诗,认为是反映君臣之情的,用意是为了符合自己“燕群臣之乐歌”的观点,他认为这首诗歌表面上是反映友朋之情的,但因为“君以臣为友”,所以这首诗歌本质上却是表达君臣之情。杨简这样强加解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到他的心学思想,显然带有曲解的色彩,所以在上述引文的后面,他作了极度的引申:
君能求贤以为友,必虚中谦和。此虚中谦和,神必听之,终致和平之福,非自外至。夫通天地神人,一而已矣,是一者在人为心,心无所不通,为孝为顺,为谦和,为众善,是心神人之所同,其机一动,其应如响。故圣贤和于朝,民人和于野,诸侯和于外,四夷和于远。及是心,因物有迁,意动情流,为傲慢,为悖厉,为危乱矣。(《慈湖诗传》卷十一)
把此诗的君臣关系上升到“心”学的高度,又和他的“意”说思想联系在一起。①杨简主张“心之精神,无方无体。至静而虚明,有变化而无营为”,“吾心本无物”,这是“本心”的本然状态。如果一旦引起“意”的分别,则这种“至静而虚明”的本心,就会流入对象化的世界之中,难免会产生“千失万过”。杨简是排斥主观性之“意”的。关于杨简“意”说思想的具体内涵,请参见陈来 《宋明理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这样的解释从学术的严谨性上来说,缺陷很明显,就是带有了过度的随意性,这也是“六经注我”带来普遍性的弊病。
杨简反对 《毛诗序》“支离”诗旨、“曲解”诗旨,自己有时却又身陷其中,正如上文所述,《诗经》中的某些诗篇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为了符合“无邪”的说诗宗旨,杨简甚至也不惜加以曲解,如杨简在谈到 《秦风·黄鸟》时说:
《毛诗序》曰:“《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本诗初无刺穆公之意,按 《史记》殉者百七十人,未必皆穆公命之使殉已也。殆穆公惠爱入人之深,西戎之俗以从死为常耳。是诗哀三良而已矣,哀三良,正心也,道心也,故孔子取焉,若是诗以殉葬为善,孔子将删去之。(《慈湖诗传》卷十一)
关于 《秦风·黄鸟》的本事,《左传》文公六年有着确凿的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 《黄鸟》。”[2]446诗意非常明了,三家诗说皆如此。且诗中已经明白地写道:“谁从穆公”,并刻画了殉葬之人临死之前战战兢兢的恐惧之态,显然也是有刺意的。朱熹说:“此序最为有据。”[3]杨简却刻意否认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他不但引用 《史记》以说明殉葬者并非秦穆公所指命,反而认为穆公怀有惠爱之心,实实在在的是强加附会。杨简如此解说的意图不过是突出此诗是通过“哀三良”来宣扬“道心”“本心”的存在,却完全漠视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则秦穆公既然要求三良殉葬,本身就是“道心”“善心”的阙失。这样的解释比起 《毛诗序》的“支离”“曲解”,主观随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在某一篇诗歌的解读上,杨简有时比《毛诗序》稍显合理,这也是正常的,但通常这种合理的解读并不是从心学思想出发,而是从具体事理上加以解读,指出 《毛诗序》的牵强附会之处,自有一定的道理,尽管他本人对诗篇的解读也未必完全准确。如杨简对 《卫风·木瓜》篇解读道:
是诗薄来厚往之意,至厚也;“永以为好”,至忠也,无非道者,正不必究见何人薄来,何人薄往也。卫宏作 《序》,推考卫国事状,他无似此者,惟齐桓封卫,卫人必厚报之情,故谓“此卫人欲厚报齐之诗”。然不思卫人亦何敢为此辞?齐施莫大之惠于卫,奚可比木瓜、木桃、木李?卫人虽思所以报齐?而卫方能国,微弱甚矣,岂能致厚报过齐桓之所施,矧曰“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乃已报之辞,非欲报之辞。(《慈湖诗传》卷五)
《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认为是卫人为了报答齐国的救卫之恩而作了这首“厚报齐之诗”。上文说过,《毛诗序》解诗有历史化的倾向。杨简认为,《毛诗序》为了附会诗旨,“推考卫国事状”,正好就找到这样一件历史事实,从而加以了比附,然而很不符合事理逻辑,主要原因就在于诗歌所叙写施舍者力量强大却给予的非常微薄,而回报者力量微弱却报答的非常贵重。因此 《毛诗序》将诗歌比附成齐卫之间的事情,就违背了常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 毛诗正义[M]∥ 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2]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朱熹.诗序:卷上[M].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