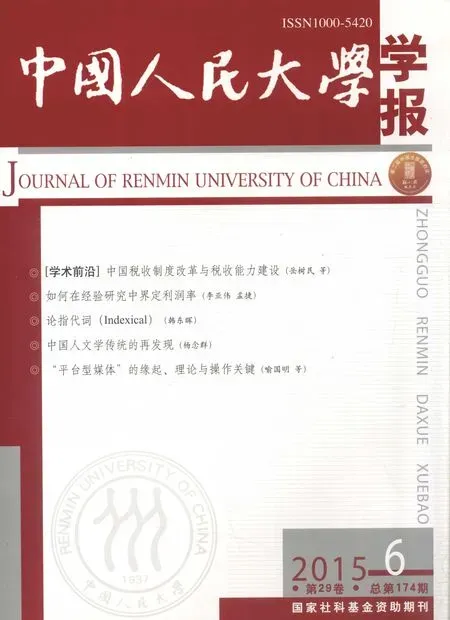论指代词(Indexical)
韩东晖
论指代词(Indexical)
韩东晖
指代词是指称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语言表达式。Indexical、deictic、和demonstrative均可充当此类语言表达式,但其中文译名和理解颇为混乱。比较而言,指代词是Indexical的比较合适的译名。指代词研究呈现出两条主要研究脉络,即语言学路径和哲学路径。其中哲学路径中包含三个主要问题:指代词使用的语言学—哲学预设,指代词的使用与个体对象的被给予方式,以及指代词与语句的真值条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准确定位指代词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指代词;语境化;指示词
我们习惯于用名字称呼某个人,也常常以指示的方式谈及某人某物甚至自己。“我”、“他”、“这里”、“现在”、“这个”、“以上”,就是后一种方式,其意义随语境而变,因对象而异。在英语中,这种方式的特点主要被称为indexicality、deixis或demonstration,相关的表达词汇被称为indexical、deictic或demonstrative。这三个术语的词源意义都是“指示”(point to),因此均可译为“指示词”。但在中文译名中,indexical大多被望文生义地误译为“索引词”,仿佛跟“索引学”(index science)有关系一样,在翻译错误中属于“假朋友”一类(faux amis);demonstrative则被过于宽泛地译为“指示词”,有点辜负了“指示词”这个好名字。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特别是哲学研究方面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术语翻译、研究脉络和哲学问题三个方面,将indexical研究比较完整地勾勒出来。
一、正名
希腊语词deixis本意为“指”(pointing)、“示”(indicating),自古希腊起论者已甚众,例如斯多亚派尝以此讨论单称可断言对象。Deixis的形容词形式deictic(deiktikos)意即“指示”,罗马语法学家用拉丁语词demonstrativus来翻译斯多亚派及其他希腊语法学著作中的deiktikos。因此,源于拉丁语的demonstrative和出自希腊语的deictic是同义的;在后来的语言学习惯中,正如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所言,deixis的使用更广泛,不仅涵盖了指示代词的功能,还包括了时态和人称以及许多在句法上相关的言语—语境特征,甚至还将哲学上的实指(ostension)或实指定义概念包括在内。[1] (P636-637)
英文词indexical源于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皮尔士指号三分法(图像、标志、象征)中的标志——index,但index本身就源于印欧语言中的词根deik-,意思是表明、表示或直接关注语词或对象,具有这个词根的有动词teach、dictate、indicate,有名词token、deixis,当然还有index——用食指指指点点。[2] (P84)皮尔士说:“标志(index)并不断言什么,它只是说‘那儿!’它抓住我们的眼睛,仿佛要强迫眼睛朝向某个特殊对象,在那里停下来。指示词(demonstrative)和关系代词差不多是纯粹的标志,因为它们指称事物而不描述事物。”[3] (P361)
就这三类指示语词在英语中的特点而言,莱昂斯指出,deixis范围比demonstrative更广,且已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indexical主要用于哲学文献,意义类似于deixis。[4] (P637)语言学家列文森最近总结道,在现代语言学和哲学领域,deixis和indexicality这两个术语是共存的,分属于不同的传统,前者属于语言学进路,后者属于哲学进路*在1983年出版的《语用学》中,列文森称之为描述进路和哲学进路。参见Stephen C.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55ff。;从范围上讲,后者可用于标示更宽泛的语境依赖现象,而前者,则在较狭窄的语言学意义上属于indexicality。[5] (P97)
列文森的两条进路说和宽窄范围说大体上符合语言学界的一般看法,或者说大家也需要比较一致的方案来处理这些词。因此,我们可以约定:indexicality的范围最宽泛,我们用它来表达这一系列指示语词和指示现象,但它与deixis的区分主要是哲学和语言学两条进路的差异*努恩伯格不同意将二者等量齐观,他认为引入与“我”、“那个”等语词相联系的特殊语义性质的,是直指词而非指代词。参见Geoffrey Nunberg.“Indexicality and Deixis”,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1993 (1)。;demonstrative的指示范围最狭窄。
基于以上的简要讨论,我们尝试为上述三个概念给出一套比较恰切的中译名。实际上,对于这三个词来说,“指示词”都是比较合适的译名。*例如,有学者将indexical和deictics均译为“指示”(参见蒋严、潘海华:《形式语义学引论》,5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有学者将deictics和demonstratives均译为“指示”(参见哈特曼:《语言与语言学词典》,91-9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不过,姜望琪明确反对用“指示”翻译deixis和indexicality系列词汇,在他看来,“指示”比较宽泛,范围大于这两个系列,例如指称语词的复指或照应功能(anaphora),也可以看做指示。他沿用戚雨村和徐烈炯的译名,将deixis译为“指别”,而将indexicality译为“直指”。(参见姜望琪:《当代语用学》,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这个观点和建议值得参考,但将indexicality译为“直指”,似乎大大缩小了其应用范围。[6]不过,考虑到这三个词虽然词源相近,本义相似,但在西语中毕竟是不同的词汇,分属于不同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和哲学研究中也在逐渐拉开距离,还是可以考虑赋予其不同的译名。由于demonstrative约定俗成地占据了“指示词”这个译名,已难改变,我们只好将deictic译为“直指词”,这个译名选自沈家煊译克里斯特尔主编的《现代语言学词典》。[7]
对于范围最广泛的indexical来说,“索引词”是完全不合适的译名,无论是古汉语中的索引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索引,都不具有“指示语词”的含义和用法。实际上,语言学家虽然很可能是“索引词”译名的始作俑者,但现在用这个译名的语言学家并不多。在这里,我们把它改译为“指代词”,相应地,indexicality译为“指代”。之所以不循index(标志)而译为“标志词”,主要还是因为“标志”在现代汉语中离indexicals的“指示”和语境依赖这两个核心特征有较大距离,而“指代”则能够体现这两点。这个译名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吕叔湘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用的就是“指代”而非其他;虽然他没有明确说明用指代翻译indexicals,但他讨论的词汇均是汉语的indexicals。[8] (P1-2)
唯一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是“指代”一词常被用来翻译中世纪逻辑和语言学中的supposition(拉丁语suppositio)。不过,由于领域特殊,知之者寡,大概不会引起麻烦。
二、研究脉络
指代词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深入的研究还是于19世纪后期在语言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领域逐步展开的,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语言学界掀起了指代词研究的热潮。*国内的研究集中在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领域,代表性的著作如姜望琪的《当代语用学》,哲学领域可参见武庆荣、何向东:《索引词研究的逻辑哲学意蕴及其启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8)。[9](P190)本文将从语言学和哲学两条主要进路出发总结其脉络。当然,从指代词研究的缘起和发展来看,它更多地由语言哲学家主导,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参与,因此,严格区分哲学进路和语言学进路实际上十分勉强,我们只能根据研究者的主要领域来归类。
(一)语言学进路
在语言学进路中,对指代词的研究可分为历史起源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
在历史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布拉格曼(Karl Bragmann),丹麦语言学巨擘奥托·叶斯柏森,语言学大家、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雅柯布森。叶斯柏森在《语言本性及其发展》(1923)一书中,将这种因其意义随情境而变的语词称为移指词(shifter),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人称代词。[10]雅柯布森在其著名论文《移指词、语词范畴与俄语动词》(1956)中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给出了从皮尔士到布勒的概念流变史。[11] (P131-133)
雅柯布森首先给出了移指词的基本特征:如果不指涉已知信息(message),则移指词的一般意义无法确定。他进而根据巴克斯的研究[12]指出,皮尔士的指号三分法已经讨论了符号学的本质:象征根据惯例规则与所表象的对象相联系,标志则与其所表象的对象处于实存关系之中。关键在于,雅柯布森认为移指词将这两种功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属于指代象征(indexical symbols)一类。这恐怕是雅柯布森不用指代词、直指词这两个名称的原因。
在讨论了胡塞尔、罗素、布勒(Karl Bü ̄hler)的观点之后,雅柯布森认为,移指词不同于其他语言信码(code)的地方在于它们对给定信息的强制指称。这一点与雅柯布森的信码—信息分析方法关系密切。他认为这种指代象征词,特别是关系代词,在洪堡传统中被视为最基本、最原始的语言底层,但实际上却是信码和信息交叠的复杂范畴。
雅柯布森坚持使用叶斯柏森的移指词这个名称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例如,这一点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否有明确关联,另一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代词的结论与他十分接近。[13] (P195-230)又如,移指词这个名称此后在文学批评领域特别是叙事研究中广泛流行,拉康对这个词也特别有兴趣,用于分析主体或“我”[14] (P139),这也有必要结合起来思考。

概言之,正如费尔默(Charles Fillmore)所言,直指现象向语法理论提出了大量重要问题,有经验性的,也有概念性的和记号性质的。[16] (P26)迪塞尔研究了85种语言中的直指词,考察了直指词的形态学、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和语法化等五个方面。[17] (P1)当然,我们关注的主要还是语义学和语用学两个方面,因为指代行为是联结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一条纽带。
经过莱昂斯、利奇(G.Leech)、列文森、费尔默、努恩伯格等语言学家的努力,我们已经能够大致梳理出指代词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基本类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列文森在《语用学》一书中将指代词分为五类:人称的、时间的、位置的、语篇的(或文本的,discourse or text)和社交的(反映社会地位的,如敬语)。这五类基本上涵盖了指代词的主要类型。由于这些文献在国内语言学界已有介绍,这里从略。
(二)哲学进路
针对指代词的哲学研究,不需远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一章“感性确定性,或‘这一个’和意谓某物”中就有精彩的思辨。黑格尔用Aufzeigen表示我们所说的指示、指明行为。*英译“pointing out”,中译“指出”或“指明”。以下引文均出自该章。指明行为作为包含“我”、“这时”、“这里”的“这一个”(dieses,this),表明了感性确定性的辩证法无非就是这种确定性的一段单纯的运动史或一段单纯的经验史,而感性确定性本身恰恰就是这段历史:这一个东西是一个普遍者;不再是一个直接事物,而是一个折返回自身的事物*德文ein in sich Reflektiertes,英译文something reflected into itself,中译文或译为“回复到自身的东西”。这个措辞可与赖辛巴赫的“token reflexive word”(自反标记词)相比较。,或一个在他者存在中保持不变的单纯东西。这种辩证法的确可以回击源于经验主义的怀疑主义,亦可诠释公孙龙《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谜题。
无独有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开始,就从符号、指示(demonstration)和两种指示方式(指明与证明,indication and proof)入手,并在第26节通过区分本质上机遇性的(或偶然的)和客观的表达式,着重讨论了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当然,这些讨论与胡塞尔关于指明、知觉和命名的思考以及意义理论本身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研究者认为,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关于指代词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强调语言的指代用法至少包括两种实质上有区别的行为,即意谓行为和知觉行为;其二,说明了这两种行为是如何关联的,也就是说,二者的联系包含一种行为(事件)对另一种行为的单方面的存在性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发生在一种特定类型的复杂整体的语境中。[18]
黑格尔和胡塞尔关于指代词的论述并不是主流的指代词理论。相对于布勒和费尔默的理论对指代现象的心理学和功能性方面的关注,皮尔士、弗雷格、罗素、赖辛巴赫、维特根斯坦则更关注符号学—逻辑学方面,成为语言哲学关于指代词研究的典范。弗雷格和罗素关于专名、意义、指称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言,我们主要关注与指称关系(referential relation)相对的指代关系问题。
弗雷格讨论指代词的文献集中在《思想》(1918)一文中,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思想到底是什么(外部事物、心理表象还是客观领域)、思想与真的关系等问题,而包含指代词的句子,特别是包含“我”的句子,对于思想的客观性的表达造成了困难。用培里(John Perry)的表述就是:当我们思考自己时,我们把握的思想是其他人不可能把握的、不能交流的,但没有比不可交流的、私人的思想更不符合弗雷格关于意义与思想的观点了。[19]弗雷格的基本做法是用专名(以及给出专名对象的唯一方式)和摹状词来消除指代词。但培里却论证说,包含第一人称信念的句子无法消除这种对语境敏感的指代词。[20]第一人称信念问题经由埃文斯、麦克道尔、皮科克(Christopher Peacocke)、培里、大卫·刘易斯、斯托内克(Robert Staalnaker)以及更早的卡斯坦尼达(Hector-Neri Castaeda)等人的工作,已经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不过,也有人不认可这种流行观点,认为弗雷格早在1897年撰写但未发表的论文《逻辑》中就强调,第一人称、现在时等性质,只是语言的特征,而非思想的性质。[21]埃文斯也认为弗雷格对指示词的处理方式本质上是正确的。[22] (P71)
有一类指代词的重要特性就是自指(或译自反、自复),也恰恰是这些词吸引了哲学家的关注。罗素曾专门讨论了自我中心的特称词(egocentric particulars)。[23]这类词的特点是意义随着说话者和他在时间与空间中位置的不同而改变,其中“我”、“这个”、“这里”和“现在”是四个基本词项。自我中心特称词的特点是靠知觉而产生的,因为在只有物质的世界里不会有什么“这里”和“现在”。知觉对于事物是从一个中心出发的;我们的知觉世界是对公共世界的一个透视。在时间和空间中近的事物引起的记忆和知觉,一般比远的事物更生动、更清楚。在物理学的公共世界中却没有这种照明中心。这也恰恰说明为什么物理学通过消除感觉的个人性质的努力变得越来越抽象。[24] (P112-113)
赖辛巴赫将指代表达式称为自反标记词(token reflexive expressions),从而区别于使用专名、概念等词项的指称表达式。[25](P284-286)这个术语将自反性与标记(实例)—类型(token-type)的区分结合在一起,既强调当下指称的特点是利用指称对象在场的条件,也关注在非当下指称时,利用的则是先前固定的(fixed)指称,从而加强了言谈语境与固定指称语境之间的区别。标记(token)确定了自我指称的实例特性,因此,“我”可以定义为“说出该标记的人”,“现在”可根据“这一标记被说出的时间”来定义,“这个桌子”也可以定义为“由伴随这个标记的姿势所指示的桌子”,等等。对自反性的进一步研究,可参见培里提出的“自反—指称理论”(reflexive-referential theory)。在他看来,指代方式的重要性根本上在于它是自反性的最高形式,是通往自反性宝库的大门。[26] (P590)
如果说培里发挥了指代词的自反性,卡尔纳普的学生、以色列逻辑学家巴尔-希勒尔则着重从type-token这个同样源于皮尔士的二分法出发,在1954年的论文中讨论了指代表达式。[27]这篇论文大大促进了对指代词的研究。类型(type)是抽象语言单位,实例(token,此处不译作标记)是类型在具体场合的体现,像“我饿了”这样的句子,作为类型没有指称,只有作为实例才有。句子的指称是命题,但后来他认为指称实际上不是实例与命题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是实例、语境和命题三者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实例必须和语境结合才能指称命题,实例本身也没有指称。[28](P18)巴尔-希勒尔利用其理论进一步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特别是所谓语用学悖论的伪问题[29] (P376),如“我死了”这样包含笔者称之为践言冲突(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句子。[30]
当然,对指代词研究影响最为突出的非大卫·卡普兰的论文《论指示词》莫属。这篇论文系未竟之作,其中心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即流传,真正出版却是在1989年(并附有长篇补记)。[31]首先,这篇论文其实是一部大部头著作的草图,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指示词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其次,论文中富有原创性的思想俯拾皆是,无论是对直接指称问题的紧追不舍,还是关于内容与特征(content and character)的区分,都令人钦佩;再次,卡普兰展现出精细的分析能力和形式化技巧,在蒙塔古之后也给出了一套形式系统。
列文森认为,在语义学的哲学进路中,经由蒙塔古、卡普兰等人的工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将指代词处理为二阶事态,即从语境到命题内容的映射(函数),从而也是一种从世界到真值的映射(函数)。在蒙塔古的早期理论(“普遍语法”)中,直指表达式的内容被捕获的方式是从语境到内涵。语境即一套标志,涉及说话者、对话者、被指的对象、时间和地点等。在卡普兰的指示词理论中,一切表达式均有这种从语境到内涵的映射(即与命题相关的内容)。指代词“我”的意义就是其特征,即一种函数或规则,在每一个语境中可变地指派给个体概念,即说话者。情境语义学也是一种有影响的二阶理论。[32]话段(utterance)是从三种情境或事态方面被解释的:话段情境,对应于蒙塔古的标志;来源情境,处理其他由语境决定的指称,如复指;描述情境,对应于命题内容。这些二阶理论的核心性质是:指代词并不直接对所表达的命题有所贡献,也不对所说的内容和所描述的情境有所贡献。相反,指代词把我们带到个体、所指物面前,它们然后被置入所表达的命题或被描述的情境当中,或如努恩伯格所言:指代词的意义是复合函项,把我们从语境要素带到受语境限制的领域的要素,然后就溜走了。[33] (P104-105)
在《哲学研究》第43节中,维特根斯坦说了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对于‘意义’这个词的利用的诸情形中的一个大(large)类来说——虽然并非对于其利用的所有情形来说——人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说明这个词: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人们有时通过指向(point to)其承受者(its bearer)来说明一个名称的意义。”[34] (P40)虽然我们可以说“语词的意义在于其使用”是维特根斯坦的总体思想,但是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却非常谨慎,一方面特意强调意义即使用只是一大类情形而非全部,另一方面又明确强调了指向指称对象来说明名称意义的方式,这自然十分接近于指代词的使用。所以在第44、45节,维特根斯坦说:“因此,它们(名称)总是可以由带着指示手势的指示代词来代替。”“但是,这恰恰没有使得这个词(‘这个’)成为名称。相反,因为名称并非总是同指示手势一起运用的,而只是经由其得到说明的。”[35](P41-42)这种运用其实是普通的、日常的,在语言休假的时候,哲学问题便出现了:将名称—命名和指示词—意指神秘化。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指示的行为和指代词的使用,是我们以不同方式学习到的,我们不能给出一个我们称之为指向这个形状(而非这个颜色)的身体的行为,因此就说,一个精神的活动对应于这些语词。维特根斯坦不过是说,指示行为需要以大量的社会舞台布景和语言训练为前提,指代词的使用已经隐含地与某种分类能力相联系了,否则(比如说)我们无从分辨所指的是书还是书的封面或颜色。指代词的使用是遵循了语言游戏的规范性的行为,而不是名称与对象的、指示与对象的因果性关联。[36] (P461)
三、指代词的哲学问题
指代词研究首先得益于哲学家在语言哲学、逻辑学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而后语言学家的持久努力也为哲学创造了进一步思考的理论和材料。同时,指代性质也与非语言因素相关,如说话者的态度、语法与文化的互动,这也为多种视角的研究提供了汇聚的场所,包括哲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学等等。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指代词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之际,哲学能够进一步做哪些工作。
(一)指代词哲学研究的定位
如果我们延续对语言学的三分法,即语形学研究指号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指号与所指物的关系,语用学研究指号的使用者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语言学中,指代词研究大致属于三者交叉领域的一部分,即一种意义—使用关系,一种对意义的语境化研究。这部分领域最独特的区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系统,在其中说话人选择了自身的视角,将人称、时间、空间信息整合在所传递的消息中:中心人物是说话者,中心时间是说话人对信息加以编码的时间,中心位置是说话人编码时的位置。
布兰顿在《言行之际》中,力图建立分析的实用主义(analytic pragmatism),以拓展分析事业,其目标是在传统分析方案所关注的语汇(vocabulary)之间的经典语义关系之外,也考虑以语用学为中介(pragmatically mediated)的语义关系。[37] (P11)这种语义关系被称为“意用关系”,有两种基本的意用关系:行—言充分性和言—行充分性(practice-vocabulary sufciency 和vocabulary-practice sufciency),前者表明何种行为和能力能让我们驾驭某种语汇以表达意义,后者表明何种语汇足以明确某类行为或能力。*此外,还有“行—行”和“言—言”充分性(PP-and VV sufficiency),表示将一种行为阐释为另一种行为的充分性,或将用一种语汇刻画另一种语汇的充分性。参见Robert 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9。以此为基础,布兰顿给出了复杂的意用关系分析,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语汇展开的分析:逻辑语汇、指代词语汇、模态语汇和规范性语汇。这里择要讨论之。
布兰顿认为对指代词的理解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罗素、卡尔纳普、赖辛巴赫等人将指代词视为自反标记词(token-reflexive),指代词的使用是标记的实例化(tokening)的表现。如前所述,一个关于类型“现在”(now)的表达式就是该标记词的实例化,我们称之为“n”,而“n”可定义为或在语义上分析为“说出‘n’的时间”。二是20世纪70年代,培里、大卫·刘易斯、安斯康等人在模态和认知语境中研究指代词的用法,否定了前者,认为用指代词表达的东西不可能用非指代词等值表达。基于这一区分,布兰顿认为,尽管在语义学上,指代词和非指代词不可还原,但完全以非指代词项谈论如下活动是可能的:为了正确使用指代词,即为了说那些本质上的、不可还原的指代的东西,我们必须做什么。[38](P25)也就是说,虽然指代语汇不可能完全还原为非指代语汇,但是非指代语汇可充当指代语汇的充分的语用学元语汇(adequate pragmatic metavocabulary),即为了使用指代词汇而必须做的一切,均可以完全用非指代词汇来描述。[39](P56)
于是,布兰顿认为指代词展现了两种独特的推论行为(discursive behavior):在语义学方面,指代词是自反标记词的表达式类型,标记词的实例化所表达的内容依赖于实例化的语境;在语用学方面,指代词的使用能够具有特殊的语用学意义,即清晰的阐释能够认可实际行为所具有的承诺。布兰顿将这两种相互依赖的特征命名为卡普兰—斯托内克语义学和安斯康—培里语用学。[40](P56-57)布兰顿由此通过语义学上的阐释(explicating)和语用学上的详释(elaborated),表明指代词与非指代词之间的关键联系。这就是说,知道如何使用非指代词的人,原则上就已经知道为了使用指代词所需要做的一切。因此,我们能够理解非指代词,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指代词神秘化。
这里之所以要利用布兰顿的理论,是因为尽管该理论复杂而风格独特,但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对类型的恰当划分和对难题的精细阐释,的确有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二)指代词的哲学问题域
布兰顿的意用分析是对塞拉斯推理主义语义学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的综合和推进。在这里,我们主要在语言哲学领域中勾勒指代词的问题域,以下三个核心问题是最值得认真考虑的。
1.指代词使用的语言学—哲学预设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2节给出了一个原始的语言游戏,其中有语境、语言共同体、语词(非指代词)、理解标准、语词使用标准。第8节则扩展了这个语言游戏,增加了数字或字母词列、指示词、指示性手势和颜色色样四种新“工具”。维特根斯坦讨论道:“‘到那里’和‘这个’也是实指地教给人的吗?——请想象一下,人们可能会如何教人学习它们的用法!在此人们指向地点和东西,——但是,在这里,这种指向可能也发生在这些词的使用中,而并非仅仅发生在这种使用的学习过程。”[41](P14)
随后,维特根斯坦指出:“为了能够追问名称,人们必须已经知道了某种东西(或者能够做某种事情)。但是,人们必须知道什么?”[42](P29)
我们也可以套用这个问题:为了能够追问指代词,人们必须知道什么?必须能够做什么事情?当然,维特根斯坦已经给了我们以提示,这就是说,以语言游戏、语言活动、生活形式为出发点,而不是将“x表示y”、“x意指y”作为一般模型去思考。
我们可以提出一组基本设想:(1)指代词的使用是人类语言活动中重要且必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指代词的使用与非指代词的使用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非指代词的使用,我们无法掌握指代词的用法;(2)指代词的使用尤其依赖于我们使用概念的能力,如区分形状、颜色、状态等描述语汇上的分类能力,对于区分(时空)距离、作用等相互关系的能力,甚至运用概念进行推理、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做出承诺与承担义务的能力;(3)指代词的使用在语用学上也依赖于其他语用方式,如复指(anaphora,又译照应)。
在这里,我们以复指为例讨论指代与复指的关系。莱昂斯在《语义学》中认为,直指比复指更基本,在文本直指(textual deixis)可以看到代词的直指功能与复指功能的联系。[43](P667)布兰顿的观点则截然相反。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用整整一章讨论了复指问题,从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论述如何指认(pick out)对象谈起,着重研究了可重复标记(token repeatables)的结构。他的基本观点是,复指绝不只是言内设置(intralinguistic device),而是指称对象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复指在概念上优先于直指,因为指代词被理解为复指式启动器。指代词从复指的先行词中指认出指称物的能力,是其他标记词具有其确定对象的能力的必要条件。直指预设复指,一个标记实例要想具有指示词的意义,其他标记实例就必须具有复指依附语(anaphoric depen ̄dents)的意义;将一个表达式用作指示词,就是将其用作一种特殊的复指启动器。[44](P462)就指认个体对象、直接指称对象而言,如果不能够复指,则直指、指代就无法在语境中将对象意义固定下来,无法给出对象的坐标位置,因此也就无从实现直指的这一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布兰顿是正确的。不过,指代词仍然具有将一般信念与语境相联系的功能,并不总是或必须用作复指启动器;相反,当我们使用复指词时,就必须有复指启动器,其中会嵌入某种指代要素(不管是真正的指代词还是专名)。[45] (P168)在这个意义上,莱昂斯的观点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在这里,指代或直指与复指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案例,提示我们应当深入思考指代与其他语用要素的关系,无论是哲学的还是语用学的关系。
2.指代词的使用与个体对象的被给予方式
特定的个体对象如何在(认知性的)语言游戏中被给予我们?我们如何在语言游戏中指认特定的个体对象?一般说来,大致有四种方式:(1)弗雷格通过区分专名的意义与指称,以专名来描述并指称对象;(2)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通过(罗素式的)摹状词或(塞尔式的)簇摹状词来描述对象,从而指称对象,专名被理解为蜕化的或缩略的摹状词;(3)密尔—克里普克意义上的直接指称论,即专名作为严格指示词直接指称对象;(4)通过指代词直接指称对象(无须弗雷格意义上的Sinn),如卡普兰的“直接指称语义学”(the semantics of direct reference)。
自从克里普克批判了描述主义之后,弗雷格和罗素的理论基本上被严格指示词理论取代了。不过,严格指示词要求某一专名N在一切可能世界中均指称同一对象O,如果用模态词汇,可以说严格指示词要求N必然指称O,这种必然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描述主义揭示了在认识论上我们对专名与对象关系的把握,往往体现出我们对专名的实际使用。在特定语境中通过描述来指称,恰恰是我们通常的指称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1)指代词是否具有描述功能?(2)指代词能否直接指称?(3)如能直接指称,指代词指称的是什么?(4)指代词是否为严格指示词?为了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考虑指代词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倘若指代词是严格指示词,则“万物一指也,天下一马也”,指代词的最大特点就是语境依赖性,因此,不可能成为克里普克意义上的严格指示词。这种语境依赖性恰恰要求我们通过详细阐明语境来确定指代词的使用,对语境的阐明自然要借助指代词所具有的语用学意义上的表达性引导作用(pragmatic expressive bootstraping),同时也要摆脱指代词,在用非指代词详释该语境,阐明为了使用指代词,我们必须要做什么、遵循何种习惯、具备何种能力。
阐明语境就是阐明指代词的用法。指代词的用法与语境中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是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我们也许可以在语言学上对指代词的描述功能、直接指称功能进行考察和分析,但在语言哲学层面上,必须在语用学层次上将指代词的使用理解为标记词的实例化行为(tokening),从指代活动而不仅仅是指代词出发理解直接指称的行为,否则甚至会导致“指代词悖论”。例如:
“克里特说谎者”。他也可以写下“这个命题是错的”取代“我在说谎”。回答可以是:“好啊,不过你意谓的(mean)是哪个命题?”——“唔,这个命题。”——“我明白,不过提到的(mentioned)是那里面的哪个命题?”——“这个。”——“好的,指的(refer to)是哪个命题呢?”如此等等。这样一来,除非他转到一个完整的命题,否则无法说明他意谓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说:根本错误就在于,我们认为像“这个命题”之类的短语,似乎能暗指(allude to)其对象(从远处指向它),却用不着充当其代理(go proxy for it)。[46] (P118-119)
指代词,至少部分指代词具有明确的语义内容,如今天、明天、昨天,似乎具有某种指称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一套相应的语用学框架作为中介,指代词无法直接指称对象;即便说话人掌握了一套关于某指代词的语用学知识,如果此人不具备使用此类词汇的能力和习惯,不经过语言共同体内的学习和练习,也不能够恰当地指称言外对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包含指代词的语言游戏的基本类型,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一般而言,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包含指代词的语言游戏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距离定位系统”(distance-oriented systems):所有指代词均指示指称对象与直指中心的相对距离。[47](P39)这种类型又可细分为:(1)时间距离系统,典型的时间距离指代词是现在、过去和将来,其直指中心是“现在”(now)。(2) 空间距离系统,典型的空间距离指代词是这里、那里,其直指中心是“这里”(here)。(3)文内距离系统,典型的文内距离指代词是上述(above)、见下(the following)。第二种类型是“人称定位系统”(person-oriented systems):说话人用指代词指示邻近听话人的指称对象。这种类型自然是以“我”、“你”、“他”为典型的,其中“我”是当仁不让的直指中心。
3.指代词与语句的真值条件
直陈句的真值条件通常包含该句子的逻辑形式和诸词项的语义内容,但对于包含指代词的语句来说,其真值条件必须强调语句及其词项的语境敏感性和依赖性,而指代特性恰恰是语境依赖性的主要表现(此外还有含混和附带特性)。因此,对于这一类句子的分析,真值条件语义学似乎应该让位于真值条件语用学。但是,在这里,出现了泛指代论(indexicalism)与真值条件语用学之间的分歧。
泛指代论认为,指代表达式除了包含明显的指代词外(如“我”、“这里”),还包含隐含的指代词。泛指代论者坚持真值条件语义学,主张即便单凭纯粹的语义知识本身不足以确定直陈句的真值条件,只要附加以语用方式提供的具体的必要信息,就能让纯粹语义知识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在不完全决定论证(under-determination argument)中,必要时用某些隐含的指代表达式就可以说明真值条件的语境敏感性。真值条件语用学论者则既反对纯粹语义知识外加语用学必要信息的主张,也拒斥对隐含指代词的使用。[48] (P438-439)
指代词的语义泛化的确会造成麻烦,如果像“邻居”、“敌人”、“朋友”、“附近”等等均可称为隐含的指代词,那么几乎所有词项原则上都容易被纳入指代行为,因其词项意义(特征)对其外延(内容)的确定,仅仅相对于所发生的语境。[49](P115)这个问题类似于言语行为理论中关于践言话段(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讨论。[50]
包含指代词的语句中最为独特的一类是包含第一人称指代词的语句。虽然使用“我”这个指代词并不等于使用“我”或“自我”这样的概念,但这个指代词的使用却很可能是关于自我中心特性、自我知识、自我意识、唯我论、第一人称信念等主题的起点,每一个主题都值得在语言哲学层次上深究。同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提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名称?是不是描述词项?当然,也包括“我”是不是纯粹指代词。
在语言哲学对这些主题的讨论中,涉及第一人称信念问题较多,这在前面已有所涉及。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按照斯托内克的概括,是因为关于信念的传统理论认为:(1)信念是有生命的主体与抽象对象(即命题)之间的关系;(2)命题具有真值,其真值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变。[51] (P131)显然,第一人称信念语句因其信念状态的主观性而无法保证命题的客观性、命题的“真”。在第一人称信念的研究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有三个理论:佩里的涵义—思想理论、刘易斯的涉己态度理论和斯托内克的命题概念理论。[52] (P1)这些理论深化了弗雷格提出的第一人称信念问题的讨论。
以上三个方面只是指代词的哲学问题中基础性的、最受关注的部分问题。此外,指代词的概念性问题、指代词语言游戏的类型分析、指代行为的整体性与规范性等问题,均有待深入讨论。更重要的是,围绕指代词,特别是核心指代词,我们期待着集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哲学研究。
[1][4][43] John Lyons.Seman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 Tony Jappy.IntroductiontoPeirceanVisualSemiotics.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2013.
[3] Charles Hartshorne,and Paul Weiss(eds.).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vol.3.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5][33] Laurence Horn,and Gregory Ward(eds.).TheHandbookofPragmatic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6][28] 姜望琪:《当代语用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克里斯特尔主编:《现代语言学词典》(第四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9] Barbara Kryk.OnDeixisinEnglishandPolish.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Peter Lang,1987.
[10] Otto Jespersen.Language,ItsNature,DevelopmentandOrigin.New York: Macmillan,1949.
[11] Roman Jakobson.SelectedWritings.vol.2,The Hague: Mouton,1971.
[12] Arthur Burks.“Icon,Index,and Symbol”.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1949 (4).
[13] Emile Benveniste.ProblemsinGeneralLinguistics.Coral Gables,Fl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
[14] Jacques Lacan.TheFourFundamentalConceptsofPsycho-Analysis.Harmondsworth: Penguin,1979.
[15] Karl Bühler.TheoryofLanguage:TheRepresentationalFunctionofLanguage.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Co.,2011.
[16] Charles Fillmore.LecturesonDeixis.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1997.
[17][47] Holger Diessel.Demonstratives:Form,Function,andGrammaticalization.Amsterdam: J.Benjamins,1999.
[18] Kevin Mulligan and Barry Smith.“A Husserlian Theory of Indexicality”.GrazerPhilosophischeStudien,1986 (28).
[19] John Perry.“Frege on Demonstratives”.PhilosophicalReview,1977 (4).
[20] John Perry.“The Problem of the Essential Indexical”.Nos,1979 (1).
[21] Edward Harcourt.“Frege on ‘I’,‘Now’,‘Today’ and Some Other Linguistic Devices”.Synthese,1999 (3).
[22] Gareth Evans.“Understanding Demonstratives”.Palle Yourgrau(eds.).Demonstrativ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3] Bertrand Russell.AnInquiryintoMeaningandTruth.London: G.Allan and Unwin ltd.,1940,Chapter seven.
[24] 罗素:《人类的知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5] Hans Reichenbach.ElementsofSymbolicLogic.New York: Macmillan Co.,1947.
[26] John Perry.“Indexicals and Demonstratives” .Bob Hale,and Crispin Wright(eds.).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Language.Oxford: Blackwell,1997.
[27][29] Yehoshua Bar-Hillel.“Indexical Expressions”.Mind,1954 (251).
[30][50] 韩东晖:《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范式的重新奠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3)。
[31] Joseph Almog et al..ThemesfromKapl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2] Jon Barwise and,John Perry.SituationsandAttitudes.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83.
[34][35][41][4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6][44] Robert Brandom.MakingItExplici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7][38][39][40] Robert Brandom.BetweenSayingandDo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5] Pirmin Stekeler-Weithofer.ThePragmaticsofMakingItExplicit.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08.
[46] Ludwig Wittgenstein.Zettel.Oxford: Blackwell,1981.
[48] Lenny Clapp.“Three Challenges for Indexicalism”.Mind&Language,2012 (4).
[49] Philippe de Brabanter,and Mikhail Kissine.UtteranceInterpretationandCognitiveModels.Bingley: Emerald Group Ltd.,2009.
[51] Robert Stalnaker.ContextandCont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2] 周允程:《第一人称信念的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责任编辑 李 理)
On Indexical
HAN Dong-hui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Beijing 100872)
Indexical is linguistic expressions whose references shift from context to context.Indexicals,deictic,and demonstratives are among such kinds of expressions,yet the Chines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se terms are rather confusing and therefore need to be rectified.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indexicals,namely,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ones.Three fundamental problems are included in the later approach and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the linguistic-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s in the use of indexicals,the use of indexicals and the way of picking out individual objects,and the truth-condition of the sentence with indexicals.
indexical;contexualization;demonstratives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当代西方哲学重大问题研究”(10XNI020)
韩东晖: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