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容(小说)
西维
花容(小说)
西维
1
我常常去肯德基上厕所。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四面封闭,只有我一个人。
出了厕所,洗完手,我对着镜子理了下头发,它们看起来像是正准备过冬的杂草,黄而且乱。当然,现在还是夏天,街心花园里的草坪碧绿柔顺。园林工人修剪草坪时散发出的气味我很喜欢,那是这城市中为数不多的让人闻了可以有好心情的味道。
我沾了点水到头发上,用手指将它们压平整。这下,它们似乎好看了一些。很快,镜子里出现了另一张脸,涂了一层精致的脂粉,像玫瑰花一样的脸。那个年轻女人一边洗手一边看了看我手边的那堆东西:一捧玫瑰花。
玫瑰花一朵朵地,包在淡紫色的玻璃纸里。我在花上洒了点水,花瓣顿时水灵了起来。身边的年轻女人还在补妆,我洗好手离开,走到拐角处,往镜子里看了她一眼,她恰好也乜斜了我一眼。我不喜欢她的眼神,那不是好奇,而是不屑。
“先生,买朵花吧!”
“不要。”
“先生,你女朋友这么漂亮,买朵花送给她吧?”
“不要不要。”
我跟了那位中年男人一段路,他有些不耐烦了。他生气,却不好发作,阴沉着脸继续朝前走。
“先生,你不会连花都不舍得送给她吧,这么漂亮的小姐。”我继续跟着他,紧贴着他的裤腿,形影不离。
“这么漂亮的小姐,你不送花给她,会有别人送的呢。小姐多漂亮。”我转身又站到了男人的跟前,挡着他,把一支玫瑰高高举起,伸到他的鼻子下。玫瑰娇艳欲滴。这些花早晨刚到,还很新鲜。
“先生就送一朵给她吧。小姐都不笑。你送给她,她就笑了。小姐笑起来肯定很好看。”我嘴角上扬,眉眼舒展,展开玫瑰花般的笑容,看着他们两个。
“好吧好吧!受不了你了。”那男人终于从上衣口袋掏出钱包。
“多少钱?”
“十块一支。”
男人翻着钱包里的钞票,从里面挑了旧的钞票。
付了钱,男人举着花,头转向身边的女孩,对着她笑了笑,女孩也笑了笑,接过花,插进背在肩上的大号单肩包里。包很深,花蕾露在了外面。
“这小丫头还挺厉害的。”女孩说。
“这些外地小孩,最难缠了,卖花,偷东西,什么都干,出门要小心你的包……”
他们的声音在进到商场的大门后才彻底从我耳朵里消失。
我对着商场的大门恨恨地骂了两声,在地上吐了点口水,来发泄我的情绪。然后离开,继续在一对对衣着鲜亮,慢悠悠快活地在街上闲逛的人中寻找第二个会掏钱买我花的人。
天快黑时,我在春蕾小学旁边等妹妹冬兰。每天约好在这里等对方。
她过了很久才来。
“姐,看,还有这么多。”冬兰沮丧着脸,看着手里剩下的花。它们已经没什么神气。花瓣边缘的颜色变得很深,因为脱水而微微卷曲。
2
老大还是一如既往的小气,说,我们两个只卖完了一个人的花,所以要饿一个人的肚子。
这个秃头窄肩膀的讨厌鬼今天的心情还是不错的,叫烧饭的刘大妈炒了几个小菜,自己出门买酒去了。想必是打牌赢了钱,要么就是那几个臭小子今天摸了大鱼。应该是那几个臭小子今天顺了风。我想起了阿丁在门口抽烟的得意样,他瞄了一眼我们手里剩下的花,吹了个响亮的口哨。
男孩子都喜欢吹口哨,尤其是阿丁这样的小混混们,他们把口哨吹得天花乱坠。天花乱坠,没错,吹口哨就像是在吹牛。他们每天都在吹牛,吹自己掏了哪个有钱人的腰包。我倒是希望他们每天都挨揍。他们不是一群讨人喜欢的家伙。
在厨房盛饭的时候,我把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又压了压,再继续添一点。出门时,刘大妈把我叫住了。
我准备接受她的训斥。老老实实地站着不动。
“别的也没了,这是早晨剩下的。”刘大妈塞给我一个馒头。
“谢谢大妈。”
我端着碗拿着馒头飞快地离开,生怕她反悔。平常,刘大妈总是说我们吃的太多,用一些她家乡的方言来骂我们。刘大妈五十出头,肥肥大大的块头,声音又哑又粗,夏天露出的小腿上布满了蚯蚓一样的红色的青色的凸起的血管。走路像只摇摆的老鸭子。她和老大是本家,也是同村的,老大让她管我们的吃喝还有其他的杂事。秃头讨厌鬼每个月会给她一些钱,我们吃的多了,剩下的就少了。我知道她在偷偷的攒钱。给我们买吃的穿的时候,总是拼死命讲价,哪怕讲下了一分钱,她都会笑开花。
听说在发育的人都很能吃,我常常觉得饿。饭菜油水少,刘大妈炒的萝卜块像是水煮的,白白的石头一样大块大块地堆在一起。
我们睡最北边的那间小屋子,一开始是四个人睡,另两个女孩去年和老大的一个同乡去了别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现在只剩了我们俩。这屋子看起来阴暗潮湿,夏天却不凉快。地底下的潮气都蒸了上来,窗户很小,它们出不去,就在屋子里游来荡去,我们就像是睡在蒸锅里,下面是沸腾的锅水。
晚上,我睡不着,躺在床上不停地翻身,听着妹妹轻微的呼吸声。肚子空荡荡,还是饿,我起来喝了点水,翻身的时候,总是听见咕咚咕咚的声音,从肚子里传出来。
在咕咚咕咚的催眠曲中,我终于睡着了。
迷迷糊糊地,我做起梦来。不是每个梦都能记得住,而印象深刻的,通常是不好的梦。因为总是会被吓醒,因而记住了梦里的东西。
我又梦见了爸爸、四妹、大姐,还有冬兰。
梦的内容每次都差不多,我和冬兰是一伙,我们被人追,要么是去执行一项命令,逃亡。奇奇怪怪的。爸爸是我的敌人,有时候在梦里我们相互厮打,我抡起棒子敲过去,他的头就出了一个洞,洞很深,不停地汩汩地冒着血,他一边流着血一边继续和我打,直到身上出现许多的洞,每个洞都鲜血滚滚。这真是恐怖的场景,如果不醒来,就在梦里没完没了地追逐着。
这次也还是一样,更多的人扭打在了一起。冬兰又不停地哭。
被冬兰摇醒时,我累得满身都是汗。
“姐,你刚才喊了。哎呀,出了好多汗。”
“做了个梦,梦见爸爸了。”
“爸爸。”妹妹的声音抖了抖。
“你想家么?”
她摇了摇头。
“我抱着你睡吧。”
“你不怕热?”
“不怕。”
她挨了过来,将瘦瘦的、软软的身体贴到了我的身上。
3
一个炎热的下午快结束的时候,雨水说来就来,哗啦啦地从天上往下倒。我跑进最近的肯德基避雨。
衣服湿了,头发也是,刘海紧贴着额头。我对着洗脸台的镜子用手指梳着头发。放在台子上的花突然被一个影子碰到了地上。那个靓丽的影子很快推开门进了卫生间。留下了浓浓的香水味。
我转过身,要把花拾起来。低下的头刚好碰到另一个人的头。
“给你。”
他把他捡起的花交到我的手里,和我手上的几支并成一束。
我的面前是一身干净的校服。春蕾小学的校服。那学校就在这附近。
“谢谢!”
“不客气。”他露出了略带腼腆的微笑。
随后,我的目光跟随着他的背影,看见了他的同伴在另一边跟他打招呼。他的同伴买了很多东西,端了满满一盘子。
我找了张空桌子坐下,人不算太多,有不少学生在这里打发时间,他们并不急着回家。上了一天的课想必是饿了,都大口大口地吃着东西。空气里都是炸鸡块的味道。
雨渐渐小了。我站到门口往外看了看。
我担心冬兰,怕她淋了雨着凉感冒。那真糟糕。
妹妹身体不好,因为早产,一直是弱不禁风的模样。她和我一样,出生不久后就被送到外婆那里养。外婆从妈妈那接过她的时候,她就像只小老鼠。外婆自己从山上采来草药帮她调理,从小河里捞来小鱼,用它们熬成奶白色的汤,给妹妹吃。都是二个手指头宽的像柳叶一样的小鱼,外婆说这种鱼熬汤营养好,不用放盐,只喝汤,不吃鱼,鱼已经没了味道。
妹妹就这样活了下来,身体依然很差。外婆死了后,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妹妹那柔弱的身板便没了照顾。就像刚抽出的嫩芽从春天一下到了严冬。
远远地看见了妹妹的身影,她穿过了一条马路,向这边跑来,正穿过一个小花坛。她的步子太急,滑了一跤。
有人将她扶了起来,白色的校服,远远的影子,他站在妹妹身边,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不多久,妹妹打着一顶浅蓝色的雨伞,到了我跟前。她的裤子留了两团湿漉漉的黄泥。
妹妹兴奋地和我说起刚才的情况。她的语速很快,急不可耐地要把刚才的事告诉我。同时,她小心地将收起的折叠伞伞面弄平整,将一侧的带子扣好。她被雨浇透了,头发和衣服都贴在了身上。但她顾不得那么多,她的眼里只有这一把漂亮的浅蓝色雨伞。
“他竟然把伞给了我呢!”妹妹又重复了这句话。
我对着她笑了笑。
“他看起来好好。他是个很好的人吧?”
我点了点头。
“姐。他是春蕾小学的学生呢!”
“嗯。”
“穿着校服,那个图案我认识的。”
妹妹不识字。但是她记性很好,她已经将那个男孩的样貌记下来了吧。
她不仅把那个男孩的样貌记下来了,还说明天要去春蕾小学把伞还给他。
我们在近门口的位置上坐下来休息,妹妹今天的任务都完成了,再加上那把蓝色雨伞,她显得很开心,左顾右盼地,往收银台那边望了望。她掏出衣兜里的钱,告诉我,今天有个人一下子买光了她手里的一捧花,还多给了她几块钱。
“那个……”
“嗯?”
“够不够?”
她将那一团钞票塞进了我的手里。她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应。
于是,我们第一次吃了蘸了番茄酱的薯条,是酸酸甜甜的土豆味。
4
晚上回去的时候看到了青玲姐。她更漂亮了,烫了头发,涂了口红。
青玲姐在和我一样大的时候做着和我一样的事。和我们不同,她和阿丁从小就跟着老大。老大很喜欢他们两个,阿丁手脚快,青玲姐则漂亮。
“秋兰你越来越好看了。”青玲姐见了我说。
“青玲姐才漂亮呢。我哪有。”我身上的衣服,都是地摊上最便宜的。哪里“好看”?
“我说好看就好看。以后会更好看。”她看了老大一眼。秃头讨厌鬼朝她笑了笑。
青玲姐带了不少吃的东西来,一一分给我们。她还送了阿丁一套帅气的衣服,秋天可以穿。
因为青玲姐来了,我们难得地吃了一顿好的。吃饱了,连睡觉都香。可以说,我每天都盼着她来玩。
我和青玲姐不算熟。没看见过她多少次,但我常常想起她来,好像她就在我脑子里的某个角落似的。细长的眉,白白的脸,黑黑的长发。
除了冬兰之外,青玲姐是唯一一个愿意和我聊天的人。她愿意听我说的话,也愿意对我笑。我相信她对我笑是真心的。她第一次见我就弯下腰,问我叫什么名字,她把我的名字记住了,过了两个月我们再碰到的时候她一下子就叫了出来。
她挺安静的,大部分时候就坐在窄小的院子里,等阿丁回来。她来基本都是找他的。我们这样一个城中村破旧的农民房中也没什么风景可看的,她一个人呆着,抽着烟,想着事情,要么就翻一本报亭里买来的讲穿衣搭配和化妆的杂志。她还送了一本给我。
“青玲姐今天穿的衣服真好看。”冬兰说,她躺在床上,还没睡着。
“她越来越瘦了。”
“是很忙吧?是比我们辛苦么?”
“不知道,在那个地方上班应该比卖花要好很多。至少有钱。”
“真的么?什么地方?”
我该怎么和冬兰解释呢。解释一个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地方,我也只是知道人们是怎么叫它,那个叫夜总会的地方,看起来像个酒馆,人们晚上在里面喝酒、玩乐,醉醺醺地出来。门口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
青玲姐穿着漂亮的裙子,她的腿长长的,踩着高跟鞋,她从那个闪闪发光的大门里走进去。
想起这样的场面,我的心里是紧张的,好像是我自己走进那样一个奇怪的地方似的。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肚子咕咕地响了几声。
吃多了也一样的难受,肚子胀胀的,只要坐起来,肚子就像块要沉下去的石头,连着皮肉往下拽。不舒服。隐隐作痛。
冬兰不久就呼呼地睡着了。我也只有躺着,平躺着,肚子的感觉才好一些。
青玲姐现在在干什么?也和我一样睡不着么?
早晨,我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脸,一抬头,就看见青玲姐从阿丁睡觉的屋里开门走出来。她的头发乱乱的,从两侧垂了下来,遮了她大半个脸。
“秋兰早啊!”青玲姐向我打招呼,没化妆的脸显得很苍白,又像是昨晚没睡好。
“青玲姐怎么这么早。”
“睡不着,就起来了。”
“青玲姐你太瘦了?你应该多吃点的。”
“瘦了好看。胖了就不好看了。”青玲姐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脸。

5
春蕾小学放学时,妹妹总是等在校门口对面的马路。她等那个男孩子,把伞还给他。
她可能只是想再见见他吧。她站在小学门口,隔着一条马路,远远地等着。
妹妹没有上过学。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我教过她,她写得挺认真,但还是歪歪扭扭的。妹妹每次写完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奇怪,那三个字竟然就是代表她自己的。名字就是代表一个人,我第一天上学时,老师让我们练习写自己的名字就这么和我说。我把这话告诉了妹妹。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写自己名字的机会。
学生们像潮水一样从那扇大铁门涌出,他们不太会注意在对面马路上站着的那个穿着土气的小女孩。我的妹妹。他们三五成群,有些被家长接走,有些则自由自在地,要在回家之前赶紧找些好玩好吃的东西。而我的妹妹,则要在这群跑动跳跃的身影中寻找出熟悉的那个。
她一直没看到他。
天气很快就凉了下来。
每次换季的时候,妹妹都要得感冒,感冒严重时,会心口疼,心胀得像是要裂开,从皮肉里钻出来。每次犯了病,她根本不敢躺下来,一躺下来,就像心要飞出来一样,胀疼得更厉害。即使是这样,我们依旧还是要干活,秃头鬼才不在乎这些。他什么也不在乎,除了钱。
妹妹站在春蕾小学斜对面,她坐在公交车站的雨棚下,打着喷嚏。天还下着小雨。这秋天的雨,像银针一样密,毛茸茸地覆在头发上、皮肤上、衣服上,不像夏天的雨那么猛烈,却是很凉,一层一层地凉进皮肉里。
我喊着她的名字,飞快地跑了过去。
她却大叫了起来。
“他,他!”妹妹一只手指向前方的校门。我朝着她手指的方向在人群中努力分辨着。
“哎!”妹妹挥着手,要跑过马路。
我紧紧地跟了上去,在马路中间拉住了她的手。车子飞快地从我们跟前开过,丝毫没有让我们的样子,司机按着喇叭,加大油门,好像就是为了让我们心惊肉跳。直到右边路口的红灯亮起,车流停了下来,我们才顺利地走了过去。
那个男孩子,早已经拉开一辆黑色轿车的车门,和同伴们告别,离开了。妹妹跟着那辆轿车跑了几步路,便蹲在路边,不停地咳嗽。
她捂着胸口,看起来很痛苦,脸色苍白。
我抱着她,抚着她的胸口,又拍着后背。就这样蹲了很长的时间。
第二天,雨已经停了,湿漉漉的地面在一夜间变得干燥。好天气又来了。天气好的时候,人的心情就会变好,他们会出来逛街,玩乐,自然,我的生意也会好一些。
要是妹妹的病也像这天气,突然就好起来该多好。我一边卖花一边担心着她。她的咳嗽越来越厉害,心口也越来越难受。早晨起来摸了摸她的额头,微微发烫。
她感到难过,这种难过不仅是身体上的。她说,她在马路中间朝着那个男孩招手的时候,他是看见他的,她的眼睛看向他,他的眼睛也看向了她。可他没有停下来,车子很快就开走了。他没有等她。他可能已经不记得她了。他怎么能像她一样一直记得她呢。她和他是那么的不同。她知道,很明白,他和她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他记得,但是故意不停下。他会是故意的么?妹妹昨晚总是这样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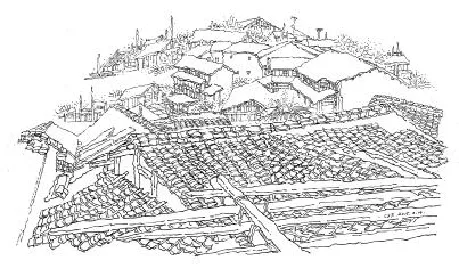
我只是想把伞还给他。妹妹重复着这句话。
因为要照顾妹妹,我早晨出来晚了点。在我软磨硬泡地恳求下,刘大妈同意帮我照看着她(老大对她的生病很不满,认为这样影响他赚钱了),并煮一锅姜汤帮她驱寒。
出门前,青玲姐来了。她招呼住我,给了我一袋吃的。说是从马来西亚带来的芒果干。她竟然出国了。出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不禁有点羡慕她,加上得到的那一大袋礼物,还有她光鲜而又漂亮的衣裳,她脖子上一晃一晃、一闪一闪的好看的挂链,我差点就把妹妹生病的烦恼给忘记了,着实是开心了一小会,和她说了几句话。
“青玲姐你是出国玩么?出国旅游好羡慕。”我想秃头老大都不一定能去得了。
“嗯。是去工作。挺累的。”青玲姐摸了摸我的脸。
“你给每个人都带了东西。你真好。”我看了看她手里大大的拎袋。
她笑了笑,又去了阿丁的房间。她将一个漂亮的盒子藏在了阿丁的枕头下。她喜欢阿丁吧。那个小混混。
可她也给所有人带礼物。她总是会买许多的东西给我们。有时候我觉得她简直像天使一样。尽管刘大妈私下里说起她,总是会带着那种表情——对那种工作表示厌恶和不屑的表情。
她为什么总是买这么多东西给我们?
6
我卖力地卖着花,口舌如簧地和人们周旋,如影随形地贴着那些被女人挽着胳膊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男人。我想着要早早地回去。
姐,你回来了!冬兰用已经不那么沙哑的声音喊我。这样的话,多好。
回到住处,我急急地奔进大门,听到了她喊姐姐,却是惊恐的哭腔。
她的恐惧一下子穿进了我的身体里。我扔掉手中剩下的几枝花,冲了过去。
声音是楼上来的。我心里一阵阵发虚,身体一阵热一阵凉。我觉得害怕,想着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祈祷。
两个迎面而来的小混混满脸不在乎地吹着口哨下了楼。可我没精力去讨厌他们。我只想马上去看妹妹。
就是前面那扇门,妹妹的哭声仍在继续。
“冬兰!”我喊着妹妹的名字,踢开了门。门只是虚掩着,我用的力气太大,让我差点摔倒。
在木板床和那个旧衣柜夹成的角落,她被绑在了那里,两块旧布条将她细得即将被折断的手绑在了床架上。她的上衣被脱掉了,长裤也被脱掉了。她的头发凌乱,扎头发的蓝色橡皮筋已经褪到了辫子的末尾,快要掉了下来。她哭着,姐姐姐姐。可我到了她的身边,她却用脚蹬我。她差点连我都不认识了。她的眼睛肿了,两片厚厚的眼皮黏在了一起。粉色的毛衣团在了一起,被人踢到了床底下。格子长裤在衣柜的镜子下。它们脏脏的,被踩踏上了脚印。
我不停地叫着妹妹的名字。冬兰冬兰。我哭着将绑住她的布条解开。它们绑得太紧了,像是和床黏在了一起,我的指甲都抠裂了,手上起了泡,却感觉不到疼痛,我只想把这张床敲得稀巴烂,放把火把房子烧了,然后带着冬兰逃跑。我手忙脚乱地帮她把衣服穿上,她却仍旧缩在角落里,不肯动,不肯出来。只是哭。我只能抱着她,拍她的肩膀。她的身体在发抖。她的脖子冰凉。
阿丁靠在门边,手里夹着烟,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只是个小小的惩罚,他们没对她做什么。”
“混蛋!”
“她太小气了。我们只不过拿了她一袋芒果干,她就追了上来,还咬了我一口。”阿丁伸出手臂,挽起右手的袖子,上面有两排小小的牙齿印。
“应该把你的胳膊整个咬下来!”
“神经病!”阿丁低低地骂了句。
妹妹的一只鞋子不见了。我找鞋的时候,阿丁已经不在了。楼下传来几嗓子跑调了的歌声。我走到走廊,继续找着那只鞋子。我翻着门口的垃圾桶,然后抬起头,发现它在楼下,阿丁的脚下,鞋子被他们踢来踢去。他们怪叫着,唱着跑调子的情歌。
很快,刘大妈养的那盆吊兰便飞到了楼下,砸在阿丁身旁的围墙上,弹出来的瓦片,斜擦过他的右边的眉骨。
再偏一点,就到眼睛里了。怎么不再偏一点?
“你怎么不去死啊!”我朝他喊。
7
我的妹妹,冬兰,尽管经历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总还是对一些事有天真的期待。
小的时候,她问我父母什么时候会来把我们接走。外婆什么时候从集市上回来,能带来什么好东西。外婆死的时候,问我她什么时候会再醒来。
我带着她逃跑,离开那个并不善待我们的家,并不友善的姐妹,我们混进车站的人群,偷偷爬上远去的火车。
我带着她辗转了大大小小的城市,我们流落街头,对着路人说着好话乞讨。
她跟着我,好像我能给她带来美好的生活。
她跟着我,把一朵一朵的玫瑰花卖到姑娘们的手上。
她跟着我,就像以前,外婆还在的时候,我们在村子里的河里抓虾,她拎着网兜,等着我把虾从石缝里摸出来,一只只放进去。
——姐姐,你真厉害!
——它们太笨了。真好抓,你试试!
——要夹我手指的,怕疼。
——不会的,你这样,轻轻地把手伸进这石头缝里。你看。就这样。
——这样?
——……
——啊!好疼,吓死了,吓死了,我再也不弄了!
——胆小!
——啊!不要用水弄我呀,衣服都湿了,外婆要骂的。姐姐!
——哈哈哈哈……
我从没想过,她哪一天会离开我。
8
那个女人在医生的办公室,呆了很久,她说的话我几乎可以背出来。我等着她离开,然后我再进去,和那个中年男医生说一些和她一样的话。
我抱着一个布袋子,里面是妹妹的衣服、裤子,她现在穿着医院的衣服,她自己的衣服都被换下来了。布袋子里还有那把蓝色的雨伞。可能还有一些妹妹喜欢而且很在意的东西,可我没时间将它们都收拾走。
最后一次去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跟着警察进去的。
那天我把阿丁的脸弄伤之后,他们抓着我甩了几个耳光,等到老大回来,我向他告状,结果是我被扣了当晚的晚饭。刘大妈什么话也没说,她那又粗又哑的嗓门比什么时候都安静。之后我找她问起当天的情况,她告诉她在睡觉,她什么也不清楚。“我一醒来,就看见你把我的花盆给砸下去了。”她的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好像是她的什么亲人被我突然砸碎了。我知道我和她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再不和她提那件事,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和她说好话,说我出去干活的时候请她照顾好我的妹妹。其实我一点也不信她,可还是和她说这样的话。
之后的几天,妹妹的情况越来越坏,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连我叫她都没有反应,像死掉了一样。我在大街上卖花,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妹妹。我恨不得抓住那个买了我花的人,和他说,“求求你,救救我的妹妹吧,她快死了。”我差一点就说出口了,要不是他们总是冷冷地有点厌恶地看着我。他们不喜欢我,讨厌我,怎么可能愿意帮助我?我根本没办法安心卖花。这街上来来往往的这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要避开我。我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我的妹妹快死了,我却还站在大街上,异想天开地想着是不是可以求助某个陌生人。
可我只能求助于陌生的人。
我站在大街上,想着去抱住那个男人的腿,他很年轻,有一张看起来挺善良的脸。他把刚才在路上摔倒的小男孩扶了起来,男孩的母亲一边整理小男孩的衣服一边和他说谢谢。或许,就是他?我跟着他,心里忐忑不安,想着去还是不去——就像每次卖花那样,去抱住他的腿。可如果他被我吓倒了怎么办?他被我吓倒了,把我推开,跑掉了。我又要等多久,才能遇上另一个?
我不再想到玫瑰花,虽然它们都躺在我的怀里,我一朵也没有卖出去。它们很快就干巴巴的,好像要枯萎了。我不再想到玫瑰花,我想到我的妹妹,她正躺在床上,我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这种迫切却让我失去了勇气,我犹犹豫豫地,跟了整整一条街,在拐角处,终于冲上前去,抱住了他。
他的确是被我吓了一跳,但他最后把我领到了警察那里。
医生的办公室不时有人进去,女人还没出来,一个男人又进去了,没多久,那女人就出来了。她看了看等在门口的我,抹了抹眼泪,我能感觉出她眼里的无助和痛苦。她在里面时,我进去过一次,医生说他有客人,让我等会再来。而现在,他又有新的客人了。
他可能什么也不会告诉我吧。我每天都去找他,他早就被我烦死了。我把他当成我的救星,每个到他这里的人都把他当成救星。穷的、富的、男的、女的,都可以把他当成救星。我们都是一样的。
男人的声音很小,小到我根本听不清楚。
过道上,一个牵着气球的男孩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他的母亲跟在后面,正打着手机。她走得很慢。气球从我的脸上蹭了过去。
我抱着那个布袋子,离开了那间办公室。
妹妹的病房有点远,我拐了许多个弯,在迷宫一样的医院里穿梭,医院里那种特殊而又浓烈的气味,让人害怕,它让所有进来的人都神情肃穆。我走在医院整洁明亮的过道里,就像走在大街。人们面对面朝我走来,他们和我擦肩而过,他们不避开我,也没有人会留意我。
我慢慢地走,走向妹妹的病房,它就在过道的尽头。
警察来了。他倚在病房门口,正在和女护士聊天,嘿嘿地笑着。
(选自《姚江》2015年春季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