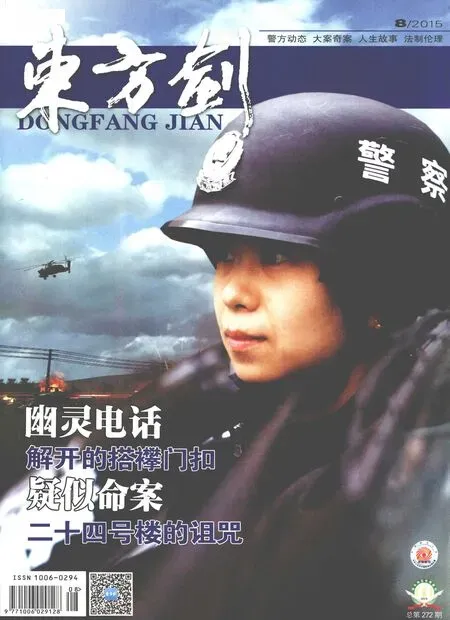乡村法官
◆ 王 爱
乡村法官
◆ 王 爱

兰香是幺奶奶的小女儿,出于对她母亲的憎恨,所有的孩子都不喜欢她。而我们对幺奶奶的这种感觉,则源于我们各自母亲对她的厌恶,我们是受了大人的蛊惑,才不喜欢兰香跟幺奶奶的。
寨子里几乎所有妇人都看不惯幺奶奶,一个精明世故且妖里妖气的女人,她从遥远的地方嫁过来,作为汉人女子成了我们土家族人的媳妇。四十多岁的妇人作二十多岁的打扮,浪声浪气说话,穿色彩俗艳的衣衫,瘦瘦的脸颊上有稀薄的头发覆盖,喜欢抹得油光发亮,上面别着几枚娇俏的花夹子,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从她嫁进寨子的第一年起,她就成了所有女人的仇敌,凡她走过的地方总有人嘀嘀咕咕,指指点点;被她屁股扭过的路口,也有妇人停下来义正词严地吐唾液。但幺奶奶看似浑然不觉,她像一只花尾巴喜鹊一样聒噪,有她在的地方,就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声响。女人们心照不宣,对她脸上堆积的笑容只能迎合,背地里憋着闷气,无形中带动了整个,形成了一股暗流,把这个外来女人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
每个妇人都有孩子,孩子喜欢模仿母亲,这种邪恶的暗示力量逐渐在我们心底生根发芽,我们开始扮演民间法官的角色。幺奶奶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可以旁若无人。兰香却没这个本事,她成了我们的审判对象。
在我们看来,兰香跟她母亲一样,长成了一个精明世故的小妖精。
因这缘故,先有人跟兰香玩,后来只要听说跟兰香玩的,就会被别人瞧不起,鄙视,久而久之,就没人跟兰香玩了。开始是迫于形势,后来就完全是顺从习惯,并且从心底认同了。兰香成了莫名其妙的绝缘体。
一开始,我们笨拙地模仿着成人的一切,对兰香的排斥是小心翼翼的。譬如,在她跟我们搭话时,我们只会敷衍一下,既不肯定也不反对。她在什么地方玩,我们就马上借故离开,绝不在同一地方玩。我们从不邀约她去玩,从不把她看成圈子里的一员。我们把兰香当作异己分子,但她自己并没意识到。出于孩童的懵懂,她知道自己孤独,但她不知道这种孤独来源于我们。她知道自己没有亲密的玩伴,但她不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我们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我们玩什么,她也玩什么。我们在小河里玩两人一组的跳水游戏,明明有个人落单,宁愿加在别人组里,也不跟兰香一组。在那个夏日里,兰香一个人一组,跟在我们后面,玩得不亦乐乎。就像一池鲜活的小虾里出现了一条鱼儿,她的存在令我们不满,她的迟钝让我们愤怒,于是我们提议去别处玩,故意大声叫名字,一个个邀请,偏偏不叫兰香的名字。兰香仍然没意识到我们在排斥她,她高兴地响应。当我们看到兰香穿好衣物准备跟随我们时,带头的人马上掉转身子,把衣服扔地上,大声说不走了,其余的人附和着也不走了。这时,兰香才明白过来。那是我看到她反应最激烈的一次,她冲着我们抬起了她的泪眼,爹一声妈一声号啕起来。我们面面相觑,第一次感到反击的力量,这种反击虽然微弱,但令我们惶恐。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记不真切了。天气的缘故,已经不适合在小河里玩乐了,我们悄悄甩掉兰香,把场地转移到山上。在那些长满了枞树,由细沙堆积而成的山坡上,我们学着各自母亲的口吻,无数次议论着她身上的一切。很多事例都是老调重弹,但我们不在乎,从这些口水缝隙里迸发出来的乐趣让我们甘之如饴,每个人都自觉比兰香高人一头,那是一种优越感,复杂微妙。议论到最后,触目惊心的一幕出现了,不知谁提议,我们应该给兰香举办一场丧事。每次想到这个幼时的情景,我的心都忍不住微微顿一下,我讶异纯真的孩童能有这样残忍的心思和恶毒的想法。
我们为活着的兰香送葬,整个场景模拟得一丝不苟。在家门口的小山坡上,我们回想着老人死亡时的情景,用细沙砾堆积了一座小坟,在坟的四周细心垒上碎石,插上新鲜的花草,然后找来一块漂亮的石块,立在坟头做墓碑。我们中写字最好看的人,用细尖的石头在上面刻下了兰香的名字和死亡日期。接着,三个人扮演道士,三个人扮演孝子,另外一些人扮演前来吊唁的宾客。大家神情悲痛,跟随着道士围着新坟绕圈,嘴里发出类似安魂的声音。道士把石块和柴刀当作锣鼓,敲得叮当响。边走边唱,伴随着孝子哀哀的假哭声。最后,我们仿着大人的样子,一个个按秩序匍匐在坟头,佯装悲伤地跟坟墓里的兰香告别。
也许,我们对兰香的排斥和厌恶并不完全来自她母亲,而是源自孩童的私心,类似于人类的奖惩游戏。这个游戏中,有人扮演好人,有人扮演恶人,各自登台,演绎乡村法则。还有人扮演死者,被扮演生者的人活活孤立。我们受着某种因素的驱使,一大群人站在一个人的对面,对她做出种种可怕的臆测、惩罚、隔离、凌驾,并以伤害她的精神为乐,从中感到趣味无穷。
一个孩子在有限的心智下能做出怎样残忍的事情来,只有自己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她才会明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促使我们这么做的最原始的动力来自何处?孩童的言行举止是否已在无意识中触摸到了人性深处?一种被巧妙掩盖着、或含蓄释放着的原始欲望。不然为什么,我们在对兰香的行为中失去乐趣后,转而寻求其他同伴。这种类似于猎物和寻找目标的行为几乎没有理由。兰香的母亲不是理由,天气不是理由,环境也不是理由。在游戏的齿轮终于滑到我这里,孩子们由恶作剧带来的乐趣,全部需要由我一个人的痛苦来支付时,我才开始用稚嫩的灵魂去感受这一切,反省这一切。
那天,在下雨,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小河里的水涨至微微发浑,雨后的日子薄脆得几乎透明,天空带着一种幽幽的苍凉。这种凉意本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个年纪。无意中,我撞见几个同伴背着背篓,相约着去什么地方找菌子。出于我们一直统一行动的惯性,我不假思索就跑回家找我的小背篓,赶紧加入到队伍中。我毫不怀疑我是其中一员,并且是群体中最重要的角色。但接着,一个平日跟我玩得最好的同伴,开始说出各种拙劣的借口,其他人配合着。我不是兰香,这种熟悉的托辞是我以往惯用的,我立刻敏感地觉察出来我的命运已经与往日不同了。
我被抛弃了,就像我当初带头抛弃兰香一样,这种人人害怕的厄运如今轮到了我,我成了那个被审判的角色。我第一次领略了孤独的滋味,我遭遇了我出生以来最大的危机,最大的陷阱,我也陷进了幺奶奶、兰香、秋红、三妹他们先后出入的坟堆里,同样一群人给我竖立了一座冰冷的墓碑。
我独自一人提着小桶和撮箕去河里撮鱼,遇见了小萍姑姑,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女孩子,已经过了玩乐的岁月。她在一块石板上洗衣服,不停地往自己的掌心吐口水,再用这些蕴含丰富的唾沫,抠洗衣服上某处洗不掉的小污点。小萍姑姑的优点是努力做一个大人称赞和喜欢的乖孩子,这些在我眼里毫无价值。一个孩子最骄傲的事情莫过于得到所有孩子的拥护,处在孩子中心,成为孩子王。小萍姑姑扮演的角色只能取悦大人,却征服不了一个寂寞孩童的心。
在那天,小萍姑姑对我异常亲热,跟我说了很多话,还教给了我许多洗衣服的偏方。但我识破了她的心思,看穿了她在特意拉拢和讨好我,她看似好心的举动,其实别有用心。她的贤良她的优秀,只是她用来保护心灵骄傲所采取的手段而已。在她这个年纪的孩子里,一些人读书,一些人打工,另一些人自愿加入成人队伍天天劳作。只有她,因为过早有了婚约,就得作为一个闺秀被所有人排斥。她被剥夺了玩伴,她不属于任何圈子,她需要整日呆在家里冥想她的丈夫、她的婆家生活。她需要为出嫁做一切准备,缝新衣服,做无数双布鞋和彩色图案的鞋垫。她必须端庄、内秀、沉稳,甚至在无人偏僻的角落里,她得悄悄哭唱几声,复习几遍妇人们教给她的哭嫁歌,以防在出嫁那天因不善哭而难堪。
我恨小萍姑姑,在一个大孩子和一个小孩子对峙的河流里,我明白小萍姑姑的处境,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山寨里所有的人都结伴走了,小河里只剩下两个孤苦的角色,站在各自生活的对立面。我的脚板心踩着那些发亮的小石子,它们那么清洁、那么秀丽、那么温顺,我的心中传来一阵阵微凉的刺痛。冰凉的河水冲刷着我的小腿,不远处偶尔有小鱼偏离出游的轨道,“啪”的一声跃出水面,小尾巴一甩,又迅速没入激流当中,它有路可走,我连小鱼都不如。我顿觉万念俱灰,周围白茫茫的水朝我挤压过来,我的心脏一阵抽痛,脑子里阵阵眩晕。为了掩饰我的窘迫,我佯装恼怒鱼儿太过狡猾,故意用脚在离小萍姑姑不远的地方狠狠跺了几下,溅起的水花爬了她一脸。我提着小桶和撮箕上了岸,我的背后像是长了一双利眼,我看见了小萍姑姑正一口一口朝手心里吐唾液,她的脸上弥漫着困惑,还有无声的悲哀。
我披散着头发,赤裸着双脚,担着我捉鱼的家什,远远地逃离了小萍姑姑,在纤细的田埂上飞奔。屋后的青山,传来一阵风的呼啸,像在下达某个命令的口哨,所有的树木迎风挥舞着绿臂,一起发出巨大的嘲笑声。整个下雨的下午,我扮演的角色让我痛苦难堪,我无所事事,只好在寨子里四处闲逛,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我逗弄着寨子里家养的畜生们,拍手吆喝吓唬它们。看猪扭着幺奶奶似的白屁股一颠一颠地逃窜。母鸡用翅膀笼着一窝小鸡,用看老鹰那种恐惧尖锐的目光防备着我。黑花被我用石头追赶到山里,口中一直发出委屈的呜呜声。我故意乐得哈哈大笑,但其实,我心里觉得无趣极了。
我只是偶尔遭受这种厄运,而兰香几乎被我们排斥在整个童年之外。《庄子·渔夫》中说道:“真悲无声而哀。”在这个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童年,兰香被这种无形的软暴力残酷隔离着,几乎发不出自己的有效声音,她是悲哀的,她的整个童年也是悲哀的。现在,我真想用我颤动的笔触来捕捉一下兰香们后来的成长气息。跟她母亲的过度妖娆不同,兰香成了一个低眉顺目的孩子,走路时永远垂着毫无生气的脑袋,别人夸一声她穿的衣服漂亮她都要脸红半天。这样一个在沉默中成长的孩子,却有最狂野的内心,某一天突然辍学出走,在我们尚不知情为何物的年龄里,她已经在重复她母亲的角色,先后跟着好几个男人私奔。
十几年后再见到兰香,她变成了一个比我们老得多的女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跟着不同的男人在不同地方停留。她性格乖张,眼神不宁,跟人谈话时不时发出神经质的笑声,引得人一惊一乍的。惨白的一张秀脸,却结了太多蛛丝,让人觉得十分怪异和荒谬,脸上始终挥之不去的两朵红晕还残留着儿时的记忆,那也许是她身上唯一鲜活的记忆。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深深忏悔,为我当年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兰香异常艰难的人生是否跟灰色的童年故事有关,我的笔墨看似接近真相,却因缺了勇气,次次从边沿处滑离开来。我们不是为了要伤害谁,在那样的岁月里,灵魂稀薄的我们必须为自己制作童年欢娱。找一个假想敌,通过一连串恶作剧,扮一回乡村法官,来达成我们的意愿。在做这些事情时,我们端严,一本正经,力求提前建筑一个成人世界,只是为了得到一颗糖果的甜味和乐趣。
发稿编辑/姬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