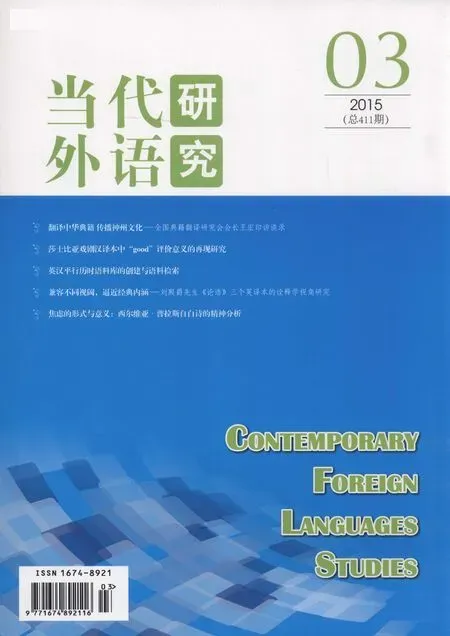论《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的爱的伦理
论《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的爱的伦理
李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摘要: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乔叟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指出这首长诗的主旨是讲述爱的伦理。诗中多处讨论爱情这个主题,而专门赞美爱的颂诗就有四首之多。诗人吸收了古罗马哲学家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和薄伽丘的长诗《菲罗斯特拉脱》中关于爱的理论,并把它们集中于《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尽力歌颂与陈演爱情。诗中的爱情属于“典雅爱情”的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在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爱情搁置了生育后代、附属于婚姻的利益关系等因素,同时两人在法律上都是单身身份,他们也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并没有违背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恋爱中的特洛勒斯认真地模仿宗教仪式去膜拜爱神,把克丽西德当作圣母玛利亚一样地景仰,如宗教狂热般对克丽西德忠诚不二。特洛勒斯借助爱的信条和他所爱的女性驯服了他体内的兽性因子,完善了他的人性因子,从而让他的理性意志成功地控制了自由意志。特洛勒斯虽然没有突破他的伦理身份带来的伦理困境,故事以悲剧告终,但诗人对他的爱情做出了最高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乔叟,《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文学伦理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5.03.012
作者简介:李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电子邮箱:junelian2002@163.com
1. 引言
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于1381年至1386年间创作的叙事长诗《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TroilusandCriseyde)①是他仅次于《坎特伯雷故事》(TheCanterburyTales)的优秀作品,此时的诗人正当盛年,主要的工作是在海关收取羊毛进口税,身为资产阶级的他在王室与纳税人之间费心周旋,1381年爆发的农民起义直接冲击了他的庇护人兰开斯特公爵的府邸,他恰好又在这一时期把古罗马哲学家波爱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DeConsolationePhilosophiae)译为英文。耐人寻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矛盾动荡和精神上的深思冥想,在他的这首长诗中却转化为对爱的最深沉的歌颂。本文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剖析这部作品中的爱的伦理。
2. 伦理事件:爱
乔叟的创作基本上都没有离开爱情这个主题,但他最为浓墨重彩地书写这个主题的作品莫过于长达5卷共8200余行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虽然这首叙事诗的背景是古代的特洛伊战争,而且两位主人公由于战争的原因而生离死别,但构成整个伦理事件的最主要线索毫无疑问是爱:主人公特洛勒斯自从爱上美丽的克丽西德后深情满怀,因相思而伤心欲绝,因相爱而振奋英勇,爱人移情别恋后仍痴情不改,直至战死升入天国。诗中多处讨论爱情这个主题,而专门赞美爱的颂诗就有四首之多,其中每一首都可以独立成诗,诗人以此对爱进行了清晰的伦理判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编号13&ZD128)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首颂诗位于第二卷,女主人公克丽西德听到女伴安提戈涅唱歌,祈求爱神赐予她美好的爱情,因为“有爱情的生活对我最为适宜,/我因此摆脱罪恶,受爱情驱使,/我追求美德,渐渐将情欲控制”(Ⅱ 852-54)。这首歌强调了爱情促人向善的效应,鼓励克丽西德向爱神臣服,勇敢接受炽热的爱情。后三首都在第三卷中。第三卷的序诗专用于歌颂爱,其中的“神明爱万物,也准许万物体验爱情,/没有爱,任何生命都失去价值,/没有爱,任何生命都无法维持”(Ⅲ 12-14)。把爱归于世界之存在的根本和价值的起点。在这一卷中,男女主人公终于倾心相爱。初次与克丽西德相会时,特洛勒斯赞美诸神的恩宠,坚定自己心中的信仰:“仁慈的爱神,你是万物的神圣纽带,/谁想得到你的恩惠,却又不愿对你礼拜,/他渴望的一切只会不翼而飞”(Ⅲ 1261-63)。稍后,第一次享受到爱情的甜美的特洛勒斯又幸福地宣告:爱统辖整个世界,万物因之结合,“自然中的泥土、水、火和空气相互抗争,/却又永久地彼此相连,/福玻斯带来玫瑰色的白昼,月亮管辖黑夜,/这一切都是爱情的伟绩丰功,/愿他的威力永受赞颂”(Ⅲ 1753-57)。四首颂诗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即强调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基本法则,是幸福和美德的重要源泉,而且颂诗并不单单指向男女之爱,还包括神圣之爱、友爱、情爱等广义上的爱。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是一首专讲爱情的诗,但是它在理论上跳出了狭隘的男女情爱关系,与波爱修斯、但丁等人的作品遥相呼应。泰特洛克指出,上述第三首颂诗就是直接“掠夺”了但丁的《神曲·天国篇》的最后一章中圣伯纳德对圣母玛丽亚的赞美(Tatlock 1906:367)。而第四首颂诗则明显改写自《哲学的慰藉》第二卷第八首诗(Robinson 1957:340-41,440),只不过诗人把波爱修斯的这首拉丁语诗歌翻译为散文,而这首颂诗采用的是后世所称的君王诗体,与全诗的格律一致。
众所周知,但丁的佛罗伦萨语长诗《神曲》一经面世便倍受关注,薄伽丘晚年更是倾注全部精力诠释和讲解《神曲》,而《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就是对薄伽丘同样用佛罗伦萨语创作的长诗《菲罗斯特拉脱》(Filostrato,另一中译为《爱的摧残》)的改写。此外,乔叟恰恰又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专注于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诗人,三位文学家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波爱修斯不仅仅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还被称为“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又是第一位经院哲学家”(波爱修斯2012:2)。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熟谙使他的思考富于理性色彩,而诗人翻译和借鉴这位前辈的作品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不但触动了诗人的心弦,而且能够为他提供相当多的哲理上的引导,包括此处对于“爱”的形而上学分析。总而言之,《神曲》是但丁在另一个世界里对此世的荣耀与卑下进行全方位的奖励和惩罚,《哲学的慰藉》是波爱修斯在监狱中沉思尘世世界的荣辱得失,而熟知这两部作品的乔叟则在《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里集中于对爱情的歌颂与陈演,由此形成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各个伦理皆由此成形、展开并最后解构。
3. 伦理选择:典雅爱情
《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心仪的一种爱情:典雅爱情(courtly love,或译“宫廷爱情”)。英国中世纪文学史家C.S.刘易斯(C. S. Lewis)认为,这个盛行于中世纪骑士文学中的概念包含“谦卑、礼貌、通奸、爱的宗教”四大因素(Lewis 1936:12)。在刘易斯看来,“在爱情诗的历史上,《特洛勒斯》以其纯粹而代表着老普罗旺斯多愁善感之作的最高成就”(同上:197)。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在中世纪被称为典雅爱情的大本营。但华裔学者李耀宗先生认为,刘易斯对典雅爱情的界定是失败的,尤其刘易斯给《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贴上“典雅爱情”的标签更是“画蛇添足”:“除了开头,克瑞西达何曾拒绝过特洛伊罗斯?他们的爱情怎么能算是通奸?有何非法之处?爱神早就成为修辞程序,还有什么宗教意味”(李耀宗2012:12-13)?其实李耀宗对刘易斯后两点因素的理解可能与路易斯本人有所出入,所以两人的结论相左。
路易斯对“通奸”一说解释得比较详细。他虽然按照常规的做法,从封建社会中贵族阶层的婚姻状况和婚姻理论两方面进行分析,但他实际上是立足于严格的宗教教条、婚姻与爱情二分法两处进行思考的:其一,从使徒保罗开始的神学家们认为,婚姻中出于生育之外的目的去满足的欲望都不是正义的,其区别只在于有的神学家比较包容,有的神学家无视这种男女激情,有的则比较严厉地予以指责,如十二世纪大名鼎鼎的神学家彼得·伦巴德就说,“一个男人对于自己妻子的激情之爱就是通奸”(参见Lewis 1936:15)。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在婚姻关系内,只要不是为了生育而有的激情或者欲望,都应归入通奸的范畴。其二,刘易斯认为,既然中世纪骑士阶层的婚姻都是出于利益关系而缔结的,典雅爱情中男女双方都无视或者排除了利益上的因素,所以具有非婚姻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眼中的“通奸”应该是指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或者肉体的激情关系,其道德与否,要依据这种感情的纯粹的程度以及对他人和公众利益的影响才能决定,因此是一个中性词。进而言之,有可能是刘易斯没有找到比“通奸”更贴切的词来表达这个独特而微妙的概念,但这个词本身又引起了其他人的误会。《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交流和肉体关系确实搁置了生育后代、附属于婚姻的利益关系等因素,因此,用路易斯式的“通奸”来标记也是有其合理之处的。李耀宗和其他批评刘易斯的学者一样,认为婚外情(或许还包括三角恋)才算是通奸,是违背亲情伦常的不道德的行为,只有部分骑士文学中才有婚外情的现象。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在法律上都是单身身份,两人相爱并没有损害他人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李耀宗对加之于两人身上的“通奸”一词打抱不平的原因。
《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的爱情是否属于不道德的通奸,两位主人公是否举行了像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秘密婚礼,作品中有些语焉不详,导致研究者们也有过很多猜测。乔叟研究专家D.S.布鲁尔从历史文本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除了薄伽丘外,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还有一些作家写过特洛勒斯的故事,等到乔叟涉及这个题材时,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框架基本定型,那就是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之间并无婚姻关系,两人的爱情命中注定为悲剧,所以,留给乔叟发挥的空间只有对两人爱情的描述了,而这构成了作品的血肉部分。《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尊重了前人设定的情节,但是,“特洛勒斯的爱情是道德的,没有违背神圣的条例,乔叟就是这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参见Brewer 1954:464)。
相应地,李耀宗对“宗教”的理解可能与刘易斯(应该还可以加上乔叟本人)的也有所出入。对于《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来说,特洛勒斯确实是在认真地模仿宗教仪式对爱神进行膜拜,把克丽西德当作圣母玛利亚一样地景仰,以及如宗教狂热般对克丽西德在口头和行动上忠诚不二。这些行为举止在中世纪的宗教环境中比较容易接受,而今天距18世纪无神论登上西欧的舞台又有几百年了,我们再目睹这一切,确实可能会把这些视为李先生所说的“修辞程序”。当然,刘易斯自己也说,“爱的宗教”的内涵并不单一,如“但丁是极尽一个人所能地严肃(对待爱神或他爱的女性),法国诗人们则毫无严肃可言”(Lewis 1936:21)。有的作品很虔诚,也有纯属戏谑之作。从上文所引的颂诗和诗人对但丁相当倾慕的现象来看,《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应当是偏向于但丁这一个极端的作品,尽管今天的读者难免会觉得诗中个别场景过于夸张,但是放在乔叟所在的14世纪的宫廷环境里,诗人也有可能会为了博取观众一笑而偶尔有意如此。
4. 伦理实践:理性意志
李耀宗对刘易斯的质疑是学界对“典雅爱情”这个概念长期争讼的一个缩影。自从一位名叫加斯通·帕里斯(Gaston Paris)的法国作家兼学者在1883年最早论及“amour courtois”(英译为courtly love或courtly amour)这个概念后,与大量的其他学术辩论一样,学者们对此形成了激烈对立的两大阵营,但它又因其独有的魅力被人们应用至今(Moore 1979)。尽管它的意义含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于典雅爱情作为一种习俗在当时的贵族社会阶层所获得的广泛传播和认可,西方的绝大多数学者也都是承认的……确实,典雅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改变了他们诸多不文明的行为”(徐善伟2003:85)。这种正面积极的效果是因为它赞美了优雅而有教养的贵族女性,同时还受到中世纪盛期在整个欧洲兴盛一时的圣母崇拜的影响,让女性获得“精神尊严和宗教价值”(伊利亚德2004:1028)。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是但丁,他不但将早年为暗恋的贝阿特丽丝写的情诗集命名为富于宗教意味的《新生》,还让她在《神曲》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圣洁高贵几乎可以与圣母玛利亚相媲美,因此,“典雅爱情”绕不开宗教式的救赎与女性在这种救赎中的重要地位这两个因素,即上文中刘易斯所称的“爱的宗教”。在《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特洛勒斯进行了一次伦理选择,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爱情的得失紧紧地绑在一起,克丽西德在他心目中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
春光明媚的4月帕拉丁节上,特洛勒斯被爱神之箭射中,对同样来参加活动的克丽西德一见钟情,“他顷刻就在爱神面前拜倒”(Ⅰ 231)。两人初遇的场景有双重的意义,其一,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节日庆典是人群聚集的场合,比较适合让作品中人物相遇相知;其二,从伦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宗教活动是神与人交流的契机,宗教信条在此对人产生影响,或者说,人物的行为遵守了宗教信条。对特洛勒斯来说,他从此皈依爱神,“心中的傲气已荡然无存,/就在目光一闪的瞬间,/神圣的爱情啊,你把人改变”(Ⅰ 306-8)。特洛勒斯的皈依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虔诚膜拜爱神,祈求恩惠,帮助他获得心仪女子的爱情,其二,“他心中再无别样欲念,/只是想着一个道理,一个目的:/克丽西德生出恻隐之心,/他至死不渝,永远是她的奴仆,/她则是他的生命,把他从死亡中救出”(Ⅰ 465-69)。如果他放纵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可以利用自己王子的身份和武力去威胁利诱克丽西德,但是他选择了遵从于爱的信条,把它圣化为爱神的形象,被爱的女性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成为可以拯救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特洛勒斯的理性意志占了上风。
面对特洛勒斯的臣服,克丽西德是强化其理性意志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刚从她的舅舅、也是特洛勒斯的密友的潘德卢斯那里得知特洛勒斯的澎湃情意时,毫无心理准备的克丽西德相当冷静地思考这件事情,决定“除非心甘情愿,她无须以爱报偿”(Ⅱ 609)。拒绝逼迫,也不曲意逢迎。接受特洛勒斯的爱情后,她坦言:“打动我的是你的道德力量,/因为它建立在忠实和真诚之上”(Ⅳ 1672-73)。并警告他:“虽然你是国王之子,/在爱情上你不能无理将我辖制。/如果你行为不当,/我不会克制自己不将你冒犯。/只要你对我效劳尽力,/我会相应地眷爱、珍视你”(Ⅲ 170-75)。从中显示出克丽西德有着独立的人格魅力和清醒的个人意识,不随意放纵情感,有效地强化了对特洛勒斯的道德约束力。
接受爱情指引和约束的特洛勒斯从此面目焕然一新,他慷慨亲切,扶弱济贫,杀敌英勇,是“爱神——愿他的恩惠得到赞美——/要求他远离一切罪孽和恶习,/骄傲、愤怒、贪婪、还有妒忌”(Ⅲ 1804-06)。他对于邪恶丑陋的事物如此地鄙视,对于美德如此地汲汲以求,以至于他后来确切地了解到克丽西德已经放弃了对他的爱情,他仍旧说“我的心/却不会、也不能不爱你”(Ⅴ 1696-97)。这种不可能有回报的爱是一种最纯粹的爱,是对爱的信条的最纯粹追随,特洛勒斯身上的兽性因子被彻底压倒,人性因子达到完美。
5. 伦理两难:爱情悲剧
前人把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爱情设定为一场悲剧,乔叟在演绎这个悲剧时详尽细致地呈现了它的各个细节,并尽力为克丽西德的背弃进行辩护。在诗人笔下,这出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人无法逃离的伦理身份以及由此引起的伦理两难。
首先,特洛勒斯是克丽西德的情人,同时又是特洛伊国王之子。作为王子与国家公民,他必须维护王族的利益,服从国家的法律,为保家卫国而冲杀在前线;作为情人,他必须信守忠诚、高尚、保密、捍卫所爱女子的名誉等爱情守则。在他们的爱情初期,这两重伦理身份对于特洛勒斯来说其实是相互增益的,他爱得越深,爱情越是甜蜜,他越是殷切地遵守各种美德,在战场无比英勇,让希腊人闻风丧胆,战场归来对王族和国家尽职尽责,深受众人喜爱,所以他的爱情实际上十分有利于国家。直到有一天,克丽西德的叛逃致在希腊人阵营的父亲卡尔卡斯在两军交换俘虏的谈判中,要求用战俘交换自己的女儿来自己身边。在特洛伊人看来,克丽西德不是战士,而是叛徒的女儿,没有战略价值,用她来交换“智勇双全的安忒诺耳”(Ⅳ 189)是很划算的,所以议会中除了赫克托尔之外,大家都表示同意。
特洛勒斯万分焦虑,他极想留下克丽西德,但交换战俘的命令已经下达。他与密友潘达卢斯商量,潘达卢斯的建议是,如果不想放弃克丽西德,就强行劫走她。他拒绝了。他首先考虑到自己骑士的身份,因为这次战争起源于抢夺海伦的事件,劫走克丽西德会进一步损害国家利益。其次是王族的身份,他不能请求父亲改变已经发布的命令,否则会影响国王和王族的权威。第三才是情人的身份,他不能公开他与克丽西德的秘密关系,因为他发誓保护她的名誉。此时国家与王族的利益占了上风,但前提是他必须牺牲自己的爱情。其后,他设法与克丽西德秘密相会,面对所爱的人,他只想抛弃自己所有的社会身份,与克丽西德偷偷出走,也就是说,他选择情人的身份而放弃王子的职责。但是这个想法被克丽西德劝阻,因为两人必将因此永远身败名裂。克丽西德提议让她去希腊人阵营,为特洛伊交换回勇士,之后她再想办法逃回来,这样除了两人暂时分离这一不确定因素之外,既服从国家法律,又保全了爱情,似乎是最佳选择,两人都同意了。
特洛勒斯的痛苦与彷徨表明,他的自由意志(选择情人身份、保全个人爱情)是很强大的,尤其是面对克丽西德时会情不自禁,但他又时刻受到来自外界、他自己和克丽西德三处理性意志的约束,而且最终向理性意志屈服,坚持履行了王子与情人两重伦理身份所要求的相应职责。然而,特洛勒斯的这个似乎能让他解除困境的决定并没有帮助他摆脱另一个伦理悖论:“特洛勒斯必须让他的秘密但于政治无害的与克丽西德的爱情遭到破坏,来换取一个保全特洛伊的微小的机会,而这座城市当初正是由于决意要保护特洛勒斯的兄长的爱情权利而身陷险境,他的哥哥[注: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带来政治上的危险,而且他们还愚蠢地公开了他们的关系”(Bloomfield 1997:291)。这个悖论的结果是,特洛勒斯的个人牺牲远远不足以消除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关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克丽西德离开特洛勒斯后,意识到特洛伊危在旦夕,于是改变心意,接受希腊勇士狄俄墨得斯的求爱;失去爱情的特洛勒斯最后失去了生命,特洛伊失去了一名勇敢的战士;牺牲克丽西德换回的安忒诺耳后来成为出卖特洛伊的叛徒,导致这座城市最终毁灭。总之,无论是这一对恋人还是特洛伊城议会的计划全部破产。
其次,克丽西德所处的伦理困境并不比特洛勒斯的简单:她的父亲是特洛伊的叛徒,而她仍旧是特洛伊的公民,必须服从国家的法令,去交换特洛伊勇士;同时她是特洛勒斯所爱的女子,这要求她以忠诚回报特洛勒斯。她承担了国家与情人对她的伦理约束,但身为“一名叛徒的寡居的女儿”(Lewis 1936:185),她从来就不是强悍的美狄亚,在父亲抛下她叛逃后,她不得不跪在特洛伊城第一勇士赫克托尔的膝下痛哭流涕,寻求人身庇护。在与特洛勒斯相爱的过程中,安全仍旧是她考虑的第一因素。尽管她个性独立,但这种被动之爱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当特洛伊人在不询问她的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决定交换她时,赫克托尔尖锐地指出,“她不是俘虏,/我不知道是谁授权你们这样做,/我主张立即通知他们,/我们这里没有习惯出卖女人”(Ⅳ 179-82)。但赫克托尔阻拦无效。所以,她父亲背叛了特洛伊,同时遗弃了她,而她还要承受特洛伊人的背叛,不得不离开特洛勒斯,她受到的伤害是双重的,但此时她还是想满足国家、情人、父亲的愿望,履行自己的职责。
克丽西德去往陌生的希腊人营地时,包括她本人和特洛勒斯在内的所有人都期望她是一个足够强大而有行动能力的人,事实上她远没有这么勇敢,“一旦特洛勒斯被留在城里,一种油然而生的孤独感让她更为强烈地渴望得到慰藉和保护”(Lewis 1936:187)。新的追求者看穿了她的心思,告诉她特洛伊必然毁灭的命运,加之她独自留在特洛伊城时的那段如惊弓之鸟的生活,使她对安全的渴望比一般人更强烈,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保全自身。她知道背弃特洛勒斯会使她恶名远扬,内心是相当痛苦和自责的,但她至少决定要对狄俄墨得斯忠诚到底,尽管亨利森(Henryson)说她后来沦落为一名妓女,接下来还要身患麻疯病成为乞丐(同上:189)。但乔叟肯定不愿意这么写,在诗人看来,“虽然她渴望天国之爱,也爱上帝,/但神圣的爱却于她不适”(Ⅰ 983-84)。这名不幸的女子的爱情不像特洛勒斯那样虔诚和执着,她只不过是依据现有的条件做出相对有利的选择而已,而且她的理性意志严厉地谴责了她的自由意志,因此,“如果我能宽恕她,无论怎样,/我出于同情,定然会把她原谅”(Ⅴ 1098-99)。
6. 结语
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爱情因特洛勒斯的战死最终落下帷幕,他的灵魂来到天国,从空中俯视地球时满怀感慨,原来“尘世只是虚空和徒然”(Ⅴ1818),鼓励人们把爱奉献给上帝,不要去“追逐尘世的虚假情爱”(Ⅴ1848)。这个结局似乎否定了特洛勒斯对克丽西德付出的所有热情,与前人对这个爱情故事的描述达成了一致。但是,乔叟给了特洛勒斯“一个非基督徒勇士所能够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和最令人羡慕的奖励”(Bloomfield 1997:300):灵魂飞升天国。薄伽丘(2012:289-90)并没有给特洛勒斯这个奖励,而同样的故事如果让但丁来写,特洛勒斯唯一的归宿将是地狱,因为他重视个人爱情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乔叟与但丁、薄伽丘在此分道扬镳,这恰恰是乔叟跳出前人的窠臼、做出自己价值判断的地方。《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在赞美爱与美德一体两面、展现特洛勒斯在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之间的挣扎后,“没有人会怀疑,是爱把他带到了这个极乐世界”(袁宪军1995:108)。
附注
① 本文对于该诗的引用出自乔叟(1999)。下引此作的标注方式为“诗节数诗行数”。
参考文献
Bloomfield, J. 1997. Chaucer and the polis: Piety and desire in the “Troilus and Criseyde” [J].ModernPhilology(3): 291-304.
Brewer, D.S. 1954. Love and marriage in Chaucer’s poetry [J].TheModernLanguageReview(4): 461-64.
Lewis, C. S. 1936.TheAllegoryofLove:AStudyinMedievalTrad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J. C. 1979. “Courtly Love”: A problem of terminology [J].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4): 621-32.
Robinson F. N. 1957.TheWorksofGeoffreyChaucer[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tlock, J. S. P. 1906. Chaucer and Dante [J].ModernPhilology(3): 367-72.
波爱修斯.2012.神学论文集哲学的慰藉(荣震华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杰弗里·乔叟.1999.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吴芬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李耀宗.2012.“宫廷爱情”与欧洲中世纪研究的现代性[J].外国文学评论(3):5-18.
米尔恰·伊利亚德.2004.宗教思想史(晏可佳等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聂珍钊.2014.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乔万尼·薄伽丘.2012.爱情十三问·爱的摧残(肖聿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
徐善伟.2003.典雅爱情的特征及其社会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6):82-88.
袁宪军.1995.乔叟《特罗勒斯》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玄琰)

《叙事研究前沿》征稿启事
《叙事研究前沿》(FrontiersofNarrativeStudies)创刊于2014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暂定每年出版一期。本刊主要栏目有中外叙事学名家访谈、叙事学前沿理论、中外叙事理论比较、中国叙事理论建构、叙事文本阐释,同时刊发国内外叙事学研究动态、综论和书评等。稿件收悉后3个月内给予回复。3个月未见回复者,请自行处理。因本刊编辑部人员有限,不能一一办理退稿。恳请理解。
来稿请按照MLA稿件格式要求排版,为提高稿件处理效率,请直接将稿件电子版发至投稿信箱narrative2014@163.com。
《叙事研究前沿》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