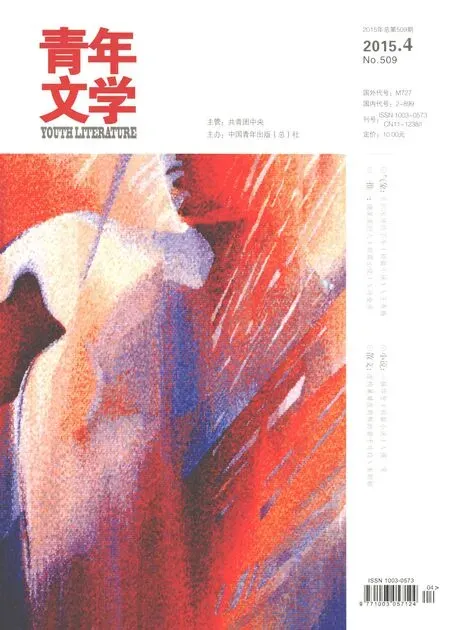虚构舅舅在朝鲜的若干片段
⊙ 文/朱朝敏
虚构舅舅在朝鲜的若干片段
⊙ 文/朱朝敏
朱朝敏: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天涯》《花城》等刊。出版有散文集《她们》《涉江》《开败时间的花朵》,小说集《遁走曲》《鱼尾裙》。曾获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湖北省第八届屈原文艺创作人才奖。
冬日灵堂前的梦
二〇一二年深冬,舅舅走了。我相信,他是在睡梦中把灵魂与身体剥离,灵魂交给了梦,一梦向北,徒留一具肉身,从此,肉身开始长久地酣眠。我唤他不醒,摇他不动,摸他鼻息一阵凉寒。我双手交搓,然后送到嘴边,哈气取暖。我没有眼泪,相反,一阵轻松。舅舅终于安然睡眠了。他离开了我们,当然,我指的是灵魂。
殡仪馆人员推走他的肉身,并以最快的速度设置了一个灵堂。舅舅躺在灵柩中,身着灰色中山装,还戴着深蓝色的工人帽。他国字型的脸庞抹了白粉,嘴唇也许涂了一点口红。这样,睡着的他看上去回到他的中年,回到我对舅舅最初的记忆。这样,我看见他紧皱的眉头下如电的目光,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坐要有坐相”,他的吼声让我不由挺直了胸膛,双手规矩地放在身体两侧。他要求我们女孩子必须是淑女,我们因为他的威望就必须是淑女。不是的,装也要装作淑女。我屏息,声容平静。舅舅开始了讲述,关于他在朝鲜的岁月。他哪里是在讲述?是在大声演讲,滔滔不绝,声情并茂。我听见了遥远的山川的落雪,还看见阳光下美丽的金达莱盛开和图们江、鸭绿江的奔腾。但,它们是什么模样?不曾一睹真容的我,凭借舅舅滔滔不绝的描绘,我仿佛真的看见了那些山川、河流、花朵,还有载歌载舞的朝鲜姑娘。沉浸在回忆中的舅舅,还用朝鲜语唱起了《道拉吉》:“道——拉——吉,道——拉——吉——”舅舅的歌声只有声调,语言是蹦跳在舌尖上的豆子,而且是被糯米和糖浆包裹的豆子,在他的舌头弹跳出清新不乏绵软的歌声。我的视线紧紧凝聚在舅舅嘴唇上,仿佛看见小豆子上下左右地蹦跳滑滚。终于,舅舅的歌声停止了,沉默顿降,我愣坐原地,舅舅也发呆似的坐在椅子上,眼睛耷拉,嘴唇紧抿。他停止了演讲。但语言,那些被他放出的语言,却蜜蜂般还在我耳边飞舞。
此刻,我守在舅舅的灵柩前,走了一圈,然后,给他盖上黑色的金丝绒。尽管,他的睡眠看上去如此深沉,可我还是希望他不受到惊扰。这也是舅舅的希望。只有在经久的睡眠中,那剥离肉身的灵魂才能飞得更快更高,才能安全地抵达魂牵梦绕的土地。在那块土地上,孑然一身的舅舅遇见他的亲人,他的灵魂才会找到依托。而曾经,灵魂那样漂泊不定,寂寞。
黑色金丝绒在我眼前制造漫长而沉重的黑夜。黑夜适合漫想虚构。我愿意被如此的黑色掏空思维。我闭起眼睛,右手托着半边脸庞打盹。而黑夜早已来临。寒风怒吼的黑夜中,我的打盹单薄又矫情。我干脆趴在桌子上睡觉。
但大风灌进大门敞开的灵堂,黑金丝绒突然被掀开。灵柩里的舅舅坐了起来,他嘴唇张开,唱起了《道拉吉》:“道——拉——吉,道——拉——吉——”他还不满足,伸手推开灵柩的顶盖,边唱边爬出了灵柩。我的心几乎跳到嗓门上。爬出灵柩的舅舅,他换了一身衣服。宽松的高丽服,套在身上,他的眉眼满是喜悦,他勾脚伸手,跳起了朝鲜舞蹈。
舅舅怎么变成了朝鲜男人?我揉眼,站起来伸手去拉。啪啦,桌子上的一瓶墨汁倒到地上,那是准备为亡人书写祭奠文的。我醒了。梦幻消失。黑色的金丝绒华贵而沉重,覆盖在舅舅的灵柩上。风一阵一阵地从门外灌来,它尖锐的呼哨却被灵堂活生生地阉割。它被削弱了声势,胆小、慌张、迟疑,根本不足以掀翻什么。
我洗了手呆坐了一会儿,重新打盹。也只不过闭闭眼而已。而黑金丝绒下的舅舅,却根本不为任何声响所动。他真正实现了大睡眠。
那么,凌晨到来时的遗体火化,真的就只是仪式了。他的灵魂,想必,已经抵达了长白山。
一条河流带来的消失
舅舅在新婚之夜消失了。消失在大红披挂的新房中。老式雕花木床还散发着桐油味,床铺上的被褥红绿耀眼,床单上的喜鹊闹春描绘成一个偌大的圆圈,稳当地停在床铺正中,而两三床绸缎被子整齐地折叠,依靠床铺内侧依次码好。被单中心的“囍”字层层堆压,反而压挤出闹腾腾的喜气。喜气从新房拥挤膨胀,从窗棂门缝中逸出,伴随冬天的冷风横冲直撞,见谁扑谁。那个时刻,每个人的脸庞都有一股红彤彤的喜气。
外公外婆自是大舒了一口气。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的舅舅终于回家了,尽管是被他们以身体有恙骗回家的,可终究回来了。回家的舅舅被捆绑了手脚,套上鲜红的礼服长袍,戴上黑色的大礼帽。外公拱手,要求舅舅好好配合,完成彼时的承诺——娃娃亲的承诺。新娘是我三外公的干女儿。她有一个美好的名字“春天”。当年,七岁的春天姑娘快要饿死在一艘春天的渡船上。渡船是我三外公的。他膝下无子无女。于是,奄奄一息的春天姑娘被我三外公带回家,被认作干女儿,还与我舅舅结成娃娃亲。那是亲上加亲。
事实上,除了娃娃亲,我舅舅能够顺畅地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全是我三外公的功劳。三外公资助我舅舅,他也认我舅舅做了他的干儿子。干儿子与干女儿的结合,等于是给我无子无女的三外公家打下了人丁兴旺的桩基。三外公是指望我舅舅给他延续香火的。可我舅舅不同意。这仿佛注定,舅舅的不同意,就是为了以后年月的告别。漫长的告别,直至人生的冬天到来。
一纸婚约算什么?哪怕身上绑着绳索。尽管进了洞房的舅舅被大舒一口气的外公他们解掉绳索,尽管红蜡烛快要滴干蜡油。舅舅支棱耳朵倾听。他是用耳朵在探路。一条开始逃逸的路途。些微杂乱又短暂的脚步声,还有遥远的狗吠,还有似有还无的鼾鸣。是时候了。舅舅站起来,扯掉繁缛的礼服,推门而出。
他直奔岛上的南边。此时,南边的长江几乎断流,裸露的沙地在冬风的肆意吹拂下已经板结,过江如履平地。过江的舅舅没有回到学校,他向南了。似乎。
的确,他没有回到学校。他只不过向南走出了孤岛,再一路向北,向北。
冬天的凛冽,在北方就是天寒地冻。一个逃逸的人,印象中,应该奔向南方。可舅舅的逃逸方向颠覆了猜测。八年后,舅舅突然一身军装出现在家里,我外公他们为这次猜测隐约地体味到自己的短见浅识。
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了。舅舅说道,他的眉宇间流露出的阔豁气,瞬间就把北方的一条河流搬运到我外公他们眼前。
鸭绿江?我外公外婆,三外公三外婆,我小舅舅小舅妈,我的三个姨妈还有我的母亲,都带有疑问而缄默不语。
身陷长江包围的孤岛上的人,不知陌生河流的模样。在他们眼中,一条河流不是伴随视力出现,而是在意念中就轻而易举地奔涌到眼前,它的出现不择时空。然而,鸭绿江是不同于长江的,它意想不到的寒冷。残暴的寒冷冰冻了两岸泅渡的心灵。我们无法听懂舅舅的嘟囔。我外公外婆舅舅姨妈还有我母亲都不懂,若干年后,我们这一辈人也听不懂。我们却在舅舅的嘟囔中听出无奈,还有失落和愤懑。
鸭绿江也许不比长江宽阔,但比长江沉重,它承载的冰雪、出发、告别、逃逸和归来,还有永久的诀别……肉体的七情六欲被河流消耗,在时光中殆尽。这令人心碎,简直绝望。可是,被时光之火炙烤的躯体中的……意念中的东西,曾经云蒸雾绕地弥漫盘结。盘结,等待有一天琥珀般结晶飞身而出。
一颗在逃逸路上被关闭路卡的心灵。它在等待一条回归的路途。
泅渡的心灵,湿淋淋地攀着晶体般的灵魂,再次越过鸭绿江,找到回归的路途。
一条河流带来的消失,却指引出一条泅渡的魂路。
虚构舅舅在朝鲜 片段一
舅舅一路向北,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雄赳赳,气昂昂……”,高亢而热烈的进行曲铺天盖地,他的逃逸显得小气不合时宜,甚至卑劣到难以启齿,但空气中激烈豪迈的气氛大海一般宽阔深邃,即刻吞没了一切不适。波澜壮阔的潮汐一波接着一波地袭来,浩大整齐,似要翻卷出鸭绿江的春天,然而春天那么遥远。冰雪满地的朝鲜土地上,枪炮、硝烟、战火、歌声、呐喊、厮杀、搏击……铁铲一般锋利无情,日夜不停地挖掘,刨出冰冻的黝黑泥土。白天与黑夜没有区别,围困与突围,奔袭与巷战,抄包与螳螂捕蝉,伏击与追剿……冷兵器和枪炮交融的战争,没完没了。睡眠几乎是找来的,趁着一个空当,倒下就睡。但一根神经绷在脑门,以微弱的脉搏感应周围的风吹草动,它往往在大脑快要疏忽的刹那猛烈地弹跳——有危险。睡眠结束。短暂的危险的睡眠,以不安稳的神经宣告,白天长于黑夜,或者说,白天几乎扼杀了黑夜。
舅舅是正宗的大学生,还是学习机械的高才生。刚开始他修理卡车坦克兼任驾驶,而后端起机枪直接上战场。他的左腿和两个胳膊分别遭受枪击。
这不算什么。可怕的是饥寒。被困于山洞,没有粮食吃,吃完了草皮树根,没有油水的肚皮紧贴在骨头,冰凉趁势起义,它以成倍的寒冷围剿活生生的肉身。他们冻坏了双脚,冻掉了耳朵鼻子,冻死了心脏。然而更多的人在闭眼休憩的刹那凉寒了鼻息。睡死——你们无法理解……诉说中的舅舅猛烈地摇头,双唇紧抿,眼球突出眼眶。他在后怕吗?也许。须臾,舅舅长嘘一口气,嘟哝道:我最担心自己睡死,它那么容易……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睁开眼皮,睁开睁开……呼,我挺过来了。
舅舅挺过来了。子弹,刺刀,严寒,饥饿,疾病。它们从舅舅身上穿过,带出舅舅的血液和皮肉,却带不走舅舅的生命。但他还是落了泪。他的泪水从朝鲜战场淌到我们孤岛上,泪水延续到八年以后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直至死亡。他的回忆充满了感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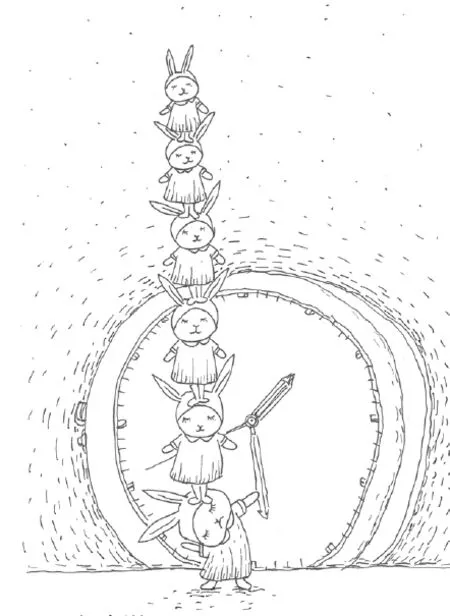
⊙ 徐俊国·钢笔画11
里尔克说,
挺住意味着一切。
我要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
全顺是我的警卫员,他为我挡了子弹,我的命是他捡回来的,我能不为他报仇?舅舅抹下眼睛,双眼透露一道精光。他似乎看见偷袭的一个白头发的美国军人。舅舅的“看见”若一面镜子,轻易地为我们呈现。“独臂白头翁”,舅舅送给仇敌一个形象的称呼,身着朝鲜服装,与他的同伴混进舅舅扎营的一个村庄,干掉舅舅的战友,摸到一棵椴树后面。舅舅正倚靠椴树在休息,他不知道匕首伸到脖子边。枪声响起,舅舅惊讶地站起来转身,发现两个人同时倒在身后,一个是身着朝鲜服装的美国兵,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全顺。而撒腿跑进树林里的正是“独臂白头翁”。
该死的仇敌,我必须要让你付出代价。舅舅说。当“独臂白头翁”混杂在一群俘虏中,被舅舅一把揪出,舅舅用刺刀解决了胸中的块垒。快意恩仇,原来就是英雄侠气,无关战争无关纪律,只以良心抉择善恶结果。
我不再是团长,但有什么关系呢?舅舅的荣光在许多年后,伴随他的讲述一次次迸现,点燃他的豪情和侠义。但,很快,舅舅眼中闪现出泪花。那复杂的液体,在岁月洪流的冲击下,昏黄又笨重,却忍不住滚滚而下,它们积蓄了体腔的热情,如此滚烫,几乎灼伤我们眼睛。我们不由低头,但我们还是以余光看见,泪水在虚幻的镜子中,犹如陈旧的黄月光,闪烁着彼时的感伤。
他报仇,却换不回为他挡子弹的兄弟。兄弟抛尸朝鲜战场,他无法不落泪,绵长的泪液也许是在遥遥地祭奠,然而,不只……泪水滚烫绵长。这个绝情的男人,在新婚之夜拒绝圆房而后逃逸,吵闹了四十年要求离婚,终于在六十岁那年,他的逃逸抵达了目的地。他自由,却白发丛生。他倔强,却孑然一身。那个名叫“春天”的女人苦苦哀求、抵抗,而后沉默,却无法焐热舅舅的铁石心肠。
你的心是铁打的。我名义上的舅妈是在感慨,还是在表达她的愤懑?也许都有,因为在我们孤岛人看来,她的话完全没有错。这个孤寡一辈子的女人,她的童年、少年、青春、盛年、老年,从来就只有影子与她相伴。她以活着表达她的生命存在,而同意离婚——我们在揪心的疼痛中,发现她的尊严。
虚构舅舅在朝鲜 片段二
舅舅身上的疤痕无数。他在朝鲜八年,有三年时间几乎每天在战火硝烟中摸爬滚打,他立下了三次战斗功、一次工作功。单从战争角度讲,这不算战功赫赫,起码也是成绩显著。但,舅舅还是愤然了。如果他不能入党还有谁能入党?这是舅舅所在部队领导的原话。是对受到误解中伤的舅舅的辩护,还有发自内心的赏识。但舅舅偏偏不能。也不是完全不能,“能够”还是“能够”的,却有前提。
说起这段往事,舅舅眯眼,抬手扶扶眼睛旁边的眼镜框——那是虚拟的眼镜框,还不够,他又搅起舌头说起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他在装扮考察他的赵干事,说:入党必须保证政治清白,你那三爹被人举报私藏黄金已被抓进监狱即将枪决,只要你承认他是反革命并与他划清关系,保证你步步青云。
啪。一声钝响,舅舅的右手拍在桌子上。他腾地一下站起来,恢复了他自己。他眼睛怒瞪,面色紧敛,嘴巴里爆豆子一般蹦出热腾腾火辣辣的豆子:人不能忘本,如果连自己亲人都背叛的人,谈爱国爱党,是他妈的扯淡。
赵干事怎么反应?我们紧张地问道。
怎么反应?他从哪里来再滚回哪里去。
可你呢?
我?舅舅的手指指在他的鼻尖上,然后坐下,放慢了语调述说。他的叙述中有朝鲜村庄,有会唱《道拉吉》的朝鲜老人,还有绿油油的开始泛黄的稻田。他的叙述再次变成了投影,我们看见了遥远的朝鲜。一九五三年初夏傍晚,残阳如血,半边天红彤彤的,从天际铺张到江河,犹如灿烂的火把群。水流注入晚霞的血液欢畅地奔腾,沿着高山丘陵喋唼迤逦,再以碎片驻留村庄湖泊。而辉煌若画的黄昏中,朝鲜男人和女人吆喝着声喉,在夺回的土地上耕作歌唱。
舅舅赶走了赵干事,继续回到村头,给他手下的士兵补习。但马上来了人,收回他的教鞭,还没收所有的粉笔。即使他再有知识和水平,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有什么资格来教育他人?
舅舅再次从副职降级。
盛夏时,板门店会议召开。舅舅带着车队,帮助返回家乡的朝鲜人运输行李粮食,遇到未来得及撤退的美国兵(他们正在伏击朝鲜有名的“和平鸽文工团”),舅舅带人去及时解围。那么又算立下一功。
舅舅的领导颇语重心长地交代,你好好地把握机会,马上又有人来考察你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要认真地掂量掂量。
见舅舅嘴巴紧抿,领导摇头叹息,直接摊牌道:我直说了吧,这次是我又打了申请报告,上级答应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惜才啊,人家不信,我已经做了担保……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答应吧。
领导吞回肚腹里的话,就是:你如果再孤注一掷、死不悔改,那么断绝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前程,还会连累关心你的领导。
舅舅僵硬着身体,等来考察他的人。
还是赵干事,还是那句话:要进步,必须保证政治清白,只要你承认你三爹是反革命并与他划清关系,保证你步步青云。
舅舅反问:凭什么说我三爹是反革命?
赵干事:私藏黄金,已经抄家抄出来了,而且他已经认罪。
舅舅:不可能。
赵干事:什么不可能,都已经……枪毙了。
舅舅站起来,推了赵干事一把,马上被旁边的一个士兵拦下并拉走。舅舅被关禁闭。他忍不住哭泣。泪水滚烫绵长,从遥远的朝鲜洒落至我们孤岛,飘坠若雨,淋湿我的童年、青春和中年。
他在为他吃了枪子的亲人哭泣。那个亲人,与他血脉相连,供养他读书直至考取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他没法止住泪水……
虚构舅舅在朝鲜 片段三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板门店会议,双方谈判代表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七月二十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金城江南岸建立新的防线。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暂停。但舅舅继续留在朝鲜,协防朝鲜边境五年。
一九五八年舅舅回国后,在昆明一家汽车修配厂工作。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只能如此。由于他在入党提干考察中负隅顽抗与冲动,为他今后的生活埋下了铲除不尽的荆棘。舅舅很坦然,每每面对诘问,他做一个后退姿势,意思是不朝那条路上走。
可是,他能改道有蒺藜的功劳路,却不肯变通死心到底的生活路。到昆明工作后,每年回到孤岛,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解除婚约。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离婚之路。锲而不舍,斩钉截铁。亲人们都劝舅舅,算了吧,都这把年纪了,就这样凑合过吧,你又没有过怎么知道无法相处?
村妇之见。舅舅的回答充满了慢和不屑。我母亲和姨妈她们再也懒得劝他。离吧,只要你离得动。她们凑一块,口气满是讥讽。但四十年后,我们所有人都被舅舅和那个名叫春天的女人震撼。他们离婚了。我母亲简直恼羞成怒,对我姨妈说,她怎么就答应了?都六十岁的老人了。开始是愤愤然,但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声音钢丝般抖颤,泪水滴淌下来。她在心疼,不仅是为名义上的嫂子,还为孑然一身的舅舅。
母亲的心疼带着小女孩般的赌气。回家后,与我父亲唠叨,全是她的揣摩——都耄耋之年了,还那样死心眼地要求离婚,可能是他在昆明有合适的人选,否则他会这样强烈要求离婚?可惜,等舅舅退休回到我所在的城市,他仍然孤身一人。我母亲才否定她的揣摩。不仅否定,还纳闷地发问:舅舅有文化,长相也不赖,难道就没有遇到爱情?
她的发问苍白。因为她以一个朝鲜女人的名字回答了她自己。金贞玉。
关于这个朝鲜女人的故事,我是听舅舅自己讲的。
她的出场,是在舅舅讲述一九五三年七月板门店会议后,舅舅在朝鲜的最后一次作战中。当时,舅舅带着车队,帮助返回家乡的朝鲜人运输行李粮食,遇到未来得及撤退的美国兵正在伏击“和平鸽文工团”,他与金贞玉的故事就在这次作战中开始了。
其时,“和平鸽文工团”只有十一名女性,大部分是刚走出学校的女学生。舅舅专门讲道,他与“和平鸽文工团”有四次相遇,几乎每个演员他都熟悉。
我们几个外甥女顿时来了兴趣,不停地追问:舅舅,谁最漂亮?
舅舅耐不住追问,轻轻答道:金贞玉。
那么,遭受美国兵伏击的“和平鸽文工团”,里面自然有美丽的金贞玉。舅舅没有直接回答,我们却从他的语气中看见了她的出场。还看见男人的英雄救美。
痛快,真痛快。那些残兵损将,被我们收拾得干净利索。舅舅用一句概括,轻轻蒙上回忆,刚刚出场的金贞玉马上消失了。
我不死心,问,你救了那个金贞玉,她高兴吗?
高兴。舅舅吐出这两个字后,马上皱眉,责备我一个小女孩家话真多。舅舅被自己的责备惹出火气,腮帮子鼓起,坐在椅子上独自纳闷、生气。
他为什么生气?
舅舅这次讲述简直不可捉摸。但我母亲回家后悄悄对父亲说,舅舅肯定在朝鲜有心爱的女人。母亲不知道我就在她的身后。我马上说道,金贞玉。母亲与父亲愕然对望,拉长了脸颊,以严肃的沉默禁锢我的嘴巴。
多年后,我来到图们江边,偶遇身着服装鲜丽的朝鲜族女人。她们白皙的脸庞总是洋溢着微笑,而她们弱柳扶风般的身姿,行动处就是优美的舞姿。我的头脑里闪现出一个女人的名字:金贞玉。由此我想象,年轻的舅舅与美丽的金贞玉依偎拥抱,淙淙的溪流淌过喃喃的情话。炮火中的歌舞,田野里的相濡以沫。晚霞满天中的执子之手。但告别还是来临了,匆忙地从相握的双手滑落,相背而去。而后,漫无边际的无法言说的隐秘思念成河,绵绵不绝。
你在一九五八年离开朝鲜时,见到金贞玉了吗?我们在成年后,斗胆问起舅舅。舅舅看我们一眼,垂下眼睑。他沉默,拒绝回答。但他低头沉默时的沮丧和哀痛,分明又变形出一面镜子:关于告别,不,永别,爱情的永别。我无意夸饰,但我必须承认,我在虚构。以虚构抵达真实。关于诀别的真实。
诀别已经到来。我的指头在颤抖,它们敲击键盘,黑字排列出汉江的花红柳绿,整装待发的舅舅与金贞玉双手紧握,满脸哀戚。我的指头听见她的哀求:留下来吧,留下来吧。但我的心灵代替舅舅回答,不可能,我的亲人还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是的,我多少知道一些历史,在朝鲜已经成家的中国军人,可以申请留在朝鲜。但舅舅与金贞玉无缘谈婚论嫁,因为舅舅是已婚的男人。金贞玉,你不能怪罪这个中国男人。我满是歉意地敲出这样的话。可我的指头电击一般,接到语言的指令,还是她的哀求:那么带我走,我愿意陪你回到你的家乡。
我的指头僵硬。我的泪水泗横。我在代替舅舅流泪,他这个绝情的男人,从来没有停止他的泪水。从朝鲜到长江边的孤岛,舅舅的泪水若暴雨,敲打并浸湿每个孤独的日子。直至他八十四岁生命终结。现在,我又代替他落泪。
照片上的男子是谁
舅舅退休后回到我们当地的县城。他是自由身,却将孤寡终老。
但这只是我们的看法。与他无关。他认为,他不是一个人生活,因为他拒绝听见“孤寡”两个字。他暴躁地切割,生硬地指责我们说话没有礼貌。他的脾气极坏,丁点不如意的事情就要跳脚叱责。
我们提着水果去看他。他刚刚接下,又推到我们手上,眨巴着眼睛问,看我一个人,你们就可怜我?我们否定。舅舅生气地反问:当我痴呆啊,你们回你父母家每次都带礼物?不要不要,你们拿回去,再不要来了。
我们真不来了。舅舅找上门,进门就责问:忘记你老舅了,是不是?我们无语。他真的老了,尘封的往事快在心胸中发霉,但他拒绝拿到阳光下晾晒。他要以生命为赌注,守住隐秘,守住青春的浪漫。但,终究憋得慌,他的内疚、遗憾、甜蜜、感伤,早已发酵出晶体,在日益衰老的皮肤血肉中,一不小心就磕疼了他。他的脾气越来越坏。不只对我们,对邻居路人也如此。
舅舅一再搬家。七十岁那年,我们帮舅舅搬到一个四合院里居住。不像往常他一个人搞定,这次他搞不定了,他双脚和双手浮肿,动弹显得吃力。我们搬来行李,在房间整理时,意外地看见一些照片。老照片以前被舅舅拿出来看过,也不陌生。但有一张快要发黄的照片惊呆了我们。上面是一个年轻的男子,酷似舅舅,却分明不是舅舅。他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倚靠在一棵树上。树木背后是广袤的田野。男子眉宇间带着探询,仿佛询问对视的眼睛:可否认识我?
这人是谁?
我们几个表兄妹交换了下眼神。随即,都垂下了眼睑。问舅舅,他会回答吗?即使回答,但不能谋面,看到这样一张旧照片,哀思和悲痛不可避免。我们匆匆收拾好照片,再也无话。
晚年的舅舅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身体迟缓僵硬。手脚越来越不利索。舅舅坚持每天走路,而且是倒着走。也许是他坚持的结果,也许是他坚韧的毅力,一度迟缓无法动弹的身体,在近八十岁时有了好转,他不仅能行动还能自己做饭洗澡。
然而,只是暂时。很快,他又行动不便了,连站立都成问题。可怕的是,他的语言中枢神经出现了问题,他面对我们,张着嘴巴叽咕,但舌头就是不能吐出他要表达的话语,哪怕一个词语。舅舅的脑门大汗淋漓,眼角渗出昏黄的泪液。他双手抓在我的右手上,似乎要摇摆,却力不从心。
他在着急。忧心如焚。他再也不能去叙述他的荣耀与愤懑,也无法表达他的内心。何况那些尘封在心灵一角的隐秘往事?哪怕,最简单的语言需求也不能。他张开嘴巴,哇的一声吼出,眼角却泪液飞扬。
我喊道,舅舅,我知道你要说的……话语此时也在我嘴巴终结。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生命历程,我所看见的、揣摩的、虚构的,算起来不过是冰山一角。但我只能这样回答。这个老人正在为生命机能的衰败而痛楚,为与外界交流被中断而忧愤。我偏过头去,泪水和鼻涕顿时肆意滴淌。
静静的图们江在流淌
二〇一四年初冬,我来到了吉林省东部的延边,这里身着朝鲜族民族服装的延边人很少,但还没有到绝迹的程度,而熟悉的《道拉吉》倒时常听到:“道拉吉道拉吉道拉吉,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挖出一两根就可以装满我的小菜筐……”我仿佛天生会唱,跟着导游应和,但我一点也没听见自己的声音。我清楚,我不是自己寻乐,而是代舅舅在唱。
原准备去朝鲜的,但中朝边境因为埃博拉病毒刚好闭关。所以只能到图们江畔去看看。遗憾不小,激动也不小。图们江蜿蜒曲折,在初冬,它内敛静泊,时不时断流,即使水域丰沛的地方,也是波澜不惊,汪着清亮的积水,镜子一般反射红彤彤的太阳。风从四方来,水面涟漪阵阵,波泽吉光羽片。
两岸的荒野,均在山坡上,宽阔而平整。绿黄的杂草上,有吃草的牛羊,但很少。偶尔出现几间矮小的房子,房顶上的烟囱冒出折不断的炊烟。是的,初冬的图们江寒冷,想必,那烟囱下面的柴火应该是在烧炕保暖。我几乎一眼不眨地盯着图们江那边,同是土地,另一块国土。
那块国土,半个世纪前,我亲人来过,并用脚步和心灵丈量过。而今,我亲人的灵魂,或许正在那块国土上,与他魂牵梦绕的另一个灵魂在一起。而静静的图们江,见证了眼泪与血液相融的际会。它内敛静泊又热烈奔放,以缓缓的流淌姿势诉说一个个动人的细节,甚至碎片。啊,只能是碎片。碎片拼凑的故事,凌驾于虚构之上,又被虚构映照,还是碎片。真实就在其中。
舅舅与图们江有关吗?图们江仅仅是一条作为边界的江河吗?
它是一个符号,一个开关,关于跨越时空的记忆和往事。
不是吗?舅舅八十寿辰那年,我女儿朗诵了一首诗歌《金达莱的故乡》:
金达莱花开呦满山岗,
我的故乡是美丽的城。
凉爽的海风从图们江吹来,
洁白的云朵山间飘过。
……
舅舅站起来,紧紧盯着我女儿,他双手拄着一根拐杖,走出座位,走到我女儿旁边。那时,他的身体器官均退化,到了冬天,站立困难,几乎难以走动。然而,舅舅不仅站起来,还走动了几步。
仿佛,他感受到了图们江的风,吹来洁白的云,云在瓦蓝的天空漫游。这自由不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