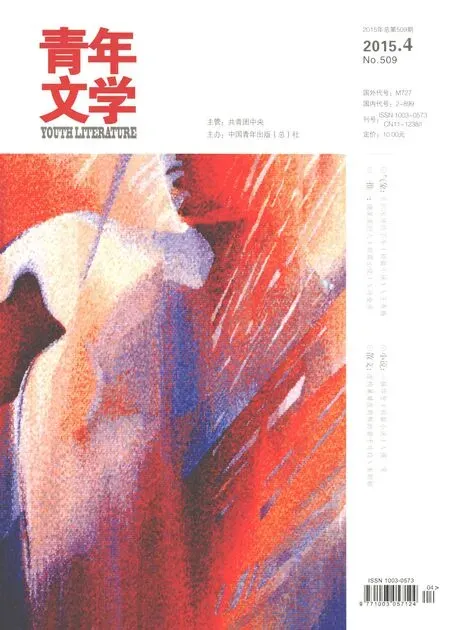红裙子
⊙ 文/曾 皓
红裙子
⊙ 文/曾 皓
曾 皓: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小说界》等刊。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奇迹发明家》,长篇小说《魔鬼连》等。
我是轧钢厂的天车司机,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工作富有诗意,他们很容易把天车想象成开往天堂的火车。这样的工作,想一想,都让人陶醉。
我与孔雀第一次相见时,那时她才十九岁,有两根细长嫩白的腿,像春天里刚长出来的葱,脚步轻盈,如跳高运动员一样,随时都能在空中来个鱼跃。我们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相识。我随着音乐朗诵自己写的那些短句,她则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那时她是个业余舞蹈演员,为挣点外快,被活动组织者请来为诗朗诵伴舞。当她从我嘴里听见天车时,突然停了下来,薄薄的嘴唇张开,发出一声长长的“呀”,眼神紧紧地咬住我,直到我和她的脸都变得通红。
后来她缠着我带她去看天车,我们的手很自然地牵在一起了。那段时间流传着工厂要倒闭的消息,有工人挑头闹事后,便停产搞起了整顿,厂区看起来很空荡。我们从轧钢厂的大门进去,被门卫室的老头叫住,他嘴里散发的大葱味让我感到莫名的愤怒。我拿出工作证,他挥手让我进去,却把她拦在了门外。
那时我除了喜欢写短句以外,还喜欢挥舞拳头。我抓住老头的衣领时,老头一丝慌乱也没有,梗着脖子轻蔑地对我说,你不就是一个天车司机吗,你敢动我,我让保卫科整顿你,到时我看你还牛不?
我把老头推到墙角,这时有人在身后拼命拉我。我看见她的眼里闪着泪花,哀求般地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的心一下软了。从没有女孩在我面前流过泪。我默默地跟着她,朝雨镇的大街走去。
她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生怕我突然转身,跑回去找那个老头打架。我们这样走过雨镇灰蒙蒙的大街,一直走到河边,淹没在一片野草中。然后,我们的身体挨在一起,很自然地发生了那事。
她是个处女,这点让我印象深刻。我对未来的妻子是不是处女并不看重。但她的处女身份让我很紧张。我手忙脚乱地解开她的衣服,就像剥开一枚果实的外壳,她的战栗和潮湿的身体散发出的腥味让我肃然起敬。我没敢莽撞,像第一次驾驶天车那样小心翼翼。
过后,我们又手拉着手走向河岸。我提议去吃烤串。她低着头,像犯了错误的孩子那样沉默不语,走出很长一段路后才说,我想回家,我只想回家。
于是她领着我,朝她家的方向走去。城市很黑,轧钢厂常年冒出的灰尘像浓雾一样弥漫。而我的心里很亮堂,也很温暖,只是感到特别饿。走到一个地方,她松开我的手,头也没回地对我说,你回去吧。
我知道她的家快到了,就对她的背影大声说,明天我带你去轧钢厂,我一定要让你看到天车。
她的身子猛地停住,接着转身,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像溺水般紧紧地抱着我。我听见她的声音有些哽咽,还有些颤抖,鼓起勇气一样小心翼翼地对我说,你答应我,这辈子一定要对我好,一定……一定好吗?
她重重地强调了“一定”两个字,我郑重地向她点了点头。
过后,厂里举办职工技能大赛,我获得了天车组第一名。我按着口袋里的奖金,就像按住一只小兔子。我本来想请她吃饭的,在去找她的时候经过雨镇商业街一家服装店,很远我就看见橱窗里的模特身上穿着一件鲜艳的红裙子,长长的微微向上卷起的裙摆,像一只奏响舞曲的大喇叭。那个本来了无生气的石膏模特似乎一下活了过来,正在华美的舞曲中优雅地翩翩起舞……
我看得呆了,在橱窗前久久不肯离去。我想到了我正爱着的那个叫孔雀的姑娘,我想到了她那两根细长嫩白如香葱一样的腿,那像踩了弹簧一样随时都会在空中来个鱼跃的曼妙身姿,如果这件红裙子穿在她的身上,那将是多么美丽的风景。
当我拿出刚获得的奖金准备买下这条红裙子的时候,那个长着两颗兔牙的售货员捂着嘴笑了好久,然后对我说,要是那点钱能买,我自己早就买了。
可是……
我胆怯地指了指裙子上的价签,接着说,那上面不是标的这价吗?
售货员又笑了。那两颗兔牙这时候看起来非常丑陋。售货员说,你把眼睛瞪大点再看看。
我又看了一遍,上面是手写的8888。我屏住呼吸,再次检验,的确,中间没有任何小数点。可这怎么可能?一条裙子八千多?
我感觉自己像遭了巨大羞辱一样愤怒地望着售货员,八千多?你们疯了吧?这个店也值不了那么多钱。
售货员突然亮开了嗓门。老板说这叫摩登舞裙,是给那些跳外国舞的人穿的,不是给一般人穿的,你懂得起不?这是我们老板从外面弄回来的镇店之宝,标这个价的意思就是非卖品,可以出租照相,不卖,你懂得起不呢?
我根本不懂啥叫摩登舞,但听到是给跳舞的人穿的,就更加坚定了想法。我说,你们是做生意的,只要是挂出来的东西,哪有不卖的,你问问老板,到底多少钱才卖?
售货员突然收敛笑容,像赶苍蝇一样将我轰出店外,嘴里骂道,你是不是有病啊?说了不卖就是不卖,你看你那样子买得起吗?就是卖给你,你送的人她能穿吗?咱们这镇上,有几个女人能穿这样的裙子?
如她所言,在这个常年灰突突的小镇,有几个女人能穿这样的裙子?不是她们不渴望美丽,而是根本没有驾驭这种美的底气。可怎么能把我深爱的孔雀姑娘和小镇的其他女人相比呢?把她放在一群庸脂俗粉里比较,这是对她的侮辱和亵渎。
我愤愤不平地跨出店门,走到街上。接下来,我干了这辈子最冲动的一件事。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在售货员的尖声惊叫中,我手里的石头像呼啸而出的炮弹,橱窗的玻璃哗地碎了一地。
我像个劫匪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那条红裙子。但我并不认为是抢,我把兜里所有的钱卷成一团扔进了店里。除了刚拿到手的奖金以外,还有整整一个月的工资。
我根本没想到这样干的后果。我的脑袋发热,全身不停地颤抖,除了激动,还有癫狂。我一路飞奔,只想快点把这件红裙子送到她的手上。我跑到她家楼下扯起嗓子喊了一声孔雀的名字,看见她从窗户朝我招了招手。我还没等到她下来,就见小镇派出所所长胡文革骑了一辆摩托车从我背后冲过来,我被摩托车把钩倒在地。胡文革从车上跳下来,解下腰带,劈头盖脸朝我招呼过来。嘴里骂道,老子看你狗日的还跑不跑?
要不是服装店那个留着艺术造型的长发老板放我一马,胡文革最后肯定会把我送进牢房。服装店老板说,你是这个镇上除了我之外最懂得审美的人,那件红裙子就按你付的钱卖给你,不过你得再赔我一块玻璃。
我走出派出所的时候,看见我的孔雀姑娘惊慌失措地站在门口。我像举着战利品一样朝她晃了晃手里的红裙子,她冲上来紧紧地抱着我,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说,你怎么这么傻呢?你怎么这么傻呢?
没隔多久,她就穿着那条红裙子嫁给了我。我们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的路上,她的脚下像装了陀螺一样,走着走着,突然就会在我面前来一个旋转。裙裾飞扬,轻云般慢移,旋风般急转,如鲜花怒放,如水波潋滟。
我无法形容她的美丽,也无法描述她带给我的惊艳和幸福。我像傻子一样笑着,她也像傻子一样不停地跳着,旋转着。街上的人像看耍把戏的一样追了我们一条街又一条街,孔雀那曼妙的舞姿和飞舞的红裙像闪电一样划过雨镇灰蒙蒙的天空,给我也给雨镇的很多人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过后,那件红裙子她再也没有穿过。她像收藏珍贵的艺术品那样,用塑料袋将红裙子包了起来,然后轻轻挤压,直到将里面的空气挤干,接着再套上另一个塑料袋。最后到底套了多少个塑料袋,大概只有她知道。
我们住在租来的平房里,很简陋,却很快乐。最开始,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激情和憧憬。有时我会给她朗诵我工作之余写下的那些短句,而她则会在我抑扬顿挫的朗诵中翩翩起舞。我说我希望以后能继续写诗,让生活充满诗意。她说她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蹈家,永远都那么优雅和华美。然后我们紧紧相拥,不厌其烦地用身体带给对方快乐。和其他夫妻一样,我们创造了自己在性爱方面的隐语,我们把做爱叫作开天车。我白天在工厂开完天车之后,夜晚就在那张铺着水蓝色床单的木板床上,继续开着我们的天车。
事情慢慢变坏应该是那天她去轧钢厂给我送饭开始的。那是我们结婚五年后的一个六月,那天天气预报说本地将迎来五十年来最热的一天,轧钢厂迎来了改制以后的第一个大订单,所有工人都要加班。因为实在太累,那天我早上睡过了头,起床后着急去上班,却忘了拿她为我准备的午饭。结婚后,为了省钱,也为了我吃得顺口,五年来一直是她事先为我准备好午饭,装在饭盒里,由我带去轧钢厂。午饭时间,工友们去吃饭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疏忽。我对自己有些生气,像惩罚自己一样接着爬上天车,继续干起来。不知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还是因为饥饿,有好几次,我都没能钩住天车下方要起吊的东西。我气急败坏地拍打着牢笼一样的驾驶舱,真想从上面跳下来。
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喊我。我扭头朝下望去,看见我的孔雀姑娘正站在起吊机下面朝我呼喊。我莫名地烦躁,向她吼了一句,你怎么来了,不要站在下面!
厂房里到处是加工的巨响和混杂的回音,她好像并没听见,她也似乎不知道 “起吊机下不能站人”的规定,侧身将手放在耳朵上,大声问,你说什么?
我再次吼了一声,她还是没听见。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心头突然毛了,火燎火燎的,立即停车,钻出驾驶舱,从天梯上倒退着爬了下来。
我走到她面前时,发现她像打量怪兽一样惊恐地看着我。这时我才发现自己除了肩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啥也没穿,而身上源源不断冒出的汗水让我像刚从水里——不,准确地说,应是泔水里走出一样,因为我身上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很正常,遇到狗日的闷热天,吊在半空的天车驾驶室就像一只冒着热气的蒸笼,轧钢厂的天车司机几乎都是这副德行。要是讲啥文明,非要穿个裤头遮羞,那用不了多久,裆里捂着的家伙非变成烧鸡不可。

⊙ 徐俊国·钢笔画5
一匹马在跑,一群蝴蝶在飞。
这匹马和这群蝴蝶互为灵魂。
她打量我的眼神还是让我有些难堪,虽然我们对彼此的身体都非常熟悉。我一把将她从吊车底下拉开,没好气地问道,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她一愣,举了举手里拧着的方便袋说,你忘了带饭,我给你送饭来。
这时我才看到她满头大汗,露在外面的皮肤像被太阳烤熟了一样通红。我问,你骑车来的?
她点了点头。
从我们租住的平房到这里,她最快也得骑半个小时。我的心头一软,本想表达心疼的意思,可嘴里蹦出的话却带着刺。我说,你傻呀,这么热的天你省那两块钱干啥?你要中了暑我还得花钱给你看病。
她的眼里泪花一闪,说,你嫌我花你钱了。那我以后自己挣,不花你钱就行了。
我听到她这样说,心里当时就后悔了。这几年,她一直没上班。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她在餐厅或其他场合跳舞挣零花钱时,那些男人用色眯眯的眼神看着她咽口水的表情。我说,你要实在想跳,就在家里跳吧。你要想学,以后想当舞蹈家,没问题,不用你去挣那点钱,这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我给你拿钱。因此,这几年,一直都是我用不多的工资在负责家庭的开销,还有一部分她学跳舞的支出。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瞎说什么呀?
大概是因为急躁,都怪那狗日的天气实在太热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也抬高了不少。
她也抬高了嗓门,你还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我摆了摆手说,好吧,我不说了,我啥也不说了,好吧。
我转身,爬上天车。而她却将饭盒一扔,也赌气地走了。
一连几天,我们都没说话。后来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时向她发出暗号,我说我想开天车了。她背对着我,没有一点回应。我按照以往驾轻就熟的套路开始了操作,这时她翻过身,睁大眼睛像打量陌生人一样望着我,用一种奇怪的语气对我说,我一直以为,天车就是通往天堂的火车,原来它跟起重机没啥区别。
我愣了好半天才说,天车本来就是一种起吊设备,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你开天车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个诗人。
我说,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狗屁诗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轧钢厂工人。
她瞬间变得有些惊慌,仿佛突然获悉了某种她不愿面对的真相,紧紧缩在床头,摇着头说,至少那时你还像个诗人,现在你连像也不像了。你知道你在天车里的样子像什么吗?
我说像什么?
她的眼圈一红,哽咽着说,就像一个囚徒,一个关在笼子里苦苦挣扎的囚徒……
说完,她终于哭出声来,不知为何那样伤心,哭了整整一夜。
过后,她再也没去学跳舞,并且不顾我的阻拦,在一家饭店当起了服务员。最开始我感到很欣慰,心想我的孔雀姑娘终于长大了,开始学做一个为家庭付出的女人了。但慢慢地,她的市侩和婆婆妈妈让我对她的变化有些无法忍受。为了能买便宜一两毛钱的土豆,她能拉着我逛遍整个菜市场,和菜贩子们讨价还价得口干舌躁,最后也不一定买,还要去别处看看。我对这种琐碎繁杂的鸡零狗碎充满了厌恶,费那般周折就为了省下一毛两毛,那我宁愿躺在床上多休息一会儿。而她却乐此不疲,并经常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地絮叨我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日子就在她详细记录收支的小本上悄然滑走,她对未来的生活目标进行了现实的规划:攒下钱了,先租一个大点的平房,条件允许了再租楼房,要是发财了就买个自己的房子,哪怕先交个首付也行,然后,再造个小孩出来。每个月我们都想攒点钱,结果都没攒住。意外支出像防不胜防的小偷,时不时把我们的钱包掏得精光。不是她头痛脑热,就是我酒喝多了,骑自行车撞到了老太太……生活中的偶然就像潜伏的敌人,时不时暗算我们一下。总之,几年下来,我们的目标一个也没实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也慢慢变成了满腹的牢骚和没完没了的絮叨。
后来有一天,有一档电视节目吸引了她的注意,那是一个舞蹈类的选秀节目。她连续看了几期,看的时候还不忘对每个选手进行专业的评点,最后愤愤不平地说,就她们跳的那个也叫舞蹈?简直就是对舞蹈的侮辱。
我说,你要上去的话,绝对秒杀全场。
我奇怪,她怎么就没听出我话里的讽刺意味。我本来是想刺激她一下,以表达她热衷这种庸俗节目的态度。没想到她抬起头,用非常期待的眼神望着我,然后说,真的吗?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她眼里闪动的小火苗就此熄灭,那是这些年来我很少看到的。我违心地点了点头,生怕她看出我的虚伪,诚惶诚恐地点头说,真的。
没想到这就是灾难的开始。她像着了火一样从床上蹿起,赤着脚在地上来了几个旋转,然后大声说,那我明天就去报名参加海选。
我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第二天我下班回来,她拉我去商场,准备买一条参加海选时跳舞穿的裙子。我对逛商场深恶痛绝,加上一天的劳累,实在不想挪窝,就对她说,我的工资卡反正在你那儿,你想买啥样的裙子都行。
我明显看出她的不高兴,我消极的态度打击了她刚刚燃烧起来的激情。但如果我立即改变主意,那样,她会更加怀疑我的真诚。她什么也没说,像生怕我改变主意那样,决绝地朝我摆摆手,然后独自走出了家门。
等她回来的时候,已是晚上,我已在床上睡了一觉。我看到她空手而归。我说你买的裙子呢?
她并没理会我的关切,扔下手里的包,连衣服也没脱,径直上了床,怕冷一样用被子将自己裹上。
看来她的心情并不愉快。我也没继续追问,共同生活的经验告诉我,那样只会自讨没趣。我关掉了灯,她像赌气一样却在床头将另一边的台灯打开。我一句话也没说,将被子拉过头顶,继续装睡。
隔了很久,她突然坐起,侧身似乎观察了一下我。接着就有靠枕朝我头顶砸来。
你是死人啊?你对我一点也不关心。
说完她就哭了。
女人真的很麻烦,问她时偏偏不说,真不理时她又感到了冷落。我说,怎么了,到底谁惹你生气了?我去帮你揍回来。
你也就那点出息!
我掀开被子,跳下床,一边穿裤子,一边对她说,你就说受了谁的气吧,我要不揍他狗日的,我就不是男人。
我气冲冲的样子把她吓到了,她显然没看出来其实我也只是做做样子。她擦了擦脸上的泪痕,接着说,你揍得着吗?我是生气现在东西太贵了,一条像样的裙子都要成百上千,还有好几千的,这么贵,它卖给鬼呀!
原来她为这事生气呢。我豪爽地说,只要喜欢,贵就贵呗,钱是个王八蛋,花完了再去赚!
她突然扑哧一笑说,你说得轻巧,银行卡上就那点钱,花完了咱俩不得喝西北风?
我就知道她心疼钱,这也是我故意显得豪爽的原因。我说,那好办,明天咱俩再去商场,你看好哪条裙子,到时我帮你抢一条回来就行了,这种事咱又不是没干过。
她朝我扔过来一个枕头。你说的是人话吗?
突然,她从床上蹦起,朝衣柜扑去,兴奋地说道,我想起来了,你原来给我抢的那条裙子还没怎么穿呢!
事隔多年,那条见证我们的爱情而又被我俩遗忘的红裙子被重新找了出来。她急不可待地穿上,接着来了个三百六十度旋转,然后双手托着裙摆,一脚向后弯曲,身体前倾,躬身做了一个舞蹈演员的答谢礼。
我当时一下就看呆了。时光的积累让她的身体略显臃肿,原本葱白一样水嫩的双腿也爬满了蚯蚓一样的静脉曲张,但穿上红裙子后的曼妙旋转,让她像重新找回翅膀的天使,那个曾经像精灵一样的舞者在她略带矜持的眼神中慢慢苏醒,瞬间光彩照人。
我突然热泪长流,张开双臂,激动地与她相拥。我拍着她的肩膀说,明天,我一定陪你去参加那个比赛……因为,你是最优秀的……
她听了我的话后,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那样,靠在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我们当时好像觉得,只要参加这个比赛,就能一扫这些年在生活中遭遇的那些委屈和辛酸。
第二天,我去工厂请完假出来,远远就看见我的孔雀姑娘穿着那条红裙子在门口等我。我们像年轻了许多,手拉着手朝电视台走去。几年前,我们也是这样手拉着手去领结婚证的。如今,她的腿已不如当年那样轻便,走在地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她的那条红裙子已经变旧,像贴在门上的旧春联,与她的皮肤一样黯淡无光。我想,等她参加完这次海选,不管能不能晋级,一定要给她买一条新裙子,我知道她喜欢红色,那就买一条火焰一样燃烧的红裙子。
去电视台参加海选的人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从几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穿着各种奇装异服,挤满了电视台的各个角落。我们奋力挤进人群,终于完成报名,然后就站在一边,竖起耳朵等广播叫她的名字。
漫长的等待中,她和其他人一样,做些进场前的准备工作,压压腿,扭扭腰。在她身边不远,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不时跑来跑去,有好几次都踩到了她的裙子。这让她很不高兴,笑着对他说,小朋友,这是公众场合,你要注意礼貌,你踩到我的裙子了。
小男孩向她吐了吐舌头,非但没有后退,反而一点一点向前挪着脚,故意跟她作对一样,照着她拖在地上的裙摆又轻轻踩了一下。
我看见我的妻子板起了脸,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小男孩这时一溜烟朝他的母亲跑了过去。
妻子拍了拍裙子,狠狠地瞪了瞪那个正朝她扮着鬼脸的小男孩,然后转过身,继续压腿。
这时小男孩又走了过来,他在妻子的身后跺着脚,妻子并没有理会。小男孩盯着妻子的背影,又上前走了两步,然后转身跑回去拉着他母亲的手,一边指着妻子,一边用他天真无邪的美妙童音大声说,妈妈,她的屁股上破了好大一个洞。
小男孩的母亲回头,果然在妻子的裙子上看到了一个破洞,刚好在臀部的位置,已经洗得发黄的白色内裤也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这时妻子不是半蹲着身,那个破洞肯定不会被人看到,它刚好在裙子的皱褶中。妻子在穿这件裙子的时候,一定照了镜子,但那个破洞刚好隐藏在皱褶里,没能发现。或许她急着出来参加比赛,根本就没注意到那个破洞。此时,她半蹲着身子,结实的臀部把那个皱褶撑开,刚好暴露了那个破洞。那一定是我们几乎用肉眼无法察觉的蛀虫潜伏在箱底,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啃食的结果。
小男孩的母亲厌恶地回过头,并强行把孩子的头扭过来,自言自语般地说,都什么人,半拉屁股露外边了还不知道。
周围的人都将目光投了过去,当他们看见妻子屁股上的破洞之后,禁不住笑了。而妻子却浑然不觉。我正要上前,奇怪的是,我听见周围人的笑声,便怯懦地停住了脚步,像个高明的潜伏者那样把自己隐藏在了观众中。
这时妻子站起身,回头奇怪地望着正打量她的人群。那个小男孩又跑上前,对妻子扮了一个鬼脸,大声对她说,你的屁股上有个洞。
妻子好像没有听清,问道,你说什么?
小男孩这次几乎是吼着在说,你的屁股上有个洞!
妻子听到了,她愤怒地对小男孩说,谁教你的,这么小就耍流氓,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小男孩的母亲听到妻子骂她的孩子,她转过身,那声音就像一块玻璃在寂静的夜里掉在了地上,亮开嗓门对妻子骂道,你才是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你的屁股上本来就有个洞,你穿不起裙子也不至于穿个破裙子出来丢人现眼,连屁股都露外边了,恶不恶心人!
围观的人群发出哄堂大笑,显然他们都看到了妻子裙子上的那个破洞。妻子听到人们的哄笑,看到他们脸上不怀好意的表情,禁不住用手去摸自己的裙子。我不知她是否摸到那个破洞,紧接着她拨开人群,脚步轻盈,像被疯狗追得惊慌失措的兔子一样,逃命似的冲出了电视台的大厅。
我也跟着向外走去,我听到背后有一群人在哄笑。我没跑,我的样子看起来很镇定,脚步虽快,却很从容。我看见妻子的脑袋像卷进旋涡的树叶一样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我感觉不妙,赶紧加快脚步,跑了出去。
我跑出大门,正在四下寻找妻子的身影。紧接着前面的十字路口,在等待过马路的人群中传来一阵嘘声和尖叫,我抬起头,看见妻子在一群呼啸的汽车面前,像个跳高运动员一样凌空跃起,长长的红裙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刺眼的光,血一样弥漫。
这是一场要命的车祸。妻子冲出电视台的大门,就在她奔跑着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没看到红灯,她的一条腿被汽车撞得粉碎性骨折,我不得不在未来的年月努力为她更换各种廉价的假肢。现在她再也不穿裙子了,不管天气有多热,她始终都穿着一条长长的牛仔裤,并用厚厚的袜子把她的一条腿和一条假肢遮得严严实实。
我们的命运就这样发生了转折。如果我一开始就不同意她去比赛,如果我一开始就陪着她去买裙子,如果我能细心一些及时发现裙子上那个该死的破洞,如果我能在她遭受嘲笑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如果我能在她跑出去时及时追上她……
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如果的事,那该死的蛀虫不仅毁掉了妻子的红裙子,也毁了我们的生活。
之后,我们不可避免地离了婚。我们在一起实在找不到话说了,从她出事的那天起,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两人都变成了哑巴。后来有一天,她终于开口对我说,我们离婚吧。我没说什么,却郑重地朝她点了点头。
办完离婚证之后,我们回来经过我工作的轧钢厂,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事,眼睛一下湿润了。她望着我,有些嘲讽地问,后悔了吗?
我摇着头说,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告诉你,天车并不是开往天堂的火车,一点诗意都没有。
她张了张嘴,声音突然哑了,说了些什么,也好像什么也没说,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瘸一拐地走了,留下我呆呆地站在大街上。
她用车祸肇事者所赔的那点钱买了一台电动缝纫机,开了一家缝纫店,帮人改个裤脚缝个纽扣之类的。我不止一次去光顾过她的生意,却一分优惠也没给我。
她让我滚远点,说不想再看到我。我却嬉皮笑脸地回应她,并故意和她作对一样,不管她的小店开到哪里,我就把房子租到哪里。有时我休班,就整天趴在窗口,看她在狭小的店里摆弄那些衣服,有时遇上式样好看的红裙子,她都从缝纫机前站起来,把裙子往自己身上比画。没过多久,她又生气地把裙子扔在地上。之后她就关上店门,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后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修鞋匠把摊子摆在了她的门前。那家伙同样是个瘸子,却能说会道,经常把她逗得哈哈大笑。两人越来越熟悉,有时修鞋匠还从外面买点卤肉或是小凉菜,两人就在店里那张用来熨衣服的大桌子上一起吃饭,看起来,很像两口子。
她过生日的那一天,我去商场想给她买点东西。即使离婚了,我仍然无法把她从生活中抹去。我在商场碰上了那个修鞋匠,他正在女士服装区徘徊。我问他买什么,他说准备给女朋友买件衣服。我问是那个缝纫店的瘸子吗?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我说,你给她买一条红裙子吧,她最喜欢红裙子。
补鞋匠摸了摸他鹦鹉一样皱巴的鼻子,不相信地望着我。我肯定地对他点着头说,你相信我吧,我是他的前夫,我知道她最喜欢什么。
我不知他最后到底买了什么,我什么也没买就走了,回到租住的那间平房,莫名的烦躁像讨厌的苍蝇一样让我心绪不宁。我爬在窗台上向妻子的缝纫店眺望,她正坐在缝纫机前发呆,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们认识的那天下午,我们躺在河边的草地上对未来生活进行憧憬时那天真的表情。
过后我听见叫骂声,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她疯了一样,手里不停地挥舞着一把裁剪尺。补鞋匠手里拿着一条红裙子,一边躲着妻子手里的裁剪尺,一边惊惶地从缝纫店里往后退。
她一直追到了大街上,她残缺的身体每前进一步,就像在蹦蹦跳跳一样,样子滑稽可笑。补鞋匠一边躲,一边委屈地喊,干啥呢?干啥呢?你疯啦……
她摔在了地上,她的那条假肢离开了身体。补鞋匠上前想扶她,却被她捡起来的石头砸中了脑袋。我以为补鞋匠这时肯定会离开,可他没有走,蹲在不远处,不管她怎样朝他扔石头,吐口水,他始终没走。他一直捂着脑袋,像颗肮脏的口香糖一样顽固地粘在地面。
她坐在地上一直哭,她的哭声惊碎了整个街道,尘土飞扬。最后她实在哭累了,就努力爬起来,然后捡起那条假肢,装在腿上,回到店里,关上了门。补鞋匠又回来坐到门前,他侧耳听了听门内的动静,之后扭转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吸了几口,又掐灭,把烟屁股装进口袋,然后靠在门上,好像睡着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孔雀缝纫店又开了门,补鞋匠也仍在店门口摆摊。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
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穿着一条崭新的红裙子,不长不短,刚好及她的膝盖。裙子下面是她穿着白色长袜的一条腿和一条假肢。
那一定是补鞋匠听了我的话买给她的那条,那鲜艳的红色让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在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