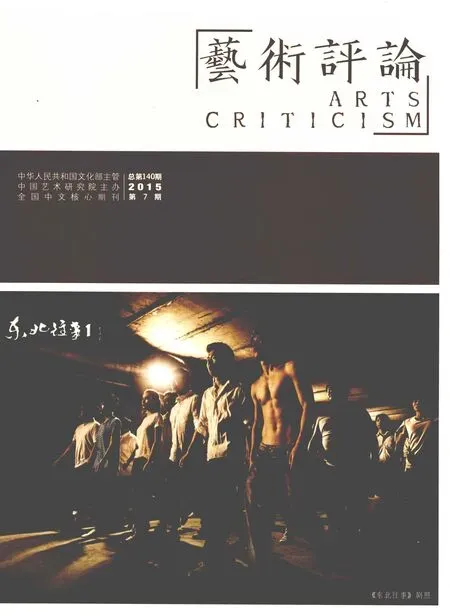生命·情怀·希望
——从我近年来的创作谈起
王丹红
生命·情怀·希望
——从我近年来的创作谈起
王丹红
我的音乐之路
音乐是美的化身,人们相信音乐的美能够产生感化甚至是改变人的艺术力量。当我还在咿呀学话的时候,音乐与我的这份缘定就已在不期然间相逢,绽放出宿命里早已刻画好的那一帧容颜。那首“红太阳照山河,小朋友们多快乐……”的儿歌第一次叩响我对音乐的渴望,歌唱伴随着我的童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父母对于音乐的喜爱,使我从小就被老式的磁带录音机里播放的那些音乐熏陶着,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后的时光,就是专心入神地趴在那台录音机前,憧憬着另外一个世界带给我的无尽遐想。这样的生活也许奠定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长大些,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吉林艺术学院红色的院墙,我都情不自禁地驻足聆听,那些从琴房里传出的琴声、歌声悄然打开了我少女时代最初的人生理想,心中犹然升起的羡慕之情使我无数次地幻想着自己也可以走进这里成为一名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这仿佛成为我心里不可回避的生命激情和最美好的真挚愿望。
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启蒙老师。尽管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艺术,但我知道,我喜欢、我热爱。这些美妙的琴声、歌声让我体会到源于心灵深处的自信和美感。也是因为这份喜爱,我努力考入了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开始了六年的钢琴专业学习;还是因为这份喜爱,使我向视野更加宽阔的创作领域拓展,先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作曲专业学习。十七年的专业学习光阴,音乐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在这期间,多少良师益友走进了我的生命,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更是因为这份喜爱,我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在中央民族乐团从事专业作曲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由的艺术创作当中。至此,音乐已然成为改变我人生的艺术力量,激发了我对于美的表现和追求,让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我相信今生有一些美丽的缘份必然相逢,与音乐的相逢是我人生的最美际遇。音乐开启了我的人生之旅、艺术之旅。
生命的感悟——《弦上秧歌》
从2005年第一首民族管弦乐曲《云山雁邈》的创作至今,我在民族器乐的写作上已有十个年头了,从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赋予作品新的时代感,创作上获得不少认可。在这些作品当中,《弦上秧歌》无疑是我最为钟爱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我所创作的唯一一部不受委约、发自内心、表达自我的音乐作品,它来自于我内心真挚的人生感悟和对音乐执着的热爱。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弦上秧歌》问世以来已上演近百场,这在一定上说明了大家对它的认可和喜爱程度。
这部作品创作于2010年。记得在乐曲的解说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秧歌这种火热、粗犷的民间艺术形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就要扭起那让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割舍的秧歌。只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才能领会秧歌,理解秧歌。秧歌是他们生活的缩影,是他们苦中作乐的寄托。在那一时刻,一切苦难都已化解,每一个舞姿都使人颤栗在浓烈的艺术享受中。人们用激情的舞蹈表达着对人生的豁达和超越。就这样,秧歌跳出了感动、舞出了生活。
对于从小生长在东北的我,虽然没有机会真正走入乡间去体会这一极具北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但是从小在街头广场上的百姓娱乐活动中,也耳濡目染了被“城市化”了的秧歌艺术。对于这一体裁形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火热、激情、欢快、浓烈的舞曲形式,而对于这一形式表象后深层次的情感挖掘甚少。在这一欢愉的民间活动背后,隐藏了多少心灵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能听到活泼欢快、思念哀伤、诙谐幽默、奋起呐喊,它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正是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中最直接、最感官的话语表达,使得《弦上秧歌》超越民间舞蹈音乐的形式,成为一部表现力丰富、感染力极强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将舞曲体裁形式最大地心灵化、情感化,就是我对这部作品的美学立意和审美追求。
北方的秧歌通常采用唢呐及锣鼓等伴奏形式。但在《弦上秧歌》这首作品中,我并没有突出吹打乐器的显性地位,而恰恰夸大了最擅长演奏歌唱性旋律的弦乐声部。对于弦乐组的运用,突出体现在音乐形象的角色化、音响的集团化、形态的炫技化等方面。在弦乐器上划奏,成为这首作品极富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其中124小节处采用弦乐组的整体划奏音响来模仿人的言语,这种音响空间的想象彰显了音乐诙谐幽默的形象感,巧妙地将作曲技术与民族音乐风格有机结合,使音乐脱离了惯性写法。同时,弦乐通常以整体集团化的块状音响形式出现,增强了弦乐组的融合性和表现力量。这种音响色彩的展示,弥补了民乐队音色音响融合性差、分离感强的不足,强调了音色分组的个性化展示,增强了各声部的音色清晰度,使乐队的音响空间凹凸有致,韵味十足。
在《弦上秧歌》这首作品中,唢呐的运用也体现了不可替代的显性地位。它多次以独奏的形式出现,使得音乐形象和意境的塑造更加“形似”和“神似”,拉近了观众的听觉亲和力,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慢板部分唢呐第一次独奏的主题,材料来自于东北著名的民歌小调《柳青娘》,配合东北大G调唢呐的吹奏,让人们在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的同时,不由地被这种婉约的心灵独白所打动。这种对中国传统旋律语言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虽然听众感受到更多的是创作的成分,但仍能感受到浓烈的地方特色。与唢呐这种纯美的歌唱性旋律相比,305小节处,所有唢呐声部的齐奏则是人类发自心底的朝天呐喊。这种接近于狂野的剧烈动态,是生存力与自信力的融合,是对苦难的豁达与超越。它如同野生天成,带着荒野的神秘和泥土的力量,充分显示了野性的挚爱,给人以心灵的颤动!
《弦上秧歌》的创作正值我人生的转折点——即将走出校门迈向社会的过度时期。当时创作思想正处于极为纠结的阶段。从本科到博士历时十一年的学习经历,使得我们对现代作曲技法及先锋的美学理念深信不疑并急于展示,但内心又常常自问,先锋的技术手段和曲高和寡的艺术追求真的能完美表达自己内心所想吗?如何将自己所学的技术理论与心中所追求的美好音乐相结合,如何在体现理性逻辑思维、高超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追求感性的最大化、听觉的最优化呢?经过《弦上秧歌》这首作品的创作实践,我最深的体会是:要通过学习和探索传统民族音乐和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点,寻找个性化的音乐语言,追求音乐的思想深度和情感依托。《弦上秧歌》试图去寻找一种抽象但却生动、深邃但却浪漫、古朴但却唯美的音乐语言,并试图用这样独特的表现手法去表达标题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
情怀的绽放——古筝协奏曲《如是》
2011年,我应邀为电影《柳如是》创作音乐。柳如是,那个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传奇女子,有着聪灵貌美、慧心多艺、果敢有力、奇伟不凡的人生。影片中,我选择古筝作为主奏乐器贯穿剧情的发展,在彰显传统意韵之美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刻画了柳如是复杂的内心世界,音乐成为画面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时隔两年后,受年轻古筝演奏家苏畅之约,我就将《柳如是》的电影音乐主题重新扩展、升华,使之提升为更具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纯器乐化协奏曲。这首作品于2012年5月由指挥家李心草先生指挥中央音乐学院EOS交响乐团首演于北京音乐厅。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喜爱,后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多地演出。目前作品已有交响乐伴奏版、民族管弦乐伴奏版和钢琴伴奏版三种演出版本。
作品的主题来自于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中的【皂罗袍】唱段。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唐诗、书法、昆曲,是中国人的三种“痴迷”。是啊,《游园惊梦》完美地栖息在悠远岑寂的昆曲《牡丹亭》中,当我们去开启她时,不由得被那一片“姹紫嫣红、断井颓垣”蓦然心惊。昆曲以她那样一种华美、细腻、精致、婉转的姿态示人,并穿越百年,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韵味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是一种独特的、波动的、耐人寻味的美感。古筝有其以韵补声的特色,通过左手细腻的演奏技巧,可使单音在延续的空间展现出极具韵味、一波三折的音响效果。这种不刻意、不造作、缓缓流淌、感化心灵的美与昆曲的婉转、深情之美不谋而合,如“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主题乐段在开场以独白的形式娓娓道来,右手异常朴素的单音演奏,却配合上左手“压”、“揉”等最具古筝特色的表达方式加以修饰,使这段音乐远离世俗的浮躁而畅达古意,用简单的笔墨技巧表现出高远意境。
接踵而至的乐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然闯入,与之前古筝宁静、淡雅的音乐表述形成反差,给听者的感官和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力。中国传统音乐中衍生变奏、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东方人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和中庸的人文情怀。一切都来得那么不慌不忙、附庸风雅。那么现代音乐所强调的个性化张扬以及凹凸有致的音响空间,就使得“过渡”、“连接”不再成为必要了。这些跌宕起伏的“块状”音响体,形成了“发散性”的音色组合和新奇的空间效果,既让人感受到了极具戏剧性的艺术张力,又使人领略了现代作曲技术所带来的音响特征。在古筝协奏曲《如是》当中,乐队两次采用了这种创作手法进入,虽然抛弃了传统音乐中旋律贯穿发展的线性感,但作为音乐发展的新动力以及艺术形象的独特造型,增加了乐曲的紧张度和期待感,也使协奏曲中竞奏原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夸张处理。前景与背景、遥远与临近的空间反差,向我们展示了多维的、立体的音乐空间。主题在乐曲结尾处以充满光明、恢宏大气的乐队全奏得到了震撼心灵的升华。我曾与很多演奏家探讨过《如是》这首作品,虽然主题来自于电影音乐,但并不是描写柳如是传奇的一生。古筝协奏曲《如是》像一朵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的艺术之花,美丽的外在形态之下饱含着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意味和东方哲学文化神韵。正如《金刚经》结尾处这样写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不断回归内心的过程中寻求心灵的净化、人生的修行与生命的参悟,而这无疑也是中国文化艺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与最高境界。
希望的腾飞——扬琴协奏曲《狂想曲》
2011年在受邀为扬琴创作一部协奏曲的时候,我曾有些犹豫和为难。扬琴,相比于其他的民族乐器,它的文化承载和情感依托并不出众,那么,该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它的艺术魅力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在我看来,这种对于歌唱和煽情的不擅长反而成就了扬琴这件乐器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国际化的艺术视角,同时敲击发声的演奏原理,也使扬琴不受音区和定弦的局限,便于展现宽幅的音响空间、和声色彩丰富多变等方面的特长,因此将这首协奏曲定位在动感、时尚、炫技、火热,定能展现一个完全令人耳目一新的扬琴作品。
这部作品最初为交响乐队伴奏,2014年,我又将其改编成民族管弦乐队伴奏。作品轻松明快,充满动感,吸收了爵士乐的风格特征,采用了狂想曲的结构形式,自由洒脱。利用非传统和声及流行音乐的节奏型,将扬琴这一传统古老的民族乐器注入了新的表现活力,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和音响中展现出一个绚烂浪漫并富有动态的音乐空间。
节奏世界的律动是音乐持续不断的动感来源,它所蕴含的无限神奇的变化和奥妙产生强大的磁场,散发出使一切音乐更为生动且更有艺术感染力的非凡魔力。在音乐开始,8/7拍的切分节奏,带有强烈的爵士乐音乐风格特征,是整首作品的核心细胞;中段运用了布鲁斯音乐的调式及和声,轻歌曼舞、摇弋生姿;第三部分,音乐是力量的积蓄、情感的激荡、高潮的爆发,环环相扣,让人荡气回肠。在乐曲的尾声,开始的核心节奏又以乐队全奏与独奏扬琴呼应问答的形式夸张再现,音乐在天旋地转般的狂野舞蹈中绚烂绽放、结束全曲。扬琴在这首作品中,既有原始的质朴美感,又被融入了现代的时尚风貌和独具匠心的现代作曲技法安排。这些丰满细致的音响效果,让我们在感受原汁原味的同时,不禁对这与时俱进的艺术质感有一些意外和惊喜。
一个作曲家的成功,除了归功于他自身的创作才华外,更要归因于他所处的时代。与其说我们颠覆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不如说是在继承发展中选择了进一步超越。艺术的道路就犹如历史走过的道路一样,一种艺术样式也好,一种文化传统也罢,都有其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但在规律面前人并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正如古典艺术在“古典时代”终结后,以另一种身姿和形象活跃于当代,人类文化的血脉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穿越时光而成为不朽的典范。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现代建构与革新,需要我们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胆识,也是我们在面对传统时应有的态度和文化精神。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应更多地跳离一般性的、指向性的文化背景,我们应看到它在拥有悠久历史的同时,也处在一个拥有年轻生命力的新时代。中国民乐新的风貌会有更广阔的前景,在面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同时,更要面对世界的未来。
年青一代作曲家应该紧紧依托民族民间优秀文化,并将其提炼、升华,创作出直通大众心灵的音乐,唤起人们审美情感共鸣的艺术力量。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层次的艺术力量,是和人的生命精神、信仰、时代进步潮流和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是能够超越时代局限而释放出日久弥新的艺术力量。
经历了20世纪音乐的发展,作曲家们更多关注创作观念、技法的发展和探索,希望用新的手段创作。这种对艺术负责的艺术家风范固然可贵,但是在忠实艺术自身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同时,艺术家如何面对社会的需求?正如作曲家唐建平先生所言:当代音乐创作应当超越并解脱现代音乐技术发展带来的创作压力和负担,从容面对学术和情感的取舍,直面人生,宣泄情感,提纯音乐的境界。
王丹红:中国民族乐团青年作曲家、国家二级作曲
责任编辑:陈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