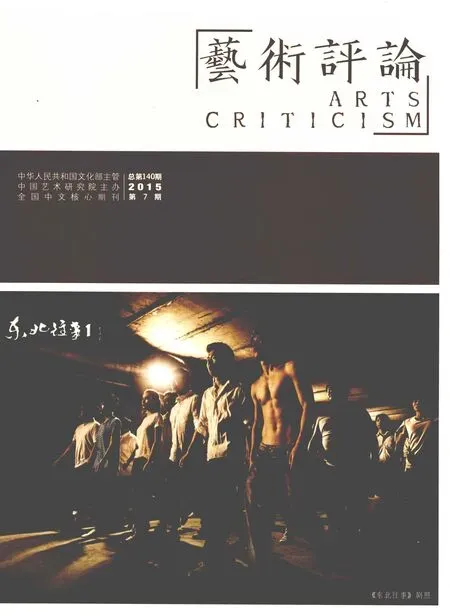努力对时代发出有价值的声音
——戏曲现代戏创作感言
陈 彦
努力对时代发出有价值的声音
——戏曲现代戏创作感言
陈 彦
戏曲现代戏创作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摸索,实践,前行,有甘苦,但更有喜悦,这个喜悦就是建立在国家积极倡导推动,观众自发接纳欣赏,并持续呼唤、催生基础上的。
传统戏曲博大精深,美不胜收,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戏曲现代戏的附丽生成。用传统戏曲的审美手段去表现当下的生活,让更多的时代故事,以戏曲的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正说明了民族戏曲这种传统审美样式的生命强大与壮阔。因此,痴迷传统戏曲的人,更应该对戏曲现代戏抱有一份深深的眷顾与爱怜。
在我印象中,我就是这样开始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首先是我有话想说,想说跟当下生活有深切关联的话语。其次是,我喜欢戏曲这种“发言”方式,既能说,又能唱,还能舞,尤其是能用更加意象的手段,以一当十地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特别是象征感。我比较喜欢象征,不管观众看没看出来,我都要十分偏执地在我的创作中嵌进这些东西,以完善我语言未尽的表达,所以,我就对戏曲现代戏这种巨大的包容形态,始终抱有一种偏好和敬重。
有话想说,这对一个创作者来讲很重要,甚至是我创作惟一的动力。如果都是命题作文,都是硬写,那就很难说是有话想说了。只有“有话想说”,才可能把话说好,说出意味,从而让观众乐于听你去絮叨。我创作过十几个现代戏,也是一点点在摸索它的规律,创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我在创作《迟开的玫瑰》的时候,就是想说,社会都只盯着成功人士,盯着白领,盯着塔尖上的人物,而漠视普通人的存在,甚至嘲弄他们的生存方式,鄙视他们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是不行的。社会的宝塔尖,是靠坚实而雄厚的塔基撑持起来的,长期漠视甚至消解社会“底座”的价值意义,这个社会是会出问题的。正像一个家庭,如果能出大人物,出优秀人物,那一定是有家庭成员要付出代价的,有的甚至是要做出巨大牺牲的。我们需要发掘这些牺牲的价值,从而让社会的宝塔更加稳固并持之久远。
这个戏在剧本初出来的时候,也并不完全被看好,因为17年前,比较流行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各种住在别墅里呼风唤雨的女人,即使农村题材,也一定是把一个村子能搅得天翻地覆的各种女强人形象。而我发掘的是一个为了家庭,为了弟妹,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由“校花”逐渐“滑落”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并最终嫁给一个靠疏通下水管道生活的“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主人公叫乔雪梅,她的生命价值自然遭到了不少质疑,但我固执地认为,这是最真实的社会存在,这是许多人都不能逃脱的生命现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叫命运的东西,我们身边这样的“背运大姐”比比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托起了家人,照亮了别人,而自己却一天天“黯淡”了下去。我就是要通过这些戏,发出一种声音:社会不能整体性地蔑视、嘲弄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更不能给这个世俗眼中的“卑微人群”伤口撒盐,甚或批判他们终日“推磨子,拉碾子”式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苟活”,要努力找回他们身上的亮色,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牺牲与忍辱负重是有价值的,他们是配享有与成功者同等地位与社会尊重的。
这个戏演出已经十六七年了,先后有二十多家剧团移植上演,至今仍是一些剧团的保留剧目,它的生命力,让我感悟到了一种内心必须永远坚守的东西。
还有一个戏叫《大树西迁》,是写上海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故事。这开始是一个命题作文,西安交大是找我写电视剧的,后来发现里面很多历史问题纠结太深,争议很大,不好把握。可我又先后在大学做了将近半年的功课,不写点啥,又觉得对那些十分真诚地接受我采访的大教授们不好交代,最后就写成了驾轻就熟的舞台剧。真正能宏观展示这个事件的,是一些诸如像彭康校长这样的大人物,可戏剧一旦纠缠进咋都叙述不清的大事件中,留给心灵的东西就不多了。因此,我最后还是只虚构了这场大事件中的几个“小人物”的故事,让他们充分打开心灵,从而折射出大事件背后的生命悸动。
一切都从采访开始,我在上百人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还是一些牢骚话,认为历史对这批“西迁”人多有不公,现在呢,与留在上海的人相比,待遇差别又很大,但他们却始终在坚守,并且成果斐然。我的主人公孟冰倩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她三十几岁随着首批“西迁”大军到西安,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五十多年中,一直有离开西部,“东归上海”的梦想,开始是自己想回,后来是想把儿女们迁回去,可阴差阳错,又始终没能如愿,并且根越扎越深,因此,忧愤、抱怨、不满,也就伴随自己走过了大半生。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一个知识分子的专业进取精神与报效国家的忠诚,她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研究创造也硕果累累,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家栋梁之才。就在她年满80岁时,终于实现夙愿,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但仅几个月时间,这颗孤独的心灵,就又悄然自我移栽回了西部,因为这棵生命之树,已经成为那片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戏我想说的话很多,想说爱,说事业,说苦难,说忠诚,说教育,说东西部文化差异,也说到了“文革”,可有一种意思似乎不能不表达,那就是民族的脊梁,有十分光鲜明亮濯拔的那种,但有时那些带着毛边、带着蒺藜、带着忧怨、带着盘回形状的普通生长样态,其实也并不缺乏对大厦的实际支撑力。
我创作的另一个现代戏《西京故事》,完全是一群小人物的生活演进史,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城中村,置身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融合“接缝处”,既想挣脱土地的贫瘠养育,又难以融进光昌流丽、看似很是文明高蹈的时尚都会,内心涌流着难以言表的希望与失望,坚守与放弃,挺立还是趴下,奋进还是沉沦的复杂思绪与情态。
我跟踪了这个群体很长时间,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我们单位屋檐下的那群人。他们有十几位,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就在廊檐下的水泥地板上安营扎寨。据我了解,他们不是要饭的,他们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嫌租房太贵,因此,一年四季就过着这种餐风露宿的日子。为了创作,为了“发言”,我又走进了真正的农民工集散地,一个叫八里村的地方。这里竟然住有十万农民工。另一个叫木塔寨的城中村,当地户口仅一千五百多人,而外来务工人员却达到五万之众,每逢上下班时,真是摩肩接踵,人潮汹涌,煞是壮观,当然,也煞是令人惊悚惶恐。这个庞大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冷漠表情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他们都在思考什么?追求什么?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这种集合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能量?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我先后多次进村,采访农民工个体,也采访村上的领导,他们说,好多年了,一直就这样,来了走了,走了来了,像流水席一样,但始终都是相安无事的。
“相安无事”这四个字,让我驻足徘徊,我就从这四个字中,去寻找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最终确定了罗天福这个主人公,并进一步建构了他那个不无代表性的家庭——一个包含了诸多社会容量的生命“细胞”。这个“细胞”在“西京梦”追逐中,在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经历了精神撕裂,甚至肉体的植皮、切腹、换肝,但他们最终并没有以变形的人格获取幸福——罗天福始终坚持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在生存与精神困境的双重挤压下,顽强持守着做人的底线与生命尊严。他的苦痛,他的隐忍,他的怒斥,他的坚守,虽然是一个小人物的知行,但却触痛了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我以为罗天福们的呐喊、撑持、肩负,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他们的故事必然振聋发聩。
这个戏短短三年,演出已过400场,走过全国二十多个城市,一百多所高等院校,尤其是在秦腔远离了西北本土后的一些南方大学演出,甚至先后引起多个省的教育部门的关注,要求教育部安排返场。而这个戏投入不到二百万元,截至目前,各种收入加起来,已近两千万元。戏演出后,几本没用上的采访素材与无法完全装进戏里的诸多思考,让我意犹未尽,我就又把它写成了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还叫《西京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发行后,先后有报纸连载,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电视剧改编等多种样式出现,而这一切都是一部戏曲现代戏产生后的反响。
通过对自己创作实践的梳理,我以为,民族戏曲既要抓好传统经典继承,抓好历史传统题材创作,也要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努力对时代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中国小说的古典成就很高,《红楼梦》至今仍是一座高山,但小说界并没有躺在那些成熟的章回体中,去不断翻新历史传统故事,相反,小说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创作,基本都是现实题材,他们在努力寻找对时代的介入深度与发言力度。中国画也一样,历史成就很高,但当代画家也有许多人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表现当代生活。更何况中国画与中国戏曲是有本质区别的,戏曲是一种更应重视文本思想精神的艺术,因此,应该在竭力保护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拓展生命空间,在现实题材创作上多点作为,多点时代的焦虑与思想精神张扬。
当然,现代戏创作也面临很多困惑与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些困惑与问题的首要方法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发自己想发的言,就是说在创作上一定要有选择,不是什么样的生活素材都能拿来入戏的,那些可能昙花一现的新闻素材,即便拿到戏里来,也不免捉襟见肘。戏曲现代戏的生态不容乐观,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多人利用这种形式做了“功利”的传声筒,以至使很多人误解了它的美学品格,导致它成了一种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垃圾筐”。长此以往,戏曲现代戏被人误解、误读将成为一种必然。
戏曲现代戏首先是一种与人的心灵有深刻关系的文学,其次是与传统戏曲美学有本质融通的艺术,因此在选材上,一定要有这两个硬指标的考量:心灵打开程度如何决定着作品的情感力量与精神深度;作品是否符合戏曲的艺术规律,是否留有充分的“做戏”空间,依凭的是作者对戏曲的美学特征的把握。否则,再修改,再加工,再“装修”,都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我始终固执地以为,写现代戏,更要深刻地研究历史传统,写古典戏,更要认真仔细地阅读现实,让昨天的历史成为对今天有温度的烛照,让今天的现实,成为对明天有回眸意义的历史。当然,这对我自己来讲,还只是一种向往与追求。就是我们越想深度融入现实社会,越想对当下社会做出有价值意义的判断发言,就越是要深刻认识我们的历史传统,在丰厚的历史传统中,去判断现实走向,去发掘真正的时代价值。因为我们不可能像生物切片一样,独立创造出一段与上下都不关联的历史来。好的现代戏,一定是对历史有承接,对当下有关切,对未来有预判的复合建构。这种东西,有时看似没有太爆裂的当下炙手热度,但却是具有恒温效应的,有的甚至是会愈久弥香的。由此就带来了一个现代戏创作的常态思维问题。
所谓常态思维,就是不闻风而动,不见利起舞,不热粘硬贴,不奋不顾身,不包打天下,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独立思考,冷静分析,沉着出手,在常态生活中,去发掘生动精彩的戏剧故事,从而让这些故事具有更大的精神涵盖与生命长度。
一切好的艺术,其精神实质,都处在恒常诉说状态,不是越新奇、诡异越好的“变脸”艺术。恒常是“道”,在“道”的层面上,平平常常、镇定自若地诉说人类精神生命不可挑战与悖谬的那些价值,才是有生命力的。因此,现代戏的发展,一定要在“道”上多引导,多总结,只有在“道”上盘桓,在规律中行进,才可能水盆显影一般地映照出丰富而深刻的现实生活,从而真正担负起高扬时代旋律与时代精神的责任。
总之,现代戏应该是一种很朴素的艺术,它应该朴素得像久演不衰的《铡美案》《窦娥冤》《杨家将》一样,让一切情感、精神、思想都从朴素中流淌、奔涌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现实标签与时尚包装。戏剧一如人的生命,戏一旦连胳膊腿都是硬安上去的,既没接通血脉,也无神经抖动,却硬要给指头上戴钻戒,给手腕、脚腕上环佩昂贵、鲜亮的玉镯、金链,还要用上好的指甲油,去涂红那些毫无血色的假指甲,岂不本末倒置,欲盖弥彰。惟一的路径,就是把一切精力,都用在对生活与故事的本质压榨上,用在洞开人的心灵上,用在对戏曲本体美学特征的继承、化合、创新上,努力让现实世界那最浓烈、最深厚、最旨远的情感、思想、精神琼浆,顺着戏曲艺术的古老磨道,精美、生动、鲜活并常态地流淌出来,那才是现代戏对时代最有力量、也最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发声。
陈彦:剧作家、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