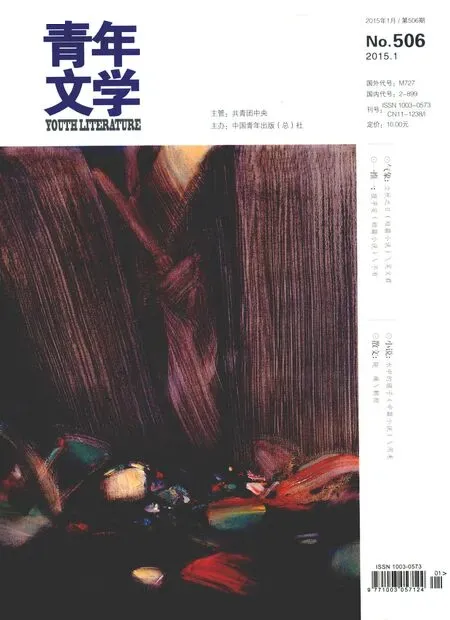阅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 文/李 浩
阅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 文/李 浩

李浩:一九七一年生于河北海兴。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长篇小说《如归旅店》,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等。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韩文。
阅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在这里,我首先抛弃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个作用是存在的,它有时确实存在,但它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还要抛弃的是书中的那些“自有”,什么“自有”黄金屋、漂亮的如花的少女、永远吃不完的粮食;它,同样也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还想到一个词:“开卷有益”。但如果把这个“有益”限定在那种太过实际的“好处”中,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偏误甚至愚蠢。
阅读能给我们带来的——我将它限制在对“自我”的针对上;也就是说,它,会在哪些方面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智慧的丰富和习惯的养成有怎样的益处;它,是如何让我们过上那种“经过思虑的生活”的。
阅读,应会给予我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不,它不是黄金屋,也没有砖和瓦的搭建,它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也只有这个具有虚拟感的房子属于“自我”。在阅读中,只有我和我在阅读的书有关系,在那时,我和他者、和爱与不爱的现实都是隔开的。在那里,我可以与书中的人物一起苦、一起乐,一起经历也一起思考,我可以让自己沉迷于故事中,“一根松针我可以想象成一个骑士、一个贵妇人或者是一个小丑”(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在阅读中,我们的“自我”才得以较完整地保存,而在其他时候这个“自我”的完整性是不存在的,你需要在种种关系中适应、改变和妥协。“我在阅读”,在这样的阅读时刻,我们只会在意我们自己的阅读感受,只会把自己摆放于故事中,那种独立性让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它携带于身体和心灵的内部。
有人说(不止一个人说),人是生而孤独的,这个孤独不会随你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而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我们承认它是事实,我们的孤独和孤独感与生俱来,尽管在许多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孤独淹没于喧嚣和过于喧嚣中,但繁华过后,孤独还如退潮后露在外面的石子,坚实坚硬。本雅明曾宣称,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它当然有它的片面性,但,也包含着巨大的合理性。
阅读,可以让我们部分地摆脱那种孤独感,可以让我们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和我们心心相印的人,有一些肯于和我们对话交流的人,有一些在黑暗中给予照亮的灯。
阅读,更为本质的是,让我们在感受孤独的同时享受它,重新审视和发现它存在中的另外侧面。在阅读搭建起的房子里,我们和我们的孤独一起上路,起伏,颠簸,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
当然,在这间“自我”的房子里,我们大约也必须和那些伟大的作家学者、伟大的作品一起思索:什么是个体?个体的同一性寓于何处?“自我”究竟靠什么来确定?进而是,一个人,是否真的能理解他自己?
阅读,可以让我们过上多重的生活,让我们体验也许此生永不可有的“阅历”。像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至今我的双脚还尚未到达过纽约、伦敦、伊斯坦布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但这不妨碍我对我之外的人物、生活、风情和经历的了解。
在一篇题为“阅读”的文字中,我曾这样写道:“我穿着一副旧盔甲,骑着一头很不像样的毛驴,去和抢夺公主和心怀不轨的人作战,去和谁的魔鬼的风车作战。我喝过一杯非常古老的毒药,在那时,我发现泪水是玫瑰色的,并且可以风化成石头。我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用厚厚的衣服裹紧了身体,但冬天的风还是钻入了我的鼻孔;在罗马,我和阿波罗的部队作战,对抗着国家和我自己的命运。我有过一副好嗓子和总是长不大的身材,敲击着胸前的铁皮鼓,唱碎了教堂对面的玻璃,使硝烟的气味、奶奶裙子底下土豆的气味、刚刚捞起的鳗鱼的气味一起透过来,让我感觉着浑浊的窒息。我还是一个幻想者,用松针和树叶编织骑士、贵妇和小丑的故事,我的舅舅在一次战斗中被迎面而来的炮弹炸成了两半儿,心怀恶意的那一半儿率先回到了家乡……与此同时,我还经历了树上的生活,骑鹅旅行的生活和镜中的生活,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生活以及炼狱中的生活,巴黎妓女阴暗潮湿的床笫生活。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品味着过于喧嚣的孤独,面对一面湛蓝的湖水不停发呆,据说一枚吸人魂魄的宝石被丢在了里面。
我说春天是黑色的,二月的墨水足够用来痛哭,我说四月是一个残酷的月份,寒冷还在继续封锁着那些本来就迟钝的根;而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石榴树的亮光照进了她们的篮子……是的,我说过这些。“在阅读中,我成了他们。”“在阅读中,我成为过法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哥萨克人、日耳曼人、犹太人。我成为过老人、孩子、强壮的男人或卑弱的男人、患得患失的男人、绝望的男人、待字闺中的女孩、沦落风尘的女子、杀人犯、吸毒的人或伪币制造者……我成为过卡夫卡、普拉斯、柯西莫男爵或者包法利夫人。我是那个被封在果壳里的国王,用心痛和麻木写着流水落花的诗;我是那个生在午夜的孩子,我是那个打开了雪夜房门的日瓦戈,我是,一个坐在书籍中间的阅读者。我承担了他们的命运,分得了痛苦、喜悦,让人心酸的笑话和沧桑感,分得了泪水、血液、愤恨和冰冷。”没错儿,阅读,让我们成他们,把他们的阅历接驳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一生有了三生五生也体验不到的多样和丰富。也正因如此,我对博尔赫斯一句略带傲慢的话深以为然:“虽然我经历得很少,但我的阅历很多。”
阅读,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灵魂,它帮助我们打开,一再地打开。巴尔加斯·略萨也曾谈及:“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尼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的城市通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的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人物)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
“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竖起的分界。”阅读,还会给我们建立一个和现实生活有所区别的彼岸世界,而这个属于幻想、想象的世界,是我们此生不能的,也是来生所不能的,可在文字中,它得以实现,并把我们带入其中。
“在阅读中,我成了他们。”——没错,在阅读中,我成了他们,他们的经历和内心的波澜也随之成为我们的,他们所喜所爱所恨所恶所不耻也随之成为我们的,他们在遇事时的释放、虚荣和算计、内心里小小的恶和毒也随之成为我们的。阅读,让我们对“非我”获得了更多的理解,让我们对不同获得了更多的理解,也让我们对习惯上的“敌人”获得了更多的理解。这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这是阅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益处之一。
通过阅读,我们开始理解恺撒、哈德良、成吉思汗、李煜、哈姆雷特、李尔王,而在此之前我们可能觉得这些“故人”或者虚构的人物与我们没有半点儿的关系,我们不会是他们,永远也不。反正我不。在日常生活中我缺乏做帝王的野心也缺乏做帝王的机会,我觉得我与农夫、铁匠的关系可能更近一些。通过阅读,我们开始理解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把她们看成是爱慕虚荣的风流娘们儿,对她们侧目,对她们的出现露出鄙视,对她们的所做表达不耻。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从没有想过试图走进她们的内心,看看其中都有什么,发生着什么。是阅读,让我们对她们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和理解,进而是体谅,真切的悲悯。
在阅读中,我们也许会参与到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站在审判者一方,也站在受审的一方;我们会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人物)一起经历罪与罚的痛苦,并和他一起为自己辩解。很可能在此之前,我们自然而然地站在“法庭”的一边,不愿对杀人者多看一眼,更不用谈什么理解和同情了。
阅读中,我们透过谢林、康德、黑格尔、尼采、罗素、哈维尔、哈耶克、米兰·昆德拉的眼,卡夫卡、卡尔维诺的眼,观看这个世界,思虑这个世界,观看其中的人和人生。阅读,会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和体谅他人,会在我们在行事的时候能够换位,站在另一个方向去思考而不是只有自我的角度,不是“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昆德拉对我们“先于理解之前做出判断”的盲目热情提出过警告,然而可悲的是,多数的人总是习惯于这种愚蠢。我成为他们,我在他们身上“发现”属于我的魔鬼和天使,这是阅读给予我们的,它会使我们部分地打开封锁我们头脑的禁锢,当然也会使我们在处理具体事物、提出建议和自我思考时变得犹疑和忐忑。
崔卫平在她的《积极生活》中说过:“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思想的第一秒钟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其相反的意思。”——别轻视这份忐忑和“摇摆”!它,恰是一种文明性的标志,是种可贵的“进步”。有了这份忐忑和“摇摆”,我们才更能够避免对他者尤其是弱者的无端伤害,才能避免和努力避免陷入那种被阿伦特指认出的“平庸的恶”,在行事、决定的时候多一些更具情怀的“人性”。我珍视它如同珍视被忽略着的黄金。
阅读,让我们的生存获得知识和智慧,这点当然需要强调。关于这点已是常识,我想我们不必过多重复。巴尔加斯·略萨在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阅读颂 虚构颂》中曾谈道:“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
阅读,让我们知史、知事、识人。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某些对人生、社会、生存认知的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更多地依赖于对文学书籍的阅读,它的作用超过我对哲学和社会学书籍的阅读。因为,文学的强光,一直追踪着个人,行动的、有血肉的个人,它更多的,是对那些个人行为的拷问。在这个拷问中,我把自己放在了里面。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泰戈尔)
⊙摄 影:印度行吟7 作 者:山 哈
我们还能在阅读中获取什么?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还想强调,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和体味文学的美妙,在那个时候,你的神经末梢都需要张开,努力捕捉贮含在“稀薄的文学性”中的让人回味、感吁和震颤的魅力。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的第一节,即向我们言说过他对文字的感受,很明显,他属于那种“理想读者”:“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到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这种看似过于玄奥的阅读感受是否时时存在?它果真如此?我想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譬如那首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它的所说、意味,当然可以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包括含在其中的吁叹,然而一经翻译,其中的魅力必然会遭受到大大的减损。在对它的翻译中,或多或少会扯断密布于词语之间、有着丰富质感和味道的神经腺,而那些可意会而难言传的微妙,恰是文学最为核心的部分。
再看另一首诗,作者是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献给父亲的挽歌》的第三节,如是写道:
什么也不能使你停下。
最好的日子不能。安静不能。海洋的摇动不能。
你与你的死亡继续前行。
树木不能。
你在树下走着,树木不能遮住你。
医生不能。
他曾警告过你,这位满头白发的青年医生曾救过一次你的命,
你与你的死亡继续前行。
什么都不能使你停下。你的儿子不能。你的女儿不能。
她曾喂你吃的,使你又成为一个孩子。
你的儿子不能,他曾想你会永远活着。
摇动你的衣服翻领的风不能。
把自己赋予你的静止不能。
变得更沉的你的鞋子不能。
不愿看前面的你的眼睛不能。
什么都不能使你停下。
你坐在你的房间中凝视着这座城市
并与你的死亡继续前行。
你继续着,让寒冷走进你的衣服。
你让血渗进你的袜中。
你的脸变白了。
你的声音裂成两半。
你斜靠在你的手杖上。
而什么都不能使你停下。
那给过你忠告的朋友们不能。
你的儿子不能。你的看着你渐渐变小的女儿不能。
你叹息中的疲劳不能。
你的充满了水的肝不能。
盛着你的手臂的疼痛的衣袖不能。
什么都不能使你停下。
你与你的死亡继续前行。
当你与孩子们玩耍时你与你的死亡一起前行。
当你坐下来吃饭,
当你在夜里醒来,泪水涟涟,你的身体在啜泣,
你与你的死亡继续前行。
什么都不能使你停下。
过去不能。
天气明媚的未来不能。
从你窗口望去的风景不能,墓地的风景不能。
这城市不能,这座木质建筑的可怕的城市不能。
失败不能。成功不能。
你什么都不做只与死亡继续前行。
你把表贴近耳朵,你感到你在滑行。
你感到你在滑行。
你躺在床上。
你把双臂叠抱在胸前,你幻想着一个没你的世界,
幻想着树下的空地。
幻想着你房间中的空地,
幻想着由于你离开而空荡的空地。
而你与你的死亡继续前行。
什么都不能使你停下,
你的呼吸不能,你的生命不能。
你需要的生命不能。
你拥有的生命不能。
什么都不能使你停下。
它当然可以重新翻译,用散文的方式,这种有些口语化的诗,似乎对它的翻译可以更容易些。它写下的是父亲的死亡,以及诗人对“死”和死者的打量——父亲走着,它缓缓“离开”,只把身体留在了这里。我们从第一句开始翻译……然而,你会发现,每动一个词都会对这首诗的意韵构成减损,每动一个词都有血迹流出,那种含着的、像苹果汁含在苹果中的味道就削减一些。形式便是内容,它的强烈的形式感帮助它的言说达至最佳,文学的魅力往往包含于那些微细之中,它有太多的丰富、歧义、智识和神经腺,它经不起不经意的触碰。
我们再看,《百年孤独》中那些恐龙骨架一般精密而细致的结构,字里行间充盈的诗性,那个奇妙的让人叫绝的开头:“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我们还可以枚举,像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布鲁诺·舒尔茨的《鸟》……比如《鸟》中,这样写道:“随着寒冷和无聊袭来,日子开始变得更加坚硬,像陈年的面包。人们开始兴味索然、慵懒冷漠地拿钝刀切这种面包。”——日子,面包,冬日这种面包,比喻套着比喻,它们获得了连绵,获得了形象和张力。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最后一句这样写道:“他把我剩在这个充满了责任和鬼火的世界上了。”——我承认我不止一次地对它们进行改写、翻译,把我想到的、能想到的意思都写在上面:然而我发现,它们内在的部分是难以穷尽的,它们在另外的语言中意味尽失。
这样的阅读对我们来说是种考验,它敞开,复杂,变化,甚至小有隐晦不明,需要我们进行猜度和填充。它需要我们时时准备停滞下来,品啜,思考,体味,并接受其中的“灾变气息”……然而一旦进入,我们就会着迷,被震撼,感觉着两块肩胛骨之间的颤动,会心,甚至感觉,这其中的妙处,只有我和它的写作者才懂。“这是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陈超先生反复强调“审美的傲慢”,在我眼里,这种傲慢应产生于我们对文字的敏感中,对言外之意的敏感中,对那些微和妙的敏感中。
当然,我们也在阅读中识见写作者的独特风格。这点也异常重要。纳博科夫特别指出:“风格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一个措辞问题。风格的含意远远超出这一切,它是作家人格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或特性。因此,当我们谈到风格时,我们指的是一位作为单个人艺术家的独特品质及其他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有必要记住的是,尽管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他或她的风格,但只有这个或那个独特的天才作家所特有的风格才值得讨论。这种天才如果不存在于作家的灵魂中,便不可能表现于他的文学风格中。”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纳博科夫认为。我承认,我也部分地如此认为。
阅读,会给我们一种智力博弈的快感,探寻的乐趣。把阅读单纯地看成是娱乐和消遣是不对的,它不止于此,远不止于此,虽然游戏和娱乐的功能一直存在。相对而言,我更看中阅读中的“智力博弈”,它让我们必须全身心地参与其中,和它的写作者一起搭建,一起寻找,并一起思考:下一步,我们将通向何处?迎接我们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冒险?非如此不可吗,还有无更为“适合”的可能?娜拉一定要出走才会获得“新生”?娜拉出走之后又会怎样,她能否因此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我和我们的身上,那条属于阿Q的尾巴被我们丢掉了没有,我应当怎样审视它?有这条尾巴还是没有了这条尾巴我们会更幸福些吗?那么漫长的时光里为什么这条尾巴一直得到继承?……
在那宗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如果错过,纳赛尔是否也可以错过故事的结局?还是,我们得和马尔克斯一起,用另一道更精密的齿轮再次缠住他,把他再次塞入结局之中?当然有时,我们还会和那些大师们、先哲们发生争辩。
说实话,我极其看中这一点。阅读从来不会是单单的顺从,即使他们的确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试图“博弈”一下……
我希望我们是那种坚定的怀疑主义者,所有的信念都必须建立于怀疑和争辩之后的基础上。我相信,如果不加棍棒,所有的真理都可能“越辩越明”,何况文学还是一种强调不断创造、摆脱旧有的特殊学科。事实上,相对于上帝而言,不只是莎士比亚有一千条错误,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也都如此,至少都会留出可供填充的空隙。
单就文学而言,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述中的某种冗长在“现代性”中似乎已无必要,如果变成当下的写作,它至少可以部分地弱化或避免;卡夫卡身上那种“现实主义”的旧蝉壳似乎也可蜕得更为干净,人物滔滔不绝的饶舌可以部分地变成“行动”;巴尔扎克太迷恋于表象和物欲了,如果有束高处的光透过来或许会更加完美;而博尔赫斯,他和巴尔扎克有显著的不同,他极力处在高处,在文字中埋伏,追问的多是形而上的问题,而如果在他身上加入些巴尔扎克式的生活质感的东西,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和《寻欢作乐》的毛姆争辩过多次,我们可能并不喜欢让·热内《鲜花圣母》中描述的生活,或者不习惯《佩德罗·巴拉莫》,它完全可以变成一部拥有四十万字的大书,那么多的线头可以黏接在一起……
不,我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值得敬仰,恰恰相反,它们太值得阅读太值得敬重了,我说的是,用今天我们所获得的更多写作经验来看,用我们“带有独特面部表情”的缪斯的眼光来看。事实上,我们需要某种“过河拆桥”,需要某种“偏执”;我们也许,可以在悄然的争辩中,拨动属于自己的“反方向的钟”。
在一则访谈和一首名为“天赋之诗”的诗中,我所崇敬的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让我激荡的话:“天堂,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没错,天堂,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我承认我鄙视过强的实用主义,正如我鄙视保障了温饱、欲望却无所事事的那些臆想的天堂——天堂,应当有劳作和耕读,有求知的分享和争论,有对美好和真理的认知发现……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这句话被我重复过不下二十次了,我想,我还会重复下去。
诗歌
特邀栏目主持:谷 禾
念及江西诗歌,其源头大体是该从陶渊明开始的,而至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陈师道等,朴素而诚实一直可称为江西诗歌的“伟大传统”,而我也认为,汉语诗歌的“地方主义特质”恰恰就在这里,不是诗人生活在哪儿就天然具备了它的传统,而是诗人有没有通过自己的写作去自觉地建构这传统,进而积淀成为它的一部分。
近读《驼庵传诗录》,顾随先生谈中国古典诗歌,首推诗人是江西籍的陶渊明,谓之“曹操乃英雄中的诗人,老杜乃诗人中的英雄,渊明乃诗人中的哲人”。渊明之伟大,在其真,在其平凡,在其简单而神秘,并以身践凡,凡中见诗。这样的观点我们是否认同是另一回事,但“发现和呈现平凡生活的诗意”总归是所有写作者面临的难题。相比于散文,宋人王安石之诗歌成就似少被提及,但一首《别鄞女》却格外动人心弦。“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决汝,死生自此各西东。”据说王荆公时任鄞县县令,奉调离鄞赴京,临行前,他在一个夜里乘船去和去世两年的女儿告别。在女儿的坟前,王安石抬头仰望浩渺星空,喃喃念出此诗,止不住潸然泪下。父女深情,人生飘零的沧桑尽在此二十八个字之中了。也许,这就是诗歌的力量,这就是朴素的力量。
读《牧斯的诗》,忽然就想到了这些。牧斯当是一个有这样“主见”的写作者,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故乡的远客,而是坚定了自我即是故乡的一部分,并与它血脉相连。故乡如此真实而酷烈,连“同一块岩石上的水/却各奔东西”这样的细节都被诗人看见。牧斯懂得如何紧贴着事物来赋其形、传其神,他笔下的故乡、亲人、出走的父亲、被生活折腾得支离破碎的堂妹,恰恰因为其朴素和诚实,才有了撼人心魄的力量。
八○后的王彦山试图通过诗歌写作搭建起与自然的某种呼应。他有一颗不安的灵魂,并在从孔孟之乡移栽至鄱阳湖畔的“不适应”里犹疑着,徘徊着,述说着。他沉溺于眼前的生活,而又认定“生活在别处”,他一回回“命里不知身是客”,却总不愿“权把异乡当故乡”。但恰恰是刻骨的异乡感和飘零感,让王彦山不断地去怀疑自我,追问自我,写下了这些属于他的“不安之诗”。
《给未知的人》出自另一位八○后女诗人吴素贞之手。在我看来,所谓“未知”,当以“不确定”或“不便确定”去理解,才更准确。对于女性来说,爱情、婚姻、家庭,似乎总是绕不过的纷纷扰扰;纠结也罢,痛苦也罢,羁绊也罢,凝结到心头,总有诗意绵绵地流泻出来,被她们织成色彩各异的动人篇章。阅读她们,其实就是阅读我们未知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愿意她们的诗歌永远是明亮的、温暖的,梦幻般美丽的。尽管我知道这只属于我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