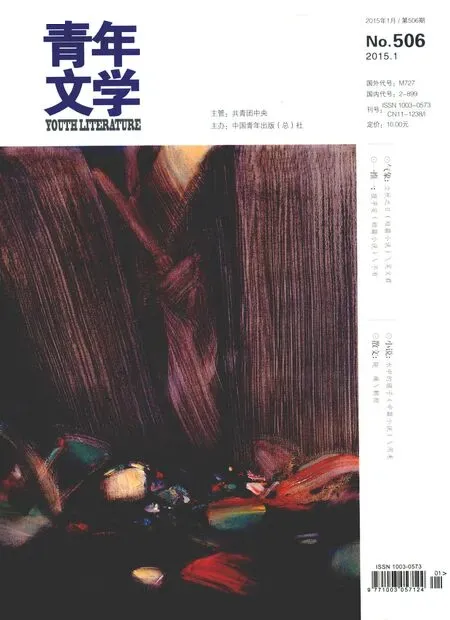月 宴
⊙ 文/俞 胜
月 宴
⊙ 文/俞 胜
俞胜:安徽桐城人,科学技术哲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亮》等。曾多次荣获省部级文学奖项。
电视机是二毛从南方托运来的。那么宽屏的一台电视机,让镇里的快递员小王忘了剩下的业务,一边帮着安装,一边羡慕地说:“乖乖,四十七英寸的液晶显示屏,再宽点就成影院里的银幕了。赵叔,搁咱赵家庄,没有比这更好更大的电视机了吧?”
赵老头想矜持一点,可是那份得意的感觉遮掩不住,那笑意汪在眼睛里,汪在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里。赵老头给小王上了一支烟说:“不一定吧,也可能是独一份的。按我说,要这么大这么好的电视机干什么呢?我和你婶都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
电视机装好了,小王往遥控板里装电池,接了赵老头的烟却不吸,先放到鼻子下闻一闻,然后夹到耳朵上,说:“赵叔呀赵叔,你真了不得,在咱赵家庄,什么东西最好总是最先出现在你家,记得三十年前,在咱赵家庄,你家是第一个有电视机的,那时候,我还从邻庄跑到你家来看过好几次呢!你家总是开风气之先。”
“开什么风气之先哪!”刘老太泡好了茶捧给小王,絮叨叨地埋怨,“我家的那个二毛是个烧包!小王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烧包真是烧得没谱了,你看看我们家的电视机是去年新换的,还是新的吧?这会儿他又送回一台,还要这么大。”
遥控板装上电池了,小王笑着说:“二毛是孝子啊,二毛也有出息,换作我,我想烧包一点还烧包不起来呢!”
刘老太继续絮叨:“这事其实还怨我,上回他打电话来,我告诉他说,现在眼睛不好了,看电视都有点发花。”
“我早就告诉你,电话里不要说那些话,什么头疼脑热啦,什么眼花背疼啦,都不要说,说了有什么用?娃又不在跟前,说了只让他着急,你偏不听。”赵老头插进来埋怨。
“那这话也不说那话也不说,电话里说啥呀,当哑巴?”刘老太不满地瞪了老伴一眼,又笑着对小王说,“我在电话里,告诉他眼睛不好了,看电视都有点发花,我琢磨他是因为这句话,就送回这么大的一台,这么大,眼睛就不发花啦?人老了哪有眼睛不发花的?小王你说说我家二毛可是过日子的人?”
小王打开了遥控板,电视机立刻打开了,声音震天动地,小王赶紧调低了音量,电视上在演清宫戏,一位美女格格正在分花拂柳。小王看了一眼,连连惊呼:“乖乖!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赵叔刘婶你看,这图像清晰得要命,连人脸上的汗毛都看得一清二楚。我说赵叔刘婶,这么大这么好的电视机,你眼睛再花可就没理由啦!”
刘老太笑吟吟地说:“人老了哪有眼睛不发花的!”
赵老头拽着小王往沙发上坐,说:“小王你就别走了,我们看会儿电视,一会儿你婶炒两个菜,中午我们叔侄俩喝几盅。”
小王忙从沙发上站起来,拒绝道:“这哪行呢!赵叔,我是快递员,我得赶快点了,把在您家耽搁的时间找回来。”小王说完就抽身往出走。
赵老头一把没拉住,小王大步流星地跨出门,赵老头撵出门喊:“快到中午了,小王你看会儿电视再走嘛!都是乡里乡亲的,虽说是快递,可哪一样是十万火急的东西,又不是送鸡毛信!”
小王笑呵呵地关上了车门。
赵老头还有些不舍,送快递的车开走了,赵老头还在对着车屁股喊:“以后得闲就来我家看电视!”
刘老太嘲讽地说:“傻老头子,你还真拿电视机当个宝了,现在谁家没有电视机!你还把现在当成三十年前吗?”
赵老头喃喃地说:“傻老婆子,别说你还真提醒了我,现在要是三十年前该多好啊!”
赵老头和刘老太站在门口果真就看见三十年前了,三十年前那个夏天拖着一条慵懒的尾巴,像一只白花猫一般跳到了赵老头和刘老太的眼前。
三十年前,生产队还没改叫村,人民公社还没改叫乡呢!三十年前,刘婶还没改叫刘老太,赵叔还没改叫赵老头呢!刘婶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赵叔在县城的柴油机厂上班,到月就能发工资。三十年前,赵家是有一个工人的家庭,那个时候,谁家有一个工人,小日子在生产队里就红火,让庄户人家着实羡慕呢。
那年的夏天,赵叔从城里扛了一个大匣子回来,四四方方的大匣子,三面都是黑色的塑料板,剩下的一面虽然也是黑色的塑料板圈边,可中间的大部分是乳白色的。庄户人家都没见过这稀罕物,男女老幼全涌到赵家来看。赵叔把大匣子摆到屋外的场地上,不慌不忙的,像魔术师在表演魔术。全庄的男女老幼盯着赵叔的手,全场鸦雀无声。大匣子通上电了,魔术师的手将大匣子上的按钮一按,奇迹果然诞生了,乳白色的一面变成了闪闪的银屏,许许多多的小人儿活动在这银屏上,还会唱歌说话,大伙儿才知道,原来这东西就是广播中说的“电视机”。庄户人家谁见过电视机呢,虽然这只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夏大叔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屏说:“这东西,怕要两百元才能买到吧?也只有你这当工人的买得起,换作我们庄户人家,两年的收入,还得不吃不喝才能攒下来。”夏大叔说完就心疼,仿佛花了他的钱似的。
黄二婶听了倒吸一口凉气说:“要两百元啊!我看我这辈子是买不起了。”谁都知道,庄子里就数黄二婶家最穷,黄二婶家八个娃,五个男娃,三个女娃。几年不给娃做新衣服穿,衣服都是大娃穿旧了传二娃,二娃传三娃……每年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黄二叔都要挑着箩筐,挨家挨户地借粮。
赵叔摆弄着电视机,听着夏大叔和黄二婶的话,心里的喜藏不住,一个劲儿地往脸上爬。刘婶急慌慌地澄清:“他大叔,他二婶,这电视机可不是我们家买的,是我们家老赵借同事的,老赵那一点工资,供三个娃上学都不够,还得靠我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哪能买得起电视机呢。我们家老赵哇,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愣把借来的电视机当成自己买的!”
电视机真是赵叔买的,赵叔花了三百一十元,那年月猪肉已经涨价了,但一斤也才卖一元八毛钱。刘婶那么说,是不想在庄子里当冒尖户呢。
那个夏天,赵家的门前热闹得像集市。
傍晚,赵叔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回来,把门前的土场子清扫干净,洒上清水。全家人吃罢晚饭,赵叔就把电视机从屋子里搬出来,摆放到门前的土场子上。
赵叔吩咐娃们把家里的椅子和凳子都搬出来。三个娃儿,二毛最喜欢干这样的事了。大毛木愣,干啥都提不起来精神的感觉。三丫开始那两天还有点兴奋劲儿,过了四五天,再让她往出搬椅子和凳子,她就噘起小嘴儿了。
家里的椅子和凳子都搬出来了,还是不够邻居们坐。三十年前,庄子里人丁兴旺呢,赵家是小户人家,也有五口人。黄二婶家有十口人,晚上全家出动,十口人齐齐地占领了赵家场院的一角。赵家的凳子不够坐了,有的邻居就从自个儿家里带出凳子来。邻庄也有人跑过来,邻庄的人不带凳子,他们不惜穿过一座田畈而来。他们借着月光随便拾一块砖头或一个土块,就聚到赵家门前的人堆里了。
三十年前的月亮似乎比现在的清亮些,月亮从树梢升起来了,升到了赵家的屋角,就挂在那里,停住了脚。
三十年前电视里的节目似乎也比现在的好看些。演《哪吒闹海》,天旱地裂,缺德的龙王却滴水不降,还命夜叉去海边抢童男童女做祭品。小英雄哪吒见义勇为,用乾坤圈打伤夜叉,又杀了前来增援的龙王之子敖丙,并抽了龙筋。
演《红军桥》,红军桥,造得好,财主老爷过不了。财主老爷走一走,跌断脚来跌断手!
三十年前的电视节目不但娃们爱看,大人们也个个看得津津有味。
白天,庄子里就多了许多“小哪吒”,娃们手上擎着竹枝或柳条做成的“乾坤圈”,在庄子里蹿来蹿去。谁是龙王太子呢?多半是谁家的大肥猪,被娃们追赶得嗷嗷直叫。
庄子里还多了许多“红军娃”,娃们学《红军桥》里的那个小娃,争先恐后地跑到晒谷场上翻空心筋斗。夏大叔笑着说,你们这哪是“红军娃”呀,明明是一只只野猴子!
那年,大毛在读高二,二毛在读初三,三丫最小,在读初一。大毛和二毛的学习成绩都不好,赵叔和刘婶觉得大毛能考上大学是痴心妄想,二毛能考上高中就算是万幸。只有三丫的学习成绩好,奖状一张张地拿回来,贴满了堂屋的一面墙。那真叫堂屋——三丫一张张红彤彤的奖状在土坯墙上亮堂着呢。
傍晚,二毛从学校里蹦蹦跳跳地回来,把手上的书包往堂屋的方桌上一扔,转眼间就没影儿了。二毛出门不是爬树上掏鸟窝就是去河滩里捞小鱼小虾,家里有了电视机,二毛添了一份差事——从屋子里往出搬椅子或凳子。反正放学回来,二毛书是不会瞧上一眼的。
那天,不知是什么由头,刘婶说起了二毛:“这大毛啊,虽说成绩也不好,可再不好也比二毛强,早先得的那两张奖状在墙犄角里还能找到,大毛再不济也考上高中了呢。我这二毛,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连一张奖状都没给我拿回来。我看我这三个娃儿,就二毛和我一样,是土里刨食的命了,唉!”
刘婶“唉”的一声像一根针,在赵叔的心尖上扎了一下。赵叔说:“二毛怎么是土里刨食的命呢?最不济,将来我也让二毛去城里接我的班。”
刘婶白了赵叔一眼,说:“让二毛接你的班?那大毛怎么办?大毛眼瞅着就高中毕业了。大毛身子弱,可不能让大毛留在乡下干农活,唉!”
赵叔的心尖儿又被针扎了一下,忙安慰刘婶说:“大毛是不会干农活,但大毛读了高中,算知识分子了。即使留在乡下,那也可以当小学老师,当个村干部啊,你别愁眉不展的。”
赵叔的话像阳光,从一丝乌云的缝隙里透出来,刘婶的眉头舒展了些,说:“我能不愁吗,娃是我生的,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养了这么多的娃……”
赵叔笑着说:“你才帮我生了三个就叫多?老黄家有八个娃呢,老黄也没有嫌多。”
刘婶不屑地说:“老黄那家还能叫家啊,跟猪圈差不多,八个娃都淘上天,老黄都快被他们气死了。”
赵叔抢白:“八个娃热热闹闹的,就是淘气,淘的也是福气。”
三十年前,赵叔就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那年夏天,刘婶开始向赵叔抱怨了:“天天晚上,不等电视说再见了,邻居们就不散!散了后,场子里一大堆砖头和土块,你说我收拾不收拾?一收拾就到半夜。一大早,我又要去田里干活,我困得慌呢。”刘婶说完,真的就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二毛听见了,自告奋勇地说:“打明儿起,场地也归我收拾,妈要困的话,就早点休息好了。”
赵叔高兴地说:“还是二毛乖,二毛是个乖娃。”
刘婶生气地说:“谁承想二毛还是个吃里爬外的娃!二毛,这不仅是收不收拾场地的问题,每天晚上开电视机不需要电吗?你知道一晚上需要多少电?这电费还不都是我们家自己掏,邻居们谁肯给你出一分电钱?大毛你说呢?”
大毛懒散散地说:“你们怎么说都行,我无所谓,少数服从多数。”
刘婶白了大毛一眼说:“大毛总是一副不要强的样子,三丫你说呢?”
大约经过半个小时的捶打,米糊就变得很细、很黏,妈妈把它从“大石碗”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放入竹匾里,让它稍微晾晒风干。过了几个小时,奶奶和爷爷把糍粑从竹匾里取下来,切成一条一条的块状,还印上福字花纹,十分好看。
三丫噘着嘴说:“爸,自从你把电视机扛回来,我晚上都没法学习了。”
听三丫说影响学习了,赵叔笑嘻嘻的面皮收敛了,说:“那明晚我就不把电视机搬出来了,搁自个儿家看。”
刘婶怪赵叔糊涂,说:“搁自个儿家看,还不一样影响三丫的学习!搁自个儿家看,邻居们能愿意吗?不信你打开电视机,人不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我不姓刘!都是你呀,身边不能存一分钱,有点钱就要发烧,不让扛电视机偏要扛个电视机回来!”
赵叔嘿嘿地笑着说:“哪是发烧呀,我是为了娃,让娃开开眼界嘛!”
刘婶撇着嘴说:“你省省吧,你发不发烧我还不知道,你就爱烧包,拿了一个小红枣子,都能当火种吹。”
赵叔和刘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赵叔把电视机带回城里去,赵叔在厂里有一间宿舍。
对这样的结果,大毛无所谓,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慢腾腾地回屋睡觉了;二毛心里好失落,像丢了魂似的;三丫很喜欢,手里拿着课本,风一般地旋进了自己的房间。
二毛抬起头,眼眶里竟窝着泪水,问:“爸,我做什么事情才能让你高兴呢?”
赵叔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说:“你向三丫学习,拿几张奖状回来,爸就高兴了,爸就带你去城里看电视。”
二毛不说话,又低下了头。
三十年后,刘老太常向赵老头念叨起当初二毛不愿读书的事来,二毛愣是一张奖状没拿回来。赵老头也总是笑着说:“人哪,有没有出息,当娃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有出息的,要不就是像三丫那样学习优秀的,要不就是像二毛那样学习差的。像大毛那样不上不下中不溜的人在社会上最混不开。”
刘老太不爱听,回赵老头道:“尽瞎说,大毛要是听了你这话,不知多伤心!有出息的好是好,可有出息的都飞到天边了,一年也难得见上一眼呀。”
赵老头听了就叹口气,可叹了气后,这样的话下回还说。下回,刘老太还用一样的话来回复他。
现在的庄子冷冷清清的。三十年前,那些把自己当成“小哪吒”,当成“红军娃”的娃们,有的像二毛和三丫那样飞到天边去了,有的没有飞到天边的,也早已扔掉了手中的锄头,像大毛一样在城里谋得一份营生了。
二毛从南方托运一台宽屏的电视机,又让赵老头和刘老太看见三十年前那个夏天的影子了,像一只拖着慵懒尾巴的白花猫。
那个夏天,庄子里的娃不相信赵叔把电视机扛回城里了,他们一连趴在赵家的窗户后面侦察了好几天。赵叔的电视机勾走了他们的魂儿,不知是谁还气愤不过,敲碎了赵家的窗户玻璃。夏大叔的儿子胜保爬到赵家屋后的桃树上,说在树上看赵家屋内更清楚些,却不小心从桃树上摔下来,摔坏了腿。
夏大叔气得指着娃骂:“人穷不可怕,就怕穷得没志气!咱不是买不起电视机吗?买不起咱就不看。”那话分明是说给赵叔和刘婶听的,害得刘婶向他解释了好多回。三十年后,夏大叔仍然耿耿于怀,因为胜保至今仍是一位瘸子。
那只慵懒的白花猫慢慢地爬到赵老头和刘老太的脚前,对着他们“喵”地叫了一声,声音也是懒懒的。刘老太的心尖儿微微一颤,对着赵老头说:“那个时候啊,我不让你把电视机搬进城里去就好了,不搬进城里去,那些娃们一准就一天天地坐在我们家门前了,一天天,一年年地看下来,庄子里一准还是热热闹闹的。那个时候啊,真怨我。”
赵老头拉了拉老伴儿的手,安慰道:“尽瞎说,土地都没把人留下来,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能把娃们留下来?相反,娃们通过电视知道了城里面是什么样子,就更早地往城里面跑了,城里面诱惑大着呢!”
新安装的电视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赵老头和刘老太觉得这声音大得就像三十年前生产队里的高音喇叭。那时候的喇叭一喊,庄子里的人就会从各家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喇叭里指定的地方。可三十年后,即使赵老头和刘老太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像高音喇叭一样,也没有人来赵家瞧一下热闹了。
赵老头看了刘老太一眼。
刘老太看出了赵老头眼里的凄怆,说:“今儿晚上啊,我们还把电视机搬到门前的场地上,一准就会有人来瞧热闹了。”
赵老头闭上眼摇了几下头,然后不摇头了,睁开眼睛说:“老伴儿啊,你就是把电视机搬到门前的场地上去,也不会有人来了。你看,现在庄子里还剩几户人家啊。剩下的几户人家谁家没有电视机呀?”
“电视机和电视机不一样,在家里看和在场地上看不一样。”刘老太赌气似的说,“没有人来,我去请,我去把老邻居们请来,请他们来看场露天电视。”
刘老太去请邻居们了。赵老头在家拾掇着,要把这个晚上过成节日样的,像过八月中秋,不过又和中秋不一样,中秋是赏月,今天晚上是欣赏电视,欣赏二毛托运回来的电视机。赵老头心情愉快极了,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准备好了点心和茶水。
三十年过去了,老邻居还剩下几个呢?从庄子东数到庄子西,从庄子南数到庄子北,从庄子头数到庄子尾,也只剩下黄二婶家和夏大叔家了。
刘老太来到黄二婶家。黄二婶午觉没睡好,哈欠连天地说:“老妹子,我现在都老眼昏花了,哪里还有看电视的兴趣啊!不瞒你说,我家里的这台电视机都是个摆设。不看了,不看了,再有多么大的电视,多么好看的节目,我都不看了。”
刘老太来到夏大叔家。
夏大叔哈哈笑着说:“老嫂子,电视机我家有三台呢,胜保两台,加上我这一台,可不是三台?胜保腿脚不方便,回来一趟不容易,出门前嘱咐我,买了电视机,就要打开看。不看,买电视机干什么?不看,电视机还容易坏。不看,难不成还要把电视机搬到城里去?现在我把这三台电视机都搬在我的卧室里,每天晚上轮番开,我自己家的电视都看不过来呢!”夏大叔的话里还影藏着一丝怨气,刘老太知道那怨气的根就生长在三十年前那个夏天。
刘老太有些扫兴地回到家,赵老头已经把两套茶杯洗三遍了,洗了三遍又用开水烫了一遍。
赵老头烫好了茶杯,把一只只茶杯往托盘里放时,看见刘老太神情落寞地回来,手就抖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问:“老邻居们都不愿意来?”
“不来就不来吧。”刘老太气哼哼地说,“不来,我俩也看一场露天电视。”
赵老头附和着说:“不来就不来吧,不来,我俩也回到三十年前。不来,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分。”
这一天晚上,赵老头和刘老太的门前就摆放着那台四十七英寸的液晶电视机了。门前的场地上还摆放着八张椅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刘老太笑呵呵地说:“八张椅子啊,就权当有六个人在陪我们看电视了。”
赵老头也笑呵呵地说:“六个人啊,每个人都要泡上一杯铁观音。”
电视机打开了,在演一个家庭伦理剧:丈母娘来到女儿家,却瞧不起女婿,把刚当了两个月爹的女婿赶出了家门。
一只蛾子看得气愤不过,从黑暗中飞过来,啪的一声撞到丈母娘的脸上,蛾子哪知道这是电视机屏幕呀,一下子撞晕了头,扑棱棱地掉到地上。
“哪有这么当丈母娘的,即使女儿赶女婿出门,你也不能赶啊。我做了许多年的丈母娘,从来没和我家女婿红过脸。”赵老头和刘老太回头一看,什么时候,黄二婶来了。
黄二婶坐到刘老太的身边说:“老妹子,今儿晚上,我心里总在琢磨你下午说的话,在自个儿家里总也待不住,总惦记要到你家门前来。”
“可不是怎么的,我原来也不想来,可我的脚痒痒的,不知不觉就走到你家门前来了。”赵老头、刘老太和黄二婶回头一看,什么时候,夏大叔也来了。
月亮从树梢升起来了,升到了赵家的门前就停住了脚。月亮清亮得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仿佛从来就没有经过岁月风沙的侵蚀。岁月的风沙只侵蚀人的青春。
四位老人感叹,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三十年,回头看这三十年的时光仿佛只是一瞬,仿佛就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四十七英寸的电视机之间转换。
三十年前的事浮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三十年里,谁来了,谁走了;谁穷了,谁富了……谈也谈不完。
这个晚上,电视机只是配角。谁也没有看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的矛盾怎么发展。
茶杯里的水浅了,又添满了,添满又浅了……月亮在赵家的门前停留了好久好久,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这个晚上,二毛从南方打电话回来,打了好多次,都没人接听。三丫从北京打电话回来,也打了好多次,都没人接听。三丫和二毛就给大毛打电话。
当年,大毛没有考上大学,二毛没有考上高中。可接赵叔班的并不是二毛。二毛初中毕业后,就往南方跑。二毛做生意,先是小打小闹,就像当年在小河里捞小鱼小虾一样。不过现在的二毛,已经在大海里捞大鱼了。接赵叔班的是大毛,大毛有点文化,有一段时间还当上了厂里的车间主任。大毛娶了一个县城里的女人,大毛的根就扎进城里了。那些年,厂子红火得很,女人在大毛的眼里,就像一只温柔的小猫。可现在厂子不景气,女人已经让大毛做一只温柔的猫了。大毛离家最近,可也不能常回来。
三丫读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城里。三丫接过赵老头和刘老太来北京城里住,北京的空气不好,赵老头和刘老太一来就添咳嗽的毛病,又觉得住在高楼大厦里不如住在乡下自在。赵老头和刘老太来北京城里最长的一次只待了三个星期。
这一天晚上,三丫和丈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得好好的,三丫的眼泪突然就不争气地往出流了。
丈夫奇怪地问:“这演的是喜剧呢,没来由的,流什么眼泪?”
三丫抽抽搭搭地说:“我爸和我妈寂寞了,他们正在流泪呢。”
丈夫觉得太无厘头了:“尽瞎说,你又不在他们跟前,他们流泪你看见了?”
三丫呢喃:“虽然我不在他们跟前,可母女连心呀!”三丫就往家里打电话了。
这一天晚上,二毛从饭桌上应酬出来,信步走到南方的街头。火热的南方,夜晚才有一丝凉意。二毛抬头,看见那一轮清亮的月了,挂在天空,像极了母亲慈祥的脸庞,二毛心头一热,就掏出怀中的电话了。
这一天晚上,大毛的儿子趴在窗口喊:“爸,你来看今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呀!”大毛上了一天的班,又忙了半天的家务,躺在床上懒洋洋地说:“傻儿子,月亮不就是那么大那么圆的吗!只要是月圆的时候,许多年来一直如此,许多年后,还会一直如此。”
这时候,三丫的电话打来了。一会儿二毛的电话也打来了。大毛就纳闷儿了,这个晚上,爸妈怎么不接电话呢?他们能去哪儿呢?他们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他们能出什么意外呢?大毛决定赶回乡下看看了。
女人骂他是猪脑子:“这么晚了还往乡下跑,你不会再给爸妈打个电话?”
大毛果真就打,大毛的电话打通了。
电话里,爸和妈兴奋地说:“晚上我们又把电视机搬到门前了,黄二婶来了,夏大叔也来了,像三十年前那个夏天一样的。不,也不一样。爸和妈还有黄二婶和夏大叔都没有看电视,是电视在看我们。看我们聊天,我们在月亮下面聊天,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这个夏天,我们准备天天晚上这样聊天,对!就在月亮下面,对!这就叫月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