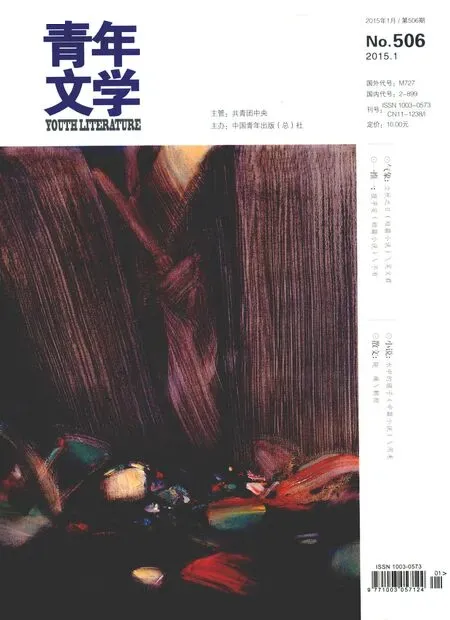冬天的事业
⊙ 文/向 迅
冬天的事业
⊙ 文/向 迅
向迅:一九八四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散文集《谁还能衣锦还乡》《寄居者笔记》《鄂西笔记》等。曾获林语堂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全国鲁藜诗歌奖等文学奖项。
一
这个冬天,父亲一刻都没有闲着。他和母亲在菜园子里挖了一个冬天的石头。他们用锄头、用镐头,像挖金元宝、挖土豆红薯一样,把深埋于地下的石头一个一个地挖出来,然后把它们整整齐齐地码在马路边。足足码了三堆呢。好像这些石头是他们前些年种到地里似的,如今一个个都长得虎头虎脑的,收成不错。
他们从来不曾像这个冬天这样,希望能在种菜和栽了许多果树的菜园子里挖出更多的石头。而在以前,他们总是抱怨,地里的石头实在是太多了,像砧板一样结实,喊天都挖不动。而现在他们却执着于这样一件看起来万分无聊而又异常艰辛的事,把目标对准了石头,没有比这更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厚厚的粗布手套不知用坏了多少双,手上不知道又添了多少新茧、打了多少血泡。大冬天的呢,他们居然只穿一件单衣,却仍干得汗流浃背。他们干活时的形象,很自然地让我联想起王家新笔下的“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
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
比一阵虚弱的阳光
更能给冬天带来生气
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
双手有力,准确
他进入事物,令我震动、惊悚
而严冬将至
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比他肩胛上的冬天
更沉着,也更专注
斧头下来的一瞬
比一场革命
更能终止我的写作
弓着身子的父亲,高举镐头扎向泥土的那一瞬,也“比一场革命,更能终止我的写作”。或者说,那个劈木柴过冬的人,就是我们的父亲。
抬眼一望,空旷的原野里落木萧萧,一派寂静,山水瘦得不成人形;没有收割的玉米秸秆孤独地站在田野中。头顶的万里晴空,像刚刚被谁搭着云梯,用蓝颜色的油漆刷过,还不小心泼了一桶,一个劲儿地蓝着呢;也像经常在电视里看见过的蔚蓝色的大海,隐隐约约地起伏着。
他们一直在眼巴巴地等待一个日子。等了大半辈子了。老皇历上说,腊月二十交大寒。大寒一来,就可以动土修建,这些石头也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下午,也就是大年前夕,当我和哥哥、嫂子、妹妹、侄子,一行五人浩浩荡荡回到家里的时候,把一件蓝色褂子扎在腰间的父亲,正抱着一个石头往墙上放。他的旁边,还有两个帮忙的师傅。
老皇历上标注的那个神秘日子已如期而至。这是他和母亲一早就计划好的——将院子前的那道堡坎打起来,这是新辟一个屋场的配套工程,也是收尾工程。只有把这道堡坎打起来了,一个院子才像个院子。
对一个山里人而言,一桩必须要完成的事,哪怕搁置再多的年头,也不会让它在脑海里生锈发霉。这件事就像一粒韬光养晦的种子,一直在等待破土而出的契机。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尽管没有能力完成这件事,但不知道已经念叨了多少回,设计了多少套方案,打了多少遍腹稿,并最终在反复权衡之下,敲定了最稳妥可行的一套,既美观大气,又节约成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他们一早就把一辈子的事情打算好了。以前咬着牙关供我和哥哥、妹妹读书,根本不敢考虑;前两年下大力气给我们和哥哥修厢房,也无暇顾及;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点自由发挥的空间,于是将这道扔了许多年的堡坎的修建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决心一鼓作气乘势将其一举砌起来了。这或许是除了给我娶媳妇、给妹妹准备嫁妆之外,他们还要干能干得动的大事业、大工程。
在他们看来,我们那几间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高大亮堂的房子,只要整修好了,只要有了这道像样的堡坎作为映衬,即使是放在整个村子里来看,也未必显得落后。母亲也多次表示,这辈子光搞修建去了,先是三间正房,然后是灶屋、厢房,确实是搞怕了,把脑壳皮都搞闷了。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后,他们以后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在给孙儿们摆经的时候,又多了一条“丰功伟绩”。
我们的到来,显然扰乱了他们的工作。我们一路上都在给他们报告行踪——到武汉了,到宜昌了,到县城了……就快到村里的时候,妹妹还给父亲打电话:你们快把饭煮好,我们都饿了一天了。
父亲那时肯定正在工地上忙活,于吵闹声中听到一首流行歌曲自腰间传来,便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直起身来,拍了拍手,拿出了那部别在皮带上的智能手机,清了一下嗓子眼,摁下了接听键。
见到我们,父亲并没有显示出多么大的高兴,只是在小侄儿叫他爷爷的时候,笑容一下子绽开了。他将手头的工具扔了,很笨拙地从那一面新墙上跨到公路上,钻进车厢帮忙拎行李。
他一头稀疏的头发无章无法,大概是有一段日子没有认真修剪了,脸又黑又瘦,下巴上的胡须也是黑黑的一片;神色有些倦怠,拎着行李从那一道坡坎上往院子里爬,背影蹒跚,比去年又苍老了许多。
我们父子在屋檐下的走廊上迎头碰上,我对他说:一年不见,您又老了不少啊!他颇为平静地答道:那肯定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呢!
他不曾因为我们的悉数归来而歇息半晌,在帮我们把行李安顿好后,又和他的伙计们投入了寂静而又热闹的工作当中。
这一天,是农历甲申年的腊月二十五。
二
我们家位于向家院子这个大屋场的最西边,院子前面是一坡旱田。一级一级的梯田,被世世代代的锄头像绣绣花鞋一样绣到了小堰塘底下的山林。西边是一条被一九八四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冲得面目全非的深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修建的一条乡村公路绕过向家院子,再环着我们家的院坝钻过一片日渐繁茂的树林拐向了海拔稍低一些的苦桥坡村。
我们家的地势要高出大屋场许多,视野也因此显得相对开阔,可见他们在建这几间房子时,并不是随意选择的一块土地。但是,若站在小堰塘的旱田里,杵着一把锄头歇稍的间隙,远远地仰望那一庄院子,竟觉得它的地势颇为险要。从东往西看,它高高在上;从西往东看,它下临沟谷,像父亲写毛笔字时的一个收笔,收得有些峻急,它所在的那块地就悬在了那里,令人心慌,不踏实。所以,给院坝打一道结实的堡坎是非常必要的。
再说,现在不光是村子里,就是向家院子里,一户户本姓人家都将房子修整得亮亮堂堂的,将院坝前的堡坎打得漂漂亮亮的,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无动于衷。按照父亲的规划,这道堡坎打起来后,我们家的院子将一跃成为向家院子里最有气势的一个院子。完工后,一丈多高的堡坎上将呈现出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坝来。若再往院坝沿子上立两排汉白玉栏杆,再往花坛里添置一些花花草草,再往院坝的西北角立一座凉亭,那俨然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乡间庄园了。
然而,那一砖一石,都得靠父亲亲手将它们一锤子一锤子地砌起来。那些被父亲从地心里挖出来的石头,那些被他细细打磨过的石头,那些被他一个个抱着放在墙壁的石头,一定都带着他的体温,吐纳着他身上带着一股香烟味儿的气息吧。
我们回家的第二晚,也就是腊月二十六的晚上,母亲给父亲的那两位伙计结了工钱,客客气气地解雇了人家:两个小工回来了,做饭的也回来了,人手够了,我们自己再干两天,就准备放假过年了。母亲的底气,来源于经过一宿歇息的两个儿子在这一天已经上阵了,搬运石头的搬运石头,搅拌水泥的搅拌水泥,干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施工进度比前几日快了许多,一天下来,那道堡坎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总工程的四分之一了。
到底人多力量大。
若干年前,父亲问母亲,当年你怎么生了一个儿子还要生一个儿子?母亲想也没想:儿子多了好打架。说完,自己先扑哧一声笑出来。
看来,儿子多了好处多,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难怪有些人家生了一胎又一胎,就是想生个儿子呢。这样想时,我正提着两桶砂浆,踩着已经砌起来的一截堡坎向父亲走去。
父亲在施工中自然担任总指挥长兼大工的角色。这不是父亲威权的显现,而是心照不宣的安排,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一条不容置疑的定理。不用说一直在外从事与此毫无关系的工作的我们兄弟俩,就是村子里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男人,都没有这个实力去挑战他的权威和地位。
记得甲午年正月初六那天,他带着我去给表哥家回年。表哥的一位亲戚见父亲岁数确实不小了,便很不确定地问他:您现在还在外面做事吗?快言快语的表嫂子马上搭腔:姨爹现在就是脚上的活路捡不起,手上的活路还没有丢呢!
父亲确实有一身好功夫,有几手令人信服的绝活。用不着怀疑,那些看起来怪不成器的石头,只认父亲,或者说,只认他的锤子。
多年以前,在我少不更事的年龄,看见父亲和来我们家里帮忙砌屋的师傅表扬大哥,夸他天赋过人,将来也是一位好石匠。我对此颇为嫉妒,便偷偷地学着父亲那样,幻想把一个没有口子的石头敲打得方方正正的,可无论怎么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可父亲只需敲那么两下子,再水货的石头,再面目可憎的石头,脾气再倔再不听话的石头,都乖乖地臣服于父亲的锤子,一个个出落得有鼻子有眼,大大方方地挺着胸脯上墙了。
那些石头,仿佛听得懂父亲的话。而父亲,就像一位因材施教的教书先生,能看见每一块石头的优点:质地好的,就做正墙,差一些的做辅墙,再不济的,就做填仓石。总之,在他眼里,没有一块石头是多余的。
三
那些天,我一直给父亲当小工,用两只小桶给他提砂浆,他往墙上砌几块石头,我便倒一桶砂浆。
父亲干活的态度是一丝不苟的,容不得半点马虎。为了把堡坎打起来,他买了好几吨水泥囤放在屋檐下。很多邻人以及公路上的过路客都对他说,不就是打个堡坎嘛,用得着这么奢侈吗?用泥巴糊一下就行了。父亲不为所动,坚持用水泥,而且用量特别多。用他的话说,这个堡坎是按照国家标准修建的!
当我在挥汗如雨地搅拌砂浆时,当我将一袋袋水泥掺和其中,再将搅拌好的砂浆一桶一桶地灌在那道一米宽的墙壁之中时,当我都觉得那是极大的浪费时……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他之所以花如此血本修建这道堡坎,一定是想为以他为开山祖的这一支向姓人家打造一方百年基业,以造福千秋万代。
现在,不仅是我们兄妹三个已经在父亲一手栽起来的大树底下乘凉了,连我那六岁多的小侄子,也时不时地扔下他恨不得整天抱在怀里的动画片,从那道坡坎上一路小跑下来,对他的祖父说:爷爷,爷爷,什么时候建好呀?然而,高瞻远瞩的父亲,当了爷爷的父亲,到底是老了,稍微大一点的石头他已经奈何不了,不得不用大锤将那些大家伙一分为二,或者是让大哥帮忙,合力将石头抬到墙上。
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他曾跟母亲吹嘘年轻时是多么孔武有力的往事。父亲确实给我们摆过诸如“老子天下第一”这样一类的古经:老子年轻时,一个人将三百多斤的石猪槽从几里之外的屋场背回来,中途连气都不用换一口,更不用说歇一回脚了。母亲不信,挖苦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光知道吹牛。我却对此深信不疑,对并他充满了敬意。
上工的第三天,习惯了在键盘上耕耘春秋的我,手心里居然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大大的血疤。那双不事稼穑的手,似乎娇惯得很呢!
这一天,我们是要挖一段地基,好将从公路上到院坝里的几步台阶砌起来。父亲让我戴一双手套再干活。我不以为然,不就是挖一段地基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古话很快就被证实了。等我把那一小段地基挖完,抬手一看,左手心里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布满了杀机,而我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们都瞄向我的手心时,始才觉得隐隐的疼。
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乡下,打个血疤,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吃一堑,长一智。然而,一双手还是不可避免地一天一天地变得粗糙起来,即使是戴着手套。就连那十个手指肚上,都磨出了一层细细的茧,刮在脸上,像极了一把硬毛刷子,异常的粗粝。
可即便这样,在收工时我还敢用刚刚从水缸里舀出来的冷水洗手。父亲就不敢了。他必须用热水洗,甚至还要用开水烫,否则手心手背在第二天就会裂开一道一道血红的口子。
父亲那与坚硬的石头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双手,布满了硬而厚的老茧,捏起来像钳子一样坚硬,摸起来比松树皮还要粗糙,如木头一般,终年弯曲,难以伸直,指缝间漏得下几把大米。
我们的父亲,脸瘦皮黄,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刮不下来一指头肉,尤其是这双手更显瘦削,没有一根手指的骨节是正常的,都被坚硬的事物和时间磨得异常粗大;没有一个指甲是完整亮泽的,每一片都凹凸不平,扭曲变形。
他绛紫色的手背上,永远布满着像被荆棘刚刚划过的白白的粗粗的线条。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敢正视他的一双手,不敢将我们的手放在一起,甚至羞于将我的手拿出来,我怕触及了闪电,以及锥心的疼痛。
我已经忘记了那双手有着怎样的温度,收藏过怎样的温暖,更忘记了那双手在抱着襁褓中的我时有过怎样的柔软。四五岁时就跟着大伯到数里之遥的山崖下挖观音土的父亲,是否有过一双细嫩柔软的手,我表示深深的怀疑。
母亲抓起他的手看了一下,仿佛这是她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注意到父亲的手,很怜悯地问:你的一双手怎么像鸡爪子一样难看哟?
父亲摆弄着一双鸡爪子似的手,很腼腆地笑。
四
每个清晨,父亲都起得特别早,我总是会在半睡半醒中听见他开门扫地、下楼梯的声音,然后是铁锨铲砂石时发出的尖锐的叫声,继而是一阵噗噗噗的声响,那准是他已将一袋沉重的水泥从阶檐上拖到了院坝里。晚上我们都睡了,他还和母亲掌着灯,一边去给刚刚造起来的台阶淋水,一边低低地交谈着,像是计划着什么。
我给他们计算了一下,他们一天仅仅休息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全部花费在了堡坎的修建和琐碎的日常事务中。我们虽然抓得很紧,夜以继日,仅仅在春节前后休息了三四天,但在我们的假期结束前,那项浩大的工程终究没有完成。一是缺少必要的石料,二是晴朗的好天气突然变卦,下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小雪。
下雪的那几天,天气出奇的冷,可父亲还是闲不下来。他担心我们冷,冒着刺骨的北风,把在工地上挖出来的树根一一拾掇回来,然后把它们锯成木柴,以供我们在炉子里烧火取暖之用。
父亲总是盼着天气快点晴起来。虽然只要干一天活儿,他那只受过重伤的右脚就肿痛得厉害,晚上还会一阵紧随一阵地抽筋,非得披着衣服起来在院坝里转上几个来回才有所缓和。
我偶尔会学着父亲那样,站在院坝里望着那还没有完工的堡坎,浮想联翩。因为有了这道堡坎,我们家的院坝往前至少拓宽了一半,于是,站在堡坎的边沿上,望见的风景,是一方气象万千的原野,是一个更加深邃而幽蓝的天空。
但遗憾的是,我不曾知道父亲站在这里时,都在想些什么。他就那样站在那里,抽一支烟,什么也不说。
我们父子曾站在院坝里,就怎样将院坝和房子休整得更加美观交换过意见。毕竟是父子,很多事情都被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然而,我们还是在几棵树是留是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院坝的左前方长着一棵漂亮至极的桂树,是父亲在一九八四年栽下的,三十年了,与那几间正房同龄,也与我同庚,现在圆圆的树冠美如华盖,好几个生意人要出大价钱将之收购,都被他们拒绝;桂树的西边还有一丛杉树,虽然生长极其缓慢,却也生得标标致致的。我的意见,是将它们都保留下来,不要砍掉或者是移栽了,夏天可以乘凉。父亲和母亲都持反对意见,他们坚持要将桂树移到院子西边的空地上去。他们担心桂树今后长成参天大树了,会影响院坝的根基。
我还告诉他们,桂树没有必要留那么多枝叶,留一两枝就好。
父亲立即反驳:养树跟养人一样,要养就要把它养好!
虽然我们意见相左,但我以为他们多少会考虑一下我这个成年儿子的意见的,没想到正月十二那天,等我和妹妹到堂弟家陪客去了,父亲就在母亲的指挥下,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将桂树连根带蔸地挖了起来。他们怕桂树倒地的那一刻会损坏刚砌起来的堡坎,还大张旗鼓地将我这个反对者叫回来帮忙。
我感觉我在家里就像个政协委员。
一二三……没想到桂树倒地的那一刻,那一方尚且狭窄的院坝顿时开阔起来!
五
在暖洋洋的日光下干活时,我们父子也曾对于我前途未卜的人生有过简短的交谈。那一天,究竟是新年的哪一天,我已经记不清了。父亲忽然询问起我去年收入多少、在新年有什么计划,我一一如实回答。偶然提及今年五月份,我就满三十岁了,可到了这个岁数,我既没有买房,也没有成婚。父亲显然比较焦急,但他并没有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
他一边吃力地往墙上抱砸好的石头,一边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看我们修建这几间房子的时候,我多少岁,你妈多少岁?一九八三年,我二十九岁,你妈才二十一岁!你妈刚刚嫁过来的时候,你知道才多大吗?十八岁!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自然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终身大事与事业,一直困扰着我,也困扰着他们。父亲一早就对我说过: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自己不抓紧成个家,以后五六十岁了,孩子还只有十几岁,看你怎么办。
母亲多次给我们上课,用很深沉的调子讲述她和父亲艰辛的创业史。
我们这几间房子是从一块贫瘠的荒地上建起来的。一九八三年,刚刚成家四年的他们,就开始着手修建属于自己的新房了。可他们那时多么贫穷呀,没有一点根基,六亲无助,除了一双勤劳的双手外,什么也没有。
最让人感到悲凉的是,思想陈旧的祖父祖母,不仅在物质上不曾给过我们半分钱的支援,还时常神经质似的跑到场院上阻工闹事,想把我们一家子赶到小堰塘那个荒山野岭的地方安营扎寨去。
那几间房子能够从一块种不了庄稼的荒袤之地上一砖一瓦地建起来,实属不易,全是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分家过日子时,祖父母仅仅给他们分了点能够维持月余的粮食,要不是外婆接济他们一点高粱,连一口饭都难得吃上了,况且母亲那时正身怀六甲——怀着我呢。然而,就是靠着那一点点种子,两个年轻人把日子过到了现在,大有越过越好的气象了。
母亲不是让我们记住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不是让我们记住祖父祖母的态度,而是让我们懂得眼下的生活,固然称不上富足,但确实来之不易!
我一直对二十年前我们家修建堂屋西边那间正房的旧事记忆犹新。
祖父那时还不算太老,但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私下里阻止我的两位会石匠手艺的叔父前来帮忙。两位叔父倒是听话,第二天就借故不来了。父亲一下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愁一大笔工钱,又缺少了人手。还好,他作为一个手艺高明的石匠,在村子里有一些同道。父亲与他们一道,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让那间房子堂堂正正地立了起来。
父亲为此背上了一大笔债务。向家院子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私底下嘲笑他这辈子再也翻不了身了,说他要被这一大笔债压倒。
年轻气盛的他,哪里会信这个邪!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果是放到别人头上,不是给愁死,就是给急死了。结果,仅仅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他就将这笔债如数还清了。谁知道他在这半个月里吃了多少苦头呢?他在这段时间里,给他一位远房表叔家里做木工活,几乎是夜夜通宵,每每回到家中都已是鸡叫头遍的光景了。他硬是用半个月的时间,将一般木工要花上两三个月才能干完的事情漂漂亮亮地解决了。
后来偶尔谈及此事,父亲也忍不住豪气冲天地大发感慨:那些年是有些本事!
曾经豪气干云的父亲,某一天在饭桌上对我们说:我以后不出门打工了,就在家里喂几只羊。每天熬羊汤喝!
再过三个月,父亲就六十岁了。
六
大哥一家在正月初六就出发回南方去了,我和妹妹正月十三才走。
记得初六那天,司机明明说好是八九点钟才来接他们的,结果六点多就来了,搞得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匆匆忙忙上车,来不及与我们告别。
父亲站在堡坎上焦急地望着他们,他一只手揣在裤子口袋里,另外一只手提到半空又放了下去,嘴巴张开了又慢慢合上。如此反复,也不曾溜出一句话来。
车子发动的那一刻,突然听到母亲在院子里大喊一声:等一下!
只见她从台阶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来,左手端着一个塑料杯子,杯子里装着两个已经剥好皮的鸡蛋,杯沿上露着一把塑料勺子的把柄,右手小心翼翼地护着,生怕杯子里的东西跑了出来。
她很慌忙地将之递到车厢里,冲里面急促地说:拿着,在路上给向泽翔吃……你们今年发财呵……
还没等母亲说完,车子一溜烟儿就不见了。父母亲朝着公路拐弯的方向若有所失地望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们的睫毛上流动着一团雾气。
我们出发的那天更早,才五点多,天还黑得要命,树梢里连星子都没有镶一颗,屋檐下飘着玉米面一样细碎的雪花。当我背着行李走下台阶时,一个小红点正从阶檐上向我蹒跚而来。那是吸着香烟的父亲。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他的脸,只有他口中叼着的那支香烟在黎明前的黑夜里闪烁其词,欲言又止,像一团小小的祝福的火光。
我们走啦!我摇下半边车窗对他们喊道。
黑暗里,一言未发的两个人,站在尚未完工的堡坎上,背对着阶檐上的灯光,看起来就像两尊挥着手的雕像,也像那两棵在年前被摘完了果子,在前一天刚刚被父亲从院坝里移栽到菜园那一块空地上的空荡荡的柚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