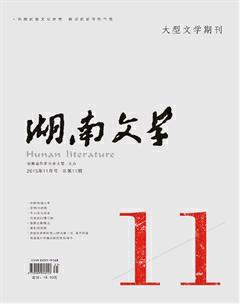女性的创世纪
孙雨婷
“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这么说。
———《圣经·创世记》
一、美丽的歌苓女士
严歌苓的名字出现在“人文中国优雅女性”获奖名单上,是与另两位年龄身份各异的杰出女性杨澜、谭晶一起。
撇开这三位女性所共同具有的优秀公众形象不谈,这实在有点像是奖项组委会有意而为之的安排———三位女性分别来自五十、六十与七十年代,又来自文学、传媒及艺术等不同领域。面对镜头时如出一辙的从容温雅,让这“优雅女性”的奖项不免有几分像一首韵脚工整的美丽小诗。
与另两位由于工作性质常年出现在镜头前不同,旅居海外从事写作的严歌苓要低调不少,在公众前亮相的次数虽不至寥寥,却远比她的文字出现频率要低。为数不多的印象里,青年或中年的她并不曾改变几许,娇小脸庞,眉目清淡,唇色却浓重,缄默或言语时总有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端庄得体却不失亲和,是多么美到令人触目的女人么?似乎并不是。但年少的我望着她丝毫不掩饰岁月剥蚀却依旧坦然雍容的笑颜,却真切觉得“这才是女人”。
是的,在这位美丽的双语作家以她自身的雅致高华叩开大众心门之前,她笔下走出来的一个个鲜丽生动的“女人”早已成为众多读者心目中“女性”这一宽广概念的代名词,而她的每部作品———或宏大或隽永———都是一道以“女性”为谜面的未知谜题,成千上万的读者在猜,却总有成千上万个谜底。
二、世界的中心是女性
从经典之作《扶桑》到转型之作《第九个寡妇》,从写实之作《一个女人的史诗》到银幕之作《金陵十三钗》,以及等等脍炙人口的严氏名篇,往往都以刻画鲜明独特又包含复杂性的人物形象为中心,尤以女性形象为甚。严歌苓笔下的世界往往以某个具备特殊冲突感与矛盾性的时代为背景,而在这种世界观中塑造而成的女性形象也往往因着时代特征的不同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色调。
严氏出品的小说具备了某种“免检”的精品性质,往往新作尚未推出便被众人关注,小说还未启封读者已经满怀期待,而严歌苓从未让读者失望的作品公信力,大概有不少取决于她笔下那些似曾相识却各展妍姿的女角们,像古时大家作人像,都只以细腻有力的写意线条勾出大致轮廓,一眼望去这个与那位有几分相似,这幅与那轴有点儿相仿,然而泼溅上了颜料,便个个有了如栩生机,头面身首都由于鲜活的细部与精巧的特色而明晰起来,于是由笔尖分娩出的女性,便都有着独属于己的精彩。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也许正是严氏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而自诩“多产”的作家,也许著作等身,笔下却始终是个影影绰绰的身影,这部读来似乎还是上部主人公的故事,不过改了名换了姓,面目苍白模糊,好像都差不多。
严歌苓的作品中,最为体现以女性形象为中心这一特征的是《扶桑》,比之她大部分以叙事为主线的作品,《扶桑》是以诗化的笔触来表达的,比起小说也许更接近一部格局宏大意境深邃的散文诗,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人格体现在女主人公扶桑身上,使这个具备具体身份与真实存在的角色被赋予了作为作品意象的使命,本为具体存在的中国妓女扶桑由此成为了主旨表达的符号,成为了严歌苓意图表现的东方文化里被打上女性印戳的生命特质的象征,成为了主题的庞大背景,“以个体代全体”的写法,在初中阶段的课本里就有所接触,而严歌苓在此之上刻意弱化了叙事而以场景与情感的连缀来完成小说整体对核心意象的刻画,笔法实在太令人惊艳。
以女性为作品中心在严歌苓其他较为通俗的作品中也并不鲜见,《穗子物语》里八九篇中短篇小说便以“印象派的少女时代”的严歌苓———萧穗子贯穿起来,意旨在主角各不相同的小说在匠心独运的编排下,构成了以萧穗子的生命历程与成长路线为主体的整体;而《一个女人的史诗》则更为大胆地将二十世纪中国的几个历程嵌入到个体田苏菲的生命与情感历程之中,“以小人物写大时代”,而女性个体与时代背景中某些彼此相辅相承的部分便对应地水乳交融起来,一如《天浴》中文秀近乎无耻的单纯对应了文革时期暗流涌动的不公与玩弄、《寄居者》中致残酷的追求美好自由对应日侵期间对“人”的血腥逼迫虐待,华彩万千的女性形象,始终占据严氏笔端世界的中心,以她们的万千青丝为经,以她们的皮肤纹理为纬,便是一个活过来的时代。
三、亚当、夏娃与莉莉斯
严歌苓所握的笔并不是一支阴柔的笔———在婉出的个个眉目鲜明的人物形象里,存在着缺少女性特征(抑或部分特征)的女性以及真正的男性,在文字间的方寸天地里,并不黯淡半分。
我觉得比起讲故事的技巧,情感的表现力更为关键,形象的色彩无疑是情感所赋予的,既然女性与男性之间是如夏娃与亚当之间一般“骨血互溶”,那么在女性情感的描绘上,怎能少了两性情感的互动呢?———严氏笔下的“两性”却不全然是爱情,像《白麻雀》里,藏族文艺女兵斑玛措与声乐老师王林凤之间的情感主线,“她知道王老师是绝不该恨的,恨王老师是造孽,但她这一刻就是管不住自己。”“一天天过去,斑玛措一天天盼望王老师训她,可王老师越来越慈爱,眼睛抠成了两个窟窿,窟窿底部,斑玛措看见她父母的眼睛朝她看来。那个她从未见过的父亲。”进退之间的微妙真切使勾勒斑玛措性格的笔触更为动人。
我实在是年纪太小,并不能全然理解严歌苓以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来刻画的冷硬苍凉的世界———在以现代社会为背景的小说《赴宴者》里尤为显著,讽刺淡漠的笔触———却也能知道她的世界里,情感并不是像三原色一般被简单划分开来,黑是黑,白是白的。她笔下的人物关系建立在多层次多方面的情感主线上。《小姨多鹤》里张俭一家三个成年人———丈夫张俭,不孕妻子朱小环,日本代母竹内多鹤之间的复杂畸形的关系便是成功典范,故事背景主设于“大跃进”时代———不同于严氏小说多以文革为背景时的深浅灰色。《小姨多鹤》的背景色从头至尾都是红的,多鹤逃难时是血球惨烈的红,遇见张俭时是经血干涸的红,连写文化大革命也少见地用了正面笔触,红得壮丽残酷———张俭一家便像扎根在鲜红土壤里一株反时令生长的树,以三个成年人之间掺杂着爱欲、依赖、嫉妒、排斥与仇恨的枝节延伸出张家下一代乃至与张俭一家关系密切的小彭、小石等人彼此之间的复杂情感。分明写着一个家庭的波折起伏,却丝毫不显琐碎,严歌苓把“代孕的日本落难女子”这点不平凡写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的惊心动魄,而这其中以小及大的表现力,正是直接来源于对角色情感的细腻描摹。
上文把作家刻画人物类比作人像,那么对人物情感的描绘润色便是上色的过程,在生活积淀之下心有所感的作者便似拥有了一张调色板,调色格子里分别盛放着种种情绪的颜料。上了色的人物方才有机会鲜活起来,而有的却是印在纸板上看似栩栩如生实则死板的彩色人像,有的却是音容笑貌似在眼前牵动情思的生命,严歌苓的调色板必是拥有无数潋滟华彩的颜色,唯有这样,她笔下才会源源不断走出那么多截然不同却又同样精彩的生命,连相似的形象也拥有自身独一无二的色阶。
我读严歌苓,读到的是她对人性的坦然与真诚,文学诚然是“雅”的,却不能沦落为了雅致高贵的卖相而丢了内里撑起来的筋骨,这并不仅仅是对文学初有涉猎的无知少年如我等才会做的事情,我读到的一些光在华衣甘饴,诗词雅趣间卖力营造高洁脱俗的境界的作品同样出自著名作家之手,却觉得好是好的,却是浮在远外,远远触目空自感叹却无真实触动的蓬莱仙境,文学本不该是这样,或者说,本不该只是这样。严歌苓写的却是市井,她一点不拘泥于哪点文人架子,她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俚俗甚至有些下流的口语化描写及对白,却“俗”得不拘一格,“俗”得真实密切,“俗”得让你想笑便笑,想哭便哭。这些尚是表象,严歌苓在描绘人生时从不避讳那些愚昧、畸形、丑恶的部分,也从不避讳那些看似匪夷所思实则源于人性本真的感官情绪,对于异性甚至同性、人类与动物、幼童与少年之间最为赤裸的情感,被她描绘得一览无余———像她在《审丑》里借赵副教授的口说的“高一层的审美,即是审丑”,在她的《白蛇》《梨花疫》《金陵十三钗》等诸多小说作品里,看似丑恶的部分恰是最最触动人心深处的部分。
严歌苓笔下每一个女主人公若都是丰丽懵懂的夏娃,她的伊甸园里必定有亚当及莉莉斯共存———亚当是有关她那朦胧、期许、渴慕、向往,莉莉斯则是有关她那冲动、无知、黑暗、恶毒。亚当与莉莉斯都存在时,夏娃才是美的,因为莉莉斯不断趋向于伊甸园外真切的光明,亚当则使夏娃成为真正的女性———女性唯有与男性并肩而立时,才是女性。维系严歌苓笔下这三者的,正是情感的力量。
四、逃离伊甸园
从人性到情感,从时代到社会,严歌苓笔下的世界从来与纯净的伊甸园无关,她落笔的美好事物无不扣人心弦,却以同样叩动人心的残酷笔触来写她的“人世”。虚无缥缈的超脱高贵在她笔下是读不到的———身为一位女性作家,严歌苓从不以女性式的风花雪月来取胜,她写的情欲爱恋,传奇纠葛一点鸳鸯蝴蝶派的影子也没有,反而蕴藏着深刻的对生命、民族、社会、人类、两性关系的思考,她笔下的丑恶畸形在历史或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如《扶桑》中对华裔及华人在美国国土上满载屈辱、血腥与仇恨、陌生的移民史,如《少女小渔》中对无法避免无法消除的文化冲突的细致描摹,如在多部语涉文革时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性整体的愚妄、盲目、麻木、恶毒的放大刻画———像在《灰舞鞋》中,萧穗子的纯真恋情被她所在的军队群体所玩弄、所欺骗、所捣毁,尽管出现了言情青春片式的男角刘越,看似在写爱情的无奈与追随,实则却从穗子个人的痛苦投射在特殊时代下变形的人与人性,探讨爱情背后两性关系的深层所在。不断思考并不断以作品表达的作家笔下的作品方才不落俗套,否则《灰舞鞋》里的多角爱情难免会被写成滥俗青春励志剧,《寄居者》的“交际花年轻女子为异族恋人瞒害未婚夫未遂”的桥段也没准成了什么大上海的铁血爱情传奇,极可能像用惯“复仇”戏码的韩片似的让未婚夫远追海外找上已成豪门富妇的“恶女”寻仇,用上倒叙手法;《赴宴者》里董丹和老十的故事也尽可以编排出“洗脚女与假记者的孽缘”之类的标题上三流杂志封面,再好的事故停留在表层的肤浅皮相,便也只是哗众取宠,严歌苓一早便跳出都市传奇陈年八卦的圈子,才写出不落俗套的故事———文学的假伊甸之外,才是真正的心灵与思考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