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 文/李建平
编 辑 万小广 wxgpeter1314@126.com
从业七年多来,我采访过大大小小的官员、形形色色的成功人士、各行各业的精英,然而回想起来,真正打动我、影响我的还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淹没在人群中毫不起眼。他们不符合新闻价值中显著性要素,如果不是种种意外,不会进入新闻的视野。然而,他们让我认识到了抛开浮光流彩的表面、面对平凡的生活时应具备的品质和力量。
勇敢无畏,在苦难面前咬牙不屈
见到古才贵是在他儿子古宜荣的病床前。这位年近50的江西籍农民工,身体瘦小、头发花白,粗糙的手上布满了长期在建筑工地干活时留下的疤痕。他给我翻看他儿子发表在校报上的摄影和文字作品。我毫不怀疑如果能够成功毕业,古宜荣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同行。然而,此刻的古宜荣头上打满绷带,全身插满管子,完全没有意识。
“恶性脑瘤”,武汉同济医院的诊断书上这样说。医生告诉我,这种病是世界难题,发病快、手术难、极易复发、生存率低。在手术切除肿瘤的半个月后,古宜荣病情忽然恶化,昏迷不醒。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就是砸锅卖铁,卖掉我老家的房子,我也要一直陪着我儿子。我要救他。”为了减轻医药负担,古才贵要求出院,由救护车护送儿子回老家,继续治疗照顾。
命运给了这个瘦小的男人太多不公。古才贵的妻子在儿子五岁时癫痫发作,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儿子自小懂事、独立自强,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并担任班长,人缘好,成绩优异,却在即将毕业的最后一年,突发恶症。
我和前来嚎啕大哭送别的同学都隐隐觉得这大概是见到古宜荣的最后一面了,他再也不会醒过来了,只是没有人敢告诉这个倔强的父亲。
送别之后,我时常想起这对苦命的父子,却又不敢打电话问。一年多后的一天,古宜荣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古宜荣恢复意识了,甚至可以在微信群里跟大家聊天。
听到这个消息,我在高兴之余,几乎是很震惊地给古才贵打电话祝贺。电话里的古才贵显得很高兴,但也还抱着忧虑:病情时常反复,要一直进行各种各治疗和康复训练。“医生说他不能吃猪肉,我就养了很多鱼,喂鱼给他吃。我还种了很多菜,给他吃新鲜的。”
这个平凡的父亲是怎样超越医疗的局限,创造了伟大的奇迹?古才贵自己并不以为然,他只是用浓重的乡音回一句:“什么伟大不伟大,我这是没有办法嘛,我肯定只有尽力救嘛。”
接触古才贵这样的人越多,我就越容易反思。当下许多报道,在面对“草根”、弱势时,记者观察和写作经常自然或不自然带着精英优越感居高临下,即使某些正面报道,也常因为缺乏底层体验,而显得假惺惺。保持敬畏之心,这是记者应该诚心学习的。
靠双手生活,忠于自己的良心
武汉鹦鹉洲大桥不远处一排低矮的棚户区里,几天没睡好觉、面目憔悴的邓双生拿着900元工钱,递给工友王成华。至此,邓双生的妻子何运香生前没有来得及结清的工钱终于一分不少全部付清了。
“人亡不赖账。自己再难不拖累别人。”邓双生说。我看了看他们的房间,一间没有窗户的棚户房,墙面斑驳,用木板和砖头搭起的床靠着墙,一道帘子隔开,外面堆放着锅碗灶具,门后放着平时做保洁用的铁锹、扫把等工具。
当过小学民办教师的邓双生努力地用普通话向前来的记者介绍情况。其实,他说方言,我也全都听得懂。我们的老家离得如此之近。采访他时,他们夫妻的形象与我父老乡亲的影子重叠了起来。
邓双生指着房子角落的一堆废旧塑料瓶子和纸板说:“运香从来都不会闲着的,没有活干时,就去捡废品卖,还去附近的工地上拌沙子、抬泥灰,这都是男人才做得来的重活。”
“她肯吃苦、肯出力,慢慢有认识的老板觉得她干活放心,就让她组织工人去接活。”邓双生说。2012年,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开始施工。有相熟的老板找到何运香让她长期组织零工去做护栏围档的清洁工作。
这种工作有多辛苦呢?工友们跟我讲,冬天的夜里,寒风刺骨,还不时有洒水车经过,有的垃圾被冲进桥面两边的沟里,要打着手电筒挨个清理,沟里积满了水,工具不好使,只能徒手伸进冰水里,把垃圾捡起来。
白班100元一天,通宵170元一天。为了多挣钱,何运香两口子没少上通宵。2014年12月28日,鹦鹉洲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何运香最后收工。次日凌晨3点,她起床去沌口一个路面扫渣土。5点,何运香被一辆渣土车撞倒,两天后抢救无效离世。
因事故责任方的赔偿没有到位,欠着医院的3.9万元医药费又没能力付清,何运香的尸体只好停在太平间。几天后,老板送来10.6万元的工钱。一接到工钱,还沉浸在妻子离世悲痛中的邓双生决定第一时间先把工友的工钱分发了。
记者们问邓双生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不出“信义”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来。但我想,无需过多的粉饰,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同为劳动者,深知挣钱的辛苦,也许只是想求得良心的安稳,但这样不善言的木讷和本能的善良,更真实可贵。
不识时务,却真实有人性
“国家领导想的是航天事业,我们想的是儿子。”“神九”上天前,我前往位于山西平遥乡下的航天员刘旺的老家里。即使在农村,刘旺家的小院也不算出众,低矮得略有些寒酸但收拾得非常整洁。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信号不好,还是县广电局临时赶过来重新给搭好的信号。
刘旺的母亲刘翠莲盯着电视机一言不发。直到几天前,她才知道儿子要执行“神九”任务。现在,她跟我们一样,只能从这台电视机的直播里,得知刘旺的信息。
此前,从新闻上看到关于“神九”即将上天的消息,她曾经打电话给刘旺,你入选了吗?刘旺问,您希望我入选吗?她说,不希望。
听闻出了航天英雄,地方政府领导特意赶到刘旺家里慰问看望。但是整个过程,刘翠莲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电视,既没有站起来回礼,也没有说一句客气话。场面略有些尴尬。
两天后,神舟九号飞船返回舱在万众瞩目中成功着陆,刘旺完好无损走出机舱。刘翠莲长舒一口气,摸了摸心脏,冷峻的脸色逐渐缓和,恢复了一个和蔼大娘的模样。
相对于社会名流应对官员和媒体从容得体的样子,我更佩服一个母亲最自然的真情流露。
诚信立身,即使失败也努力保持体面和担当
张学斌,湖北天门的一个下岗工人,白手起家办米厂,终于把米厂办成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却因为还贷后银行不再续贷,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 2014年6月18日,作者李建平(中)在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老矿区职工宿舍区里采访飞奔接住坠楼男童的颜德荣。
张学斌说:“我半夜起来,蹲在厂房地上抽烟,机器不能运转,我心里着急。银行不续贷,电话不接,上门找说领导不在。没办法,11月份天寒地冻,我凌晨4点开车到市区,在银行门口一直等到天亮,截住行长求情。”
而这些都是没用的,贷款迟迟不下来,在政府、银行、债主间来回奔波,煎熬了两年多。这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大汉,瘦了几十斤,却没有垮,银行的人送他“张坚强”的绰号。
有人说他傻,如果当时不还贷,现在日子还好过,反正有其他企业主就这样赖着账,也没有人真拿他有什么办法。
在我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稿件发出来后,有中央领导批示,但最后到了地方还是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问题没有实质进展。在这个几个月间,形势越来越严峻。去采访的其他人私下跟我说,常担心老张会跳楼。
然而,我在另一次采访任务时,看到了张学斌,他新修理了头发,看起来精神了许多。“我刚去了一趟九江,在找其他门路。反正我不会跑路,有问题我就顶着,有希望我就去争取。我不跑,我也不垮,我就死扛着。”
一个从卑微走向成功,又遭遇人生重挫的人,在面对挫折时,尽自己力量维持信誉和尊严,虽然悲惨然而壮烈。
即使卑微,也竭尽所能尽职尽责
采访周小贺的事迹时,周小贺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只能从他生前的遗物里去试图了解这个最基层的植保站站长的生平。
书柜里满满装着一摞摞老式的硬壳笔记本,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他殉职的2013年,记录的是安陆市16个乡镇的田野监测观察数据。
能看得到的是数据,看不到的是数据背后的汗水。我大概能体验得到,农村夏伏时期那令人生畏的溽热。明晃晃刺眼的阳光下,田野里没有一丝风,热气蒸腾,连农民都不会挑正午这样的时间出来干活。这个基层的植保站站长几十年在他的岗位上做到了。
周小贺一生只是挂靠在农业局下面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生前还常为发不出工作人员工资而发愁。从仕途上看,他并不成功。然而,他带给一地农民的作用和改变是难以想象的。当地农民跟我讲,他怎么教他们打药,怎么种菜,怎么防虫,一个电话就赶过来了,许多人在他知识的帮助下,脱贫致富了。我相信他的精神世界一点都不贫困。
接触的人越多,我越深深感到: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们那个世界的存在而奋斗。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也有绚丽的生命之花在悄然开放。而当记者,就应当发现更多普通人的生命之花。
版权声明:
若转载本刊文章,请务必注明转载自《中国记者》,包括期数、作者等要素。
《中国记者》微信公众号:京原路8号。微信号:zgjzzzs,敬请关注、评论!

P63李菲
“因为……所以……”
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因为热爱,所以激情……这是许多卓有成就的新闻同行在获得荣誉后流出的真情告白。看似简单造句的背后是多少隐忍、拼搏、孤独,甚至牺牲!一位地方报纸首席记者如何做到职业生涯的高境界?他怎样看待“职业”与“事业”?

P70李建平
“那些影响我的采访对象”为何受欢迎?
自本刊开辟此栏目以来,所刊发的文章颇受欢迎,有的经微信公众号“京原路8号”推送后更是得到众多关注与点赞。比如张严平撰写的《只因生命中遇到你》,一经发出很快获得单篇近4万阅读量。本期相关反馈也表明,新闻实践中不少记者是从优秀采访对象身上汲取了力量!欢迎继续来稿交流。

P80黄小希等
今天媒体如何“传帮带”?
“传帮带”一直是新闻业的老传统,如今常将这一概念挂在嘴边的确实少了,但是否已成为一种“行规”?转型大潮来袭,带来剧烈变动之际,一些年轻记者难免心旌摇动,今天的“传帮带”有何变化?新特点新路数何在?新老关系以怎样的面貌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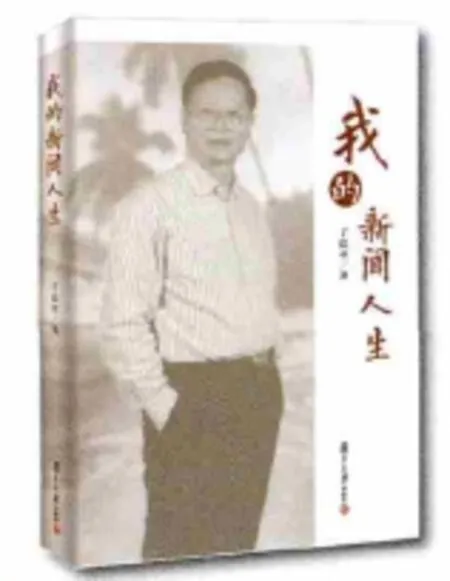
P78吕怡然
呈现踔厉风发的新闻人生
丁法章是大家熟识的知名新闻人,对现在的年轻同行而言可谓前辈。在此推介,重要的还不完全在于他曾于上世纪90年代先后任《新民晚报》总编辑和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副社长等职,也不完全在于他的成就和著作等身。而在于他过人的勤奋好学等素质造就的“踔厉风发的新闻人生”!
在书中还可看到作者收录的1987年第7期《中国记者》的文章。
(文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