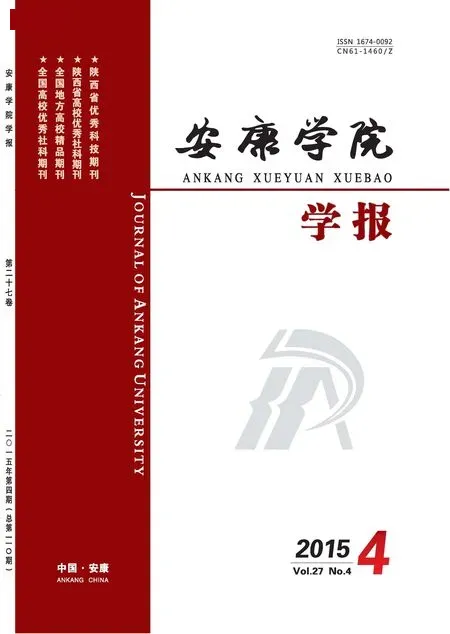五四女作家情爱叙述中的主体认同分析
李艳云
(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在长期的封建父权社会制度里,女性被置于为女、为妻、为母的修饰性“他者”地位,其生存的空间仅仅被囿限于家庭之中,其性别的文化品格在父权文化规训下自动呈现为内囿性。五四以来,在由男性精英倡导的现代启蒙思想的“国家——民族”的构建规划中,女性解放作为国民性改造的一个程式,被动地在时代大潮下开始演绎自己。而女性文化品格的内囿性与女性解放原初的非自主性,决定了女性在告别自己传统的文化角色时的艰辛。对于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具有一定主体反思能力的女性而言,传统父权文化机制的潜在内化决定了其对自己生存境遇的审视,依然逃脱不了男性目光对其性别身份的规定。只是,在现代化个人“主体性”的诉求中,女性开始对父权文化逻辑下自己的这种被规定和限制了其生命存在状态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传统父权文化场的潜在身份规定、时代思潮对人主体性的号召、女性生命内在自由的鲜活体验,这三种对生命的不同认知与体验,在现代女性小说的创作中,表述为小说文本中的爱与欲、情与智的矛盾冲突。显现了女性在走出传统文化的身份训诫,在现代性话语中自主建构自己身份时的困顿与迷茫。而女性作家多把这一在传统与现代中指认自己的思考,放置在离她们个人经验最近的爱情、婚姻中来考察。
一、五四女作家的情爱书写
在社会现实存在中,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情爱类型。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对爱情的需求是继生理需求和获得安全感之后的很自然的感情诉求。对于爱情的认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明三点:(1)爱情是以性欲为基础的,但又决不同于单纯性欲;(2)爱情是以互爱为前提的,妇女与男子处于同等的地位;(3)爱情以双方结合为实现目的,持久而热烈。”[1]
在现代的情爱观念中,真正的爱情是以互爱为前提的。这一方面是指爱情具有对象性和选择性,需要主体双方产生感情的共鸣;另一方面是指女性和男性一样,在性爱中是独立的个体,可以实现自己爱的自由和爱的权利。而这一点,在古代的爱情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婚姻作为爱情最终的实现目标,是爱情的记录与佐证。婚姻的现实状况正是爱情记录的晴雨表。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语境下,女作家对于爱情自主、婚姻自由的表述,是当时反封建、追求人的自由平等的时代主流话语在文学叙述中的一种具体呈现。这种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建构表现在女性小说作品中,呈现为女性对待爱情的三种姿态:义无反顾、游离、失望。从这三种姿态以及衍生在这种姿态中的女性性爱意识,我们能够体察出女性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对自己生命状态的认知。
(一)爱的义无反顾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面对爱情,子君决绝地对封建旧家庭说不。在“文学革命”的大时代语境下,女性小说家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子君式的“叛女”形象,她们打破封建旧家庭的藩篱,逃到那个许诺给她们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去。而平等、两情相悦的爱情成为她们逃出家门最具有感召力的借口。决绝而义无反顾的叛女形象,可以冯沅君小说作品《隔绝》《隔绝之后》中的隽华为代表。在冯沅君的叛女叙述中,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预想,是有某种乌托邦宗教情怀在里边的,它是诗意的、纯净的、与性爱无关的神圣的感情。在这里,爱情不仅仅是爱情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与阻碍自我主体发展的外在力量对抗的精神力量。爱情,不只是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更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话语编制,成为时代情绪的能指符号。
现代的爱情观念是认可与正视性欲的,强调爱情双方在性爱中的主体地位,而在冯沅君的叛女叙述中,爱情是没有欲望根基的,它成为男女主人公共同确认现代人独立品格的一种粘合剂。在《隔绝》中,冯沅君这样写道:“不然我怕没有一个人,只要他们曾听见过我们这回事,不相信并且羡慕我们的爱情的纯洁神圣的。试想以两个爱到生命可以为他们的爱情牺牲的男女青年,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和接吻密谈外,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算不算古今中外爱史中所仅见的?”在她的另一小说作品《旅行》里,她同样一遍遍的强调着纯洁爱情与肉欲的不相关性。由此可见,冯沅君等女性作家,更多的是在爱情的名义下,给予爱情反封建、实现时代话语感召的自由“人”的时代意义,而有意回避了爱与欲的现实相织性。女性潜意识里仍保留了传统道德对女性在性爱生活中的规范与禁忌。女性一方面顺应时代感召叛离父亲的家庭,成为爱情自由的实践者;一方面又要在父权传统的道德规训中,保留自己女儿身份的贞洁性。因此,在冯沅君式的叛女叙述中,叛女情人的形象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她们更多的是作为叛女理想爱情的投射对象,其在文本中也只是一个虚设的促使叛女行动的功能性结构。
在冯沅君式的叛女叙述中,爱情实则是指向爱情之外的“我们”与“他们”的文化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女性作家通过小说文本寻求的是主体的时代身份的认同。当然,在这种寻求认同的过程中是充满着自我指认的艰辛的。正如前文叙述,这里的创作主体流露的是在传统父权文化的潜在身份规定话语、时代思潮对人主体性的号召性话语、女性生命内在自由的鲜活体验话语三种不同质的话语交错与互相对话中生成的认同经验。在这里有传统父权文化机制的身份规训——女儿身份的伦理价值所指;也有时代主潮下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身份所指——爱的自主权拥有者的社会人;以及生成在前两者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的鲜活的生命体验——叛女经验。在这三重指认的交错纷争中,无法最终指认自己的隽华只能选择生命的终极逃离——死亡。在叙述中,作者想要借爱情演绎当时主流叙述中的反封建旧家庭的时代主话语,然而,人物命运的最终设置却恰恰显示了主流叙述中掩饰不住的现实女性生存的实际心理经验流露。
(二)爱的游离与失望
与上述爱情表述姿态不同的另一种女性爱情经验是对爱情的游离与无望的心态。对于爱情的游离与无望的书写,主要表现在凌叔华、庐隐、丁玲等女性作家的小说叙述中。凌叔华的小说《绣枕》叙述了一位待嫁深闺的大小姐,通过精心的刺绣来编制迎合传统礼教为自己分配的爱情。而那汇集着她的心血与爱情期望的绣枕,最后却在不经意间被分配给自己的爱情对象践踏与抛弃。在《女人》与《花之寺》中,凌叔华则通过叙述两位通过自由恋爱与丈夫走在一起女子,在婚姻内对于丈夫与爱情的审视。在这里,爱情似乎已经修成了正果,但是身在婚姻之中的她们并没有完全体味到现代情爱观许诺给她们的完全的幸福与自由,更多体味到的是婚姻之后爱情的虚指。在凌叔华的叙述中,爱情似乎离得很近,却又难以完全地把握,女主人公眼中的爱情似乎总是处于游离之态,无法切身。比起凌叔华的温婉,庐隐对于爱情的表述则是激烈而强势的。在她的小说叙述中,庐隐表述的则是对于放置在女性现实生活语境中的现代爱情观念现实兑现可能性的质疑。庐隐笔下的走出父亲家门的叛女,在现代爱情观念的指引下开始寻找理想的爱情,开始打造自己的现代人生。然而,以爱的名义去在社会中求证自己的主体实现,注定失败。《或人的悲哀》中的女主人公亚侠,在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中,接二连三陷入情感旋涡中,欲罢不能,“想放纵情欲”又不甘堕落;与人周旋又让她内心异常痛苦,在自己对人生的游乐中,她却最终发现自己被人生所愚弄,而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人生。《丽石的日记》中受新思想洗礼的丽石,也由于遇不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如意郎君,又不愿听任“媒妁之言”的撮合,自己更无法将心事道与别人,最后在无法释怀的失落和自卑的折磨中抑郁而死。
理想爱情的难以兑现让现代女性作家笔下走出家门的女性苦闷、绝望。而当某些幸运的女性找到了理想爱人,进入婚姻中时,她们却又陷入了另一种生存的苦闷之中。在庐隐的《何处是归程》中,女主人公在自由婚姻中体验到更多的,是新式婚姻中女性传统“为妻”“为母”的角色对曾经事业志趣的挤压与替代,陈衡哲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更是直接地讨论了女性家庭角色与事业之间的二重冲突。凌淑华通过《小刘》进一步证明了婚姻对于女性个性生命的扼杀。女性逃离父亲的家门,走入“夫”的家门,依然是女性“他者”生活的轮回。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个人主体身份确立的过程,又是民族文化主体建构的过程。个体通过与家族礼教制度决裂而获得崭新的‘个人’身份,民族也藉由摈弃传统而认同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而获得现代民族的文化身份。”[3]在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中,寄予更多的是自己在现代民族身份构建过程中个人“主体”身份的社会认同。无论是对于爱情义无反顾决绝的姿态,还是对于现代理想爱情追求破灭后的无奈与绝望,其更多印证的是自己作为现代人的自由、平等的主体属性。爱情只是她们用来验证自己身份的试剂。而在这种验证过程中,她们验证到的却是自己被编织为现代身份的虚幻与自己难以逃脱的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悲哀。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释放出来的现代个性解放话语许诺她们为人的平等与自由性,然而在她们实践自己的这种主体属性时首先发现的却是自己在爱情、婚姻与事业中的被压抑性。她们从父权式的旧家庭出走,以决绝的姿态告别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度,然而,与现代民族构建话语配套的社会机制以及与之相适的意识形态机制并未完全伴生建立。时代局限以及女性性别意识的不自觉,难以使她们一下子探究出自己被压抑生存状态的深层原因,更不能为自己摆脱这种境遇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于是,我们看到女性作家们只能选择让自己的女主人公或者在死亡中逃离,或者在悲凉与无奈中继续悲戚。
因此,此时期女性情爱叙述话语中求证更多的是自己“现代人”的主体身份,“女性问题只是被看成人的整体解放的一部分,她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精神存在的特殊性,在女性自身实现自我完善所必需的自我认识与批判性内省这一层面上,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4]
二、一个特殊的文本:《莎菲女士的日记》
发表于1928年的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从发表的年代来看已经处于“五四”精神的落潮期。然而其话语表述与情绪所指又集中代表了“五四”女性作家对于“五四”精神的文本叙述姿态。从文本中流露出来的“五四”时代苦闷感以及女性体验的性别焦灼歇斯底里式表达的写作姿态上来看,《莎菲女士的日记》被视为“五四”女性文学的终结篇是极其合理的。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流淌的个人情绪表述,已经寓含了作家“五四”时代书写的焦虑。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书写的文本形式,记述了一位离家到都会寻找出路的女子在三个月内发生的爱情纠葛。丁玲把莎菲形象的塑造寓于莎菲对于爱与欲的认知与处理上。莎菲的形象被普遍认为带着很重的叛逆烙印,这种叛逆相当程度表现于她情欲表达的主动、大胆。莎菲是一个有着现代情爱观念,大胆追求真正爱情、渴望灵肉统一的知识女性。她孤高自傲,愤世嫉俗,满怀希望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美好的生活。她希望得到现代爱情观念许诺的平等能够给自己带来身心愉悦的爱情。而她接触到的两位男性——苇弟与凌吉士都不能兑现自己对于爱情的预想。苇弟的愚钝、狭隘、不通风情的关心,是一种基于哀求地位的痴心与善良;外表华丽、风度大方的美男子凌吉士在莎菲一见倾心之后,却暴露出灵魂的俗气、肮脏与丑恶。她向往灵肉一致的爱情,但在与两个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的却是无爱的痛苦与沉溺欲望之后的幻灭与绝望。她被称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她是叛逆者,是因为她不再是传统父权文化规训下温婉含蓄的传统女儿,而是个性乖张、寻找自我欲望满足的走出父门的现代知识女性。但莎菲又是苦闷的,她是“五四精神”落潮后的个人主义实践者与陷落在传统父权文化体系阴影中的现代知识女性。个性解放下个人自由的追求,在20年代末的民族主体建构中显得格格不入。思想得到启蒙的女性实践其主体身份的场域却依然存在着难以打通的父权意识壁垒。她的苦闷是双重的,因此这种苦闷中压抑的声音成为“绝叫”。
表现性爱是文学创作中的敏感领域,在保守、封闭的文化语境中,性爱或沦为色情,或被视为禁区,而二者同样渗透着陈腐的封建主义性别观。相形之下,女性文学中的性爱描写则大多是围绕探讨两性关系特别是女性心理展开的,其中的性别意识较多地剔除了封建因素,体现了两性平等的现代观念。在丁玲笔下,莎菲被塑造为“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莎菲向往悬置于肉体之上的爱情,但是爱情交往中感受不到爱情的她,又留恋于凌吉士的丰仪与红唇柔发、骑士风度,而情愿与其展开欲望纠葛。在这里,丁玲赋予莎菲对于性欲合法性的认可,把觉醒了的女性欲望,直白地表达出来。它让人们认识到女性性欲的合法性,跨越了对女性性表达的阻隔,因而《莎菲女士的日记》被视为女性意识很强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在丁玲的写作中,莎菲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掌握着一向由男性所操控的主动权,瓦解了男权社会的情爱统治。莎菲虽然是传统的激烈反叛者,对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发起冲击,但是,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在她脑海中仍然扎根甚深。她在接受了凌吉士的爱抚之后,表现出的竟是“后悔”——“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这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不出来的”,痛恨自己“甘于堕落”。也就是说,莎菲在自己心中,仍存着“正经女人”的观念。这正是封建贞操观与道德观在她脑海中作祟,她不自觉地便流露出这一已经内化了的集体无意识,这与她追求性自由、性解放是完全背离的。莎菲懊悔着自己在欲望中的徜徉,却又难以走出对于给予她色情想象的凌吉士的迷恋。现代爱情观念与传统父权文化的潜在规训双重加重着莎菲的苦闷:只有欲望没有爱情的感情让莎菲绝望,对于欲望的放纵后对于自我认识的传统性的反思又加重了这种绝望。
“‘五四’后期女性创作尽管依重爱情题材,但总的却是回避肉体的。而现在丁玲的叙述中多了一重眼光,坦然直面肉体.具有对肉体含义的了悟。这种醒觉,或者说让肉体出场,走上前台亮相,这并非完全由于丁玲的独创性和敏感,而与时代密切相关;20年代末‘五四’精神退潮,都会半殖民地化加剧,社会性能量膨胀,肉体浮出。”[5]11320年代末,伴随着都会的殖民地化,视觉文化也随之发展,影像、歌舞娱乐等文化消费形式逐渐兴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前,1927年丁玲曾发表小说《梦珂》,叙述了一位在都市生活中渐渐同化为男士色情对象的女孩子的生活经历。在其中,对于都市的电影、舞厅等消费娱乐场所的描写有所涉及,透露出了丁玲写作语境中的都市化气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凌吉士是一个生活在大都会,享受着现代都市提供给他的种种娱乐消费形式的人。从他对莎菲的态度中来看,莎菲无疑也是他在都会色情文化诱导下的欲望消费品之一。同样生活在大都会中,敏感的莎菲无疑对凌吉士对于自己的态度有所警觉,她看透了他灵魂的肮脏与鄙琐,因而对其是厌弃的态度。但是,受都市色情文化的诱导,凌吉士白嫩的面庞、鲜红的嘴唇、耀人的眼睛同样刺激了莎菲的欲望想象。凌吉士同样成为莎菲在视觉文化诱导下的欲望想象对象。在这里,作者对于莎菲的内心情感、心绪以及性格表达做了极力的张扬。莎菲做为欲望主体审视着凌吉士,而苇弟与凌吉士等男性人物的主导性地位则被降格,淡化成为一种背景和衬托而成为莎菲的审视对象,成为莎菲确认自己主体存在的一种参照物。在莎菲对凌吉士的形体相貌与仪态举止的审视和欣赏过程中,莎菲确认着自己的主体性的两性审美体验。对于凌吉士作为莎菲欲望想象的视觉消费对象的设置,显示了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作的女性主义姿态的书写。
莎菲清醒于自己与凌吉士这种游戏式的“爱情”,因而她是苦闷的:爱与欲分离的无奈,欲与欲的游戏式狂欢后的虚空,这都使得莎菲在自我咄咄的日记式审视中做歇斯底里式的倾述。在这之后掩藏的恰是其对于自我主体地位诉求所遭遇到的挫折的嚎叫与无奈。莎菲是清醒的,因此也是痛苦的。她认清了女性在男性统治的文化中被消费与被审视的客体地位,因此她用自己的方式——与男性周旋、玩弄男性的方式来确认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她不喜欢苇弟却依然乐于与其保持暧昧关系;她迷恋于凌吉士带给她的欲望想象,然而清醒凌吉士对于自己的真实态度,所以“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这位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5]118,以期掌握在这场爱情游戏中的主动权。
在莎菲的叙述中,始终流淌着一种焦灼的情绪。在日记中对于自己的审视,透露出莎菲对于自我认知的敏感,日记中有她对于爱情与身体欲望的思考,更渗透了她对于自己生命主体价值的自主诉求。在她与苇弟与凌吉士的爱情游戏中,她最终感觉到的却是自己对于自己生命浪费的虚空。而她却无力摆脱这种虚空的感觉,能做的却仅仅是搭车南下,“浪费生命的余剩”。文本中流露出来的自始自终都是莎菲对于自己主体价值难以兑现的焦灼与无望。
莎菲作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其时代苦闷体现为五四女儿逃离父门在爱情实践中遭遇挫折之后的精神无着。这种姿态的叙述与五四其他女作家是相似的。但在丁玲的叙述中,女性第一次从女性经验出发如此鲜活地表现出对于性爱自由的合理性诉求。丁玲通过对男女两性人物关系的颠覆性设置(男性成为女性的审美对象、欲望对象、价值评判对象),女性欲望(性自由取向、性与爱相统一的情爱追求)的激越性表达,建构了与“五四”时期寻求与男性结盟以反抗父权文化的女性文本截然不同的话语形态。
“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确立‘我’与‘自己’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关系、女性的称谓与男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6]丁玲通过莎菲形象的设置,把女性对于自我的认知放置到身体欲望的层面,正视女性作为欲望主体的性别经验,而现代的自我认同意识恰恰包含着对于自我身体欲望的肯定与满足。莎菲无疑是有着强烈自我认同感的现代知识女性。正因为莎菲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她对于爱情的表述中一方面呈现出五四女性共同表述的爱情幻灭感,更多的却显示出女性作为性别主体的性别体验的鲜活感。虽然这种鲜活的代价是内心的种种苦痛与焦灼,但恰恰显示出女性作为独立性别群体的丰盈。
[1]庄春梅.对女性情爱问题的经典性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女性情爱观新探[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5):66-69.
[2]鲁迅.伤逝[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78.
[3]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2010(5):206-219.
[4]黄晓娟.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J].江海学刊,2005(3):184-188.
[5]乐砾.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1.